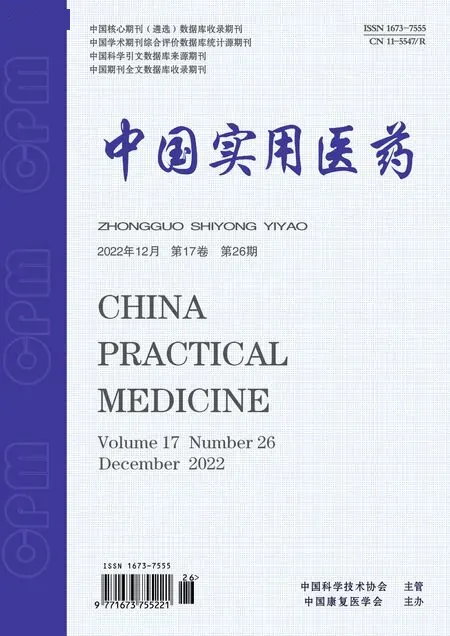氯吡格雷精準用藥對缺血性腦卒中腦動脈重建術后療效的影響
農媛 楊智文 楊吉 秦柱貴 黃日玲
CYP2C19 基因多態性是影響氯吡格雷療效的重要因素,尤其是CYP2C19*2 和CYP2C19*3 功能缺失型(loss of function,LoF)等位基因,其可造成氯吡格雷抵抗、血小板抑制率不足、抗栓治療失敗、血栓事件再發風險高[1,2]。而中國近60%的人群攜帶CYP2C19 LoF 基因[3],因此,有必要對擬用氯吡格雷治療的患者進行CYP2C19 基因多態性檢測,以優化患者的抗血小板治療。目前心血管疾病領域的多個研究顯示,基于CYP2C19 基因檢測結果指導的個體化抗血小板治療,有助于減少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患者冠狀動脈支架置入術后主要血管不良事件的發生,同時不會增加中、重度出血風險[4-6]。但對于缺血性腦卒中(ischemic stroke,IS)腦動脈重建術后患者,氯吡格雷精準用藥治療是否有相似的效果,尚缺乏相關研究支持。本文通過比較氯吡格雷精準用藥與常規用藥治療對缺血性腦卒中腦動脈重建術后患者的療效及安全性,以期為臨床提供相關數據支撐。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20 年1 月~2022 年1 月貴港市人民醫院收治的255 例行腦動脈重建術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臨床資料,研究期間失訪12 例,最終納入243 例。將患者根據是否進行CYP2C19 基因多態性檢測指導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治療分為研究組(87 例,精準用藥)和對照組(156 例,常規用藥)。采用傾向性評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方法控制兩組的混雜因素,通過PSM 成功匹配77 對,研究組和對照組各77 例。見圖1。納入標準:①年齡18~80 歲;②確診為缺血性腦卒中,且經腦血管造影檢查證實存在與患者癥狀相關的大血管(頸內動脈、大腦中動脈、椎動脈及基底動脈)狹窄>70%;③術前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腦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評分<25 分;④患者及家屬知情同意行狹窄動脈支架置入術。排除標準:①溶栓患者;②合并惡性腫瘤疾病患者;③合并必須行抗凝治療的疾病如深靜脈血栓、肺栓塞的患者;④嚴重心、肺、肝、腎功能不全的患者;⑤合并出血性疾病或出血傾向的患者;⑥既往有過腦卒中病史且改良Rankin 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mRS)≥2 分患者;⑦孕期或哺乳期婦女。本研究通過貴港市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批件號:GYLLPJ-20211111-32)。

圖1 研究對象納入及排除流程
1.2 方法
1.2.1 CYP2C19 基因檢測 研究組患者于術前使用真空采血管采集靜脈血2 ml 行CYP2C19 基因型檢測,樣本處理與檢測嚴格按照測序反應通用試劑盒(北京為朔醫學數據科技有限公司)說明書進行,采用原位雜交法,使用Fascan 48E 多通道熒光定量分析儀(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進行CYP2C19 位點*17、*2 及*3 的檢測。根據檢測結果分為正常代謝型(野生型純合子CYP2C19*1/*1),中間代謝型(CYP2C19*1/*2、CYP2C19*1/*3、CYP2C19*2/*17),慢代謝型(CYP2C19*2/*2,CYP2C19*3/*3 和CYP2C19*2/*3) 和快代謝型(CYP2C19 *17/*17 和CYP2C19*1/*17)[7]。
1.2.2 治療方法 研究組中間代謝型患者術后給予氯吡格雷150 mg/次、q.d.+阿司匹林100 mg/次、q.d.治療;慢代謝型患者術后給予替格瑞洛90 mg/次、b.i.d.+阿司匹林100 mg/次、q.d.治療;快代謝型患者術后給予氯吡格雷25 mg/次、q.d.+阿司匹林100 mg/次、q.d.治療;正常代謝型患者及對照組患者則按指南給予氯吡格雷75 mg/次、q.d.+阿司匹林100 mg/次、q.d.治療。所有患者按以上方案用藥3 個月,3 個月后均改為阿司匹林100 mg/次、q.d.長期口服。同時根據患者病情,個體化給予脫水劑、降糖藥、降壓藥及抗生素治療等。
術后隨訪6 個月,隨訪頻率為1 次/個月,采用門診+電話隨訪模式,了解隨訪期間患者有無缺血性腦卒中復發、出血事件、全因死亡及mRS 評分。
1.3 觀察指標及判定標準 分析研究組PSM 后CYP2C19 基因型分布;比較兩組PSM 前后的臨床資料,兩組PSM 后的療效及安全性。①收集兩組患者的臨床資料,包括年齡、性別、民族、既往病史、個人史、基線NIHSS 評分、病灶部位(前循環或后循環)、是否取栓、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入院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水平、有無發熱等。②療效評價指標為缺血性腦卒中復發情況、術后隨訪6 個月時的預后結局。以6 個月時mRS 評分≤2 分為預后結局良好,mRS 評分≥3 分為預后結局不良[8]。③安全性評價指標為隨訪期間的全因死亡及與抗血小板治療相關的出血事件發生情況。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6.0 統計學軟件對研究數據進行統計分析。運用傾向性評分匹配PSM 最鄰近法對兩組間資料進行1∶1 匹配,卡鉗值設定為0.2[9]。PSM 前后,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和四分位數間距[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U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 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研究組PSM 后CYP2C19 基因型分布 PSM 后,研究組中CYP2C19 正常代謝型和中間代謝型占比一致,均為42.9%(33/77),慢代謝型占比為14.3%(11/77),快代謝型占比為0。CYP2C19*2 和CYP2C19*3 攜帶率為57.1%(44/77),CYP2C19*17 攜帶率為1.3%(1/77)。見圖2。

圖2 研究組CYP2C19 基因型分布
2.2 兩組PSM 前后一般臨床資料比較 PSM 前,研究組女性占比為18.4%,高于對照組的9.6%,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年齡、民族、糖尿病史、高血壓病史、腦卒中病史、吸煙史、飲酒史、基線NIHSS 評分、責任血管、取栓情況、入院LDL-C、BMI、發熱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PSM 后,兩組年齡、性別、民族、糖尿病史、高血壓病史、腦卒中病史、吸煙史、飲酒史、基線NIHSS 評分、責任血管、取栓情況、入院LDL-C、BMI、發熱情況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1 兩組PSM 前一般臨床資料比較[n(%),M(P25,P75)]
表2 兩組PSM 后一般臨床資料比較[n(%),M(P25,P75),]

表2 兩組PSM 后一般臨床資料比較[n(%),M(P25,P75),]
注:兩組比較,P>0.05
2.3 兩組PSM 后療效及安全性比較 術后隨訪6 個月,研究組患者復發率為3.9%,低于對照組的15.6%,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研究組患者預后結局良好率、出血事件發生率、全因死亡率均略低于對照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PSM 后療效及安全性比較[n(%)]
3 討論
氯吡格雷是行血管內治療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術后常用的雙聯抗血小板藥之一,但在臨床實踐中,采用標準劑量氯吡格雷治療的患者抗栓效果差異較大,相當一部分患者可出現氯吡格雷低反應或無反應,這種現象被稱為氯吡格雷抵抗,其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下降,血栓形成風險增加;而少數患者則表現為氯吡格雷超反應,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增強,出血風險增加[10,11]。研究顯示[12],亞洲人群出現氯吡格雷抵抗率最高,約為70%,主要影響因素為CYP2C19 基因多態性[13,14]。CYP2C19 為氯吡格雷在體內代謝轉化為具有活性產物的重要的肝酶,其活性狀態影響氯吡格雷活性產物的高低,而CYP2C19 基因有多個等位基因,不同等位基因編碼的CYP2C19 活性各異。其中,CYP2C19*2 和CYP2C19*3 為LoF 等位基因,其可導致CYP2C19 酶活性下降,致氯吡格雷在體內的活性代謝產物減少,抗栓治療效果差,血栓形成風險增加。薈萃分析顯示,在服用氯吡格雷的患者中,攜帶1~2 個CYP2C19 LoF 等位基因的患者發生不良臨床事件的危險性可能會增加55%~76%[15];CYP2C19*17 是功能增強等位基因,其可導致CYP2C19 酶活性增強,氯吡格雷活性代謝產物增加,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增強,出血風險增加[16,17]。
在我國,近60%的人群為CYP2C19*2 和(或)*3攜帶者,1%~3%為CYP2C19*17 基因攜帶者[3,18,19]。2010 年3 月美國FDA 修改的氯吡格雷說明書中黑框警示:CYP2C19 基因型檢測結果應作為醫生調整治療策略的參考,對于CYP2C19 慢代謝型患者,建議考慮調整治療方案或治療策略[7]。而《癥狀性顱內動脈粥樣硬化性狹窄血管內治療中國專家共識2018》推薦對于行血管內治療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術后應用阿司匹林聯合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治療至少90 d,但在應用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治療時需關注藥物抵抗性,可參考相關基因檢測的結果調整抗血小板藥物治療方案[20]。但具體的藥物調整方案尚存爭議,尤其是針對中間代謝型患者。有研究認為,對于中間代謝型患者,CYP2C19酶缺陷可以通過氯吡格雷劑量遞增部分克服,并能產生足夠的抗血小板作用,使風險正常化,而不會增加成本和出血風險[21]。但Wu 等[22]研究顯示,攜帶1 個CYP2C19 LoF 基因的中重度腦血管狹窄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在服用阿司匹林基礎上聯合大劑量氯吡格雷(150 mg/d)較常規劑量氯吡格雷雖然3 個月內發生的血管事件更少,但兩者間的差異卻不顯著。薈萃分析顯示[23],替格瑞洛與大劑量氯吡格雷(150 mg/d)相比,能顯著減少CYP2C19 中間代謝型和慢代謝型行冠狀動脈介入術(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s,PCI)后患者的主要不良心腦血管事件,雖不增加主要出血風險,但卻增加了呼吸困難發生率。
本研究以行腦動脈重建術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為研究對象,分析CYP2C19 基因指導的氯吡格雷個體化抗血小板治療的療效及安全性,其中對基因檢測結果顯示為中間代謝型患者采用雙倍常規劑量氯吡格雷治療,而慢代謝型患者采用替格瑞洛替代治療。結果顯示,本研究中,CYP2C19*2 和CYP2C19*3 攜帶率為57.1%(44/77),CYP2C19*17 攜帶率為1.3%(1/77),與其他研究相似[3],提示氯吡格雷抵抗在臨床中普遍存在。術后隨訪6 個月,研究組患者復發率為3.9%,低于對照組的15.6%,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研究組患者出血事件發生率、全因死亡率均略低于對照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①依據基因型指導的抗血小板治療,可有效識別患者對氯吡格雷的代謝能力,優化抗栓治療方案,減少缺血事件發生,同時不增加出血及死亡風險,是安全有效的;②對于中間代謝型患者,采用增加氯吡格雷劑量治療方案,而慢代謝型患者采用替格瑞洛替代治療是可行的。同時,本研究結果還顯示,研究組患者預后結局良好率略低于對照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原因可能為:①研究組患者的基線NIHSS 評分略高于對照組,神經功能缺損相對較重,故而有可能影響功能預后;②研究組取栓患者占比略高于對照組,而這有可能增加圍手術期并發癥的風險,影響患者術后功能的恢復;③本研究中的缺血性腦卒中復發多為非致殘性卒中復發,故對預后結局影響不明顯。本研究雖為回顧性研究,但通過PSM 有效降低了兩組的混雜偏倚,并達到模擬隨機對照研究的效果,增加了結果的可信度[24],但同時本研究樣本量偏小,且為單中心研究,故結論推廣需進一步多中心大樣本研究數據的支持。
綜上所述,通過進行CYP2C19 基因多態性檢測指導氯吡格雷精準用藥,雖對缺血性腦卒中患者腦動脈重建術后短期預后結局無顯著影響,但可有效降低患者術后缺血性腦卒中復發風險,且不增加出血及死亡風險。故對擬行腦動脈支架置入術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推薦術前行CYP2C19 基因檢測,以識別患者的氯吡格雷代謝能力,并根據檢測結果選擇合適的抗血小板治療方案,使得抗栓治療效果最大化,風險最小化,使患者真正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