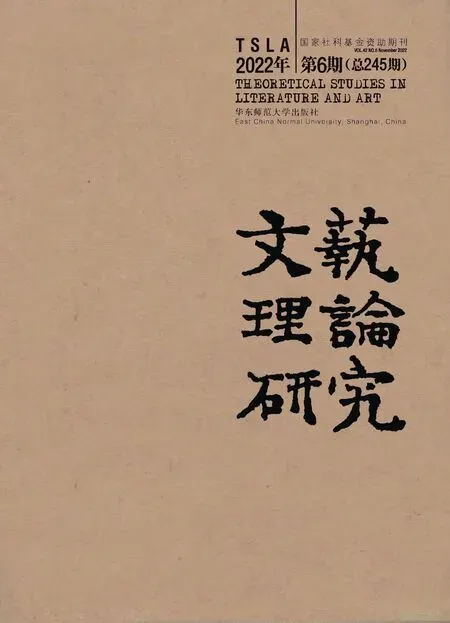論藝術學發源之真相
萬書元
馬采在《從美學到一般藝術學》一文中指出,藝術學(Kunstwissenschaft)①是“由距今一百多年前德國藝術學者菲特萊奠定了其作為一門特殊科學的基礎,后來又由特京瓦[德索]和烏鐵茨賦予其一個特殊科學的體系”(1)。最初“提出藝術學必須獨立成為一門學科的,是菲特萊[費德勒]”(2)。馬采還說,在費德勒之前,“謝林已經于1802—1803年間在耶拿大學的《藝術哲學講演錄》中,對于藝術的組織進行了根本的研究。故藝術體系學的創始人可說是謝林”(10)。在這里,馬采提出了一個藝術學發生和發展的三段論,即19世紀初由謝林創立藝術學體系概念,19世紀后期由費德勒強力倡導和推進,20世紀初再由德索等人建立起一般藝術學學科。這一說法,顯然已經成為當下中國藝術學界普遍采信的權威說法。
其實,馬采的這一說法源自前哈勒大學的教授烏提茲。烏提茲曾于1922年在《一般藝術學概論》一文中提醒藝術學同仁,藝術學能夠發展到當時那么熱火的局面,必須感恩費德勒,因為正是“費德勒開啟了藝術學的新時代”(Utitz,KantStudies14)。早在20世紀初,烏提茲就曾在多個場合表達過類似觀點(Utitz,Leproblèmed’unesciencegénéraledel’art),且影響很大,以致“費德勒是藝術學之父”在藝術學領域成為一句頗為時髦的流行語。
由于德國沒有專設的藝術學學科,且又是藝術學的原產地,德國學者們犯一點“睫在眼前常不見”的迷糊,完全可以理解。②但是,對擁有專設的藝術學學科的中國藝術學界來講,我們的學者們無論是一味因循舊說,還是采取“道為身外更何求”的姿態對這一學科的來龍去脈既往不“究”,這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過去的。
一、溫克爾曼與藝術學之發端
盡管從知識背景角度,我們可以將藝術學的源頭上溯到老普林尼甚至更早,但從這一概念的提出到研究的起步,我們還是必須也只能從溫克爾曼及其《古代藝術史》開始。
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年出生于德國小城斯滕達爾的一個鞋匠世家。這位連上小學都要申請贊助的窮家子弟,本來是與藝術無緣的。但是,在知識淵博、和善慈愛的老師的教育和引導下,溫克爾曼在中學時期就立下了研究希臘藝術的遠大志向。
1738年,出于家庭經濟的原因,溫克爾曼不得不進入哈勒大學神學系。幸運的是,哈勒大學是德國最早倡導學術自由和教學自由的大學。而且,就在溫克爾曼進入大學的前一年,被伏爾泰稱為“德國學者的王冠”(Disselkamp and Testa,eds.6)的鮑姆嘉通剛剛擔任了哈勒大學的編外教授。雖然鮑姆嘉通于1739年底離開哈勒大學另謀高就,溫克爾曼卻正好逮住機會修完這位年輕教授開設的三門課程,即古代哲學、形而上學的邏輯與歷史及哲學百科。應該說,與鮑姆嘉通的相遇,既是溫克爾曼得以跨專業滿足自己的學術志趣的一次難得的契機,也是他學術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雖然在此期間,鮑姆嘉通的《美學》第一卷還沒有出版,但是他1735年出版的《哲學沉思錄》已經給他帶來了不小的學術聲譽。一個年僅21歲的青年人,在一篇碩士學位論文中提出要建立一個與倫理學和邏輯學并列的新學科——美學學科,這種勇氣和膽略實在是不同凡響。正因為如此,這個曾經在孤兒院接受教育、與溫克爾曼有著同樣坎坷的經歷的學術新星一登上大學講壇,就吸引了青年學子們崇拜的目光。
許多學者往往更關注鮑姆嘉通后來出版的《美學》(1—2卷)(1750—1758年)。該書在學術上確有開創性貢獻,因為鮑姆嘉通的整個美學思想體系都體現在其中了。但他關于美學和美學學科的原創性觀點,卻是首先在《哲學沉思錄》中提出的。不僅如此,鮑姆嘉通還在這部書中,引發了一個在賀拉斯《詩藝》中濫觴的古老的議題,即詩與畫的關系這個元美學和元藝術學問題。從詩與畫的關系,又引申出聽覺與視覺孰優孰劣的問題。因此,鮑姆嘉通不僅在美學學科上有開創之功,在藝術批評和藝術學研究方面,也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至少是前承法國學者杜波(Jean-Baptiste Du Bos)的《對于詩歌和繪畫的批評思考》(Réflexionscritiquessurlapoesieetsurlapeinture,1719年),后啟溫克爾曼的《古代藝術史》和赫爾德的《批評之林》。所以赫爾德說:“性情平和的鮑姆嘉通以其罕見的近乎可怕的精確性,在并非刻意為之且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不僅成為一個嚴苛的批評流派之父,而且也成為德國美學和藝術之父。”(Herder,BriefezuBef?rderungderHumanit?t149-150)
赫爾德的評論總體是到位的。但他說鮑姆嘉通是“并非刻意為之且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Herder,BriefezuBef?rderungderHumanit?t149-150),卻并不準確。因為,鮑姆嘉通發明美學或“感性學”這一概念并創建這一學科,既非心血來潮,也非誤打誤撞,確實是“刻意為之”。當然,歐洲學術經驗的積累和知識生產方式的改變,時代的科學精神的召喚,哲學家沃爾夫等人的引領,乃至由歐洲近代知識危機引發的學科分類需求的驅動,這些外部因素,都可成為鮑姆嘉通命名和建構美學學科的基礎條件。但是,鮑姆嘉通內在的創新意識卻是至為關鍵的因素。因為,鮑姆嘉通是以學科補位的思路,通過在倫理學和邏輯學之間的狹小縫隙中打楔的方式,為美學找到合適的位置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行為本身也具有頗為微妙的美學意義。因為鮑姆嘉通是按照知、情、意這樣一個知識范疇序列來對應邏輯學、美學和倫理學的,這里所包含的邏輯上的嚴密性、詞與物之間的對稱性、感覺上的和諧性,使鮑姆嘉通的學術思維具備了濃厚的形式感,也可以說是對他的“美學是優美地思考的藝術”(ars pulchre cogitandi)的定義的一個注腳(Baumgarten3)。
鮑姆嘉通在哈勒大學開設的哲學百科全書(philosophische Enzyklop?die)課程,對我們了解鮑姆嘉通,同時評估溫克爾曼從鮑姆嘉通那里受到的啟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本書,除了哲學類詞條如倫理學、心理學、生理學、美學、文獻學、類型學、詞匯學、音韻學等之外,還包含大量自然科學詞條,比如數學、氣象學、植物學等。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更直觀地看出這位二十歲出頭的青年教授在知識的博洽、學術的敏感與學科的預見性方面,已經達到了怎樣的高度。
溫克爾曼聽了鮑姆嘉通的三門課,最受益的課程很可能就是這門哲學百科。據說,他在十年之后,即1748年,還曾利用外出旅行的間隙,專門探訪了鮑姆嘉通(Disselkamp and Testa,eds.7),說明這個老師——他的學術上的重要領路人,在他的心目中是有相當的分量的。
由于哈勒大學選課自由,圖書館藏書豐富,再加上溫克爾曼勤學好思,等到大學畢業時,溫克爾曼在語言、歷史、文學和藝術甚至在圖書版本學和古物鑒定學方面已經打下了非常扎實的基礎。只是由于家庭的原因,大學畢業后,他還是不能直接從事自己向往已久的藝術研究。直到1848年,他應邀到納特尼茨擔任著名歷史學家布瑙(Bünau)伯爵的圖書管理員,才真正能夠定下心來,一方面大量地閱讀和寫作,一方面頻繁地到文物市場鑒賞古董。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1754年,溫克爾曼為了獲得到羅馬從事古代藝術研究的機會而被迫皈依天主教。這一舉動雖然在當時和后來飽受抨擊(包括尼采激烈的批評),但是,對于一個出身貧苦又想從事藝術這項貴而雅的研究工作的年輕人來說,這本來就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事實證明也是一個明智而正確的選擇。因為他終于在1755年到達羅馬,實現了自己的夢想,并且在1764年完成了他的皇皇巨著《古代藝術史》。
說溫克爾曼的《古代藝術史》和鮑姆嘉通的《哲學沉思錄》一樣,從理念的意義上創立了一個學科——藝術史學科,估計不會有任何人提出異議。因為《古代藝術史》和鮑姆嘉通后來出版的《美學》一樣,也是這個學科的開山之作。歌德說:“溫克爾曼就像哥倫布一樣,他不是發現新世界,而是預示了一個新世界的即將到來。”(溫克爾曼244)黑格爾贊許溫克爾曼“在藝術領域里替心靈發見了一種新的機能和新的研究方法”(黑格爾78—79)。他們顯然都是贊許溫克爾曼在新的時代,在人文科學領域,為藝術史開辟了一個新世界,因此將他與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相提并論。但是,被很多中外學者視為藝術學的開山祖師的謝林卻另有一套說法。他認為溫克爾曼不只是開辟了藝術史這個新世界,他其實還是“一切藝術學之父”(Schelling,PhilosophiederKunst557)。
顯然,這里的“一切”,至少包含了四個領域:第一,當然是藝術史;第二,古典考古學或藝術考古學;第三,應該是指美學,因為溫克爾曼的《古代藝術史》一直也是西方美學史研究繞不過去的一部重要著作,但是,有鮑姆嘉通在前,說溫克爾曼是美學之父,并不合適;第四,只能是藝術學了。
我們不能不佩服,作為一位著名的哲學家,謝林竟然能夠如此細心。因為溫克爾曼確實和他的老師鮑姆嘉通一樣,充當了一個學科概念的發明人。③在《古代藝術史》中,他第一次運用了“Kunstwissenschaft”這個概念。
必須指出的是,國內美術史界通常把“Kunstwissenschaft”翻譯為美術學,雖然這種譯法并非完全站不住腳,但極易產生誤會。因為在20世紀之前,美術概念和藝術概念的內涵大體是一致的。在狄德羅和達朗貝爾主編的《百科全書》(Encyclopedie,1751—1765年)的“序言”中,達朗貝爾明確界定,美術包含繪畫、雕塑、建筑、詩歌和音樂等形式;而且還與“純文學”(belles-lettres)聯系在一起。在法國,“純文學”是指文學、修辭、詩歌藝術的總體(d’Alembert35,39)。這就意味著,在當年那個特定語境下的美術學,其研究范圍不僅可以等同于,甚至有可能大于當今的藝術學,與當今的美術學不可同日而語。因為當今的美術學,只限于造型藝術。
在《古代藝術史》第四章第二節“著衣人像的表現形式”的小結“本研究對藝術創作和藝術學的意義”(Die Bedeutung dieser Betrachtung für Kunstschaffen und Kunstwissenschaft)這個標題中,“藝術學”首次在這里赫然現身。
溫克爾曼這段只有區區1 430個字符的文字,只是“著衣人像的表現形式”這個部分的小結。他并沒有對藝術學概念作任何闡釋,只是強調三點:第一,在著衣人物雕塑的研究方面,藝術專家比藝術家更有用武之地。第二,衣服與裸體的關系,猶之乎思想的表達形式與思想本身的關系。找到思想比找到其表達形式更容易;描繪衣服比描繪裸體更難。但技藝高超的希臘藝術家更愿意創作姿態優雅的著衣雕塑(說明希臘雕塑家藝高人膽大)。第三,裸體雕塑同質化水平較高,而著衣雕塑則注重個性化和差異性,較少同質性,因而屬于藝術領域中的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方面(Winckelmann179)。
如果我們只拘泥于“藝術學”概念出現的這個局部,我們就只能從溫克爾曼的這一小段文字中尋找有關藝術學的微言大義。雖然并非一無所獲,但是說服力多少有些不足。
如果我們對《古代藝術史》這部著作作一個全面的考察,就很容易為這個看似突兀的“藝術學”標簽找到其生成邏輯和學理意涵。
溫克爾曼在《古代藝術史》序言中曾經表白:
我所寫的古代藝術史,不僅僅是詮釋藝術的年代更迭和藝術的變化,我是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在希臘語意義上使用“Geschichte”(歷史)這個詞,我是要作一個系統的嘗試[……]不過,不管從哪個方面看,挖掘出藝術的本質都是我最突出的目標。(Winckelmann11)

在溫克爾曼之前,撰寫過藝術史并有可能對溫克爾曼產生影響的有兩位。一位是意大利的瓦薩利,算是溫克爾曼的外國老前輩;另一位是德國本土畫家兼學者約阿希姆·馮·桑德拉特(Joachim von Sandrart),他在1679出版的《德國建筑、雕塑和繪畫藝術學派》中,首次對多國藝術家及其藝術風格進行了詳細的記錄與評述,這也是第一部德語藝術史。瓦薩利的特點是把畫家置于時代的大背景下來為藝術家立傳;桑德拉特采用了類似的寫法,但大大突破了標題所規定的國家界限。因此,這兩人的藝術史正好就是溫克爾曼必欲打破的“歷史變遷與藝術變化”的敘述模式。
溫克爾曼的《古代藝術史》也可以說是一部“名不符實”或“實過于言”的著作,因為它并非嚴格意義上的藝術史,而是藝術學理論的濫觴之作。它沒有為任何一位藝術家立傳,也沒有關于任何作品的線性的年代學考訂。誠如菲利皮所說:“溫克爾曼通過流暢而空靈的文字和他錘煉出的一套敘事方式,嘗試了范式轉變,力求使其文本也能達到藝術作品的那種完善的境界,從而使古代繪畫詩學(Ekphrasis,也譯作“藝格賦詞”)煥發出新的生命。”(Filippi233)
不過,溫克爾曼的范式的改變,還遠遠不只是語言上的和敘述上的改變這么簡單。可以說,溫克爾曼是在揭示藝術的本質這一核心目標下,以一整套審美評價體系(諸如高貴的單純與靜穆的偉大)為參照標準,在一種系統性的、整體性的、立體的研究框架(諸如對藝術的生物學生長模式的詮釋與藝術盛衰規律的構擬)中,來完成對古代藝術的理論的建構,而非客觀事實的記錄的。
盡管作為一種原創性的、開拓性的嘗試,溫克爾曼的藝術學研究并不完滿。但是,他畢竟播下了藝術學的種子,確立了藝術學研究的基本原則,且最早嘗試了藝術學的理性與感性兼容的系統化研究路徑。這種創始之功,我們是絕不應該忽視或者遺忘的。
溫克爾曼本來還可以為藝術學理論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只因他不幸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邂逅了他的貪婪而狠毒的舊鄰居④,他的生命的刻度就永遠地停在了51歲這個位置,實在令人唏噓感嘆。
二、赫爾德的感官分類學與藝術學研究范式的革命
約翰·哥特弗雷德·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年)是德國近代史上一位頗有影響的重要人物,既是哲學家,又是神學家,同時是語言學家、文學家、美學家,還是藝術學家。在藝術學的創始階段,赫爾德扮演了承前啟后的關鍵角色——前承溫克爾曼,后啟謝林,是藝術學最得力的推動者。
赫爾德在《批評之林》第三卷中,在談到錢幣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時,間接引用了德國古錢幣學學者和美學家克洛茲的一段話:
[……]有些人看到錢幣時首先想到的是炫耀其博學,并且這種傾向會與他們稱之為品味的東西交織在一起;有些人一看到錢幣立刻就明白其藝術技法,并且(以現在人們稱之為“kunstwissenschaft”或藝術品位的方式)對錢幣的圖案加以品評,如果他們具有活躍的精神,還會為上面的藝術形象感到愉悅;最后,還有些人首先看到的是美,而并不是要做學問,也無意創造藝術名作。(Herder,KritischeW?lder.Bd.331)
赫爾德引用的這段話,除了隱晦地表達了他對克洛茲的硬幣美學的不屑之外,也透露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即,藝術學這個概念,自從1764年由溫克爾曼提出,到赫爾德出版《批評之林》的1769年,在這四五年間,已經在學術界傳播開來了。因為赫爾德借克洛茲之口,不僅很隨意,甚至有點心不在焉地把“藝術學”和“藝術品味”等量齊觀,而且還用了“現在人們稱之為”的句式,說明“藝術學”在當時的德國,至少在學術界,已經成為比較時髦的概念了。無獨有偶,被耶魯大學托馬斯·克里斯滕森(Thomas Christensen)譽為“站在歷史的重要關頭”(Koch and Sulzer5)的哲學學者蘇爾壽(Johann Georg Sulzer)在他于1771—1774年出版的兩卷本《美術百科全書》中,兩次提到藝術學一詞,兩次也都是以很隨意的、順帶的方式提出來的。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赫爾德只有一次正面提及藝術學,此后再也沒有提及這一概念。那么,赫爾德只是與藝術學發生了一次不期然而然的“偶遇”嗎?
顯然不是。赫爾德雖然沒有再提“Kunstwissenschaft”一詞,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忽視或者忘記了藝術學。事實上,他的《批評之林》和《論雕塑》從來就沒有離開過藝術學這一中心。只是就赫爾德的偏好來說,他更喜歡用“美學”來指代“藝術學”。⑤(在赫爾德的術語系統里,“藝術學”“藝術理論”和“美學”是具有同等意涵且是可以替換的。)如果我們能夠建構一種歷史的同一感,還原到赫爾德時代特定的語境,是不難理解赫爾德的這種選擇的。因為,無論從起源還是發展的角度來看,藝術學與美學這兩個學科注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解難分的。弗洛里希(Fr?hlich)直到1831年,還在維爾茨堡大學開設“作為藝術學的美學”的課程,藝術學的旗手德索在1906年左右出版的著作以及雜志仍然都取名為《美學與一般藝術學》,而美學家福克爾特在1924年—1926年出版的《美學體系》中則宣稱,藝術學通常被視為“先驗美學的出發點和定位點”(Volkelt50)。
當然,赫爾德所說的美學,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哲學美學,而是具有特定內涵的、“自下而上”(von unten nach oben)的美學。赫爾德的意圖很明顯,就是明“修”美學之“棧道”,暗度“藝術學”之“陳倉”。這里的“修”不僅帶有對鮑姆嘉通的美學理論的“繼承”和“拓展”之意,更有對他的美學進行“修正”和“重新定位”之意。
赫爾德對鮑姆嘉通創建美學這一學科的功績一直是給予充分肯定的。他還專門寫了《永遠感念鮑姆嘉通》一文來向鮑姆嘉通致敬。但是,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鮑姆嘉通美學理論中存在的問題。赫爾德指出,鮑姆嘉通的美學,首先是名實不符,表里不一。他說:鮑姆嘉通的美學“不是它的名稱所昭示的那樣,是美學——感覺科學的美學。它汲取的原始資源根本不是希臘的情感、美的直覺和內在情感,而是思辨”(Herder,SelectedWritings41)。也就是說,在赫爾德看來,鮑姆嘉通雖然聲稱他的美學是“感性學”或“感性知識的科學”,實際上仍然還是一種忽視“情感”、忽視藝術直覺和“內在情感”的“思辨”的科學。因為,“在鮑姆嘉通這里,我們經常看到一些主要命題從高處降落下來,然后我們還必須為它們在地上找到(安放)空間”(Herder,SelectedWritings133)!這種“自上而下”的美學路徑,顯然違背了鮑姆嘉通的初衷。所以,赫爾德要通過他的“更精確且更實用的定義”,即“自下而上”的美學,“追隨希臘風格”的自然(感性)美學(其實就是追隨溫克爾曼的那種直抵希臘藝術的核心的美學),來“拯救”鮑姆嘉通正處在迷失之中的美學,“剝除這一概念的虛假功能并摘下它名不副實的桂冠”(133)。
赫爾德不僅對鮑姆嘉通的美學的名與實錯位的問題進行了矯正,對他同時代的幾位重要藝術理論家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比如,《論品味文集》(EssayonTaste)的作者、蘇格蘭神學家杰拉德(A.Gerard),《美術與科學理論》(Theoriedersch?nenKünsteundWissenschaften)和《美術與文學理論》(TheoryoftheBeauxArtsandBellesLettres)的作者里德爾(F.J.Riedel)。赫爾德認為前者的著作沒有系統性,算不上藝術理論(Herder,SelectedWritings278);后者的著作只能證明作者對藝術的本質一無所知(261)。除了上述兩人之外,克洛茲、萊辛和休謨等人都處在赫爾德抨擊的范圍之內,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赫爾德的質疑或批評(277)。總而言之,從鮑姆嘉通到赫爾德時代的理論家們,沒有任何人能夠提出令赫爾德滿意的、真正的藝術理論,他們的理論與赫爾德的“自下而上”的美學理念都存在很大的距離。
赫爾德認為,鮑姆嘉通在對美學的定位上就出了問題,連赫爾德本人早先也曾經被嚴重誤導。由于鮑姆嘉通將感性認知定位于一種較低的心靈能力(Herder,SelectedWritings185),美學也就相應地被定位于一個次要的、輔助性的位置。赫爾德認為,美學如果只是充當邏輯學的輔助學科的角色,那就意味著它背叛了感性,轉而去追求“更高”的觀念能力,這不僅以貶低的方式為美學自身建構了一個不適當的模型(Herder,Sculpture9),而且使它陷入了一種荒誕的境遇之中。赫爾德尖銳地指出,這種情形完全是由鮑姆嘉通內心的矛盾造成的:鮑姆嘉通本來有一個理想,就是讓自己的心中同時容納兩個靈魂——詩人(感性)的靈魂和邏輯學家(理性)的靈魂,最終實際上是后者驅逐了前者(Herder,SelectedWritings23-24)。但是,理性主義和邏輯學不可能為以感性為基礎的美學提供合適的研究范式。聲稱“我感覺,故我在”(Herder,Sculpture9)的赫爾德必須首先讓美學回歸感性的軌道,在此前提下,再為美學在哲學的學術殿堂掙得一個席位。所以,赫爾德宣稱,美學“是最嚴謹的哲學,是關于人類心靈與自然之模仿的極具理論價值和意義的哲學;它甚至是人類學的一部分,人類知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Herder,SelectedWritings191)!
為美學正名且重新定位只是赫爾德要做的第一階段的工作,或可叫作理論的清障工作。建立一套“自下而上”的美學或藝術學研究的范式,才是赫爾德工作的重點之所在。
赫爾德既然已經明確將美學定位于“最嚴謹的哲學”,他就可以毫不猶豫地“把感受美和創造美的產品的靈魂力量作為研究對象”,將“最嚴謹的哲學”進一步發展成為“一種偉大的哲學,一種感官感知理論”,憑借“一種想象和詩的邏輯”,使藝術學研究者成為“機智而有洞察力的感官判斷和記憶的研究者,美的分析者”,并創造一種美學或“品味(taste)哲學”(Herder,SelectedWritings189)。這樣一來,一種既能確保“我感覺,故我在”的感覺基礎,又能確保“機智而有洞察力”的理論品質的新美學就通過《論雕塑》等著作呈現在世人面前了。
赫爾德的這種“自下而上”的新美學最大的成功,在于他建構了一套由“感官生理學”和感性(藝術)分類學嚴格配對的、具有高度原創性的系統的藝術學研究范式。
盡管赫爾德在不同語境下所調用的藝術類型和感官類型略有出入,但是,歸結起來,他選取的主要還是詩歌、繪畫、雕塑和音樂這四大門類,分別對應人類的四種感官,即不分器官的感覺、對應眼睛的視覺、對應手和身體的觸覺以及對應耳朵的聽覺。赫爾德將這四種藝術類型按序歸并到四種生理感官中之后,對這些感官不同的性質和功能進行了深入的剖析。
赫爾德指出,這四種藝術類型各有自己的呈現方式。繪畫藝術在虛擬空間中呈現,只提供由平面、顏色、輪廓和光影合成的不完整的二維世界圖像——可以產生三維幻覺的二維世界圖像;雕塑藝術是在實體空間中以深度和圓度呈現或通過實體空間展開的;音樂是在時間中展開的充滿活力的連續的藝術;詩歌是融合了多種其他藝術形式的綜合性藝術,它并不特別偏好任何特定感官,因為它是與心靈對話而非與任何一種感官對話。盡管在赫爾德看來,所有感官都是靈魂的表現和感覺方式,但是四種感官對藝術的感受方式卻各不相同。觸覺是我們利用我們的身體和肢體感知空間、體量和深度的最基本的和最高級的感官;“聽覺是人類感知外部世界的中間感官;感覺只是在自身之中并通過感官來感知一切;視覺將我們遠遠拋出自己之外;聽覺居于視覺和感覺的中間,起著某種程度的溝通作用”(Herder,PhilosophicalWritings108)。
赫爾德也從審美效用角度對四種藝術類型作了界定。他說,雕塑是真,而繪畫是夢。前者是整體呈現,后者是敘事魔術。“我跪在雕塑前,它可以擁抱我,可以成為我的朋友和伴侶:它存在,就在那里。最美的繪畫無非是一個瑰麗的故事,一個夢的夢。”(Herder,Sculpture45)
詩歌和音樂是密不可分的姐妹。因為耳朵最接近靈魂(Herder,SelectedWritings256),所以音樂是一種和諧而又震撼心靈的獨特語言(238),是人類靈魂迷宮的神秘回聲(246),而詩則是發自個體靈魂最深處的古老的、有魅力的形式(117)。
顯然,赫爾德受狄德羅的影響,對觸覺(雕塑)的重要性作了矯枉過正的強調。在赫爾德之前,感官哲學一直是由視覺主導的哲學。視覺似乎始終被視為最重要、最精致的感知方式,在理性時代尤其如此。艾迪生(Joseph Addison)就是視覺優先主義的典型代表,他曾經在《旁觀者》(1712年)一書中將視覺描述為“所有感官中最完美和最令人愉悅的”(Addison2)。必須承認,視覺確實能夠以最直接和客觀的方式傳達外部世界的信息。就連赫爾德也承認,視覺是“最具哲理性的感官”,它的對象是最清晰的。但赫爾德顯然有一種用觸覺取代視覺的強烈的“矯正性”動機,而不僅僅是不滿于他那個時代占主導地位的視覺主義。赫爾德聲稱,視覺是一種膚淺而潦草的感官,缺乏必要的穿透力(Herder,SelectedWritings200),通常是匆遽地掃過對象的表面就滑過去了;視覺使我們變成了一個與周圍的物體沒有任何接觸的冷漠的觀察者。但是,觸覺卻不同。觸覺,也只有觸覺能夠給我們提供空間、廣延、體量和深度這樣的概念;只有觸覺,才能使我們通過我們的手,在三維空間中感知物體的存在,并且在上述概念所包含的全部意義上真正地把握這個世界。
赫爾德一再強調,真正的形式的美和身體的美,其實并不是來自視覺上的美的概念,而是來自觸覺上的美的概念;因此,每一種美最初都必須到觸覺上尋找源頭。眼睛既不是美的來源,也不是它們的評判者。連那些描繪美的美學語匯,也都是從觸覺衍生出來的,比如粗糙、溫柔、柔軟、細嫩、飽滿、動感等,不勝枚舉(Herder,SelectedWritings210)。視覺不是創造,而是破壞了雕塑的美,它把雕塑變成了平面和表面,把雕塑優美的豐滿、深度和體積轉化為鏡面游戲(Herder,Sculpture41)。相反,觸覺是直接以肉身(體量)的方式在場的,而且總是從容的、富有穿透力的,也是具有親和力的。由觸覺獲得的美構成了我們對世界的體驗的一個主要部分(Herder,Sculpture14-15)。觸覺也是人類最早發展出來的、最可靠、最真實的感官(Herder,SelectedWritings228)。因此,赫爾德主張要在審美領域恢復觸覺的古老權利。
杰森·蓋格爾(Jason Gaiger)曾經提到,赫爾德在東普魯士柯尼斯堡大學學習期間,對當時的兩位大思想家康德和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都很崇拜。但是兩位老師的觀念相左。哈曼是一位虔誠的宗教思想家,對18世紀流行一時的理性主義充滿敵意,推崇感官體驗,他認為世界、自然和歷史的外在輝煌都是神的活生生的表現(Herder,SelectedWritings3)。康德卻向赫爾德灌輸了一種強烈的哲學使命感,傳授他分析的方法,告誡他,只有在獲得可靠和可證實的證據的基礎上,才能采用分析方法,將特殊的理論上升到一般原理,同時鼓勵他相信人類理性思考和自決的能力。赫爾德對兩位大師的觀點采取了兼收并蓄的策略。同樣,赫爾德對德國的萊布尼茨和沃爾夫的經驗主義和英國的洛克、康迪拉克及法國的狄德羅等人所追求的感覺主義也都比較欣賞,也試圖把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整合起來,并且盡可能克服兩個學派各自的不足(7)。赫爾德還曾作過這樣的表白:“一個只想擁有一顆腦袋(理性)的人與一個只想擁有一顆心臟(感性)的人一樣,都是怪物;完整、健康的人應該二者兼而有之。他既有腦袋也有心臟,且各安其位,心不在腦中,腦也不在心里,這正是人所以成其為人的原因。”(3)
令人遺憾的是,這樣一種態度,在赫爾德對待視覺和觸覺的問題上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盡管我們承認,赫爾德有關觸覺的論述對我們研究審美感知極具啟示意義,但是,赫爾德將兩種感知器官及其感知效果完全對立起來,不免牽強,也不免偏頗。他把視覺和觸覺按照清晰/曖昧、冰冷/溫煦、哲理性/身體性、即時顯現/延時感知、提供最安全最可靠的外部知識/提供含混但更為內在的知識這樣兩極對立的模式進行抑此揚彼的并置,完全排除了兩種感官互動合作的可能性。甚至,為了凸顯觸覺的重要性,他對他曾經說過的雕塑可以按照環形線路多視角移動觀察的觀點進行了如下修正:“當雕塑的鑒賞者從一個觀察點轉移到另一個點的時候,他的眼睛變成了手,光線變成了手指,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具備了比他的手或光線還要精細的靈魂之手。他試圖用他的靈魂去抓住從藝術家手臂中和靈魂里躍升出來的形象。現在他抓住了!”(Herder,Sculpture41)
很顯然,在觸覺優先的慣性的裹挾下,赫爾德已經有些失控了。明明是視覺,在赫爾德這里,不用任何魔法,就輕輕松松地被轉化為觸覺了,連他自己熱衷的所謂“感官共同體”(sensorium commune)(Rousseau and Herder110),這個時候也突然消失無蹤了。
從總體上說,赫爾德和溫克爾曼一樣,他的研究也帶有明顯的“溢出”癥候——有點“實過于言”。他的書雖然名為《論雕塑》,實際上研究了包括雕塑在內的幾乎所有的藝術形態,比如繪畫、雕塑、音樂、詩(史詩、抒情詩、寓言等)、舞蹈、建筑等。與此同時,他布局了一套囊括了所有的感官類型、堪稱全息感官生理學的系統:視覺(眼睛)、聽覺(耳朵)、觸覺(手與身體)、味覺(舌頭),嗅覺(鼻子),還有感覺。在藝術本體的肉身性重建、藝術的呈現和感知的生理與心理的構擬方面,赫爾德的研究都堪稱空前的創舉。這樣一種既立足于藝術的感官性、個別性和具體性,又體現理論建構的系列性、整體性和宏觀性的研究路數,⑥對“自下而上”的“非思辨的”藝術學理論的信奉者來說,無疑具有教科書般的指導意義。這也是加拿大麥克吉爾大學哲學與政治學教授查爾斯·泰勒稱贊赫爾德是極富創新精神的思想家中的稀有物種之一(Heinz,hrsg.7)的重要原因。
三、從榮格-斯蒂林到謝林:一般藝術學理論的系統創構及其思辨研究模式的確立
如果說溫克爾曼對作為特殊藝術學的藝術學這一概念有首創之功,那么,對一般藝術學(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Jung-Stilling93)有首創之功的就是榮格-斯蒂林(Johann Heinrich Jung-Stilling,1740—1817年)了。
榮格-斯蒂林是海德堡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他在177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論稿》一書中,首創“一般藝術學”概念。有意思的是,德國美學家齊美爾曼遲至1862年才在一篇文章中提及這一概念,耶拿大學哲學系教授蘭伯特·維辛竟然誤認為自己找到了這一概念的發明人(Wiesing204)。
今天的人,可能很難理解為何一個經濟學教授會對藝術學產生興趣。其實,在19世紀以前,大學的科(院)系和今天的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古典時期的“七藝”或曰“三科”(文法、修辭、辯證法)、“四學”(算數、幾何、天文、音樂)這種大學科思路一直延續到了中世紀。比如,古代的哲學,就包含天文學、數學、心理學、生物學等一大批學科(柏林3)。隨著大學的產生,當“faculties”的觀念和體制引入大學之后,到17—18世紀,學科門類開始出現了細分的趨勢,但仍然是粗線條的,系科之間的界限依然是相對模糊的。所以,一些博學多才之士很樂意也有能力跨越多個學科,而學校的學科制度也樂其所哉。伯克就曾提到,“化學家”利巴菲烏斯(Andreas Libavius,1540—1616年)在耶拿大學教授歷史和詩歌,而“政治科學家”康令(Hermann Conring)則在黑爾姆施泰特大學教授醫學;荷蘭自然哲學家布爾哈夫(Herman Boerhaave,1668—1738年)在萊頓大學同時兼任了醫學、植物學和化學等學科教授的職位(Burke91)。如此看來,即使斯蒂林僅僅是憑興趣跨學科來研究藝術學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單純從藝術學或經濟學各自的學科角度看,它們都難免與對方的學科交叉。藝術經濟學、藝術市場學出現在彼此的學科中都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更何況,在后哥倫布時代,隨著荷蘭登上歐洲政治和經濟的霸主寶座,到17世紀,阿姆斯特丹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藝術拍賣中心。18世紀中葉前后,隨著荷蘭的衰落和大英帝國的崛起,藝術拍賣市場一方面將重心向倫敦偏移,一方面也在歐洲的一些重要城市全面鋪開。在溫克爾曼和鮑姆嘉通活躍的年代,歐洲許多城市的古物展覽和拍賣活動已經相當普遍了。到榮格-斯蒂林撰寫《政治經濟學原理論稿》的時候,藝術品已經成為一項新的重要的商品,藝術拍賣活動也就成為經濟學家不能不關注的一項重要的經濟活動了。
所以,《政治經濟學原理論稿》的第二編“民商學基礎理論”總共三個章節,榮格-斯蒂林就用了兩章來談藝術問題:第二章討論“一般藝術經濟學”,第三章討論“一般藝術學”。
榮格-斯蒂林一方面把藝術經濟學和一般藝術學并列,一方面又把藝術學置于藝術經濟學的子類。他顯然交叉采用了開放和封閉兩種視角(這難免讓人對他的分類邏輯的嚴密性感到擔憂)。在其理論體系中,藝術經濟學由藝術學和作坊手工藝兩大部類組成。其中,藝術學主要解決如何規劃具有經濟價值的(藝術)產品的問題;作坊手工藝主要涉及產品生產的環境及其產品的品質問題(Jung-Stilling93)。這里的藝術學,當它與作坊手工藝并列,變成一個寬口徑的大類的時候,就發揮一般藝術學的功能了。作為單列的大門類的一般藝術學同樣分為兩大部類:美術與工匠的歷史(Geschichte der Künste und Handwerker)、工藝品(Kunstgewerbe)。前者主要追溯船、帆、漿這類傳統交通工具的起源,烹調、服裝和裝飾的起源,繪畫和雕塑和建筑的起源,紙、筆、墨、書法和書籍印刷的起源,還有現代交通工具的起源以及各個時期的技術改進與創新(這就是他把“工匠”放進標題的原因)等,可以說是一種融入了技術史的開放性的藝術史研究。后者其實是建構了一個實用藝術的分類學體系,包括三大序列:一是來自人類、動植物與礦物三界的工藝品原料序列;二是利用這些原料制作的工藝品序列;三是加工這些工藝品的機械和小工具序列。如此開闊的視野,如此混雜的類型,還真配得上他所采用的“一般藝術學”的概念。
榮格-斯蒂林雖然始終圍繞著經濟在談藝術,但是,他對藝術或者說藝術學還真可以說是別具慧心。他說:“藝術的目的是要使產品具有獨特性,而且也能滿足市場的口味。因此,藝術的本質首先在于產品的獨特性,其次在于市場對藝術的這種需求。”(Jung-Stilling103)從供求關系視角來要求藝術的品質,這是經濟學家特有的視角。
榮格-斯蒂林指出,如果單是從貿易上來比較,手工藝品和藝術品之間的差異可以忽略不計。如果從創作來講,藝術品(純藝術)的價值是遠高于手工藝的。因此,藝術家希望獲得比匠人更高的特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整個手工藝鏈,無論是付出最少勞動的小件作品,還是付出最多心血的大件作品,其中多多少少包含著一些奧妙的技巧和艱辛的制作,它們都應被視為藝術;工匠的作品也應該和藝術家的作品一樣,被稱為藝術品。如果所有的工匠都能獲得更多的藝術(家)的尊嚴,這對藝術產業也是有益的(Jung-Stilling111)。這種觀點,已經超越了一般經濟學家的知識范圍,顯示了作者寬廣的胸襟和睿智的識見。
當然,一般藝術學理論到底應該包含哪些內涵,這不是,也不應該是由一位經濟學家來回答的。榮格-斯蒂林能夠提出“一般藝術學”的概念,且大體與藝術學理論的研究范圍吻合,這已經相當不容易了。
榮格-斯蒂林之后,除了前面提到過的蘇爾壽之外,我們尚未發現還有其他學者對“藝術學”或“一般藝術學”有過比較深入的、值得我們留意的研究。不過,從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年)在《藝術哲學》中提及藝術學的語氣來推測,到1802年冬謝林在耶拿大學舉辦《藝術哲學》系列講座時,“藝術學”和“一般藝術學”的概念至少在德國學界已經廣為人知了。
戴維·辛普森在謝林《藝術哲學》的前言中指出,“藝術和美學對謝林的(整個思想)體系具有獨特的重要性”(Schelling,ThePhilosophyofArtX)。我們也可以說,藝術學在謝林的《藝術哲學》中具有獨特的重要性,而且這種重要性怎么估計都不會過分。
在所有倡導藝術學的哲學學者中,謝林應該算是在哲學界影響最大的一位。雖然他的名氣不如同時代的黑格爾。但是,按照鮑桑葵的說法,黑格爾的美學思想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謝林的影響(鮑桑葵411)。不僅如此,海德格爾對謝林也推崇備至。很多后輩哲學家都承認,謝林是少數幾位被低估的實力派哲學家之一。
如果閱讀謝林的《藝術哲學》德文文本,我們會很明顯地注意到:第一,謝林并沒有采用他的前輩學者溫克爾曼、赫爾德以及榮格-斯蒂林等人共用的“Kunstwissenschaft”一詞,而是采用了一個意義完全相同,但是表達稍顯復雜的合成詞組“Wissenschaft der Kunst”。這恰好表現了謝林對藝術學的不同尋常的重視,當然,也表現了謝林善于變換概念的學術個性。第二,謝林在《藝術哲學》中,通常只提“Wissenschaft der Kunst”(“藝術學”)概念,唯有一次提到“一般藝術學”(allgemeine Wissenschaft der Kunst)的概念。謝林的原話是這樣的:“在某些情況下,在[個體藝術家的]風格和手法之間進行區分,或者在彼此相互轉化的過程中進行鑒別,所涉及的困難太多,一言難盡。但這不是我們應該做的,并且也與一般藝術學(allgemeine Wissenschaft der Kunst)無關。”(PhilosophiederKunst477)這足以說明,謝林所討論的藝術學,絕對不是門類藝術學或特殊藝術學,而是一個考慮周詳而完備的一般藝術學體系。
謝林的《藝術哲學·緒論》可能是史上最詳備、最全面和最系統的一般藝術學的宣言。這篇緒論,德文版有15頁,英文版有16頁,篇幅相當大。在這篇緒論中,謝林主要論述了如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建立藝術學學科的緣由。謝林倡導藝術學,既有社會和文化的考量,也有學術的考量。就社會而言,謝林試圖為德國上流社會不良的文化風氣糾偏;就學術而言,謝林試圖為整體的藝術研究糾偏。
在德國的傳統文化中,宗教價值一向被視為最高價值;藝術則被視為緊隨其后的一個重要領域。但是,信仰宗教、珍視藝術這樣一種優良的傳統到謝林時代顯然正在走向沒落。謝林不無憤慨地指出,德國“那些直接或間接參與國家管理的官員既不接受藝術,也并不真正懂得藝術,真是可恥之尤。對那些王公貴族和當權者來說,沒有什么比珍視和欣賞藝術、寶貝藝術作品、策勵藝術家創作更為可敬的了;反過來說,沒有什么比那種明明有能力有資源推動藝術繁榮卻把這種能力和資源白白浪費在窮奢極欲、野蠻爭斗、賄賂公行這類卑鄙無聊的事物上更為可悲和丟臉的了”(Schelling,ThePhilosophyofArt8)。這讓謝林極為不解:在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并不重要的東西都能夠吸引我們的注意力,鼓動我們渴求知識的欲望,甚至是激發我們對科學研究的興趣,為什么我們反而對我們所熱愛的、包含了最崇高的目標的藝術表現得那么無動于衷呢?所以,從扭轉社會風氣、引導社會的價值導向的角度,從文化教育的角度(這也是謝林一向極為重視的領域),謝林覺得自己有一種使命感。他覺得他有責任讓高貴的藝術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之中。
在德國的藝術研究方面,謝林也感到情況不容樂觀。謝林覺得在他之前的所有研究美學和藝術哲學的學者中,除了康德(可能也要算上他甚為贊許的溫克爾曼)之外,都或多或少地偏離了藝術研究的軌道,基本上“處在文學的農民戰爭”的水準(Schelling,ThePhilosophyofArt11)。謝林認為,德國在康德之前的所有的藝術理論,基本上都是鮑姆嘉通美學的派生物。由于鮑姆嘉通的美學本身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沃爾夫哲學的翻版,因此,這一時期大凡受到鮑姆嘉通影響的美學理論或者藝術理論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流行的淺薄的藝術觀念和經驗主義的影響。“他們試圖用經驗主義心理學來解釋美,并且,總體上說,他們對待藝術奇跡與對待幽靈故事及其他迷信如出一轍”(Schelling,ThePhilosophyofArt11),因而他們的學術喪失了藝術研究應有的科學性。謝林認為,正因為如此,從(康德)那時起,卓越的智者所播下的真正的藝術體系論或藝術學的種子,至今并沒有形成一個科學的整體(8),所以現在他提出藝術學的問題,非常及時。
此外,謝林發現,處在實踐第一線的藝術家嚴重缺乏理論的訓練。他說,在他這個時代,這種情況幾乎很少有例外:
人們很難從那些真正的藝術實踐者那里了解到有關藝術本質的知識,因為他們自己通常就都得不到關于藝術和美這類理論的指導。正是在那些處在實踐第一線的藝術家身上體現的這種[創作能力與理論儲備之間的]嚴重的失衡,成了我們通過科學手段,追尋藝術真實的理念和原則的一個極為緊迫的理由。(Schelling,ThePhilosophyofArt11)
這就帶有很濃的為藝術家啟蒙的味道了。
第二,闡述了建立藝術學學科的可能性。這是當時的人們頗為擔心的問題。由于謝林通常將藝術學和藝術哲學混用,因此,藝術學學科建構的可能性問題,就演化為哲學和藝術這兩個各自獨立的學科如何能夠統合為一個獨立的學科的問題。
謝林指出,盡管藝術是一種將現實與理想統合于一體的終極的、完美的形式;哲學也體現為一種相同的建構,即將知識的最終對立矛盾轉化為純粹的同一性。兩者看似無關,實則關系密切。
兩者彼此最終在頂點上相遇,正是由于這種共同的絕對性,彼此既充當著對方的本原又充當著對方的映像。這就是為什么沒有一種感性能比哲學更深入地、科學地滲透到藝術的內部的原因;事實上,這也是為什么哲學家在洞悉藝術的本質時擁有比藝術家自身更好的穎悟力的原因。就理念總是現實的更高的反映而言,哲學家就必然擁有比處在現實之中的藝術家更深刻的對理念的省思。由此可見,在廣泛的意義上,藝術可以成為哲學的知識對象,更具體地說,在哲學之外,或者不通過哲學,要想在絕對意義上了解藝術,絕無可能。(Schelling,ThePhilosophyofArt6)
謝林在此強調了兩點:首先,哲學和藝術,從來就是唇齒相依的,誰也離不開誰;其次,沒有任何一種普通的感性或經驗性認知能夠與哲學的深刻的洞察力和穿透力相比較,因此,藝術學的研究必須,也只能仰賴哲學,而哲學的發展也為藝術學學科的建立提供了足夠的背景和條件。
第三,建構了藝術學理論的基本架構。謝林在這篇緒論(甚至整部《藝術哲學》)中,雖然沒有集中而清晰地搭建起藝術學的系統的架構,但是,我們通過對他的片段的、零散的觀點的拼接和組合,還是能夠為他構擬出一套體系。大致說來,他的這個架構可以歸結為以藝術哲學為統領,藝術史學、藝術教育學、藝術風格學、藝術類型學和神話(宗教)藝術學為主干的六維結構。
第四,確立了藝術學的內涵與性質。緒論開宗明義,第一句就為藝術學定調,強調藝術學是系統性的研究(即溫克爾曼所說的“系統的嘗試”),也就是一般藝術學所要求的宏觀研究和整合研究。在一般藝術學這個前提下,謝林特別指出,在“藝術哲學”中增加“藝術”一詞,只是限定而非拋棄哲學的一般概念。這意味著,我們將要系統地或科學地予以探究的,應該是哲學,這是最根本的。也就是說,謝林雖然倡導藝術學學科,藝術學的總的學科歸屬還是在哲學,而非藝術。
謝林解釋說,強調藝術學的目標之一是開展理性直覺的訓練,并不意味著藝術學或者藝術哲學仍然只固守哲學一隅。否則,我們就只能看到普通哲學中那副“自在自為的真理的嚴苛面孔”了(Schelling,ThePhilosophyofArt13)。事實上,在限定為藝術哲學的這一特定的哲學領域之后,“我們進入了對永恒之美和一切美的原型的直觀”(13)。“哲學是一切事物的基礎,囊括一切,并將其結構擴展到知識的一切勢位(potenzen)和對象之中。唯有通過哲學,我們才能達到知識的至高點。通過藝術學,我們就可以在哲學范圍內形成了一個更小的學術圈,由此我們能夠通過可見的形式更直接地審視永恒。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藝術學與哲學是完全一致的。”(13)
謝林不僅將藝術學定位于哲學,而且還規定它是純粹思辨的科學。這種思辨,不同于純粹的哲學思辨,是一種以感性為基礎、以理性抽象為鵠的的感性和理性融通和統一的運思方式。在這種思辨中,作為理性的理性,同時以感性的形式出現(Schelling,ThePhilosophyofArt382)。因為哲學不能從純理性角度進入藝術之中,它需要關注藝術的感性特質。“藝術的諸種形態乃是自在之物的根本形態,是初象之物的根本形態。因此,在其可以被普遍理解的意義上,從自在宇宙和自為宇宙本身的角度出發,對藝術的諸種形態的呈現進行構擬乃是藝術哲學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7)而這一過程,正是藝術學調用其感性手段的過程。
謝林不僅強調藝術學要堅持理性與感性對立統一的原則,同時也強調一般與特殊對立統一的原則。他指出,藝術學依然還是哲學在最高效力(potenzen)上的一種重構。藝術學的體系不僅包含普遍性,而且還將擴展到那些能夠彰顯這種普遍性的藝術家個體中。藝術學需要對藝術家個體及其藝術世界進行剖析。作為一個思辨藝術學的范本,謝林的《藝術哲學》也完美地詮釋了這種一般與特殊、普遍與個別、宏觀與微觀的研究方法。
顯然,謝林所謂的藝術學或藝術哲學(在《藝術哲學》中,兩個概念互通),不僅與他瞧不起的鮑姆嘉通的美學研究不同,與他看得上的溫克爾曼的研究不同,與他不加評論的赫爾德的研究也不同。因為謝林的這些前輩的研究基本上是圍繞藝術的感性外觀來進行的。而謝林明顯偏向理性,偏向所謂“絕對”。事實上,謝林為藝術學研究規劃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理想的模式:由思辨統帥的理性與感性結合的模式。謝林也深知,就理想而言,哲學家的確最適合揭示出藝術的深不可測的特質,也最適合挖掘出其中的絕對性。但是,謝林提出了一個疑問。他問道:在一般的意義上,哲學家是否真的具備專業上的能力?他是否能夠根據藝術的法則,得心應手地把握藝術中真正的可理解的東西,并確定其高低?(Schelling,ThePhilosophyofArt7)
正是出于這樣的擔心,謝林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對藝術學研究提出了四點要求。
其一,從藝術學研究的技術層面而言,哲學要盡可能將自己降低到經驗層面、材料與媒介層面甚至操作層面(Schelling,ThePhilosophyofArt7),深入作為現實者的藝術的內部,一窺藝術的堂奧。但是,謝林在此也設置了一個前提:當研究者以哲學的姿態對藝術的理念進行抽象的時候,必須排除過于感性的、經驗性的、表面性的東西。否則,就會降低藝術學研究應有的深度和純度。
其二,必須關注藝術史,掌握必要的、足夠的能夠支撐研究的文獻。謝林說:“我們將同時呈現藝術的歷史維度;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期望最大限度地把我們理論大廈以最完滿的形式建構起來。”而藝術史也“將以最具啟示性的方式向我們展示它與宇宙的直接聯系的狀況,從而展示它與宇宙先驗的絕對同一性。只有在藝術史上,一切藝術作品的本質的和內在的統一才能顯現出來”。(Schelling,ThePhilosophyofArt19)藝術學的理論大廈必須獲得一個強大而堅實的基礎來支撐,這個基礎就是藝術史。
其三,從方法學角度說,謝林倡導建立一套對立統一的思維范式,由此來切近藝術的內在本質。謝林在《先驗唯心主義體系》和《藝術哲學》中都卓有成效地示范了這種方法。
謝林認為,一切審美作品的創造都始于一種與無限的沖突之感,因此,隨著藝術作品的完成而來的也必定是一種與無限和解的寧靜感,這種感覺反過來也必定會傳導到藝術作品本身。因此,藝術作品的外在表現是一種寧靜、靜穆和宏偉,即使其目的是表現最大強度的痛苦或歡樂。
這里所說的藝術作品,當然是指希臘雕塑。這些關于希臘雕塑的審美品質的描述,顯然來自溫克爾曼關于希臘雕塑的經典表述。但是,謝林在這里所要詮釋的重點,是體現在雕塑內部的一種對立,即,無限和有限的對立、沖突與和解的對立、寧靜和躁動的對立。處在創作過程之中的藝術作品總體表現為有限與無限的沖突,且無限占優勢,因此,其外在表現是一種沖突感;完成之后的雕塑作品正好相反,在無限與有限的沖突中,有限占據優勢,其外在表現是一種平衡感或寧靜感,因為沖突已經趨于和解了。但是,內在的充滿了張力的沖突依然隱約存在,只不過外表的寧靜、靜穆和宏偉完全遮蔽了內在的情緒的劇烈的起伏而已。
其四,謝林通過自己在《藝術哲學》中采用的一套藝術分類體系,示范了他所主張的宏觀與微觀、感性與理性、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的研究路徑。
謝林《藝術哲學》主要由兩大序列構成:第一個序列是“藝術哲學的一般范疇”;第二個序列是“藝術哲學的特殊范疇”。第一個序列是關于藝術學的總論或綜論,主要是概述古希臘羅馬神話、詩歌以及更具有普遍意義的幾種審美形態,諸如優美與崇高、素樸與感傷等。第二個序列相當于分論,就是按照謝林的分類學邏輯,分別對作為現實(實在)序列的音樂、繪畫、雕塑和建筑以及作為理想(理念)序列的抒情詩、敘事詩和劇詩進行具體的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一個序列其實已經包含了若干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研究手段。第二個序列,這兩種研究手段的結合就更加明顯了。一方面,謝林按照現實的藝術的架構,把四種藝術類型即音樂、繪畫、雕塑和建筑納入其中進行整體論述;另一方面,又對這每一種藝術類型進行單獨的、具體的研究。理想的藝術這個序列也是如此。這樣的安排,既展現了作為藝術的大類的共性和普遍性,又凸顯了作為具體的、特定的藝術類型的個性和差異性。
必須指出的是,在謝林的整個思想體系中有一個統領一切的東西,也就是說,有一個總綱。這就是“絕對”。這個“絕對”非常像《道德經》中的“道”——作為萬物或萬有之母的“道”。謝林思想中所有的二元對立,其源頭都可以追溯到“絕對”。謝林解釋說:“絕對,或神,是一種與實在或現實相關且直接從理念中或單憑同一性法則產生的東西,或者說,神是對他自己的直接肯定。”(ThePhilosophyofArt23)“由于其理念,神直接成為絕對之總全(All)。”(24)“任何藝術的直接始因是神。”(32)
“絕對”就是神,在謝林這里,也是一切的始源。也因為如此,謝林說,神的造型的基本法則,就是美的法則。因為美是我們在現實中直覺到的“絕對”;而神就是我們在特殊之中真實地直覺到的“絕對”(Schelling,ThePhilosophyofArt40)。這樣,在絕對、神和美之間,就形成了謝林特有的三位一體關系。
但是,謝林對美有一個更具有學理性的定義,這就是“在有限中表現無限”。美作為古典藝術的終極目的,就成為連接絕對與神性的紐帶。當謝林根據“在有限中表現無限”的公式來劃分現實的藝術和非現實的藝術即理念的藝術的時候,他的整個理論系統就以分而合或合而分的形式清晰地凸顯出來:一方面是向上,是向“絕對”輻輳、聚合;一方面是向下漫溢、彌散。有分有合,有收有放,這就是謝林的分合兼用、收放結合的研究妙法。
黑格爾說:“到了謝林的哲學中,科學才達到它絕對的頂點;藝術雖然早已在人類的最高旨趣中顯出它的特殊性質和尊嚴,可是只是到了現在,藝術的實際概念及其在科學理論中的地位才被發現。”(鮑桑葵409)這個評價是中肯的。
我們不能用當今的學科分類體系或知識系統來衡量謝林,糾結于他的藝術學研究的學科歸屬。更何況,藝術學的概念,從德索以來到當今,內涵和邊界已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需要牢記的是,繼溫克爾曼、赫爾德和榮格-斯蒂林之后,對藝術學的理論體系闡釋最全面、最深刻、最系統的是謝林,對藝術學的研究最深刻、最系統、最具有思辨性的,也是謝林。謝林從1802年開始,在耶拿大學和維爾茨堡大學連續講授了四年的藝術哲學,持續地宣傳和倡導藝術學,在德國學術界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只要查一查德國當年的《耶拿文獻通報》,我們就不難發現,從19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直到20世紀,謝林的藝術學理念不僅一直活躍在大學講壇上,從某種程度上說,整個美學界也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謝林的影響。⑦謝林對藝術學用情之專、用功之勤,對藝術學的影響之巨,用空前絕后來形容也是不為過的。
也許有人認為,赫爾德剛剛開創的自下而上的非思辨藝術學研究路徑,到謝林這里,又被還原到自上而下的思辨性研究路徑了。謝林是否有將藝術研究引向歧路的嫌疑呢?我認為這種看法顯然是受到了費德勒等人的反美學的藝術學觀的影響。確實,在藝術學的發展史上,美學與藝術學的學科之爭,思辨與非思辨的路徑之爭,幾乎一直就沒有停止過。藝術學內部也存在著美學(思辨)導向的藝術學和純藝術學導向的藝術學之爭。前者更多地執著于研究的理論深度,后者更多地偏向于研究的感性溫度。兩方都有理。但謝林是在思辨研究的框架下,依然強調理性與感性的融合;費德勒卻認為美學思辨只會傷害我們對形式的感知,執意要把美學這具“僵尸”徹底拋棄掉,似乎藝術學研究只有他認可的才是唯一的選擇。其實不然。我覺得溫克爾曼、赫爾德和謝林三人已經約略為我們示范了三種研究路徑或境界:第一種是思辨的、理想的境界,比較難,是由謝林的《藝術哲學》呈現出來的;第二種是非思辨的、現實的境界,稍微容易一些,是由赫爾德的《論雕塑》呈現出來的;第三種是前二種的融合,是由《古代藝術史》呈現出來的。相對而言,三種境界中,理想境界反而最為重要,因為這是藝術學理論研究獲得不斷提升的動力和保證。
如果我們把謝林作為一個參照點,瞻前顧后,左顧右盼,我們會發現,到19世紀前后這個關口,與藝術緊密相關的三個學科,也正在采取一種既彼此滲透又相互排斥的方式,按照自身的邏輯,逐步發展。這三個學科,第一,當然是美學,從鮑姆嘉通到康德到黑格爾,美學發展可以說達到了一個高峰;第二是藝術史,藝術史學科的歷史最為悠久,從老普林尼到菲奧里諾,藝術史學科在德國已經開花結果了;⑧第三是藝術學,從18世紀中期初露端倪,到19世紀初,在謝林的強勢推動下,藝術學的艦船正待拔錨起航。
謝林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也好,藝術歷史的發展也好,都包含了某種必然中的偶然,或偶然中的必然。謝林舉例說,時鐘的發明者并沒有真正發明它;這位幸運兒只是在時鐘從盲目發展的力量中出現時發現了它。拉斐爾在畫《雅典學院》時也屬于這種情況(Schelling,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145)。時代盲目發展的力量總是在為應時而出的英雄們準備成熟的條件。蘋果已經熟透,需要的只是一只碰巧遭遇的手。但是,遺憾的是,歷史還需足足等待一個世紀,藝術學才會有邂逅這只姍姍來遲的手的幸運。
綜上所述,藝術學無論是作為一個學術概念,還是作為一個學科概念,它的發生學真相,與當下中外學者的研究結論大相徑庭。藝術學的創始人既非費德勒,也非謝林,而是溫克爾曼。一般藝術學的創始人既非齊美爾曼,也非德索,而是由經濟學家榮格-斯蒂林最先提出,由謝林豐富和完善。藝術學研究的實踐,也是由溫克爾曼創始,由赫爾德發展,由謝林總其大成。總之,藝術學從概念的提出,到其學術和學科內涵的豐富和完善;從整個學科體系的建構,到其研究實踐的系統性的示范,到19世紀初謝林在耶拿大學講授《藝術哲學》時,都已經全部完成了。溫克爾曼、赫爾德和謝林通過不到半個世紀的學術接力,不僅合力完成了一般藝術學的理論的系統化建構,鞏固了藝術學的學科基礎,而且也開創了非思辨、思辨以及二者兼具這樣的三種研究范式。謝林雖然算不上藝術學的創始人,卻是藝術學歷史上唯一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學術大師,直至當今,依然無人超越。
注釋[Notes]
① “Kunstwissenschaft”,國內起初譯為“藝術學”,后修改為“藝術學理論”。在本文中,“藝術學”和“藝術學理論”同義。需要說明的是,早在1996年“藝術學”就被列入當時的“文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藝術學”之下的二級學科(碩士點)目錄。兩年之后,“藝術學”獲得博士點授予權。當時的藝術學學科評議組并沒有介意一級學科與二級學科重名的問題。2011年,“藝術學”升格為門類之后,原來的二級學科“藝術學”升級為一級學科。為了避免重名的問題,“藝術學”就變成了現在的“藝術學理論”。最近藝術學的學科目錄又在作調整,“藝術學理論”似乎又面臨著改名的問題,因此,關于“Kunstwissenschaft”的考古學和學術史研究就變得格外緊迫起來。
② 康斯坦茨大學教授尤爾根·米特爾斯特拉斯(Jürgen Mittelstra?)花數十年時間編輯,于2015—2018年出版的《哲學與科學理論百科全書》(Enzyklop?diePhilosophieundWissenschaftstheorie,Stuttgart·Weimar:J.B.Metzler,2018年)(8卷本)竟沒有收入“藝術學”這個條目;烏立克·普菲斯特爾(Ulrich Pfisterer)編輯的《梅茨勒藝術學詞典》(MetzlerLexikonKunstwissenschaft,Stuttgart·Weimar:J.B.Metzler,2011年)對藝術學的起源也語焉不詳,可見在學科體制上沒有藝術學學科的德國對藝術學的基本態度。
③ “Kunstwissenschaft”作為一個一般概念,或狹隘的美術學概念,或許早已存在,但是作為一個學科概念,說由溫克爾曼發明,應該是站得住腳的。
④ 按照斯達爾夫人的說法,溫克爾曼最終是在羅馬被一位偶然搭識的同性戀者所殺害。(Sta?l27)
⑤ 赫爾德的論敵里德爾在《美術與科學理論》中曾經宣稱“創造產品的技能稱為藝術;藝術理論稱為科學”,即藝術學。在另一場合,里德爾還提出了“一般藝術理論”的概念,這也可以視為一個“藝術學”概念。為了凸顯區別,赫爾德可能有意回避采用“藝術學”一詞。(Riedel31,277)
⑥ 赫爾德對古代雕塑詮釋的這種整體觀顯然受到希臘的“kalokagathia”(至善至美)概念啟發。他主張美與善的統一,即內在與外在的完美統一。對赫爾德來說,身體不僅僅是各個部分的集合體,也是意義的承載者和主體的內在生活的表達。靈魂通過身體來說話,如果我們要理解和欣賞雕塑形式的深層意義,我們必須學習它的語言。(Herder,Sculpture26)
⑦ 受到謝林較大影響的美學家有齊美爾曼、福克爾特、柯亨和烏提茲等。追隨謝林藝術學理念的學者有:卡爾·弗里德里希·巴赫曼(Karl Friedrich Bachmann,1785—1855年),他一直年在耶拿大學開設藝術學概論,并且于1811年將該教案以《巴赫曼藝術學理論學術講演錄》(DieKunstwissenschaftinihremallgemeinenUmrissedargesiesstfürakademischeVorlesungenvonC.F.Bachmann,Jena:Cr?kerschen Buchhandlung,1811)為題出版;努斯萊因(F.A.Nüsslein),于1819年出版《藝術學概論》(LehrbuchderKunstwissenschaft,Landshut);弗洛里希(Fr?hlich),1831年在維爾茨堡大學開設“作為藝術學的美學”(AesthetikalsKunstwissenschaft)課程。參見Jenaischeallgemeineliteratur-zeitungApr.1813:48-50 & Mar.1831:98-100;Tennemann,Wilhelm Gottlieb,GrundrissderGeschichtederPhilosophiefurdenakademischenUnterricht,Leipzig,J.A.Barth,1825,479;482。
⑧ 1810年,哥廷根大學首設藝術史教授崗位,菲奧里略成為史上第一位藝術史教授。這標志著德國的藝術史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這也是藝術史告別普通歷史,從此走向獨立發展的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信號。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ddison,Joseph.TheSpectator.Vol.2.London: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Ltd.,1891.
Baumgarten,Alexander Gottlieb.Theoretischesthetik.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83.
以賽亞·柏林編:《啟蒙的時代》,孫尚揚、楊深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
[Berlin,Isaiah.TheAgeofEnlightenment.Trans.Sun Shangyang and Yang Shen.Peking:Guangming Daily Publishing House,1989.]
伯納德·鮑桑葵:《美學史》,張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
[Bosanquet,Bernard.AHistoryofAesthetics.Trans.Zhang Jin.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85.]
Burke,Peter.SocialHistoryofKnowledge:FromGutenbergtoDiderot.Cambridge:Polity Press,2000.
D’Alembert,Jean le Rond.Discourspréliminairel’Encyclopédie(1751).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6.
Disselkamp,Martin,and Fausto Testa,eds.WinckelmannHandbuch:Leben-Werk-Wirkung.Stuttgart:J.B.Metzler Verlag,2017.
Filippi,Elena.VonderGeschichtederKunstzueinerKunstwissenschaft.Entwicklung.NachidealistischePerspektiven.Regensburg:S.Roderer-Verlag,2013.
Haupt,Klaus-Werner.JohannWinckelmann:BegründerderklassischenArch?ologieundmodernenKunstwissenschaften.Weimarer Verlagsgesellsch,2014.
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美學(第一卷)》,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
[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Aesthetics.Vol.1.Trans.Zhu Guangqian.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85.]
Heinz,Marion,hrsg..HerdersMetakritik:AnalysenundInterpretationen.Frommann-Holzboog,2013.
Herder,Johann Gottfried vonBriefezuBef?rderungderHumanit?t.Bd.8.Riga:Hartknoch,1796.
---.KritischeW?lder.Bd.3.Riga:Hartknoch,1769.
---.PhilosophicalWritings.Trans and ed.Michael Neil Forster.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Sculpture:SomeObservationsonShapeandFormfromPygmalionsCreativeDream.Trans and ed.Jason Gaig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
---.SelectedWritingsonAesthetics.Ed.Gregory Moo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Jung-Stilling,Johann Heinrich.Versuch einer Grundlehre s?mmtlicher Kameralwissenschaften.Lautern:Verlag der Gesellschaft,1779.
Koch,Heinrich Christoph,and Johann Georg Sulzer.AestheticsandtheArtofMusicalCompositionintheGermanEnlightenment:SelectedWritingsofJohannGeorgSulzerandHeinrichChristophKoch.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馬采:《藝術學與藝術史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年。
[Ma,Cai.CollectedWorksonKunstwissenschaftandArtHistory.Guangzhou: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1997.]
Riedel,Friedrich Just.TheoriederschonenKunsteundWissenschaften.Jena:Cuno,1767.
Rousseau,Jean-Jacques,and Johann Gottfried Herder.OnTheOriginofLanguag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
Schelling,Friedrich Wilhelm Josephvon.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intotheEssenceofHumanFreedom.Trans.Jeff Love and Johannes Schmidt.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
---.PhilosophiederKunst.Stuttgart:Cotta,1859.
---.SystemofTranscendentalIdealism.Trans.Peter Heath.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78.
---.ThePhilosophyofArt.trans and ed.Douglas Whitaker Stot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9.
Sta?l,Madame de.TheDangerousExil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Sulzer,Johann Georg.AllgemeineTheoriederSch?nenKünste.Bd.2.Leipzig:Bey M.G.Weidmanns Erben und Reich,1774.
Tennemann,Wilhelm Gottlieb.GrundrissderGeschichtederPhilosophiefurdenakademischenUnterricht.Leipzig,J.A.Barth,1825.
Utitz,Emil.“über Grundbegriffe der Kunstwissenschaft.”KantStudies34.1-4(1929):6-69.
---.“Le problème d’une science générale de l’art[1922].” Traducteur.Fran?oise Joly.Trivium6(2010):3637.
Volkelt,Von Johannes.Systemdersthetik.Grundlegungdersthetik.Band I.München:C.H.Beck’ 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925-1927.
Wiesing,Lambert.TheVisibilityoftheImage:HistoryandPerspectivesofFormalAesthetics.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6.
Winckelmann,Johann Joachim.GeschichtederKunstdesAltertums.Weimar:Hermann B?hlaus,1964.
約翰·約阿希姆·溫克爾曼:《希臘人的藝術》,邵大箴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
[Winckelmann,Johann Joachim.HistoryofAncientArt.Tran.Shao Dazhen.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