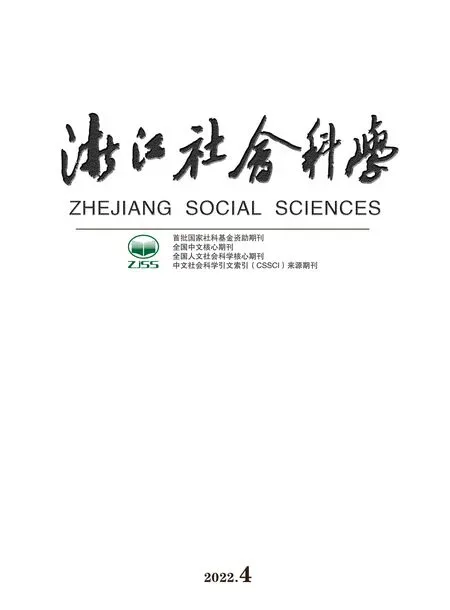重審“開放馬克思主義”與法蘭克福學派的新遺產(chǎn)
□ 孫 亮
內(nèi)容提要 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作為法蘭克福學派支流方向,如今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一幅豐富而飽滿的思想圖景。新馬克思閱讀學派及其所延展出來的“開放馬克思主義”在一定的意義上,凸顯了這一圖景的理論特質(zhì)。“阿多諾式的底牌”成為理解兩者的關鍵,特別在霍洛威的思想中顯現(xiàn)為:不要從同一性的視角出發(fā),而是更注重非同一性的一面;以批判同一性的“綜合”,拒絕對現(xiàn)實生活作一種目的論的倡導;非同一性是創(chuàng)造力,同一性則是對創(chuàng)造力的否定。返回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可以看到,他們作為理論支架的“交換抽象”,及由“交換抽象”所形成的資本主義批判方式,實質(zhì)上遮蔽了資本與勞動的交換、從而遮蔽了私有財產(chǎn)權制度,他們號召拒絕抽象勞動,但真正要拒絕的是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
思想史的“主流”往往被無限地衍生,但“支流”也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重新得到關注,更甚的是,還可能出現(xiàn)主流與支流的“換位”。以法蘭克福學派來講,無論是馬丁·杰伊(Martin Jay),羅爾夫·威格豪斯(Rolf Wiggershaus)、埃米爾·瓦爾特-布什(Emil Walter-Busch)的經(jīng)典法蘭克福學派史的書寫,還是德米洛維奇(Alex Demirovic)在關于法蘭克福學派發(fā)展脈絡的最新作品中的勾勒,基本上是將筆墨留給核心人物霍克海默與阿多諾,然后再推進到本雅明、波洛克、諾伊曼、馬爾庫塞、哈貝馬斯、霍耐特等人。這一被勾畫為“主流”的思想譜系以其對現(xiàn)代性統(tǒng)治的支配結構批判而不斷得到學術界關注。譬如技術批判、文化工業(yè)批判、啟蒙批判等等,總體來說,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卻成為了被“遺漏”的視角。對于漢語學術界來講,法蘭克福學派與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之間的關系直到現(xiàn)在依然是一片尚待展開的研究領域。實質(zhì)上,在霍克海默與阿多諾的文本中,政治經(jīng)濟學都得到過論述。譬如,霍克海默在《傳統(tǒng)理論與批判理論》中已經(jīng)引出,在運用社會批判理論對當代進行研究時,可以對“交換為基礎的經(jīng)濟特征的描述為出發(fā)點”,并且“具體的社會關系被判定為交換關系”,“批判理論所概述的交換關系才支配社會現(xiàn)實”,由此,“社會批判理論始于直接商品交換的觀念”。①而阿多諾則將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看成為對歷史整體的批判,認為政治經(jīng)濟學的不可改變的本性是資本主義及其前身享有特權地位的來源。②也就是說,政治經(jīng)濟學已經(jīng)在阿多諾那里被看作為現(xiàn)實支配體系的意識形態(tài)表達。我們從《阿多諾與索恩·雷特爾的書信集(1936—1969)》中更可以看到,在1944年,雷特爾在給阿多諾寫信告訴其正在為將康德認識論抽象的形式統(tǒng)一性(Formal identity)奠基于交換抽象而努力,這將引出意識形態(tài)的哲學解釋。③顯然,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遺產(chǎn)之一的“政治經(jīng)濟學” 批判范式應該重新被坐實為其理論的核心要素。這一方面的努力,我們不妨從另一個側(cè)面來看:經(jīng)過雷特爾借用西美爾的“現(xiàn)實抽象”,使得這條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的范式被當代西方左翼積極呼應。譬如,齊澤克以精神分析的方式去重構“現(xiàn)實抽象”,即“它是這樣一種現(xiàn)實,它的本體一致性暗示處參與者的某些非知。如果我們‘知道得太多’,洞悉了社會現(xiàn)實的運作機制,這種現(xiàn)實就會自行消解”。④更不用說像亞瑟、普殊同等人更是將“現(xiàn)實抽象” 推展到資本主義特有的統(tǒng)治結構,并且以《資本論》的重新解讀來支撐這一論說,“資本主義的特征之一是,它的本質(zhì)關系是一種獨特的社會關系。它們并不作為直接的人際關系而存在,相反,它們是對立與個人的一套準獨立的結構”。⑤更有趣味的是,喜歡福柯權力批判的人,在面對當今馬克思或者《資本論》解讀的時候,會將這種政治經(jīng)濟學意義上的抽象結構直接對等于權力的結構加以批判。那么,我們不禁要問,究竟當代西方左翼在何種意義上能夠說真正支撐起法蘭克福學派這一思想新遺產(chǎn)?我們一旦能夠找到支撐點,并且對支撐點本身給予批判性的分析,才能夠真正抓住西方左翼的問題所在。為此,我們試圖通過開放馬克思主義 (Open marxism) 這一新流派為視角,對上述問題進行求解,從而能夠重繪法蘭克福學派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范式版圖。
一、新馬克思閱讀學派的分叉與主體的抵抗
新馬克思閱讀(Neue Marx-Lektüre)與開放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最為緊密,但對于后者來說,顯然沒有前者那么直接地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 “正名”。譬如,埃爾貝(Ingo Elbe)在《馬克思在西方:1965年以來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的新馬克思閱讀》一書中作出如下判斷:阿爾弗雷德·施密特、漢斯-格奧爾格·巴克豪斯和赫爾穆特·賴希爾特是“馬克思的新解讀”的代表人物,并且與傳統(tǒng)西方馬克思主義相互區(qū)分。與“盧卡奇-科爾施式”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同,在新馬克思閱讀看來,魯賓和帕舒卡尼斯以與正統(tǒng)觀念截然相反的方式處理了馬克思主義價值論和國家理論的核心問題,才是更值得關注的。⑥因而,隨著價值形式相關研究在漢語學術界的展開,使得人們對從魯賓經(jīng)過新馬克思閱讀達至普殊同的理路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如果人們注意到《開放馬克思主義文集》(1-4),將會很有趣地發(fā)現(xiàn),開放馬克思主義的任何討論都少不了新馬克思閱讀學派的身影。在第一冊中,博納菲爾德不僅收集了巴克豪斯的《哲學與科學:作為批判理論的馬克思社會經(jīng)濟學》的論文,而且對他作了如下的介紹: 作為阿多諾的一名學生,他正在與赫爾穆特·萊希爾特一起研究與批判理論相關的政治經(jīng)濟學方法。巴克豪斯的出版物致力于價值理論、貨幣理論和辯證法。他關注的是政治經(jīng)濟學方法的哲學維度和經(jīng)濟維度之間的關系。在收集的論文中,他主要強調(diào)了馬克思主義范疇的“雙重特征”(包括主觀和客觀、抽象和具體)。他將客觀性定義為異化的主體性,從而發(fā)展了阿多諾的概念。對巴克豪斯來說,馬克思的抽象范疇是具體的,價值是作為社會實踐和矛盾性的存在。⑦
但是,對于開放馬克思主義本身,以及開放馬克思主義與新馬克思閱讀學派之間的真實關系的論題并沒有得到嚴肅的討論。從如何理解價值形式的方面去看,筆者曾試圖以新馬克思閱讀學派將“價值形式”自主化,取消了現(xiàn)實生產(chǎn)關系的內(nèi)在矛盾,而開放馬克思主義則傾向于將“價值形式”動詞化,并主張以勞動的重構去抵抗“價值形式”結構,⑧進而呈現(xiàn)兩者之間的差異。在這一方面,開放馬克思主義相對側(cè)重主體,而新馬克思閱讀學派則著力于客體的結構,謝貝爾(Mario Sch?bel)認為兩者最大的區(qū)別是:前者為觀念論的,后者則是唯物論的,并進一步認為,可以說開放馬克思主義更類似于馬爾庫塞的方法,而新馬克思閱讀更接近阿多諾的觀點。后者是基于客體的首要地位的,當然非常奇怪的是,這正是新馬克思閱讀學派針對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客觀主義的嚴格批判的結果。顯然,開放馬克思主義也贊同這種批評。與開放馬克思主義不同的是,阿多諾并沒有完全屈服于主體性。按照謝貝爾的看法,開放馬克思主義冒著對唯物主義解釋導致對唯物主義反轉(zhuǎn)的風險,從而消除了馬克思辯證法中的所有唯物主義元素,就像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剝奪了它的所有唯心主義元素一樣。⑨這個評價是有一定道理的,以霍洛威(John Holloway)為例,他的核心理念就是改變從客體出發(fā)的視角,主張從主體入手:“我們就是資本的危機”,所以,明確的起點就是“我們”。但是,“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的起點并非是我們,而是它們、是資本”。⑩因而,這一傳統(tǒng)會更注重去談論資本主義統(tǒng)治以及關于資本主義統(tǒng)治的改變形式,不過,“如果我們從資本開始,我們將繼續(xù)嘗試并闡述統(tǒng)治理論。通過闡述統(tǒng)治理論,我們實際上是在封閉自己。”?不過,開放馬克思主義哲學也絕對不是從“無產(chǎn)階級”的主體出發(fā),因為,這一概念依然太“公式化”了,它會使得我們從無產(chǎn)階級上溯到資本主義統(tǒng)治,于是,思維又回到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的闡釋方式中,也“最易于成為‘第三人稱話語’即我們將工人階級思考為他們”。由此,在霍洛威看來,這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將他們作為一種客體的政治學。現(xiàn)在需要有一個“抵抗資本主義的語法轉(zhuǎn)變”,從反資本主義和反資本主義行動形式的轉(zhuǎn)變上進行重新思考。?這樣來看,開放馬克思主義哲學似乎與新馬克思閱讀學派毫無關聯(lián)。
但是,問題不在于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主體維度還是客體維度的傾向,而是如何看待資本主義本身。對于新馬克思閱讀學派來講,“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最主要是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jīng)濟結構”。?而對于這一結構的建構,主要是通過商品流通領域的現(xiàn)實抽象完成。“商品所具有的價值對象性不是具體勞動的對象化,而是抽象勞動的對象化。如果如前所述,抽象勞動是一種只在交換中存在的社會性的有效關系,那么,商品的價值對象性也只在交換中才存在”。?由此,現(xiàn)實抽象所形成一種“形式規(guī)定”,譬如最為核心的價值形式則成為了物被顯現(xiàn)為商品,行動(Do)被生成為資本增值活動,人則被經(jīng)濟范疇化為謀生勞動者的基本形式結構。那么,對于開放馬克思主義者來講,是不是完全否定了這一看法呢?實質(zhì)并非如此,反而可以看到,在這一個問題上,他們并沒有什么實質(zhì)的差別。譬如,他們同樣認為存在一個抽象化所形成的結構,即抽象化的結構不過是社會關系被資本主義編織而形成的,“這是一個無人控制的過程。事實上,沒有人控制它,使它絕對必須要推翻:它不僅是對人的自決權的否定,而且它的動力也正在引導我們走向人的自我毀滅。同時,正是因為沒有人控制它的事實才使得它很難被推翻,因為對于我們來說,便是樹立面前的一張?zhí)煲聼o縫的網(wǎng)。”?顯然,對于霍洛威來說,雖然他想從結構的視角撤退到主體的維度進行討論,但是,依舊承認結構本身的存在,將資本主義視為封閉體系,而在打破這一體系的思考上,他們在要跳出新馬克思閱讀學派的思考上,提出讓人們換一種語法進行思考,即需要有一個從名詞到動詞的思考方式的轉(zhuǎn)變,“從‘形式’到‘形式過程’,或者更好地,從‘形式’到‘形成’的轉(zhuǎn)變”,具體來講,就是要將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形成的所有“形式” 都被理解為“形成過程”,“商品被理解為商品化,貨幣為貨幣化、資本為資本化,國家為國家化,等等,那么所有這些都會發(fā)生變化。”?在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新馬克思閱讀還是開放馬克思主義哲學都認同了抽象化的結構,只不過后者更表現(xiàn)為一種主體意志論的抵抗,因而,才會反復說,不要再從結構決定論出發(fā),但從來沒有反對結構對現(xiàn)實存在的建構性,我們可以認為兩者都共同享有了將資本主義理解為一種形而上學的展開,這也是后來亞瑟等人展開的“確證黑格爾的邏輯與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之間的相關性”時,認為需要論證“資本主義體系的本體論基礎”的根本出發(fā)點。?因而,開放馬克思主義在開始斗爭那一刻,已經(jīng)承認任何的斗爭都遭受到結構決定論影響。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并沒有像謝貝爾說的最終就是一種馬爾庫塞的理想主義的再版,?其實,這個判斷錯誤是雙重的。一方面,馬爾庫塞對于“結構”的看法,實質(zhì)上是要求給予一種階級斗爭式的革命性變革,“如果不想讓自治僅僅停留在一種管理形式上的變革,就必須讓它在一個已經(jīng)克服了階級社會束縛的政治上活躍的工人階級內(nèi)部得到發(fā)展”。?另一方面,霍洛威的對策對于價值形式所造成的結構來說,只是一種自我的撤退,“要瓦解行動到勞動的抽象化,我們的運動必須從下而上。我們從許多不同的起點出發(fā),反對統(tǒng)一的、壓制性的抽象力量”。?
二、“阿多諾式底牌”:走出傳統(tǒng)闡釋模式的邏輯呼應
無論是新馬克思閱讀學派還是開放馬克思主義哲學,如何看待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是判定二者之間存在某種親緣性的關鍵。在法蘭克福傳統(tǒng)中,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一直被作為理論反思的對象而處理,其最初的理論目標是要解釋物化及其根源,從而給予變革性方案,但是,隨著二戰(zhàn)爆發(fā),解放的替代方案便徹底消失,“反抗越來越具有存在主義式色彩的形式。它此時基于個人與社會之間非同一性的強化”。?這種相異于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模式,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闡述為第二自然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并不因此建立起一種自動的解放,其批判意圖恰恰相反,旨在從一個非理性社會的自動化中解放出來。篤信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發(fā)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反馬克思主義者作為最高科學或非科學預言的證明,這種斷言必須理解為一種批判性的陳述。”?20世紀60年代,施密特便以歷史與結構的關系討論在認知上理解而非在本體論上確立邏輯在歷史之前的首要地位,這對于巴克豪斯反對20世紀60年代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李嘉圖主流,指出勞動形式理論是馬克思和李嘉圖之間的差異是存在接續(xù)關系的,因為,對于巴克豪斯來講,從交換價值到價值到價值形式的發(fā)展,作為“從直接的‘存在’到‘本質(zhì)’再到中介的‘存在’”的辯證運動,是難以理解的,“如果沒有這種對黑格爾邏輯的方法論借鑒,如果沒有價值論作為價值“內(nèi)在超越”的過程及其作為貨幣的設定,馬克思試圖證明的必要的“商品與貨幣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就會被撕裂。?客觀地說,在20世紀70年代,對于邏輯—歷史正統(tǒng)的方法論的重新理解始終成為新馬克思閱讀學派試圖做出理論貢獻的 “理論杠桿”,而對一項工作的深入也使賴希爾特和巴克豪斯利用阿多諾的一系列思想作為他們重建馬克思對經(jīng)濟目標的理解的指導原則。埃爾貝有一個非常準確的概括:第一,阿多諾將經(jīng)濟客觀性認定為“在現(xiàn)實本身中占主導地位的概念”,將“交換價值”認定為“僅僅是思想”,認為“普遍對特殊的支配”。這些主題一直延續(xù)到賴希爾特后來的有效性理論中,該理論試圖將價值解讀為一種“思想的東西”(thing of thought)。第二,阿多諾的“客觀性的優(yōu)先地位的顛倒形式”的想法,回蕩在賴希爾特的客觀性主導理論中,并且表明了資本主義社會相對于行動者的意圖和需要的真正獨立性。第三,對方法論個人主義和客觀主義社會理論的批判。根據(jù)阿多諾的觀點,真正獨立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不能以一種“社會唯名論”的方式被行動者的意圖穿透,但它也不是獨立于個人行為而存在的自在。第四,有一種對“實證主義”作為一種幼稚的經(jīng)驗主義方法論的批判,它忽略了“事實”的歷史—社會中介,并將中介轉(zhuǎn)化為直接的東西。?當然,對于新馬克思閱讀學派與阿多諾之間的關系,有了這種基本的判斷之后,我們便不再進一步詳細論述,因為這已經(jīng)足夠指明阿多諾與新馬克思閱讀學派所主張的結構優(yōu)先性,以及通過人的現(xiàn)實抽象完成的結構對人們存在的“同一化”的統(tǒng)治的親緣性。
那么,開放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會采用阿多諾作為其理論基礎嗎?答案是肯定的。在霍洛威發(fā)表的《為什么要阿多諾》中表達了采用阿多諾的諸多原因。首先,不是從同一性的視角出發(fā),而是更注重阿多諾的非同一性的一面。因為,“破裂、反抗、脆弱、不確定性、開放和痛苦是阿多諾思想的中心:這就是他如此令人興奮的原因。”?故而,“辯證法是指從那些不存在的地方那里思考世界,從那些不存在的人,那些被否定和被壓制的人,那些不服從和反抗打破身份界限的人,從我們存在于資本內(nèi)部和資本之外的人那里思考世界。”?對于阿多諾來講,同一性與非同一性各自的談論都不是獨立的,沒有同一性作為理論的支架,不可能有非同一性的出場,因為非同一性正是要克服同一性,相反,沒有非同一性的同一性,則無法建構其批判理論的姿態(tài)。在這種同一性與非同一性的辯證法下才能夠建構出瓦解的邏輯,“不是傾向于每一客體和其概念之間的差異中的同一性,而是懷疑一切同一性,它的邏輯是一種瓦解的邏輯”,?所以,從一種同一性原則出發(fā)則無法看到這種邏輯的出路,因為,從同一性原則的肯定式的術語學就能夠表明這一點,“簡單的論斷行句子被叫作 ‘肯定的’。系動詞說:它是如此而不是別的樣子。系動詞代表的綜合行為標明‘它’不應是別的樣子”。?毫無疑問,這正是霍洛威呼吁要從名詞轉(zhuǎn)向動詞的語法革命的源頭。正是有了這個轉(zhuǎn)變,非同一性作為阿多諾所突現(xiàn)的思維自身的突破力量,在霍洛威等開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非同一性不再僅僅是一個哲學的概念,而是作為一種有希望成為超越現(xiàn)實結構性統(tǒng)治的社會力量被處理的。
其次,以批判同一性的“綜合”,從而拒絕對現(xiàn)實生活作一種目的論的倡導。我們知道,對于西方左翼學者來說,對于一種美好生活的完美結局的看法是他們共同懷疑的,霍洛威也是一樣,他認為,在奧斯威辛和廣島這樣人類的災難事件之后,尤其不能保證一個幸福的結局。這就是為什么有必要放棄辯證法的概念,即否定的過程導致綜合,否定的否定導致肯定的結局。我們現(xiàn)在唯一能把辯證法看作是否定的運動,是一種瓦解的運動,而不是綜合的運動,是一種否定的辯證法。?那種依靠辯證法,能夠?qū)ο笸耆{入概念之中的想法是荒謬的; 異質(zhì)性和偶然性才是事情本身的狀態(tài),任何對這一本然狀態(tài)無視的思維方式,注定只能是一種暴力式的對事物的強加,但是,歷史終究反復證明這種暴力最終并沒有兌現(xiàn)其承諾。正如阿多諾描述的那樣,“一旦意識到概念的總體性是純粹的光耀,我別無它途,只能內(nèi)在地按其自身的尺度去沖突總體同一性的光耀。”?也只有突破這種同一性,邊緣的、矛盾的、不可見的東西等才有機會被審視到,那種始終以可見在場的東西才能夠從自己俯視的站臺上走下去,而這一切不是丟掉了同一性的視角就可以實現(xiàn)的,而是需要從辯證法本身的理解中去為這些非同一性打造出場的道路。霍洛威等人明確地指認,“我們需要的不是拒絕辯證法,而是針對辯證法的綜合理解,換句話說,堅持否定的辯證法,一種不一定會帶來幸福結局的不安的運動。歷史并不被視為一系列的階段,而是一場無休止的反抗運動。”?也就是說,辯證法要告誡的是: 唯一能擁有的真理的概念只能是否定的。一種美好結局(Happy ending)的目的論理念便失去任何辯證法的保證。
最后,非同一性是創(chuàng)造力,同一性則是對創(chuàng)造力的否定。以往的哲學一再表現(xiàn)出對真正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非同一性的漠視,“非概念性、個別性和特殊性。自柏拉圖以來,這些東西總被當作暫時的和無意義的東西而打發(fā)掉,黑格爾稱其為‘惰性的實存’”,?從而,這種特殊性被當作矛盾剔除掉,也就自然剔除了從非同一性出發(fā)思考的視角,以此轉(zhuǎn)向?qū)Y本主義敘事的話,必然讓非同一性消融在同一性方面。其實,“我們在日常每一天都能體驗到它,尤其從我們的生活世界中過度充斥著的導航 (或者用一個更糟糕的說法,叫瞄準)的需求也可以看出來,‘絕對’是一個神學范疇”,?這種導航必然是自相矛盾的,它能夠瞄準的只是自己已經(jīng)圖繪過的領域,而對于非圖繪的其實是毫無顧及的。在阿多諾的意義上講,和同一性不相協(xié)調(diào)的事物是矛盾的,它始終去嘗試抵制任何一致解釋的嘗試。因而,辯證法總是要指向具體的事物,它揭示了概念和事物的深思熟慮的對抗、是同一性與非同一性的對抗,要談論前進,就要求從矛盾、特殊、非同一性去思考,它的運動不再是要求每個對象和與其差異的概念之間總是謀求同一性; 相反,它堅守差異性,并對任何同一性都保持抵抗的姿態(tài)。當霍洛威將此滑向?qū)Y本與勞動分析時認為,從同一性視角看,否定位于肯定作用之下,勞動在資本作用之下,它具有資本的拜物教形式。?從抵抗資本這種同一性的視角看,勞動力才是真正的創(chuàng)造動力,而資本只能是對創(chuàng)造力的不斷否定。
三、“交換抽象”的“非自在性”與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
既關注生活被給定的“規(guī)定性”的統(tǒng)治結構,也關注人從這種結構中重寫獲得新的生活形式的可能性,從而激發(fā)人的全部可能性,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總體特點,構成對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闡釋方式的反思。譬如,對于霍洛威等人的開放馬克思主義來說,阿多諾的否定辯證法已經(jīng)內(nèi)在地要求我們必須以“開放性”而非“封閉性”去理解資本,以及由資本所塑造的資本主義世界。也就是說,開放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不再認為現(xiàn)存的一切形式是人類學的存在,而認定其為特殊時代的產(chǎn)物,“認為它們是階級斗爭的產(chǎn)物,在這個意義上,是一種開放的東西。因此,它不同意任何將馬克思主義變成只是正確描述現(xiàn)有社會的功能性理論的方法。也就是說,開放馬克思主義拒絕將對價值的理解看作是一條規(guī)范資本主義再生產(chǎn)的法則。”?當然,對現(xiàn)存的一切形式持有批判而非肯定的理解,將其作為一種必須要加以廢除的錯誤狀態(tài),其實自施密特以來就存在。這對于新馬克思閱讀學派來講也沒有什么改變。其實,在1965年,雷特爾在與阿多諾的對談筆記中把這個原則說的很清楚了,交換抽象建構的范疇“要求撇開(遺忘)它們的社會起源,撇開一般的起源,而歷史唯物主義是對起源的回憶”,?當然,這與賴希爾特表達的唯物辯證法的方法就是退回(Widerruf)的方法大意是相同的。馬克思在談論價值形式也明確地表達這層意思。“勞動產(chǎn)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chǎn)階級生產(chǎn)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chǎn)階級生產(chǎn)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chǎn)類型”。?因而,無論是新馬克思閱讀學派還是開放馬克思主義,均努力去揭示了馬克思所分析的經(jīng)濟客觀性的“自然”外觀假象,以及將傳統(tǒng)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發(fā)展為對經(jīng)濟范疇(形式) 的客觀性的批判,社會批判理論在開放馬克思主義的手里轉(zhuǎn)化為對經(jīng)濟形式的批判和政治形式的批判,被確立為“形式分析”的社會批判理論。
從形式分析的視角表面看來,有很強的理論誘導性,在馬克思的文本中也能夠找到相應的文本給予相應支撐。問題可能還不在這里,而是在于我們究竟使用什么樣的方法去理解形式本身。表面上看,開放馬克思主義者霍洛威比新馬克思閱讀學派從交換抽象建構其“形式規(guī)定”高明的地方在于,它已經(jīng)開始進入到勞動的層面。但是,霍洛威根本沒有進入到生產(chǎn)領域中的剩余價值生產(chǎn)邏輯。他認為馬克思把“勞動的雙重性”置于了政治經(jīng)濟學的批判的中心,“勞動的雙重性” 是指有用或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之間的區(qū)別。從交換的角度來看,從價值觀念的角度來看,衡量勞動唯一的東西是數(shù)量,而不是其質(zhì)量或特性。產(chǎn)生價值的勞動不是有用的具體勞動,而是抽象勞動,從具體特征的抽象中看到的勞動。因而,在任何社會中都存在有用的或具體的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或更一般地說,商品生產(chǎn)社會),它獲得了一種特定的社會形式,即抽象勞動的形式。?這里很明顯,霍洛維并沒有真正將勞動置放到特定的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之中去分析抽象勞動及其分析形式產(chǎn)生的根由。他和新馬克思閱讀學派一樣,借助于交換去理解抽象勞動的形成,“交換的過程(市場的運作)強加了一種抽象,這種抽象在實施具體勞動的方式上反彈。”?這種不停地抽象,從而獲得自主性,成為一種外在于我們的異己力量。在這個意義上,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成為了霍洛威建構其批判理論的出發(fā)點,“勞動(或行動)的兩個方面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非同一性,不迎合,活生生的對立性的關系:在抽象勞動和具體行動之間的不斷的活生生的對抗。”?那么,這種分析的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呢?
對于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而言,抽象勞動不是對具體勞動的一種理論的抽象,而是一種現(xiàn)實的抽象。值得注意的是,當代西方左翼也喜歡使用現(xiàn)實抽象這個概念,他們和霍洛威一樣都最終將現(xiàn)實抽象的生成機制交給了交換領域加以裁定。譬如,海因里希雖然認識到價值對象性并非是物固有的屬性,但是認為,“建立其這種對象性的價值實體,不是來自單個的商品,而是只能共同地存在于商品交換中。”?那么,問題的關鍵已經(jīng)非常清楚了,就是價值對象性到底是在生產(chǎn)領域還是在交換領域中決定的? 回到這個問題之前就要問一個基本的問題,是不是存在一個能夠脫離生產(chǎn)而獨立自主的交換領域。(a)“表現(xiàn)為”存在。這是在一般消費品的意義上的相互交換,“當產(chǎn)品直接為了消費而交換的時候,交換才表現(xiàn)為獨立于生產(chǎn)之旁,與生產(chǎn)漠不相關”;?(b)不存在。譬如,“在生產(chǎn)本身中發(fā)生的各種活動和各種能力的交換,直接屬于生產(chǎn),并且從本質(zhì)上組成生產(chǎn)”,作為產(chǎn)品交,“是用來制造供直接消費品的成品的手段,在這個限度內(nèi),交換本身是包含在生產(chǎn)之中的行為”;“實業(yè)家之間的交換,不僅從它的組織方面看完全決定于生產(chǎn),而且本身也是生產(chǎn)活動。”?即使對于(a)來說,實質(zhì)上,交換及其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以分工、私人生產(chǎn)、生產(chǎn)結構所決定的,因而只是“表現(xiàn)為”不存在。那么,西方左翼為什么要反復地“交換抽象”的“自在性”視角,同時片面地將資本主義社會歸因到抽象勞動的抽象性原因中? 他們不懂得生產(chǎn)與交換之間的關系嗎?筆者認為,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理論接口,那就是他們在人們經(jīng)驗意義上的日常生活的交換與“資本與勞動”這種特定生產(chǎn)方式下的交換之間造成了混亂,從而造成對“資本與勞動”之間真實生產(chǎn)機制的遮蔽,但是,我們知道,正是因為“資本與勞動”的交換是以私有財產(chǎn)制度為前提才可能產(chǎn)生的交換。這一遮蔽并沒有能夠阻礙其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譬如,通過交換抽象的過程,展開對現(xiàn)代社會的同一性權力機制的批判,而這一批判正好對接到福柯等人意義上的現(xiàn)代資本主義批判。換句話說,資本主義批判完全不需要朝向私有財產(chǎn)制度,這便是新馬克思閱讀學派或者開放馬克思主義學派,雖然在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的意義上去討論經(jīng)濟領域的交換生活,但是,不會觸及到私有財產(chǎn)制度的根本原因。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在 《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III.資本章]的“資本和勞動的交換”中看到馬克思對混亂使用“交換”的批判。在資本與勞動的交換中,實質(zhì)上存在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 一個是一般商品交換的意義上的勞資交換,即“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勞動,即作為商品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樣也有價格的使用價值,同資本出讓給他的一定數(shù)額的交換價值,即一定數(shù)額的貨幣相交換”,這個交換“完全屬于普通的流通領域的范疇”;資本與勞動的交換的特殊性質(zhì)發(fā)生在第二個方面,“這種勞動是創(chuàng)造價值的活動,是生產(chǎn)勞動; 也就是說,資本家換來這樣一種生產(chǎn)力,這種生產(chǎn)力使資本得以保存和倍增,從而變成了資本的生產(chǎn)力和再生產(chǎn)力”,如果說這也是交換,那純粹的刻意的“濫用字眼”,“它本質(zhì)上是另一種范疇”。?這種混同還會造成一個結果,那就是無法找尋到真正的資本主義的“革命主體”,譬如霍洛威最后退回到一個超越了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的“自我”,“一旦為我們自身、我們自身的思想、我們自身的安排創(chuàng)造一個統(tǒng)治結構,就真的沒有出路了,我認為,重要的是,從能夠打破這些結構的力量開始”,“重要的就是從我們自己開始”,?而不是認為只要拒絕為資本服務便可以停止制造資本主義。其實,資本對勞動的占有所形成的價值增殖過程,也只是因為這一勞動本身是處于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條件之下。因此,不是去拒絕抽象勞動,而是要抵抗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也正是這一關系導致了資本與勞動的分離,產(chǎn)生了資產(chǎn)階級社會分裂為對立的階級,所以,私有財產(chǎn)批判與無產(chǎn)階級自我的解放是一致的,共同構成從資本主義生產(chǎn)過程的內(nèi)在矛盾展開對資本主義的本質(zhì)性批判。
注釋:
①曹衛(wèi)東編選:《霍克海默集》,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198頁。
②T.W.Adorno,Can One Live after Auschwitz?A Philosophical Reade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93.
③Christoph G?dde,Theodor W.Adorno und Alfred Sohn-Rethel : Briefwechsel 1936-1969,Edition Text Kritik,1991.s112.
④齊澤克:《意識形態(tài)的崇高客體》,季廣茂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頁。
⑤普殊同:《時間、勞動與社會統(tǒng)治》,康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45~146頁。
⑥??Ingo Elbe,Marx im Westen: Die neue Marx-Lektüre in der Bundesrepublik seit 1965,De Gruyter,2012.ss32~33、68、74.
⑦Werner Bonefeld,Richard Gunn,Kosmas Psychopedis,Open Marxism,Volume 1: Dialectics and History,Pluto Press,1992.p,xviii.
⑧孫亮:《西方左翼對〈資本論〉語境中“價值形式”的兩種闡釋》,《山東社會科學》2021年第5 期。
⑨??Mario Sch?bel,Is Open Marxism an Offspring of the Frankfurt School?,Ana Cecilia Dinerstein,Alfonso García Vela,Edith González and John Holloway,Open Marxism,Volume 4:Against a Closing World,Pluto Press,2020.p,77、77、79.
⑩???John Holloway,In,against,and beyond capitalsim,kairos:PM press,2006.P.1、2、3、30.
???米夏埃爾·海因里希:《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 馬克思〈資本論〉導讀》,張義修、房譽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37、37頁。
?????John Holloway,Crack capitalism,Kairos:pluto press.2010.p.95、208、92、92、98.
??John Holloway,We Are the Crisis of Capital:A John Holloway Reader,PM Press,p.14、100~101.
?克里斯多夫·約翰·亞瑟:《新辯證法與馬克思的〈資本論〉》,高飛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頁。
?赫伯特·馬爾庫塞:《馬克思主義、革命與烏托邦》,高海青等譯,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41頁。
?斯蒂芬·埃里克·布朗納:《批判理論》,孫晨旭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88頁。
?Beverley Best,Werner Bonefeld,and Chris O'Kane(eds),The SAGE handbook of 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theory,California : SAGE Publications,2018,p368.
????John Holloway,F(xiàn)ernando Matamoros and Sergio Tischler (eds),Negativity and Revolution: Adorno and Political Activism,London:Pluto Press,2009.p12、15、12、7.
????阿多諾:《否定的辯證法》,張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5、127、3、5頁。
?阿爾伯特·托斯卡諾、杰夫·金科:《“絕對” 的制圖學》,張艷譯,長江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39頁。
?索恩·雷特爾:《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謝永康、侯振武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76頁。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0、232~2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