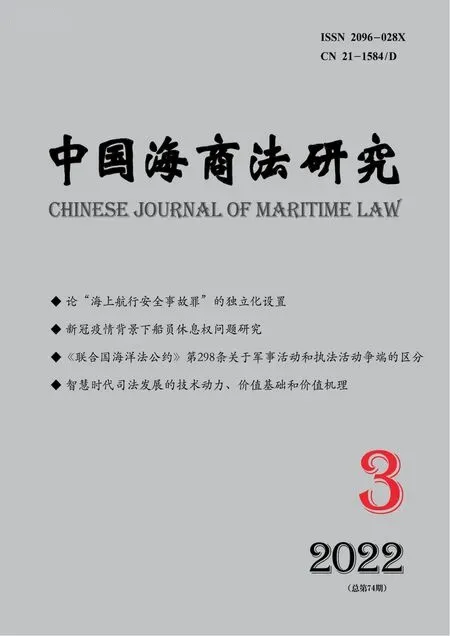《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8條關于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爭端的區分
孔令杰,韓 茜
(武漢大學 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湖北 武漢 430072)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簡稱《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的可適用性問題在近年發生的幾起案件中成為了國際海洋法法庭和《公約》附件七仲裁庭裁定自身(初步)管轄權需要解決的焦點問題。這些案件包括“南海仲裁案”(1)在2013年菲律賓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中,由于中國在2006年通過聲明排除了關于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的爭端,仲裁庭必須確定菲方提起的第12項和第14項訴求所反映的爭端是否屬于該條所指的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參見PCA: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29 October 2015),paras. 409,411。、“黑海、亞速海和刻赤海峽沿海國權利案”(簡稱“烏克蘭訴俄羅斯案”)(2)在2016年烏克蘭提起的《公約》附件七仲裁程序中,俄羅斯主張烏克蘭第(a)、(b)、(d)、(e)、(f)、(g)、(h)、(i)、(m)、(q)、(r)項訴求反映了“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仲裁庭審查了以上訴求中被控訴違反《公約》的活動的性質。參見PCA:Dispute Concerning Coastal State Rights in the Black Sea,Sea of Azov,and Kerch Strait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Coastal State Right),Award Concerning the Preliminary Objectio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1 February 2020) (2020 Award),paras. 8,311,336-340。、“關于扣押烏克蘭三艘軍艦案”(簡稱“刻赤海峽案”)(3)在烏克蘭于2019年向國際海洋法法庭提起的臨時措施程序中,根據《公約》第290條第5款的規定,法庭在作出關于臨時措施的命令前必須先裁定自身對案件具有初步管轄權。參見ITLOS: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Request for the Prescrip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Order (25 May 2019),para. 1。及“關于拘留烏克蘭軍艦及船員案”(4)在2019年烏克蘭提起的《公約》附件七仲裁程序中,俄羅斯提出初步反對,認為本案爭端關涉軍事活動。參見PCA:Disput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and Servicemen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Preliminary Objectio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4 August 2020),paras. 24-74。。第298條是《公約》第十五部分第三節中的一個條款,其規定締約方可通過書面聲明,對于該條第1款所列明的爭端的一類或一類以上,不接受第十五部分第二節規定的一種或一種以上的有拘束力裁判的強制程序。其中,第298條第1款(b)項規定了關于如下兩類活動的爭端:“軍事活動,包括從事非商業服務的政府船只和飛機的軍事活動的爭端”(簡稱“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以及“根據第297條第2和第3款不屬法院或法庭管轄的關于行使主權權利或管轄權的法律執行活動的爭端”(簡稱“關于執法活動的爭端”)。迄今共有28個《公約》締約國根據第298條第1款(b)項作出聲明,排除了兩類爭端或其中的一種爭端(5)阿爾及利亞、阿根廷、白俄羅斯、佛得角、加拿大、智利、中國、古巴、丹麥、厄瓜多爾、埃及、法國、希臘、幾內亞比紹、墨西哥、尼加拉瓜、挪威、葡萄牙、韓國、俄羅斯、沙特阿拉伯、斯洛文尼亞、泰國、突尼斯、英國排除了“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和“關于執法活動的爭端”,多哥、烏克蘭僅排除“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烏拉圭僅排除關于執法活動的爭端。參見United Nations Oceans and Law of the Sea:Declarations Made upon Signature,Ratification,Accession or Succession or Anytime Thereafter,訪問網址: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convention_declarations.htm。。由此,如果某案件所涉爭端被定性為第298條第1款(b)項所指的關于軍事活動或執法活動的爭端,則第287條規定的任何法院或法庭對案件或某訴求便無管轄權。
隨著各國越來越頻繁地以協作和綜合的方式使用海軍和執法力量來執行各種海上任務,海上軍事活動與執法活動之間的界限就變得越來越模糊(6)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 64。。然而,《公約》本身并未明確定義或列明“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也沒有規定區分二者的規則、標準或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作出的“刻赤海峽案”關于臨時措施的命令中,國際海洋法法庭首次提出了區分《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所指的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的一般方法,即“以客觀評價有關活動的性質為主,同時考慮個案中的相關情況”(7)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 66。。法庭還強調不能單憑活動所涉船只和人員的性質、當事國對活動性質的認定等來確定活動的性質(8)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s. 64-65。,并指出軍艦通行行為自身不構成軍事活動,認為俄羅斯在抓扣過程中使用武力的行為屬于在執法活動場景下的使用武力的行為(9)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s. 68-73。。針對法庭關于《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的解釋和適用問題,本案共有四位法官發表了反對意見或單獨意見,該案所涉的海洋法問題也備受國際法學界關注。其中,克洛德欽法官(Judge Kolodkin)完全不同意法庭對《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的解釋和適用。他認為:“一國軍艦在海上的任何活動均具有軍事屬性,烏克蘭軍艦在刻赤海峽的通行行為也不例外。”[1]高之國法官則認為:“法庭對軍事活動例外的解釋提高了第298條第1款(b)項的適用門檻,可能造成各國為了達到該門檻而加大力度部署海上武裝力量,從而導致沖突升級。”[2]石井由梨香(Yurika Ishii)教授認為:“法庭對軍事活動范圍的解釋相當狹隘,從而降低了確立管轄權的標準。”[3]克拉斯卡(James Kraska)教授甚至警告:“法庭的做法實際上縮小了軍事活動的例外。”[4]在高健軍教授看來:“考慮到雙方在‘刻赤海峽事件’發生前后的緊張關系、事發海域的爭議性質,以及俄羅斯的行為涉及對外國軍用船舶使用武力,其活動應屬于軍事活動。”[5]還有部分學者和法官指出,該案可能是關于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的混合爭端(10)參見Shi Xin-xiang,Chang Yen-Chiang:Order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in Ukraine versus Russia and Mixed Disputes concerning Military Activities,發表于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2020年第2期,第278,288-293頁;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Gao,para. 50;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Lucky,para. 21。,而且有關活動的性質可以隨著沖突的升級發生改變,從執法活動轉變成軍事活動(11)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Gao,paras. 25,34,37;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Kolodkin,para. 21。。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在2006年依照《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作出聲明(12)2006年8月25日,中國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書面聲明,對于《公約》第298條第1款第(a)、(b)和(c)項所述的任何涉及海洋劃界、領土主權、軍事活動等的爭端,不接受《公約》第十五部分第二節規定的任何國際司法或仲裁管轄。,對該條規定的“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和“關于執法活動的爭端”皆不接受第十五部分第二節規定的任何一種強制程序。2021年2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警法》規定(13)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警法》第2條、第12條、第83條。,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海警部隊統一履行海上維權執法職責,海警機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警察法》等法律法規及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執行防衛作戰等任務。[6]因此,中國有必要明確本條所指兩類爭端的內涵和外延,并密切關注關于認定和區分兩類爭端的國際法律實踐的發展。
基于以上認識,依照條約解釋之通則,筆者將討論第298條第1款(b)項中有關用語的通常含義,為區分關于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的爭端提供文本依據。針對國際海洋法法庭在“刻赤海峽案”中所提出的區分兩類活動的一般方法,筆者將分別討論“客觀評價有關活動的性質”及“在個案中考慮的相關情況”的相關問題。
一、第298條第1款(b)項中的有關用語:區分關于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爭端的法律依據
從《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的文本來看,“關于”(concerning)、“軍事活動”(military activities)、“執法活動”(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爭端”(disputes)四個用語共同限定了本條所指的可由當事國通過聲明排除的爭端類型。其中,“關于”是兩類活動與“爭端”之間的連接詞,它反映并界定了二者之間的關系。四個用語在本條中的含義往往是爭端當事國在個案中爭議的焦點,從條約解釋的角度而言,有必要先來討論它們在《公約》特別是第298條中的通常含義。
(一)第298條第1款(b)項中的“關于……爭端”
在國際法上,“爭端”特別是主權國家之間的國際爭端有相對確定的內涵和外延(14)參見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29 October 2015),para. 148。,一般被定義為“雙方在法律和事實上存在不同意見,形成法律觀點和利益的對抗”(15)參見Mavrommatis Palestine Concessions,Judgment of Jurisdiction (30 August 1924),PCIJ Series A,No. 2,p. 6 at p. 11。。同時,關于認定爭端是否存在、爭端的主題事項、爭端的性質等問題,國際法上亦形成了較為豐富、一致和確定的國際判例(16)如“核試驗案”(新西蘭訴法國)、“漁業管轄權案”(西班牙訴加拿大)、“美國駐德黑蘭外交和領事人員案”(美國訴伊朗)等。參見Nuclear Tests (New Zealand v. France),Judgment (20 December 1974),I.C.J. Reports 1974,p. 457 at p. 466,para. 30;Fisheries Jurisdiction (Spain v. Canada),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4 December 1998),I.C.J. Reports 1998,p. 432 at pp. 448-449,paras. 30-32;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Tehran (United States v. Iran),Judgment, I.C.J. Reports 1980,p. 3 at pp. 19-20,para. 36。。因此,《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中的“爭端”應依此進行解釋。從上下文來看,“爭端”是《公約》第十五部分中多個條款的共同用語,該詞在這些條款中應被賦予相同的含義(17)參見《公約》第281-283條、第286-288條、第297-298條等。。更具體地說,第298條第1款(b)項所指的“爭端”必然是第一節和第二節所指的“有關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的任何爭端”(18)參見《公約》第279-283條、第286條、第288條等。在“南海仲裁案”和“烏克蘭訴俄羅斯案”中,仲裁庭均通過優先處理該案爭端是否涉及主權問題,來判斷該爭端是否屬于《公約》第286條中的“有關本公約解釋和適用的爭端”,然后再來處理其他管轄權事項,如有關第298條第1款(b)項軍事活動的例外。,且必須屬于本條所指的關于軍事活動或執法活動的爭端,否則就根本不存在締約方通過聲明排除的必要。
在有關成案中,對第298條第1款(b)項中“關于”或“關于……爭端”的解釋是當事國爭議的焦點。當事國往往采取于己有利的做法,選擇對其作較為寬松或限縮的解讀,而國際法庭的解讀也不盡相同。例如,在“烏克蘭訴俄羅斯案”中,俄羅斯以其在克里米亞的軍事活動與訴求中的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為由,主張爭端屬于《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中所指的“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19)參見Coastal State Rights,Preliminary Objectio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paras. 140,144,148。。相反,烏克蘭則將該條中的“關于”(concerning)解釋成“be about”或“in reference to”(20)參見Coastal State Rights,Written Observations and Submissions of Ukraine on Jurisdiction,para. 125。,并進而主張只有在訴求中違反《公約》的具體行為本身構成軍事活動時,才得援引第298條規定的例外情況。那么,應當如何解釋第298條第1款(b)項中的“關于……爭端”呢?依條約解釋之通則(21)參見《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和相關國際判例,筆者認為,對“關于”這一術語,既不能解釋得過于寬泛,也不能過于狹隘,必須確保“爭端”與“軍事活動”或“執法活動”之間有適當的聯系,才足以從爭端主題事項的角度將其定性為本項意義上的“關于”軍事活動或執法活動的爭端。
首先,“關于”(concerning)一詞具有有關(about sth)、涉及(involving sth)、有關聯(relating to)等的意思,[7]433,[8]表示事物之間存在關聯。[9]結合《公約》上下文來看,第298條第1款(b)項使用了“關于”一詞,第208條、第214條、第232條、第263條和第297條等則使用了“由……引起”(arising from,arising out of)和“引起或與之有關”(aris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等外延看似更為寬泛的用語,原則上不得給予它們相同的含義。在“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在解釋“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時就直接指出,該案的相關問題是“爭端本身是否涉及軍事活動。如果原告起訴的爭端并不涉及軍事活動,而被告在隨后的審判程序中對該爭端開始動用軍事力量,則第298條第1款(b)項不適用”(22)參見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Award (12 July 2016),para. 1158。。同樣,在“烏克蘭訴俄羅斯案”中,仲裁庭更是直接駁回了俄羅斯以克里米亞軍事活動與訴求中的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為由將爭端認定為“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的主張。在這一點上,仲裁庭特別強調“軍事活動若與爭端中的活動僅存在因果關系和歷史上的聯系,這并不能觸發第298條第1款(b)項的適用”(23)參見Coastal State Right,2020 Award,para. 330。。可見,在對“關于”不得作過于寬泛的解釋這一點上,似乎已經形成了較為一致的國際法律實踐。
其次,《公約》第十五部分中第286條、第287條、第288條、第297條第2款(a)項和第297條第3款(a)項亦使用了“關于”一詞,應給予第298條第1款(b)項與上述條款中的同一用語相同的含義。因此,國際法庭在有關案件中對《公約》第十五部分上述條款中“關于”一詞的解釋具有直接的參考價值。在“‘路易莎’號案”中,國際海洋法法庭認為圣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根據第287條所作聲明中的“關于”一詞不僅使聲明包含具有“逮捕”或“扣押”字眼的條款,它還將整個聲明的適用“擴展”至與“逮捕”“扣押”船只“有關聯”(have a bearing on)的《公約》的任何條文(24)參見The M/V “Louisa” Case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v. Kingdom of Spain),Judgment (28 May 2013),ITLOS Reports 2013,p.4 at p.31,para. 83。。在“加納—科特迪瓦劃界案”中,國際海洋法法庭特別分庭認為,雙方“關于它們在大西洋中海洋邊界劃界的爭端”的特別協定中的“關于”一詞可以理解成涵蓋不屬于劃界的一部分但確與劃界緊密相關的(closely related)問題的爭端(25)參見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Ghana and Cte d’Ivoire in the Atlantic Ocean,Judgment (23 September 2017),para. 548。。在“愛琴海大陸架案”中,希臘曾試圖將“A concerning B”解釋成“A were likely to arise out of B”來縮小A的范圍,以擴大國際法院的管轄權,但國際法院駁回了該抗辯意見(26)在“愛琴海大陸架案”中,希臘在試圖將“關于特定案件或主題事項明確的爭端,如領土地位,或屬于明確界定類別的爭端”解釋為“可能由鄰國對現有解決方案不滿而提出領土主張而引發的爭端”。參見Aegean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 (Greece v. Turkey),Judgment (19 December 1978),I.C.J. Reports 1978,p. 3 at p. 23,para. 55;p. 29,para.72;p. 36,para. 86。。由此可見,國際法院和國際海洋法法庭并未對“A concerning B”表述中的“關于”作過于嚴苛的解釋,如認為A只能包含B本身,也沒有作過于寬泛的解釋,如認為A包含與B相關的任何內容,而是認為A與B之間存在適當的聯系。在這一點上,“烏克蘭訴俄羅斯案”仲裁庭的做法尤為值得關注,它認為《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中“關于”一詞將軍事例外的排除事項限定為“主題事項是軍事活動”(subject matter is military activities)的爭端(27)參見Coastal State Right,2020 Award,para. 330。,該解釋與國際法庭在上述案件中的解讀并不一致,明顯抬高了啟動軍事例外條款的門檻。
最后,對第298條第1款(b)項中的“關于”一詞作過于寬泛或狹隘的解釋均不符合《公約》的目的與宗旨。第298條第1款(b)項的締約過程表明,“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之所以能被強制爭端解決程序排除,主要是因為有關國家認為軍事秘密是不能被公開的,軍艦活動不得適用國際司法程序。[10]從《公約》文本來看,直接規范軍艦活動的條文數量有限,且軍艦行使緊追權或登臨權的行為又通常被視為執法活動。[11]63,[12]因此,如果將第298條第1款(b)項所指的“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限定為主題事項為軍事活動的爭端,這意味著爭端必須同時構成關于公約解釋和適用的爭端及主題事項屬于軍事活動的爭端才得觸發軍事活動的例外情形,但這種情形將極為有限,明顯不符合現實情況中海軍活動的多樣性及保有軍事用途的靈活性的特點,[13],[14]285-286,291-292也不符合該條的締約目的。同樣,若對“關于”一詞作過于寬泛的解釋可能導致另一種極端情況,即只要案件中存在軍事活動,不論它與爭端本身存在何種聯系,都足以觸發第298條第1款(b)項的適用,這也不符合《公約》作為一攬子協議與《公約》第十五部分第二節設立導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強制程序的宗旨。[15]1846-1847總之,結合公約的文本及相關國際判例,筆者認為,某個爭端是否被認定為《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所指的“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或“關于執法活動的爭端”主要取決于此爭端與有關活動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既不能過于松散,如僅存在因果關系或歷史聯系,也不得要求爭端與有關活動之間存在過于密切的聯系以至于達到二者完全等同的程度。
(二)第298條第1款(b)項中的“軍事活動”
第298條第1款(b)項是《公約》中唯一使用“軍事活動”這一用語的條款,它既沒有定義“軍事活動”,也沒有列舉典型的軍事活動。“軍事”(military)一般是指“軍事的”“軍隊的”“戰爭的”“與武裝力量、戰爭有關的”;[7]1361,[16-17]“軍事活動”(military activity)則是指與以上術語有關的活動。典型的軍事活動不僅包括明顯屬于武裝侵略的行為,如一國武裝部隊侵入攻擊另一國領土,封鎖另一國家的港口、海岸,攻擊另一國陸、海、空軍或商船等的行為(28)參見Definition of Aggression,A/Res/3314 (14 December 1974)。,還可包括安理會在多項決議中提及的如“敵對行為”“軍事占領”“軍事報復”“軍事征服”等行為(29)參見The Indonesian Question,SC/Res/27 (1 August 1947);The Indonesian Question,SC/Res/30 (25 August 1947);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SC/Res/248 (24 March 1968);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SC/Res/252 (21 May 1968)。。由于《公約》規范的是海上活動,因而第298條第1款(b)項中的軍事活動主要是指海上軍事活動(30)博克賽克(Boleslaw Adam Boczek)還指出,專屬經濟區內的海上軍事活動可包括航行、飛越、戰略及軍事情況的收集、部署浮標和其他導航裝置、埋設常規武器(如地雷)及建造導彈發射設施等,參見Boleslaw Adam Boczek:Peacetime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Third Countries,發表于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1998年第6期,第447-448頁。,包括武器試驗、情報收集、測試和使用船只及設備設施、部隊訓練、非武裝沖突、武裝沖突等。[11]43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軍艦、軍機等軍事力量,第298條第1款(b)項還明確將從事非商業服務的政府船只和飛機納入實施軍事活動的主體范疇。如果以上主體實施的活動違反《公約》某條款下的義務,則該爭端就可能構成“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因此,在適用《公約》中涉及軍艦、軍機及從事非商業服務的政府船只和飛機的條款時,應提示爭端可能存在某種軍事活動,如第20條、第30條、第31條、第32條、第95條、第96條。同時,在適用涉及以上主體在某水域中享有某種活動權利的條款時也可能涉及軍事活動,如關于領海無害通過的第17條、第18條、第19條、第45條、第52條以及關于在海峽、群島水域過境通行的第38條、第39條、第40條、第53條、第54條等條文。杰西法官(Judge Jesus)在“刻赤海峽案”的單獨意見中指出:“《公約》第19條為檢驗烏克蘭軍艦的通行行為是否構成軍事活動提供了法律依據。”[18]他認為,雖然《公約》沒有給出“軍事活動”的定義,但卻列明了具有軍事性質的一些具體活動,比如《公約》第19條第2款(a)項至(f)項中提到的活動便是具有軍事性的,如果烏克蘭軍艦因為實施了這些行為而被捕,這表明事件涉及軍事活動(31)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Jesus,paras. 15-16。。
此外,有關國際法律實踐還表明,“軍事活動”往往具有某種軍事目的。例如,在剛果問題上,聯合國安理會授權聯合國秘書長“采取必要措施……向剛果政府提供必要的軍事援助”,這后來證明構成《聯合國憲章》第七章的行動(32)參見The Congo Question,SC/Res/143 (14 July 1960);Georges Abi-Saab:The United Nations Operation in the Congo 1960—1964,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年出版。。如此,若安理會根據《聯合國憲章》第42條,以支持軍事援助等活動(如盤旋、拋錨和起飛飛機等不屬于無害通過范圍的支持活動)為目的,要求其他國家開放沿海水域,則在此水域的“通行、通過”應被視為“軍事活動”。在“尼加拉瓜訴美國案”中,直升機從國際水域上的航母起飛為針對陸地(北圣胡安)的攻擊提供火力支援的行為同樣被國際法院視為“軍事活動”(33)參見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erits,Judgment (27 June 1986),I.C.J. Reports 1986,p.14 at p.48,para. 81。。在“石油平臺案”中,國際法院認為美國所主張的自衛行為亦具有“軍事活動”的性質,因為其攻擊目標需要是“合法的軍事目標”(34)參見Oil Platforms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udgment (6 November 2003),I.C.J. Reports 2003,p.161 at p. 186,para. 51。。可見,即便軍艦通行和通過行為本身可能并不構成“軍事活動”(35)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 68。,但當軍艦的通行和通過已遠超其航行本身且服務于某種特定的軍事目的時,可將其視為“軍事活動”(36)參見肖鋒:《對海軍“海上實際存在”國際法規則的理論探析——航行自由 VS 存在自由》,發表于《邊界與海洋研究》,2020年第6期。。
(三)第298條第1款(b)項中的“執法活動”
“執法活動”一般是指一國為了迫使有關行為主體遵守本國法律而采取的行動或強制措施。[19-20]從國際司法實踐來看,典型的海上執法活動包括緊追、登臨(37)“‘賽加’號案”“刻赤海峽案”等存在緊追、登臨的活動。、執法使用武力(38)“紅十字軍案”“‘賽加’號案”“刻赤海峽案”“烏克蘭訴俄羅斯案”等均存在執法使用武力的情況。、對海上設施的監管(39)“烏克蘭訴俄羅斯案”“圭亞那訴蘇里南案”涉及監管或驅逐海上石油平臺的情形。等。第298條第1款(b)項沒有定義或列舉“執法活動”,但《公約》中的其他條款卻使用了“執行法律”(enforcement of laws)(40)參見《公約》第73條。或“執行”(enforcement)(41)參見《公約》第212-222條。等用語。這些條款不僅列舉了一些執法活動(如第73條規定了為確保其依照本公約制定的法律和規章得到遵守所必要的措施),還規定了一些需要進行執法活動的情景(如第十二部分第六節規定的針對陸地、海底、“區域”內活動和傾倒等污染來源的執法)。
與“軍事活動”不同,第298條第1款(b)項中的“執法活動”還受到第297條第2款和第3款有關海洋科學研究和漁業爭端的限制,此條中的爭端僅限于根據第297條第2款和第3款規定不屬于法院或法庭管轄的爭端。[15]1930至于該條中“執法活動”發生的場景,需要依照第297條來理解。在“‘北極日出’號案”的管轄權裁決中,仲裁庭將第298條第1款(b)項中“根據第297條第2款和第3款不屬于法院或法庭管轄的關于行使主權權利或管轄權的法律執行活動的爭端”歸為如下幾類(42)參見PCA:The Arctic Sunrise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v. Russian Federation),Award on Jurisdiction (26 November 2014),para. 75。:一是由沿海國針對在其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上的海洋科學研究行使權利和斟酌決定權而引起的爭端;二是由沿海國作出暫停或停止某一海洋科學研究計劃的命令而引發的爭端;三是有關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生物資源的主權權利及其行使的爭端。
上述歸類對于國際法庭在未來認定第298條第1款(b)項中的“關于執法活動的爭端”具有重要的參照作用。
二、區分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的一般方法:客觀評價有關活動的性質
從上文對第298條第1款(b)項有關用語的解釋可見,判斷某爭端是否適用軍事活動、執法活動例外的關鍵是確定被指控違反《公約》的具體行為的性質。在“刻赤海峽案”中,國際海洋法法庭提出了認定活動性質的一般方法,強調必須“以客觀評價有關活動的性質為主”(43)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 66。。那么,何為有關活動?應當如何確定哪些具體的活動構成爭端的有關活動?如何客觀評價有關活動的性質?
(一)有關活動
確定爭端所涉的“有關活動”往往并非難事,原告一般會主張被告因為實施了某些特定行為,或本應履行而沒有履行某些義務,導致該國違反《公約》中的某些條款。這些被指控違反《公約》的特定行為一般就是國際海洋法法庭在“刻赤海峽案”中提及的“有關活動”。值得注意的是,法庭使用的是“活動”一詞的復數形式(activities in question),這至少意味著在法庭看來該案中的“有關活動”可能不只是某一方的某一個特定活動,如僅指俄羅斯扣押烏克蘭軍艦和逮捕軍人的活動(44)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 67。。
事實上,法庭還考察了與俄羅斯逮捕扣押烏克蘭軍艦和軍人密切相關的雙方的行為,回顧了整個事件的發生過程。在這一點上,法庭強調并著重考察了三個“特別相關”(particularly relevant)的情況:“烏克蘭軍艦的通行”,這是包括抓扣在內的雙方全部后續活動的起點;“雙方對刻赤海峽通行制度理解不同而引發的互動”,這是雙方摩擦的起因,也是導致本案所涉爭端發生的重要原因;“使用武力”的活動,其為俄羅斯在抓扣過程中采取的強制措施(45)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s. 68-73。。可見,以上三個活動與俄羅斯抓扣行為之間均存在非常緊密的聯系,這也說明“有關活動”不僅包括違反《公約》的特定具體行為,還包括與它存在密切聯系且可能構成事件起因、經過、結果的其他活動。
從“有關活動”的行為主體來看,需要考慮的“有關活動”不僅包括被告的行為,特別是原告指控被告違反《公約》的行為,還應該包括原告的行為及雙方行為的互動。除了“刻赤海峽案”之外,“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在評價中方在仁愛礁阻止菲方輪換和補給這一活動性質時(46)2014年12月7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于菲律賓共和國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轄權問題的立場文件》第58段援引中國根據《公約》第298條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的聲明,提出“對于涉及海域劃界、歷史性海灣或所有權、軍事和執法活動……等爭端,中國政府不接受《公約》第十五部分第二節下的任何強制爭端解決程序,包括強制仲裁”。中國政府提出,“即使仲裁事項涉及有關《公約》解釋或適用的問題,也構成海域劃界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已被中國2006年聲明所排除,不得提交仲裁”。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件并未提及《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的可適用性問題,也未主張菲方提出的任何一項訴求所反映的爭端構成本條款所指的“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或“關于執法活動的爭端”。,同樣注意到的是中菲雙方的活動(47)參見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Award (12 July 2016),paras. 1159-1161。,并據此認為雙方實質上形成了一種軍事對峙局勢,構成《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意義上的軍事活動的例外。
可見,判斷爭端性質的“有關活動”不僅包括原告聲稱被告違反《公約》從而形成關于《公約》解釋和適用的爭端的特定行為,還包括與該關鍵活動密切相關的其他活動。這往往既包括原告的活動,也包括被告的活動,既涉及引發爭端的活動,也涉及促成爭端形成、發展和清晰化的有關活動。
(二)爭端的主題事項與有關活動的性質
對國際法庭而言,裁定《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的可適用性至少涉及兩個問題或需要先后處理的兩個步驟:一是認定案件所涉的爭端屬于關于《公約》解釋或適用的爭端,即確定爭端的主題事項;二是斷定該爭端是否屬于第298條第1款(b)項所指的“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或“關于執法活動的爭端”,即評價爭端所涉“有關活動”的性質。確定爭端的主題事項與評價爭端所涉有關活動的性質是兩個不同的事項,但二者之間存在不容忽視的重要聯系。其中,爭端的主題事項往往是確定爭端所涉“有關活動”的依據。例如,“刻赤海峽案”所涉爭端的主題事項是《公約》第32條、第58條、第95條和第96條規定的軍艦豁免權問題(48)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 67。。該爭端是由俄羅斯的逮捕扣押行為及后續司法審判活動所引起的,法庭緊緊圍繞逮捕扣押事件的起因、經過和結果選取了爭端的“有關活動”。同樣,在“烏克蘭訴俄羅斯案”中,仲裁庭駁回了俄羅斯的一項訴求,即克里米亞的軍事活動導致有關爭端應適用軍事活動的例外的訴求。仲裁庭強調,克里米亞事件根本不是該案所涉爭端的一部分,它只是爭端的背景(49)參見Coastal State Right,2020 Award,paras. 329,331。,烏克蘭所提相關訴求的主題事項涉及的是俄羅斯是否侵犯了烏克蘭依照《公約》享有的海洋權利的問題。具體而言,克里米亞軍事活動不是導致烏克蘭訴求所涉俄羅斯行為的直接原因,它也不在烏克蘭訴求所依據的相關事實范圍之內。總之,應該圍繞爭端的主題事項來確定爭端的“有關活動”,這些活動應該構成訴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至少與之存在密切的聯系。
值得注意的是,案情復雜的案件往往涉及多個活動,這些活動存在內在聯系和先后關系,進而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事件。當事國可能基于這些活動或其中的某些活動提出主題事項不同的訴求。此時,應考慮與各訴求中的行為存在密切關系的“有關活動”,因為它們可能反映案件所涉的潛在爭端或核心爭端,幫助判斷案件所涉的具體爭端是否屬于軍事活動或執法活動的例外情形。“刻赤海峽案”所反映的主題事項是關于《公約》豁免權的問題,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很難認定該主題事項具有軍事屬性。在這一點上,法庭并沒有局限于此,而是考慮了雙方的潛在爭端(烏克蘭軍艦的通行行為)和核心爭端(雙方對通行制度的不同理解)(50)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s. 68-73。。
(三)客觀評價有關活動的性質
在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的區分問題上,國際海洋法法庭特別強調要客觀評價有關活動的性質,這一要求與關于認定爭端是否存在及其性質的國際判例是一致的。例如,國際法院在“核試驗案”中提出,要“分離本案中的真實問題,并查明申訴的客體”,在“西班牙訴加拿大漁業管轄權案”中,法院則“通過審查當事國雙方的立場,客觀地裁定當事雙方之間的爭端”(51)參見Nuclear Tests (New Zealand v. France),Judgment (20 December 1974),I.C.J. Reports 1974,p. 457 at p. 466,para. 30;Fisheries Jurisdiction (Spain v. Canada),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4 December 1998),I.C.J. Reports 1998,p. 432 at p. 448,para. 30。。事實上,爭端是否存在、爭端的主題事項是什么、爭端是否屬于關于《公約》解釋和適用的爭端以及爭端是否為關于軍事活動或執法活動的爭端等事項,都需要依據確鑿的證據作出客觀的認定。
客觀認定有關活動的性質的一個基本要求是不得單憑當事國自身的主觀定性來判斷活動的性質,如國際海洋法法庭明確指出的,當事國的態度往往是主觀的和利己的,與實際情況根本不符(52)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 65。。在這一點上必須指出的是,在“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僅以中國對于有關活動性質的看法直接認定了菲律賓第12(a)-(b)項和第14(d)項訴求中所涉島礁建設活動的性質(53)參見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Award (12 July 2016),paras. 937-938,1028,1164。,這種武斷和錯誤的做法與國際海洋法法庭所強調的客觀認定有關活動性質的要求顯然是完全相悖的,也不符合關于客觀認定爭端是否存在、爭端的主題事項及其性質的國際判例。
客觀認定有關活動的性質還要求充分考察當事國雙方的活動,并依據確鑿的證據和事實來確定有關活動的性質。杰西法官在“刻赤海峽案”的單獨意見中指出,對于軍事活動的考察不應該僅圍繞俄羅斯逮捕扣押的行為,還應該考察烏克蘭軍艦的通行行為(54)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Jesus,para. 2。。雖然杰西法官認為烏克蘭軍艦的通行行為很有可能構成軍事活動,洛奇法官(Judge Lucky)注意到事件可能存在軍事和執法活動并存的情況,但他們均認可了法庭在臨時措施階段主要僅以俄羅斯的行為性質來決定案件是否觸發第298條第1款(b)項的適用的做法(55)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Jesus,paras. 3,20;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Lucky,para. 21。。因為法庭可依賴的證據非常有限(“Nikopol”號航行準備清單、烏克蘭海軍中將塔拉索夫的聲明、烏克蘭海軍軍方報告等)(56)參見Nikopol Small Armored Gunboat,Checklist for Readiness to Sail (09:00 Hours on 23 November 2018 to 18:00 Hours on 25 November 2018);Vice Admiral Tarasov Declaration;Ukrainian Navy Report。,且俄羅斯選擇不出庭,僅向法庭提交了“關于扣押烏克蘭三艘軍艦臨時措施的諒解備忘錄”。由此,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形下,國際海洋法法庭不能認定烏克蘭軍艦的活動構成軍事活動,而僅能依靠已有證據認定俄羅斯的逮捕扣押行為發生在執法活動的情境下(57)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Lucky,para. 12;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s. 69-70。。值得注意的是,法庭在該案中僅須依照《公約》第290條第5款裁定《公約》附件七仲裁庭是否對案件具有初步管轄權即可(58)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 36;ITLOS:ARA Libertad (Argentina v. Ghana),Provisional Measures,Order (15 December 2012),para. 60。,杰西法官和洛奇法官均表示判斷烏克蘭軍艦的通行行為是否構成軍事活動將是上述仲裁庭的職責(59)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Jesus,para. 20;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Lucky,para. 21。。
總之,客觀認定有關活動的性質要求裁斷者不能主觀臆斷,要客觀評價雙方的活動,并依據確鑿的證據和事實認定有關活動的性質。
三、區分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的重要手段:考慮個案中的相關情況
除了強調要客觀評價有關活動的性質,國際海洋法法庭還要求“考慮個案中的相關情況”(60)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 66。。在客觀評價過程中,根據爭端的主題事項找到與之特別相關的活動是至關重要的一步,而根據個案中的相關情況和因素認定有關活動的性質則是落實客觀評價的重要手段。那么,哪些情況構成特別相關的情況,應當如何考慮這些情況呢?
(一)個案中的相關情況
關于相關情況,國際海洋法法庭在“刻赤海峽案”的命令中使用了“個案中”的表述,強調應依個案的具體情況來判斷活動性質。
當案情相對簡單或僅需評價某一個特定活動的性質時,所考慮的相關情況應聚焦該活動本身。其中,活動的內容和目的往往是需要重點考量的因素。“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在評價中方在仁愛礁的活動性質時就考慮了雙方活動的內容和目的,并據此認為雙方實質上形成了一種軍事情勢(61)參見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Award (12 July 2016),para. 1161。。同樣,在“烏克蘭訴俄羅斯案”中,在內容方面,仲裁庭認為:拘留民用船只的船長并在其支付罰款后釋放的行為,屬于執法活動而非軍事活動;在石油平臺上站崗和監督行為本身也不構成軍事活動;而對烏克蘭船只的騷擾則主要包括危險接近、妨礙無線電通信及其他一般的違反安全和航行規則的行為,不能導致爭端涉及軍事活動(62)參見Coastal State Right,2020 Award,para. 338。。在目的方面,仲裁庭注意到俄羅斯授權油氣許可證的對象是民營商業公司,并在民事法律框架下管制該爭議區域的漁業資源開發。考慮到這個背景,仲裁庭認為所謂的強制力被直接用于維持石油開采和漁業發展等民事活動,并不導致爭端涉及軍事活動(63)參見Coastal State Right,2020 Award,para. 336。。在“刻赤海峽案”中,國際海洋法法庭也重點考察了案件的事實內容和證據能否支持俄羅斯主張的秘密入侵這一問題,最終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認定烏克蘭軍艦通行行為并不構成軍事活動(64)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 70。。
除了活動的內容和目的,傳統觀點多將行為主體因素作為軍事活動認定的唯一標準,強調行為主體的“軍事”性質。[21]也有學者和法官強調應考慮“刻赤海峽案”中俄羅斯使用武力的對象是烏克蘭的軍艦(65)參見高健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8條中的“軍事活動例外”——評國際海洋法法庭在“扣留三艘烏克蘭海軍船只案”中的臨時措施命令》,發表于《國際法研究》,2019年第6期;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Gao,para. 33。。然而,單憑主體因素來認定某活動的性質這一做法顯得越來越不合理,如國際海洋法法庭所注意到的,軍艦和執法船只傳統上扮演的角色的區別已變得相當模糊,各國使用兩種船只合作執行多種海上任務的情形并不罕見(66)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 64。。同樣,“烏克蘭訴俄羅斯案”中仲裁庭也指出,在石油平臺上站崗和監督經常由私人保安公司實施,俄羅斯軍方進行的水下考古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是與平民合作進行的,不能認定活動具有軍事性(67)參見Coastal State Right,2020 Award,paras. 338,340。。
在復雜的案件中,往往還需要考慮其他的相關情況。例如,在“刻赤海峽案”中,法庭考慮了三個特別相關的情況,即本案的潛在爭端、核心爭端及使用武力的場景(68)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s. 68-74。。雖然他們與該案的有關活動存在交織,但卻體現了該案極為特別的情形,因為并非每一個案件都存在爭端的主題事項之外的潛在爭端和核心爭端,也并非每一個案件均存在使用武力的情形。法庭最終在分別考察了以上相關情況的性質之后,認定該案逮捕扣押發生在執法活動的情境之下(69)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 75。。可見,以上特殊的相關情況對該案爭端性質的判斷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此外,法庭還考慮了俄羅斯后續的司法活動,認為“該行為進一步支持了逮捕扣押的執法屬性”(70)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 76。。雖然該司法審判活動本身并不構成該案的有關活動,但它有助于確認法庭基于其他三個特別相關的情況得出的結論。
有法官和學者指出,評價活動性質還應該考慮當事國的國際行為、官方立場和法律文書(71)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Gao,para. 30。、事發時兩國的政治關系及事發地的爭議屬性等因素(72)參見高健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8條中的“軍事活動例外”——評國際海洋法法庭在“扣留三艘烏克蘭海軍船只案”中的臨時措施命令》,發表于《國際法研究》,2019年第6期。。無容置疑,評價活動的性質時應該綜合考慮各個相關的情況和因素。“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僅憑當事國對活動性質的認定這一項因素便武斷認定了島礁建設活動的性質為民事而非軍事活動,這表明仲裁庭為了確立自身對菲律賓訴求所反映的某些爭端的管轄權而罔顧相關實際情況和客觀事實。
(二)使用武力
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都可能涉及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的情況,若存在使用武力的情況,區分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往往要結合使用武力的目的、主體、對象、手段、后果等因素來判斷使用武力的場景。
首先,使用武力的總體情勢是區分場景性質的關鍵所在。[22]“南海仲裁案”中,中菲雙方在仁愛礁形成了一種僵持局面。仲裁庭認為這實質上是一種軍事局勢,即一方的軍事力量與另一方的軍事和準軍事力量形成對抗的情勢(73)參見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Award (12 July 2016),para. 1161。。在“圭亞那訴蘇里南案”中,蘇里南要求鉆井平臺在12小時內撤離,否則后果自負(74)參見Arbitration between Guyana and Suriname,Guyana Memorial,Annex 175,176。。很明顯,蘇里南對平民威脅使用武力導致了事態的緊迫性及危險性,仲裁庭最終裁定蘇里南的行為“更像是一種軍事威脅行動,而非執法活動”(75)參見Arbitration between Guyana and Suriname,Award (17 September 2007),para. 445。。反觀“刻赤海峽案”,克洛德欽法官、高之國法官及克拉斯卡教授均質疑法庭根本沒有處理兩國是否存在武裝沖突這個問題(76)參見James Kraska:Did ITLOS Just Kill the Military Activities Exemption in Article 298?訪問網址:https://www.ejiltalk.org/did-itlos-just-kill-themilitary-activities-exemption-in-article-298。。克洛德欽法官更直接指出“‘刻赤海峽事件’是兩國武裝沖突的新事例”(77)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Kolodkin,para. 18。。克萊因(Natalie Klein)教授也認為“由武裝沖突引發的爭端,屬于軍事例外的范圍”。[14]285因此,當使用武力所呈現的情勢極有可能引發兩國間的武裝沖突時,該場景可認定為構成軍事活動。
其次,禁止或限制使用武力所適用的國際法規范是考量場景性質的依據。《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所指的武力一般僅指武裝力量。[23]若使用武力的事實行為構成《聯合國憲章》所禁止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那么有關活動很可能屬于軍事活動。如上所述,“圭亞那訴蘇里南案”中,仲裁庭正是注意到蘇里南向石油平臺威脅如不撤離后果自負這種武力威脅手段的危險性,因此裁定蘇里南的行為不僅構成《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所指的以武力相威脅,也更像是一種軍事威脅行動(78)參見Arbitration between Guyana and Suriname,Award (17 September 2007),para. 445。。相反,在“烏克蘭訴俄羅斯案”中,即便俄羅斯的確使用“武力”(physical force)阻礙了烏克蘭前往油田和漁區,然而仲裁庭強調執法力量通常被授予使用武器或強制措施的權利,但其行為并不會因此被視為軍事活動(79)參見Coastal State Right,2020 Award,para. 336。。同樣,“‘賽加’號案”和“刻赤海峽案”中也都涉及依照國際法上的一般原則使用武力的典型海上執法的情況。在“‘賽加’號案”中,幾內亞對“賽加”號的緊追活動并不滿足《公約》第111條所要求的連續性和發出停止信號后才可以開始的規定,且不分皂白的開槍還造成了重要設備的毀損和人員的重傷,構成過度使用武力的情形(80)參見The M/V “Saiga” (No. 2)Case,(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v. Guinea),Judgment (1 July 1999),ITLOS Reports 1999,p. 10 at pp. 59-61,63,paras. 147-148,152,158。。在“刻赤海峽案”中,國際海洋法法庭注意到烏克蘭軍艦試圖駛離該海域,俄羅斯海岸警衛隊命令其停下來,但烏克蘭軍艦繼續前行,在這種情境之下,俄羅斯海岸警衛隊使用了武力,先鳴槍示警,然后對目標開火,法庭認定其構成在執法場景下使用武力(81)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Order,paras. 73-74。。
最后,使用武力的類型和結果往往并非判斷使用武力場景的決定性因素,但使用武力的強度的升級可能導致局勢升級,從而可導致活動的性質發生變化。
(三)有關活動性質的變化
在“刻赤海峽案”中,高之國法官和克洛德欽法官均提及事件存在從執法活動向軍事活動轉變的可能性(82)高之國法官認為,本案在烏克蘭海軍被封鎖那一刻起,就從一個普通的通行行為升級到了海上對峙。隨后發生的一系列行為以及烏克蘭對該事件性質的認定,將本案從“關于執法活動的爭端”轉化為“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Gao,paras. 25,34,37;克洛德欽法官認為俄羅斯第一次發現烏克蘭軍艦后進行溝通和警告時是執法活動。隨著俄羅斯海軍和直升機參與到事件中,執法活動便升級為軍事活動。直到烏克蘭海軍及其軍事活動被迫停止時,才明顯恢復到之前的執法活動(逮捕、扣押等)。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Kolodkin,para. 21。。從理論上講,當案件的相關情況發生變化時,有關活動的性質也可能隨之改變,這也是評價活動性質時需要考慮的情況之一。
對于非沿海國而言,即便軍艦的通過和通行行為本身并不構成軍事活動,但若活動的內容、目的、主體等發生變化則可能會導致活動的性質發生改變。例如,非沿海國的軍艦通過行為僅違反《公約》第21條第1款[包括第19條第2款(g)項至(j)項],并不必然構成軍事活動。然而,若軍艦違反以上條款后,拒不改正或不按要求離開領海,且又伴隨了活動內容的改變,如試圖強行通過、與沿海國艦船發生惡意沖撞、使用武力回擊等;或者該國附近其他軍艦和軍機前來支援,并與沿海國形成對峙,導致非沿海國事先單純的通行目的發生改變,此時,該軍艦的通行和通過行為就可能發展成軍事活動。
對于沿海國來說,在執法活動中使用武力本身并不一定使其轉變成軍事活動,是否轉變的關鍵在于使用武力的場景是否發生變化。首先,當武力的使用已經升級為足以構成《聯合國憲章》所禁止的使用武力時,或當一國執法中的使用武力能夠引起另一國行使自衛權時,該執法活動將轉變成軍事活動。其次,當一國使用武力的意圖和內容發生改變,已經明顯不是為了執法目的,或視射擊目標為合法軍事目標時,該執法活動也將朝著軍事活動轉變。再次,緊張的政治因素及國家的態度也可能導致某次執法活動的性質發生改變。這種情況可能出現在雙方因某種權利義務(比如對通行制度的不同理解)頻繁發生爭議的情勢中。當一國多次行使某種其自稱應享有的權利而遭到另一國反復執法驅逐和外交抗議,兩國因該情形已經出現政治上的緊張局勢時,沿海國在某一次執法中以使用武力的方式強迫他國遵守本國法律法規便有可能導致執法活動轉變為軍事活動。例如,在“科孚海峽案”中,證據表明阿爾巴尼亞在1946年5月后持續密切關注科孚海峽,要求外國軍艦進入其領海須事先得到本國允許。國際法院注意到,阿爾巴尼亞政府在此種情勢下有時甚至會使用武力來迫使外國遵守本國的法律,如1946年5月向英國巡洋艦開火以及向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拖船開火(83)參見Corfu Channel Case (UK. v. Albania),Judgment (9 April 1949),I.C.J. Reports 1949,p. 4 at p. 19。。在該種情境下,阿爾巴尼亞布設或縱容布設水雷,或者以攻擊他國軍艦等強制手段迫使他國遵守本國法律的行為,均可被視為軍事活動。因此,當兩國政治局勢緊張且已發生過多次海上摩擦時,雙方應該能夠認識到存在“武裝沖突”的可能性,沿海國在某一次執法過程使用武力很可能導致事態升級。在這個過程中,被執法對象特別是軍艦若使用相應或更強的武力進行回擊,沿海國使用武力執法的情境就會發展成雙方的軍事對峙和沖突。
由于活動性質可能發生變化,高之國法官、洛奇法官及部分學者還提出存在同時構成關于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爭端的混合爭端的可能性(84)參見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Gao,para. 50;Detention of Ukrainian Vessels,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Lucky,para. 21;Shi Xin-xiang,Chang Yen-Chiang:Order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in Ukraine versus Russia and Mixed Disputes concerning Military Activities,發表于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2020年第2期,第278,288-293頁。。理論上講,這種混合性爭端是可能存在的。然而,在涉及《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適用的案件中,一旦某爭端被認定為是關于軍事活動或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并存的爭端,就會直接觸發軍事活動例外條款的適用,不論爭端的重心在于兩類爭端中的哪一種。
四、結語
在國際法上,《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中關于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爭端的認定和區分已經從值得研究的理論問題發展成重要的現實問題。國際海洋法法庭、《公約》附件七仲裁庭在近年來受理和裁判的幾起案件中均涉及到第298條第1款(b)項的可適用性問題,然而《公約》沒有定義或列舉兩類活動,也沒有規定認定和區分兩類爭端的規則、標準和方法。國際海洋法法庭在2019年裁判的“刻赤海峽案”中首次提出了區分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的一般方法,即以客觀評價有關活動的性質為主,以考慮個案中的特別相關的情況為輔。因此,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厘清第298條第1款(b)項所指兩類爭端的內涵和外延,明確關于兩類活動的爭端所涉的若干關鍵步驟和具體國際法問題。
第一,對于《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的解釋和適用不得背離有關用語的通常含義及締約方的真實意圖,不得利用條約解釋隨意提高或降低法庭確立管轄權的門檻。通過分析該項中的三個關鍵用語,即“關于……爭端”“軍事活動”“執法活動”,可以發現是否認定某爭端為“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或“關于執法活動的爭端”取決于此爭端與有關活動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既不能過于松散,也不要求過于密切以至于將二者完全等同。
第二,區分關于兩類活動的爭端的一般方法是要求“客觀評價有關活動的性質”,這涉及確定“有關活動”、明確爭端的主題事項與“有關活動”的關系、客觀評價“有關活動”的性質等關鍵問題和步驟。“有關活動”不僅包括訴求中聲稱違反《公約》的特定行為,還包括與該關鍵活動密切相關的其他活動,這往往涉及原被告雙方的活動,還涉及導致爭端產生、形成、發展的有關活動;爭端的主題事項的確立是選取“有關活動”的基礎,“有關活動”還可反映主題事項之外的其他爭端,并幫助判斷爭端的性質;“客觀評價”要求裁斷者不能主觀臆斷,應客觀評價雙方的活動,并依據確鑿的證據和事實認定有關活動的性質。
第三,區分關于兩類活動的爭端時以一般方法為基礎,同時要求“考慮個案中的相關情況”,這涉及如何確定并考慮案件的“相關情況”、有關活動性質是否可能發生變化、是否存在混合爭端等重點問題。應綜合考慮案件所涉情況和因素來確定“特別相關的情況”;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均可能涉及使用武力的情形,應重點判斷使用武力發生的場景;有關活動的性質可能隨著爭端的發展而發生變化,如某典型的沿海國執法活動可能因雙方沖突升級而發展成軍事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