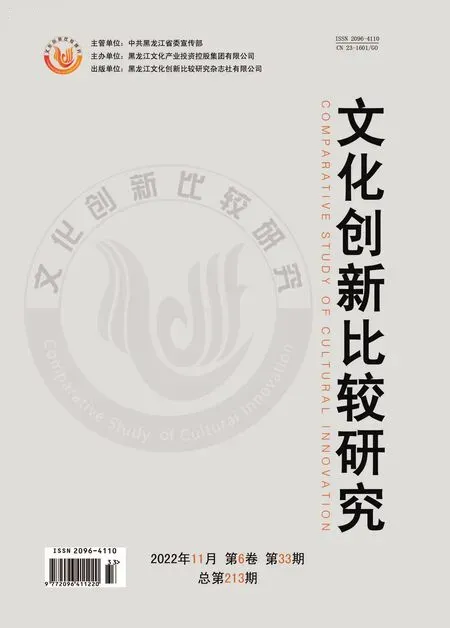生命在欲望中燃燒
——太宰治的《人間失格》評析
汪涵穎
(西南民族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四川成都 610041)
1948年出版的小說《人間失格》是日本著名的現代小說家太宰治的傳世遺作,同時也是一部具有半自傳性質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多體現出的是關于人生境況的思考,但他在敘事層面上多是消極的話風,以頹廢墮落的生活態度詮釋特立獨行的生存之道。因此,他也被評為“無賴派文學”的代表。《人間失格》是他極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作品中有時代鴻溝給人心靈的創傷,有家族的封建傳統給人生存的窒息,有父權制社會給女性的桎梏,有關于死亡背后的人生所求,甚至將人間定義為“失格”,都是作者所蘊含的深意。日本本土的著名學者小野正文曾高度評價《人間失格》中大庭葉藏這個封閉在自我世界中飽滿的人物形象,從全方位視角多角度把握作者的思想內涵,也有助于把握主人公大庭葉藏的人生的價值追求。
在日本學界,太宰治于日本現代文學發展有舉重若輕的地位。有人立足于作品內涵的頹廢因子,提取無賴派文學中的共性,從絕望、虛無、彷徨中總結人生認識作者;而有人則從精神分析中研究在百廢待興的時代下,人們縱情于物欲的世界里,作者反其道而行的人間清醒,從他多次的自殺經歷來看,結束恰恰是一種反抗。在《人間失格》的分析研究中,許多學者的目光都聚焦在“消極頹廢”的關鍵點上,從敘事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大庭葉藏與作者的自我建構;也有人從文本反觀作者的自我呈現;也有學者另辟蹊徑在作品中分析包裹的死亡意識,然而 “如何生存”貫穿了主人公大庭葉藏的一生,主人公多數時候傾向于用死亡去證明生的意義,在別無選擇的余地里,死亡成了最好的解脫。不可否認頹靡是小說的主旋律,“欲望”反而承載著對世間的認可和留戀,承載著活下去的信念。文本中隨處可見的欲望是值得去捕捉和分析的,無論在大環境中還是家族體制內抑或是塑造的每一個人物形象背后,總有消極意義的積極成分存在,矛盾的個體也給這個“失格”的世間提供了卑微的生存指示。從“欲望”的視角去解讀,或許也能給文本研究提供一點新的視野。
1 暗藏在時代洪流下的欲望
在《人間失格》中作者寥寥數筆渲染了日本傳統的文化壓抑,交代出了主人公大庭葉藏在父親絕對權威下成長的壓抑感和幸福的缺失。在對太宰治的頹廢美學的研究中,貴族精神實際上是其內在精神的主要組成部分,貴族精神的喪失實際也是日本傳統文化美感的遺失。太宰治曾在自己的另一本小說《斜陽》中借“弟弟直治”這一形象投射了“貴族”這一身份所構成自我的矛盾,不敢茍同卻又無法拋棄,貴族的沒落和精神物質的匱乏讓“貴族”這個頭銜不再高雅,被各種“主義”充斥的社會不再有統一的身份認同標準,存在的意義開始無限被擴大和質疑。整本小說都是站在第三人稱的視角,以一個“他者”的角度在審視自我,就像戰后的日本,以“無罪”的意識在麻痹自我,人以一種茍活的姿態在社會上行走,安逸享樂成了社會生活的主旋律。人是為著什么而活著呢?這是葉藏來自靈魂深處的拷問,也是直指社會的一把劍,幼年的葉藏尚有生存的欲望,“盡管我對人類滿腹恐懼,但是怎么也沒法對人類死心”[1]。葉藏在談到一場演說時,提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欺騙,將其形容為 “一種顯得干凈利落而又純潔開朗的不信任案例”“就連我自己也一樣,從早到晚都是依靠搞笑來欺騙著人們”“我沒有向任何人控訴那些男女傭人所犯下的可憎罪孽,并不是出于我對人類的不信任……而是因為人們對我這個名叫葉藏的人緊閉了信任的外殼”。葉藏的孤獨感是扎根在生命的底色中的,這只是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人中的一個縮影,人與人的疏離已是時代背景下的趨勢,而這時候的欲望還留有生命力,還在等待成長。
太宰治用大量的筆墨描寫了葉藏家庭中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在學校中與人相處的點滴小事,看似是大家寵兒的他,實際在不斷的搞笑中將自我推向了世間的邊緣地帶。他在思考“幸福”的定義時,就表達了自己與常人的不同,“自己的幸福觀與世上所有人的幸福觀格格不入,這使我深感不安,并因為這種不安而每夜輾轉難眠、呻吟不止,乃至精神發狂”。作為家里最小的孩子,他卻并未得到對等的關愛,父親公務纏身,母親身體孱弱,童年的缺失是其性格孤僻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學者也對此分析道:“這樣微弱不起眼的家庭地位勢必會造成大庭葉藏不甚健全的心理以及纖細敏感的個性……這些年少時的經歷都對他日后的成長軌跡、生存轉臺和死亡意識的形成起到了深刻的影響。”[2]通讀小說,不難看出大庭葉藏其實是個極致的理想主義者,當現實與理想大相徑庭時,其性格也轉變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后記》中老板娘提及葉藏時,“我們所認識的阿葉,又誠實又乖巧,要是不喝酒的話,不,即使喝酒……也是一個神一樣的好孩子哪”。在文本中,不難看出正是無窮無盡的欲望造成了這“失格”的人間,被欲望包裹的社會也侵蝕著時代下的人民。時代在變換中選擇了摒棄傳統文化價值,沒有了將其視為生命的精神源泉和滋養。
2 女性:欲望的角色依托
葉藏毫不夸張地說自己是在女人堆里長大的,讀書期間的伙伴竹一也曾預言過 “我”會討女人喜歡,從手記中也不難看出人生中三個主要的女人給他帶來的人生意義。這也是多數人認為《人間失格》是太宰治的一部半自傳小說的原因。從人生經歷來看,太宰治也曾和女人相約自殺,他的一生共有5次自殺,4次自殺未遂的經歷在《人間失格》的敘事中也有所影射。太宰治第2次自殺是和咖啡店的女店員一起,結果該女子自殺成功,太宰治被救活,這便和小說中的葉藏選擇和常子自殺的情形相似。葉藏和常子的性欲給了葉藏生的指示,葉藏曾說:“跟這個詐騙犯的妻子所度過的一夜,對于我來說,是獲得了解放的幸福之夜 (不假思索地在肯定意義上使用這樣一種夸張的說法,我想,這在我整篇手記中都是絕無僅有的)。”這個從未有過幸福感的人(盡管打幼小起“我”就常常被人們稱為幸福之人,可我總覺得自己深陷于地獄之中)在和常子的情欲中感到了溫暖,這一刻的欲望給了葉藏活的希望,他給常子的定義是“恩人”。常子的死給了葉藏很深的打擊,他采取著一種敗北者的消極態度對待生活,然而,從他微妙的心理也能看出,他其實對家庭、對父親還抱有期待,但“比目魚”的虛榮做作又壓垮了一根可以拯救自我的稻草,再次打壓了他生的欲望。常子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實際豐富了葉藏的性格特性,暗藏了他對人生的價值期許。
隨后,葉藏遇到了靜子和她5歲的女兒繁子,他們的同居生活被葉藏嘲諷為男妾似的生活,盡管“靜子還說很多奉承話抬舉我,可一想到那恰恰是屬于男妾的可鄙特征,我就變得越發消沉,萎靡不振。我暗地里忖度著,金錢比女人更重要,我遲早會離開靜子,去過自食其力的生活。我也為此煞費了苦心,可反倒越來越依賴靜子了”。在這里,可將靜子看作是葉藏具象化的物化“產品”,她是他目前賴以存活的欲望,盡管這樣的欲望帶給葉藏的是壓抑,但當他在門外聽到靜子和繁子開心的談話時,樸實的幸福感帶給了他沖擊,他選擇離開是一種成全,靜子和繁子的出現使 “我開始隱隱約約地明白世間的真相了”。在日本電影《人間失格:太宰治和他的三個女人們》中,靜子常穿的也是梅紅色西式衣著,太宰治送的是一朵梅花,以及房間里梅紅色的玻璃和裝飾品背景,這一梅紅元素無疑是幫助塑造了靜子剛烈性情以及生子打破傳統禁錮的“革命”精神[3]。或許將靜子的形象定義為“革命”的存在,能夠減輕一點葉藏對世間的恐懼,盡管他們仍是在情欲中相遇。而書中筆墨最多之人便是良子這一形象,緣起緣落都在生與死的欲望中。良子本是世間最可愛的化身,可是她被侵犯了,這樣的沖擊帶給葉藏的只有深深的恐懼,讓他的“頭上出現了白發,對所有的一切越來越喪失信心,對其他人也越來越懷疑,永遠地遠離了對人世生活所抱有的全部期待、喜悅與共鳴”。后來他選擇吞服良子的安眠藥自殺。葉藏在電影中的這些經歷和太宰治的人生經歷有重合部分,從傳記學批評的角度看,這與他人生中的第4次自殺是何其相像,他們都因妻子出軌而選擇了服藥自殺。葉藏在面對死亡時都是冷靜地對待,這是一種向死而生的選擇,他追求的是解脫之美。當令人恐懼的死亡終點延展開實則是對生命的追溯與推崇,體現了對生命意義的更高層次的訴求。所以每一次被救活,葉藏在世間的絕望就又加深了一分,他的心里和良子再沒有家,他在心里已下定了決心和良子分離,當良子承擔不了他任何的欲望時,良子的失貞帶給他的是凄烈至極的決絕。
3 生命欲望的文化表象
《人間失格》又名《喪失人的資格》,較之前者更直觀地表現了“喪文化”的內涵,悲觀絕望是文本的主基調,但在文本中于絕望的筆觸下卻處處透露著對本土傳統文化的懷念與向往。在日本的傳統文化中,“物哀”“幽玄”與“寂”是日本最集中的三大審美范疇,而三者皆強調審美的主客體一致,“美”是日本文學中最高的價值追求。通過大量的學術研究,在太宰治的作品中幾乎都蘊含著悲切的“死亡”意識。然而他定義的死卻是在追求一種極致的“脫胎換骨”的生,“向死”和“知生”在他的作品中有著高度的統一性,選擇自我毀滅恰恰表明了作者對生命的崇高敬畏。顏翔林在《死亡美學》中談道:“死亡意象屬于美學范疇,當然也是個積極的范疇,它能夠被人欣賞,它可能在更深刻的精神層面啟迪人的靈魂,為人的情感運動提供活力,為人心理上領悟非知識的價值觀和精神信仰打開一扇神秘的門窗。”[4]在文本中,不難看出葉藏追求的始終是精神層面的自由,他對“世間”的諸多疑問和恐懼皆來自不能將自我與人世達到自我滿意的和諧統一,他骨子里的善良促使他用搞怪的方式在維持人際,也是擔心人類不能接受“我”這樣的異類。有學者在研究太宰治作品中“向死”和“知生”這一對文化意象時說道:“向死所體現的并非對死亡本質的追求,而是人物對于自身及生存環境中‘惡’的摒棄,對于‘善’的向往。其作品往往鮮見對死亡的敘述,也并非以‘死亡’為目的來體現美感,而是將‘死亡’作為唯一的手段來尋求美的終極。”[5]在太宰治及葉藏選擇多次自殺的動機中也可窺見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在作者思想中凝聚著關于美的訴求和生命的欲望。《人間失格》是太宰治后期創作的作品,作品中濃厚的“貴族意識”蘊藏在葉藏的反抗精神中,大正至昭和時期貴族階層的沒落,很大程度地帶給了太宰治一定沖擊,造成了精神上難以言說的苦悶,從他開始進入地下組織參與共產主義的運動,也可看出他在找尋一條平衡理想與現實的出路。當葉藏在共產主義讀書會交流中,開始選擇扮演搞笑的角色,充當“同志們”的“丑角”時,這條路注定是失敗的。“這些單純的人們認為我和他們一樣單純,甚至把我看成一個樂觀而詼諧的‘同志’……我并不是他們的‘同志’,但我每次必到,為大家提供作為‘丑角’的搞笑服務。”畢竟參加運動的最高風險便是被捕入獄,而“我”恰恰認為“與其對世人的‘真實生活’感到恐懼,還不如被關進牢房來得暢快和輕松”。貴族的身份與革命的意識沒辦法統一的太宰治,最終還是選擇了前者,在文字中釋放精神空虛。
在 《人間失格》中隨處充斥的欲望并不使人厭煩,藏在欲望深處的是有待被發覺的美學氣息,其絕望悲涼的文本基調反倒成了最表象的文化特征。從“父親”這一角色上也可窺見一二,“父親”終其一生帶給葉藏的都是無限的壓抑,但葉藏對父親永遠都有深切的渴望。幼年時期葉藏希望父親給他帶書,但為了滿足父親刻板印象中對孩童的幻想,他選擇扮演一個天真的孩子,在這里并未有任何搞笑的成分意味;青年時期,他與妓女相約自殺,不僅未遂還被爆出,惹得父親勃然大怒,然而他想如果父親仍然愿意資助“我”讀書,“我”的人生應該會不同;后來從大哥口中得知父親胃潰瘍去世后,他說道:“得知父親病故以后,我愈發萎靡頹廢了。父親已經去了。父親片刻也不曾離開我心際,他作為一種可親而又可怕的存在,已經消失而去,我覺得自己那收容苦惱的器皿也突然變得空空蕩蕩……甚至喪失了苦惱的能力。”在這也可看作是生的欲望的指引,“父親”雖承載了葉藏一生的苦惱,但他于葉藏而言,卻也永遠是可親的存在,“父親”這個角色反而在延續他的生命力。在小說中,葉藏多次將自我放在于“人類”而言的“他者”地位中追問“世間”,最終他也得出了至高的哲學性的答案——“一切都將逝去”。“美”是沒有盡頭的,它永遠沒有實質性的答案,在尋“美”的路上釋放欲望也是和“美”融合的一個過程,然而在過程中就有了關于“生命”的意義。不可否認葉藏的人生是墮落的,他的人生軌跡遭受社會主流文化的排擠,但“私小說”的寫作手法卻是在借消極的事物傳達積極的追求。這就像葉渭渠在《日本文學思潮史》中談到的 “墮落論”的定義,“這實際上是一種 ‘價值顛倒說’,他們不是以新取代舊,以真善美取代假丑惡,而是認為墮落中就存在著真與美,以轉換顛倒價值觀的方式為墮落意味著向上,頹廢意味著健康……”[6]。《人間失格》中的葉藏就是以這種“向死而生”的態度在傳達對世間的美好祈愿,這或許也是太宰治寫作中獨特的文化審美范疇。
4 結語
太宰治作為“無賴派文學”的代表,被譽為“昭和文學不滅的金字塔”,他的《人間失格》是具有其自傳性質的一部作品,通過對文本的細致研究多能從葉藏的人物形象中看出作者的自我價值追求和審美意蘊。誠然,小說的主基調是苦悶絕望的,但作者的倔強氣質仍然流露在葉藏的一次次的反抗中,對世間的每一次不妥協都表達了主人公對生的渴求,欲望在時代中浮沉,在女人堆中發酵,在文化氛圍里追逐……都是作者在展現獨特的存在意義。太宰治“向死而生”的生命選擇正是給了“迷惘一代”一記有力的敲打,精神文化的建設才是擊退頹廢的有力武器,傳統本土文化之美正是精神建設的最好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