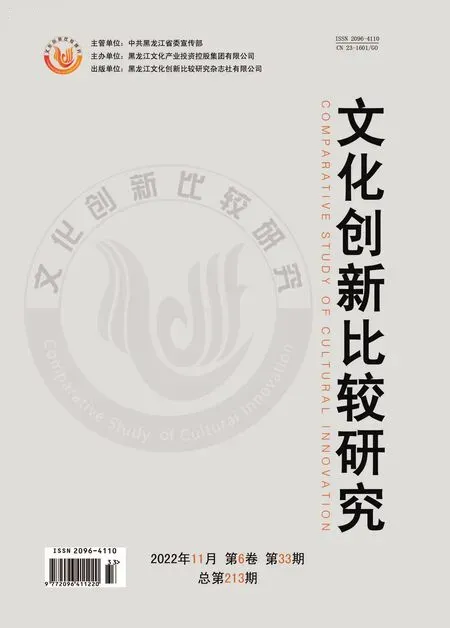古雷州府海上絲綢之路對雷州文化生成的影響
謝小羽,張楷昕,鐘景媚,劉瑩瑩,劉剛
(廣東海洋大學,廣東湛江 524003)
近年來,隨著海上絲綢之路逐漸受到重視,學界對粵西地區雷州半島的關注度也在不斷提高。雷州半島涵蓋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徐聞古港和南海航線的起點雷州港,是海上絲綢之路航線的重要地理位置,因此雷州半島的文化生成也勢必受其影響。然而學界的研究多著眼于海上絲綢之路史跡推廣對雷州半島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較少提及海上絲綢之路與雷州文化生成之間的關系。本文從宗教文化、瓷器貿易、農業生產結構三個角度探討古雷州府海上絲綢之路對雷州文化生成的影響。
1 古雷州府海上絲綢之路
古雷州府是一個歷史地理概念,唐貞觀八年(634年)置雷州,下轄海康、徐聞、遂溪三縣,歷經南漢、宋、元、明、清而不變。清后幾經改制,今為湛江市位處雷州半島的行政轄區,在地域上涵蓋雷州文化核心區,也是湛江海上絲綢之路物質文化遺存的主要分布區。
在唐中期以前,中國對外貿易主要依賴于陸上絲綢之路。后因戰亂、經濟重心遷移等原因,海上貿易道路得到開辟。“絲綢之路”的命名最早是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提出的,而“海上絲綢之路”的提法則稍晚,直到1913年才由法國著名漢學家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 年) 提出[1]。在此之前,這條海上貿易之路叫作“廣州通海夷道”。隋唐時,海上貿易道路以運輸絲綢為主,到了宋元時期則以運輸陶瓷為主,因此也稱 “海上陶瓷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指的是古代從中國出發的中西交通海上航線,分為東海航線和南海航線。東海航線,是中國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直至東南亞的重要通道;南海航線,是中國通往東南亞、南亞、西亞、歐洲、非洲的海上通道[2]。其中,南海航線是中外海上交流的主要通道,到達國家眾多,開辟了古代最遠的航線,影響深遠,學界稱之為“南海絲綢之路”。
古雷州府海上絲綢之路就屬于南海航線。西漢時期,南越國與印度半島之間海路已經開通。漢武帝滅南越國后憑借海路拓寬了海上貿易的規模,“海上絲綢之路”由此興起。有學者根據《漢書·地理志》梳理了海上絲綢之路:從徐聞(今廣東徐聞縣境內)、合浦(今廣西合浦縣境內)出發,經南海進入馬來半島、暹羅灣、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南部的黃支國和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3]。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古雷州府與海上絲綢之路結下了不解之緣。《漢書·地理志》載:“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赍黃金雜繒而往。”[4]由此可見,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始發港應在徐聞。據考證,徐聞港遺址在今湛江市徐聞縣二橋村、南灣村、仕尾村前舊稱三墩港的海灣,即今人所稱“大漢三墩”。
南海航線全長1.4萬km,途經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一條海上貿易線路,在宋元時期其貿易覆蓋范圍之廣,成為東西方文化經濟交流的重要載體。海上絲綢之路將我國儒家文化與傳統手工藝品帶向國外,在世界掀起一陣“中國熱”。與此同時,海外的工農業商品、宗教文化等也通過這條線路傳向國內。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古雷州地區文化的形成深受其影響。
2 雷州文化的生成過程
對于雷州文化的概念,多位學者都提出過自己的見解。司徒尚紀將雷州文化定義為“泛指形成、發育于雷州半島,并輻射周邊地區的一種區域文化”,認為雷州文化的概念應包括雷州半島的地理環境、雷州文化的歷史演進過程、雷州文化的空間拓展過程,以及雷州文化的特質和風格[5]。趙國政將雷州文化定義為 “歷史上雷州半島居民外化于各種物質形式中的主觀意識”,并從時空范圍、文化主體、文化本體、文化載體四個部分對雷州文化進行分點闡述[6]。
基于上述認識,本文在研究雷州文化的生成過程時,重點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創造文化的人類主體;另一方面是影響人類創造文化的區域地理環境。雷州半島上的居民作為文化主體,其生產和生活活動所創造出的物質和精神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構成了雷州文化的現今狀態。區域文化的生成與地理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得天獨厚的環海地理位置決定了雷州人“以海為商”,也決定了其文化勢必受到海上貿易的影響;打通廣闊的海路,也給外來文化進入雷州半島創造了有利條件。在雷州文化中,除了海洋文化占據重要地位之外,多民族文化融合也是其文化特性之一。
雷州文化的形成經歷了從史前社會到現代社會幾千年的演進,大致可以分為3個時期。
2.1 萌芽時期:史前—先秦
雷州文化在歷史發展中存在明顯的4次斷層,其中史前至先秦時期雷州文化經歷了兩次文化斷層。
第一次斷層在舊石器時代。雷州文化的源頭可追溯到6 000年前的遂溪鯉魚墩人生活時期。遂溪鯉魚墩人是由北向南遷入的移民,以海生資源為主要食物,陶器上繪有獨具海洋特色的水波紋,可見雷州海洋文化的源頭在此。同時,遂溪鯉魚墩人的曲肢墓葬蘊含著史前人類文化交流的重要信息——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地區也存在同樣的葬式,說明了新石器時代的雷州文化就存在著與其他地區文化融合的因素。
夏商時期是第二次歷史斷層,據學者推測這一時期的文化仍舊保留原始社會的部分習俗。先秦時期雷州半島尚未有統一的行政規劃管轄,屬于駝越、南越、西甌交匯之地,民族文化融合的現象初見端倪。后來楚國南平百越,也為雷州半島帶來了荊楚的建筑文化和青銅文化。
2.2 多種文化融合時期:秦漢—宋元
雷州文化以百越文化為原始基礎,不斷融合中原文化、荊楚文化、漢文化、閩潮文化及海外文化,形成了多種文化融合的雷州文化核心。
秦朝統治時期,雷州文化開始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秦朝前期雷州半島歸屬象郡,雷州文化與中原文化開始融合。秦朝末年南方戰亂,雷州半島屬于南越國,卻因遠離番禺政治中心,而未真正進入中原文明狀態。到了漢朝,雷州半島正式進入中原文明化的進程,其中,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是這一時期雷州文化飛速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力。漢武帝在雷州半島上設置了徐聞縣,并以徐聞港作為海上絲綢之路南海航線的始發港。同時,徐聞縣占據軍事要地北部灣和瓊州海峽,徐聞成為雷州半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圖志》中為徐聞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徐聞縣案本漢縣名……故諺云:‘欲拔貧,詣徐聞’。”[7]海上絲綢之路還為雷州半島帶來了國內其他沿海地區,甚至海外的文化,印度佛教便是通過漢代海上絲綢之路航線進入雷州半島的。因此雷州文化中的異域色彩,可以在此時期找到源頭。
隋唐時期大量中原漢人遷往雷州半島,為雷州文化注入了中原文化。隋唐時期人口的大量南遷,有著被動因素和主動因素,被動遷移是戰亂影響,主動遷移是開發南疆的需要。在兩位對雷州文化有重要貢獻的人物——冼夫人和陳文玉的推動下,漢文化和本土的俚僚文化不斷相互融合。陳文玉任職期間,為當地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百姓尊陳文玉為“雷祖”,每年舉辦3次敬雷活動,祭拜雷祖活動是半島共同信仰和風俗形成的起點。當然,文化融合的過程中也存在著巨大的文化沖突,隋唐時期存在著上文提到的雷州半島的第三次文化斷層,表現為崇狗信仰和食狗行為的文化沖突,實際上這是俚僚文化與漢族主體文化之間文化沖突的外露
宋代文人蘇軾、蘇轍等人曾被貶至雷州半島,或被貶時途徑雷州半島,他們帶來了中原的精英文化,對中原文化的傳播、雷州半島地區的民風開化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雷州百姓為紀念這些為雷州半島做出巨大貢獻的官員修建了“十賢祠”,供奉著寇準、蘇軾、蘇轍、秦觀、李綱、趙鼎、李邕、王巖叟、胡銓、任伯雨10人。北宋滅亡后,宋王室南遷,大量閩人遷入雷州半島;其中莆田人由海上路線遷入,并成為雷州半島的主要人口成分。他們帶來的媽祖崇拜與依海而生的雷民生活需要相契合,使得民間祭拜媽祖活動盛行,閩潮文化在此時占據重要地位。北方漢人南遷來也極大程度地推動了半島手工業的發展,宋元時期制瓷業極為繁盛,使得雷州窯名震四方,滿載著大宋風韻的瓷器從雷州港出發遠銷世界各地,主要依靠的就是海上絲綢之路航線。
2.3 成熟時期:明清—近現代
明清時期雷州文化逐漸走向鼎盛,在各個領域都表現出文化成熟的特點。
多形態文化的定型是雷州文化成熟的標志。在語言方面,雷城話成為最標準的雷州方言,清代雷州方言正式定型;在戲曲藝術方面,從漢末雷謠演變而來的雷劇,從宗教祭祀發展為民間藝術活動的飄色,都代表著雷州歌劇的成熟;在史書編撰方面,史志編纂活動空前繁盛;在文化人物方面,以“三陳”——陳瑸、陳昌齊、陳喬森為代表的杰出人才的涌現是雷州人文成熟的重要標志。
清中葉至近代,雷州半島經濟活動迎來漢代以后的第二次高潮。隨著海禁政策逐漸松動,由民間自發形成的赤坎商埠走向繁榮,赤坎展現出近代港口都市的繁華景象,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商業文化出現。近代中國國門被迫打開,雷州半島的廣州灣成為法租界。法國殖民者的侵略一方面帶來了西方現代技術和商貿的繁榮,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如瘟疫般蔓延的低劣文化,毒品貿易泛濫,賭博風氣橫行,妓館隨處可見。
新中國成立后的雷州半島又重新迎來了發展機遇,形成了傳統色彩濃厚、時代特征鮮明的現代雷州文化。
3 海上絲綢之路對雷州文化生成的影響
通過梳理雷州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情況,可見雷州半島長期以來一直保持著兼收并蓄的文化態度,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博采眾長,最終形成了多元的雷州文化。在文化傳入的各類途徑中,海上絲綢之路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交通路線的開辟與文化傳播之間的關系密不可分”[8],自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形成至清代海禁中斷,到現代重提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戰略地位,這條交通要道一直扮演著文化交流樞紐的角色,從中足見其對雷州文化的生成有重要影響。
3.1 宗教文化的輸入與融合
雷州文化的多元性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現為本土民間崇拜與外來宗教相互融合。雷州半島原著居民長期以來信奉原始圖騰,將狗視為守護神,形成了以石狗像為圖騰崇拜的形式;除了石狗崇拜之外本土居民還崇尚雷神,形成了獨特的雷文化。隨著海上絲綢之路貿易往來的日益密切,外來的佛教、媽祖崇拜也開始融入本土居民的宗教信仰中。
3.1.1 佛教的傳入與影響
多位學者提出佛教是從古印度分海陸兩種方式傳入中國的,并且南海海上傳播途徑遠早于西域陸上傳播途徑。吳廷璆、鄭彭年通過分析《漢書·地理志》的有關記載,提出:佛教由中印航線傳入交州,而中印航線在西漢時期就已經開通,始發地正是雷州半島,由此可以推斷出,雷州半島是中國受到佛教影響最早的地域之一。
佛教文化不斷影響著雷州人的生活,典型表現為殯葬文化的變化發展,將當地殯葬方式逐漸由土葬改化為火葬。藝術方面,形成了雷州佛樂中心、雷州佛像雕塑藝術中心,且在嶺南地區占據較高地位。同時,雷州窯瓷器中也含有佛教元素,制瓷藝術審美受到佛教的影響。在有型文化遺產方面,雷州半島留下了大量佛教圣地,如雷州市天寧樣寺、高山寺、萬壽應、寶林梯寺、天竺庵,徐聞縣華捍寺、三元堂,遂溪縣護國寺、龍華庵,昊川縣古興龍寺,湛江市城區楞嚴寺、福壽山玉佛寺、清涼寺、白良寺等。唐代時佛教被尊為國教,雷州半島也因此成為嶺南最大的佛教文化中心。
3.1.2 媽祖崇拜的傳入與影響
媽祖崇拜產生于宋代。媽祖姓林名默,原生于福建,相傳是能夠呼風喚雨、預知福禍的神女,閩人在其死后尊其為海神,修建寺廟祈福,以求海上活動能得到庇佑。隨著閩人海上航行經商及宋代之后大量閩潮人遷入雷州半島,媽祖崇拜傳播至此,成為雷州民間信仰的一部分。
媽祖崇拜能夠在雷州半島扎下根基,有以下4個原因:第一,唐末五代便開始有大量移民由北往南遷,宋朝時閩潮移民數量龐大,信仰媽祖人數占比高;第二,雷州半島三面環海,海洋地理因素對民眾生活影響大,漁業是重要的經濟來源,航海活動不可避免,媽祖崇拜寄托了人們對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第三,由于雷州半島地區常年受到臺風侵襲,雷州半島居民臨海生活危險因素較多,因此媽祖作為海上守護神形象能夠成為人們應對自然災害的精神支撐;第四,粵西地區長期盛行巫術,為媽祖俗信融入雷州文化奠定了社會基礎。除此之外,還有學者提出其他原因,如上層統治階級的支持、媽祖信仰靈應、少數民族外遷[9]等。
媽祖崇拜的根源在于雷州人認同媽祖文化中保守的、敬畏海洋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媽祖作為沿海地區的守護神,她是救民于危難的神女,而非是搏擊大海的英雄形象。因此,在媽祖的庇佑下,雷州人對于海洋探索的態度并非勇于開拓,而是趨于保守甚至回避,這種態度外化為雷州半島以農耕為主、漁獵為輔的保守型文化。
雷州人對媽祖的祭祀活動遍布雷州半島,到了明清時期雷州半島媽祖廟多達30座,其中雷州11座、徐聞7座、遂溪12座[10],可見媽祖崇拜對雷州半島民俗文化的影響之大。
3.2 雷州窯的繁榮與海上絲綢之路
雷州窯同樣是雷州文化中燦爛的一部分,它和廣州窯、潮州窯并稱為廣東三大窯系,是國內多地造窯技術結合而成的產物。其藝術形態顯示出文化融合的特征,既飽含雷州風情,又具備異地特色。
雷州窯產生于唐代,上文提到漢人的遷移為雷州注入了中原文化,與此同時中原的制瓷技術也被帶到了雷州半島,褐彩瓷技術被廣泛運用到雷州瓷器的制作中。宋元時期的雷州窯“窯口密布,規模較大,主要生產青釉下赭褐彩繪罐、枕、棺等”。其繁榮主要表現為:第一,窯口數量多、分布密集,形成了多處集中的窯址群。宋元時期雷州半島窯址,集中分布在雷州半島中部,南渡河中上游的兩岸及東西兩側濱海地區,截至2002年仍存有窯址群150余處。第二,制作技術精湛。雷州窯主要生產青釉瓷,汲取了褐彩瓷制作技術,線條流暢,花紋繁縟,有著鮮明的南方制瓷特色。
雷州窯的興盛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關系極為密切。海上絲綢之路也稱為“陶瓷之路”,海外對中國瓷器的需求刺激了雷州窯的發展。雷州窯生產的瓷器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主要貨品,遠銷海外,“在廣東沿海絲綢之路航線、海南島沿海、西沙群島、東南亞諸國,甚至埃及均有出土”。雷州瓷的出口,對航海線路沿線地區的制瓷業產生巨大的影響,例如,考古發現越南與泰國部分窯址生產的瓷器與雷州瓷有著相似的外觀特征,應是沿用了雷州窯的制瓷工藝。
雷州窯憑借著融合多地制瓷技術工藝、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經貿地位和便利的通商環境,在宋元250多年里一直保持著繁榮的景象。直到明清時期因為“海禁”政策及其他窯址的興起,雷州窯才走向衰落。
總而言之,海上絲綢之路對雷州窯的繁榮起到了直接促發的作用,雷州窯的繁榮也推動了海上貿易的深入發展。在雷州窯文化里,海上絲綢之路貿易活動是其生成的重要因素。
3.3 農業文化的更新
海上絲綢之路航線不局限于陶瓷、絲綢和香料的商貿往來,還引入了大量的農業作物,改變了雷州地區的農業種植結構,深遠地影響著雷州以至于全國的飲食文化。其中最為典型的外來作物就是番薯和花生。
3.3.1 番薯
番薯的傳入與雷州半島有著不解之緣,最早是吳川人林懷蘭經由海上絲綢之路帶入雷州半島的。據清道光《電白縣志》卷二十記載:
“霞洞鄉有番薯林公廟,副榜崔騰云率鄉人建立。相傳,番薯出交趾,國人嚴禁,以種入中國者罪死。吳川人林懷蘭善醫,薄游交州,醫其關將有效,因薦醫國王之女,病亦良已。一日賜食熟番薯,林求食生者,懷半截而出,亟辭歸中國。過關為關將所詰,林以實對,且求私縱焉。關將曰:今日之事,我食君祿,縱之不忠,然感先生德,背之不義。遂赴水死。林乃歸,種遍于粵。今廟祀之,旁以關將配。其真偽固不可辨。”[11]
吳川人林懷蘭在明代萬歷年間,為安南國國王之女醫治疾病,安南國將原本禁止出口的番薯賞賜給了他。林懷蘭從海路將番薯帶回吳川,此后番薯進入了雷州半島的農業文化,慢慢遍布全粵。對于最初番薯傳入的記錄,吳建新在其《明清時期主要外來作物的再探》中進行了詳盡的梳理,他指出在康熙年間的縣志府志中多有番薯的記載:雷州府的電白縣、石城縣、徐聞縣,瓊州府的樂會縣、瓊山縣、文昌縣的縣志上都對番薯有所提及[12]。可見雷州半島和瓊州島區域在清代已有大規模番薯種植的情況存在。
番薯的傳入不僅對農業文化產生了影響,還對飲食文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改變了雷州人長期以稻米谷物為主糧的飲食習慣,擴大了人們對主糧的選擇范圍。因其高產且對環境適應性強,能夠在全國大規模種植,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饑荒問題。
3.3.2 花生
如果說關于番薯的傳入帶有部分傳奇色彩,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關系相對來說是間接的,那么花生的傳入與海上絲綢之路就有著更為直接的關系。花生的栽植和食用習慣被廣泛記載于清代乾隆、嘉慶、道光及之后的各類方志和筆記中。
花生的傳入方式和傳入地在清乾隆年間檀萃的《滇海虞衡志》中已有記載,“粵估從海上諸國得其種歸種之”“大牛車運之海上船,而貨于中國”[13],證實了花生最早經粵西傳入中國。對于花生的種植和加工,人們也已經有了深入的認識。例如《廣東新語》卷二十七“落花生”條有關于小粒花生種的生態、性狀的記載:“落花生草本蔓生種者,以沙壓橫枝,則蔓上開花,花吐成絲……以清微有參氣亦名落花參。”且清代花生的種植在雷州半島已十分普遍,雷州半島也成為花生的主要產區,在清乾隆年間張渠的《粵東聞見錄》文中記載了雷州、高州盛產花生。花生喜濕熱,雷州半島的氣候正適合大面積種植。且花生能夠改善土壤質量,通過與其他作物輪流種植,可提高復種指數。
花生富含蛋白質且食用方法多樣,或生吃,或入菜,或制糕點,或制醬料。《滇海虞衡志》記載:“市上也朝夜有供應,或用紙包加上紅箋送禮,或配搭果菜登上宴席,尋常下酒也用花生。”[14]雷州地區的傳統小吃中,葉搭餅便是使用花生碾碎入餡,豬腸餅在上桌前要撒上一把花生粉才算地道的雷州風味。
除此之外,人們還學會用其來榨油、做肥料,逐漸成為我國日常主要的油料作物。范端昂 《粵中見聞》卷二十五提道“黃白豆、落花生皆可榨油充用”[15];張渠《粵東聞見錄》中還提到花生油已作為食用,但“落花生油亦多,而力殊不及”[16],意指花生油產量雖多,但仍不及豬油。花生榨油之后所剩的渣滓還被人們用于作肥料,不僅肥效高,而且易獲取。
由此可見,花生從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傳入后,豐富了雷州人民的飲食結構,改變了經濟作物占比情況,人們對花生的種植與研究也從未間斷。除了農業文化之外,花生更是被賦予了吉祥、長壽、默默奉獻的精神意義。從古至今流傳著許多關于花生的諺語與謎語,都體現其已深入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花生土內長,秧苗節上生”“小胖子,穿麻衣,紅衫白肚躲殼里”[17]。
4 結語
綜上所述,雷州文化的生成與海上絲綢之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海上絲綢之路自漢代開辟以來到清末海禁為止,一直是中國對外交流的重要通道,雷州半島作為粵西地區乃至于整個嶺南地區對外交流的窗口,華夏文明通過這里向外傳播,海外文化通過這里引進大陸,中原文化和外來文化在這里交融。這條航線不斷通過商品貿易等物質形式,改變雷州人的宗教信仰、飲食習慣、生產生活和風俗人情,使這里原本的俚獠風氣不斷文明化,如此才誕生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展現出多樣性、海洋性的雷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