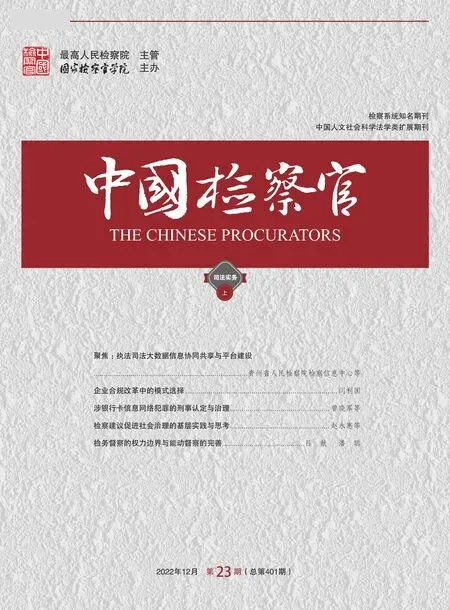涉銀行卡信息網絡犯罪的刑事認定與治理
● 曾曉軍 張鳳京 蔡超嶸/文
一、涉銀行卡信息網絡犯罪的現狀
2020年4月8日,最高檢召開以“嚴厲打擊網絡犯罪,共同防控網絡風險”為主題的新聞發布會。會上介紹,近年檢察機關辦理的信息網絡犯罪年均增幅達34%以上。2018年至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信息網絡犯罪嫌疑人89167人,提起公訴105658人,較前兩年分別上升78.8%和95.1%。2019年至2021年1月,檢察機關起訴信息網絡犯罪案件5萬余件,14萬余人。
以Q市H縣信息網絡犯罪數據為例,2016年以來,該地區信息網絡犯罪類型排名前四位為開設賭場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以下簡稱“幫信罪”)、詐騙罪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下簡稱“掩隱罪”),四類案件人數占信息網絡犯罪總人數的93.35%,而非法租售銀行卡是此類犯罪得以持續高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Q市H縣涉銀行卡信息網絡犯罪案件呈現以下特點:
一是犯罪年輕化、文化水平低。犯罪行為人以20歲至30歲青年為主,占比達50.6%;其次為31歲至40歲,占比達33.8%;20歲以下及50歲以上占比均在10%以內,其中18歲(含)以下相對較少,僅占總人數的2%,可見大部分刑事處罰對象為20歲至50歲的青壯年男性。從受教育程度上看,大專以上學歷占比僅11%,高中文化程度占比19.07%,初中文化程度占55.5%,小學文化程度占比12.96%,整體文化程度不高。

圖1:H縣網絡犯罪主要類型數量
二是類型集中化、程度遞進化。主要表現為銀行卡尚未被使用,但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數量已達5張以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向個人(團伙)出租、出售銀行卡(第三方支付帳戶)的;在提供銀行卡(第三方支付賬戶)后為配合他人實施轉賬、套現、取現又提供刷臉等驗證幫助的;明知為轉移犯罪資金,而直接使用銀行卡(第三方支付賬戶)操作轉賬、套現、取現的。
三是偵查取證難、定性爭議多。實踐中,涉銀行卡犯罪主要集中于幫信罪及掩隱罪,對兩罪的入罪標準及罪名適用存在諸多疑難爭議,如幫信罪涉案銀行卡中查證為詐騙款項的資金是否限制于單筆達到3千元以上;收購、出租、出售5張(個)信用卡或相關可用于支付結算的賬戶、工具中的張(個)數如何認定性質;明知他人實施掩飾、隱瞞犯罪所得,仍以提供信用卡形式進行幫助是否一概認定為共犯;行為人實施“跑分”行為,但未能查證上游犯罪的,是認定為幫信罪還是掩隱罪,等等。而造成爭議集中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上下游犯罪多系網絡犯罪,犯罪方式手段專業復雜,且多系跨地域犯罪,取證難度大,導致證據難以采信,影響了案件處理效果。
二、罪名適用與解析
(一)入罪解析——幫信罪“情節嚴重”的認定
1.涉案資金查證的認定方法。“兩高一部”相關內設機構于2022年發布的《關于“斷卡”行動中有關法律適用問題的會議紀要》(以下簡稱《2022年會議紀要》)規定,涉案信用卡中的資金超過30萬元,且其中至少3千元經查證系涉詐騙資金,認定為“情節嚴重”。那么是否應查明單筆資金至少3千元的涉詐資金,才能認定為“達到犯罪程度”?實踐中,詐騙團伙為逃避偵查或采取的詐騙手段不同,多使用數張銀行卡騙取多名被害人的多筆資金。如網絡刷單詐騙中,刷單數額由幾十元至上千元不等,實務中常見幫信行為人提供的某張信用卡中,同時有多筆由不同被害人匯入的涉詐資金,但單筆均未超過3千元,如機械強調單筆構罪,則較易被犯罪行為人規避,難以達到打擊目的。
一般而言,同一電信網絡詐騙團伙在同一時間區間內,由多名行為人使用一至二種相對固定的手段進行詐騙,并將資金歸集于團伙所掌握的信用卡內。為防止各自非法所得混同難以區分,不同的詐騙行為人之間并不會在同一時間段內共用同一信用卡歸集資金,雖詐騙行為人詐騙單個被害人的金額未達立案標準,但多個被害人被騙金額累計達到3千元,仍可認定構成詐騙罪。故筆者傾向認為,在把握同一時間段、采取相同手段的基礎上,同一信用卡內匯入的單筆被騙資金未達立案標準,但數筆被騙資金累計達3千元的,即可認定為“達到犯罪程度”。
2.其他“情節嚴重”情形的認定。司法實踐中,對“兩高一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中的“收購、出租、出售五張(個)信用卡或相關可用于支付結算的賬戶、工具并提供超過五張信用卡”如何認定存在有不同認識。如行為人提供了兩張信用卡、該2張信用卡配套的網上銀行數字證書及綁定該2張信用卡的第三方支付軟件等三種工具,在單向流入信用卡的資金未超過30萬的情況下,認定行為人提供了兩張信用卡或認定其提供了5個具有支付結算功能的工具是區分罪與非罪的關鍵。
筆者認為,無論是網上銀行數字證書,或是第三方支付軟件,均需通過所綁定的信用卡實現支付結算功能,本質上信用卡賬戶才是支付結算資金的實際載體,將依托于同一賬戶的支付結算功能進行拆分,有重復評價之嫌,故應當以實際發揮支付結算作用的信用卡為計算標準,只有行為人提供了不同的信用卡,或提供信用卡的同時又提供了與該信用卡無關聯的其他支付結算工具,合計達到5張或5個以上,才能認定為“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二)各罪解析——關聯犯罪的正確適用
1.明知他人實施掩飾、隱瞞犯罪所得,仍以提供信用卡形式進行幫助的行為定性。從理論角度出發,明知他人實施某種犯罪而提供幫助,除法律及司法解釋另有規定,一般以共犯論處。司法實踐中,不乏行為人明知他人實施掩飾、隱瞞信息網絡犯罪所得行為而以提供信用卡進行幫助的情形,此種情形是否能夠直接認定行為人成立掩隱罪的共犯爭議較大。筆者認為,偶然以提供信用卡形式幫助他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或掩飾、隱瞞犯罪所得,不能一概認定為幫助對象的共犯,對于單純提供信用卡,而未參與后續信息網絡犯罪的,應當將相關犯罪的幫助犯限縮于幫信罪。信用卡的本質用途是用于資金的儲存與流轉,要么被用于接收被害人匯入的資金,要么用于轉移犯罪所得,此時幫信罪行為人主觀上實際對信用卡的使用目的持放任態度,如以實際幫助的結果進行評價,那么提供信用卡的行為則可以直接認定為幫助對象的共犯,此時幫信罪將失去適用的空間,并導致前述行為此罪彼罪的界限不明,致使罪責刑不相適應。對明知他人將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詐騙或掩飾、隱瞞犯罪,偶然提供信用卡,未實施轉賬等行為的,應當評價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行為,但與幫助對象形成長期、穩定的配合關系的則另當別論,因此時行為人與幫助對象已形成實施某一犯罪的共謀,則應以共同犯罪論處,而偶然提供信用卡、獲取少量售卡報酬的行為難以認定雙方達到了“共謀”的程度,這一觀點與《2022年會議紀要》第5條的幫信罪及其關聯犯罪的界限規定是契合的。
2.“跑分”行為的性質認定。隨著對電信網絡犯罪打擊的不斷深入,犯罪手段亦開始翻新,分工愈加明確,并呈現鏈條化犯罪模式,彼此之間聯系極為隱蔽,多使用“紙飛機”“蝙蝠”等具有加密功能的通訊軟件,為司法機關打擊相關犯罪帶來新的挑戰。
所謂“跑分”,是指行為人利用信用卡、第三方支付軟件等工具,將他人違法犯罪資金以在不同賬戶間劃轉、化整為零或聚零為整并轉移等方式進行“洗白”,并從中牟取“手續費”等非法利益。該行為實質上是掩飾、隱瞞行為,在查證屬實確有犯罪資金的前提下,實踐中一般以掩隱罪或上游犯罪的共犯予以認定。但正由于“跑分”行為的隱蔽性,司法機關往往難以查證行為人所轉移資金的性質,此時便失去認定掩隱罪的大前提——犯罪所得,從而導致出罪。筆者認為,“跑分”行為人使用多個信用卡或第三方支付軟件,轉移已查證屬實的犯罪資金的行為,應當以掩隱罪予以處罰;而“跑分”行為人使用多個信用卡或第三方支付軟件轉移資金性質不明的款項,可以以幫信罪進行認定。
(1)掩飾、隱瞞犯罪所得中的轉賬行為即是《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幫信解釋》)第12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支付結算”。一般認為,“支付結算”是行為人在經濟活動中使用銀行卡等結算方式進行貨幣給付、資金清算的行為,主要表現為資金轉移。實際上,“支付結算”的定義在涉卡犯罪相關規定中已有體現。《2022年會議紀要》第4條規定,行為人出租、出售的信用卡被用于接收電信網絡詐騙資金,但行為人未實施代為轉賬、套現、取現等行為,或者未實施為配合他人轉賬、套現、取現而提供刷臉等驗證服務的,不宜認定為《幫信解釋》第12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支付結算”行為。換言之,行為人實施或配合他人實施轉賬、套現、取現等行為,即可認定為“支付結算”行為。行為人明知是信息網絡犯罪資金,仍以轉賬方式進行轉移,且查證屬實的犯罪資金達到20萬元以上,同時符合幫信罪與掩隱罪的構成要件,此時兩罪競合,應當擇之重罪認定,即以掩隱罪認定。
(2)以“跑分”方式轉移資金,但因客觀原因未能查明資金性質的罪名認定。司法實踐中,在“跑分”行為人準備轉移的資金進入行為人所使用的賬戶前,往往已經多次拆分劃轉,司法機關難以溯源,無法查清資金性質,此時“跑分”行為人雖實施掩飾、隱瞞的行為,但因資金性質不明,無法認定為犯罪所得。那么,“跑分”行為人明知其轉移的資金不合法,仍將巨額資金在不同賬戶間頻繁劃轉,是否可以推定該資金為犯罪資金?筆者認為,行為人采取異常的方式轉移資金,僅能推定其主觀上明知是犯罪所得,但無法推定該資金客觀上就是犯罪資金,缺失客觀證據印證資金性質,仍然無法成立掩隱罪。
《幫信解釋》第12條第2款規定,實施支付結算行為,確因客觀條件限制無法查證被幫助對象是否達到犯罪的程度,但相關數額總計達到前款第2項至第4項規定標準五倍以上,即其中支付結算金額在一百萬元以上的,應當以幫信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據此,在確定利用信用卡進行轉賬的行為屬于“支付結算”行為的基礎上,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幫助支付結算一百萬元以上,雖因客觀條件限制無法查證被幫助對象是否達到犯罪程度,但仍可認定其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行為達到“情節嚴重”,以幫信罪進行處罰。
三、涉銀行卡信息網絡犯罪的刑事處遇及治理建議
(一)堅持刑法謙抑,少捕慎訴慎押
對涉銀行卡信息網絡犯罪打擊,伴生較大社會成本。嚴厲的打擊對于抑制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有一定效果,但伴隨而來的是每年新增刑事案件上萬件,其中幫信罪一躍成為全國刑事犯罪的第三大罪、信息網絡犯罪鏈條上的第一大罪。從Q市H縣涉銀行卡信息網絡犯罪數據中可發現,大部分刑事處罰對象為20歲至50歲的青壯年男性,該群體是從事社會生產、建設的中堅力量,多為家庭頂梁柱,打擊的同時亦伴生較大社會成本。在司法辦案中應把握好刑罰的尺度,理性平衡司法投入和產出,積極貫徹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將部分涉銀行卡犯罪從刑事處罰中分流出去,保持刑法在社會治理中的謙抑性,減少社會矛盾和刑罰負面產出。同時還應當堅持對高發犯罪的訴源治理,進一步完善不起訴制度的規制功能,對于此類犯罪嫌疑人的釋法說理、教育引導、行刑銜接等綜合治理應有效跟進,方能使刑法的威懾、教育、引導功能在涉銀行卡信息網絡犯罪案件中不打折扣。
(二)由末端到前端,延伸治理效能
經對Q市H縣幫信罪及洗錢類掩隱罪進行分析,行為人提供或使用已開辦的閑置信用卡占比為37.26%,提供或使用新開辦信用卡占比為55.68%,另7.03%兩者兼具。據此,可從閑置信用卡的清理及嚴控新開辦信用卡兩方面進行治理,達到減少信用卡存量,從根源上壓縮涉卡犯罪的生存空間。
1.進一步清理閑置信用卡。2016年起,中國人民銀行發布新規,將個人銀行結算賬戶分為I類、II類及III類,同一客戶在同一銀行只能開立一個I類賬戶,以此逐步開展銀行卡清理行動,但歷經幾年的清理,凸顯清理門檻過高,清理成效不明顯等問題,市面上仍存有巨量閑置信用卡,并未對涉銀行卡信息網絡犯罪的滋生造成實質性影響。實踐中,行為人即便在某銀行僅有一個賬戶,但在該賬戶下可同時持有多張信用卡,行為人仍有充足的信用卡資源用于出租、出售。相關監管機構應當加大清理力度,降低清理門檻,縮減信用卡的閑置時間,同時建立審查機制,將符合清理條件的閑置信用卡予以注銷,最大限度減少閑置信用卡存量。
2.嚴控新開辦信用卡。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銀行機構對個人新開辦信用卡大開綠燈,在某個時間段內甚至將開辦銀行卡數量作為銀行工作人員的績效考核指標,在加大力度清理閑置信用卡的同時,銀行機構應當嚴格限制信用卡的開辦手續,壓縮新開辦信用卡數量,并在各銀行間建立信息互聯共享機制,嚴格控制個人信用卡數量,防止實踐中行為人同時在多個銀行新開辦多張信用卡的情況出現。探索以公民身份號碼為唯一賬戶的金融賬戶體系,建立健全金融安全監管與相關信用卡犯罪防范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