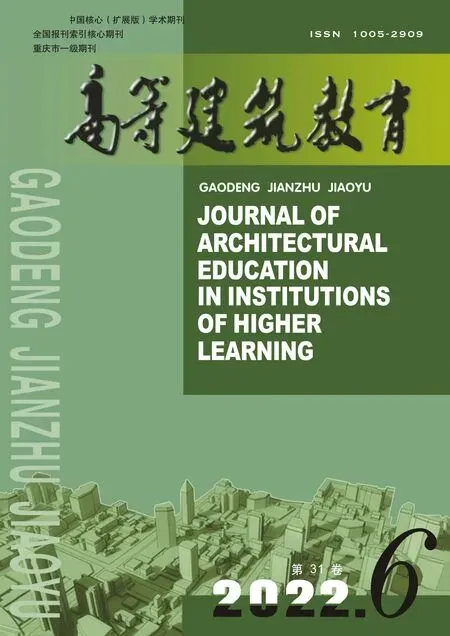城鄉規劃專業課程考評體系研究
——以城鄉生態與環境規劃課程為例
曹 陽,劉晨宇
(鄭州大學 建筑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城鄉規劃專業課程考評一般采用圖紙成果評價、研究論文評分和知識閉卷考試等幾類傳統方式。目前多數課程對學生的考核存在以下弊端:一是偏重實踐能力考評;二是參評主體單一;三是注重最終成果的考核;四是考評重心傾向空間設計,無法依托課程進行考評和實現在講述課程和主干設計課程間形成互補和相互支撐的作用。城鄉生態與環境規劃課程是城鄉規劃專業的核心課程,同時也是架構城鄉規劃理論和生態規劃實踐的重要“橋梁”。課程授課對象為大學四年級城鄉規劃專業學生。課堂授課后,學生會利用課下時間完成課程實踐作業,課程作業選取自然生態環境和生產生活中的典型場所,融合城市生態學知識技能和城鄉規劃以及國土空間規劃最新要求,探索以生態學原理為指向的專項規劃,包含景觀生態規劃、文化生態規劃和水環境生態規劃等多個選題。課程考核沿用傳統設計課程評圖方式,由任課教師來考評。因此,需在精準把握專業課程與設計課程差異的基礎上,探索兩者之間的耦合點,改變傳統對學生實踐能力評價作為課程考評的唯一考核方式,構建具有課程特征的考評體系和探索教學體系考評的構成要素,掌握城市生態規劃課程所涉及的實踐方法和技術,以為設計課程提供理論支撐,促使課程向精細化建設轉型,進而對學生教學考核做出較全面的評價。
一、與設計課程融合為目標導向的課程教學特征
(一)教學重點:注重課程本體研究的系統性
1.哲學層面的系統性
設計課程和城鄉生態與環境規劃課程都需要引導學生進行系統性思考。城市設計課程的系統性是指對設計中城市總體要素的整體性思考,偏重于推敲空間塑造和城市系統的對接,圖紙表達和外在要素、物理環境的對應,以及不同層級空間結構的對應。該系統性較局限于物理空間層面。相比之下,城鄉生態與環境規劃課程研究系統更復雜、場景更宏大。在城鄉規劃設計中生態本底的限定性作用較強,需要把握好物質空間和社會空間的映射關系,評估人為空間的介入是否與自然生態系統、社會生態系統之間相適應,以追求最大共存性與相適性,在動態中尋求統一,最終形成連續、完整、系統的生態保護格局和開敞空間網絡體系,在理清各種空間邊界基礎上保護生態環境,最大程度實現保護生物多樣性。
2.城鄉規劃層面的系統性
城市設計從屬于城鄉規劃大系統,存在于人為控制和創造的環境中,與自然環境的生態屬性聯系較弱。生態規劃中的“生態”不包含于城鄉規劃的范疇中(圖1),城鄉規劃在生態實踐過程中只是處理人和自然共存的手段,是幫助人順應自然的過程。由于“生態”是前置條件,城鄉規劃在被動過程中通過引導、修補、適應性改造等方法和技術手段蘊含了其主動性。雖然在強化資源環境底線約束的今天,三條控制線確定了不同的空間,但城市內外的生態空間也需要相互滲透,通過河流、山脈等自然載體,或通過農田、林園等人工載體在不同空間之間流動。

圖1 生態規劃與城鄉規劃、城市設計的關系
因此,課程教學不僅需要適度延展原有設計課程關注的物理空間系統,幫助學生構建城鄉生態與環境規劃課程中自然和人共建的認知系統,還需要引導學生了解生態規劃和城鄉規劃之間的關系,研究根植于空間的內在原理,認識城鄉規劃是手段而并非目的,進而樹立城鄉規劃為生態系統服務的理念。
(二)教學目標:培養規劃設計實踐的生態價值觀
前期主干設計課程偏向培養學生形態設計和形象空間塑造的能力,關注物質空間構成要素和人在空間中的使用感受。受設計課程影響,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對生態規劃實踐理解存在單一化、表象化和設計化等認知誤區(圖2)。生態規劃并非是以景觀綠化為單一形式的規劃類型。廣義上,生態規劃的內涵本質是需要具有基于自然環境需求、社會訴求、經濟效益和文化生態等城市效益的全域視野,做好資源配置和利用、創建智慧型城市社會、挖掘本土性經濟資本和提取地域性文化特征等內容規劃[1]。為更好融入設計課程,城鄉生態與環境規劃課程通過知識傳授和實踐指導改變了學生對生態規劃的原有認知,認識到規劃實踐不僅是一項建設性活動,還是空間治理背景下的治理性規劃,需對資源利用開展多視角分析。通過以生態環境質量為目標導向的規劃站位,引導學生在課程實踐中樹立多元價值觀,拓寬規劃設計實踐視角,推動生產、生活空間生態化。

圖2 學生語境下的生態規劃
(三)教學過程:注重多階段屬性教學的理性思維關聯
以生態規劃實踐為主線的課程教學包含生態調查、生態研究、規劃策略和空間設計四個階段。生態調查階段,注重對具有或潛在生態功能區域的綜合考察,兼顧對視覺記錄無法感知的社會文化要素以及相關區域或層級的生態系統考察;生態研究階段,學生根據地塊實際狀況對生態因子進行關聯分析,挑選對人類活動有影響的生態因子,探索問題背后的科學原理并分析生態敏感性和建設適宜性分區,進而厘清問題和生態目標之間的差距;規劃策略階段,生態規劃實踐在強調改造和創造的同時,更多注重順應與協調,明晰生態目標利于學生培養和整合生態學規劃思維,使城鄉規劃方法和技術與科學生態價值觀相統一;空間設計階段,通過對生態、活動、功能和空間的適應性過程反饋,結合研究結論和規劃策略,引導學生形成設計邏輯并外化為具體的設計表達,注重課程各教學階段的思維遞進關系。調查對生態研究的支撐性較強,研究結果可對后續規劃精確指導。先規劃后設計的秩序較明顯,規劃對設計有較強控制。
(四)教學思路:體現空間設計的“被約束性”
學生在設計課程中通過空間設計改造地塊的人工構筑環境,形成紀念性或標志性的節點空間以提升形象展示。空間設計在設計課程中的主動性較強,通常強調空間創造的過程和空間改變的結果,很少考慮生態問題。生態規劃被動屬性較強,強調設計的適應性調整,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規劃技術和設計手段。在實踐中,空間設計的相對克制,體現了以生態本底和自然環境為約束底線和前提的低影響力開發屬性。在約束性利用生態資源前提下,確定人工參與的程度。因此,城鄉生態與環境規劃課程和設計課程關注“想法”“設計手法”和“物”“空間”的教學思路有所區別:不過度強調設計的好壞,在分析和研究基礎上,建立“被約束性”的空間設計意識,進而真正理解“底線”與“上限”。
二 、城鄉生態與環境規劃課程考評體系分析
根據課程考評弊端和教學特征,不僅可為考評體系建設提供思路,也可為考評過程清晰化和評價結果科學化提供建設方向,從而結合教學重點確定考評內容;依據教學目標提出客觀評價方法[2];根據多階段教學過程篩選考評因子;依據教學關注點平衡各因子權重(圖3)。

圖3 課程考評體系建設的技術框架
(一)考評內容:研究能力和實踐能力共構,強調考評的協調性和客觀性
課程考評建立以與設計課程考查相補充和協調為方向,立足課程教學重點,以考評學生研究性實踐能力為主要內容。研究性是指以人和自然共建的系統為研究對象,重點分析人及其活動與自然的相互作用,進而形成較系統的生態研究框架;實踐能力是指在系統研究的框架下,采用城鄉規劃手段平衡不同價值空間的能力。
(二)評價方法:多元主體共評,順應課程實踐的時空特征
課程實踐作為考評的重要載體,持續八周時間的課程實踐是對教學培養目標——生態價值觀的重要培養,生態價值觀包含景觀、經濟、科技和文化價值等,能直接體現學生專業能力情況。由于學習能力不易量化,課程考評則可采用主觀定性評分方法進行分析。僅以任課教師作為參評主體存在知識缺口、視角局限等問題[3],易導致評價結果的非科學性。為避免評價結果失真,考評采用任課教師主評、不同知識背景的多位教師參評的方法。
(三)評價方式:多因子共存,緊扣各時段考查目標
考評緊扣教學各階段考查目標,依托階段性成果進行評價。生態調查階段,重點考查發現、評價和預測問題的能力;綜合研究階段,重點考評學生對自然生態系統、社會經濟系統等問題的研究能力;規劃策略階段,重點考查在生態底線約束下,學生統籌城鄉規劃方法和手段解決核心問題的能力;空間設計階段,重點考查適應性設計能力。選取生態調查、綜合研究、規劃統籌和適應性設計能力作為考評的四個一級因子,根據各階段對應的具體內容篩選20個二級因子構建指標體系,根據二級因子依據與設計課程考查內容重疊的不同程度,劃分為設計課程拓展性能力、設計課程差異性能力和設計課程相似性能力。
(四)因子權重:各層級共判,多類型引導合理化分配
生態調查是后三個學習階段的基礎,生態研究與規劃策略之間關系較緊密,結論策略是空間設計的支撐框架。課程強調生態系統研究的指導性和空間設計的克制性,因此設置前三個階段的考評權重高于第四階段。其中,綜合研究能力考評權重最高、生態調查和規劃統籌能力權重相同。同時,分別設置二級考評因子中設計課程差異性能力最高權重、設置設計課程拓展性能力較高權重、設置設計課程相似性能力較低權重(表1)。

表1 城鄉生態與環境規劃課程考評因子及權重
三、課程過程性考評體系實施的教學路徑

圖4 教學資源結構
課程考評的專業性和多元主體參與性等特征,對課程教學資源結構、教學環節組織、課程成果要求和教學進度控制等方面提出了要求。以考評有效實施和教學價值提升為目標,圍繞考評體系與教學實踐提出了相應對策。
(一)教學資源結構
課程以研究性實踐能力為考評內容,因此,教學資源結構突出研究基礎寬厚、實踐主線分明的特征。教學資源(圖4)采用理論基礎知識和專題講座結合的形式,秉持認知先于實踐的原則,突出從研究到實踐的教學秩序并兼顧實踐作業。為避免理論與實踐脫節,采用通識和原理類教學內容先于方法技術類教學方式,以生態原理等理論教學和鋪墊型、引導型、修正型專題研究教學交錯并行的組織思路,通過“教、學、研”等教學程序引入至實踐環節[4]。其中,實踐階段通過嵌入代表性案例解析教學對知識-方法、技術-操作進行串聯。
(二)教學環節組織
依據課程實踐各階段特征,教學組織(圖5)通過探索針對性訓練方式和創造適宜的評價情境,實現加強學生互動參與,和獲取真實考評信息。針對同一選題的學生,可按照規劃師、市民和政府管理者等角色組建學習小組。調查階段由同一選題的學生通過思想碰撞的訓練方式共同參與,將調查信息進行“頭腦風暴”匯總;生態研究階段訓練自主研究能力,由于學生對知識的認知深度存在差異,采用個體形式完成[5];規劃策略階段訓練需要鼓勵學生思考不同站位的價值訴求和能夠平衡多方利益,采用多角色體驗的小組交叉方式。由于設計和表達層面的發揮千差萬別,空間設計階段由個人完成。為避免部分學生在合作過程中懈怠,集體成果需要標注個人工作內容并進行分別評判和打分。

圖5 不同階段的教學組織方式
(三)課程成果要求
課程成果是依據各階段教學目標和教學環節組織進行制定的。同時,成果形式能支撐考評內容、順應考評方法,較直觀地反映學生各階段知識掌握的狀況。因此,可采用可視化和可聽化的成果形式來提升考評效率。根據各階段課程成果要求,引導學生在教師指定的框架內深入思考,減少思維發散,促進多階段屬性學習成果形成合力,激發學生展現顯性和挖掘潛在的能力,進而有助于教師獲取有效的考評信息。

表2 城鄉生態與環境規劃各階段課程成果形式及要求
(四)教學進度控制
各教學階段的進度控制需要根據學生認知節奏和相對薄弱的環節來合理分配課時。生態調查、生態研究和規劃策略這三個教學階段是幫助學生建立理性思維關聯和錘煉專業能力的重要環節[6],為空間設計提供了較具體的解決措施與手段。其中,綜合研究階段的設計課程差異性考評因子數量最高;生態調查和規劃統籌階段的設計課程差異性考評因子較高;設計表達階段的設計課程差異性能力考評因子最低(圖6)。以往課程較缺乏生態研究訓練,因此生態研究階段給予了相對較充足的教學時間。生態調查和規劃策略涉及不同形式的集體協作,需要適度放慢教學進度,以為學生提供多次休整時間。空間設計在前期成果的控制下,生成了形式追隨功能、結構先于設計的理性邏輯[7],弱化了形態的精美設計,適度減少了設計階段的教學時間。

圖6 各教學階段的考評能力
四、結語
城鄉生態與環境規劃課程考評體系研究是任課教師提升教學質量,促進教學空間健康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課程教學特征為考評體系提供了合理、科學的技術路徑,促進考評過程較清晰、考評角度較豐富、考評結果較直觀,體現了精細化課程建設的價值導向。加強考評內容的差異性,有利于協調城鄉生態與環境規劃課程和主干設計課程的關系,明確課程教學重點;采用任課教師領銜、其他教師參與的考評方法,多因子評價的考評方式覆蓋教學全周期,有助于整合師資力量,促進多元能力的培養;合理設置考評因子權重可以進一步突出課程考查方向。考評體系需要與教學實踐相銜接,使考評的實施更具有可操作性。在國土空間規劃時代和人才培養能力的動態變化驅動下,考評還應在考評內容、考評方法、考評方式和考評傾向等方面進行調適,以期考評體系在教學實踐探索中得到持續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