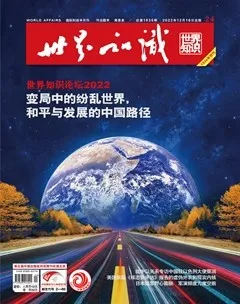東盟:積極應對大國博弈,努力重振“中心地位”
2022年,東南亞地區內部形勢相對穩定,但面臨來自外部的多重考驗,主要是應對中美戰略博弈、烏克蘭危機、新冠疫情和臺海局勢四大沖擊。
東南亞各國政局基本穩定。東盟已經宣布基本克服疫情威脅,恢復正常經濟活動。東盟輪值主席國、柬埔寨總理洪森表示,2022年東盟整體增長率將達5.3%,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成績斐然。未來一段時間東盟的主要任務是聚焦經濟復蘇,應對糧食、能源、金融等方面的安全風險。
四大外部因素沖擊東盟的外交與安全。中美戰略博弈具有全局性和決定性,導致亞太地區秩序加速重組,東盟國家“選邊站”的空間被壓縮。烏克蘭危機則使飽受疫情“摧殘”的東南亞各國進一步面臨能源危機和糧食危機。烏克蘭危機與臺海局勢升溫相互疊加,在“今日烏克蘭、明日南海”“今日烏克蘭、明日東南亞”的國際惡意輿論炒作與影響下,部分東南亞國家的“憂患意識”增強,各國安全立場選擇與政策調整進一步分化。
東盟是加強東南亞區域治理、應對外部沖擊的主體,而“統一性”“中心性”和“大國平衡”是東盟政策的三個“關鍵詞”。內在邏輯是,維護東盟“中心性”是東南亞繼續成為全球投資熱土和經濟發展高地的重要保障,也是提升東盟在大國博弈中戰略價值的基礎。維護東盟“中心性”取決于內外雙因素:內部因素是鞏固東盟的“統一性”,堅持用“同一個聲音”說話;外部因素是堅持“大國平衡”戰略,確保東盟作為“緩沖區”“協調者”的作用。
從2022年的外交實踐看,東盟國家把握機遇,協力打造了亞洲“高光時刻”,其“中心地位”有所回升。具體表現為,柬埔寨、印尼、泰國在11月先后主辦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二十集團(G20)峰會、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此前的2022年5月,為頂住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孤立俄羅斯的壓力,柬埔寨、印尼、泰國三國外長曾發表聯合聲明,宣稱將確保合作精神,強化東盟“中心地位”,邀請所有成員參加這三大會議。
東盟仍面臨一系列困境。緬甸問題和大國博弈削弱了東盟的“統一性”。美國強化盟伴體系之舉則激化了本地區的安全架構之爭,直接威脅到東盟的“中心性”。烏克蘭危機、臺海問題、“印太經濟框架”出臺等事件都成為東盟各國立場選擇的“試金石”。東盟以實際行動給出的答案是,外交上宣稱不“選邊站”,同時根據自身利益在具體議題上“選邊站”,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亞太形勢的復雜性和地區秩序走向的不確定性。
如果以更長時段為觀察尺度,人們會發現東盟對中美戰略博弈的認知與應對表現出較強的動態性與戰略自主性,大致經歷了“擔心與勸和”“明確表達拒絕選邊”“尋求第三條道路”三個階段。在“擔心與勸和”階段,東盟與中美兩國保持密切互動,同時出臺《東盟的“印太展望”》加以應對。2022年以來,東盟的表態出現變化,新加坡明確要求大國不能迫使東盟“選邊站”,印尼總統佐科在G20會議發言中表示東盟不是大國“代理人”。部分東盟國家進而提出要尋找“第三條道路”,即,如果中美不能相互達成妥協,其他國家則需要嘗試在科學、技術、供應鏈領域建立一個更開放包容的多邊網絡,形成“不結盟運動”,而不是靠向哪個陣營。新的“不結盟運動”尚停留在外交討論初期,或將引發更多發展中國家的關注和共鳴。
南海局勢繼續保持斗而不破的基本態勢,出現“三大反差”。一是海上斗爭依然激烈,但相關國家的外交表態都比較克制。中國始終堅持低調處理南海問題。相關東南亞國家從過去的高調轉為相對低調,部分原因是地區整體安全形勢動蕩,各國均有意避免使南海問題同步激化從而“火上澆油”。
二是較之南海直接當事國的克制,域外國家尤其是美國仍持續介入、炒作和制造新話題。美國在2022年發表了《關于海洋界線的第150號報告》《美中在東海和南海的戰略競爭》《中國在全球漁業發展中的作用》等報告,試圖進一步坐實所謂“南海仲裁案裁決”,利用“漁業非法捕撈”等議題抹黑中國,同時強化與東南亞國家在海上態勢感知等領域的安全合作。

2022年11月13日,第二屆東盟全球對話會在柬埔寨首都金邊召開。
三是臺海問題和南海問題形成反差。臺海、南海問題的聯動性顯著加強,臺海局勢的升溫引發周邊國家高度關注。8月,東盟外長發表聯合聲明,支持一個中國原則。同時,部分東南亞國家著手制訂保護本國在臺僑民、投資等安全的預案。相比之下,南海問題有所降溫。但從更長期看,南海問題對周邊環境的整體影響度仍然顯著,中美戰略博弈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決定南海局勢的主要因素。
未來一段時間,中國應堅持“雙軌思路”,進一步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推進“南海行為準則”(COC)磋商,在“全球發展倡議”與“全球安全倡議”指引下,通過海洋可持續性發展實現海洋安全的可持續性。中國還應加強實力建設,加強南海危機管控機制建設,應對因美國等域外國家不斷將南海問題司法化、國際化、軍事化帶來的現實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