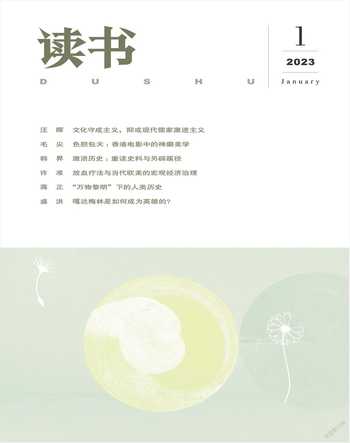作為一種話語策略的“少年中國”
周旻
同許多晚清輸入的新語詞相似,“少年中國”在根源上對應于英語中的“Young China”, 語義中包括意指“將事物變得更好”的 Reform(改革)及譯作“革命”“ 叛亂”的Revolution,最初是英語世界觀察晚清革新變局的框架。一八九八年前后,力主保皇的康有為與一心排滿的孫中山曾不約而同地將它作為一種話語策略,宣傳自己的政治理想。觀察梁啟超“少年中國”概念發(fā)展的“前史”,或許能讓我們理解這一話語不可思議的潛在勢能。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英文報刊及知識界以十九世紀青年運動比附“戊戌變法”,并以代際結構(generation)理解政治變革力量的內在產生機制,創(chuàng)造出“Young China”。
法國革命開創(chuàng)“以青年為主體的許諾美好未來的政治修辭”,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少年英格蘭”“少年德意志”等變革組織先后在歐洲出現(xiàn),青年成為一種充滿活力與反叛力的新興政治力量。“少年歐洲”運動既強調老少的對抗體系,又隱喻傾向改革的政治綱領,即“呼吁給人民更多自由和權利”。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變,則是一場朝廷官員領銜的“變法運動”,意在從政體制度的內部解決國家落后的問題,參照系應是中國歷史上的商鞅變法、熙寧變法等。這原本是中國的內政,但此時期正是汪暉所說的“全球范圍內的共時關系達到前所未有深度和密度的時代”,英美各國的官員、傳教士及背后的政治勢力都聚焦于正在發(fā)生的政治事件,英語世界亟須一套易于接受、理解的敘事模式。“少年”(Young)、“改革”(Reform)、“中國”(China)結合而成的話語結構,在英文報刊場域迅速完成構型,為清末的政治變革提供了一個世界性、全球化的解釋框架。
清末最重要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曾刊發(fā)數(shù)篇報道、社論、評論,追蹤戊戌政變之始末。特別強調了“變政者”與“不可變政者”的年齡差:前者是年輕的、熱情的、熱衷了解新事物的“干事”,或是沒有實權的青年官吏;后者則年齡衰老、精力不濟,“因循茍且,畏難偷安”。英文中并無直接對應“變法”的語詞,中文“變法”的概念,也無涉于年齡;因此,年輕者與變革者(reformist)之間畫上等號,是典型的英文邏輯。變法事件中的不同陣營,如光緒與慈禧、康有為與李鴻章,被劃分為生理年齡的界限,權力斗爭被描述為“中國野蠻地謀殺了他的第一批愛國青年”。在《字林西報》公布的光緒留給康有為的密詔中,變法完全向年輕人與“新觀念”傾斜:“我們只有采用西方的方法,才能拯救我們的帝國;我們只有鏟除老派的保守大臣,替換成年輕的、有知識的、了解西方事務的人,才有可能施行我們想要的改革。”至此,“少年改革中國”的主旨已盡顯無疑。在此視閾下,中國將被改造為現(xiàn)代意識形態(tài)中的民族國家。
變法后康有為的言論方式,進一步鞏固了“少年中國”的框架。一八九八年十月七日,康接受《中國郵報》的專訪,用英文向世界講述維新事件的“真相”,這則采訪是親歷者首次公開發(fā)言,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文中,他大量使用此前并不流行的“少年”話語,有意確立變法主體、犧牲黨人的“青年”身份。茅海建指出,康有為所控訴的老舊勢力阻撓維新,是為了宣揚變法的正當性—他雖然是個失敗者,但失敗的原因是守舊者的阻礙,是當政者未能采用他的治國方針。總體而言,康有為的策略是順勢利用英文報刊上的話語形式,一方面總結經驗,構建老/ 少、新/ 舊、保守/ 改革的政治結構,一方面使用“維新少年”“少年革命”等語詞“重寫”自己的政治理念,在原本的變法綱領中注入對未來國家政體、社會組織的想象,將其歸入“改革”的時代洪流。其目的也很明確:一則為事變正名,一則尋求英國政府的支持。因此,積極迎合西方社會對政治變革中“少年”的看重,也可說是維新黨海外政治活動的一環(huán)。戊戌政變一年之后,康有為再與英人分析中國政局,便提出“中國之人分為三黨”,“其一帝與后也,其二則老耄而守舊者,其三則少年而維新者也”;再次以“少年”的特性擴大了維新黨人的范疇—熱血于愛國、想要改變中國者皆為“維新少年”。
康有為把維新運動敘述成一場少年改革中國的壯舉,帶有后置性;出身夏威夷、求學港澳,輾轉于跨語際之間的孫中山,更早就意識到革命話語與國際化輿論接軌的重要性。據(jù)陳建華考辨,一八九五年前后,孫中山初登歷史舞臺,即在“revolution”(革命)一詞的使用上遭遇困境,概因“革命”在英語世界中所指不明,不乏“造反”“叛亂”“暴力”等負面色彩。于是他緊扣“reform”這一更易為西方接受的語匯,對外呈現(xiàn)出溫和改良的立場。
一八九七年, 孫中山的英文自傳《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London )在英國出版。書中稱早年加入了名為“Young China Party”(少年中國黨)的團體:“它的宗旨是如此賢明,如此溫良,如此充滿希望,因此我贊同他們的宗旨,并立刻加入成為該會成員,而且我自信入會后定能盡全力為國為民牟取福利。我們計劃采用和平的改革手段,希望呈遞一份有理有節(jié)的改革方案給朝廷,促使其創(chuàng)行一種與現(xiàn)代時勢相符合的新政體。最主要的目標是制定立憲政體以代替守舊、腐敗和衰弱不堪的舊政體。”事實上,他加入的是基督教“教友少年會”。原本旨在“聯(lián)絡教中子弟”的宗教團體經孫中山改寫,搖身一變?yōu)榇龠M改革的政治會黨。孫中山的政治才能已鋪陳在字里行間。
一八九六年,廣州起義失敗,孫中山轉往歐洲,向華僑宣傳革命,“欲除虜興治,罰難救民,步法泰西”;在英國又遭清政府誘捕,命懸一線。幸得康德黎設法搭救,及英國媒體對此事的報道,他才在十月二十三日脫險。《倫敦蒙難記》在這起轟動中外、震動歐洲的事件背景下出版,又因英國民眾對此事的持續(xù)關注而流行暢銷,成功將孫中山塑造成一名受到腐朽政府迫害的政治英雄。“少年中國黨”概念的出現(xiàn),很可能是為了回應新聞報章對他的采訪。《每日新聞》的記者詢問孫中山是否為白蓮教成員,他答道:“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團體,我們的運動是新的,限于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他們大部分住在國外。”更有《中國郵報》將其比作金田軍起義。面對媒體的追問,孫中山需要一個合適的團體,為自己洗脫傾覆朝廷的嫌疑,模糊自己的革命活動。“少年某國”在當時的歐洲,是對維新政黨的一種稱謂,無疑是一個恰切的命名。事實也證明,避談“革命”而只說“少年中國”的話語策略是成功的;《倫敦蒙難記》出版后,英國的書評紛紛應和,稱孫中山“致力于政治活動,參加他所稱的‘少年中國黨’,其目標是國家體制—向皇上獻政改之策,建議建立起一個立憲政府”。
按孫中山的解釋,使用“Young China”概括自家的政治活動,乃“事急從權”:英人較為保守,不宜與其談革命,需要一個可以容納革命思想而又不至于引起英人反感的表述方式,因此他想到了“少年某國某政團”。根據(jù)馮自由的回憶與解讀,這一固定的命名結構,來源于十九世紀西方各國的政治運動,鼻祖正是馬志尼的“少年意大利”。就中國而言,自一八九五到一九0九年,無論改革或革命、保守或激烈、立憲或共和,一切政治團體都可認為是為中華之崛起,故也都可以“少年中國”為名。這一兼具愛國性和先進性的語詞組合,不僅“掩護”了孫中山的“革命”,成功奠定了他愛國、求變的先鋒形象,更于無意間打破了“少年”與“改革”相捆綁的穩(wěn)定結構,在作為一種策略已取得成功的“少年中國”話語中埋下“革命”的伏筆。
一九00年梁啟超寫作《少年中國說》時,與孫中山有短暫的交往和合作。“少年中國”的未來烏托邦宏論也許曾出現(xiàn)在二人的談話中,留下“革命家”(revolutionist)的言說印記。兩年后,革命與維新兩大陣營曾就“少年”身份的歸屬展開爭奪,這番后話也印證了“少年中國”話語本身所蘊含的充沛能量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