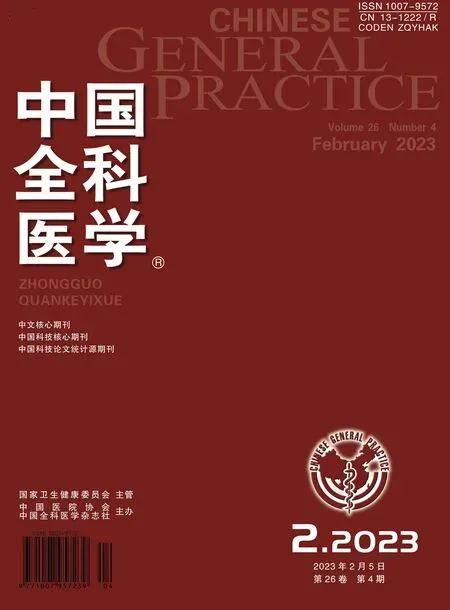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與死亡趨勢及其年齡-時期-隊列模型分析
趙虹琳,李巧梅,李婷婷,丁國武
艾滋病又可稱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AIDS),是由艾滋病病毒〔即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一種病死率極高的惡性傳染病[1]。盡管中國出臺了“四免一關懷”政策[2],但艾滋病防控工作仍面臨嚴峻挑戰。2003年,全國因法定傳染病死亡的人數為6 474例,其中379例死于艾滋病,艾滋病是中國第五大傳染病死因。2008年,全國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數增至5 389例,艾滋病成為中國傳染病致死的主要原因。2018年,全國共報告64 170例新發艾滋病病例,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數增至18 780例,是其他各種傳染病死亡人數總和的4.3倍[3]。2017年,全球有近3 690萬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約94萬例因艾滋病死亡,約有180萬例新發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4]。由此可見,艾滋病仍是全球范圍內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Joinpoint回歸模型和年齡-時期-隊列模型目前已被廣泛應用于流行病發病與死亡趨勢分析[5-6]。目前,國內學者多基于省/市級數據對艾滋病發病與死亡趨勢進行分析,且尚缺乏將年齡-時期-隊列模型運用于艾滋病發病與死亡率趨勢分析的研究報道。通過運用年齡-時期-隊列模型,可有效避免年齡、時期和隊列3個因素之間交互作用導致估計結果出現偏差這一問題的產生;能夠在控制任意兩個變量的情況下,分析第三個變量與艾滋病發病率/死亡率之間的關系[7]。本研究基于中國公共衛生科學數據中心現有數據,并引入Joinpoint回歸模型及年齡-時期-隊列模型,對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與死亡趨勢進行分析,并探究年齡、時期及隊列3個因素對中國艾滋病發病率與死亡率的影響,以期能夠為中國艾滋病防控工作提供參考與建議。
1 資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于2022年3月,以中國公共衛生科學數據中心2004—2018年的網絡直報系統數據作為數據來源,提取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各年齡組發病人數、發病率、死亡人數及死亡率數據(數據庫識別符:c2ca694e-3995-4c7f-9078-3ed0aaf14556)。 由 于 0~4歲及≥80歲年齡組艾滋病發病與死亡情況數據缺失,因此本研究選取5~79歲居民的數據進行分析。
1.2 數據處理 采用Excel 2019軟件建立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與死亡情況數據庫,并進行繪圖。利用提取的原始數據計算2004—2018年中國歷年艾滋病發病人數、發病率、死亡人數及死亡率。各年齡組標準化發病率、各年齡組標準化死亡率分別由各年齡組粗發病率、各年齡組粗死亡率與各年齡組標準人口構成比計算而得,其中各年齡組標準人數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1.3 統計學方法
1.3.1 Joinpoint回歸模型 采用由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開發的Joinpoint 4.9.0.1軟件對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與死亡率進行趨勢分析。Joinpoint回歸模型通過對數線性模型對數據進行擬合,將長期趨勢線科學地分成若干段,并通過Monte Carlo置換檢驗的方法判斷連接點的個數、位置及P值,根據修正貝葉斯信息準則選擇最佳模型[8]。計算艾滋病發病率與死亡率的年度變化百分比(APC)、平均年度變化百分比(AAPC)及其95%CI。APC>0,表示發病率/死亡率逐年遞增;APC<0,提示發病率/死亡率逐年遞減;當無連接點時,即APC=AAPC時,發病率/死亡率呈單調遞增/單調遞減趨勢[9]。檢驗水準α=0.05(雙側)。
1.3.2 年齡-時期-隊列模型分析 采用由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研發的基于R語言的網絡分析工具(https://analysistools.cancer.gov/apc/)分析年齡、時期、隊列因素對艾滋病發病率與死亡率的影響。年齡-時期-隊列模型的一般表達式為:Y=αo+αXa+βXp+γXc+ε,其中Y代表發病率或死亡率,Xa、Xp、Xc分別代表年齡、時期、出生年份,α、β、γ分別代表年齡效應、時期效應、出生隊列效應,αo為截距,ε為殘差。該模型要求年齡、時期和隊列的間隔保持一致[10]。以5為間隔對年齡、時期和隊列進行分段:將5~79歲分為15個年齡組;將2004—2018年劃分為3個時期(為提高發病與死亡風險的時間精度,本研究采用2008、2013及2018年單年度數據代替各個時期的5年平均數據[11]);出生隊列由時期減去年齡得到(1929—2013年),將隊列分為17組。選取中心年齡、時期和隊列作為對照組,年齡對照組=(年齡組數+1)/2,時期對照組=(時期組數+1)/2,隊列對照組=時期對照組-年齡對照組+年齡組數。評價參數包括:(1)凈變化,按時期和出生隊列顯示的總體對數線性趨勢,即全人群發病率/死亡率的APC;(2)局部變化,按時期和出生隊列顯示的各年齡組對數線性趨勢,即各年齡組發病率/死亡率的APC[12];(3)縱向年齡曲線,調整時期偏差后特定年齡組的發病率/死亡率曲線,可看作年齡效應;(4)時期率比(RR)值,以對照時期為參照的時期的年齡別RR值;(5)隊列RR值,以對照隊列為參照的隊列的年齡別RR值[13]。采用Wald χ2檢驗進行參數估計。檢驗水準α=0.05(雙側)。
1.3.3 年齡-時期-隊列模型的共線性問題 由于該模型中年齡、時期、隊列三個因素間存在完全共線性,采用內生因子法解決參數不可估計的問題。YANG等[14]發現基于內生因子法的估計值與基于傳統廣義線性模型的估計值接近,且內生因子法具有不需要先驗信息的特點,其估計值收斂且唯一。
2 結果
2.1 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與死亡率總體變化趨勢 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與死亡率均呈上升趨勢,發病率從2004年的0.248 9/105上升至2018年的4.956 9/105,死亡率從2004年的0.060 5/105上升至2018年的1.431 2/105,見圖1。

圖1 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與死亡率變化趨勢Figure 1 Trends of AIDS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2004—2018
2.2 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與死亡率的Joinpoint回歸模型結果 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的Joinpoint 回歸模型結果顯示,模型優選結果為2012年1個節點,2004—2012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 年 均 上 升 34.20%〔95%CI(30.20%,38.20%),P<0.001〕,2012—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年均上升 9.00%〔95%CI(7.00%,11.10%),P<0.001〕,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年均上升22.70%〔95%CI(20.70%,24.80%),P<0.001〕。
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死亡率的Joinpoint 回歸模型結果顯示,模型優選結果為2010年1個節點,2004—2010年中國艾滋病死亡率年均上升34.50%〔95%CI(16.30%,55.50%),P=0.001〕,2010—2018年中國艾滋病死亡率年均上升8.30%〔95%CI(4.40%,12.40%),P=0.001〕,2004—2018年 中國艾滋病死亡率年均上升18.80%〔95%CI(12.10%,25.90%),P<0.001〕。
2.3 中國艾滋病發病率與死亡率的年齡-時期-隊列模型分析結果 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與死亡率的凈變化、總年齡偏差、總時期偏差、總隊列偏差、全時期RR值、全隊列RR值及所有局部變化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01),提示中國艾滋病發病率與死亡率的變化均受到年齡、時期、隊列因素的影響,見表1。

表1 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與死亡率年齡-時期-隊列模型檢驗結果Table 1 Age-period-cohort effects on AIDS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8
2.3.1 年齡效應分析結果 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和死亡率縱向年齡曲線均呈“J”字形上升趨勢。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從5~9歲組的0.000 4/105上升至75~79歲組的2 828.828 5/105,5~49歲發病率呈緩慢上升趨勢,從50~54歲組開始上升速度加快,其中65~69歲組后上升速度相對較快,在75~79歲組達到高峰(圖2);中國艾滋病死亡率從5~9歲組的0.000 4/105上升至 75~79 歲組的 740.297 4/105,5~49 歲死亡率處于較低水平,自50~54歲組開始上升速度加快,于75~79歲組達到峰值(圖3)。

圖2 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的縱向年齡曲線Figure 2 Temporal trend curve of age-specific AIDS incidence in China,2004—2018

圖3 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死亡率的縱向年齡曲線Figure 3 Temporal trend curve of age-specific AIDS mortality in China,2004—2018
2.3.2 時期效應分析結果 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與死亡率的時期RR值隨著時期的推移而增加,以2009—2013年時期組為對照組(時期RR值=1.000 0),2014—2018年時期組發病風險〔RR值(95%CI)=2.024 4(1.877 1,2.183 2)〕與死亡風險〔RR值(95%CI)=1.522 6(1.412 8,1.640 9)〕均達到峰值,見圖4~5。

圖4 中國艾滋病發病率的時期效應Figure 4 Period effects on AIDS incidence in China,2004—2018

圖5 中國艾滋病死亡率的時期效應Figure 5 Period effects on AIDS mortality in China,2004—2018
2.3.3 隊列效應分析結果 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與死亡風險出生隊列效應均呈上升趨勢,以1969—1973年出生隊列組為對照組(出生隊列RR值=1.000 0),1929—1968年出生的隊列艾滋病發病與死亡風險的RR值均<1.000 0,且呈緩慢增長趨勢,1983年后的出生隊列隨出生年份的推移艾滋病發病與死亡風險增長速度呈逐漸加快的趨勢,2009—2013年出生隊列組發病風險〔RR 值(95%CI)=471.385 3(118.524 3,1 874.755 6)〕與死亡風險〔RR值(95%CI)=93.634 5(21.168 0,414.182 4)〕均達到峰值。但2004—2008年出生隊列組與1999—2003年出生隊列組相比,艾滋病發病與死亡風險略有所下降(圖6~7)。

圖6 中國艾滋病發病率的出生隊列效應Figure 6 Birth cohort effect on AIDS incidence in China,2004—2018

圖7 中國艾滋病死亡率的出生隊列效應Figure 7 Birth cohort effect on AIDS mortality in China,2004—2018
3 討論
本研究采用Joinpoint回歸模型和年齡-時期-隊列模型分析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與死亡趨勢,并探討年齡、時期和出生隊列3個維度對艾滋病發病率及死亡率的影響。Joinpoint回歸模型結果顯示,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與死亡率均呈上升趨勢,分別年均上升22.70%和18.80%。2004年中國出臺了“四免一關懷”政策,2006年頒布的《艾滋病防治條例》、2012年發布的《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動計劃》(國辦發〔2012〕4號)及2017年發布的《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動計劃》(國辦發〔2017〕8號)中均提出要“擴大監測覆蓋面,最大限度發現感染者”[15]。在上述政策背景下,艾滋病病毒抗體篩查工作在全國范圍內得到了較為廣泛的開展,這也使得越來越多的艾滋病病例能被及時地發現。目前,對于將艾滋病病毒從體內徹底清除尚缺乏有效手段,加之中國艾滋病治療藥物的種類較為有限,艾滋病病毒耐藥性激增[16],因此艾滋病的死亡率呈現上升趨勢。
年齡-時期-隊列模型結果顯示,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與死亡率均受到年齡、時期及隊列因素的影響。從縱向年齡曲線來看,隨著年齡的增長,艾滋病的發病率與死亡率均呈現上升趨勢。在艾滋病流行的早期階段,青年群體是艾滋病的高發人群,健康教育宣傳活動的目標人群以年輕人為主,老年群體常未被包含在內,導致老年群體對艾滋病相關知識相對缺乏[17]。既往研究表明,老年人艾滋病防治知識知曉率較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風險意識薄弱[18]。同時老年人的性需求常被其伴侶和社會所忽略,但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當代老年人的身體狀況與過去老年人相比有了明顯改善,部分老年人仍處于性活躍狀態[19],且無保護措施的性行為在該群體中較為常見,因此危險性行為加劇了艾滋病在中老年群體中的流行。已有研究證實,艾滋病患者血紅蛋白水平與其死亡風險有著密切關系,艾滋病患者血紅蛋白水平下降可導致其死亡風險增加[20],而≥50歲群體貧血患病率較高[21],其在感染艾滋病病毒后更易出現長期貧血,死亡的風險也就相應增加。中老年群體死亡風險較高的原因還可能為:大量艾滋病患者在接受抗反轉錄病毒治療后存活多年,病程延長,進入中老年階段后免疫系統功能明顯下降,艾滋病相關并發癥和其他疾病共同導致其死亡[22]。
時期效應是指某個特定的時期自然條件或社會環境發生變化而導致的發病/死亡風險[23]。根據年齡-時期-隊列模型結果,艾滋病發病與死亡風險均隨著時期的推移逐漸上升。在2004年前,中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隨訪管理尚未形成統一的標準和規范,導致隨訪效果不理想,且由于檢測遵循自愿原則,報告的發病人數明顯少于實際發病人數[16]。而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優化了艾滋病病毒檢測策略。自愿咨詢和檢測(VCT)站點數量隨著時期的推移成倍增長,持續推進高危人群VTC、醫療機構擴大篩查、社會組織動員檢測、重點人群自我檢測等[24]措施的實施使得中國艾滋病檢測率大幅提升,從而使越來越多的艾滋病病例能夠得到及時診斷。另外,由于艾滋病的潛伏期為8~9年,隨著大量早期發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陸續進入艾滋病期,中國逐步進入艾滋病發病高峰期[22]。CD4+T淋巴細胞水平及診斷時機是艾滋病患者抗反轉錄病毒治療效果的重要影響因素[25],CD4+T淋巴細胞水平越高且越早接受科學、規范的治療,艾滋病患者死亡風險越低。已有研究證實,超1/3的艾滋病新發病例CD4+T淋巴細胞水平偏低[26-27];一項橫斷面研究結果顯示,2012—2016年我國西南地區報告的45 000例艾滋病新發病例/艾滋病病毒新發感染者中,45%就診時已經處于晚期階段[28]。因此,在今后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要加快推進艾滋病早期篩查和早診早治。
隊列效應反映了生命早期環境的變化,是指同一出生隊列中的個體在假定同樣暴露于某種疾病危險因素的情況下發病/死亡的風險[29]。本研究發現,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與死亡風險出生隊列效應均呈上升趨勢,1929—1983年出生的隊列艾滋病發病與死亡風險處于較低水平,1983年后的出生隊列隨出生年份的推移艾滋病發病與死亡風險增長速度呈逐漸加快的趨勢。1981年,全球首例艾滋病病例被報告,艾滋病開始被世界所認識。與其他國家(地區)相比,艾滋病在中國流行較晚。1985年,中國發現首例艾滋病患者;1989年,我國在云南省瑞麗市吸毒者中首次發現規模人群感染艾滋病病毒;1994年末至1995年初,在中國中部和東部部分貧困地區的農村出現了較多非法從事倒賣原料血漿活動的單采血漿站,捐獻血漿帶來的可觀收入吸引了收入水平較低的農民反復參加獻血活動。非法從事倒賣原料血漿活動的單采血漿站所采取的重復使用一次性醫療用品、使用未經消毒的器械和設備等行為使得艾滋病病毒在血漿供體間快速傳播[30-32],這更加劇了艾滋病的流行。性傳播是艾滋病病毒傳播的一個重要途徑,中國通過異性性行為感染艾滋病病毒者數量逐年上升[33],中國男男性行為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超過靜脈吸毒者,且有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男男性行為群體中艾滋病毒流行率逐漸上升[34]。隨著同性戀群體得到社會更多的理解和接納,以及互聯網的飛速發展,男男性行為者常通過男同社交媒體與多名性伴侶保持聯系。同時越來越多的同性戀酒吧、俱樂部和其他同性戀場所的出現都為艾滋病的傳播提供了條件[35],且高風險行為在該群體中也較為常見。一項針對中國2 250例男男性行為者的性行為進行的研究表明,僅40%的男男性行為者在過去6個月內進行肛交時持續使用避孕套[36],且在“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觀念、“傳宗接代”的思想和對同性戀身份的恥辱感的影響下,部分男男性行為者選擇與異性結婚,而只有25.6%的男男性行為者在過去6個月內與女性發生性關系時會持續使用避孕套[37]。因此,男男性行為者還有可能將艾滋病病毒傳播給女性伴侶,甚至下一代。此外,既往研究顯示,該群體并不傾向于每年定期接受艾滋病病毒檢測,甚至有部分感染者在感染艾滋病病毒前從未接受過艾滋病病毒檢測[38],這也可能會導致該群體艾滋病發病與死亡風險的上升。
綜上所述,2004—2018年中國艾滋病發病率與死亡率均呈上升趨勢,老年人是高危人群。針對該群體,可開展形式多元化、接受度高且覆蓋面廣的宣傳教育活動,同時應呼吁子女主動關心和重視老年人的精神生活,給予老年人更多理解和包容,引導老年人培養積極的興趣與愛好,鼓勵老年人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針對男男性行為者,應加強對其的安全性行為教育,并向其推廣艾滋病病毒自我檢測試劑盒,以增強其艾滋病病毒檢測意識,提高檢測的便利性,最大限度地保護其隱私。衛生健康行政部門應加強重點人群艾滋病主動篩查工作,積極推進艾滋病早期篩查和早診早治,進而從整體上降低艾滋病的發病率與死亡率。此外,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應積極開展旨在宣傳艾滋病危害和防治措施的自省式健康教育活動,以提高居民對艾滋病相關知識的知曉率,確保艾滋病防控的各項工作順利推進[39]。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未能將0~4、≥80歲人群的數據納入分析,且受限于數據,未能對不同性別、地區等特征人群的艾滋病發病與死亡情況進行亞組分析。
作者貢獻:趙虹琳負責文章整體構思與設計、數據收集與數據處理、文章撰寫與修改;李巧梅負責對文章提出修改意見;李婷婷負責部分數據的整理;丁國武負責文章質量的控制和監督。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