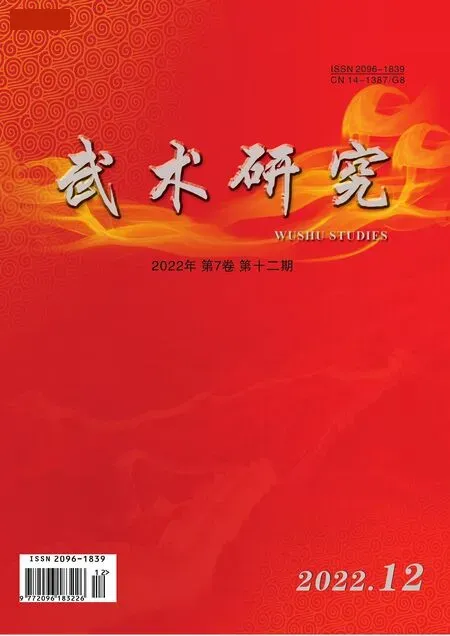近代社會轉型中我國傳統武術的嬗變分析
曾麗春 吳寶升
溫州大學體育與健康學院,浙江 溫州 325000
1 前言
傳統武術衍生于農耕文明,派系種類繁多。歷史變革,時代遷移,一切生活需要,漸次遞變,于是由前傳后的傳統武術,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傳統體育經過幾千年的積淀,形成了以儒家“天人合一”和“氣一元論”為哲學基礎,以保健性、表演性為基礎模式,以崇尚禮讓、寬厚、平和為價值取向的體育文化。在外在形式上主要以健康長壽為終極目的的養生和以保身護體、技擊與套路相結合的武術為一體的內外合一,整體圓融、穩定而豐實的結構體系[1]。那么,作為中國傳統體育極具代表性的項目——傳統武術,在鴉片戰爭后的近代社會轉型中產生了何種變化?傳統武術又如何突破傳統文化的穩定結構,適應時代的變化發展?窺一斑而知全豹,處一域而觀全局。本文集中關注的是鴉片戰爭后國門被打開后的中國,其社會轉型的漸進發展對傳統武術產生的具體影響,試圖厘清綿延幾千年的傳統武術在1840-1937年間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自身的轉變狀況,以期為當今社會轉型中傳統體育活動適應時代發展的生存演化提供經驗啟示。
研究主要選取了洋務運動(清朝統治階級的自救運動)、甲午中日戰爭(回光返照帝國的重創)、辛亥革命(社會結構的重新構建)以及“土洋體育之爭”(中國體育的發展道路)這四個代表性事件,從具體的社會歷史出發,既是縱向上隨著時間推進社會轉型變化的深入成像,也是橫向上綜合深入考慮政治改革、戰事動亂、社會革命、思想革新的重點聚焦,推敲傳統武術的時代性與流變性,分析社會轉型的漸進發展對傳統武術產生的具體影響。
2 近代社會轉型與傳統武術嬗變
封建社會專制行政之網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形成了一個自洽的封閉系統。中世紀的幽靈消失后,資本主義的“浪潮”從西歐向世界擴張,受這股勢力影響,中國運行了幾千年的自洽封閉系統也開始向新的社會形態轉變。在傳統社會中,人們從事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生產,以家庭為中心承擔特定的角色,以地緣、親緣為人與人之間的主要聯系紐帶。鴉片戰爭后的中國,西方列強的侵入、西學東漸的思潮以及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社會轉型,使中華民族面臨著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社會轉型將原先的秩序打亂,支持傳統武術開展的社會結構被破壞,新生的社會結構尚未成型。牽一發而動全身,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其政治生活的革新,社會思潮的變化或多或少地影響著傳統體育活動。
2.1 洋務運動:傳統武術裂變伊始
一個民族的獨立首先是民族精神獨立,在外來文化入侵時,人們會情不自禁地從傳統文化中尋找理論來抵御外來文化的入侵。在洋務運動中,西式體育和傳統體育活動二者同時在國人生活中并立,因西方體育是伴隨著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炮艦進入中國的,所以人們以傳統觀念來審視西方體育時,或者敬而遠之,或者不屑一顧[2]。在文化觀念的偏差上,傳統武術與西式兵操,傳統體育與西式體育的對擂揭開序幕。
2.1.1 底層大眾的生存需要:民間傳統武術螺旋式上升發展
在混沌的局勢中,清王朝行政管理的執行力開始下降,禁武令的執行管理因社會形式的復雜性未能自始至終貫徹實現,輔之以西方侵略者夾帶著西方文明的進一步入侵,民族危機加劇。民族矛盾的加劇激化了國內階級矛盾,在社會底層的大眾,因缺少生存生活資料,不能同商賈官吏一樣可以依靠金錢權力換取平穩安定的生活,只能寄期望于習練傳統武術,以達自保,在混亂的社會中以求容身之所。各地農民運動的上演就為傳統武術活動的展開提供了畸形的歷史軌跡。1841年,廣東三元里人民的英勇抗英斗爭掀開了中國人民反帝運動的序幕,為了在復雜動蕩的社會下安身立命,許多礦工、紡織工及其它行業的工人都組織有武館,工余時間常請武師到館教授武藝[3]。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在當時的民間嚴禁習練拳術的社會背景下,太平軍對軍事訓練有著足夠的重視,促進了農民的習武活動。軍中許多名將都是精通武藝的好手[4]。隨著義和團的發展壯大,清政府害怕其以武力威脅乃至更替政權,便施強制手段以期禁武。當時社會人民,頗以武為危事而咸懷戒心。然武術在中國相沿成風,官府雖施強制手段,依然不能制止[5]。在浩浩蕩蕩的農民革命的新局勢中,其社會大背景的禁武并未割斷傳統武術的生存命脈,也未在戰爭與革命的炮火中銷聲匿跡。雖有不少武術名家歿于革命暴亂斗爭之中,但傳統武術命脈一直系于農民大眾之中。農民大眾成為傳統武術的主要根基力量,成為燎原星火的點燃者,在戰爭中,傳統武術其中于民間呈螺旋式上升發展趨勢。
2.1.2 上層階級引入西式兵操:未觸及傳統武術根基
隨著西方的堅船利炮侵入中國,審時度勢后,國人將目光投向了西方的“技巧”,紛紛投身借“西法以自強”的活動。在“中體西用”的指導思想下各精英人物深信“師夷長技以制夷”,為此紛紛探索和利用西方近代新式體育。從曾國藩建立湘軍,李鴻章設立淮軍,左宗棠創辦福建船政學堂,再到張之洞興辦兩廣水陸師學堂,這些在當時具有先進思想的精英人物都看到了西方的先進利器和西洋體操的軍事價值,且紛紛將西方兵操體育引入自己陣營之中[6]。在濃厚的軍事烙印之下,以期驅侮自強的國人毫不猶豫地將西方的所有一并拿來學習。此時,國人對西方體育存在一定的認知偏差。于軍隊開展的“兵式體操”,在王維泰看來不過是我國古代舞蹈遺留下來的鍛煉方式。“體操者實非西法,乃我中古習舞之遺意,而教子弟以禮讓之大本也。”[5]作為政治變革的產物,此時西式兵操僅是一種達成強兵御侮的手段。這種自上而下的器物改革并未觸及傳統武術根基,故當火器未盛之時,武術實為軍中之操法,及改習外國兵操,仍不棄武術[5]109。這場關于西方器物學習的改革并未對我國傳統武術產生較大影響,但是傳統武術也開始由輝煌走向沒落,艱難地走向了轉型之路。
2.2 尚武思想:傳統武術在價值審視后消沉
甲午海戰中北洋水軍落敗,這極大地刺激了國人,中國先進分子紛紛試圖求尋“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之道。梁啟超在其著作《中國之武士道》中就大聲疾呼中國應提倡尚武精神,“今者愛國之士,莫不知獎勵尚武精神之為急務”[7]。乙巳四月初三日《時敏報》登載的題為《論尚武主義》一文,即闡明“曠觀古今之歷史,橫覽中外之大勢,見夫國家忽興忽亡,忽強忽弱,而究其所以致此之由……在乎民質尚武與否而已。蓋民質者,國家之要素,社會之基礎,興亡之根源,而國家所賴以成立也。民質能尚武,則其國強,強則存;民質不尚武,則其國弱,弱則亡。英、法、德、美何以強?強于民質之尚武也;印度、波蘭何以亡?亡于民質之不尚武也[8]。隨著民族危機的加重,各仁人志士在思考和對比中將目光轉向日本,得出的共識是:日本之所以能擺脫積貧積弱的處境,與“富國強兵”之國策有關。中國欲救亡圖存,唯有學習日本和西方,提倡尚武,重視體育[9]。據此,近代中國人開始從更深的層面接受西方體育和認識西方體育[10]。在此情形之下,政府改練新軍,學校增設體操一科,頒布《奏定學堂章程規定》[5]。“嗣科舉既各省遍設學堂,武術遂棄而不用,各處之武學館亦列入天演淘汰之列。北京一隅仍多派各門武術專家,但傳授生徒不能如前之自由,較之前之盛況相去遠矣,軍事上,綠營裁撤,各軍隊均改外國操法不復專事武術;在民間集團多用火器,各省鏢局亦不負往昔之盛。各富商巨紳響之須延武士保護者,今亦自置火器,不負專恃武術。”[5]甲午一役極大地挫傷了傳統武術在官方及民間的正統地位,輔之以1901年清政府頒布的廢除武舉制政策,中國習武(傳統武術)之風江河日下、日暮途窮。同時,在各精英人士的疾聲呼吁及政府的合力之下,整個社會形成尚武風氣,但此尚武亦非“傳統武術”之武,它泛指的是涵蓋傳統武術在內的身體鍛煉活動方式。主要是通過期望國人通過身體鍛煉增強身體素質。西式體育“尚武之風”悄然“潛入夜”,割據中國體育土壤,傳統武術漸入消沉。
2.3 辛亥革命:國術日益趨重,期待傳統武術奮揚民志
辛亥革命以后,民國成立,國人亦重體育,各界人士,競尚各種體操,各種運動,嗣漸多趨重我國固有之武術[5]。西方國家入侵所帶來的后果之一就是迫使中國人開始接受西方近代民族主義,在爭取民族獨立時代命題下,民國時期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被西方近代民族主義思想楔入,得出了“發展我國體育,不可不從我國實際出發,注意國情”的結論[11]。在此思潮下,以國術(武術)為代表的傳統體育項目開始受到關注。國人寄希望于國術,以期通過習練國術達到民族自強的目標。提倡國術者指出,國術乃我國固有之體育,適合我國國情,尤其在民族危機的時候,國術乃救國之利器,因此,提倡國術為當務之急。“壬子癸丑學制”(1912-1913)后,武術以合法的方式進入學校并成為體育教學內容[12]。李芳宸先生在其國術館的講話上指出“我為救濟民族的衰落起見,設立國術館。這并不是無故消耗政府的錢財,而是希望達到強國強種的目的,奮揚民志的皓的。因為國術與民族之存亡,是有密切關系的[13]。這實際上是把傳統武術等同于“工具”,希望傳統武術成為武裝自己的刺刀,提倡國術就是希望能讓身體增強戰斗力,去實現強國救種的目的。在中國傳統體育與西方的近代體育的回合較量之中,一方面,在社會結構轉型下的西方體育以其獨有的特征傳入有深厚文化傳統積淀而又長期閉關自守的中國,最終扎根,并且為人民喜聞樂見;另一方面,對于衍生于中國土壤的傳統武術在面對社會轉型之下的起承轉折,更多表現為思想上的沉浮。而傳統武術在當時承擔的并非作為體育項目強身健體的功能,更多的是承載著國人期待崛起的強烈自尊之心以及肩負著民族振興的光榮使命。這種國粹主義思想在一定情形下推動了傳統武術的繁榮。
2.4 東西體育之辯提供多元視角——在對立中走向前進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并沒有完成兩種不同性質社會之間的過渡,社會混亂,軍閥割據,多元思想林立。中國體育的體育發展道路問題的討論,從1914年將馬良創編的《中華新武術》引入國民教育體系中起這種爭議就已初見端倪。1932年,中國人第一次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會后,“土洋體育之爭”西方體育(由歐美傳入的近代田徑和球類運動項目)與東方體育(以武術為代表的中國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的爭論達到了高潮。發表在《大公報》上的《今后之國民體育問題》呼吁,“請從此脫離洋體育,提倡‘土體育’!中國人請安于做中國人,請自中國文化之豐富遺產中,覓取中國獨有的體育之道。”認為應當舍棄西洋競賽運動的方法,從此不必參加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5]。這篇社論引發了學界就今后中國體育道路問題的深刻討論。吳蘊瑞就此社論發表了《今后之國民體育之我見》回應了關于摒棄洋體育的觀點,并且認為今后國民體育途徑,主要是看它是否能適應個性,適應社會。各種體育都有自身獨特的用處。“故今后欲適應環境,為捍衛國家計,宜訓練智勇兼備之士,養成跑跳奔攀之技,然此端賴游戲器械田徑運動等有養成之,絕非土體育單獨所能奏效。”[5]過去的信仰又或者說是意識形態似乎在西方資本主義市場化的浪潮下失去了有效的解釋力,因此對傳統文化產生了動搖,或者說是懷疑。這種思想在土洋體育之爭中顯現出來。當然,這場論爭更進一步地加深了國人對土洋體育各自特點和實質的認識,為中國傳統體育與西方體育的初步融合提供了思想基礎,使“洋”體育更好地走進中國,也為中國的“土”體育走向世界創造了更好的條件[10]。同時,在這期間所謂的“土體育”,也抓住了發展契機,與西方體育的對話讓傳統武術更深切地扎根中國土壤,從當時誕生的武術社團組織就可見一斑。根據習云太的《中國武術史》記錄的在冊的民國時期的武術社團組織共49個,除去1914年之前成立的武術社團組織以及部分沒有確切成立時間的武術社團,在東西體育之辯思想浪潮中共衍生武術社團組織35個。總體而言,民國年間不同思潮的激烈交鋒以及連年戰火等,影響了武術的發展。但這一時期的武術,仍呈發展趨勢。在“土洋體育”之爭的論戰中,人們對傳統武術的認識逐漸深刻,傳統武術的科學化闡釋也漸進開展。

表1 民國時期部分武術社團組織
3 結語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在面對內憂外患的情形之下,呼聲“政治救國”“實業救國”“體育救國”,實際上是希望借助某種工具實現中華民族的崛起。而“體育救國”中體育的目的,無外乎是由民眾健康擴大到復興民族。可以說,救國的思潮一直充斥著整個中國近代史,當體育救國興盛時,國術與國民健康的關系,舶來的體育與國民健康的關系,中國體育與舶來體育之間的關系,就展開在民眾眼前,對于它們的討論也變得熱切。從洋務運動的“借西法以自強”,甲午海戰失利后直接將“救亡圖存”與“體育”相勾連,辛亥革命提出國術為救國利器,最后的東西體育之辨,這種將民眾健康亦或是體育置于急功近利的蔭蔽之下我們可以從中窺見一斑。實際上,這種體育工具化的思想也維系著傳統武術的生命活力使其能夠完成時代浪潮下的蛻變。傳統武術的發展態勢是否可以看作就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對抗之間的結果?隨著中國社會轉型的進程,東方國家變得更加西方化還是更少西方化,抑或是兩者相互矛盾的交織?這些問題很難一言以蔽之,在不同的社會,乃至同一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答案都有所不同。正如中國近代歷史上兩次不同性質的思想爭論一樣,維新派與封建頑固勢力的論戰,保皇派與革命派的論戰,這些勢力新舊更替,勢力變化,角色轉換。而傳統武術的繁榮,與對抗之間的結果息息相關,當此思想興盛時傳統武術繁榮,彼思想興盛時,傳統武術蟄伏。
當然,今日之中國已然是世界之中國,伴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儒學思想”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正在有力地回應“西方文化霸權”。傳統武術,或者是傳統體育的背后文化意識形態如何保持自我的獨立性,才是傳統武術不斷推進,適應民眾需要,滿足社會大眾的情感的重中之重。不可否認的是,傳統武術在轉型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問題,直至今日,傳統武術的現代化轉型依然沒有完成,但文化的交流絕非簡單的文化單向移植,人類歷史的前進也離不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對于傳統武術亦或是傳統體育而言,擁有文化輸出和文化健全機制,方能獲得文化補償,贏得空間上的擴展和時間上的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