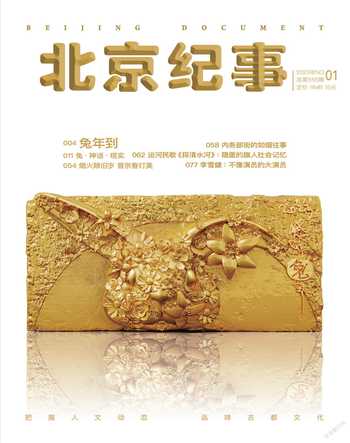“北門鎖鑰”的傳說與人
毛巧暉
編者說
北京市非遺項目門類豐富,具有多民族、多地域文化交流交融的特色,又兼容并包南北方文化特質。希望通過這一欄目的開辟,使廣大讀者能夠感受到流傳在民眾中口耳相傳的民間傳說、精彩絕倫的傳統技藝、美輪美奐的傳統舞蹈、精雕細琢的手工藝品中那一份厚重的歷史文化內涵。
八達嶺長城是護衛京城最重要的關隘,素有“北門鎖鑰”之稱,也是中國長城軍事防御建筑遺產的代表,因而有“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之說。八達嶺長城蜿蜒于京北燕山山脈,始建于戰國,沿線100多個村落里流傳著豐富的長城傳說。這些傳說題材廣泛,涉及長城修建、神仙佛道、村落風俗等內容,涵蓋風物傳說、人物傳說、歷史事件傳說等類型,語言樸實,保留了大量的方言俗語,是北京北部長城沿線歷史和文化的縮影。
八達嶺長城傳說
八達嶺長城的關城建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明代八達嶺關城相聯、墩堡相望、地勢險要,相當于萬里長城的關口、居庸關的隘口,是北京地區最為雄偉和堅固的一段長城。八達嶺一帶寨寨屯兵,每一處村、寨、城、關甚至石、泉等都留下了膾炙人口的風物傳說。如《六郎影》中抵御外辱的楊六郎石像,《仙女泉和青龍倒吸水》中的仙女送水和康熙飲泉,《望京石》《穆桂英點將臺》分別提及慈禧太后、穆桂英曾站過的巨石,還有《彈琴峽》《烏龜石》《白果樹》等,這些傳說雖說是解釋風物的來歷,但呈現著民眾對歷史人物、事件的看法以及當時的社會觀念。
“八達嶺”這個名稱的由來可以說眾說紛紜、異文較多。有說諧音自元代蒙古皇帝“巴達黎黎”賜名的“巴達嶺”;有說諧音自明代防守北方韃靼之嶺的“把韃靼”;也有說諧音自“八大嶺”,因為長城要在這里轉八道彎,越過八座山嶺。從“八達嶺”地名傳說之豐富可以看到,歷代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在建立政權時給北京留下的文化印記,因而八達嶺長城傳說在農耕、游牧、漁獵文化的層累和糅合中形成,跨越了長城作為“邊界”的意味,更象征著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的美好理想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歷史發展趨勢。
孟姜女傳說在八達嶺長城傳說中極為豐富,《孟姜女尋夫八達嶺》講孟姜女生于瓜中,《孟姜女和最早的一段長城》講孟姜女的前世是蘭香,長城是白馬尾巴變的,孟姜女還同“關溝七十二景”四橋子村的“千年大神樹”、長城邊的廟宇“掛紙庵”相勾連,具有延慶的地域文化特征。“孟姜女傳說”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同時作為北京長城文化的組成部分,極大地豐富了長城文化帶的內涵。“朝朝海上望夫還,留得荒祠半仞山。多少征人埋白骨,獨將大節說紅顏。”這首康熙帝的題詩,與坐落在八達嶺長城腳下的孟姜女風物,一起向世人講述著孟姜女與長城的故事。
八達嶺長城傳說集萬古之重載,又根植于民間,因而內容豐富,種類繁多,地域性強,時間跨度大。它的產生既與當地險峻的地理環境、歷史狀況有關,又與長城內外民眾的生產生活、民風民俗、歲時禮儀等密不可分。這些傳說經過無數人的講述、記錄、整理才得以傳承至今,在不同時代發揮繼承優秀傳統、弘揚民族精神、豐富文藝創作的功能。在八達嶺長城傳說的傳承方面,長城腳下的這些講述人可謂功莫大焉。
長城根兒的講述人
明代修八達嶺長城的時候同時建造了三個城,即鎮山城、關城、營城。鎮山城是舊時兵部下派的首領住所,關城和營城是守備軍隊扎營的地方,八達嶺長城傳說的傳承人池尚明,就出生在營城村。
營城村屬北京延慶縣永寧鎮,村內有長城、敵樓,村北不遠處有烽火臺,村東的磚窯遺址據說是燒制長城磚的地方,這里的民居大部分都是城磚建造的。2002年,村里出土了一塊長城碑,立碑時間是萬歷初年,可見營城村與長城的伴生關系。
營城村有唱河北梆子的傳統,村里請過保定、張家口唱河北梆子的名家。池尚明的父親主要學武生,師從專門教武戲的楊斌,池尚明的母親則學青衣。父母常常登臺表演,隨河北梆子劇團到昌平十三陵、懷柔二道關、黃花城一帶演出,名氣很大。由于河北梆子每一出戲都是一個故事,池尚明跟著父母從小接觸河北梆子的演述者、曲目等,養成了愛聽故事的習慣。他的舅舅也是說書藝人,每年端午、中秋、春節的時候,從他居住的東輝嶺村趕到營城村說書,村民都聚在池尚明的姥姥家聽書,炕上地下坐滿了人。東灰嶺村的盲藝人楊九興是其舅舅的師傅,拿手絕活是貼片大鼓書、彈三弦,村民婚喪嫁娶、滿月、蓋房等重要儀式都請他去表演,只要有空閑,他就在大柳樹底下跟人說故事。戲曲這一文藝形式為八達嶺長城傳說提供了極好的傳播載體,發生在延慶石峽村的傳說《三疑記》就依托梆子戲流傳至全國,并成為許多地方戲表演的劇目。

1949年前,關城“居庸外鎮”和“北門鎖鑰”兩門均已倒塌,其他敵樓、垛口、墻體也破敗不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多次撥資修復,基本恢復了八達嶺長城原貌,可供游覽的長城長達1660.7米,樓臺8座。1958年起,正式向游人開放。池尚明1962年出生,當時長城旅游還未像現在這樣火熱,只有零星游客到訪,但長城傳說的講述在村里很流行。池尚明青年時期常和家人、村民聚在一起聽故事,村里藏書很少,也沒有太多文娛活動,最主要的文化生活除了聽廣播,就是大家聚在一起閑聊。1979年,池尚明因語文成績較好,通過班主任老師結識了延慶縣(今北京市延慶區)文化館負責民間文學搜集工作的孟廣臣,得知縣文化館刊物《八達嶺》正在征集長城傳說,池尚明與全縣34位愛好者一起四處走訪、記錄傳說并向刊物投稿。每年年底,文化館將當年的刊物《北京說唱》《民間文學》等贈送給投稿作者,每人三至五本。在此期間,文化館還邀請民俗學者鐘敬文、張紫晨等為大家開展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工作的培訓,這也成就了一支專業搜集長城傳說的隊伍。
1984年,在中央“愛我中華,修我長城”的倡議下,八達嶺長城修復敵樓19座、垛口1252座、城墻3757米,游覽面積由過去6180平方米增加到現在的19348平方米,并先后建成詹天佑紀念館、烽火臺、長城博物館及夜長城等10余處新景觀。同時,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后改稱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以下簡稱“民研會”)通知延慶縣文化館開展長城傳說的搜集整理工作。也是在這一年,文化部、國家民委和民研會聯合簽發了《關于編輯出版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的通知》〔文民字(84)808號〕,延慶縣開啟民間文學的全面普查。

“三套集成”和長城傳說搜集雙管齊下,重任都落在文化館,這讓孟廣臣壓力很大,正好年富力強的池尚明喜好民間文學,他當即決定加入文化館的工作隊伍,參與集體采風和經驗交流。這支采風隊伍有三十多人,有專門負責開車的,也有管后勤的,還有專門給長城傳說畫插圖的,分工很明確。《北京晚報》在1986年8月1日第1版稱贊延慶縣文化館的采風隊“踏遍青山尋珍寶 堅持不懈采風忙”,稱他們采錄的長城傳說地方色彩濃郁,既有豐富的人文景物,又有機智幽默、寓意深長的文學語言。1987年12月,中國長城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物的保護卓有成效地進行,但無形之物的保護還較為滯后。孟廣臣等人加緊整理手頭的一百多篇傳說文本,于1992年出版《長城腳下的傳說》,在每個傳說下面,附有搜集整理者和講述者的署名。成果出版后,縣文化館的工作人員都很欣慰,1980年代以來跋山涉水、翻山越嶺的走訪工作總算有了初步成果。
守護傳說是我的責任
2008年,“八達嶺長城傳說”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2015年,池尚明作為八達嶺傳說的傳承人,被列入第四批北京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從此他走上長城文化宣講之路。他先后配合延慶區博物館錄制長城傳說故事20集,在區博物館展廳播放;兩次做客北京廣播電臺講述八達嶺長城傳說故事;連續三年參加端午節、世界自然遺產日的演出20余場次;在各區圖書館、文化館、檔案館及多所大中小學、鄉鎮和民宿講述長城故事,開展長城文化講座;還多次義務到水關長城為游客講解。
池尚明積極參與各種公益演出活動,在宣傳和展示長城文化之外,還投身校園教育,主持大中小學校與長城傳說相關的課外實踐。2016至2018年,連續三年擔任區文化館和八達嶺小學聯合舉辦的“尋找八達嶺長城傳說”主題夏令營的主講,帶領學生到傳說的發生地具象地感受敘事內容,活動地點以八達嶺長城、水關長城為主,延伸到居庸關長城、慕田峪長城、金山嶺長城、司馬臺長城以及門頭溝長城和張家口大境門長城。他要求學生不但聽故事,還要自己學著講故事,鍛煉他們的講述能力。后來這場夏令營活動被評為2018年全國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優秀案例提名獎。
為講好長城傳說,池尚明自費創建“八達嶺長城傳說工作室”,到北京周邊地區的長城以及河北的倒馬關、戰國趙北長城遺址,山西的雁門關、殺虎口長城等地考察,收集有關長城的實物資料,包括銅版畫、木雕、中外報紙和書籍、老照片、明信片、長城門票、劇本、唱片等。注重文字與圖像、影音等媒介的結合,不斷探索長城傳說跨媒介、多元的表述方式。
由于印刷技術的進步、視聽媒介的發展、學校教育的普及,當代民間文學的傳承方式發生變化,口頭性趨于弱化,民間文學創作和傳承的媒介更加多元,創編越來越多地發生在書案、手機或電腦上,民間敘事依托紙質和電子媒介增強了其傳播速度,也擴大了傳播范圍。池尚明不斷探索長城傳說傳承的新路徑,他為文化宣傳部門錄制長城故事視頻60余個,還找到民間剪紙藝人霍海霞,與史鳳祥、王永計組成文創小組,將100則生動有趣的長城傳說設計成剪紙,延慶電視臺和北京電視臺均為此事作了專題報道。2017至2018年,他協助北京市文化局非遺傳承人口述史項目和北京市社科重點出版項目,完成體現延慶地區長城文化地域特色的《八達嶺長城傳說——池尚明》口述史著作2部,希望為延慶長城文化建設增光添彩。2020年,他同海淀區非物質文化遺產辦公室合作,在“拾遺聽69”公眾號定期發布圖文音頻作品,還在喜馬拉雅、荔枝FM、蜻蜓FM、懶人聽書等平臺持續更新講述內容,這樣從微信公眾號即可聽到他以說書口吻演述的長城傳說。“拾遺聽69”舉辦“海淀非遺少年說”主題活動,召集7—18歲的北京市少年兒童作為“小小講述人”朗誦長城傳說,在青少年中培養了一批講述長城傳說的“小傳承人”。
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為深入推進長城文化資源保護利用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長城沿線孕育的類別豐富、數量眾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成為彰顯長城精神的重要文化載體。如何創新發展,探索文旅融合的“非遺+長城”路徑,成為學者討論的焦點。池尚明一方面堅持自己的八達嶺傳說的采風搜集;一方面進行傳說的普及、宣傳與研究,應邀參加“2020年非遺教育與學科建設國際學術論壇”,并對中外學者做了《傳承人視角下非遺進校園模式——以八達嶺長城傳說為例》的會議發言,與科研人員合作開展長城研究。2021年11月30—2022年2月在延慶區文化館舉辦“長城故事與剪紙創意”展覽,繼續為八達嶺長城傳說的傳播作貢獻。
傳承人是“文化記憶締造的參與者與踐行者”,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主體,長城傳說的傳承需要后繼有人。因而,培養傳承人也是池尚明的重要責任,在他的指導下,多位年輕人加入長城傳說的講述,其中較為出色的是崔東升和王永計,他們積極推廣八達嶺長城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