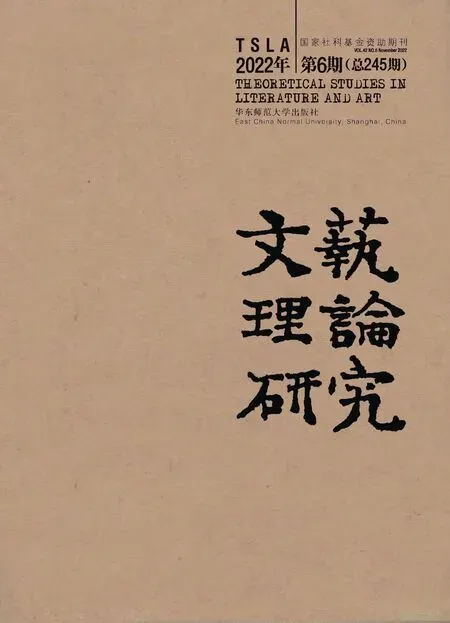雷蒙德·威廉斯之于當今文學(xué)和文化研究的意義
王 寧
當我們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語境下討論世界文學(xué)問題時,我們無法忘記當年歌德是如何率先將這個話題概念化的,盡管歌德不一定算是第一個使用“世界文學(xué)”(Weltliteratur)這一術(shù)語的德國作家和思想家。當代西方學(xué)者通常受到歌德關(guān)于世界文學(xué)的猜想的啟發(fā),認為世界文學(xué)是一個文學(xué)生產(chǎn)、流通和翻譯的過程(Damrosch,WhatIsWorldLiterature?4)。雖然他們并不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世界文學(xué)概念的成型所作出的奠基性貢獻,但他們卻很少沿著這條線索去探討馬克思主義對世界文學(xué)和文化研究所作出的不可替代的貢獻。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但丁、莎士比亞、歌德、席勒、巴爾扎克、狄更斯、易卜生等世界文學(xué)史上的經(jīng)典作家及其文學(xué)成就,始終予以高度的重視,并在不同的場合作出了許多富有深刻理論洞見的評點和批評。尤其是當文學(xué)研究在當今時代面臨文化研究的挑戰(zhàn)時,他們的這些深刻洞見更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xué)研究顯示出重要的指導(dǎo)價值和啟迪意義。在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的啟迪下,包括雷蒙德·威廉斯在內(nèi)的當代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理論家在這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威廉斯留下的寶貴遺產(chǎn)應(yīng)該受到我們的高度重視。
一、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與世界文學(xué)研究
在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學(xué)派中,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最具有獨特的本土特色,而且具有始自馬克思本人的悠久傳統(tǒng),這一點也體現(xiàn)在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和文化理論的歷史發(fā)展和當代形態(tài)中。的確,馬克思、恩格斯并非專業(yè)的文學(xué)理論批評家,也沒有寫出專門討論文學(xué)藝術(shù)的學(xué)術(shù)專著,但他們關(guān)于文學(xué)和文學(xué)批評的零散見解卻由后來的東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解讀、發(fā)展并建構(gòu)起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xué)敘事(王寧,《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xué)敘事》42—50),其中英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雷蒙德·威廉斯和特里·伊格爾頓,作為有著自己堅定信仰的學(xué)者型文學(xué)理論家和批評家,也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xué)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雖然他們沒有直接參與21世紀初開始的關(guān)于世界文學(xué)問題的討論,但他們的理論貢獻在當今的世界文學(xué)研究中,尤其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出發(fā)進行的世界文學(xué)研究,仍經(jīng)常被今天的世界文學(xué)研究者所引用和討論。坦率地說,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批評原則的深刻見解和作家作品評論,也啟發(fā)了包括我本人在內(nèi)的中國世界文學(xué)和文化研究學(xué)者。2021年是威廉斯100周年誕辰,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都把他視作當代英語世界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理論的一位先驅(qū)者和領(lǐng)軍人物,尤其重視他留下的寶貴的文學(xué)批評、文化研究和文學(xué)理論遺產(chǎn)。他們以不同的方式紀念他,討論他的文學(xué)和文化理論遺產(chǎn)之于當下的意義。①
當然,討論馬克思主義與世界文學(xué)問題,我們首先應(yīng)該從閱讀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的著作開始。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對世界文學(xué)現(xiàn)象給予了極大的關(guān)注,但他們也受到歌德建構(gòu)的世界文學(xué)理念的啟發(fā)。根據(jù)現(xiàn)有的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雖然歌德并非使用“世界文學(xué)”(Weltliteratur)一詞的第一人,但他卻被認為是最早對之作出理論闡釋并加以概念化的作家和思想家。而歌德之所以能提出他的“世界文學(xué)”構(gòu)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他閱讀了幾部非西方文學(xué)作品,包括一些中國和印度的文學(xué)作品。他對前來拜訪他并幫助他工作的青年學(xué)子艾克曼說,“我越來越認為”,歌德繼續(xù)說:
詩是人類的共同財富,而且正成百上千地,由人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時間創(chuàng)造出來。一個詩人可能比另一個詩人寫得好一點,浮在水面上的時間也長一點,如此而已……我們德國人如果不跳出自身狹隘的圈子,張望張望外面的世界,那就太容易陷入故步自封,盲目自滿了哦。因此我經(jīng)常喜歡環(huán)視其他民族的情況,并建議每個人都這樣做。一國一民的文學(xué)而今已沒有多少意義,世界文學(xué)的時代即將來臨,我們每個人現(xiàn)在就該為加速它的到來貢獻力量。(艾克曼,《歌德談話錄》195)
歌德在這里用“詩”來泛指文學(xué),指出各國和各民族文學(xué),包括那些長期以來被世界大多數(shù)讀者忽視但卻具有持久吸引力的東方文學(xué),具有共同的審美特征。正是基于他對世界文學(xué)的廣泛閱讀和涉獵,他構(gòu)建了他的世界文學(xué)理念。歌德認為,中國作家和歐洲作家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并沒有太大的差異,因為作家的文心都是相通的。但是我們卻發(fā)現(xiàn),在歌德的內(nèi)心深處仍有著一些歐洲中心主義,甚至德意志中心主義的固有觀念。但總的來說,與他的同時代歐洲作家相比,他的“世界文學(xué)”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所閱讀到的非西方文學(xué)作品的啟發(fā),其中包括一些在文學(xué)史上并不占有突出地位的中國文學(xué)作品。今天的中國古代文學(xué)研究者可能很少去討論諸如《好逑傳》《玉嬌梨》《花箋記》等這些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并不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但是歌德恰恰是通過英文或法文譯本閱讀了這些作品,進而萌發(fā)了“世界文學(xué)”的構(gòu)想。這尤其應(yīng)該引起我們比較文學(xué)學(xué)者的注意。
后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合著的《共產(chǎn)黨宣言》(1848年)中借用了“世界的文學(xué)”這個詞來描述資產(chǎn)階級文學(xué)與文化生產(chǎn)和流通的“世界性特征”,認為這是全球資本化的直接后果。在考察了資本主義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的擴張之后,他們得出了這樣的結(jié)論:“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guān)自守狀態(tài),被各民族的多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zhì)的生產(chǎn)是如此,精神的生產(chǎn)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chǎn)品成了公共的財產(chǎn)。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xué)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xué)。”(馬克思 恩格斯,《共產(chǎn)黨宣言》30)在這里,馬克思和恩格斯顯然受到了歌德早期猜想的啟發(fā),試圖指出世界文學(xué)的形成也有自己的規(guī)律。但他們大大地拓展了世界文學(xué)的范圍,使其包括所有資產(chǎn)階級文化和知識的生產(chǎn)和流通的世界性特征。由于文化知識的生產(chǎn)和流通,世界文學(xué)和文化與跨國物質(zhì)生產(chǎn)和流通也密切相關(guān),因為這是其必然的結(jié)果。
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考察文學(xué)和文化現(xiàn)象的方式,對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理論家,包括雷蒙德·威廉斯,在世界文學(xué)和文化的研究中產(chǎn)生了直接的影響并給予了某種啟迪。雖然馬克思主義被我們當作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shè)的指導(dǎo)原則,但是我們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世界文學(xué)方面的研究成果卻知之甚少。威廉斯在中國的文化研究領(lǐng)域似乎比在文學(xué)理論界更受到重視和追捧,當然,不可否認,西方學(xué)界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世界文學(xué)研究的著述也不算多。我在本文中想提及的英語世界最早的且現(xiàn)在仍是唯一的一本專門討論馬克思本人與世界文學(xué)之關(guān)系的著作就是牛津大學(xué)的教授西格伯特·所羅門·柏拉威爾的《卡爾·馬克思與世界文學(xué)》(KarlMarxandWorldLiterature)。這本書于1978年在英國出版,中文版很快就于1981年推出。該書主要回顧了馬克思對世界文學(xué)史上的一些杰出作家和作品的評點,并提供了大量的珍貴史料和討論。該書自1981年在中國出版以來,一直受到中國學(xué)者的高度評價。然而,柏拉威爾并未把世界文學(xué)看作一個理論概念,他的著作也不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思想的深入研究。因此,該書對當前國際學(xué)界關(guān)于世界文學(xué)問題的研究和討論影響甚微。更為令人不解的是,今天西方學(xué)界主要的世界文學(xué)研究者竟然從不引用或提及這部早期的著作,甚至故意忽略它。②但是,這本書對后來的研究者所起到的奠基性作用卻是不可否認的。作者認為,馬克思與世界文學(xué)的關(guān)系并非孤立的,而是與他對自己所處時代的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反思密切相關(guān)。因此,在作者看來:
這并不是一本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的書,也不試圖建構(gòu)另一個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理論。相反,它試圖以作者自己的定位所允許的公正和充分的方式,向英國讀者呈現(xiàn)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的不同時期對文學(xué)所作的評點;他如何利用自己所閱讀的許多小說、詩歌和戲劇作為欣賞、消遣或指導(dǎo);以及他如何將文學(xué)批評的術(shù)語和概念引入與文學(xué)無關(guān)的作品中的。(Prawer,KarlMarxandWorldLiterature,“Preface”vii)
的確,這本書并不是非常理論化和學(xué)術(shù)性的,但讀來十分有趣,其中披露了許多關(guān)于馬克思對世界文學(xué)的興趣和愛好的故事及軼事。毫無疑問,作者想讓英語世界的讀者知道,馬克思本人對文學(xué)的熱愛和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批評的論述,為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理論和世界文學(xué)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雖然馬克思主要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哲學(xué)家,并沒有寫出一部專門的文學(xué)批評著作,但他的經(jīng)濟學(xué)、哲學(xué)和政治學(xué)著作卻時常揭示出他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理論批評的洞察力。如果說,在評論馬克思本人對世界文學(xué)的閱讀和批評時,柏拉威爾掌握了豐富的原始資料,那么討論20世紀下半葉的社會文化現(xiàn)實則是馬克思自己也無法體驗的現(xiàn)實。因此,他的這本書的價值還在于,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解釋今天我們所面對的社會文化現(xiàn)實:
然而,《共產(chǎn)黨宣言》的預(yù)言并沒有完全落空。在我們這個20世紀,通過翻譯、平裝紙質(zhì)書籍、劇院巡回演出、廣播、電影和電視,我們看到“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xué)的融合和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傳播,這些均改變了我們的文化視角,馬克思也不會感到驚訝。“世界文學(xué)”作為一個巨大的想象豐富的博物館,作為一個偉大的巴貝爾圖書館猛然到來了。(Prawer,KarlMarxandWorldLiterature146)
因此,柏拉威爾指出,馬克思雖然無法預(yù)見到20世紀文學(xué)與社會發(fā)展到今天會是什么樣的狀況,但針對今天的后工業(yè)和后現(xiàn)代社會的文學(xué)狀況,馬克思依然準確地預(yù)測了當代社會的一些癥狀,這自然也是符合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的。事實上,由于生產(chǎn)和流通手段的發(fā)展和更新,文學(xué)的生產(chǎn)和流通也變得越來越便利,這便使得文學(xué)的傳播擴大到全球的范圍,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僅限于特定的民族和國家。因此,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學(xu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便有了很大的空間。在這方面,威廉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出版了大量文學(xué)作品和理論批評著作,使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理論在各派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獨樹一幟。
二、重讀威廉斯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xué)》
如果說柏拉威爾的開創(chuàng)性著作只是描述了他個人關(guān)于馬克思如何熱愛和討論世界文學(xué)及其經(jīng)典作家的一些觀點,那么我們應(yīng)該說,正是威廉斯開始系統(tǒng)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理論,并取得了一些創(chuàng)新。作為威廉斯“馬克思主義理論系列”中“最優(yōu)秀和最完備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文學(xué)》以批評性討論的方式探索了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理論的一些基本問題:“一方面,它對法國的符號的任意性觀念進行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編碼抗爭。另一方面,文本則是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和文學(xué)理論的所有元素中最能引發(fā)討論的因素,而他就在這方面作了許多令人信服的改進和發(fā)展。”(Fekete,“Raymond William”733)而對于這一點先前的研究者并未予以足夠的重視。
威廉斯從語言這一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理論的基本要素開始探討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理論,這一點也受到各種形式主義和結(jié)構(gòu)主義理論家的高度重視,因此他在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同時,可以與秉持語言中心主義教義的形式主義和結(jié)構(gòu)主義文學(xué)理論進行對話。他辯證地指出,“形式主義者優(yōu)先考慮具體的物質(zhì)表達是正確的,因為這是一部文學(xué)作品。但是他們不應(yīng)該把重點放在‘文學(xué)語言’上。他們以具體的方式探索表達是正確的,比如在具體的‘方法’的學(xué)說中是可以的”(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191)。因此,威廉斯試圖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與各種形式主義學(xué)說和文化因素結(jié)合起來,從而彌補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理論在這方面的一些缺憾。尤其應(yīng)該指出的是,威廉斯與西方學(xué)界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不同,他們只把馬克思主義學(xué)說視為西方眾多哲學(xué)學(xué)派之一,而威廉斯則與馬克思主義有著天然的親緣關(guān)系和割舍不斷的必然聯(lián)系。毫不奇怪,威廉斯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和文化理論家得以在英國異軍突起,與他的出身背景不無關(guān)系。他出生在威爾士的一個工人階級家庭,從小就清楚地知道當時工人階級的生活多么艱難,并有著一些親身經(jīng)歷,因此他更容易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并在其后積極地投身到英國的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他作為當時國際聯(lián)盟的支持者,參加了在日內(nèi)瓦舉行的國聯(lián)青年會議,回國途中經(jīng)過巴黎時,他買了一本《共產(chǎn)黨宣言》,首次讀到馬克思的著作,不禁倍感親切。從此他便與馬克思主義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并視其為自己畢生的事業(yè)。他對馬克思主義是這樣理解的:“然而,在從馬克思到馬克思主義的過渡中,在主流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發(fā)展中,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的命題一直被普遍認為是馬克思主義文化分析的關(guān)鍵。”(75)可以說,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較為準確的把握使他得以探索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批評思想的實質(zhì)。而他的出發(fā)點也正是唯物主義。
眾所周知,英國在歐洲國家中有著悠久的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馬克思生前特別關(guān)注英國的工人階級運動,并在大英圖書館里寫下了他的許多著作和文章,其中有些著作,馬克思同時用德文和英文撰寫。在今天的英國大學(xué)里,仍有不少學(xué)者稱自己為馬克思主義者,并從不避諱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作為英國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雷蒙德·威廉斯和特里·伊格爾頓確實是杰出的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不僅在英國,在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其他國家也是如此。他們都是文學(xué)學(xué)者和批評家,他們的許多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后,很快便在中國的語境中得到批評性和學(xué)術(shù)性討論。所以他們的作品可以說也成了世界文學(xué)或世界文論。我本人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幸與伊格爾頓相識,并邀請他參加1995年我在大連舉辦的“文化研究:中國與西方”國際研討會。他應(yīng)我邀請發(fā)表了一個十分雄辯和具有感染力的主旨演講,給所有的聽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③因此,在我看來,他們雖然并未專門將世界文學(xué)當作一個理論概念加以詳細的討論,但依然為當今的文學(xué)和文化研究者進一步深入研究世界文學(xué)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chǔ)。
與馬克思、恩格斯所不同的是,威廉斯在他的文學(xué)理論中特別強調(diào)語言和文化的維度,而這一維度恰恰在很大程度上被馬克思本人所忽視。在威廉斯看來,“文學(xué)是一種語言的社會和形式屬性中形式構(gòu)成的過程和結(jié)果”(46)。因此,他在構(gòu)建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理論體系時,特別重視語言的作用。對他來說,“文學(xué)被說成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工具。其他任何東西,雖然重要,但都是次要的,在這樣一種情形下,真正的工作或者由此開始,或在其中被接受。而作品本身則處于這一‘媒介’中”(158)。也就是說,如果把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概括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話,那么威廉斯的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和文化批評原則便可以概括為一種文化唯物主義,在這其中,語言和文化起著關(guān)鍵作用。語言的功能就像是一種“媒介”,但另一方面,“語言又不是一個純粹的媒介,因為通過它,生活的現(xiàn)實,事件的現(xiàn)實,經(jīng)驗或社會的現(xiàn)實均可以‘流動’。因此它又是一種社會共享和互惠的活動,并已嵌入積極的關(guān)系中,在這種關(guān)系中,每一個動作都激活了已經(jīng)得到共享和互動的東西,或者可能成為這樣一種情形”(166)。因此,在威廉斯看來,語言也是一種社會、文化和審美的媒介,而不僅僅是語言和形式的媒介。這應(yīng)該是威廉斯最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理論貢獻。正如伊格爾頓所總結(jié)的那樣,“‘文化唯物主義’這個詞是由英國首席社會主義批評家雷蒙德·威廉斯于20世紀80年代創(chuàng)造出來的,用來描述一種分析形式,這種分析形式更多地將文化視為一種物質(zhì)形態(tài),而不是一組孤立的藝術(shù)紀念碑,從而完整地包含了其生產(chǎn)模式、權(quán)力效應(yīng)、社會關(guān)系、可識別的受眾和受歷史制約的思想形態(tài)”(Eagleton,LiteraryTheory198)。誠然,威廉斯在其理論體系中,不僅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則,而且還根據(jù)當代的具體情況,將文化因素融入其中,從而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這些原則。在第一章“馬克思主義和文學(xué)的基本概念”中,威廉斯從他自己對文學(xué)的定義開始討論,顯然,這些定義不同于政治、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學(xué)等其他概念:
把“文學(xué)”作為一個概念來理解是比較困難的。在一般用法中,它似乎只是一種具體的描述,然后所描述的東西作為一個規(guī)則,又受到如此的高度重視,因而特定的作品和作品種類的具體價值幾乎立即與未被注意到的轉(zhuǎn)移作為一個概念而發(fā)揮作用,但仍然被果斷地認為是實際存在和具有實用性的。事實上,“文學(xué)”作為一個概念的特殊性質(zhì)就在于,它在許多特定的偉大作品的具體成就中,要求突出這種重要性和優(yōu)先性,而不是其他概念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以及與其相反的它們所界定的各種實踐。因此,“文學(xué)”常常被定義為“豐富的、居中心地位的、直接的人類經(jīng)驗”,通常與“細節(jié)”有關(guān)。(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45)
既然文學(xué)是語言的藝術(shù),那么就應(yīng)該具有不同于政治、意識形態(tài)乃至物質(zhì)文化等概念的“想象”“象征”和“詩意”特征,因為威廉斯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是當今時代少有的既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又在理論批評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文學(xué)學(xué)者。他在長期的著述生涯中發(fā)表了大量的文學(xué)作品,可以說,他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著豐富的親身體驗。因此他仔細地審視了英國的文學(xué),將其作為特殊個案,也即英國文學(xué)史,但是他重點討論的主要是優(yōu)秀的英國文學(xué)作品:“關(guān)注文學(xué)史,縱覽那些卷帙浩繁和門類復(fù)雜的文學(xué)系列,從《馬賓諾金》到《米德爾馬契》,或從《失樂園》到《序曲》,不禁致使人們短暫的猶豫,而當各種與這一概念相關(guān)的范疇,如‘神話’,‘浪漫’,‘小說’,‘現(xiàn)實主義小說’,‘史詩’,‘抒情’,以及‘自傳’”一一出現(xiàn)并各就其位時,這種猶豫感便消失了。”(46)
我們都知道,英國文學(xué)是世界文學(xué)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少偉大的作家同時也是世界級的大作家,他們在世界文學(xué)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所以威廉斯在書中提到的這些作家對我們考察世界文學(xué)現(xiàn)象也有著不可忽視的啟迪意義,特別是之于我們今天對中國文學(xué)和文化的研究。與威廉斯的其他著作相比,他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xué)》一般被認為是一部近乎“純理論”的學(xué)術(shù)專著,他在撰寫這部著作時,花了大量時間實地訪問并考察歐洲、北美以及亞洲的一些國家,對那里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及其研究狀況作了詳細的調(diào)研,以凸顯其文學(xué)思想的相對普遍意義。在廣泛閱讀馬克思原著的基礎(chǔ)上,他發(fā)現(xiàn),相比之下,馬克思主義對語言本身的理論貢獻并不明顯,因此他決定從那里開始,并提出了貫穿全書始終的“文化唯物主義”重要思想:“從這一歷史中產(chǎn)生的許多問題都與馬克思主義有關(guān),在某些領(lǐng)域,馬克思主義本身對這些問題有所貢獻。在歷史唯物主義方面,這些貢獻也擴展到對那些為人們所接受的主要范疇的基本重估方面。然而,重要的是,相比之下,馬克思主義對思考語言本身卻貢獻很小。”(21)因此,他便從語言問題開始研究,因為他知道,文學(xué)既然是一種語言的藝術(shù),那么語言的作用就不應(yīng)該被忽視,因此他認為有必要進一步建構(gòu)一種探索語言的文化唯物主義。如果我們考慮到威廉斯的著作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國家和地區(qū),包括在中國的接受情況,我們就可以說,他的這個目標已經(jīng)基本實現(xiàn)了。我們今天在中國的語境下談?wù)撐幕ㄎ镏髁x,至少不會對這一概念感到全然陌生。
我們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都特別注重現(xiàn)實主義文學(xué)創(chuàng)作,馬克思把莎士比亞作品的藝術(shù)特征總結(jié)為“莎士比亞化”(Shakespeareanization),也即一種意識到的深刻思想內(nèi)容與莎士比亞式的人物塑造的完美結(jié)合。恩格斯甚至通過強調(diào)細節(jié)的真實來定義現(xiàn)實主義。威廉斯也對現(xiàn)實主義文學(xué)藝術(shù)情有獨鐘,并在書中探討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一些與之相關(guān)的基本問題:
最簡單的“反映”論是建立在機械唯物主義基礎(chǔ)上的。但是,如果“現(xiàn)實世界”不是作為一個孤立的對象,而是作為一個具有某些固有特質(zhì)和傾向的物質(zhì)社會過程來把握,那么就可能得出一種不同的解釋。正如在早期的理想主義那里一樣,但現(xiàn)在隨著具體規(guī)則的改變,藝術(shù)可以被視為反映的并非分離的物體和表面事件,而且是其背后的基本力量和運動。這反過來便成為區(qū)分“現(xiàn)實主義”(動態(tài))與“自然主義”(靜態(tài))的基礎(chǔ)。(96)
也就是說,現(xiàn)實主義并非僅反映表面的真實,而更重要的是要揭示隱于表面真實之背后的本質(zhì)的東西,這與恩格斯關(guān)于現(xiàn)實主義的定義大致相同。根據(jù)馬克思主義的文學(xué)原理,一部優(yōu)秀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的力量,除了應(yīng)該具備細節(jié)的真實之外,還應(yīng)該再現(xiàn)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威廉斯也相當重視馬克思主義的典型化核心概念,并試圖將其與類型加以區(qū)別:
但是“類型”仍然可以通過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理解:作為一種“標志”或“象征”,或作為一種重要分類的代表性案例。后者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占主導(dǎo)地位……對于一個可知的(通常是整體上可知的)現(xiàn)實,有一個一以貫之的前提,其中的典型化將可以得到識別,而且確實(在“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正常過程中)得到確證。這個預(yù)設(shè)可以重復(fù),如果以更為復(fù)雜和有時顯得非常復(fù)雜的形式,那么所有理論的基本二元論都集中于“反映”這個概念,或者,在其一般意義上,集中于“中介”,或者,我們現(xiàn)在可以補充一點,一般意義上的“典型化”。(102—103)
因此,威廉斯也將馬克思主義的典型化思想發(fā)展成為一種可供當代和未來的作家和藝術(shù)家遵循和實踐的范式。
我第一次讀到這本書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的中國讀者并不熟悉雷蒙德·威廉斯的名字,但我立即被他那獨特的思想和對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理論的能動理解與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所打動,我覺得這與那些教條主義者和庸俗社會學(xué)家所闡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理論完全不同,而且也迥然有別于形式主義導(dǎo)向的結(jié)構(gòu)主義文學(xué)教義。今天,當我在全球化和世界文學(xué)的背景下重讀這本著作時,我發(fā)現(xiàn)威廉斯所提出的許多基本問題,仍然在當前國際學(xué)界關(guān)于世界文學(xué)和文化研究問題的辯論中得到討論。多年前,我就認為,我們中國的文學(xué)理論家和批評家需要從威廉斯這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那里得到啟示,從而建構(gòu)我們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批評理論話語。后來我寫了一篇書評,并在《文藝研究》雜志上發(fā)表,因為我認識到這是威廉斯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xué)研究的獨創(chuàng)性貢獻。(王寧,《威廉斯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xué)〉》135—136)書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文化領(lǐng)導(dǎo)權(quán)、主導(dǎo)文化、殘余文化和新興文化等形式,仍然是當今的東西方文化研究領(lǐng)域內(nèi)被人們熱議的核心概念。因此,這本書除了可被視為世界文學(xué)和世界詩學(xué)之外,還應(yīng)被視為對世界文化的重要貢獻。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當精英文學(xué)走向衰落時,由于威廉斯在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領(lǐng)域內(nèi)的重要影響,他仍然是中國的文學(xué)和文化批評界不斷地被人們討論的一個中心人物,對于威廉斯之于當今中國的文學(xué)和文化研究的意義,我將在結(jié)束本文前簡略地加以討論。
三、威廉斯之于當代中國的文學(xué)和文化研究的意義
毫無疑問,一位來自西方的理論家之所以得以在中國的語境中不斷地為人們所討論,至少說明了他的理論教義之于中國的批評實踐有著一定的借鑒意義和價值。由此人們可能會問:為什么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文學(xué)和精英文化日趨衰落,威廉斯和他的理論仍然能吸引中國讀者呢?我認為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威廉斯并不是從抽象的意識形態(tài)概念來討論文學(xué)問題,而是把他的理論闡述建立在自己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理論批評之上。即使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xué)》這樣的純理論著作中,他仍然花費大量的篇幅討論文化問題,試圖區(qū)分文學(xué)、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因此,這部著作讀來并不像是教條主義的說教,而倒是更容易打動讀者。其次,威廉斯與中國也有著某種不解之緣。他年輕時就思想“左傾”,并通過閱讀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RedStarOverChina)對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革命斗爭有所了解并深表同情。這一切也許都與他后來接受馬克思主義有著直接的關(guān)系。威廉斯的著作進入中國時,正值中國剛剛邁入改革開放時期,文學(xué)理論批評界出現(xiàn)了一個“語言學(xué)轉(zhuǎn)向”。也即人們認為,以往的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批評對文學(xué)文本的解讀和闡釋重視不夠,因此這種批評模式便受到從俄國引進的形式主義批評和從英語世界引進的新批評派的挑戰(zhàn)。顯然,形式主義批評十分注重文學(xué)形式,即主張從用于文學(xué)作品創(chuàng)作的語言入手。但由于過于注重文學(xué)作品的形式,反而缺乏對文學(xué)作品的歷史意識、批評分析和理論闡釋的關(guān)注。而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方法正好彌合了兩者之間的鴻溝,因為他既重視文學(xué)的意識形態(tài)傾向性和歷史意識,同時又不忽視其語言形式,而且他的批評并不是從理論到理論,更沒有遠離文學(xué)作品本身。
20世紀末新世紀初以來,面對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以及各種商業(yè)大潮和高技術(shù)的沖擊,文學(xué)及其批評理論日益被邊緣化。即使是更具包容性的文化理論也不像過去那樣具有吸引力了。因此,伊格爾頓這位曾經(jīng)在80年代的中國以其《文學(xué)理論導(dǎo)論》十分走紅的文學(xué)理論大家,也不得不使用文化理論這個新的術(shù)語來代替文學(xué)理論。但即使在談到文化理論的現(xiàn)狀時,他仍然沒有充分的希望,而是悲觀地宣稱:
文化理論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雅克·拉康、克羅德·列維-斯特勞斯、路易·阿爾都塞、羅蘭·巴爾特和米歇爾·福柯的開拓性著述已經(jīng)遠離我們幾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絲·伊瑞格里、皮埃爾·布爾迪厄、朱麗亞·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達、愛萊娜·西蘇、于爾根·哈貝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和愛德華·賽義德早期的那些具有開拓意義的著述也遠離我們多年了。(Eagleton,AfterTheory1)
我們縱然不可否認,文學(xué)和文化理論在西方語境中也許確實處于衰落的境地,但這并非意味著文學(xué)和文化理論在所有國家都面臨這樣的狀況。可以說,在西方理論的啟迪下,中國的文學(xué)理論工作者始終對所有有益于中國文學(xué)理論話語建構(gòu)的西方理論有著強烈的興趣,仍然通過翻譯的中介積極地引進最前沿的國際理論潮流,并就此展開熱烈的討論。還有些學(xué)者并不滿足于在國內(nèi)發(fā)聲,他們還瞄準國際文學(xué)理論大家,就其理論著作中的疑點或困惑與之進行直接的切磋和對話(Zhang and Miller,“Exchange of Letters About Literary Theory Between Zhang Jiang and J.Hillis Miller”567-610),進而產(chǎn)生了較大的國際影響。因此,當我們緬懷威廉斯時,我們自然會更加珍惜他對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理論的巨大貢獻,并試圖繼承他的批評和理論遺產(chǎn)。威廉斯生前始終堅持這一立場:“文學(xué)理論不能脫離文化理論,雖然它可以在文化理論中加以區(qū)分。這是任何社會文化理論的重要挑戰(zhàn)。”(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145)但是,威廉斯的文學(xué)理論和文化遺產(chǎn)對我們中國的文學(xué)和文化研究者有何意義呢?這正是我在結(jié)束這篇文章之前,試圖加以概括的。
我在前面已經(jīng)簡要地討論了威廉斯對世界文學(xué)和文化研究的貢獻,在這里我只想提及他之于當代文學(xué)和文化研究的意義和影響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我們都知道,威廉斯在以下三個領(lǐng)域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方面,他出版了不少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和戲劇,退休前在劍橋大學(xué)的正式職位是戲劇教授;(2)在文學(xué)理論方面,尤其是本文討論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xué)》堪稱力著,這本書不僅標志著文化唯物主義的崛起,而且它本身也成了世界文學(xué)和世界詩學(xué)作品;(3)在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方面,他更是被公認為英國乃至整個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先驅(qū)者和領(lǐng)軍人物之一。他的“最重要的遺產(chǎn)”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新興的文化研究的跨學(xué)科領(lǐng)域——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他在英語世界的這一領(lǐng)域的影響無可比擬,同時他還開創(chuàng)并鞏固了這一領(lǐng)域”(Fekete,“Raymond William”731)。即使在文學(xué)理論走向衰落的后理論時代,威廉斯仍被視為英國文學(xué)和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和先驅(qū)者之一。(Wang,“Gender Studies”14-30)威廉斯不同于那些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創(chuàng)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運用到對當代社會文化現(xiàn)實的考察研究中,對各種社會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時期得到了發(fā)展。他在眾多西方馬克思主義學(xué)派和思潮中異軍突起,對我們當下致力于構(gòu)建中國特色的文學(xué)理論話語也頗有啟示。他雖然也受到歐洲大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葛蘭西、阿多諾等人的影響和啟迪,但他更加立足英國本土,聚焦英國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和批評實踐,提出自己的理論建構(gòu)。在考察英國的文化狀況時,威廉斯認為當時的英國有三種文化:“主導(dǎo)文化”“殘余文化”和“新興文化”。(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121-122)當我們今天在中國的語境下討論中國的現(xiàn)代性時,這三種文化形態(tài)也可以在當代中國見到,也即中國的現(xiàn)代性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另類的現(xiàn)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由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和后現(xiàn)代各種成分組成,并且?guī)в絮r明的中國本土特色。(Wang,“Multiplied Modernities”617-622)因此在威廉斯看來,“既然我們總是在一個文化過程中考慮關(guān)系,那么我們對于新興的文化的界定,就如同對殘余文化的界定一樣,只能在一個完整的意義上與主導(dǎo)文化相關(guān)來作出界定”(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123)。也即威廉斯所強調(diào)的是,文化是一個動態(tài)的形成過程,而不是一個停滯不前的東西,也不是“基礎(chǔ)”的簡單反映,因為它是“生產(chǎn)性的”。因此他總是試圖探尋一種共同的文化。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一種共同的文化呢?在我看來,這顯然是威廉斯設(shè)想出的一種具有普適意義的理想的文化形態(tài)。正如伊格爾頓所總結(jié)的:“對于威廉斯而言,共同的文化(common culture)是由其成員的集體行為,不斷重塑和重新定義的,而不是由少數(shù)人建立的價值觀,然后被多數(shù)人接管和被動地經(jīng)歷。因此,他更喜歡‘共同擁有的文化’(culture in common)這個詞。”(Eagleton,TheIdeaofCulture119)這無疑給了我們深刻的啟示,使我們得以正確地理解威廉斯的文化遺產(chǎn)。這一點也尤其對我本人的研究有很大的啟發(fā)。早在20世紀90年代,我本人就開始從事文化研究,甚至率先將這種研究方法引入中國學(xué)界,但我主要還是從事比較文學(xué)和世界文學(xué)研究,只是在自己的文學(xué)研究中引進文化的因素,或者將文學(xué)研究置于一個更為廣闊的跨東西方文化的語境中。④受到威廉斯在上述三個領(lǐng)域的實踐所啟發(fā),我還嘗試著將對世界文學(xué)現(xiàn)象的分析置于廣闊的世界文化語境中,從而將文化研究與文學(xué)研究有機地結(jié)合起來。當然,對我啟發(fā)最多的便是,在威廉斯那里,文學(xué)研究并不一定與文化研究相對立,而是處于一種共存、互補的對話狀態(tài)。因此,威廉斯在文學(xué)批評和文化研究兩個領(lǐng)域都獲得了學(xué)界的高度重視,這就不足為奇了。
這樣,在威廉斯的啟迪下,我作為一個比較文學(xué)學(xué)者,總是試圖拓展文學(xué)研究的狹窄領(lǐng)域,以便將文學(xué)現(xiàn)象置于一個更為廣闊的跨文化語境中來考察和研究。當我作文化研究的時候,我總是盡量不偏離文學(xué)和文學(xué)研究太遠。我的許多西方先驅(qū)者也是如此,比如諾斯洛普·弗萊、F.R.利維斯和雷蒙德·威廉斯。這也是中國的文化研究的一個特點:許多來自文學(xué)學(xué)科現(xiàn)在又從事文化研究的學(xué)者將自己的研究與文學(xué)研究相結(jié)合,這樣,既克服了純形式主義的文本中心之局限性,同時又拓展了文學(xué)研究的領(lǐng)地,使之具有跨學(xué)科的立體感。此外,中國的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是由文學(xué)研究者引進的,因此許多著名的文學(xué)學(xué)者也參與其中。在這些文學(xué)學(xué)者的共同努力下,當代中國的文化研究也呈現(xiàn)出與西方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新面貌。或者我們應(yīng)該說,我們正在建構(gòu)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研究。因為在當今時代,文化的內(nèi)涵也在發(fā)生巨大的變化。正如伊格爾頓多年前就不無正確地指出的:
(文化)這個概念,也像大多數(shù)官方的神圣空間一樣,既受人崇拜又被人忽視,既具有中心位置同時又被邊緣化。文化不再是對一個人是什么的描述,而是對一個人可能是什么或曾經(jīng)是什么的描述。與其說它是為你們自己的團體而命名,倒不如說它是為你們的波西米亞異見者而命名的,或者說,隨著19世紀的發(fā)展,是為那些生活在遙遠的地方,不那么世故的人而命名的。因為文化不再像它本身那樣可以雄辯地描述某個社會了。(Eagleton,TheIdeaofCulture31)
因此,中國語境下的這種文化研究,不僅要結(jié)合當前西方乃至國際文化研究中所討論的許多問題,而且還要結(jié)合中國語境下的文化問題和文化現(xiàn)象的研究,如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及其產(chǎn)品、地方戲曲和民間文學(xué)、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及其產(chǎn)品影視、消費文化和社區(qū)文化,甚至包括網(wǎng)絡(luò)寫作和抖音現(xiàn)象,因為文化總的來說是范圍廣泛的和具有包容性的。只有保持這種對待不同文化的開放和多元態(tài)度,才能推動中國的文化研究向縱深發(fā)展,并與文學(xué)研究和國際文化研究學(xué)者進行平等的交流和對話。在這方面,威廉斯的文學(xué)和文化研究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可以效法的榜樣。
從上述中國的文化研究實踐來看,我們不難看出,中國的不少文學(xué)和文化研究者或多或少也都受益于威廉斯三十多年前留給我們的理論和批評遺產(chǎn),他的理論和著作仍在今天的文學(xué)和文化研究界得到討論和研究,并將繼續(xù)對我們今后的文學(xué)和文化研究給予啟迪和指導(dǎo)。也許這正是我們在一個新的語境中緬懷威廉斯及其對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理論發(fā)展的巨大貢獻的最好方式。
注釋[Notes]
① 為了紀念雷蒙·威廉斯百年誕辰,英國斯旺西大學(xué)與深圳大學(xué)合作于2021年10月27日舉辦了一個線上學(xué)術(shù)研討會,我應(yīng)邀出席并作了英文主旨發(fā)言,現(xiàn)將主旨發(fā)言改寫成中文,特此向會議的主辦者致謝。
② 我在撰寫本文時,查閱了當今西方世界最多產(chǎn)的三位世界文學(xué)研究者——莫萊蒂(Franco Moretti)、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和德漢(Theo D’haen)的世界文學(xué)著述,發(fā)現(xiàn)他們不但沒有引用柏拉威爾的著作,甚至都未在書中提及他的名字。這實在令人遺憾和不解。
③ 應(yīng)《新文學(xué)史》主編拉爾夫·科恩的邀請,伊格爾頓將會議主旨發(fā)言改寫后在該刊發(fā)表:Eagleton,Terry.“The Contradictions of Postmodernism.”NewLiteraryHistory28.1(1997):1-6.
④ 參考王寧:《大眾文化與文化研究》,《文藝報》1994年2月19日號;王寧:《文化研究:今日西方理論批評的主潮》,《上海文化》1996年第1期;王寧:《文化研究:西方與中國》,《國外文學(xué)》1996年第2期。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約翰·彼得·艾克曼:《歌德談話錄》,楊武能譯。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8年。
[Eckermann,Johann Peter.InConversationwithGoethe.Trans.Yang Wuneng.Chengdu: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2018.]
Damrosch,David.WhatIsWorld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Eagleton,Terry.LiteraryTheory:AnIntroduction(2ndEdi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
---.TheIdeaofCulture.Oxford:Blackwell,2000.
---.AfterTheory.London:Penguin Books,2004.
Fekete,John.“Raymond Williams.”TheJohnsHopkinsGuidetoLiteraryTheoryandCriticis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731-734.
卡爾·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產(chǎn)黨宣言》,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Marx,Karl,and Friederich Engels.TheCommunistManifesto.Trans.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66.]
Prawer,Siegbert Solomon.KarlMarxandWorldLiterature.Oxford: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78.
王寧:《威廉斯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xué)〉》,《文藝研究》1(1986):135—136。
[Wang,Ning.“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LiteratureandArtStudies1(1986):135-136.]
---.“Multiplied Modernities and Modernisms?”LiteratureCompass9(2012):617-622.
---.“Gender Studies in the Post-Theoretical Era:Mainly A Chinese Perspective.”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ies54.1(2017):14-30.
——:《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xué)敘事》,《人民論壇·學(xué)術(shù)前沿》21(2020):42—50。
[---.“On Marxist Narrative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Frontiers21(2020):42-50.]
Williams,Raymond.MarxismandLiterature.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Zhang,Jiang and Joseph Hillis Miller.“Correspondences on Literary Theory Between Zhang Jiang and J.Hillis Miller.”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ies53.3(2016):567-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