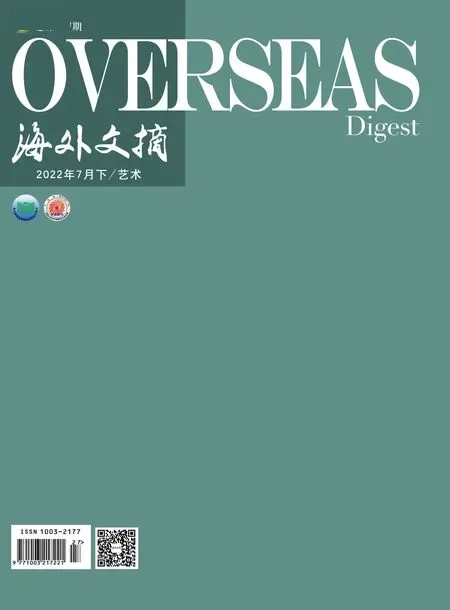論西維亞·喬邁動畫電影的諷刺和理念糾葛
□李泓瑾 趙建梅/文
西維亞·喬邁(Sylvain Chomet)是法國動畫電影導演。他的作品仍保留傳統動畫的元素,以夸張怪誕的造型與默片作為特點,在尖銳的現實諷刺中融入親情、愛情等美好理想。但由于西維亞·喬邁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劇情安排充斥著諷刺欲望,使得其傳統人文關懷主題被掩蓋,而其作品劇情核心結構與表現元素的相互糾葛,又造成了觀眾理解認知上的模糊。在《瘋狂約會美麗都》中角色造型夸張與諷刺細節冗雜,掩蓋了影片核心的情親主題;而《魔術師》雖然在影片整體畫風上獲得了與主題的一致,但深層隱含的諷刺結構仍暴露了作者理念的糾葛困境。
隨著近幾年中國電影產業的不斷發展,國產動畫電影也由早期的低齡向、低成本小制作漸漸走向成熟的產業化之路。《大圣歸來》《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作品在資金、技術等方面達到了新的水準,其受眾也已經擴展到青年甚至成人。面對逐漸繁榮的國產動畫電影市場,大量影迷對未來中國動畫電影產業持樂觀態度,部分影評人也認為就此開啟了中國動畫學派的“復興”“進擊”[1]。但過分樂觀并不可取,原因有二:從動畫制作角度看,爆火的幾款電影基本上都采取了當下慣用的3D動畫制作模式,特效和美術設計的技術含量并未超越皮克斯、夢工廠等歐美大廠;從劇情設計角度看,它們仍然沿用了迪士尼動畫電影的主角養成路線,核心思想也不外乎個體自由、尊嚴等常談,只不過在套路上使用中國古典神話傳說進行增繪。
相較于對美國式自由民主論調的亦步亦趨,我們更應關注歐洲動畫電影所展示的獨立思想,結合中國古典美學進行再創作,從而真正完成所謂“中國學派”的自我認知。法國動畫電影是歐美動畫電影的重要力量,其整體繪畫風格偏向怪誕與嚴肅,情節則以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快餐文化的戲謔與人性諷刺等現實主義題材為主。可以說,在動畫所能夠表達的人性深度與社會廣度上,法國動畫電影才是我們真正應當學習的對象。如何從迪士尼、皮克斯等成熟的商業化模式和模式化的“探討人生命題”中跳脫出來[2],在豐富的動畫技術的支持下展現出豐滿而獨特的動畫品格,才是目前“中國動畫學派”所面臨的真正挑戰,也是在繼《大圣歸來》等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自身的合理方向。
1 諷刺形象的建構
人物形象的夸張與變形是動畫電影獨特的表現手法,但美國商業動畫電影與歐美文藝動畫電影的形象夸張取向卻有很大不同。在商業動畫電影中,夸張的形象設計往往著重于突出次要或反面人物的特征,從而達到諷刺與滑稽的效果,而主要人物的形象則相對寫實,或是以部分特點突出其性格。可見商業動畫電影的形象夸張主要目的在于抓人眼球,同時做出簡單的人格隱喻,并不超越觀眾的期待視野。比如,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幼年哪吒的黑眼圈格外突出,咧嘴的寬度也遠超常人,給人以乖戾感;而成長之后的少年哪吒雖然還保留著標志性的黑眼圈,但其身材修長壯碩,相貌英俊,給觀眾以愉悅的觀感。這種形象建構方式可謂是美國商業動畫電影大廠的標準范式:
為了達到滑稽的目的,就要將這些特征進行夸張放大,于是我們看到《超人總動員》的超人先生上身的寬度遠遠大于腰部和腿部,《美食總動員》里大廚奧古斯特胖的只有肚子沒有大腿……人對動物和物的模仿是身體戲仿引發笑的一種形式[3]。
西維亞《瘋狂約會美麗都》中的形象建構則不僅僅是對其他事物的戲仿,而含有深層隱喻成分,從而加深了諷刺的力度。在這部電影開頭展現了一段舊錄像,內容為“美麗都”三重唱組合的表演。其動畫風格與整部動畫形成差異——黑白顏色,人物形象渾圓,線條滑利而缺乏質感,表情夸張,在行動時常伴有身體的變形。這些其實本屬于早期迪士尼的動畫風格。
這種集群式的形象構建比碎片元素的夸張更為高明,因為它所使用的諷刺隱喻并非生理性的,而含有歷史與文化的內涵。兩種動畫形象建構的對立其實顯露出西維亞對迪士尼開啟的動畫形象審美的嘲諷。在迪士尼風格與法國風格之間,可愛活潑的迪士尼畫風被西維亞用來描述美國的浮華與混亂:身材肥胖的貴婦人,猥瑣的小紳士,填滿整個舞臺的巨嬰等;而主線故事的畫風粗糙而怪誕,卻用于表現出舊時代的親情與自然,其反諷的意圖可見一斑,也不由得讓人驚嘆其獨特的藝術旨趣。
但存在的問題卻正在此處——動畫人物的夸張形象雖然承載了西維亞的諷刺意圖,卻不可避免地附加上獵奇,造成妨害主題表達的喧賓奪主。在《瘋狂約會美麗都》中,孫子的青年形象十分古怪:無神的雙眼、枯瘦如柴的上半身與過度發達的下半身、巨大的鼻梁與細縫般的嘴巴。在這些設計中唯一與主題相關的就是其眼神,代表了他從小的自閉癥,而身材的設計是對自行車運動員的夸張,面部則夸張了白種人的生理特征。類似的夸張在商業動畫中并非罕見,但西維亞將其夸張到令人不適的程度卻是值得思考的。
不難推測西維亞的動機——對固定范式的破壞,背叛觀眾的期待視野從而引導思考。但由此產生困境:怪誕與獵奇的參與對親情這一傳統主題所制造的張力以何為限度?這一張力的不足自然會令影片重回商業動畫的老調,但張力的過度則必然撕裂主題與表現的統一,造成負面的多義性。許多觀眾的視線被這些古怪的形象所誤導,從而對本來簡單的劇情產生的過度乃至錯誤的解讀。在小男孩長大后,他的奶奶幫助他進行自行車的訓練。這一本應溫馨的場景被西維亞設計的近乎恐怖:跛腳的奶奶不停吹哨督訓孫子,孫子則一副死人模樣,有氣無力;回家后吃的晚飯是混雜著魚骨的綠色糊狀物,椅子下設置了體重計,吃不到兩口便到達了限定體重不能再吃,投喂給養的肥狗……無怪乎有的觀眾為此驚異,甚至于早早開始分析這部影片是否是在諷刺嚴酷的家庭教育以及父母功利心對孩子的壓抑[4]。
西維亞并非不能認識到這種形象夸張帶來的主題偏差,但他似乎有意制造這種效果使得表達曖昧化。美麗都三姐妹是影片中的正面人物,但作者卻設計她們利用手榴彈炸湖里的青蛙吃。閑庭信步的貴婦人端坐在湖旁,一邊撐著傘一邊拿著小網,而天空正下著一陣由青蛙的殘軀組成的血雨。幽默背后的恐怖很難被單純理解為對都市中貧困現象的批判,因為種種夸張隱含的深意似乎可以在“動畫”這一語境中被消解,變成無稽的幽默或戲仿。但被取消了意義的設計對主題的表達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是不可回避的話題。
2 諷刺情節的設計
除卻形象建構的奇詭怪誕,西維亞作品的情節設計也別具一格。必須從兩個層面來理解西維亞作品的情節,即作為深層結構的中心思想和組成這一結構的具體情節。在一般的商業動畫中,二者并不構成戲劇性,因為前者是淺顯明晰的,后者則不過是在其之上增添的一些點綴。在皮克斯動畫電影《美食總動員》中,其核心思想是通過一只老鼠的烹飪去表達“人人皆可烹飪”(Anyone can cook)的前代廚神精神,但構成情節主線的卻是青年廚師小林與甜姐的戀愛、與史老板的產業爭奪,是一個添加了愛情線索的王子復仇套路。簡單來說,這些情節實際上對主題不起到隱喻作用,僅僅讓電影的商業性成為可能,是觀眾所期待的戀愛、沖突與所習慣的故事發展薈萃。
而西維亞作品的特殊之處在于如何處理二者的辯證關系。《瘋狂約會美麗都》講述了一個奶奶從黑手黨里解救自己孫子的故事,而《魔術師》則講述了一個過氣魔術師撫養小女孩長大并最終分道揚鑣的故事,主體結構很簡單,所以主要的表現力集中于細節設計。筆者將以兩個情節設計重點展開討論:第一個值得關注的細節是主線劇情所發生的時代與地點設定。在《瘋狂約會美麗都》與《魔術師》中都存在時間交替的二重空間。《瘋》中的奶奶和孫子居住在法國鄉村,而孫子被黑手黨綁架帶到了現代大都市“美麗都”;《魔》中的魔術師從大都市來到小山村遇到了小女孩,而小女孩則跟著魔術師一同去了大都市。“鄉村—都市”的轉化隱喻著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對立,而這也構成了西維亞作品諷刺內核的中心。《瘋》的核心情節雖然是奶奶營救孫子,但卻并未大費筆墨描寫奶奶與黑手黨的斗爭,而著重于奶奶前往大都市的艱難,在大都市的境遇以及“美麗都三重唱”姐妹的生存困境。而故事的結束是黑手黨在大橋上為奶奶所毀滅,奶奶和孫子一同逃離美麗都回到鄉村。
這其中我們不難看出隱藏在主線之下的深層結構。親情的發展基礎是以農業文明的靜穆和諧為基礎的,而美麗都這樣的現代都市則滋生著罪惡與腐敗,黑手黨以此為據點以人命為賭博的籌碼。所以筆者以為,西維亞《瘋狂約會美麗都》的核心矛盾是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矛盾,人性美與草菅人命的矛盾,而并非單純情親與反情親的矛盾,“彰顯出了現代符號統攝下的人類生存環境的異化, 是之于現代文明對傳統文明侵蝕下人際關系嬗變的反思與批判。[5]”親情主題不過是一個過去時代挽歌中最響亮的音節,被挑選出來作為時代的表征,而批判的機鋒真正指向的是“自由女神”滿腦肥腸、貧民區藏污納垢的大都會,以及滋生這一場域的當代文明。
這樣就引出第二個關注要點:在主線劇情之外的情節設計所構成的語境。筆者以為這正是西維亞作品的癥結所在。由于深層建構的掩蓋,以及對于動畫中夸張、諷刺元素泛濫的不加節制,使得構成深層結構的細節難以形成統一的語境,也令作者的人格曖昧不明。在明顯隱喻美國的美麗都,所有人都是夸張的梨型身材,嬰兒的重量可以撞壞行駛的汽車。前文提及西維亞在《瘋》的開頭用迪士尼風格表現了美麗都的奢靡混亂,這還可以理解為一種時代隱喻,可是在三姐妹居住的貧民區中,公共廁所馬桶里漂浮的糞便卻拼成了米老鼠圖案,就恐怕是一種對于商業電影的過度諷刺了。
原本的時代隱喻似乎變成了商業與政治之間的攻訐與玩笑,損害了主題所應具有的嚴肅品格。當然,這可能是一種我們難以理解的西方式幽默——迪士尼動畫《唐老鴨從軍記》是一部征兵宣傳動畫,可動畫內卻將軍隊生活表現得滑稽怪誕,但也并不妨害其宣傳目的。但就中國觀眾的文化心理與期待視野出發,恐怕并非值得學習的正途。
可見,西維亞作品的核心結構與具體構成間存在差距。作為一個極具人文氣息的導演,他的作品能夠深入到文明、人性與歷史的層面進行思考,但在表現的過程中卻受到動畫的特殊性以及獵奇嘩眾的心理影響,從而失卻了應有的持重姿態。值得注意的是,從《老婦與鴿子》《瘋狂約會美麗都》到《魔術師》,其作品中的獵奇色彩正逐漸減弱,而既具深刻性又令觀眾感到清新舒適的風格逐漸占據主導。
3 諷刺內核的糾纏
《魔術師》可以看做是西維亞作品的轉變節點。在這部作品中,導演開始以相對寫實的風格去塑造人物形象與自然環境,同時放棄了無意義的夸張獵奇,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具體而發人深省的細節。電影敘述了一個魔術師撫養鄉村小女孩長大并最終離開的故事,以魔術之名象征著父母的奉獻精神與養育的偉大力量。可以說諷刺并非這部電影的主題,但在溫暖的色調與悲憫的情節間,我們能隱約窺見作者欲言又止的糾纏表情。
迪士尼模式的商業電影中,主人公人格的遞進成長是推動劇情的重要動力,人格服務于情節。國產動畫電影《寶蓮燈》主人公沉香便經歷了長大、尋找孫悟空、尋找神斧等情節,逐漸塑造出獨立自強的人格形象。文藝電影由于在表達上具有強烈的概念性,因此情節服務于角色人格,而人格本身保持相對的穩定。西維亞的《魔術師》很好地體現了概念表達、角色人格與情節邏輯之間的配合與沖突,但由于并未處理好這些沖突,使他的反諷是失敗的。
因此,如果我們反過來看反諷藝術和反諷文學,即刻見出它們既有表面又有深度,既曖昧又透明,既使我們的注意力關注形式層次,又引導它投向內容層次[6]。
筆者將從兩點切入展開討論:小女孩人格的單面化與魔術師人格的轉變。在電影中,小女孩是個天真而幼稚的形象。她在偏遠的蘇格蘭山村長大,沒有受過教育,因此當她看到來自大城市的魔術師表演魔術時,居然真的相信了魔法的存在。而魔術師偶然的善念——替她“變”出了一雙新鞋子(實際是魔術師買的)——促使她離開山村追尋魔術師,以為這樣可以實現幸福,以至于對魔術師索求無度,使之陷入困窘。西維亞為了突出小女孩的幼稚與魔術師的無私,不惜在寫實風格的動畫中違背現實的邏輯——小女孩跟隨魔術師入城數年之久,竟仍持一副不諳世事的幼稚模樣,明知飲食開銷已經難支,卻仍不停向魔術師索要錢財來購買大衣與首飾。導演原本只是想突出女孩的幼稚,結果卻起到了反效果,讓觀眾以為這是一個貪婪、愛慕虛榮的形象,即便通過整體故事得以感受導演的意圖,也會為女孩的過分索求而產生憤怒之情,難以進入反思。
小女孩的人格是單面的,即現在所謂的“工具人”,只有在與魔術師的交互中才能形成復雜的意義。事實上,魔術師對小女孩無私的養育有兩重意蘊:第一是為了彌補自己不知在何處的女兒;第二則是實現自己魔術的價值。作為一個過氣魔術師,小女孩對他魔術的篤信是他生存下去的唯一價值。他可以放棄舞臺,去洗車、做廣告,自己忍饑挨餓來給小女孩換來大衣與首飾,只為了保存這個最后的觀眾。可以說,小女孩是為了是魔術師的形象更為豐滿的犧牲品,但卻因此將影片的情親主題添加了時代與個體的色彩。
但魔術師人格的轉變卻讓感人至深的電影以一個反諷來結尾。在離開女孩的列車上,魔術師遇到了一個尋找短蠟筆的小朋友,魔術師用自己手中的長蠟筆作出假象,但最后仍將短蠟筆還給了他。最后的魔術標志著魔術師人格的轉變,在經歷了對小女孩的無私奉獻后,他拒絕再給孩子以美好的幻想了。這一行為使魔術師由情節的主體變成了被審視的對象,在理想人格背后,那個面對新時代無力抵抗的過氣魔術師顯現。這種面對時代洪流的人的異化,在“遠離于‘個性’的情感與氛圍、遠離于‘緩慢’的情感與氛圍和遠離于‘陳舊’的情感與氛圍”這三個方面得以體現[7]。
西維亞結尾處的意圖我們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設計使整個故事成為一個巨大的反諷:以自身價值為支撐的魔術師,在這個陌生女孩身上所消耗的不僅僅是時間與金錢,而是作為魔術師所應給予他人的美好幻想。正如魔術師留給女孩的紙條所言:世界上沒有魔術師。可以說,魔術師依靠女孩確認了自己作為魔術師的價值,但西維亞卻揭示了這一價值最終崩塌的事實,魔術師在自戕式的付出中并未得到救贖,而是走向消亡。
4 結語
西維亞·喬邁的這兩部作品,無論是諷刺手法還是理念表達,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現實主義的人文關懷和荒誕奇崛的形式建構之間的糾纏。其作品諷刺手法成熟圓融,卻也因其部分運用的不當而對核心理念表達產生妨害。他一方面試圖去編織美好的親情童話,一方面卻難以抑制思想深處的悲憫目光,留下了輕輕一扯即歸于散亂的線頭。這種悲憫的目光并未真正傳達給觀眾,反而誤導觀眾去關注凸顯的諷刺與憤懣。原本希望引導觀眾進入思想層次的設計,卻讓觀眾的目光滯留于形式,這很值得深思。國產動畫一方面要充分學習其面對現實的尖銳目光,但同時也不能沉迷于無意義的喧囂,仍應把握動畫所秉持的童話內涵與終極關懷,如此才能發展出屬于中國學派“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風格。■
引用
[1] 司紀中.“中國動畫學派”的復興——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為例[J].出版廣角,2019(21):82-84.
[2] 付瑤.迪士尼動畫電影敘事:題旨的隱喻與戲劇沖突[J].電影評介,2019(9):106-108.
[3] 胡奕顥.美國皮克斯動畫電影幽默美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4] 周鮚.動畫電影分析[M].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7.
[5] 宋玉.西維亞·喬邁銀幕動畫:法國動畫電影的現實指涉與人文蘊藉[J].電影評介,2018(21):109-112.
[6] [英]D·C·米克.論反諷[M].周發祥,譯.北京:昆侖出版社,1992.
[7] 羅任敬.動畫世界的另類憂傷——解讀法國人文動畫導演西維亞·喬邁[J].文教資料,2012(32):19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