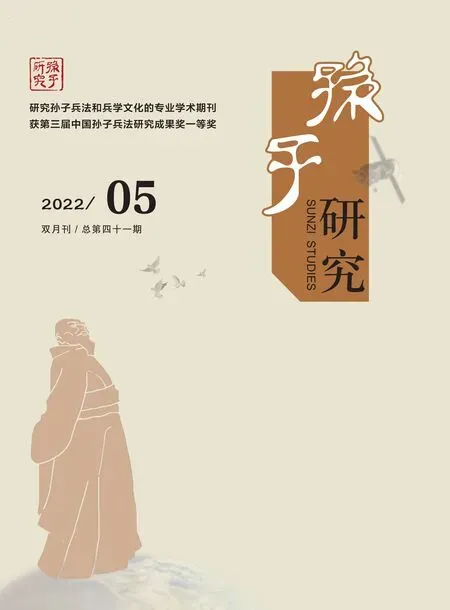戚繼光與明朝中后期“名將北調”現象研究
王淇銘
有明一代,邊疆危機以“南倭”和“北虜”為主,前者于嘉靖年間為戚繼光、俞大猷等將領蕩平,后者則遺患甚久。關于戚繼光抗倭的相關問題,學界業已取得豐碩成果,然而,還有一個現象似值得深究,即有學者曾提道:“明王朝為充實九邊,也常將內地諸鎮的名將北調,如戚繼光在倭患平定后便被調到薊鎮。”〔1〕薊鎮攸關京師防衛,如此調動足見朝廷之重視。據《明史》載,隆慶初年,大臣吳時來向穆宗上疏,“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宜用之薊鎮,專練邊兵,省諸鎮征調。帝皆從之。”〔2〕繼譚、俞、戚之后,又有胡守仁、湯克寬等抗倭名將奉命北上御虜。本文試圖以“名將北調”這一現象的重要參與者戚繼光為中心,對其中的歷史經緯進行考察。
一、對“南倭”與“北虜”的再審視
作為一種將多位南方御倭名將調赴北方的現象,“名將北調”與明朝主要的邊疆危機——“南倭”與“北虜”有著直接聯系。因此,當考察這一現象時,有必要對“南倭”與“北虜”進行討論,從而有助于更好把握“名將北調”這一現象的時代背景。
(一)抗倭名將的“御北”經歷與情懷
有研究顯示,抗倭名將唐順之曾作《日本刀歌》抒發馳騁邊關的保國之志,然而,“唐順之手持倭刀之時,所思慮的卻是北邊之危,與對‘北虜’的切齒之痛。”〔3〕他對“北虜”的憂心,是否也符合其他抗倭名將的所思所想抑或是直接行動呢?在這種追問下,可對幾位抗倭名將的相關經歷進行簡要梳理:
俞大猷,字志輔,晉江人。自小愛好讀書,對兵學思想有獨到研究,愛好習武。父親死后,他“棄諸生,嗣世職百戶。”嘉靖二十一年(1542),土默特部的首領俺答攻入山西,朝廷“詔天下舉武勇士”,俞大猷向巡按御史自薦,盡管他對軍事的見解折服了宣大總督翟鵬所,使其“下堂禮之,驚一軍”,但并未得到重用。〔4〕之后,俞大猷平定南方叛亂,開始了平定反叛和征剿倭寇的道路。嘉靖三十七年(1558),御史彈劾胡宗憲放走倭寇,而胡宗憲“委罪大猷縱賊以自解。帝怒,逮系詔獄,再奪世蔭。”〔5〕俞大猷入獄后,在其好友陸炳的幫助下,才得以釋放。兩人俱在大同巡撫李文進手下,一起籌劃軍事對付北方騎兵,“乃造獨輪車拒敵馬。嘗以車百輛,步騎三千,大挫敵安銀堡。文進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車營。京營有兵車,自此始也。”〔6〕后來,俞大猷受到薦舉,被朝廷重新錄用,并在恭順侯吳繼爵回京后代之,獲得平蠻將軍印。此后,俞大猷一直在福建、兩廣一帶平倭患、剿匪徒。隆慶初年,吳時來薦舉北調將領人選時,俞大猷儼然在列,最終未能成功赴北,而是繼續留在了南方。
譚綸,字子理,宜黃人。他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的進士,曾任南京禮部主事、臺州知府等職。東南御倭時,他與戚繼光等一同投身練兵事業中。后來,“倭犯柵浦,綸自將擊之,三戰三捷。倭復由松門、澶湖掠旁六縣,進圍臺州,不克而去。轉寇仙居、臨海,綸擒斬殆盡。”〔7〕隆慶元年,他與戚繼光一同被薦赴北練兵,總督薊、遼、保定軍務。
戚繼光,字元敬,號南塘,晚號孟諸。其父戚景通,“歷官都指揮,署大寧都司,入為神機坐營,有操行。”〔8〕戚繼光自幼家貧,喜好讀書,于嘉靖中期備倭山東,取得系列戰果。嘉靖倭寇平定后,他在吳時來的薦舉下,始任北京神機營副將,后總理薊門、昌平、保定練兵等事務,從事抵御“北虜”事業十六年。
胡守仁,字子安,號近塘,在戚繼光麾下任職,一路隨戚平定倭寇。隆慶元年(1567),戚繼光調北練兵,胡守仁留守浙江杭嘉湖。第二年十一月,戚繼光因練兵所需,“奏遣偏將胡守仁等,往募南兵鳥銃手三千赴薊”〔9〕,胡守仁因此也由東南赴北,開始了短暫的北方“御虜”之途。與胡守仁一同北調的,還有在抗倭戰爭中立下大功的李超。
陳第,字季立,號一齋。他本是“學宮子弟”,愛好音韻學,曾被抗倭名將俞大猷招攬至幕下,“教以古今兵法,南北戰守方略,盡得其指要,勸以武功自見”。譚綸對他評價極高:“俞、戚之流亞也”,后來,陳第亦趕赴北方,在戚繼光手下為將十年,他常與戚繼光論兵,兩人“扺掌相得,慨然有長驅遠略之志。”〔10〕
湯克寬,邳州衛人,“承世蔭,歷官都指揮僉事,充浙江參將。”在平定倭患的過程中頗有戰功,與俞大猷、戚繼光等曾并肩作戰。之后,由于犯錯,“尋赦免,赴薊鎮立功。”〔11〕
此外,還有嘉靖、萬歷年間的抗倭名將、戲曲家汪道昆。他在任義烏縣令時配合戚繼光招募“義烏兵”,與之建立深厚情誼。他對“北虜”也極為關注,曾多次向皇帝上奏折《薊鎮善后事宜疏》《遼東善后事宜疏》《保定善后事宜疏》等,并在隆慶六年(1572)赴遼薊巡視邊防,作《薊門會閱》等詩,描繪北部邊疆的情景,并肯定戚繼光的練兵成績。
上述幾位抗倭名將或十分關注“北虜”邊患,或因各種原因而親身參與到御北事業中去。從抗倭名將的“北虜”情懷與具體經歷中,亦可感受到“北虜”問題的嚴峻性。朝廷在倭患漸平時便急調幾名大將赴北練兵,以及湯克寬赴北“戴罪立功”直至戰死沙場的殘酷結局,也是對“北虜”之患十分危急的佐證。
(二)軍功中的南北差異
關于明朝軍功的記錄,能夠更為直觀地反映出“北虜”之患的嚴峻。
《明史》載:“正統十四年造賞功牌,有奇功、頭功、齊力之分,以大臣主之。凡挺身突陣斬將奪旗者,與奇功牌。生擒瓦剌或斬首一級,與頭功牌。雖無功而被傷者,與齊力牌。蓋專為瓦剌入犯設也。是后,將士功賞視立功之地,準例奏行。北邊為上,東北邊次之,西番及苗蠻又次之,內地反賊又次之。世宗時,苦倭甚,故海上功比北邊尤為最。”〔12〕可見,在世宗之前,若“視立功之地”而論功行賞,北邊之功賞最多。
趙翼也觀察到南北軍功的“迥異”之處:“有明中葉,戰功固不足言,然南北更有迥異者。大率用兵于南則更易于蕩掃,用兵于北則僅足支御。”“較之黔、粵用兵,何啻千佰之十、一,而乃以之入功冊,遷官秩,可知北強南弱,風土使然,固非南剿者皆良將,北拒者盡庸將也。”〔13〕俗語有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北方功賞遠高于南方,印證了“北虜”的危急性與緊迫性。
(三)“南倭”漸平而“北虜”未止
自明朝建立以來,“北虜”就是明朝北部邊疆一大威脅。明朝設立“九邊”就與“北虜”密切相關。〔14〕嘉靖年間,俺答在蒙古內斗中獨占鰲頭,對中原造成了巨大威脅。“庚戌之變”中,俺答兵臨北京城下,與明王朝軍事沖突達到了極其激烈的地步。實際上,至少在“庚戌之變”二十一年前,俺答等就不斷侵擾明朝北方邊疆,并一直持續到“庚戌之變”及其之后的幾十年:
“世宗嘉靖八年冬十月,吉囊、俺答寇榆林、寧夏塞,總督王瓊率兵御卻之。”
“(嘉靖——引者注,下同)十年春三月,入大同塞。秋五月,犯陜西。冬十月,犯大同。旋出松潘,犯西川西境。”
“十六年,虜寇大同,調遼東游兵備之。已出邊,遣回,而令此后非重警勿調。”
“十八年移三邊制府鎮花馬池。是時,俺答諸部強橫,屢深入大同、太原之境,晉陽南北煙火蕭然。”巡撫都御史陳講請求朝廷派兵加強防御,朝廷同意,“然兵將率怯弱,其健者僅能自守而已。”
“十九年七月,俺答諸部大舉進犯宣府。”
嘉靖二十二年,巡按山西御史陳豪進言:“敵三犯山西,傷殘百萬,費餉銀六十億,曾無尺寸功。”
“二十五年,薊州告急,宣、大總督翁萬達請調山東、河南、保定兵及京營軍挑選者。下樞臣議,止調保定兵。已,給事中齊譽言:‘京師之兵,居重馭輕,不宜以小警輕出。’帝然之。”
“二十九年,俺答攻古北口,從間道黃榆溝入,直薄東直門,諸將不敢戰。敵退,大將軍仇鸞力主貢市之議。明年開馬市于大同,然寇掠如故。又明年,馬市罷。”
“四十五年春正月,俺答寇宣府塞西陽河。”〔15〕
足見,“北虜”的常年進犯,對明朝北方邊防造成了持續性威脅,再加上遷都北方的因素,這一威脅便顯得更為重要,這是“南倭”所無法比擬的。而把眼光投向東南戰事時,則會發現,在嘉靖末年到隆慶初年,“南倭”已經不足為患。〔16〕
與之相反的則是同時期北方不斷惡化的局勢:嘉靖四十三年“四十三年春正月壬辰,土蠻黑石炭寇薊鎮,總兵官胡鎮、參將白文智御卻之。二月己酉,伊王典楧有罪,廢為庶人”〔17〕;嘉靖四十五年“秋七月乙未,俺答犯萬全右衛。冬十月丁卯,犯固原,總兵官郭江敗死。癸酉,犯偏頭關。閏月甲辰,犯大同,參將崔世榮力戰死”〔18〕;“(隆慶元年——引者注)俺答數犯山西,是秋長驅破石州,而土蠻同時入寇,薊鎮昌黎幾不保。”〔19〕
另外,為鞏固海防而著的《籌海圖編》有云:“今比年海內憂世之士,游談聚議,必曰南倭北狄。然言倭事者略矣。”〔20〕這句話亦可作為反證之用。此前大明“憂世之士”對“北狄”的“游談聚議”更甚于“言倭事”,而《籌海圖編》是為了彌補“言倭事”之不足而作。
二、明朝邊防與戚繼光等的大練兵
嘉靖年間,明朝空虛而羸弱的邊防與邊兵,為俺答等的“來去自如”提供了“便利”。而作為一種現象的“名將北調”,也正是以練兵固防為名義開始的。
(一)邊防羸弱與募兵
對于明之邊防,雷海宗曾如此評價:“明朝是盛唐以后漢族唯一的強大時代,不只中國本部完全統一,并且東北與西北兩方面的外族也都能相當的控制。”但這種狀況處于“勉強維持”的狀態,到了明末“漸不能自保”。〔21〕這一評價較為符合實情。明朝建國時通過幾次北伐重挫蒙古的軍事力量,結束其對中原的統治,邊境在一定時間內得到穩定。后來,永樂皇帝遷都北京,有“天子守國門”之說。
到了明朝中后期,隨著邊疆危機愈發激烈,“特別是在北部邊疆及東南沿海地區,偶爾的征調作戰往往變成長期性的在外流動作戰,世居一地的衛所制逐漸運行不便。加之世襲軍戶制度弊端的日益顯現,衛所士兵大量逃亡,往往衛所能征可戰之兵數量極少。”〔22〕伴隨衛所士兵逃亡的是邊兵戰斗力低下,致使明朝邊防岌岌可危。為了應對不斷惡化的邊疆局勢,明朝不得不通過雇傭的形式募兵,以補充軍隊的建制。作為一種兵役制度,“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世兵制”。〔23〕而為了提升所招募士兵的戰斗力,地方軍事將領開始關注對士兵的訓練。而譚綸與戚繼光二人,正是其中表現突出的兩名將領。
(二)戚繼光的大練兵戰略
戚繼光在嘉靖倭患時期,就十分關注練兵。他力排眾議,親自招募本地義烏兵,創立“戚家軍”。《明史》記載:“鄉兵者,隨其風土所長應募,調佐軍旅緩急。其隸軍籍者曰浙兵,義烏為最,處次之,臺、寧又次之,善狼筅,間以叉槊。戚繼光制鴛鴦陣以破倭,及守薊門,最有名。”〔24〕針對原來戍守東南的“客兵”戰斗力不強的問題,戚繼光招募英勇善戰的本地士兵;針對江南水鄉特點和倭寇戰法,他又設計了用“狼筅”“叉槊”等組成鴛鴦陣法。可以說,戚繼光在南方練兵的突出表現,應是他被看重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訓練邊兵并固防,正是朝廷將之北調的目的所在。
隆慶元年(1567)十月十四日,戚繼光被調往北京,始任神機營副將。第二年春正月,戚繼光迫不及待地向朝廷上《請兵破虜疏》,他首先向朝廷表示忠心與決心:“西北有警,召臣還京聽用,正臣立功報主之日也。”接下來,他力陳時弊,認為此前“掣肘多而便宜難,議論多而責效速”。他請求朝廷能“授臣以十萬之師,假臣便益”,經由訓練之后“布昭神武、問罪匈奴”,使國富兵強、一勞永逸。如果不能滿足十萬人的練兵需求,那么訓練五萬兵馬也能“一當匈奴,令其不敢南牧”;如果五萬兵馬都無法滿足,訓練三萬士兵也能“待虜來,伺有可乘,因而擊之”;如果連一萬人都無法訓練,則“緩急無益于事”。對于具體練兵練將人選,他認為應當給予充分自由選擇權,“臣舊部將與新訪堪認將領者若而人,列名奏取赴京,與臣等歃盟,同心共濟。”〔25〕然而,戚繼光的“破虜”方案沒有被朝廷接受。
隆慶二年(1568)三月十六日,朝廷命譚綸總督薊遼保定等地軍務,譚綸立刻向朝廷上奏:“今之策虜事者,皆曰乘障,曰設險。然薊昌十區之地,東西兩千余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分隸于諸將之手,散布于二千余里之間。”在北部邊防整體羸弱的情況下,敵人只需要集中兵力攻其一點,即可輕易進犯。因此,譚綸“亟請練兵”。〔26〕譚綸請求練兵的數量與戚繼光的“預算”相比大大減少,“請調薊鎮、真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為三營,令總兵參游分將之,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另外,練兵非朝夕就能見到成效,“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以濟緩急。三年后,邊軍既練遣還。”由于邊臣對練兵之事多有掣肘,譚綸還建議:“今宜責臣綸、繼光,令得專斷,勿使巡按、巡關御史參與其間。”對此,“巡撫劉應節果異議,巡按御史劉翾、巡關御史孫代又劾綸自專”。在張居正的努力下,“穆宗用張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綸,而諭應節等無撓。”〔27〕經過譚綸“打折扣”式爭取,朝廷終于同意讓戚繼光總理薊、昌、保定的練兵事務,并且調南方名將胡守仁、李超率三千浙兵(南兵)赴北。隆慶三年(1569),當胡守仁帶領的南兵出現在薊州郊外時,“天雨,軍士跬步不移,邊將大駭。自是薊兵以精整稱。”〔28〕
戚繼光練十萬兵馬的愿望始終沒有實現,清人認為,戚繼光“出鎮之后,當事掣其肘,不得行,中道齟齬,卒以罪廢。”〔29〕朝廷的做法正是如此:“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因此,“召還總兵郭琥”,命令戚繼光為總兵,“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30〕如此一來,戚繼光職務被削弱,由總理薊、昌、保定練兵事務變成了薊州總兵官。〔31〕自此,戚繼光只能專注于加強薊州一隅的防務,離“問罪匈奴”“一勞永逸”的愿景越來越遠。
戚繼光在東南以練兵效果顯著而聞名,在北調后卻無法全力發揮才干,不得不說是一種損失。但是,戚繼光仍然堅持在薊練兵。在他練兵之前,“薊人夙多木疆,律以軍政即不堪。”〔32〕還有人評論:“以故嘉靖間,薊州練兵,終不能成列,王思質中丞,以此坐重辟。”后至“隆、萬間,戚少保(繼光)為帥,反用浙兵于薊,由是精兵稱朔方第一,亦時勢使然。”〔33〕
三、東南名將御“北虜”
盡管多有掣肘、大材小用,但是戚繼光并沒有因此而懈怠,而是專注在薊一隅履職。這位聞名于東南的武將在大明北疆,仍然展示出名將風采,為抵御“北虜”做出貢獻。
(一)整頓防務
戚繼光在得知朝廷不會允許他訓練十萬兵馬用以主動出擊“御虜”之后,開始思考如何在薊鎮一隅有所作為。上任不久,他巡行塞上,認為薊州當下之急是構筑敵臺。〔34〕他提出:“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圮,徒費無益。請跨墻為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為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隆慶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詔予世蔭,賚銀幣。”〔35〕據載:戚繼光在“練兵之議寢不行”之后,“大修邊墻二千里,樓櫓敵臺,翼然壯麗”。此后,“比年,東西鹵(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巫卜不詳,遂謝去,東胡款關入貢。部言鹵(虜)數苦薊內備,不戰而伐鹵(虜)謀,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36〕
除了修筑敵臺之外,戚繼光還加緊對薊鎮軍隊的整頓。首先,戚繼光認為明軍的后勤保障能力弱,需要做出改變:“無馱載馬騾,往往枵腹數日,徒具人形,莫能荷戈,焉望鏖戰?”由此而大大影響到明軍的行軍與作戰能力,而“北虜”騎兵機動性強,“不知馳騖之虜,行百里矣。故虜入內,必變客為主,我軍常以主為客。”為此,他請求增設輜重營,因為這是“軍中所必用而不可缺者矣。”〔37〕戚繼光敏銳地觀察到明軍在抵御“北虜”時常因輜重問題而“以主為客”的現象,因此才建議設立輜重營。
在設立輜重營的倡議得到同意后,戚繼光又建議設立車營。《明史》載:“至隆慶中,戚繼光守薊門,奏練兵車七營……十二路二千里間,車騎相兼,可御敵數萬。穆宗韙之,命給造費。”朝廷對戚繼光建議設立車營的建議表示支持。然而,接下來的記載則是:“然特以遏沖突,施火器,亦未嘗以戰也。”盡管車營“未嘗以戰”,但是之后“遼東巡撫魏學曾請設戰車營”;“萬歷末,經略熊廷弼請造雙輪戰車”;“天啟中,直隸巡按御史易應昌進戶部主事曹履吉所制鋼輪車、小沖車等式,以御敵”。上述幾位戍北將領,對設立車營“情有獨鐘”,盡管其“皆罕得其用”。對此,《明史》中的觀點是:“大約邊地險阻,不利車戰。而舟楫之用,則東南所宜。”〔38〕對此,有學者曾質疑,認為史書對明代戰車持否定態度是不合理的,史實證明,明代戰車曾參加過戰斗,并取得戰果,只是在當時的作用不能高估罷了。史書的否定態度本身則表現出缺乏戚繼光、熊廷弼等文臣武將的遠見與革新精神。〔39〕實際上,除了對未來戰爭形式發展的高瞻遠矚外,戚繼光之所以提倡設立車營,或是因為車營是其在薊門一帶整頓防務、構筑“防御體系”的一個環節。所謂車營,應與“馬步軍”“拒馬器”“長鎗”“筤筅”“輜重營”等相互配合使用,這是專門針對“寇騎”進攻特點所構建的防衛體系。〔40〕
在戚繼光整頓防務之后,“薊州軍容”成為邊鎮中的翹楚。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東南抗倭時,“戚家軍”便以軍紀嚴明立身。在北方,戚繼光仍然格外關注軍隊風氣:“自將領以及軍士,皆以阿諛奉承為念,只顧眼前,再不慮后事如何也。”〔41〕在戚繼光的整頓下,“邊鎮修舉,虜不敢犯。”〔42〕
對于戚繼光在整頓防務方面的貢獻,明清之際的張岱評論:“戚繼光在邊日久,其所置亭徼、煙墩、炮臺、譙麗之屬,堅如鐵桶,虜不敢窺視內地。”又“嘉靖間以其身為邊塞之安危者幾二十年。今之至薊門者,觀其關隘、臺垣、亭障、器械,其功爛焉不可泯也。使后之人能讀其《紀效新書》《練兵要略》,尊其法而固守之,胡人猶能牧馬南下,吾不之信矣。”〔43〕對戚將火器應用于邊塞防衛的做法,時人頗有贊賞:“戚繼光帥薊門,又用火鴉、火鼠、地雷等物,虜胡畏之,不敢近塞,蓋火器之能事畢矣。”〔44〕今日來看,戚繼光的諸多兵學實踐,仍值得深入研究。
(二)出兵御虜
戚繼光在薊構筑了層層防御,使北方敵人一時難以入關。再加之隆慶年間,明廷高拱、張居正等人籌劃對俺答封王、通貢和互市,大大減少了明朝與蒙古之間發生戰爭的幾率。一時“宣、大以西,烽火寂然。”然而,好景不長,北蠻小王子“徙居插漢地,控弦十余萬,常為薊門憂”,還有“朶顏董狐貍及其兄子長昂交通土蠻,時叛時服”,再次為大明北方邊關帶來危機。萬歷元年(1573)春,北蠻小王子與董狐貍籌劃進犯明朝邊關,他們率兵馳往喜峰口“索賞”,遭到拒絕后便在當地“肆殺掠,獵傍塞,以誘官軍。”戚繼光出兵“掩擊,幾獲狐貍”。夏天,董狐貍又進犯桃林,被戚繼光再次擊退。董狐貍之侄董長昂隨后進犯界嶺,又被擊敗。“官軍斬獲多,邊吏諷之降,狐貍乃款關請貢。”朝廷同意了他們獻關求賞的請求。萬歷二年,董長昂聯絡董狐貍共同逼迫董狐貍的弟弟董長禿“入寇”,被戚繼光擊潰并活捉。于是,董狐貍等人率領親族叩關,董狐貍身穿素服苦請赦免董長禿,戚繼光與總督劉應節等商議后,接受了他們的投降。董狐貍等將之前所劫掠的邊人歸還,并且“攢刀設誓”。董長禿被釋放后,雙方像之前一樣通貢,“終繼光在鎮,二寇不敢犯薊門。”〔45〕不久,戚繼光因戍邊有功,升左都督。萬歷四年(1576)六月,炒蠻求賞不得,在古北口關附近劫掠,同為北調名將的湯克寬中伏而戰死,戚繼光因此而被彈劾。
由于薊門固若金湯,“土蠻數侵邊不得志。”〔46〕萬歷七年十月,數萬土蠻騎兵進犯遼東,從前屯錦川營進入。大將李成梁等率軍與之交戰,戚繼光率軍急忙趕往,“偕遼東軍拒退之”,〔47〕第二年十月,十萬土蠻進犯遼東錦州,戚繼光再次率兵援助。戚繼光因功被封為太子太保,又進封少保,這就是戚繼光被稱為“戚少保”的緣由。
如何評判戚繼光鎮守薊門的效果?這可以從黎民百姓的呼聲中窺得一二。萬歷十一年(1583),五十六歲的戚繼光被調回南方任廣東鎮守,都督南粵軍事。薊門“闔鎮父老詣闕請留,當國不允,雖罷市遮道擁泣,攀轅追送出境者不絕。”〔48〕后來,“及北鹵(虜)入黑峪關,薊人愿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49〕《明史》有評:“自戚繼光鎮守十年,諸部雖叛服不常,然邊警頗稀。”〔50〕可見,戚繼光在薊鎮確實起到了御敵于外的作用,并獲得了百姓擁戴。
(三)戚繼光御北期間的人際交往
戚繼光北上之后,注重與上級和同僚保持較好的關系,這為他鎮守薊門提供了種種便利。《明史》有云:“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后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確,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咸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51〕由上可見,當國大臣對戚繼光頗為器重,其中,以張居正最為突出。
張居正入閣之后,對邊關之事十分關注,他曾力勸明穆宗封俺答為順義王,以保證北方穩定。明人曾贊其風格:“江陵(指張居正——引者注)行事雖過操切,然其實有快人意者……至其結馮保以收諸內豎之柄,北任戚繼光而虜不敢窺塞垣,南任譚綸而倭寇服,其才智明決,有過人者。”〔52〕《明史》也云:“居正喜建豎,能以智數馭下,人多樂為之盡。俺答款塞,久不為害。獨小王子部眾十余萬,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寇。居正用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門。成梁力戰卻敵,功多至封伯,而繼光守備甚設。居正皆右之,邊境晏然。”〔53〕對于戚繼光、李成梁等鎮北將領,張居正盡可能為之在朝堂之上提供便利。
倘若對明朝文武關系有所了解,便可知張居正此舉極為難得。明中期以來,朝廷素有“崇文黜武”的氛圍,而幾乎同一時期出現的,則是“文人尚武”與“武將好文”的風尚。〔54〕黃仁宇曾為武將鳴不平:“將士們即使出生入死,屢建奇功,其社會影響,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塊文章。”〔55〕由此可見張居正在這一背景下的格局與遠見。沈德符曾感慨:“若武帥之重,則提督之外,如今上初戚繼光在薊鎮,以總兵官加總理,專司訓練,并督撫麾下裨將標兵俱屬操演調遣,生殺在握,文吏俱仰其鼻息,則江陵公特優假之,非他帥所得比。”〔56〕然而,這種特別的“幸運”恐怕也易在另一方面帶來不幸。在黨同伐異的明廷之上,戚繼光等北調將領既然能獲得“江陵公”的“特優假之”,他們自然也要因“江陵公”權勢倒塌而被視為同黨。萬歷十年(1582),張居正病逝,“及江陵歾,人言波及,繼光移鎮南粵”〔57〕,回到南方之后,戚繼光郁郁不得志,竟在貧困交加中隕落。
除了與張居正交好外,戚繼光與譚綸亦是友誼深厚,他們兩人共事多年,常為外人稱“譚戚”。隆慶二年(1568),譚綸亦被調赴北方,任薊遼總督。他與戚繼光一同商議鞏固邊防問題,從居庸關到山海關修筑上千座防御臺,因功升任兵部尚書。萬歷五年(1577),譚綸于任上去世,在薊門的戚繼光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絕,他充滿深情地寫下祭文。首先回顧了譚綸在御倭中的功績,而在之后則使用了更大篇幅來寫兩人在北方的交往。當時,北方“大為虜創,春復告急。烽燹后百無所資,”譚綸在此時“上疏重創筑,慎訓練,立車營,增敵具,刑逋逃”,如此一來,“邊垣有待”。戚繼光還回憶譚綸對他的支持與信賴:“某咨白一切報可”;“以國士待某”。〔58〕
另外,在明朝名將中“如郭登、戚繼光、陳第、萬表,皆有詩名。”〔59〕戚繼光的詩名則在薊州廣泛傳揚:“至隆萬間戚少保為薊帥,時汪太函、王弇州,并稱其文采,遂儼然以風雅自命,幕客郭造鄉輩,尊之為元敬詞宗先生,幾與縉紳分道揚鑣。”〔60〕對于戚繼光、蕭如熏等名將與文人的交往,有載:“薊鎮戚繼光有能詩名,尤好延文士,傾貲結納,取足軍府。如薰亦能詩,士趨之若鶩,賓座常滿。”〔61〕有學者指出:“戚繼光的文化交游活動是晚明社會‘武臣好文’現象的典型代表”。〔62〕錢謙益也對此有如下評價:“生平方略,欲自見于西北者,十未能展其一二,故其詩多感激用壯,抑塞僨張之詞。君子讀而悲其志焉。”〔63〕在“文人尚武”背景下,戚繼光所寫詩歌,時而流露出戰場肅殺氣氛,時而抒發忠誠保國之心,時而感慨邊關失意之情,無疑能引得文人墨客的滿堂喝彩。另外,關于名將俞大猷與文人交往的研究也顯示:通過與文人“談兵”,“俞氏主動爭取社會威望,構建并維護自身的官場人脈資源也是不爭的事實。”〔64〕
結 語
在明朝中后期的邊疆危機下,曾誕生一批有為名將。這一群體不僅投身于抗倭事業,也曾擁有“御北”經歷抑或情懷,他們共同譜寫了“名將北調”的歷史。諸北調名將的不同結局,亦值得深思。
與戚繼光一道被提名北上練兵的俞大猷,最終未能成功赴北,成為其人生遺憾。清人查繼佐有評:“一時海內稱俞、戚,以大猷為龍,繼光為虎。然大猷每以不得當鹵(虜)為恨,而繼光在薊,又值鹵(虜)受欵,未盡展所能為,則正以不一當鹵(虜)為功。嗟乎!負五等之才,而須其時。”〔65〕俞大猷的軍旅生涯因“御北”情懷而起,但卻未能為鞏固明朝北部邊疆發揮才能,只能含恨嗟嘆。
早在戚繼光遭受牽連之前,一同北調的譚綸就已于萬歷五年卒于任上。譚綸素與張居正交往甚密,對先于張居正而卒的他來說,沒有遭受牽連,反而獲得了百官尊崇的謚號“襄敏”,不得不說是一種幸運。
跟隨戚繼光腳步來到薊州的胡守仁,在萬歷年間又回到福建擔任總兵,繼續完成追剿倭寇的任務。對他而言,“北調”不過是其人生履歷中的一個階段。然而,連他也逃不過“清算張居正”的牽連,以罷官返鄉收場。
當戚繼光離開薊州歸南后,對于赴北追隨戚繼光的名將陳第而言:“已而俞老戚罷,邊事隤廢,督府私人,行賈塞下,侵冒互市金錢。公力持之,為督府所怒,嘆曰:‘吾投筆從戎,頭須盡白,思灑一腔熱血,為國家封疆大計。而今不可為矣,仍為老書生耳。’遂拂袖歸里”。〔66〕作為坐鎮薊門十年的游擊將軍,陳第在官場失意、致仕歸里后,醉心古音,竟成為著名音韻學家,令人唏噓感嘆。
萬歷初年,抗倭名將湯克寬調赴薊鎮“戴罪立功”。“萬歷四年,炒蠻入掠古北口。克寬偕參將苑宗儒追出塞,遇伏,戰死。”〔67〕湯克寬的戰死沙場,贏得了軍人榮譽。
對戚繼光等北調的武將而言,生不逢時、才不盡用、命運多舛,是為將生涯的悲劇;對大明王朝而言,則有可能引發滅頂之災;最為痛苦的則是薊門黎民百姓,他們曾在流離失所時等到戚繼光等赴北名將,終于能夠免遭擄掠之苦,獲得保全生命的希望。可是,這種希望也不過持續了十余年。
“名將北調”是朝廷在“倭患”漸平和“北虜”強勢的大背景下采取的應急之舉,它以戚繼光、譚綸奉調北上練兵為開始的標志,而戚繼光的南歸,即宣告這一現象漸入尾聲。戚繼光作為明朝中后期“名將北調”現象的代表性人物,在薊州鎮守十余年,為明朝北方邊疆的防衛建設貢獻了才智。北調伊始,他懷著滿腔熱情向朝廷進言,力陳過往軍事行動中的弊病,希望能練出一支精銳之師,有朝一日,為大明“布昭神武”。然而,在種種現實原因下,其雄心壯志接連受挫,只能在薊一隅竭力施展自己的兵學才智,力保一方安寧。從“名將北調”重要目的——大練兵來看,這批地跨朝廷南北的調動有其局限性,因為譚、戚之所以倡議大練兵,并非一廂情愿,而正符合朝廷“名將北調”的初衷。然而,對于真正懂得練兵的武將,朝廷卻無法給予必需的空間與資源,反而發生諸多齟齬與不幸。
陳第曾云:“自嘉靖庚戌,虜大舉入犯,至隆慶丁卯,一十八年,歲苦蹂躪,總兵凡十五易。自戊辰南塘戚公來薊,時總督者,二華譚公也。至萬歷壬午,一式五年,胡塵不起,民享生全極矣。乃論者謂其不宜于北,竟徙嶺南,嗟乎!宜與不宜,豈難辨哉!”此言抨擊了那些認為戚繼光不宜北調的“論者”,其證據便是譚、戚在任時邊關平穩無虞、人民安居樂業。王世貞也曾贊賞戚繼光在南北兩地均有作為:“自兩浙、閩、廣,以及薊門邊塞,大小數百戰,所殺虜數萬計,稱東南名將無偶。”〔68〕作為一種現象的“名將北調”在一定時空內起到了積極影響,也展現出戚繼光等將領的報國熱情、使命擔當與兵學才能。其中的歷史經緯,對以“安國保民”為追求的后世兵家而言,不乏鏡鑒意義。
【注釋】
〔1〕肖立軍:《明代邊兵與外衛兵制初探》,《天津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第38頁。
〔2〕《明史》卷210《吳時來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564-5565頁。實際上,俞大猷最終未能赴北練兵,而是留在東南剿滅海賊。
〔3〕劉曉東:《嘉靖“倭患”與晚明士人的日本認知——以唐順之及其<日本刀歌>為中心》,《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7期,第109-111頁。
〔4〕《明史》卷212《俞大猷傳》,第5601-5602頁。
〔5〕《明史》卷212《俞大猷傳》,第5605頁。
〔6〕《明史》卷212《俞大猷傳》,第5605頁。
〔7〕《明史》卷222《譚綸傳》,第5833頁。
〔8〕《明史》卷212《戚繼光傳》,第5610頁。
〔9〕戚祚國等:《戚少保年譜耆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237頁。
〔10〕錢謙益著:《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陳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第542-543頁。
〔11〕《明史》卷212《湯克寬傳》,第5609-5610頁。
〔12〕《明史》卷92《兵四》,第2261頁。
〔13〕趙翼:《明中葉南北用兵強弱不同》,《廿二史劄記校證》卷34,王樹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814-815頁。
〔14〕《明史》卷91《兵三》,第2235頁。
〔15〕以上可次第見于:《明史紀事本末》卷60《俺答封貢》,河北師范學院歷史系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911頁;《明史紀事本末》卷60《俺答封貢》,第911-912頁;《明會要》卷60《兵三》,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157頁;《明史》卷91《兵三》,第2239頁;《明史紀事本末》卷60《俺答封貢》,第912頁;《明史》卷91《兵三》,第2240頁;《明會要》卷60《兵三》,第1157頁;《明史》卷91《兵三》,第2240頁;《明史紀事本末》卷60《俺答封貢》,第924頁。
〔16〕《明史》卷18《世宗本紀》,第248-249頁;《明史》卷212《戚繼光傳》,第5612頁;《明史》卷91《兵三》,第2246頁。
〔17〕《明史》卷18《世宗本紀》,第249頁。
〔18〕《明史》卷18《世宗本紀》,第250頁。
〔19〕戚祚國等:《戚少保年譜耆編》卷6,第197頁。
〔20〕鄭若曾:《籌海圖編》,李致忠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988頁。
〔21〕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年,第97頁。
〔22〕芮趙凱、蘭延超:《<全浙兵制考>若干問題再探討》,《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7年第4期,第21頁。
〔23〕范中義:《論明朝軍制的演變》,《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37頁。
〔24〕《明史》卷91《兵三》,第2251-2252頁。
〔25〕戚繼光:《請兵破虜疏》(隆慶戊辰),載《戚少保奏議》,張德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35-38頁。亦可見戚祚國等:《戚少保年譜耆編》卷7,第201-203頁。
〔26〕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卷322《譚襄敏公奏疏》,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432-3433頁。
〔27〕《明史》卷222《譚綸傳》,第5835-5836頁。
〔28〕《明史》卷91《兵三》,第2241頁。
〔29〕張怡撰:《玉光劍氣集》卷8《武功》,魏連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372頁。
〔30〕《明史》卷212《戚繼光傳》,第5614頁。
〔31〕關于戚繼光在北方職務問題的探討,詳見范中義:《戚繼光大傳》,第137-139頁。
〔32〕戚祚國等:《戚少保年譜耆編》卷8,第241頁。
〔33〕沈德符撰:《萬歷野獲編》補遺卷3《兵部·士兵》,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73頁。
〔34〕參見戚祚國等:《戚少保年譜耆編》卷八,第250頁。
〔35〕《明史》卷212《戚繼光傳》,第5614-5615頁。
〔36〕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19《戚繼光傳》,第2407-2408頁。
〔37〕戚繼光:《戚少保集·建輜重營》,載翟清福主編:《中國邊境史料通編》,第10110-10111頁。
〔38〕《明史》卷92《兵四》,第2268頁。
〔39〕劉利平:《明代戰車“未嘗一當敵”“亦未嘗以戰”質疑》,《廣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40〕《明史》卷212《戚繼光傳》,第5615頁。
〔41〕戚祚國等:《戚少保年譜耆編》卷8,第253頁。
〔42〕張怡撰:《玉光劍氣集》卷8《武功》,第373頁。
〔43〕張岱:《石匱論贊·石匱書·兵革志》,欒保群校點,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年,第42、120頁。
〔44〕沈德符撰:《萬歷野獲編》卷17《兵部·火藥》,第433頁。
〔45〕《明史》卷212《戚繼光傳》,第5616頁。
〔46〕《明史》卷238《李成梁傳》,第6186頁。
〔47〕《明史》卷212《戚繼光傳》,第5616頁。
〔48〕戚祚國等:《戚少保年譜耆編》卷12,第410頁。
〔49〕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19《戚繼光傳》,第2408頁。
〔50〕《明史》卷239《尤繼先傳》,第6225頁。
〔51〕《明史》卷212《戚繼光傳》,第5616頁。
〔52〕謝肇淛:《五雜俎》卷15《事部三》,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29頁。
〔53〕《明史》卷213《張居正傳》,第5646頁。
〔54〕參見陳寶良:《明代的文武關系及其演變——基于制度、社會及思想史層面的考察》,《安徽史學》2014年第2期。關于“文人尚武”與“武將好文”,亦可參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55〕黃仁宇:《萬歷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78頁。
〔56〕沈德符撰:《萬歷野獲編》卷22《督撫·提督軍務》,第555頁。
〔57〕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19《戚繼光傳》,第2408頁。
〔58〕戚繼光:《祭大司馬譚公》,《止止堂集·橫槊稿下》,王熹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224、226頁。
〔59〕王士禛撰:《池北偶談》,靳斯仁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420頁。
〔60〕沈德符撰:《萬歷野獲編》卷17《兵部·武臣好文》,第434頁。
〔61〕《明史》卷239《蕭如熏傳》,第6222頁。
〔62〕萬明:《從戚繼光的文化交游看晚明文化視域下的“武臣好文”現象》,《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63〕錢謙益著:《列朝詩集小傳》下集《丁集中·戚繼光》,第540頁。
〔64〕秦博:《論明代文武臣僚間的權力庇佑——以俞大猷“談兵”為中心》,《社會科學輯刊》2017年第4期,第154頁。
〔65〕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19《戚繼光傳》,第2408頁。
〔66〕張怡撰:《玉光劍氣集》卷8《武功》,第373-374頁。
〔67〕《明史》卷212《湯克寬傳》,第5610頁。
〔68〕張怡撰:《玉光劍氣集》卷8《武功》,第3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