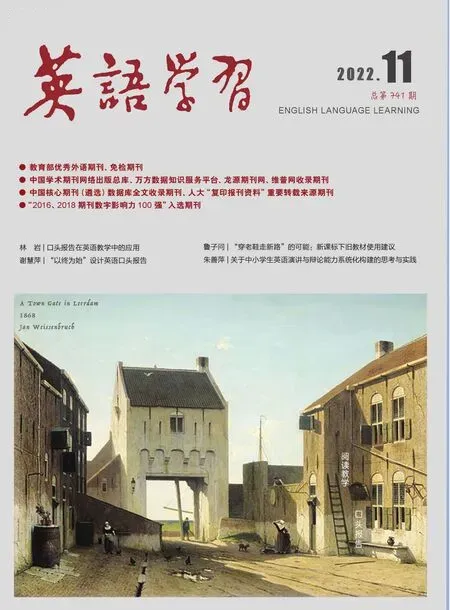《簡·愛》中理想化的英國民族身份(下)*
文 / 張靜波 張雪寧
殖民主義和東方主義對比中的英國民族特征
在小說《簡·愛》中,為了突出簡的英國民族特征,作者使用最多的技巧是將簡和殖民地及東方人物對比。羅切斯特的牙買加妻子伯莎是小說中的最怪誕恐怖的異域殖民地形象。羅切斯特滔滔不絕地比較了簡和放蕩不貞的妻子在外形和心理上的差異,并后來向簡說明,這種差異根植于種族。在小說中,伯莎在瘋癲后,一直遭受監禁,未曾發聲。簡如此描述伯莎:“好像是四肢著地在爬行,又抓又嗥像只奇怪的野獸。然而它卻穿著衣服,一頭濃密的灰白頭發,蓬亂得像馬鬃似地遮住了它的頭和臉。”(勃朗特,1996)伯莎是黑人還是白人,評論家為此爭論不休。然而19 世紀的英國普遍認為,在殖民地的白人也同樣低等墮落、酗酒成性。而因之前羅切斯特和歐洲情婦廝混以及與殖民地女性的聯姻,他和桑菲爾德府都受到了“污染”,必須毀滅,才能獲得重生。
伯莎的肥胖臃腫,象征著違背維多利亞道德規范的縱欲濫交。羅切斯特向簡解釋了他如此對待妻子,皆因伯莎的酗酒淫亂。事實上,伯莎只是一種女性意象——意指情感不受約束、恣意妄為的殖民地外族人。伯莎的形象和維多利亞時期的家庭女教師構成了鮮明對比:前者放蕩不羈,破壞力極強;而后者壓抑緘默,維護維多利亞時期的道德規范。
在《簡·愛》這部小說中,和英國人對立的另一類人是“東方人”。小說的后半部分以對比敘事的手段,映襯了簡理想的英國特征,強化了簡的英式民族意識。賽義德(Edward Said)(1979)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分析了西方人歷史想象中的東方。賽義德認為,提起“異國”,歐洲首先想到的就是東方,東方固有的神秘莫測吸引著西方的目光,資本主義的擴張也涉足至此,歐洲也以異于西方“規范”的異國特征來定義東方。在這一視角下,東方人不僅被認為價值觀和歐洲人對立,還被視為色情淫蕩的象征。在小說中,“東方”被隱晦地意指為和維多利亞時期新興中產階級道德觀相沖突的落后文明。
在小說開篇,簡這樣描述自己:“我爬上窗座,縮起雙腳,像土耳其人那樣盤腿坐著,把波紋厚呢的紅窗簾拉得差不多合攏,于是我就像被供奉在這神龕似的雙倍隱蔽的地方”(勃朗特,1996)。“土耳其人”并未指明男女,隨即又是“波紋紅窗簾”,這令人想到后宮(后宮意象在小說的不同語境中數次出現)。簡認為自己是盎格魯中心主義之外的“東方異國人”——他們在繪畫作品中盤腿而坐,突出東方人異于西方的舉止習慣和社交習俗。簡的這種自我認知,強調了她被“常規”家庭視為異類。簡的女性身份還令人聯想到深宮后妃,這帶來雙倍的排斥感。但隱藏之意和“神龕”一詞,揭示了簡不同于手無縛雞之力的閨中女子。此時的簡已展現出內在的力量和優勢,后來簡與羅切斯特關于“后宮議題”的對話,也進一步強調了簡的與眾不同。簡閱讀的書籍,如托馬斯·比尤伊克(Thomas Bewick)的《英國禽鳥史》(History of british birds),體現出她對“海鳥棲息的地方”感興趣,證明了她身上毋庸置疑的英國民族特征,
開篇處,簡將自己比作“土耳其人”,實則是諷刺里德一家對簡的排斥,認為她“滿腔惡意、心靈卑鄙、陰險狡詐”。在簡證明自己是英國淑女之前,她必須糾正他人對她的誤解。簡的“隱藏”,體現了內在的真實與真誠,這正是她英式特征的核心,也將簡與里德一家區分開來。里德一家并不是“真正的”英國人,反而簡這個“奇怪的、格格不入的異類”“闖入者”,最終體現了英國的民族意識。
簡進入洛伍德學校(Lowood School)后,校長勃洛克赫斯特(Brocklehurst)認為她“比向梵天祈禱、向訖里什那神像頂禮膜拜的小異教徒還要壞”(勃朗特,1996)。在維多利亞時代,此典故指異教徒誤入歧途后作出的最邪惡的行徑,他污蔑簡持有偏離 “上帝的羔羊”的基督教道德觀。勃洛克赫斯特批評印度教這種東方宗教助長了怪誕的宗教習俗;而事實上,他自身對于印度教的諷刺也映射了他極端苛刻的處事方法——踐踏學生的情感,摧毀孩童的神氣。
簡在去往洛伍德學校時,帶了一本《阿拉伯故事集》。這部無意間被提到的東方書籍蘊意深長,其中的東方故事充斥著“粗俗的方言”和“低級的娛樂”,摻雜著迷信和陰謀,“和那個時代的理性主義形成有趣的對比”(Kabbani,1986),彰顯出西方人眼中基督教高于“異教”的優越性。這些歐洲人編寫的東方故事集里,到處都是有著“羚羊般雙眸”的女奴(Kabbani, 1986)。之后,簡沉迷于欣賞英國冬季的典型風景,聆聽貝茜講述“最迷人的故事、唱了最動聽的歌”(勃朗特,1996),這是典型的英式娛樂方式。同時這一幕發生在簡去洛伍德學校之后,她的生活邁入嶄新的獨立階段,這本《阿拉伯故事集》更不適合她讀。在學校里,海倫閱讀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的《拉塞拉斯》(Rasselas),這是一部與眾不同的東方故事集。雖然書中主人公并非基督徒,但故事卻肯定了基督教價值觀。簡謙遜地承認個人品味“淺薄”,“真正嚴肅和內容豐富的書,我還消化不了,也理解不了” (勃朗特,1996)。
小說的后半部分又引用了《一千零一夜》中的意象,如羅切斯特稱簡為“善良的妖怪”,簡描繪情敵布蘭奇·英格拉姆(Blanche Ingram)為“烏油油的鬈發,東方人的眼睛”(勃朗特,1996),是典型的異國風情形象。同時這些東方意象進一步彰顯了當時的維多利亞思潮:上流社會的英格拉姆輕視工作,對家庭教師階級鄙夷傲慢,和簡的勤奮樸實形成鮮明對比。簡希望成為有用之人,為他人服務,而不僅僅只取悅男性——她崇尚清教徒的職業道德,這是她作為維多利亞時代典范女性的重要品質。相反,維多利亞文學和繪畫作品中的東方女性被描繪成懶惰且貪圖享樂的形象。卡巴尼(Kabbani , 1986)如此描述維多利亞時代畫作中的東方人物:“東方繪畫中的女性不工作……她們不動針黹,不進廚房,從不禱告,幾乎不履行任何責任。她們只為男人梳妝打扮,等待他們的垂青。”在桑菲爾德府中,英格拉姆一身西亞公主裝扮,讓羅切斯特用“貴重的手鐲和耳飾”裝飾她,而簡認為她“既無識別能力,也無獨立見解”,“頭腦十分空虛,心田天生貧瘠” (勃朗特,1996),十分符合維多利亞語境下東方女性的形象。
在第十二章中,勃朗特將福音主義基督教價值觀,即“真正的英國特征”,與“東方”所代表的奢侈放縱所對比,由羅切斯特自喻為“穆罕默德”而引發。羅切斯特在初遇簡時,曾經說道,“我看,山是永遠都帶不到穆罕默德跟前來的,所以你只能幫穆罕默德到山跟前去。我只好請你到這兒來了。”相比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在19 世紀的某些社會條件下可能有其優勢,但未被正視;另外西方在對東方的殖民入侵中,將一夫一妻制立為家庭模范,進而將一夫多妻制等同于暴虐的男權統治和后宮嬪妃。事實上,小說的前半部將羅切斯特比作“穆罕默德”,是為之后的情節埋下伏筆。小說后半部揭露了羅切斯特至少與三名情婦廝混,與簡結婚時還為重婚狡辯開脫。通過東方隱喻體現羅切斯特的一夫多妻傾向,是英國基督教所倡導的一夫一妻制的反敘事。一夫一妻的英國家庭,才是維多利亞浪漫愛情皆大歡喜的典范特征。
在羅切斯特和簡之后的交流中,“后宮”意象表現得更加直接。在兩人商談結婚的過程中,羅切斯特贈與她大量珠寶和綾羅綢緞,簡就像蘇丹“贈以金銀珠寶使之變富的奴隸”,這個場景類似于羅切斯特猜謎時賜予英格拉姆珠寶的情景。簡的質樸與維多利亞視角下東方的放蕩淫亂形成了鮮明對比:
他咯咯地笑了起來,搓著雙手。“喔,看著她,聽著她說話真有趣!”他大聲說道。
“瞧她多奇特,多潑辣!哪怕拿土耳其皇帝后宮的全部嬪妃來換這個小個子英國姑娘,我也絕不會答應,盡管她們有瞪羚般的大眼睛,天仙般的身材,還有一切的一切!”
這樣用東方嬪妃來作比較,又刺痛了我。“我可絲毫也比不上你的那些嬪妃,”我說,“所以千萬別把我當成她們那樣的人。要是你對嬪妃之類有愛好的話,先生,你就趕緊去伊斯坦布爾的市場,把你在這兒不知怎么花才好的所有余錢全帶上,買它一大批女奴吧。”
“那當我在討價還價,忙著購買成噸成噸的肉和各種各樣的黑眼睛時,簡妮特,你將做點什么呢?”
“我將打點一下,去做傳教士,去向那些受奴役的人——當然也包括你那些后宮嬪妃——宣傳自由。我要到你的后宮里去。鼓動她們起來造反,盡管你是個三尾帕夏,先生,你仍會一轉眼工夫就落到我們手中,給戴上腳鐐手銬。就我個人來說,除非你簽署一個民權憲章,一個專制君主所頒發過的最開明的憲章,否則我是不會同意砍斷你的鐐銬的。”(勃朗特,1996)
這段對話將東方視為專制獨裁和性別壓迫的存在,但含義不止如此,其中復雜地交織著東方主義、經濟平等以及體現維多利亞道德價值觀的福音主義。對羅切斯特來說,蘇丹的男權后宮象征著控制,男性能夠輕易支配女性。羅切斯特宣布整個后宮也不能跟他交換這個英國姑娘,一方面彰顯了白人的民族優越感,另一方面這種比較也是對簡的貶低,暗示著羅切斯特的暴君傾向和文化自負。由于簡在經濟上處于劣勢,這番比較令她感到自己如同奴隸,不過是等價交換的物品。簡馬上進行了反駁,即“開明的傳教士拯救被動的東方人”。這段對話又一次強化了簡的英式民族特征——追求自由、獨立和兩性平等。
后宮意象在維多利亞文學中隨處可見。正如卡巴尼(1986)所言:“歐洲被有著各種可能性的閃耀東方所吸引,東方預示著情欲想象,遠離自我的航行,一次大都市中產階級道德的逃避。”后宮的意象還體現一夫一妻制在民族道德感中的優越性。簡強有力地支持維多利亞時期福音主義推崇的一夫一妻制。在《簡·愛》中,勃朗特深知維多利亞時代的兩性婚姻對于女性的壓迫和自主的否定。艾德麗安·里奇(Rich,1979)認為,在這個著名的情節中,簡在桑菲爾德府邸的抗議,實則是勃朗特的“女性主義宣言”,簡呼吁女性應該擁有更多平等和自由,應該在工作中實現自我,發揮才能。這段宣告激情澎湃,在維多利亞小說中無出其右。
小說試圖調和簡對獨立自主的追求以及和羅切斯特婚姻中的矛盾,調和辦法是在婚姻感情中,簡要掌控情感中的感性和理性——理性是勃朗特筆下英式女性的追求目標,理性可以駕馭感性。伯莎雖不是東方人,但卻有著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式”的淫亂縱欲、毫無理性,最終走向毀滅。而具備理性克制等英國特征的簡則出類拔萃,邁向幸福。此外,在羅切斯特融入和睦節欲的英式福音家庭之前,他的一夫多妻傾向必須得以糾正。因此羅切斯特的眼睛(男權/國王的凝視)和手都受傷了,簡將羅切斯特稱作“身處籠中的野獸或者鳥兒”“籠中雄鷹”“失明的參孫”(勃朗特,1996)。
19 世紀上半葉后,男性和女性的地位緩慢發生變化,男權社會受到女性的質疑。克勞迪婭·納爾遜(Nelson,1995)認為 ,羅切斯特的權勢在小說中逐漸走弱,標志著男權地位在英國被削弱,也說明社會“對女性越來越著迷”,簡因此增強了個人力量和權威。納爾遜同時認為,在維多利亞早期,“理想婚姻愈加強調陪伴、平等和愛情”,這種“感性家庭”逐漸“削弱了中產階級家庭父親的既有權力”,“提高了母親的道德地位”。在小說的后半部,簡重獲話語權,向失明的羅切斯特描述世界,成為家庭的主導權威。在兩人的婚姻生活中,殘疾將羅切斯特束縛在家庭內,兩人舉案齊眉。“我們整天都在交談,而相互交談只不過是一種更加生動活潑、可以聽見的思考罷了”(勃朗特,1996)。夫婦倆主觀意見完全融合,兩性達成平等。因此,小說結尾可視為簡發動了一次強勁女性運動的勝利,簡成為跨越性別和階級的英式淑女代表。
維多利亞的英式淑女與民族意識
小說結尾,簡·愛和羅切斯特居住于芬丁莊園,這種安排更加鞏固了簡的英國女性身份。芬丁是英國理想化家庭的縮影,簡的好友戴安娜和瑪麗也具有真正的英國特性,芬丁和她們二人的小家庭聯系起來,形成了“想法不謀而合、觀點彼此相同”(勃朗特,1996),有著統一信仰和價值的共同體。
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Anderson,1991)認為,共同信仰和價值是民族意識的基礎。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家庭和民族使命的關系,需要置于維多利亞時期社會和歷史背景下分析。19 世紀初,在《簡·愛》面世前,莎拉·劉易斯(Sarah Lewis)出版了《女性使 命》(Woman’s Mission),強 調了維多利亞民眾對于女性參與社會政治和慈善活動的關注,以及英國女性在廢奴運動中異常活躍的現象。由于擔心女性活動擴展到政治領域,英國社會開始制訂“家庭使命”,重新界定女性的活動范圍,局限其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并且為女性加上道德桂冠“家庭天使”,將其囿于家中,強化了對女性的束縛。但是女性知識分子則認為,女性地位不僅限于家庭,應該為女性的政治權利和平等發聲。在小說中,簡也數次宣稱,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不只是局限于“做做布丁、織織襪子、彈彈鋼琴、繡繡錢包”(勃朗特,1996)的日常瑣事,而是在家庭之外也能施展才能。
在小說結尾處,圣約翰的“教化使命”和簡的“家庭使命”花開兩朵、各自燦爛,其歷史背景則是英國對印度實行的帝國政策。19世紀早期,福音派和功利主義改革者的熱情從國內擴張到印度,東印度公司早期實行“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政策,只要不干擾殖民貿易,就可接納印度的宗教和文化活動。此政策是對英國傳教士欲將印度改造為基督教國家的退讓和屈從。之后福音派和功利主義者不斷擴張發展,將印度描繪成迷信、無知和無可救藥的國度,催化了傳教士對印度民眾的改造進程。廢奴運動領袖威廉·威爾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聲稱,將印度轉變為基督教國家是“最偉大的事業,它比廢除奴隸運動更重要。”1813年,威爾伯福斯向下議院宣揚,次大陸(sub-continent)將“以基督教光明和真理,來取代此地的黑暗、血腥的迷信”;他還認為印度教諸神是“徹頭徹尾的惡魔,淫蕩放縱,處事不公,殘忍邪惡。總之,他們的宗教令人深惡痛絕。”(Moorhouse,1983)
埃里克· 斯托克斯(Eric Stokes)(1959)對于邊沁功利主義對印度的影響頗有見地。他認為,英國功利主義對于印度立法和司法的歷史構建影響巨大,但英國功利主義者并非單獨行動,而是與福音派教義相互交織。福音派致力于皈依和教育,而功利主義強調法律的作用,即“通過人為地將個人行為與懲戒關聯,幫助人們規避有害的行為”(Stokes,1959)。他們的改革熱情堪比19 世紀30 年代的種族主義者,“對于維多利亞時代的民眾而言,無論生活在女王統治的早期或后期,都認為英國人天生就是‘一個征服的、統治的和文明的民族’;被他們統治的低等種族原本就匱乏管理和教化的能力。”(Brantlinger,1988)因此,“教化使命”貫穿小說的后半部分是很自然的。
在小說結尾處,簡發自內心地贊譽去印度傳教的圣約翰:“他在危巖和險境中埋頭苦干,再也沒有比他更不屈不撓、更不知疲倦的先驅者。他堅定、忠實、虔誠,精力充沛、熱情洋溢、無限真誠地為他的同類勤奮地工作著。他為他們開辟艱難的前進之路,他像巨人般砍倒阻塞在這條路上的信仰上和種姓上的偏見。”(勃朗特,1996)事實上,簡作為英國的家庭意象和圣約翰代表的英國帝國形象有些對立。筆者認為,簡反對圣約翰的專橫無情,而這代表家庭與帝國之間輕重緩急的復雜辯論。簡對于圣約翰的冷酷頑固、自我犧牲,以及在傳教時對無情的教條的尊崇無法茍同,認為教義與自己溫和寬廣的福音教導格格不入;但同時簡也保留了對圣約翰勃勃野心的崇拜和尊重,這在某些方面也對應了“女權主義宣言”的雄心壯志。但簡對于真情實感和浪漫愛情的渴求削弱了她的野心。雖然她曾聲稱準備和姐妹們去印度,但不會做陌生人的助手,說明她需要有著共同價值觀和知識追求的共同體。簡不愿成為圣約翰的妻子,屈從于沒有愛情的婚姻家庭。但從人格而言,簡崇拜圣約翰的才華。在小說結尾處,簡介紹了圣約翰的境況,將圣約翰比作班揚《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中的“武士大心”,這表明簡同樣認識到,英國需要圣約翰這樣的男性——放棄情愛、斗志昂揚。如果說羅切斯特是拜倫式的英雄,那么圣約翰則是由基督教十字軍感召下的帝國形象——“冰冷、笨重的石柱子”。缺乏人類浪漫情感的圣約翰在英國格格不入——他的“大事大業”及遠大目標,都與“小人物的情感和要求”相悖,因此只能在帝國殖民的海外區域得以表達和實現。
結語
縱觀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可以看出其文化背景的浸潤。在“人是文化的動物”這一本性中,既包含了人的‘生物—自然’屬性,也包含了人的‘精神—社會’屬性(謝暉,2020)。維多利亞小說的人物基本都是英國民族特性的代表人物,他們被視為英國身份和“優越性”的典范,這種理想化的民族特性是建立在英國道德優越感的既定基礎之上的。《簡·愛》中,作為中產階級淑女代表的簡的成長歷程體現了社會的三點重要進步:一是英國的民族特征本質是其固有的、廣泛認可的真誠和自由;二是維多利亞社會中的福音主義道德價值觀和文雅的社會禮儀被中產階級廣泛認可并遵從,維多利亞的民眾推崇樸素優雅和真誠高尚的風尚,強調一夫一妻制并遵從嚴格的職業道德觀和家庭使命感;三是《簡·愛》將家庭和民族意識聯系起來,簡之所以能夠獲得經濟和地位獨立,至關重要的一點是獲得了從事殖民地貿易的叔叔的遺產財富收入,勃朗特巧妙地將教化文明和帝國殖民聯系起來。這種國內的家和萬事興與對殖民地的文明擴張交織互文,使《簡·愛》呈現出一種強大的民族敘事特征,成為彰顯維多利亞時期英國文化和文學特征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