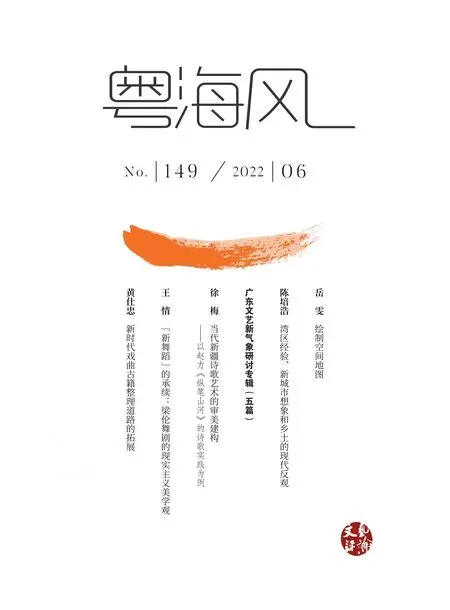“中國故事”話語構建中的廣東文學
文/郭冰茹
在全球化語境和世界文學的格局中,講好“中國故事”,塑造中國形象,并以此構建中國文學的話語體系是當代文學的歷史使命。21世紀以來,尤其是近些年的文學創(chuàng)作,以書寫重大現(xiàn)實題材來重建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借助創(chuàng)造性地轉化文學傳統(tǒng),探索能夠體現(xiàn)“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民族形式”;利用“文體融合”或“綜合寫作”表達文學觀念的新變。這些文學實踐都體現(xiàn)出文學界構建中國文學話語體系的趨向和努力。廣東文學,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參與者,一方面顯現(xiàn)出緊隨當代文學走向的整體趨勢,另一方面也以鮮明的地方性特征,努力講好當代“嶺南故事”,讓“嶺南故事”成為“中國故事”的有機組成。
一
弗雷德里克·杰姆遜曾在《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中說:“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于個人和力比多趨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沖擊的寓言。”他的這一基本判斷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回到文學本身”的呼聲中受到一定的質疑,但很快,在文藝界對“純文學”的反思,對社會現(xiàn)實、社會文明建設的關注中,重大題材、主旋律作品又回到創(chuàng)作者的視域中來,曾經被個人的情感、欲望、私密空間所拆解的宏大敘事得以重建。這一方面是因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對主旋律文藝作品的倡導從未間斷,并提供了相應的制度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文學自身的自律性要求,顯然過于執(zhí)著“小我”的狹小空間,沉浸在人生無常或歷史的虛無感中,會使文學失去把握現(xiàn)實的能力,失去升華的空間,進而失去文學本身的生命力。也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重建宏大敘事成為開啟文藝界講述“中國故事”的新篇章,而廣東文學也在這一脈絡中凸顯出自身的特點。
近年來,廣東文學對宏大敘事的主要書寫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對重大題材的處理。廣東的紀實文學對現(xiàn)實生活的介入表現(xiàn)出一種特有的迅敏,《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中國橋——港珠澳大橋圓夢之路》《嶺南萬戶皆春色》等作品聚焦于小康社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qū)建設、扶貧攻堅這些新時代人們最關心的歷史命題展開記錄。作品的落腳點雖然是嶺南,反映的卻是時代的脈搏;書寫的是當代中國人的精神風范,從中更透出開放兼容、務實進取的廣東精神。
二是對革命歷史的再次書寫。這不僅體現(xiàn)在紀實性作品中,比如長篇報告文學《信仰——周恩來嶺南紀事》《腳印——人民英雄麥賢得》《黎明之前——廣州起義紀事》,也體現(xiàn)在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比如龐貝的《烏江引》、王溱的《第一縷光》。這些作品既寫出了革命者的理想、信仰、奮斗和犧牲,也寫出了革命者的困境、掙扎和個人情感;既寫出了革命斗爭的恢弘壯闊,也兼顧到日常生活的尋常細碎;既有偉大中的平凡,也有平凡中的偉大。這些作品能夠直面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塑造豐滿生動的英雄形象,不僅在價值層面上表現(xiàn)出理想和信仰的崇高,在美學層面上顯現(xiàn)出人性的崇高,也改變了碎片化的歷史敘事方式,在一定意義上重建了整體性的歷史觀。
三是對現(xiàn)實的強烈關懷。非虛構寫作在這方面有著獨有的優(yōu)勢,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孫善文的《深圳買房記》、王國華的《街巷志:深圳體溫》都是從寫作者個人的觀念、立場、感受出發(fā),帶著自身的困境和思考,書寫“小人物”在大時代中的生存感受。雖然都是以個人化的方式介入文學書寫,但與20世紀90年代流行的“個人化寫作”非常不同,這些非虛構寫作并沒有在個人經驗上敲敲打打,而是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可以說是文學書寫介入社會生活最尖銳也最有沖擊力的方式。與非虛構寫作相呼應的是小說創(chuàng)作,張欣的《千萬與春住》、吳君的《曬米人家》、盛可以的《女工家記》等作品,都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在世俗的點滴中寫出經濟的飛速發(fā)展、現(xiàn)代文明的快速擴張帶給人的復雜影響。這其中是混雜著傷感與茫然的奮斗、困頓與消沉的進取,現(xiàn)代生活的兩面性在這些書寫現(xiàn)實的文本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呈現(xiàn)。既叩問人性,也表達出一種試圖建構現(xiàn)實生活詩意烏托邦的努力。
近年來的廣東文學從不同角度重建宏大敘事,讓“中國故事”再現(xiàn)了“歷史創(chuàng)造者”的激情和理想主義的光輝。如果文學不僅僅被理解為對社會現(xiàn)實的反映,更被視為一種想象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方式,那么21世紀以來,尤其是近些年對宏大敘事的重建也就不完全是杰姆遜所說的服務于現(xiàn)實文化需要的“民族寓言”,而是當代中國在與歷史和現(xiàn)實的不斷對話中,確立并確認自身主體意識的話語方式,廣東文學無疑深刻地參與其中。
二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當代文學一直是在回應西方現(xiàn)代性的沖擊,或者說在“影響的焦慮”中講述著“中國故事”。20世紀80年代中期幾乎同時出現(xiàn)的“尋根文學”和“先鋒小說”,就分別從回到民族文化傳統(tǒng)和積極學習西方兩個向度,探尋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性之路。隨著“尋根”的落幕,“先鋒”形式實驗的無以為繼,當代文學需要重新處理自身與文學傳統(tǒng)的關系,90年代出現(xiàn)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以及在創(chuàng)作中“先鋒派”的集體轉向,都在某種程度上顯現(xiàn)出重新認識傳統(tǒng),創(chuàng)造性轉化傳統(tǒng)的迫切性。
回溯百年新文學的發(fā)展歷程,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借助批判章回體小說來批判“舊傳統(tǒng)”是新文學發(fā)軔之初新舊文化沖突的必然。但是,新文學這種對待“舊傳統(tǒng)”的態(tài)度在20世紀30年代“文藝大眾化”運動中發(fā)生了變化,茅盾對新文藝作品只能進入知識分子的閱讀圈感到非常失望,認為新文藝應該學習舊小說講故事的方法,以爭取更廣泛的讀者。“舊傳統(tǒng)”因此在“舊形式”的意義上得到了部分吸收和肯定。1940年代,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構建中強調“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和“民族形式”,民間的、傳統(tǒng)的、本土的敘事資源再次在形式的意義上受到關注,利用“舊形式”創(chuàng)造“新內容”成為當時的普遍共識。然而,正如杰姆遜對藝術形式的分析,“當過去時代的形式因素被后起的文化體系重新購入新的文本時,它們的初始信息并沒有被消滅,而是與后繼的其他信息形成新的搭配關系,與它們構成全新的意義整體”。中國當代文學對“民族形式”的成功探索出自《小二黑結婚》《紅旗譜》這類靈活化用傳統(tǒng)敘事資源的作品,而非完全套用章回體形式講述革命歷史的“革命英雄傳奇”。即便是新時期文學中的“尋根”,在寫作方式上也多使用西方現(xiàn)代小說的敘事技巧,比如敘事時間的中斷、停滯和跳躍,敘事人的視角越界,借助人物夢境、幻覺、潛意識塑造人物性格等。這都說明民間的、本土的文化資源逐漸超越了文藝界對“舊形式”的理解受到關注,而要講好“中國故事”,探索屬于中國自己的“民族形式”則需要我們將民族文化傳統(tǒng)視為一個包含了內容、形式、審美、精神意蘊的意義整體。
1997年獲得“茅盾文學獎”的《白門柳》可以視為廣東文學中較早對文學傳統(tǒng)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文學實踐。小說寫明末清初的社會巨變和知識分子的人生選擇,具體的歷史語境和真實的歷史人物都需要作者將承載明末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tǒng)作為一個意義整體來表達。這部作品雖然沒有借用章回體,但文中大量古典詩詞營造出的意境,構成了古典文學傳統(tǒng)與當代文學的對話空間。新近出版的《燕食記》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小說從嶺南飲食風物著眼,寫大灣區(qū)的世紀滄桑。李敬澤說:“《燕食記》里,時間流逝、人世翻新、眾人熙來攘往,如夢華錄、如上河圖,這盛大人間中,舌上之味、耳邊之聲,最易消散,最難留住,也最具根性,最堪安居。”這一評價實際上也點出了《燕食記》與中國古典世情小說的淵源。
作為意義整體的“民族形式”當然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作品的形式,當文學成為一種想象世界的方式時,地方性經驗往往成為其中最重要的構成。近年來廣東文學對地域文化、風土人情的描摹早已超越了當年“尋根文學”對地方色彩的認知,成為一種地方性知識的表達。郭小東的“中國往事”五部曲(《銅缽盂》《仁記巷》《光德里》《桃花渡》《十里紅妝》)以家族史的方式,借商貿往來帶出了潮汕地區(qū)的民俗風物和世態(tài)人情,這其中對銀錢匯兌和僑批中蘊含的誠信與契約精神的書寫,展現(xiàn)出傳統(tǒng)的嶺南文化中極具現(xiàn)代意識的部分。陳繼明的《平安批》借潮汕地區(qū)僑批文化中的誠實守信、重情守義,將個人命運匯入民族大義和家國情懷中,以一方人的道德情操寫出了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盧欣的《華衣錦夢》選擇的是粵劇服飾的制作技藝,并以戲服文化串聯(lián)起祭祀、飲食、日常交往等社會民俗,寫出廣州近百年的市民生活史。還有梁鳳蓮的《賽龍奪錦》原是一首描述嶺南端午龍舟競渡的熱鬧場面的絲竹樂曲,作者將其用作書名,以歷史的大視野為廣東音樂的創(chuàng)始人和傳承人立像,更是為百年流芳的廣東音樂立傳。這些作品對民風民俗的細膩勾畫不僅成為“民族形式”的標識和體現(xiàn),也傳達出一種來自民間的堅忍不拔和自強不息,也正是這種地方風物和民族精神成為一種與全球化相對應的地方性知識,為毛澤東當年提出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注入新時代的內容和意蘊。
作為“中國故事”的表達方式,當代文學對文學傳統(tǒng)的利用,對地方風物的書寫不僅是探索“民族形式”的需要,也是當代文學成為“中國制造”的文體需要。近些年廣東文學的這些文本實踐反映出當代中國在本土與西方、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不斷對話中建構自身文化身份的一種努力。
三
講好“中國故事”,才能有效地服務于當代中國話語體系的構建。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分析了構成話語實踐主體部分的陳述(statement)所具有的某種整體性特征,說它包含了對一個話語事件的界定和闡釋、對其發(fā)展過程和各種對應關系的描述,以及對其結果和意義的評論,等等。在此,陳述本身不僅是一個被敘述的單位,同時也是一種功能。因此,當我們將“中國故事”視為一種陳述時,在關注其內容和形式(被敘述的單位)的同時,還需要進一步考察基于這種文學生產帶來的觀念變化(功能)。換言之,也只有將“中國故事”視為一種“整體性”的陳述,才有助于我們從宏觀上把握當代文學之于中國話語建設的實踐意義。
文學觀念的變化與語境有關,也與經濟發(fā)展狀況有關。新時期以來經濟社會的迅速發(fā)展,促進了文化消費市場的成熟和作家創(chuàng)作主體性的增強,也促使文學生產過程中的寫作觀念、表現(xiàn)方式和審美追求從一元走向多元。這些轉變直接沖擊了既定的文體意識和雅俗邊界,成為文學觀念變化最直觀的表達。
就文體意識而言,現(xiàn)代文學中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的文體四分法是知識界對中國傳統(tǒng)“雜文學”的現(xiàn)代分類,每一種文體因此有了自己的文體標準和寫作規(guī)范,但在具體的寫作過程中,文體之間依然遵循著“大體須有,定體則無”的原則。早年蕭紅就曾為自己的小說寫法辯解過,她說:“有一種小說學,小說有一定的寫法,一定要具備某幾種東西,一定寫得像巴爾扎克或契訶夫的作品那樣。我不相信這一套。有各式各樣的作者,有各式各樣的小說,若說一定要怎樣才算小說,魯迅的小說有些就不是小說,如《頭發(fā)的故事》《一件小事》《鴨的喜劇》等等。”這多少說明了文體之間的邊界是流動的,是可以相互滲透的。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伴隨著寫作者文體意識的自覺,文學如何反映生活、如何書寫現(xiàn)實、如何處理寫實與虛構之間的關系就不僅是技術問題,也表現(xiàn)為對文體邊界的再認識。韓少功在討論敘事藝術的危機時說,“我想可以嘗試一種文史哲全部打通,不僅散文、隨筆,各種文體皆可為我所用,合而為一。”祝勇在與敬文東關于《舊宮殿》的對話中也說“在今天,要想較為恰當?shù)卣故疚覀兊纳钜约拔覀兊氖澜纾C合寫作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單一的文體模式在運用上十分單調和單薄,與歷史的復雜性不可同日而語”。事實上,21世紀以來不少文學創(chuàng)作都呈現(xiàn)出這種文體跨界的寫作趨勢,比如李洱的《應物兄》、王堯的《民謠》、李敬澤的《青鳥故事集》等。近些年的廣東文學也回應了韓少功“為我所用”的文體意識。熊育群的《己卯年雨雪》是一部書寫戰(zhàn)爭中的仇恨與寬恕、人情與人性、大歷史與小命運的長篇小說,但作者同時也疊加了其他文體的表現(xiàn)手法,完成了一次文體跨界的寫作實踐,通過將大量田野調查所獲得的一手材料、閱讀積累的相關知識以及收集整理的歷史文獻融入作品,這部有著鮮活人物和繁復故事的長篇小說也呈現(xiàn)出史傳文的某種敘述風格。
不過,從文體意識上看,最具有文體開放性的是近些年引起廣泛關注的“非虛構寫作”。徐剛在《虛構性的質疑與寫作的民主化》一文中對“非虛構寫作”做了如下界定:“當它與文學‘嫁接’時,產生的是諸如報告文學、紀實文學等常見文類;當它向新聞靠近時,則會呈現(xiàn)出類似深度報道、特稿和特寫的藝術風貌;而當它與社會人類學相關時,我們看到的則是田野調查、口述報告和民族志研究意義上的作品。由此,旅行筆記、個人日記、歷史散文、社會調查、深度報道,甚至某種意義上的學術研究,都可構成非虛構寫作的重要內容。”在非虛構寫作方面,黃燈的《大地上的親人》《我的二本學生》成為廣東文壇上的代表性作品。
文體意識方面的“綜合寫作”和“為我所用”同樣表現(xiàn)在當代文學的內容生產上,這是因為文化市場的成熟賦予了文學作品以文化消費品的性質。換言之,如果“中國故事”不能為更廣大的文化消費者提供精神上的滋養(yǎng),那么文學中關于中國形象的表達、關于現(xiàn)實人生的反映將無以附麗。也正因如此,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怎么寫”就不僅涉及寫作層面的表現(xiàn)方式和敘事技巧,還需包含閱讀層面的讀者體驗,反映在內容生產上便是嚴肅文學對通俗文學的類型征用。比如,麥家的“特情小說”以懸疑小說寫理想信仰,寫人性的崇高和偉大;馮唐以“情色小說”寫青春和夢想;等等。
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文化市場發(fā)展得更為成熟,張欣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寫廣州這座她居住的國際性大都會。那些俊男美女、香車寶馬穿梭在公司商場、豪宅會所之間,上演著一幕幕欲望都市里的情感歷險,圖書市場直接將她的小說定位為“都市言情”。這些小說有著類型小說的物質外殼,卻能深入到人性的細微之處,屬于叫好又叫座的暢銷書。此外,一些更年輕的寫作者也嘗試通過類型文學,以一種更敏銳的思辨力和想象力重新構建人與現(xiàn)實的總體性關系,這突出地反映在對科幻小說類型的利用和轉化中。比如龐貝的《獨角獸》、王威廉的《野未來》、黃金明的《幻想故事集》等,都以科幻小說的方式,探討人工智能時代科技社會帶給人類的種種倫理困境和心理沖擊,這類作品可以說是對“科幻現(xiàn)實主義”的某種探索。另外,還有王十月的《如果末日無期》、陳崇正的《黑鏡分身術》《貓頭鷹》等,它們或者將科幻小說與創(chuàng)世神話融會,或者讓科幻小說與鄉(xiāng)村怪史連接,構成一個個虛實結合、神秘奇崛的文本空間,這些創(chuàng)作顯現(xiàn)出寫作者想要突破寫作慣性,在文學領域重建一種“未來詩學”的努力。
隨著主體經驗、客觀知識、大眾審美等因素越來越自由地進入故事的講述過程,傳統(tǒng)的文體邊界和雅俗壁壘也得到相應的調整。文學觀念上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代文學的生產樣貌,也為我們重新講述和闡釋“中國故事”提供了新的視角。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當代文學正在與歷史的對話中重建宏大敘事,在與現(xiàn)代文明的交匯中探索民族形式,在文體融合和雅俗并舉中呈現(xiàn)文學觀念的變化,這些文本實踐不斷探索著“中國故事”的講述方式,也顯現(xiàn)出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一種趨向和努力,廣東文學正以積極的方式參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