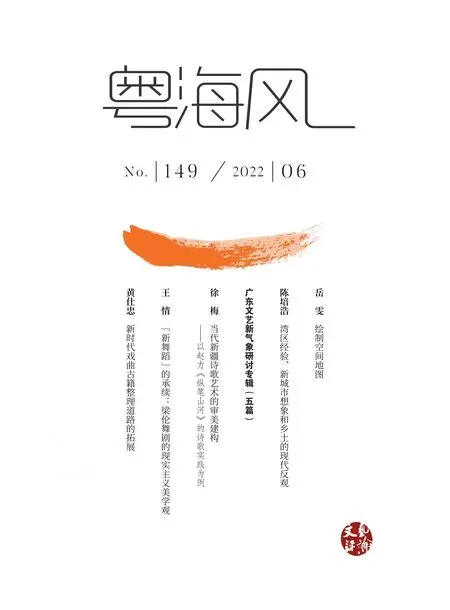史料的拓進與歷史的還原
——評陳思廣《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編年史(1922—1949)》
文/陳煒 伍明春
作為記錄歷史事件的編寫體例,編年史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的特點,讓讀者更好地了解歷史事件生成與發展,把握歷史的整體脈絡。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編年體例書寫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成為熱點,也為呈現相對完整、系統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譜系作出了突出貢獻,陳思廣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編年史(1922—1949)》(三卷本)(以下簡稱《編年史》)就是其中成績卓著的典范之作。
回望20世紀中國文學創作實績,現代長篇小說的發展與繁榮不可忽略。但如陳思廣所言,由于時代等因素影響,“關于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展史貌,學界至今沒有詳盡的‘家底’”[1],因此《編年史》重新對關涉現代長篇小說發展的史料逐一梳理,功莫大焉。《編年史》輯錄正式公開出版的中國現代新體長篇小說共356部,涵蓋了1922年2月15日至1949年9月30日期間的現代長篇小說出版時空,包括創作言論、評論文字、廣告、書信、日記、初版書影等原始資料,另有作品梗概、編者簡評等有價值的補充,可謂力求原貌摘引、原意呈現,不僅還原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史的整體發展,也為現代長篇小說的研究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史料參考。不僅如此,編年史作為一種體例,它還承載著研究者獨特的歷史態度與研究立場[2]。而從整體梳理到細節補充,《編年史》正是以重返現場、史論結合的方式,充分顯示出陳思廣先生系統、開闊的編史意識與文學史觀,為學界開拓出了顯豁光明的研究視野。
一
現代長篇小說的崛起與轉型也離不開晚清長篇章回小說的裂變,當我們談論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誕生與發展時,勢必不能忽略晚清小說在內容與形式上的突破與新變。為此,《編年史》導論部分對晚清小說的特質與缺失作了簡要回顧。不同于以往文學史十年為一斷代的創作分期,陳思廣的《編年史》以客觀的時代與環境為歷史背景,將現代長篇小說的發展劃分為發軔與奠基(1922—1929)、發展與深化(1930—1937)、低回與復興(1938—1949)三個主要階段,更另辟章節討論東北與華北兩個淪陷區及延安解放區的長篇小說創作圖景,力圖還原與呈現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整體發展。
1922—1929年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軔期,據編者統計,此時期公開出版的現代長篇小說共有71部。相比五四時期中短篇小說,現代長篇小說發展較為緩慢,一開始并未出現相對成熟的作品。但以《沖擊期化石》《一葉》為起點,作家們的創作構思從晚清民初時章回小說敘述故事的模式轉向了塑造人物形象,陸續出現了一批高揚“人的文學”創作旗幟的、帶有實驗性質的現代長篇小說。對于此時期的長篇小說,《編年史》提煉出其特質是“對人性弱點的批判與對雙重文化的觀照”[3],比如老舍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以油滑幽默的風格展開對國民文化的反思與批判,《二馬》從東西方雙重角度對國民的劣根性進行文化的觀照。
“史料是人們尋求歷史知識的開始和唯一手段,有一種史料是過去遺留下來的,所以它就為復原那個使之產生的過去提供了可能性”[4],《編年史》不僅限于對經典作家作品的史料挖掘,更將目光投向曾經被主流文學史邊緣化的長篇小說作品,如1929年上海春潮書局出版的葉永蓁的長篇小說《小小十年》。該書再現了北伐革命時期青年找尋自我的艱難歷程,對此《編年史》不僅輯錄了《小小十年》出版信息與內容梗概,還呈現了魯迅在《春潮》第1卷第8期發表的《〈小小十年〉小引》,可見魯迅對青年作者與長篇小說的評價與鼓勵,極具史料價值。
1930—1937年深化期現代長篇小說的史料挖掘,陳思廣以1937年全面抗戰為標志,將20世紀30年代以后的現代長篇小說發展分為前后兩期,使讀者可以清晰地了解時代變化對文學創作的深遠影響。據編者統計,1930年1月至1937年7月,共出版現代長篇小說113部(其中“三部曲”算作一部),此時期長篇小說的數量及藝術水平都明顯高于發軔期。《編年史》相應地輯錄了這些作品的初版與再版史料,比如在“1932年”條目下詳細記載了茅盾的《蝕》于4月份“由上海開明書店印行第四版(普及本·分冊)(文學周報社叢書)”[5],這為《蝕》的版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信息。在“1933年”條目下更有對《子夜》銷售數量的記載,“茅盾近作《子夜》,銷數之驚人,超出意外,聞只上海復旦大學一處,十天內共售去四百本……平均每三人購一本《子夜》云”[6],據此我們便可以看到當時《子夜》的傳播與接受情況,可見《編年史》對每部長篇小說的演進軌跡都作了詳細的研究梳理。
1938—1949年低回與復興期的現代長篇小說創作,陳思廣認為這一時期的現代長篇小說以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界,在創作分期內部形成了低回與復興兩種不同的發展情況。由于“歷史的現實性與現實的復雜性”[7],此時期的長篇小說創作有傳遞強烈抗日意志的長篇小說《邊陲線上》,也有揭露社會黑暗的《腐蝕》,批判人性弱點的《駱駝祥子》與《呼蘭河傳》,同時還有以“現代主義思想探詢及其意義”[8]的《圍城》等;東北與華北兩個淪陷區的創作更有存在美化日本侵略者嫌疑的長篇小說作品,體現了時代與人性的局限;而陜甘寧邊區的創作則以“文字為政治服務”為創作方針,誕生了一批民族化、大眾化且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作品,如《種谷記》和《高干大》等延安文藝思想轉變后的轉型之作。
可以說,《編年史》不僅對三個不同階段的現代長篇小說提供了翔實可靠的史料,還以時間與事件搭建坐標系,系統精準地呈現出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整體發展態勢。
二
《編年史》的編年體例的寫作優長,還在于最大限度輯錄了現代文學30年間的白話新體長篇小說,力求讓史料本身說話,以客觀的史料挖掘方式將被隱沒的歷史細節得以重現。錢理群認為研究者不僅要對“‘一個年代’的歷史事件、人物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了然于胸,善于作時、空上的思維擴展”,更要具有“思想的敏感與穿透力”,才能夠判斷出“‘細節’背后的‘史’的意義與價值,也即‘細節’的‘典型性’”。[9]《編年史》正是如此,在對中國現代長篇小說作整體研究的同時,也不忘掃描歷史細節,顯示出編者踏實且富有價值的史料研究工作。
陳思廣認為,編年體長篇小說發展史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創作生態史料、創作發生學史料、創作傳播接受史料、長篇小說的思想藝術評價以及裝幀藝術。[10]在這五方面梳理中,他挖掘出許多以往文學史忽略的史料細節,如輯錄老舍的《駱駝祥子》時,《編年史》凸顯了老舍于1935年11月10日發表在《文學時代》創刊號上的《一個近代最偉大的境界與人格的創造者》一文。老舍在文中詳細闡述了康拉德對他的影響,并寫道:“Nothing,常常成為康拉得的故事的結局……他的人物不盡是被環境鎖住而不得不墮落的,他們有的很純潔很高尚;可是即使這樣,他們的勝利還是海闊天空的勝利,nothing。”[11]這一史料的補充,對我們理解《駱駝祥子》中祥子的故事與結局有著重要的啟示。此外,《編年史》中關于《駱駝祥子》出版與接受傳播的相關史料條目就接近70條,許多過去被遺漏的歷史評價也因此而重現于讀者眼前,如梁實秋曾于1942年在《中央周刊》第4卷第32期發表《讀〈駱駝祥子〉》,以“人性論”的角度對祥子的性格悲劇作出了深刻獨到的評價,并從祥子的悲劇聯系到這類人物為代表的底層階級的人的悲劇,這一重要評價至今“仍失收于關于老舍研究的資料中”[12]。可見,即使是對作家的專題研究,仍可能存在遮蔽歷史細節的缺陷。
除了對重要作家作品史料進行補充,《編年史》還特別關注到了東北與華北兩個淪陷區現代長篇小說的發展細節。1932年,偽滿洲國被日本侵略者扶持成立后,大批愛國作家南下,東北淪陷區的長篇小說創作陷入死寂。為了改變這一局面,1939年后《大同報》及《新滿洲》等特設獎項征集長篇小說,如《大同報》以“建設滿洲文學”為由試圖培養一批“發榮”“滋長”的長篇小說作家作品[13],選出的作品如金音《生之溫室》和古梯《掙扎》,或直抒或隱寫對“侵華日軍”與“偽滿政權”的服膺,表現出濃烈的奴化思想。由于時代局限,華北淪陷區的長篇小說發展也呈現出停滯局面。據編者統計,1937—1939年間,華北文壇不僅沒有出版一部完整的長篇小說,連報刊上少量連載的小說也多為“未完成之作”。當時《中國文藝》編者更是感到華北文壇作家們都“失去了創作欲”,讀者也被“失望與悲觀”的情緒籠罩,[14]可見這一時期的低回之態。
細節往往從小處著眼,看見大歷史的發展。編年體文學史對細節的挖掘與考察,不僅是對文學整體發展的補充,也是對“太整齊的系統”的突破[15]。《編年史》除了對“遺漏”史料的補充,更有對現代長篇小說裝幀設計與廣告的突破,這些歷史細節不為人所熟知,但對于長篇小說整體而言卻不失價值。在裝幀設計上,陳思廣總結出現代長篇小說的封面多以漢字或色塊為主,具有“民族風”特點,如老舍的《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茅盾的《霜葉紅似二月花》、柳青的《種谷記》、張資平的《沖擊期化石》等,都以漢字為主要元素,字體多變、簡約樸素,顯示出濃厚的民族文化特點。更重要的是,《編年史》收入了這些長篇小說初版書影與版權頁,部分書影甚至首次出現,且都以彩印形式呈現,使讀者能夠更直觀感受到每部書的裝幀藝術與版本信息。可以說,《編年史》對現代長篇小說初版書影與裝幀藝術的強調,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歷史現場感,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開拓了新的研究視野。
在文學廣告史料上,陳思廣也盡可能搜集了當時出版社或文學界對每部長篇小說的廣告與評價。這些廣告評價涉及了長篇小說生產、傳播、接受過程,更牽扯到資本與商業的消費層面。比如在“1931年”條目下,可看到4月14日《時報》刊載了一則巴金新著長篇小說《激流》的預告,“為應讀者需要,特請‘巴金’先生撰述一部長篇小說,不日可在本報上發表”,其中“巴金先生新著”與“長篇小說”都以大字、黑體刊出,[16]可見當時文壇與讀者對巴金及其作品的期待。在編者“按語”中,亦可了解到當時《時報》與巴金連載《激流》的矛盾之處。由于《時報》的受眾多為市民階層,《激流》因長篇小說文體限制難以滿足市民對內容輕松活潑、語言通俗易懂的期待,險遭腰斬。僅一則廣告,就可以呈現生產傳播、消費群體與資本運作間的關系,可以超越傳統文學文本解讀,為文學研究打開全新視角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據。
總之,《編年史》對歷史細節的把握,不僅拓進現代長篇小說的史料工作,也從細枝末節處補齊長篇小說之系統生態景觀,還原出一個現代中國長篇小說歷史現場的“更完整的整體”[17]。
三
史料工作是無盡的,這就要求編者具有獨到的文學史觀和寫作追求,在史料的取舍之間做到既能平衡整體與細節之關系,又能體現文學自身的內在邏輯。
《編年史》首先從輯錄對象選擇上體現了其系統、清晰的編史意識。在凡例中,《編年史》聲明所收錄的現代長篇小說是“1922年2月15日—1949年9月30日期間正式公開出版的中國現代新體長篇小說,不包括長篇章回小說及雖在報刊上連載卻未正式出版單行本的長篇小說”[18]。不僅如此,編者還針對現代長篇小說的“入選標準”作了界定,所選入的小說都“以不同時期的征文字數要求為標準”[19],且都以初版作品的字數為準(1922—1929年為6萬字以上;1930—1935年為8萬字以上;1936-1949年為10萬字以上),不同時期的字數標準界定所依據的也是創造社、《良友》、“文協”等主流報刊與組織的征文要求,具有一定的客觀性,這也顯示出編者“用事實說話”的編史意識。為了防止編年史體例可能帶來“歷史碎片化”傾向,著者還特意在全書結構設計上專設“導論”與“作品索引”。前者大致梳理了自晚清以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發展至1949年的整體概貌;后者則以書中提到的356部長篇小說為索引,并按小說標題首字母有序排列,將每條與之相關的史料所在的目錄頁逐一標注,這一編史方式有效減輕了讀者翻閱每部小說史料的難度。
史論結合的敘述方式,也體現了《編年史》開闊的編史意識。全書通過“按語”的方式間接評論、解釋或補充重要史料,使讀者能更深入地理解每部現代長篇小說的創作內容與價值。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按語”也是編者對自己文學史觀的實踐與呈現。《老張的哲學》中的老張,《編年史》評價是“一群受現代化文化沖擊,卻被傳統文化戕害,尚未真正覺醒的迷茫者”[20],并且聯系《趙子曰》對國民劣根性之批判,總結出老舍“從傳統與現代的比照中體察國民的缺失”的創作思想。這些評價精準到位,體現了編者對所輯錄對象的深刻理解與思考。透過《編年史》中的“按語”,可以看到編者評價與分析都盡量貼合了當時長篇小說發展的歷史語境,顯示出新穎獨到的文學史觀。
總之,陳思廣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編年史(1922—1949)》是一部關于現代長篇小說整體發展的扎實而深刻的文學史著作。編者立足于客觀歷史事實,在“整體”之外力求對“細節”的挖掘,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通過其系統、開闊的編史意識還原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30年的發展歷程。編者還以其獨到的眼光收錄現代長篇小說相關的廣告、初版書影等,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研究提供了極富價值的史料。《編年史》所涉及史料之豐富,敘事之嚴謹,立意之創新,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研究意義。
注釋:
[1] 陳思廣:《前言》//《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編年史(1922—1949)》(上),武漢出版社,2021年版,第2頁。
[2] 段美喬:《“編年”:不僅僅是體例》,《文學評論》,2014年,第3期。
[3] 陳思廣:《導論》//《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編年史(1922—1949)》(上),武漢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頁。
[4] [荷蘭] 里斯·洛萬:《紀念碑——作為歷史研究的史料》,孫虹、孫立新譯,《史學理論研究》,1997年,第3期。
[5] 陳思廣:《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編年史(1922—1949)》(上),武漢出版社,2021年版,第300頁。
[6] 陳思廣:《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編年史(1922—1949)》(中),武漢出版社,2021年版,第343頁。
[7] 同 [3],第29頁。
[8] 同 [3],第38頁。
[9]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頁。
[10] 同 [1],第3頁。
[11] 同 [1],第8頁。
[12] 同 [1],第9頁。
[13] 同 [6],第630頁。
[14] 同 [3],第52頁。
[15] [17] 劉勇:《關于文學編年史現象的思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7期。
[16] 同 [5],第258—259頁。
[18] 陳思廣:《凡例》//《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編年史(1922—1949)》(上),武漢出版社,2021年版,第1頁。
[19] 同 [18],第2頁。
[20] 同 [5],第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