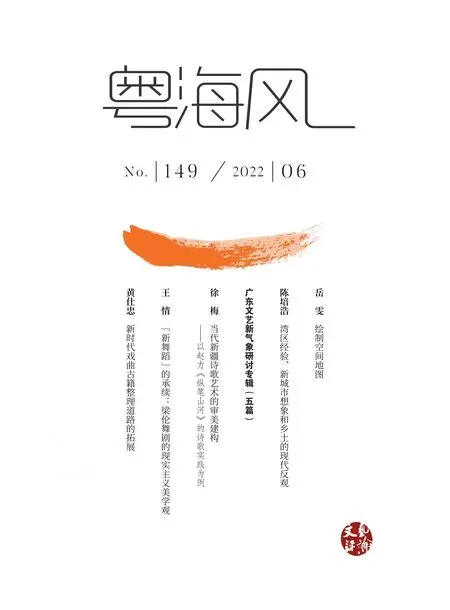網絡文藝中的廣東力量:從產業優勢到文化優勢
文/鄭煥釗
一、廣東網絡文藝:地位與瓶頸
第一,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以其“開風氣之先”的開拓精神,成為全國網絡文藝最早的發源地和網絡文學作家的重要孵化地。2001年11月,廣東陽江的林庭鋒和臺灣籍人士羅森等一眾玄幻文學愛好者,在“西陸”網絡論壇一同發起“中國玄幻文學協會”(CMFU),中國大陸原創網絡文學的“拓荒”由此開始。2002年6月起點文化傳播公司在陽江成立,影響中國網絡文學進程的“起點中文網”正式運營,并探索中國網絡文學的閱讀消費制度(付費閱讀、會員制度)和文化出海(“起點國際”)。在它的影響下,廣東成了網絡文學的熱土。著名網絡作家如當年明月、南派三叔、天下霸唱、慕容雪村、李可等,都從廣東起步。后續網絡文學新生力量也不斷出現,多年來,廣東網絡作家數量和企業數量基本位居全國第一,涌現出叢林狼、厭筆蕭生、天堂羽、南陳朝、夜獨醉、阿菩等網文大神。近年來,廣州、深圳、東莞、茂名四地作家大量涌現,形成了廣東網絡文學的“四小虎”現象。除此之外,廣東還是在全國最早探索網絡文學主流化建設與發展的省份,全國最早成立了省級網絡文學作家協會,創辦了全國第一份網絡文學專業期刊(《網絡文學評論》),后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的需要更名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最早將網絡文學納入省級“魯迅文藝獎”的評獎范圍等,顯示出推動網絡文藝發展的制度創新優勢。
第二,依托于文化產業發展的堅實基礎,廣東數字文化產業的發展走在全國前列,以網絡游戲、數字動漫、電競產業、數字音樂為主體的網絡文藝,迸發出強大的產業優勢,成為全國網絡文藝生產的中心。網絡文藝是數字文化產業的重要構成部分,是文藝與技術、媒介、商業高度融合的產物,強大的文化產業基礎和完整的文化科技融合產業鏈,是促進網絡文藝發展的必要條件。在這方面,廣東擁有堅實的文化產業發展優勢。作為全國文化產業的第一梯隊,廣東的文化產業增加值連續18年領先全國。近年來廣東立足前瞻視野,布局文化科技新興業態,聚焦做強文化科技集群優勢。憑借著龐大的產業規模、強大的集群效益和文化科技的融合優勢,廣東已成為全國最重要的數字文化生產強省,尤其在網絡游戲、電競產業、數字動漫、數字音樂等方面,廣東不僅有騰訊、網易、三七互娛、奧飛等頭部游戲動漫企業,歡聚集團(YY)、虎牙、網易CC直播等一批電競直播龍頭企業,酷狗音樂、荔枝FM等數字音樂龍頭企業,更擁有完整的研發、運營、直播等產業鏈條優勢。無論是從業規模還是產值規模,都在全國乃至全球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目前,廣東集中了全國37.7%的游戲產業人員,31.6%的全國電競從業人數,以及全國規模最大的原創音樂人。經濟規模上,2020年廣東電競產業收入達1197.6億元,占全國總產值的75.56%;2021年廣東網絡游戲以2300多億的產值占據全國總產值近8成;[1]而在數字音樂方面,單數廣州一市,其產值就占全國的1/4。除此之外,廣東游戲企業對國內游戲企業的投資占比為41.8%,借助資本的介入對全國游戲產業產生重要影響。毫無疑問,廣東已經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網絡文藝生產的產業中心,網絡文藝也已經成為廣東影響全國乃至全球的力量新秀。
第三,在文化輸出的層面上,憑借著外向型的經濟優勢,廣東成為中國網絡文藝海外輸出的重要基地。數字貿易是廣東外貿的重要構成部分,2016—2021年,廣東省數字貿易進出口額年均增長率為14.2%,從貿易逆差394.9億美元轉為貿易順差2.7億美元。2021年,廣東省數字貿易進出口規模已超800億美元,位居全國第二。其中,數字貿易出口規模實現407.5億美元,同比增長27.7%,占全省服務貿易出口規模的比重為51.5%,與世界平均水平(52%)基本持平。[2]依托國家數字服務出口基地、國家文化出口基地(首批為天河區,第二批為番禺區),廣東加快推進互聯網、虛擬現實與數字媒體的融合發展,加大高質量數字內容產品供給,推動動漫游戲、網絡文學、電子競技、數字音樂等數字內容的創作生產,通過打造境外出海平臺和生態系統實施文化產品的本土化,推動網絡文藝的“出海”。據相關數據顯示,廣東網絡游戲產業規模占全球的18.5%,[3]2021年廣東省網絡游戲出口規模達到389.2億元,同比增長22.6%,占全國游戲出海總規模的33.9%左右。[4]其中,像三七互娛這樣的游戲公司,早在10年前就開始布局海外市場,目前已在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行超過120款移動游戲,包括《斗羅大陸:魂師對決》《叫我大掌柜》等精品游戲在海外市場引發火爆的同時,也成為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力量。[5]
但毋庸諱言,廣東網絡文藝的力量與優勢更多呈現為產業優勢和經濟優勢,在文化的影響力方面,目前仍存在著如下問題:首先,相比于浙江、上海等地在網絡文學、網絡動漫、網絡影視等方面精品迭出,產生全國性的文藝影響力而言,廣東網絡文藝仍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局面,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網絡文藝作品和作家、藝術家仍數量較少,高端網絡文藝創作生產人才仍非常欠缺;其次,從網絡文藝所發揮的對經濟社會的文化引領方面,廣東網絡文藝與傳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跨界融合還遠遠不足,網絡文藝在賦能廣東文化的整體發展上仍有較大空間;再次,在高端文藝文化人才層面上,廣東是網絡文藝人才的孵化器,但還不是“宜居地”,特別是網絡文學作家外流江浙滬現象較為嚴重,客觀上體現了廣東網絡文藝發展制度環境和人文環境建設仍存在薄弱之處;最后是文化力量的介入和引領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相比于其他省份,廣東無論是網絡文藝的學術組織、研究機構還是智庫平臺建設仍較為欠缺,針對廣東網絡文藝的批評實踐和理論研究沒有得到重視。
從總體上言,廣東網絡文藝的發展,是以市場力量和產業發展的驅動為主導,較好地借助市場機制推動產業的壯大,但是文化介入的力量存在明顯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廣東網絡文藝的精品生產、文化影響和人才吸引。可以說,文化影響力與產業影響力存在著明顯的不匹配,其強大的產業優勢仍未能真正轉變成為廣東獨特的文化優勢。
二、當下網絡文藝文化形態與文化生態
如何將廣東網絡文藝的產業優勢轉變為文化優勢?這需要立足當下網絡文藝的文化形態與文化生態,不再只是將網絡文藝視為一種與主流文化不同的亞文化形態,而是從其主流化發展的邏輯中,來尋找網絡文藝廣東力量的文化蓄能的視野與方法。
其一,不同于單純的民間性與商業性,網絡文藝是網民自發與產業介入的協同發展所催生的新型的融合文化形態,而在技術、媒介與產業的共同作用下,其生產、傳播和消費的相互滲透與高度一體,形成網絡文藝互動共生的文化生態。如何定性網絡文藝,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實際上,早期網絡文藝的發展具有極強的草根性特征,但隨著商業模式的建構與產業資本的介入,網絡文藝主體上已成為商業通俗文藝的重要構成部分。然而,由于網絡文藝不同于傳統商業類型文藝的媒介互動性與社交性特征,凸顯了受眾、用戶等接受者在網絡文藝的創作生產、傳播消費過程中的突出作用,這就使其顯示出既不單純等同于民間文藝的民間性,也不單純等同于文化工業的商業性的混雜特征,可以說規模龐大的網民的自發創作催生文藝的新類型與表述的新方式,而產業和資本的介入推動該網絡文藝類型的規模化快速發展,網絡文藝成為用戶參與所展現的民間性與商業通俗文藝的商業性融合的形態。互聯網媒介的即時互動功能、社交媒介對互動展示的技術激勵、流量經濟對用戶深度互動的商業建構等,驅動著網絡文藝生產、傳播與消費關系的不斷重構。如果說傳統文藝報刊、影視的時空與物質制約,使其生產者、傳播者和消費者分別處于不同的環節階段與物質時空。彼此相對區隔和獨立的話,那么,網絡文藝的上述技術、媒介和商業機制,極大地激發了三者之間的相互滲透和融合,尤其在社交媒介中形成“生產—傳播—接受”的高度一體化,形成網絡文藝對用戶日常生活的全面滲透。這種融合特征,正是文藝時代特征的重要表征:網民的自發性不僅構成了網絡文藝新類型、新特征不斷涌現的內在發展動力,這種自發的互動更成為塑造網絡文藝與大眾日常生活深度滲透關系的基礎,而正是網民自發性與產業介入兩者的協同發展,使網絡文藝在社會中的位置顯示出其復雜性。
其二,文化科技的深度融合、網絡平臺的粉絲集聚和數字文化的跨界發展,共同帶來網絡文藝的“平臺化功能”與“體制性影響”,成為改變當下中國文化與文藝發展的深度文化邏輯。文化科技融合所帶來的文化發展的驅力與文化形態的改變、粉絲集聚與網絡傳播所帶來的文藝供給邏輯的不同,以及跨界發展所帶來的文化與生活的關系的重構,使網絡文藝愈來愈成為一種具有“平臺性”的文化生產體制,深層次地改變著包括網絡文藝和主流文藝的生產與消費邏輯。之所以不用“載體”而用“體制”,就在于“載體”不如“體制”那樣生動地揭示傳統文藝與網絡文藝融合過程中,從內容生產、傳播方式到消費接受的文化邏輯和文化生態的全方位的改變。“后疫情時代”傳統文藝形態或主動或被動與數字文化和直播產業的深度融合,正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網絡文藝對傳統文藝的深刻影響。因此,在我看來,網絡文藝的文化生態已不能用“亞文化生態”來表述,正是在于網絡文藝所發揮的這種“平臺性功能”和“體制性影響”,使其越來越成為主流文化生產和傳播的主要力量。尤其在創意產業發展的時代,經濟的轉型升級、鄉村的脫貧致富、社會價值的塑造,無不借助網絡文藝所發揮的多層次跨界聯動的力量。這就使網絡文藝的界定,已不能作為一種單純的文藝類型、一種與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相區別的商業通俗文化來理解,而應視為新時代主導性的文化生產邏輯來理解。
其三,在網絡文藝用戶規模全覆蓋的背景下,無論從監管、產業到公眾,網絡文藝與主流文化已經形成“雙向奔赴”的融合格局,日益成為當下文化的主導形態。隨著近10年中國移動互聯網的快速普及,中國網民數量已超過9億,網絡也成為當下中國文化最富有活力的生產和消費空間。以網民的自發性生產為起點,企業和資本的介入、推動為驅力,包括網絡文學和網絡影視、電子游戲和網絡電競、數字音樂和短視頻等在內的網絡文藝,已經成為當下參與人數最多、產值規模巨大、影響日益廣泛的文藝形態和文化形式。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包括彈幕在內的發端于網絡文化的各種亞文化形式,已經愈來愈被其他文化所借用而普遍化;另一方面,隨著網絡文化對年輕人的深刻影響,國家層面上,網絡文藝與青少年的成長已經上升為一個涉及塑造未來中國主體的問題。在這一意義上,無論是管理部門,還是行業本身,都試圖擺脫其亞文化的性質,而促進網絡文藝的主流化,并日益成為一種新的主導的文化生產邏輯。
三、從產業優勢到文化優勢
我們需要立足“網絡文藝作為一種主導性的文化生產邏輯”這一新認識,來思考廣東網絡文藝的文化優勢的發揮與文化力量的激發的問題。
首先,加大力度扶持網絡文藝精品創作,使廣東網絡文藝真正成為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文藝精品的創作中心。網絡文藝以其獨特的文化形態和文化生態,成為覆蓋面、影響力和滲透力極強的文藝形式,隨著媒介融合和文化融合的逐漸增強,網絡文藝領域毫無疑問已成為中國文藝的主陣地。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推出更多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優秀作品”,這是指導網絡文藝精品化創作的根本要求,創作更多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文藝精品,必然成為中國網絡文藝的創作方向,從而更好地發揮網絡文藝傳播力強的優勢。作為中國網絡文藝的創作生產的中心,廣東網絡文藝及其更龐大的數字文化產業的發展,只有從根本上滿足這一要求才能獲得更好的發展空間。因此,加大加強更多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廣東網絡文藝精品的創作,就需要充分發揮政策引導、行業指引、學術研究和文藝評論的力量,引導廣東網絡文藝從市場驅動向文化驅動與市場驅動共同作用的方向發展。
其次,要在全局性的文化發展格局和文化生產邏輯中,推動網絡文藝與各種文藝形態和文化形式的深度融合,既守正、開新,又協力發展。在日益“平臺化”和“體制化”的網絡文藝發展趨勢下,網絡文藝的生產傳播和消費高度一體、彼此滲透的邏輯已經深度嵌入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深層肌理之中。廣東網絡文藝要深入認識網絡文藝的主流化趨向,及其作為一種主導性的文化生產邏輯的內涵,撬動網絡文藝對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系統性影響的力量,促進廣東網絡文藝作為以嶺南文化為中心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平臺,發揮網絡文藝對各種類型的傳統文化的技術賦能與形態創新的重要作用。實際上,這方面目前已有不少探索與實踐,如廣東網絡游戲《我是畫卷修復師》中,將廣彩、廣繡、廣州欖雕等16個極具廣州特色的非遺項目,以畫卷拼圖的方式進行展現,寓教于樂。《我是大掌柜》以《清明上河圖》為藍本進行設計,融合宋朝的市井、雅集、山水、茶事、龍舟、皮影戲等元素,一經上線就憑借精美畫風“出圈”,實現游戲收入7億元,推動中國文化的傳播。《率土之濱》打破日本對三國類游戲的壟斷,激發日本玩家用文言文郵件的形式寫“檄文”,在社交媒體上舉行了日本版的《中國詩詞大會》等。又比如,廣東舞劇《醒·獅》在四川大劇院的線下演出因為疫情影響改為線上直播,在短短48小時,就在社交網站獲得1000萬人次關注,吸引300萬人圍觀,觀眾覆蓋三十多個省、市和自治區。這種傳播效應正是網絡所帶來的。
再次,如何改變廣東文化長期存在的“過堂風”現象,使網絡文藝真正在廣東能夠“沉得下去”和“立得起來”,成為廣東文化發展的新標志和新高度。20世紀八九十年代,廣東依靠改革開放的政策優勢和開放風氣,憑借港臺文化傳入內地的窗口,成為國內流行文化的發祥地,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發展,早期聚集于廣東的文化人紛紛北上,文化人才的外流曾導致廣東文化影響力的下降。網絡文學的發展,似乎也重復了網絡作家在廣東成長,成名后外流的問題。因此如何建設真正吸引網絡文藝人才的制度環境與人文環境,成為制約廣東網絡文藝發展的關鍵問題。理查德·弗羅里達在《創意階層的崛起》中曾指出,對創意人才而言,除了工資收入、技術發展等條件外,創意人才還特別注重區域環境,而具有多樣性和包容性的“人文環境”對吸引創意人才集聚具有重要作用。[6]近年來,深圳、廣州、東莞、佛山等城市不斷完善城市人文環境建設,比如深圳不僅對標世界發達的文化城市的硬件設施“查漏補缺”,更利用其強大的經濟實力、文化科技集聚的產業優勢,以及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政策優勢,創造適合文化人才聚集的各類條件。然而,像浙江那樣為網絡文藝的發展,專門出臺一系列包括人才引進、稅收優惠、空間聚集和精品扶持的政策,在廣東仍然沒有出現。立足網絡文藝作為未來主導性文化形態的前瞻認識,如何借力網絡文藝的產業優勢來創造和發揮文化優勢,人才制度環境與人文環境的建設亟待進一步破題。
最后,面對網絡文藝作為一股嶄新的廣東力量的崛起,以及網絡文藝的平臺性功能和體制性影響,我們必須發揮文化力量的介入作用,以引導網絡文藝的發展。網絡文藝從根本上表征著數字文化時代文化的新形態、新規律與新經驗,不僅從根本上代表了一種技術與媒介時代的集體性的想象和體驗方式,更是深層次理解“Z世代”群體深層次的心理情感結構的重要載體,而且以其與產業資本、商業形態和技術形式的深度關聯,成為整體性、系統性地理解我們這個時代社會文化的樣貌和結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加強網絡文藝的批評理論研究,既是因應國家文化治理的戰略需求,未雨綢繆地發展和解決文化安全問題的需要,也是引領數字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的風向標,能夠幫助文化企業和創作者總結創作生產規律,及時發現文藝作品和文化產品中存在的問題。一種產業的發達和文化類型的發展,總是需要建立其相關的學術場域和文化場域。在這方面,我們期待廣東能夠更加重視專門性的網絡文藝研究機構、學術平臺和智庫的建設,從而發揮學術文化場域對本地網絡文藝發展的作用。
注釋:
[1] 據廣東省游戲產業協會發布的《2021廣東游戲產業報告》顯示,2021年廣東游戲收入為2322.7億元,占全國營收的78.7%,占全球網絡游戲營收規模的25.9%。
[2]《數字貿易、文化貿易齊頭并進 主賓省廣東亮出雙名片》,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9759591 [引用日期:2022-10-18]。
[3] 洪曉文:《廣州抓好數字文化“風口”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21世紀經濟報道》,2022年3月19日。
[4] 數據來自前瞻產業研究院《中國網絡游戲行業商業模式創新與投資機會分析報告》,https://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300/220705-36b64951.html [引用日期2022-10-17]。
[5]《三七互娛積極探索前沿科技與文化融合》,《廣州日報》,2022年10月10日,第9版。
[6] [美] 理查德·佛羅里達:《創意階層的崛起:關于一個新階層和城市的未來》,司徒愛勤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本,第286-3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