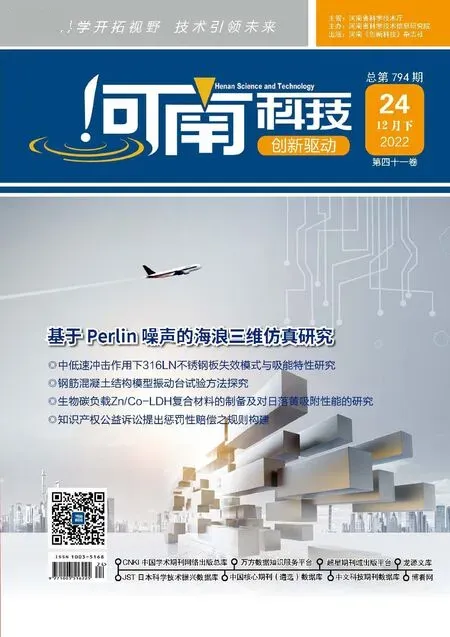網絡文學作品融梗行為侵權研究
蔣思齊
(中原工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0 引言
“互文性”是文學作品的一個特性,是指文學中包含了時代大環境中的文化體系,導致一個新的文學作品與之前作品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因文學作品這一特性的存在,導致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任何作品在嚴格意義上都無法被認定為初次創作。正因如此,這讓許多融梗作者有機可乘,他們打著“互文”的旗號對別的作品進行融梗行為,混淆原作者和讀者的視線。
但是,在文學上“梗”的范圍是有界定的,經過大眾認可后可以進行無限傳播的大框架,是可以被互文的“梗”,但原創作者的創意想法,并不在互文的范圍之內。因此,融梗在著作權法侵權認定的爭議之處就是要界定融梗作者究竟是進行了互文還是對文學作品的融梗,如果是被廣泛運用的“梗”就可以稱作互文,不構成侵權認定,但如果是帶有作者個人思想的并在網絡文學作品中對推動故事發展起到一定作用的“梗”則不在互文范圍內,因此運用原作者的“梗”進行再創作的行為會引發了侵權嫌疑。
因此,不同類型的融梗在著作權法的觀點中需要進行單獨討論,對融梗行為是否構成侵權需要論情況而定。著作權法鼓勵作者進行文學創新,加快推動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因此在著作權法認定融梗侵權的案例中,需要重點關注的內容是網絡作品的作者是否對另一作品的實質進行了融梗,如果只是單獨地對另一作品的思想元素進行融梗,在著作權法規定中是不構成侵權行為的,屬于合理使用的范疇,但是如果該作品對另一作品的核心要素(關乎劇情走向、人物命運發展等)進行融梗,導致兩個作品的實質性相似,那在著作權法中可以被認定為侵權行為。
1 融梗行為的含義及特點
1.1 融梗的含義
由于“融梗”一詞最開始是由網絡流行用語演變而來,其出現的時間節點和提出人難以溯源,所以融梗一詞并沒有被收錄進中華詞典中。“梗”即“哏”,是指作品中經典的文學橋段或者獨有的創意等,帶有原著文學色彩,融梗是網絡文學作者將別人作品里值得學習的閃光點通過自己加工、改造融合進自己作品的行為。
從字面上理解,把融梗拆分來看,“融”即融合、匯聚,是指作者在作品中把他人作品的想法、創意融入自己作品里,這種融合可能是單獨的一個作品,也可能是很多個作品的創意碎片揉捏而成的,融合的方式也大相徑庭,有的只是簡單的復制粘貼,有的是經過深入加工后改頭換面的成果,但是追其根源,無論怎樣變換都與原著有直接或者間接的相似性。“梗”就是被融入的“梗”,這個梗可以是故事的發展情節、人物臺詞、被引用的名言詩句等,又或者是原作中刻畫的人物形象、故事背景和人物之間的關系等。“梗”的內容可大可小、可多可少,這也就決定了融梗作者文章與原作者文章的相似度。
1.2 融梗的特點
網絡作品的融梗行為具體有五種表現形式:一是對作品類型的融梗;二是對人物設定的融梗;三是對故事背景的融梗;四是對故事情節的融梗;五是對具體表述的融梗,下面筆者將具體分析不同類型的融梗行為在著作權法中的侵權認定。
1.2.1 對作品類型的融梗。網絡文學作品的類型相對來說比較固定,例如重生類、穿越類、都市類、商戰類等,作品題材有限,這些梗屬于公共領域的范疇,不在著作權法的保護范圍內。因此,如果文中的“梗”僅是同一題材,并不影響故事的發展脈絡,是不構成侵權行為的。
1.2.2 對人物設定的融梗。對人物關系的融梗同理與上述對作品類型的融梗,也屬于公共領域之內,不在著作權法的保護范圍內。近期網絡文學中比較熱門的梗有“嫡子梗”“廢后梗”“霸道總裁梗”等,這些都是基于作品最基礎邊緣的內容,與作者本意想表達的中心思想相距甚遠,因此,作者所選的“梗”是人物關系同樣不構成侵權。但是如果是作者刻畫的有具體性格的人物,其獨創性細節可以構成表達。
1.2.3 對故事背景的融梗。故事背景是一部文學作品刻畫故事的幕布,是作品中人物發展的基礎,網絡作品的背景梗也有很多,例如“民國風”“辦公室劇情”“商場劇情”等,這些都屬于公共領域,作者為了表現某一主題時,運用了相似場景描述或者在某一歷史事件下進行敘事,這種必要的融梗行為,就類似于植物的葉子一樣,不傷及主干,屬于相對抽象的表達,作者引用此“梗”不屬于侵權行為,不在著作權的保護范圍內。
1.2.4 對故事情節的融梗。一部文學作品的故事情節分為主線情節、支線情節、插入情節等。文學作品的情節有較多相似之處,部分情節也已經進入公共領域,因此要具體分析融梗的具體內容。主線情節是作品的脈絡,其余情節圍繞其展開,主線情節在一部文學作品中屬于作者的核心思想,很大程度上有原創性,因此如果融梗行為融入的是具有作者原創性的“梗”時,是對原作者思想創意的剽竊,屬于著作權法的保護范圍,構成侵權行為。支線情節是主線情節的分支,是在主線情節基礎上的思想發散,在認定融梗侵權時,應該判斷是否是公認橋段,如果不是,一般情況下也在著作權法的保護范圍內,這里需注意一點:具體情節已經具體到明確的時間、地點、因果關系、人物、背景設置,而人物對話、心理描寫更是體現作者獨創性的重要方面[1]。在著作權案件中首次引入“具體情節”這一名詞作為侵權認定時,是在“瓊瑤訴于正案”中,瓊瑤舉例了《宮鎖連城》中的21個橋段進行引證,較為經典的相似之處是兩部作品都是清朝背景下正室膝下無子,侍妾得寵威脅到正室,然而正室又再次產女,為了保住地位只能替換成男嬰,并且“遺棄溪邊”且“肩膀有胎記”等都非常相似。這個案件是著作權法中關于融梗侵權的一個經典案例,目前已經被寫成《瓊瑤訴于正案始末》一書出版。因此,在判斷情節的著作權侵權時,側重于對情節排布、因果邏輯和細節設計等形成的具有獨創性表達的具體鏈條進行整體分析。如果只是單獨使用其中的一個環節則不構成侵權。
1.2.5 對具體表述的融梗。一部網絡文學作品是作者耗費心力刻畫出來的各種場景、表達的綜合體,在文學作品中最重要的就是表達和敘事方式,是帶有作者個人色彩的語言展示,每個作者慣用的敘事方式、修辭手法也不同。這里的具體表述就是指作者使用的修辭手法、形容詞,或者引用的具體典故所形成的帶有個人色彩的具體表述,這屬于獨特的語言表達,在著作權法的保護范圍內,如果作者選用這些進行融梗,不管是直接借用還是經過再加工的“洗稿”行為,都是可以被認定為侵權的。電視劇《山河令》就被質疑在言語表述上侵權《殺破狼》,《山河令》在劇中引用了《殺破狼》中的經典語句“未知苦處,不信神佛”,劇中蝎王與趙敬在原著也不是義父子關系,這種關系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殺破狼》。
2 關于網絡文學作品融梗侵權認定的難點
2.1 難以識別的隱晦性
提到融梗,多多少少有些貶義的意味,給人的第一感覺就是不那么光明正大。融梗作者雖然在原作者創意的基礎上進行了創新,但是與原作的關系卻難以割舍,只是經過修飾手法后變得隱晦了,因此融梗具有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隱晦性。融梗的作品給人一種似曾相識、捕風捉影的感覺,讓讀者感覺好像見過但又帶著陌生,這與抄襲的寫手是有非常明顯的差距的,是一種有技術含量的寫作手法,抄襲作者是完全剽竊原作的想法創意,在著作權法中可以被認定為侵權,但融梗在著作權法中侵權的認定則比較困難。
2.2 公共領域的區分
在網絡文學作品侵權認定的過程中,多采用“思想與表達二分法”原則來判斷公共領域的范圍。“思想與表達二分法”是著作權法的一個重要原則。其認為一個文學作品分為思想和表現兩方面,而在著作權法范圍內保護的是思想和概念的原始表達,而不是思想和概念本身。公共領域對于知識產權案件的判決起著基礎作用[2]。在著作權法中,我國尚未明確規定公共領域的范圍,公共領域范圍界定的不清晰極易造成借鑒和抄襲的邊界模糊不清。這就要根據具體案件來分析被融入的“梗”是否屬于原作者的原始表達,在網絡作品盛行的年代,網絡作者對許多“梗”已經爛熟于心了,例如“重生梗”“失憶梗”“絕癥梗”等,這些已經被廣大讀者接受并廣為傳播的老梗很明顯不在著作權法的保護范圍內。
我國的司法程序中公共領域已經有了現實的實踐。著作權法中公共領域的理論與原則構建,可以為建立科學、合理的著作權保護理論體系提供強大的理論支持,并用以指導著作權立法完善與著作權司法實踐[3]。在著名的《宮鎖連城》與《梅花烙》案件中,瓊瑤就以抄襲為由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認定于正侵權并賠償,這其中就涉及了公共領域的范圍,雖然在此案件中,《宮鎖連城》與《梅花烙》中相似的劇情很少,并且于正認為并不存在抄襲,兩部作品中類似的劇情屬于公共素材范圍,不受著作權保護,但是這一主張卻被法院駁回,法官認為,雖然相似點較少,但《宮鎖連城》有融梗行為存在,在原有作品基礎上進行發揮擴散,但其實質思想內容與《梅花烙》有創作來源的關系。法院最終根據于正作品的性質、影響力、侵權使用等判令于正及四家公司連帶賠償瓊瑤500萬元。
2.3 合理使用的界定
在著作權法中,有一項很著名的規定叫作合理使用。三步檢驗法就是著作權法中用來判斷合理使用的標準,“三步檢驗法”最早出現在1967年的斯德哥爾摩會議上《伯爾尼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公約》第9條第(2)款中[4]。第一步:抽象化,具體地區別想法和表現,排除想法;第二步:過濾掉不屬于公共領域的表達;第三步:表示比較,判斷被懷疑剽竊的文學作品是否與以前的作品相似。三步檢驗法的核心是確定融梗作品的合并是否會對原作品產生侵權和侵權的影響程度。
但是結合實際情況,在運用三步檢驗法界定合理使用時,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官的主觀意識,這就類似于規定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在評判網絡作品融梗作品是否侵權時,非常考驗法官對原作品和融梗作品的了解程度,以及法官個人對著作權法中合理使用的理解。融梗行為是否構成侵權不能單純考慮與原作的相似性,而是要更加深度的剖析融梗作品是否在初始創意上抄襲了原作。我國的國產動畫片顛覆之作《哪吒之魔童降世》在上映后被中影華騰指控在人物角色、故事情節等方面大量抄襲其作品《五維記憶》,而《五維記憶》只是一部舞臺劇,兩者連表演方式都差異巨大,但卻陷入抄襲糾紛,由此可見在判定侵權案件中不僅需要原告被告當事人對作品了解入微,某些特殊情況下甚至需要法官有一定的文學素,否則審判結果也屬于法官個人的主觀臆斷,難以作出對原被告都公平的裁決。
2.4 侵權行為的認定
在認定網絡文學作品是否侵權的案件中,可以參照美國版權法上的“四要素標準”從根本上分析融梗作品與原作品是否有實質性相似的內容以及“梗”在原作品中的占比,而不是僅從經濟學角度判斷。雖然網絡作品的類型非常多樣,同類題材被替換的可能性也很高,導致融梗作品的利用率有可能不會對原始作品產生影響,但是如果融梗的來源涉及了原作品的核心思想,仍然是對作者智力成果的侵犯,是構成侵權行為認定的。同時,不能以是否獲利來界定網絡融梗作者是否構成對原作的侵權,從經濟學出發,不能以一部作品相比其他作品具有更高的價值,就更值得著作權的保護來界定侵權,從潛在市場或原創作品的價值的角度來看,很難從某些簡單的人物關系設置、劇情節點就判斷其對原作品的影響有多大。這是因為基于網絡寫作的大環境,難以明確的界定是否原作品一定比融梗作品更具有經濟價值,即使大多數融梗作者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創新,帶給讀者新的觀感且部分作者并沒有因融梗獲利,但是融梗行為依舊侵犯了原作者的創意想法,對原作者構成侵權行為。
總而言之,對融梗作品侵權的認定不管是使用“三步檢驗法”還是“四要素標準”,想要在不侵權的情況下進行融梗就要嚴格的把借鑒的創意造成的影響控制在比較小的范圍里,這樣可能會被認為是合理使用。一般情況下,如果單純對人物形象設定和人物關系進行融梗對原作的影響比較小,這種融梗也是比較常見的行為,但是如果是對具體情節和推動故事發展的劇情走向進行融梗,就容易引發侵權行為,在融梗的同時還要注意原作品的受眾群體、銷售市場等,避免影響原作的盈利,例如《哪吒之魔童降世》作品中的哪吒人物形象,雖然與《五維記憶》的銷售市場完全不同,但《哪吒之魔童降世》作品的成功無疑讓另一部作品的作者認為是自己的創意被剽竊才有了《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成功,進而引發糾紛。
3 融梗侵權行為的認定
融梗行為是否能被認定為侵權一直是司法行業的難題,侵權主體的認定,侵權范圍的認定等,都是值得反復考究的問題。
3.1 被融之梗是否屬于作品的實質部分
要認定網絡文學作品融梗是否構成侵權首先要關注的是被告所選取的“梗”是否屬于一部作品的實質內容,這里的實質內容并不是指所有正文部分,而是作品的核心要素,是能夠決定故事發展的關鍵情節,這些內容可能字數不多,但卻是作者核心思想的體現,因此只要被告選取原作者核心內容進行融梗,就算是經過拆解、美化后使用到自己的作品中,都屬于侵權行為。郭敬明的作品《夢里花落知多少》被莊羽指控與其作品《圈里圈外》作品構思相同、人物設定相同,在莊羽的列舉中,郭敬明全書具體情節中只有57句與其構成相似,但是法院還是認定相似部分是書中的實質性內容,與整個故事的發展走向關聯比較緊密,因此郭敬明的行為構成了對莊羽著作權的侵犯,最終判定郭敬明對莊羽進行賠償。
3.2 被融的“梗”與原作品是否有實質性相似
僅靠表面觀察是不容易看出融梗作者的作品與原作者的相似度的,因為融梗作者通常會對選用的“梗”進行美化、發散、拆解再整合等行為,這是比“洗稿”更加高級的行為,洗稿只是把文章改頭換面,而融梗選取的是作者的創意和具體情節,再把這些內容巧妙的放入自己的文章中,讓人難以察覺,因此只是看文字的相似度是無法準確判斷是否構成了融梗的侵權行為的,而是要對比兩部作品的內在,通過具體分析判斷兩部作品在劇情安排、人物構造上是否有實質上相似,融梗作者如果過度融梗會造成兩部作品有實質上的相似,那融梗作者就構成了對原作者著作權的侵權行為。《錦繡未央》這部作品就被認為融梗過度,《錦繡未央》的前身是網絡文學作品《庶女有毒》,這部作品被11名作家聯合起訴,其中《錦繡未央》中的大部分橋段被認為與其他作者的作品內容有實質上的相似,被認定為侵權,這一著名案例也被列為“2019年度北京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大案例”,讓更多網絡文學作者的內心得到慰藉。
3.3 是否構成轉換性使用
美國最高法院確認的判定轉換性使用的規則,需要考慮兩個方面:一是后期作品是否基于原著添加新的理解、美學或信息;二是原著的使用是否具有全新的功能或是創造價值,還是只停留在原著創造價值的水平。皮埃爾·萊托認為若要構成合理使用,二次作品必須要在原作基礎上增加新的內容,具有其他目的或不同的性質,創作出新的信息、新的美學、新的認識和理解[5]。根據對美國法院相關判決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國最高法院在對著作權侵權案件的認定過程中,一般涉及對兩種行為是否構成轉換性使用的認定,一是復制行為,另一種是演繹行為。如果融梗作品被法院判定為構成轉換性使用,則不構成對原作品的侵權。復制行為是指融梗作者并非簡單的復制行為,而是在融入了原作品梗的基礎上又演繹出了新的內容和思想,和一般“全文復制即構成復制權侵權”的認知不同,這種復制行為是不構成著作權侵權的;演繹行為是指融梗作者雖然使用了原作的內容,但是其寫作目的和方向發生了改變,導致融梗作品的文學價值功能發生了改變,因此是不影響原作的市場的,也不構成著作權侵權的行為。著名的“谷歌案”就是我國司法程序對轉換性使用進行實踐的案例,“數字圖書館”是谷歌公司設定的圖書搜索引擎,王某對谷歌公司的“數字圖書館”項目提起訴訟,認為谷歌公司在數字圖書館中載入其書籍內容侵犯了其著作權,但是法院認定谷歌公司的數字圖書館是把傳統文字轉化成了數字信息,雖然內容沒有變但是其使用方向發生了改變,而且運用谷歌搜索引擎搜索出來的書籍內容并非全部,而是不連續的部分片段,并沒有侵犯作品的實質性內容,所以我國法院認定為谷歌公司屬于“轉換性使用”的范疇,因此不構成對王某作品的著作權侵權行為。
我國司法實踐中,認定剽竊、抄襲的具體標準有四點:一是看作品出版時間的前與后;二是看作品是否有獨創性;三是看剽竊、抄襲的客觀條件是否具備,如有無接觸別人的作品的可能;四是看作品特征對比(如人物、主要情節、主題思想、細節等)是否相同。隨著著作權理論的演變,評估抄襲案的標準也應當逐步從含糊的抽象轉向指摘和實際行動。筆者認為,我國著作權法對“抄襲”的認定應該能更明確、更完美,抄襲的定義要與大數據和智能技術的發展相對應,更加精確的考量融梗作品與原作品文本和邏輯的實質性相似有多少。
4 對網絡作品融梗侵權行為界定的建議
網絡文學作品融梗的現象層出不窮,融梗的花樣繁多,使許多真正有創意的網絡文學作者沒有受到應有的保護。“融梗”一詞不具有法律意義不僅使原創作者維權的道路變得艱辛,而且成為剽竊作者開脫的借口,導致網絡文學作者對維權喪失信心。在這種環境下,更應該凈化網絡文學寫作體系,拒絕惡意的抄襲、剽竊、融梗、洗稿等行為,摒棄用電腦工具一鍵識別出來的作品內容,從真正意義上保護原創作者的思想和文字,從法律角度杜絕融梗侵權行為,才有助于我國文化的發展。
網絡作品融梗侵權案件在進行侵權認定時通常是一項較為細致的工作,需要法官對網絡作品有較為深入的了解,需要有一定的文學素養,因此,筆者認為可以借助外界力量,例如聘請其他作家或者與作品相關聯的人員來幫助評審,確認兩部作品是否有實質性相似的地方,相似度為多少,這樣可以更準確地認定侵權。也可以借助讀者力量,作為參考意見,來進行侵權認定,讀者通常是除了作者之外最了解文學作品的人,雖然不是專業人士,但其敏銳程度還是極其高的,可以作為參考意見參與著作權侵權認定的過程中,如豆瓣上非常著名的關于作家墨香銅臭與霹靂布袋戲融梗案件的剖析的帖子,讀者甚至列出具體章節中的臺詞以及故事中人物出場的時間線,這種細致的分析可能專業人士都難以達到。
隨著網絡文學作品發展越來越迅速,融梗侵權的案例也越來越多,為了避免融梗行為打擊網絡文學作者的積極性,筆者認為還是要從立法者的角度出發,早日把“融梗”納入我國的法律范圍內,確保侵權認定時有法可循,進而極大提高網絡文學作者的寫作積極性,加快推動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