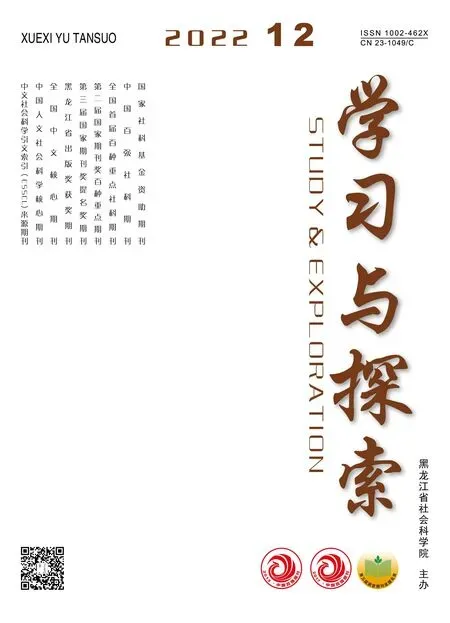俄國象征主義詩學語境下的暗示觀
劉 洋
(1.黑龍江大學 文學院,哈爾濱 150080;2.黑河學院 美術與設計學院,黑龍江 黑河 164300)
一、“暗示”詩學觀念的理論緣起:象征主義的神秘詩學觀
俄國象征主義詩學受到了西歐非理性主義哲學思潮和象征主義文學的深刻影響,在俄國象征主義文學的創作理念中也呈現出了非理性的現代性傾向與話語訴求,認為客觀世界是主觀世界的投射,直覺高于理性。象征作為俄國象征主義詩學的基本觀點,其最重要的美學機制就是暗示性。暗示性為象征主義詩歌開拓了含蓄蘊藉的審美空間,賦予了詩歌具有藝術感染力的神秘內涵。基于暗示思維是蘊含在象征的美學觀念中的,我們有必要對俄國象征主義的神秘主義世界觀進行解析,進而了解“暗示”在象征主義中的詩語功能。
俄國象征主義理論家梅列日科夫斯基于1892年發表的《論當代俄國文學衰微的原因及新的思潮》一文被視為“象征主義的宣言書”,提出了作為俄國白銀時代新藝術的三要素,即神秘的內涵、象征的暗示手法和藝術感染力的擴展。在這之后的俄國現代派文學就朝著梅氏在宣言書中卓有遠見地指出的新藝術方向發展起來,象征主義文學由此發展壯大。俄國象征主義的發展與20世紀初的俄國宗教哲學、美學領域中的變革結合在一起,賦予了象征主義獨特的現代主義詩學特質。法國象征主義詩學的超驗哲學思想在俄國就轉變成了藝術對精神世界的契合,藝術與人主體意識神秘體驗緊密結合的追求彼岸神秘世界的精神美學。吉皮烏斯指出“詩即是祈禱”,認為詩歌是對神靈的禱告;安·別雷認為詩是對“神性”的抒發;梅列日科夫斯基認為詩歌的終極目的是實現人神合一。這些理論觀點在象征主義詩學領域里均表現為詩人不斷尋求極致的精神體驗與創作實踐的追求。象征主義詩人一致認為是象征構成了人的精神領域的世界觀與哲學觀。別爾嘉耶夫曾這樣詮釋象征的意義,即它“是兩個世界之間的聯系,是另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上的標記。象征主義作家相信有另一個世界”[1]。這里的另一個世界指向了象征主義者思想領域的精神世界、彼岸的世界,而現實世界與精神世界的載體就是象征。象征作為溝通現實世界與人主體精神世界的媒介物通過具體可感的意象去暗示個人的體驗和思想感情,同時,象征也經常通過象征符號去構建現實世界與精神世界的二元關系,“象征就是一種符號,一種表征意指關系的動態符號,它把天地、生死、內外、虛實、理想與現實等聯系了起來”[2]。可以說,是象征聯通了觀念與思想意識的領域,更多地表現了對人主體的精神性表達。象征的多義性、朦朧性,力圖表現詩歌意義的無限性,正是通過暗示性的語言去表現。象征依托詩人最初的天性以及個人理想與精神性的詩性抒發,賦予理想的詩具有人無法把握的靈性,具有一種永恒的自然力量。象征主義者認為所謂最高的象征也就是神秘的精神世界的象征,而在俄羅斯民族的精神文化結構中,象征的觀念更多地體現在其具有民族性的二元對立的雙重精神意識中。別爾嘉耶夫在他的文藝理論中強調,俄羅斯的獨特地理位置決定著該民族的精神意識,進而構成了俄羅斯人精神觀念的雙重性及其對民族靈魂的雙重影響。俄羅斯人的精神觀念融入了東正教的靈魂、基督教的禁欲主義和具有自然因素的多神教,精神意識作為認知世界及文學創作活動的認知方式,把現實世界看作理想世界的反映和象征,通過象征、直覺、暗示等去接近永恒的彼岸世界,實現精神世界的充盈與圓滿。這種二元對立的哲學觀對俄國象征主義詩學中的象征觀提供了理論意義上的認知模式。
俄國象征主義詩人創作“象征主義的詩”,將藝術創作體驗融入自身的精神領域,進而尋求對彼岸世界理想化的精神寄托。這樣的詩學觀使象征主義的創作美學導向了體驗美學的方向,將內容與形式相等,在創作中力圖賦予藝術觀念一種可感知的形式,通過觀念的強調和重視,挖掘人的內心進行表達。巴爾蒙特強調,“詩人創作自己象征主義作品時從抽象走向具體,從理想走向形象 ——讀了他的作品的人從畫面本身走向畫的靈魂,從獨立存在時就很美的直接形象走向隱含在形象中、賦予形象以雙倍力量的心靈理想”[3]。在這里,詩人表達了象征主義詩歌的創作主體理念,即藝術的創作來源于藝術家的主體意識,運用象征將抽象的觀念轉化為形象,進而賦予具體的文學作品以作家的心靈體驗。從體驗美學的視角來看,象征是詩人融入了個人觀念及理想世界的神秘體驗,借由藝術形象表現出來,在詩歌創作中更多的借由意象承載象征的暗示意義。伽達默爾認為,象征要求以一種“形而上學的原始類似性”為前提,而這一點是隱喻所不具備的。象征“決不是一種任意地選取或構造的符號,而是以可見事物和不可見事物之間的某種形而上學關系為前提”[4],這種以可見事物暗示不可見事物的過程就構成了象征主義詩學暗示觀的美學邏輯,而“暗示”這一美學功能就通過象征去實現。由于俄國象征主義創作觀拋棄了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摹仿說,對人的認識與客觀事物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在非理性認識論的指導下,認為藝術的真實存在于詩人的直覺感受以及由此建構的神秘精神世界,追求具有強烈主觀色彩的形式主義藝術,運用象征、隱喻營造非理性的藝術真實世界。象征在這里被賦予了詩學上的符號功能,側重于對人心理內化的文學表述,在詩學形式上具有暗示性形式功能的能指意義,同時在意義的指向上,轉向了人最終極的精神體驗。俄國象征主義詩人勃留索夫、巴爾蒙特等接受與借鑒了法國象征主義詩學理論,將其融入自身象征主義詩學觀念建構與詩學實踐中,不同的是俄國象征主義詩學更側重象征理論主體精神的建構,這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烏斯等理論家的詩學思想中體現得更為深刻。梅列日科夫斯基提出了象征主義中重要的要素之一就是神秘主義的內涵,神秘主義是人和神秘的精神世界、理想世界相互的“通感”,詩人變成了靈魂世界的“洞觀者”。所謂“通感”或“通靈”,反映了俄國象征詩派神秘主義的哲學觀和形而上意識。象征主義詩人這種神秘主義的世界觀和主體意識,映射在具體的象征暗示性的文本意義上,就賦予了象征物多重的意義解讀空間,進而在具有私人化的象征表現手段中,就間接性地營造出朦朧與多義的詩學意蘊。俄國象征主義詩學中的象征觀念具有形而上層面的哲學向度。梅列日科夫斯基認為依托詩歌這一文學載體,“象征”打開了通往彼岸世界的大門,“象征”以物質世界之有限呈現了思想無限的一面,而詩歌中的形象通過象征的暗示性實現了現實世界與精神世界的契合,象征主義關于兩個世界的神秘二元論觀點為詩歌的暗示理論的建構提供了哲學基礎。
二、“暗示”詩學觀念的形成:理論演化與文本意義
“暗示”是象征主義的普遍傾向和重要詩學觀點。俄國象征主義詩人汲取了法國詩人馬拉美的主張,進一步拓展了象征主義的詩語功能。俄國象征主義文學是關乎人的主體情感與情緒的藝術,區別于浪漫主義的抒情性創作美學。象征主義詩歌中的情緒需要通過意象及特定的情境來表現,這種間接的藝術表現方式通過文字與語言將作者的情緒引導出來。象征在俄國象征主義詩學觀中,更突出象征意義的主觀性,強調與人精神世界的隱秘聯系,在創作中更注重象征意義的朦朧性。象征主義與象征范疇密切相關的詩學概念就是暗示。黑格爾在論述象征的類型與功能時就對象征與暗示的關系加以論述,“所謂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現于感性觀照的一種現成的外在事物,對這種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來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種較廣泛較普遍的意義來看”[5]。黑格爾認為,象征并不直接表現外在客觀事物,對事物的表現意義要遠遠大于事物的原本意義,象征暗示性地拓展出事物的多重價值與意義。“暗示”美學構成了象征理論的普遍意義,這種普遍意義往往是約定俗成的,在宗教中,具有普遍的“公共性象征”意義,在不同的時代就有了約定俗成的意義與價值。俄國象征主義詩學中的象征觀念涉及藝術家的私人化象征,同樣的象征物在不同創作者的象征創作體系中,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這就形成了作品意義的多重性,極大地拓展了欣賞者再創作的審美空間,象征的暗示性在象征主義詩歌中就表現在依托于詩人情緒與價值觀表達的個性價值。勞·坡林認為,象征就是“一個暗示某事物或觀念,或者意指多種事物或觀念的東西”[6]。人的主體精神世界如何反應在具體的文學作品中,這就需要依托于象征主義的詩歌文本,在象征文本意義闡釋中呈現暗示意義。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關于象征的字面意義與暗示意義之間的結構性描述,指出了這一點,“傳統的藝術理論認為模仿應該與象征是相對立的,一個是對現實的再現,是對自然的客觀如實的摹寫,一個則是傳達主觀的觀念、情緒,只強調暗示、隱喻、曲折描寫和心理印象”[7]307,顯然,由于象征主義文學不夠重視對現實的模仿與再現創作,呈現為對人主體意識、觀念、情緒的表達,更多地展示人的主觀思想,表現為對理想世界、自然世界的哲思等。所以,在解讀象征主義詩歌文本時,我們被作者引向了詩人豐富而多彩的主體意識世界,迷失在象征的森林中,在藝術家的暗示思維中尋求文本意義的多元化解讀。
在俄國象征主義創作實踐中,詩人創作詩歌的過程主張晦澀與朦朧,直抒胸臆的創作風格并不適用于象征主義,也不需要像現實主義詩歌那樣試圖再現社會生活,詩歌更多地是表現詩人的主觀情緒與審美取向,呈現為對詩人精神領域的體驗與表達。詩歌的快樂正在于一點點地暗示出詩人的情緒,借助詩歌的語詞與文本,暗示詩人對自我的情感認知、對理想世界的追尋,營造多義、朦朧的詩學意蘊,將意象賦予象征的審美功能,暗示詩人主體經驗的“客觀對應物”,借物喻情,托物言志,賦予詩歌作品豐富的意義闡釋空間,以有限表現無限。托多羅夫認為象征可以理解為字面的直接意義和延伸出來的言外之意,而言外之意正是象征的暗示意義。象征的暗示意義在這里就具有了象征主義語境下的詩學價值。對于象征主義文學作品來說,象征觀念的精神性以及詩歌的象征表現手段正是通過暗示得以呈現。
俄國象征主義詩學在自身的象征主義理論建構中,尤其在詩學表現及藝術創作實踐中印證了暗示作為與象征范疇緊密聯系的詩學主張。“從超驗性走向內在性,語言承受了讓人去感受到‘神秘’的存在的全部職責,從此之后,詩人就再不能借助外在于語言、高于語言的任何東西,而只能從語言中,從語言的潛能中,去隱約感受到另一種意義的存在。達到這一目標的途徑,便是‘暗示’。”[8]象征主義者認為對思想的直接表達會削弱文學的藝術性,象征主義詩人的情緒應當間接性表達出來,眾多的象征主義詩歌的讀者在藝術接受的過程中,才能感知到詩人創作中的含蓄與美感。直接表露作者的思想對詩人藝術創作過程中的愉悅性沒有用處,只有具有暗示性的詩歌文本才具有神秘的、審美的魅力,“在詩歌中應該永遠存在著難解之謎,文學的目的在于召喚事物”[9]42。俄國象征主義理論家勃留索夫認為“象征主義可以稱之為暗示的詩歌”[9]176。勃留索夫更注重從讀者這一藝術要素的視角去關照詩歌的文本問題,他認為通過藝術想象與閱讀感受,讀者在意識中具有再闡釋的能力,可以復現作家創作中的思想,即使作為象征主義詩歌的讀者群體面臨著對文本的晦澀的隔膜與解讀。勃留索夫將“暗示”引入到接受美學中讀者再創作的理論視野,拓展了象征美學的文本意義。“暗示”這一馬拉美詩學中的最高境界,成為俄國象征主義詩人、理論家筆下慣常出現的字眼,而在藝術中如何去暗示,梁宗岱使用了幾個高度精練的詞匯,證明了他對象征主義的了然于胸的獨到見解,即以部分代表整體,單一影射復雜,有限表現無限等。他得出的結論是藝術的表現必然是間接的和象征的,而間接和象征的程度又視各種藝術的工具之不同而異,而“暗示”就是構成象征在詩歌文本中展示多元魅力的有效手段。在俄國象征主義詩歌作品中暗示性的詩學特質表現尤為明顯。象征作為象征主義詩學的核心內涵,在藝術表現中,是借由其暗示性將詩人對理想世界的寄望、內心的情感抒發置于詩歌作品中不斷顯示與表達,通過語詞的媒介,表達詩人苦悶與彷徨的內心世界。
三、暗示詩人整體象征的藝術:通感理論
俄國象征主義詩學主要表現在詩人對事物的創造性想象,對主觀意識和客觀事物的辯證法,借助“通感”等藝術手段使事物夸張變形的修辭學這種藝術手段,使各種感覺瞬間挪移,達到感受的新奇,創作暗示的顯性審美空間。“象征主義為通感手法提供了深奧的理論依據,即“暗示”的美學。”[10]“通感”這一詩學概念來自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應和”,其詩歌《感應》認為世界是以象征的形式而存在的,人的主體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隱秘的聯結,只有通過人類的感官才能感知與互通。“應和”理論認為,對于外在的客觀現實,只有憑借主體意識的直覺觀照才能領悟。詩人最終是要通過創作表現出精神世界的神秘。真正的詩人,擁有非比尋常的對待外界事物的感知力,能夠準確感受大自然、宇宙、理念世界,接近于物我相通的境界,表現為精神與外物的交流與感應。“應和”理論可被稱作是象征主義的基本詩學主張與美學綱領。從修辭格意義角度出發來看,“應和”被當作“通感”,并且較為明顯被眾多俄國象征主義詩人采用。運用“通感”可以讓各種感覺在歷經廣泛長期且有意識的錯位,以及基于各類形式的痛苦、情愛及瘋狂,詩人才能最終成為通靈者,其所謂的“通靈者”意味著可見世界屬于神秘宇宙的表征,一般人能夠像詩人一樣,可以在幻覺中學會由可見世界向不可見世界返回,進而實現對心靈或者是精神的隱秘沖動的慰藉。
“暗示”是“應和”論的具體表現內容,備受斯威頓堡的直接影響,更遠能夠追溯至柏拉圖以及中世紀宗教精神。其能夠將象征主義詩人含而不露的想法表明出來。象征主義能夠普遍將對于超驗主義的追求表現出來。與此同時,其所強調的是個人情緒的全面表達以及個人創造性與獨特體驗性的表達。很多人指出,重視內在精神是俄國象征主義詩歌的主要特點。可見,“暗示”是俄國象征主義詩人較為常用的原則與手法,這種類型的“暗示”多是運用私人化語言以及曲折形式化途徑完成的,進而得出,不確定以及朦朧、晦澀成為俄國象征主義詩歌的共同化特征內容。在很多時候,其均為作者主觀行為所產生的效果,利于讀者進行潛意識的再創作,使之能夠更多的關注本體理念及精神世界。“通感”是俄國象征主義詩學中的基本原則,建立在神秘主義與超驗性的哲學理念之上。象征主義詩人認為自然界花草樹木的芳香、顏色、風聲、雨聲全在互相感應,詩歌里的具體形象,相互感應,作用于不同的視聽感官,強化了人自身感覺的主體性,強化了人主體意識的感知能力。將感覺進行轉移與互文的過程,即“通感”。以“神秘主義”美學理念為依據而提出的“應和”論,被俄國象征主義詩人接受并在詩歌創作中加以運用。“應和”理論將通感視為感覺之間的聯通運動,將視覺、聽覺、味覺、觸覺等感覺進行平移,人與自然、理想世界、宇宙之間均存在感應。俄國象征主義詩歌的創作運用通感去暗示詩人與自然、宇宙以及理念的感應,構成整體性的象征活動,象征著人的感覺與精神的互動,構成了藝術體現世界整體性的精神活動。對于俄國象征主義詩人來說,暗示與象征賦予詩歌觀念層面的文學性與形象性。總體來說,通感并不僅僅是詩學手段,也不是簡單的感知層面的同構現象,而是暗示詩人整體象征藝術的詩學理論。
俄國詩人費·伊·丘特切夫比較早在詩歌中運用了象征和通感手法,開啟了暗示詩的創作,對俄國詩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丘特切夫運用直覺性的審美意志去抒發對宇宙和生命的感悟,深刻影響了象征主義詩歌中通感手段的運用和創作。費特詩歌中對純粹境界美感的重視和將美本身作為心靈直覺觀照的對象,呈現出詩歌中對幻夢、心靈、回憶和藝術之間的復雜聯系的探測,以及他們試圖觸及的詩歌“暗示”美學的努力,更使得象征派的美學原則明朗化。俄國象征主義詩歌不再渴望浪漫主義者所追求的彼世,也開始關注現象世界,通過直覺、內省的方式感悟世界。勃洛克在他的詩歌《陌生女郎》中寫道:“每晚,在家家餐館的上空,彌漫著濃烈沉悶的熱氣。是腐味的春的氣息在驅動,傳來了醉后叫嚷的聲息。遠處,在小巷積塵之上,當城郊別墅被寂寞籠罩,那花形面包剛閃出金光,就傳出一陣陣孩子的哭叫。”[11]詩中將不同的主體感官意識運用金光、熱氣、腐味、叫嚷等語詞表現出來,喚起了人與自然氣息、人與城市生活的感應,強化了詩人自身主體性的精神感受,暗示性地表達出詩人內心的孤寂與悵惘。詩歌中通感的運用,也構成了暗示整體情境象征的手段。
四、象征主義的暗示原則:詩與音樂的呼應與相等
俄國象征主義詩學理論中的通感、象征、音樂性,細究起來都是圍繞“暗示”這一詩學觀點而存在。通感作為暗示的表現形式通向神秘的理念世界。暗示作為象征的表現功能展現了作為詩人思想感情的抽象觀念,借助象征詩學手段將詩人抽象的、主觀的精神世界依托具體的意象、語言呈現出來。而音樂性構成了“暗示”的深層意蘊的情感張力與詩歌形式。由于瓦格納等音樂家的直接影響,象征主義特別是包括后期象征主義者,極為希望詩歌等藝術形式能夠緊緊靠攏音樂,所以其對于藝術的音樂性特點給予了普遍關注,尤其是在戲劇及詩歌等方面。就象征主義者而言,其對音樂性的全面強調,早期備受音樂家瓦格納歌劇及其理論的影響。瓦格納能夠在重視強調詩歌音樂性的同時,將詩歌和音樂置于同等地位。這同時也是象征主義者的意見。象征主義的主要原則在于對詩與音樂間相等的合理化追求。基于此,象征主義者們發現瓦格納歌劇凸顯的音樂性,可以大大啟發詩歌創作,原因在于,象征主義不只是將詩歌看作是音樂性的,同時還將音樂性看作是世界所擁有的神秘本質,其所對應的神秘音樂性逐步趨向于藝術化的進程可謂是不斷實現象征化的進程,也就是說在藝術形式實現神秘音樂性象征化過程。可見,象征主義強調的音樂性,從根上并不是側重對文學藝術感官美感的重視,而是將詩歌等所具有的暗示性以及含蓄性、對心靈的細膩挑動性等內容進行強調,進而使得戲劇及詩歌等藝術形式跟神秘超驗世界與主觀精神相互之間存在的隱秘關系得以凸顯。俄國象征主義詩人對音樂、韻律的重視,不僅僅表現在詩歌形式的美感方面,更深層次地表現在象征主義通過詩歌的音樂性深化了詩人的精神體驗,是對超驗的直覺瞬間的體悟。“象征主義對音樂性的強調,根本上不是側重于文學的感官美感,而是突出詩歌與精神世界和神秘未來的聯系,以及詩歌的含蓄、暗示和對于心靈的隱秘挑動。”[7]318這種音樂性的存在,成為俄國象征主義詩人針對象征觀念以及神秘感覺進行表現的重要形式。其具體表現涵蓋兩方面主要內容,第一,要求詩歌具備音樂般的節奏及韻律,象征主義詩歌魅力不衰,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詩歌語言音響與節奏的革新;第二,要求將詩人內在的靈魂音樂以及心靈旋律充分表達出來。實踐證明俄國象征主義者真正追求的是后者。俄國象征主義詩人非常重視詩歌的音樂性,并不是簡單地追求節奏之美與藝術韻律,深層次原因為其對詩歌等藝術形式所具備的含蓄性以及暗示性、象征性、情感引發性等給予充分關注。詩詞語言所擁有的特別節奏韻律,總是在很多時候,能夠跟我們無形的心靈之弦產生共鳴,就好似神秘的超驗王國在忽隱忽現地向人們招手呼喚。
音樂性在俄國象征主義詩歌創作中表現為具有韻律美和對感官美的追求,音樂與韻律打破了語詞在詩歌語言表現中的精確性,使藝術作品的表現更加深邃,進而加強了對精神世界的感召力和與神秘的理想世界的聯系。象征主義的暗示原則就是追求詩與音樂的呼應與相等。在象征主義詩學中,詩歌的韻律與視畫性具有異質同構的關聯,在美學表現上也暗示了象征主義詩歌的情感感染性,如安·別雷詩歌中的金色暗示著詩人心中對神性的向往,巴爾蒙特詩歌中的太陽暗示著詩人的宇宙意識,象征著絕對的力與美。英國唯美主義運動的理論家和代表人物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認為不同的藝術類型都具有音樂性的方面,而安·別雷認為音樂與色彩給予了藝術比較高級的存在形式,藝術在極大的接近音樂的時候,藝術作品也變得極具意蘊,悠遠深邃。俄國象征主義對音樂與色彩的強調,根本上是暗示了詩歌與人的主觀情感感受,以及詩歌的含蓄和對于心靈的感情抒發。詩歌是語言的音響,象征主義詩人運用考究的韻律、同音與疊音的音調,表現出了詩人心中的理想世界,暗示出詩人的心靈直覺瞬間的象征。俄國詩人巴爾蒙特的詩歌具有突出的音樂性美學意蘊。巴爾蒙特在詩歌《俄語節奏舒緩》中寫道:“俄語節奏舒緩,我是它雅致的晶體,對于我來說,其他詩人都屬于先驅,我第一個發現了這種語言的傾向,反復吟誦那憤怒的、溫柔的音響……大地自守一格,獨具色彩的石頭,綠色五月森林里往復回蕩的呼聲。”[12]詩中著重對詩歌的節奏與韻律的內容進行了強調,形容詩歌就是語言的音響,俄語特殊的音律運用到詩歌的整體語言塑造中,強化了詩歌形式的藝術表現力。詩人又運用自然的色彩呈現詩歌的視覺美感,用綠色的森林、彩色的石頭融匯出精致的詩句。詩人陶醉于俄語詩歌創作的音韻美感,同時也創新和發展了俄語詩歌美學的傳統。這首詩歌可說是巴爾蒙特對詩歌音樂性觀點的直接表述。
結語
俄國白銀時代象征主義詩學通過詩歌的暗示性表達詩人私人化的情緒與意志。“暗示”作為通感的表現內容,在詩歌創作中更多地作為整體性的象征營造象征情境的森林,作為詩歌的整體創作美學而呈現。在詩歌的文本意義上,通過暗示性召喚詩人的觀念性精神世界,以此喚起詩人的感覺世界與精神世界的感應,為讀者創作暗示的多重審美意義闡釋空間。音樂性深化了象征的“暗示”美學效果,表現了象征主義詩學的形式美學傾向、強化了詩歌語言的音響化詩學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