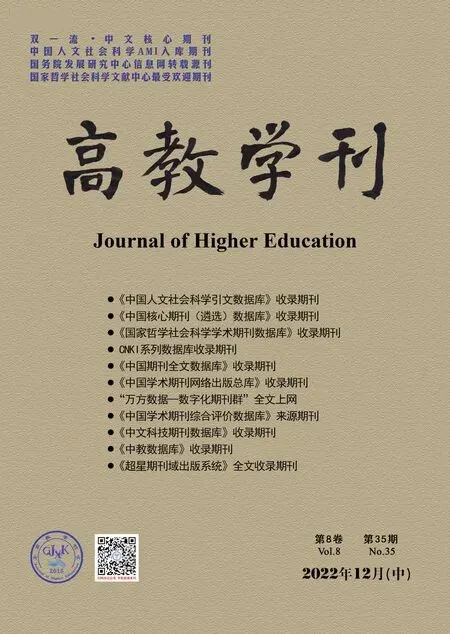“文明互鑒”視域下日本文學選讀課程考核模式構建探索
孫立成
(燕山大學,河北 秦皇島 066004)
2019 年5 月,習近平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提出:“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1]”中國與日本同為東亞國家,兩國之間具有悠久的友好交流歷史。202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 周年,在這一背景之下,如何共建符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成為重要課題。
2020 年所發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日語專業教學指南》(以下簡稱《指南》)對日語專業的學生提出了“日語運用”“文學賞析”和“跨文化交際”等方面的能力要求,指出日語專業的學生應具有“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良好的道德品質”和“社會責任感”,還應具有“中國情懷”和“國際視野”。
日本文學選讀是國內各高校日語專業所設置的“語言文學方向課程”中的一門,多數學校都將其定位為專業必修課。“任何一個文學文本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語境(culture context)中形成的,因此文學文本的故事、情節和人物當中就必然蘊含了特定的文化意義[2]”。《日本文學選讀》教材所優選的作品是學生近距離接觸日本優秀文化的絕佳材料,教師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下,可利用這些文學文本開展以“德”為中心的美育教育。課程考核是日本文學選讀課程教學工作的重要一環,但長期以來施行的“一卷定終身”傳統考核方式不利于學生各項能力的提高,也無法全面評價教學質量。為培養具有中國情懷、情理兼修和銳意創新的新時代跨文化交際人才,基于“立德樹人”的教育理念,現提出“文明互鑒”視域下“多階段多類別”的日本文學選讀全過程課程考核模式,并對課程考核預期效果進行展望。
一、“多階段多類別”考核: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各階段考核+階段測試+結課考試
《指南》規定了培養具有良好綜合素質的日語專業人才和復合型日語人才的目標,并提出檢驗和促進學習為目的、注重“形成性評價”與“終結性評價”相結合的評價要求。日本文學選讀課程的“多階段多類別”考核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這一模式的建構旨在打破單一的考核方式與簡單的考核過程,對學生學習的全過程進行合理且有效的評價,以幫助學生自覺地將教師的授課內容與已存儲的知識相聯系,進行知識體系的建構,實現課程學習知識的遷移,成為“一專多能”的復合型人才、新時代的跨文化交際人才。
(一)“課前自主閱讀”階段線上考核(占比5%)
教師結合教材內容,選取合適的日本近現代文學相關課外閱讀材料,引領學生建立課外閱讀“檔案袋”,引入“形成性評價”,制定量化考核細則,以“評”促“學”。開課前利用“學習通”等教學軟件發布課外閱讀材料,主要包括與教材中優選文本的關聯作品及與作家相關的背景材料。以日本大正文豪芥川龍之介的《鼻》為例,除了提供與其具有互文性的原典《今昔物語集》中的“池尾禪珍內供鼻語”與《宇治拾遺物語集》中的“鼻長き僧の事”(長鼻僧的故事)之外,還會發放與作品“外部研究”相關的“書信”“心理”和“社會”等方面的“外部材料”,比如芥川龍之介所寫的《或舊友へ送る手記》(《寫給老朋友的手記》)等。而“閱讀檔案袋”主要包括“閱讀日記”“讀后感”和“作品短評”等項目,為后期的評價、考核提供確切依據。
(二)“課前預習”階段線上考核(占比2.5%)
學生預習之后需在線完成教師布置的考核任務,教師授課時亦需結合此階段所發現的問題進行相應的講解。以日本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川端康成所著的《伊豆の踴子》(《伊豆舞女》,下同)為例,教師提前將從作品中抽選出來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專有項”發給學生,要求學生對其展開調查分析,探究每一個專有項所內蘊的獨特信息。授課時再與學生共同“尋找”整篇文本中的所有“文化專有項”并一一釋放其內涵。筆者在日本文學選讀授課實踐過程發現,日語專業的本科生與碩士研究生對文學作品中的“文化專有項”有“視而不見”的傾向,即便注意到了它們的存在,也無法正確釋放其中所蘊含的社會、文化信息,致使文學作品解讀能力停留在低階程度,與《指南》中所規定的培養目標相背離。另外,現有的日本文學經典名著漢譯本中也存在日語“文化專有項”不譯、訛譯的現象。這些現實情況表明,如何發揮日本文學選讀課程的文化交流功效是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將該項考核置于“課前預習”階段可以有效引導學生關注文學文本背后所隱含的重要信息,汲取其中的營養,為更高層次的學習做準備。
(三)“課堂教學”階段線下考核(占比10%)
此階段主要考察分組討論、課堂提問時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與“知識綜合運用能力”。教師以課堂行為為判斷基準,評析各個團隊學習效果及各個學生的學習能力、學習態度。同時,將每位同學的優缺點記錄于“表現反饋表”中并在課程結束后及時反饋,對錯誤之處給出相應的修改建議。此項的評價方式為“學生互評+教師評分”。以日本國民作家宮澤賢治的《セロ彈きのゴーシュ》(《大提琴手高修》)為例,教師將“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設為分組討論的主題,讓同學們結合宮澤賢治所創作的童話作品內容就“人與自然的關系”及“生物多樣性”等熱點話題展開討論,然后根據每位同學發言的深度、廣度和寬度來進行綜合評價。思辨能力的培養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長期以來,形成一種包括日語專業在內的外語專業學生的思辨能力普遍低于其他專業學生的判斷傾向。對于此觀點,有專家通過實證研究進行了論證,得出以下結論:“大學外語教育能夠促進學生思辨技能提高,這有助于外語專業教師和學生增強思辨技能培養信心,并為進一步提升思辨技能培養效率做出努力。[3]”當然,思辨能力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完成的,在日本文學選讀的“課堂教學”考核階段,教師設定與某篇文學文本相關的課題,適當引導學生就此展開討論,以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與問題意識,提高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邏輯分析能力。另外,于潤物無聲中的“思政教育”也會在這個階段得以順利開展,教師引導學生關心國家大事,以中國立場向世界發聲,以國際化視野客觀地看待變化中的世界。
(四)“課后復習”階段線上考核(占比2.5%)
教師結合每次課的課上教學內容布置線上作業,并對學生的回答做出測評,以了解學生們的知識掌握情況,為之后的授課做準備。比如結合《鼻》一文的文末“反身”表達“長い鼻をあけ方の秋風にぶらつかせながら”(任由長鼻飄蕩在佛曉時分的秋風中)設定線上作業,讓學生去收集其他文學作品中的相關表達,結合語境分析“反身”表達在各個作品中的效用。這項考核可以培養學生的日語語感,引導他們領會文豪們的獨特創作手法與語言所具有的藝術魅力,在中日語言比較中提升自己的美學修養。
(五)線下“階段測試”(占比10%)
此環節通過線下小測及發表會的方式對學生的單元學習效果進行考核。為了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與創新能力,“階段測試”的考核重點為考察學生撰寫讀后感、研究綜述能力及作品續寫能力。此項的評價方式為“學生互評+教師評分”。以《伊豆の踴子》為例,該作品的擦肩而過的“悲美”結局具有開放性,是作品續寫的優良材料。文學作品的讀后續寫具有促學優勢,“能夠抑制母語漢語遷移,阻止漢語語境知識補缺[4]”,提高學生的日語表達能力與審美能力。
(六)“社會實踐”階段線下考核(占比10%)
1.“問卷調查”實踐活動
2022 年1 月,習近平在2022 年世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的演講中說道:“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才是人間正道。不同國家、不同文明要在彼此尊重中共同發展、在求同存異中合作共贏。”作為日本文學選讀課程“社會實踐”的一環,教師以這一理念為指導組織學生做“關于當代大學生‘日本文學觀’的問卷調查”,并引導學生完成相關實踐報告的撰寫。教師制定相應評價標準并基于此對學生提交的實踐報告進行評價,對不足之處給出修改建議。
2.“文學沙龍”實踐活動
結合作品內容,組織相應主題的“文學沙龍”活動。活動可邀請各個院系的日本文學愛好者參與其中,要求本專業學生每人寫一篇與教材中某篇文本相關的散文或詩歌作品并在“文學沙龍”活動中進行朗讀,之后接受與會人員的點評,與大家進行多元化交流。此項的評價方式為“學生互評+教師評分”。以日本“小說之神”志賀直哉的《城の崎にて》(《在城崎》)為例,教師組織一次以“花開花落皆為詩”為主題的“文學沙龍”活動,學生可結合該作品來寫一篇“心境小說”式文章(以“韻文”為中心的“歌物語”或者“俳句紀行文”亦可)。這一環節既可以讓學生體悟日本“心境小說”的獨到之處,也能讓他們在中日文學比較之中體會不同民族的文學與文化之美。
(七)線下“結課考試”(占比60%)
“結課考試”試題分閉卷和開卷兩部分。閉卷部分主要為基礎概念題和客觀題,占比30%;開卷部分為“知識靈活運用”的項目設計、分析論述等非標準答案的主觀題,占比30%。其中,對課外學習內容的考核占比為30%。
總之,日本文學選讀全過程課程考核模式中包含多元化要素,而各階段各類別的比例可結合實際情況進行適當的調整。
二、“多階段多類別”課程考核對教學目標達成度的支撐
各個類別及各個階段的日本文學選讀課程考核模式會形成合力,有效地促進教學目標的達成。下面,筆者將結合《指南》中所規定的日本文學選讀課程的授課目標探析“多階段多類別”課程考核與各個授課目標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以論證前者對后者的有力、有效支撐,由此闡明此考核方式施行的必要性。
(一)對“培養中國情懷的跨文化交流者”目標的支撐
“課前自主閱讀”階段及“課前預習”階段的相應考核可促使學生廣泛接觸各種類型的日本近現代名家名作,使其增強閱讀興趣,為順利過渡到“課堂教學”階段打下堅實的基礎。另外,課外閱讀“檔案袋”的量化考核及“課堂教學”階段的分組討論等環節的相關考核對學生創新思維的形成及知識綜合運用的能力”培養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階段測試”及“結課考試”試卷中也會加入“中日文學比較”相關題目。這種跨文化研究能力的考察及“關于當代大學生‘日本文學觀’的問卷調查”的“社會實踐”活動有助于學生成長為具有中國情懷的跨文化交流者。而“花開花落皆為詩”的“文學沙龍”活動有益于學生人文素養的提高與文化底蘊的提升。
(二)對“提高學生語言素質”目標的支撐
“課前自主閱讀”階段考核及“課前預習”“課堂教學”“課后復習”和“結課考試”等階段的考核都會激發學生的日語語言學習熱情,督促學生進行高效率的預習、復習,并對自己語言測試中出現的問題點進行查缺補漏,夯實語言基礎,進行基于高階思維的深度學習。
(三)對“建立文化自信”目標的支撐
“階段測試”的項目之一為“名家名文漢譯”,在日譯漢的過程之中,學生會發現蘊含豐富日本文化信息的“文化專有項”并深入理解日本文化、日本社會。當然,在“課前預習”及“課堂教學”階段也會涉及到對日語“文化專有項”的學習。了解外國文化是正確認識本國文化的前提之一,只有跨越中日之間文化障礙,才能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跨文化交流人才,以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立文化自信。另外,“關于當代大學生‘日本文學觀’的問卷調查”的“社會實踐”活動將有助于日語學習者了解中國大學生的“日本觀”,為促進中日之間的友好交流做準備。
(四)對“培養思辨能力及論文撰寫能力”目標的支撐
“課堂教學”階段及“階段測試”“結課考試”階段的考核主要考察學生的分析論述能力,對于學生知識體系的匯通及思辨能力的提高將大有裨益。另外,“社會實踐”階段的實踐報告的撰寫也會為畢業論文的書寫奠定基礎。這與《指南》中所規定的“研究能力”的培養理念相契合,即培養具有一定調查研究能力和理論研究能力,以及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日語專業人才,而“多階段多類別”課程考核模式的構建將會為此助力。
三、“多階段多類別”課程考核預期效果
(一)推進課程思政建設
日本文學選讀課程考核秉承“立德樹人”教育宗旨,以學生為中心,厚植學生的人文素養與文化底蘊,使得學生在正確理解認知日本文學現象的同時,以日本文化這一“他者”為鏡來映照本國文化,進而更深刻地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承繼者、創新者與傳播者。以《伊豆の踴子》的作者川端康成為例,中國的道家思想對其文學創作及藝術觀的影響從很多作品中都可窺出端倪。在川端康成的藝術理念中,“處處折射著莊子的思想。這無疑從一個側面有力地說明了中國道家思想對日本文化的廣泛滲透和深遠影響,同時也證明了莊子在日本文化人心中所占據的重要位置[5]”。對川端康成等日本作家與中國文學、文化的影響關系的分析研究也是日本文學選讀課程考核中的重要一環,這有利于中國日語學習者建立本國文化自信,為推進課程思政建設添磚加瓦。
(二)健全“多元化”學業考核評價體系
“在高等教育中,學業評價是重要的環節之一。隨著高等教育課堂教學改革的日益深入,多元化考核評價體系逐漸得到教育界的共識。[6]”“多階段多類別”的日本文學選讀考核評價體系將突破傳統課程考核的單一考核方式及簡單的考核過程,采取靈活多樣、多層次多階段的考核方式,建立一套科學的、可操作的全過程日本文學選讀課程考核模式,為素質教育和創新人才的培養加油助力。
(三)革新固有教學模式,匯通師生雙方的知識體系
近年來,日本文學選讀教學模式單一固化問題凸顯,“教”與“學”之間對立脫節。傳統教學模式的束縛,教材資源的陳舊,師生角色的固化,課程評估手段的單一,差異化、個性化教學的缺失[7]導致課程考核方式缺乏科學性和先進性。而“多階段多類別”的日本文學選讀課程考核促使學生推進自主學習、交互式學習和探究式學習,打破固有的“個人學習”或者“被動學習”模式,引導學生在日本文學選讀課堂上采用高效的“團隊學習、主動學習與參與式學習”方式,實現教學方式與學習方式的根本轉變,達成“教”“學”關系的和諧和“教”“學”視域的匯通。
四、日本文學選讀課程考核新模式構建的資源配置分析
課程資源是參與者獲取并了解專業知識及學術規范與行為(academic literacy norms and behaviors)的最直接來源[8]。目前,和日本文學選讀課程有關的教材出現了很多精品,大多數教材不僅附有“作家介紹”“讀解參考”和“思考題”等必備項,還加入了“學習目標”“譯文鑒賞”“研究現狀”和“文學作品讀解要領”等特色項目,有利于教師推進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及考核新模式的建構。
另外,隨著信息化時代的發展,中國大學MOOC(慕課)等各個平臺也推出了與日本文學選讀相關的慕課資源。有的慕課是日語專業一線教師建設的日本文學線上課程,有的是中文系教師主講的中國文學及中日比較文學方面的精品課,也有文學批評一類的理論指導性課程。同時,也出現了完備的、與日本文學及中日比較文學論文相關的資源共享平臺,為日語專業學生的自主學習提供了優良的資源,也為“多階段多類別”的日本文學選讀課程考核模式的構建提供了便利條件。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多階段多類別”的日本文學選讀全過程課程考核模式改變了傳統的過度依賴一次性結課考試進行評價的形式,有機地融入過程性考核,順應時代潮流,結合線上線下混合式授課方式進行多元化的、嚴謹科學的學業測評。人類文明的進步與世界的和平發展需要文明互學互鑒,在此視域下構建日本文學選讀全過程課程考核模式是培養優秀的跨文化交際日語人才的最佳途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