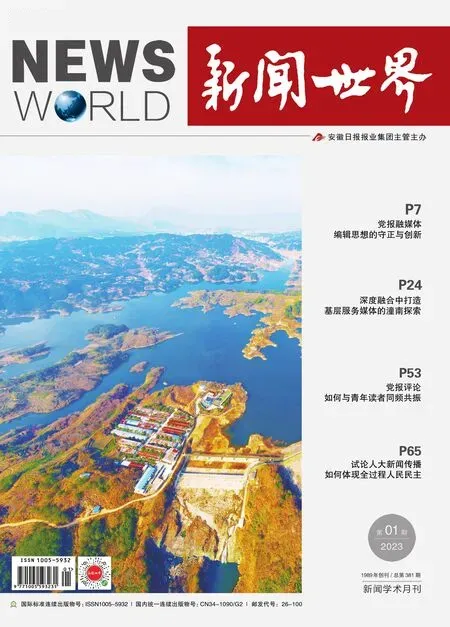全媒體環境下網絡輿情治理困境及應對策略
○馮海兵
一、引言
史料記載“輿情”作為一個詞組可以追溯至唐朝,發展至康熙時期,該詞的主要內涵為民眾的意愿、態度,有時也指民眾的疾苦、情況。[1]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網絡輿情一詞正式被提出,但目前尚無統一定義。中國傳媒科技雜志認為“網絡輿情是以網絡為載體,以事件為核心,是廣大網民情感、態度、意見、觀點的表達、傳播與互動,以及后續影響力的集合,是社會心態最直觀的反映,也是社會治理水平的體現;[2]邵德奇、馮超等人基于新媒體視域認為,“網絡輿情是當前熱點現象和問題在網絡空間引起的集中反映,是網民對其產生的各種理性與非理性的意識、態度、行為、觀點、情緒的總和。[3]進入全媒體時代,自媒體、新媒體深刻滲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為公眾的閱讀、視聽、學習、娛樂提供了無限空間。但與此同時,全媒體視域下互聯網也帶來了網絡輿情事件的頻發,進一步影響了公共政策和政府決策。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研究網絡輿情的變化態勢、表現特征、治理困境和應對手段,對于完善新時代互聯網社會治理具有重要意義。
二、全媒體環境下網絡輿情新變化
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新的媒介技術在傳播領域應用越來越廣泛,尤其是5G時代的來臨加速著媒體向智能化傳播方向轉變,信息的傳播方式也隨之發生深刻改變,社交媒體成為網絡議事的公共平臺,在此背景下網絡輿情傳播更具復雜性。人人都是信源,人人兼具傳播者和受傳者雙重身份,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和海量的情緒訴求、呈現空間聚集和意見交鋒,對網絡輿情的引導和可控性提出了新挑戰,如突發性事件、公共事件、危機事件和群體極化行為等易爆發在網絡平臺,引發全網討論。例如全球新冠疫情自2020 年12 月暴發后,圍繞“物資”“防控”“救援”,從各類假消息滿天飛、網絡謠言、媒體跟蹤報道到官方辟謠、網民點贊正能量事件,各個傳播主體(政府、機構、企業、媒體、個人等)在各大網絡平臺充分表達了不同群體的情感態度和輿情認知。總體來看,全媒體環境下網絡輿情出現以下新變化。
(一)輿論主體更加多元、個體性增強
當前,由于互聯網的低門檻和匿名性,使得處于不同社會地位、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文化水平的網民得以在地球村相遇,利益訴求的差異化使得網民成為網絡輿情產生、傳播過程中的重要參與主體,人群畫像構成趨于復雜化、多元化。公共關系學通常將輿論主體劃分為三類:社會組織、媒介和公眾,三者之間的對話互動促成了整個社會輿論生態的動態平衡。
(二)對話溝通成為達成共識的主要方式
“每一種網絡輿情的發生都會反映出特定群體的某種利益訴求,非理性因素需要、欲望則是利益訴求產生的心理基礎”。[4]網民隨時隨地通過博客、微信、抖音、知乎、小紅書等新媒體平臺進行跟帖、發言、留言、互動,以公開或匿名的方式對社會事務自主地進行意見表達、交流和認同。在這個過程中,更加強調雙方的情緒、情感、政治傾向、現實需要、個體欲望等非理性色彩能在具體的對話場景中達成共識。
(三)傳播渠道豐富,平臺分散化、圈層化、場景化
隨著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深度融合加速,全媒體移動化傳播格局開始形成,各類信息傳播平臺呈現出分散化、圈層化趨勢。如微博聚焦短快新的社會新聞,抖音、快手主打短視頻,今日頭條、一點資訊等聚合各類資訊,小紅書側重Z世代生活經驗分享,知乎、貼吧主攻隱匿化的圈層交流;同時,信息傳播新技術(VR、AR、MR等)還催生出各類新興的交互式媒體平臺,這也促使今后的輿論傳播渠道更趨于豐富化和場景化。
(四)輿論表達群體化、碎片化、情緒化
數字化媒體傳播的實時性、內容的海量化、群體的異質性特征決定了網民言論表達呈現出碎片化、分散性等特點,輿情傳播變得更為復雜和不可控。此外,受不同立場影響,加之自身的媒介素養差異,網民極易受到圈層文化的情緒感染、社會政策環境的多感知性、網絡上意見領袖的煽動,造成思想紊亂或立場態度的反復,從而在輿情表達中帶有強烈的群體情緒。
(五)輿論場的復雜度加大,網民的參與度加深
全媒體環境下,網絡輿情事件不再只是普通的危機事件,更是一種社情民意的集中反映,政府、組織、機構和相關個體廣泛參與其中,相互探討、爭論,聲音龐雜。網絡輿情事件發生時,輿論場以互聯網為載體,充分實現了意見交換,網上網下民意聯動。
三、全媒體環境下網絡輿情治理困境
當前,隨著互聯網技術及新媒體的崛起,網絡已成為人們表達利益訴求、宣泄情緒、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重要窗口,傳統的輿論格局面臨嚴峻的挑戰。在人人都是自媒體、人人都有麥克風的互聯網時代,網民對于身邊發生的不實報道或者令人憤恨的內容,均可以快速通過新媒體渠道曝光并傳播出去,從而形成實時熱點。然而,在網絡輿情傳播過程中,由于新的傳播平臺層出不窮、群體情緒反復發酵、輿論訴求多元化等主客觀成因,涉事主體在輿情傳播的各個時期面臨多重困境。
(一)輿情潛伏期:對網絡輿情事件的預警觀測存在困難
一般來說,輿情事件并非突然發生的,而是在網絡平臺已有“征兆”。常見的是報料人對于涉事主體的舉報、投稿和匿名發帖,隨著話題被各大平臺轉發和各大V 的介入,普通網民開始參與對該起事件的討論和意見表達,并在各個傳播平臺形成實時話題熱度。雖然在輿情事件爆發前期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系統獲取到一定的線索,但由于許多網絡平臺各自為政,數據資源難以共享,進而造成了輿情預警觀測的鴻溝。此外,信息檢索的精準度也影響著后期輿情的分析研判和快速處置。
(二)輿情爆發期:缺乏對網絡輿情事件的應急反應
在全媒體時代,與傳統輿情相比,網絡輿情具有傳播速度快、信息流量大、信息來源廣、謠言泛濫等特點。輿情爆發期,伴隨著輿情事件進一步發酵、放大,民意沸騰,謠言四起,有關部門或主體若還處于觀望狀態或反應遲鈍,將很難應對后續輿情發酵的連鎖反應。如“南京玄奘寺供奉牌位事件”發生后,圍繞“吳阿萍”“玄奘寺”“南京大屠殺”“日本戰犯”等話題,網絡上開始對報料人、涉事主體“吳阿萍”、住持“傳真”進行人肉搜索和“扒皮”曝光,主流媒體對相關監管部門進行了嚴肅追責,南京玄奘寺在此起事件中因反應遲鈍和責任缺失成為眾矢之的。
(三)輿情蔓延期:缺乏對網絡輿情事件的正確引導
在輿情蔓延期,網絡輿情正處在輿情事件爆發的高潮階段,傳播主體之多、速度之快、范圍之廣,經過官方部門、權威媒體、網絡大V 的大量關注與轉發,吸引了全民的眼球和注意力,形成了輿論大爆發和大討論。在此期間,相關責任主體如果缺乏對于輿情事件的正面引導和進行矛盾轉化,將很難收拾殘局。如“邵陽學院1800 萬引進菲律賓博士”事件發生后,遭到了廣大網民的集體質疑和官方媒體的痛批,校方對于天價引才的花費雖然進行了正面回應,但并未及時對“學歷購買”和“水博士”現象進行深刻反省和情況說明,更未積極引導輿論向有利于高校師資良性發展的方向轉變,最終給自身形象和未來發展帶來惡劣的影響。
(四)輿情消退期:缺乏對網絡輿情事件的深刻反思
網絡輿情事件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即任一特定的突發事件都會從其萌發走向消退。輿情消退期表現為相關事件的社會關注度明顯下降。這一時期,雖然輿情事件相關責任人已經受到了處罰(拘留、降職、警告、誡勉、通報等),但是對于社會風氣造成的影響已經無法逆轉,如相關組織主體缺乏自省意識可能再一次引發輿情。如網絡上經常爆出的校園欺凌現象,這反映出教育主管部門和基層教育單位在學生管理方面和輿情應對方面依舊存在思想麻痹大意,對輿情的危害性、持久性、反復性認識不足等。
四、全媒體環境下網絡輿情應對策略
目前,社會各界都在致力于打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運用了監測、預警、應對和處置機制,但依然面臨許多問題,網絡暴力、人肉搜索、造謠攻擊、虛假新聞等現象時有出現,在削弱相關主體公信力的同時,很容易誘導大眾形成帶有違背社會道德規范的認知、情感和行為傾向,產生不良的社會影響。一般來說,網絡輿情事件的發展都會經過潛伏、爆發、蔓延、反復、緩解、消退、長尾六個時期,把握好這幾個時期的發展規律,有利于準確應對輿情事件。

圖1:網絡輿情事件演化過程六階段示意圖
(一)輿情潛伏期:樹立危機預警意識,加強模擬,防患于未然
輿情潛伏期是輿情的孕育階段,也是民意上網的初曉階段。網民在微博上的一次吐槽,或是在知乎論壇的一次爆料,亦或是抖音短視頻平臺上的實名舉報,都會在短時間形成一定的話題和影響力。在全媒體時代,輿論傳播潛伏期就像一顆不定時炸彈,不知什么時候突然引爆,繼而短時間內引發輿論,因而需要政府、企業、機構或個人在平時的一言一行中樹立輿情觀念和預防意識,并能夠基于以往案例建立應急預案,定期開展模擬練習,防患于未然。
(二)輿情爆發期:收集網絡大數據,檢測動態環境,了解社情民意
輿情爆發期是輿情發酵的第一階段,在全媒體矩陣的助推下輿情傳播呈現裂變式和病毒式發展。隨著越來越多的普通網民、媒體、網絡大V 參與到事件的討論中,輿情的影響力呈幾何級數快速增長,進而引發輿情走勢向峰值攀升。這一時期,由于輿情事件參與主體顯著增多,事件話題極易演變為網絡熱門話題。因而,需要利用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技術等搭建輿情監測平臺,實時動態捕捉網民和媒體關注的話題,實現信息自動抓取、自動識別、自動分類、情感分析、詞云聚焦,達到輿情監測的全面化、自動化、精準化,從而做好相應的輿論引導工作。
(三)輿情蔓延期:主動介入,言明事實,誠懇致歉,多方聯絡
輿情蔓延期是輿情發酵的第二個階段。輿情事件在網民的積極討論和大量轉發下借助各種新媒體手段實現全網傳播,公眾對該事件的注意力和關注度達到頂峰。在這一階段,涉事單位或主體需要及時介入,慎重地采取干預措施。首先,建立輿情事件應急小組,制定處理輿情事件的基本方案,保證組織對外口徑一致;其次,針對事件本身進行事實陳述,重點對受害公眾或當事人誠懇道歉、安撫、補償,對相關責任人作出處罰措施,強化致歉態度,求得公眾諒解;第三,主動向新聞媒體及時通報事件調查進展和處理措施,保持聯絡并提供完整的信息資料;第四,立即與政府相關部門聯系,配合政府部門的工作,誠實地提供關于輿情事件的所有信息。
(四)輿情消退期:舉一反三,做好總結,謹防反彈
輿情消退屬于輿情的長尾階段,包含反復期和緩解期,有關單位或責任人切忌盲目樂觀,掉以輕心,以為事件已經過去。相反,應該圍繞事件本身自查自省,舉一反三,彌補工作中的漏洞和輿情治理的短板。互聯網是有“記憶”的,媒體往往會在事件發生的一年或兩年后仍持續關注,如果后續處理或引導不當,很容易再次陷入“輿情反轉”,進而演化成輿情風暴。對于發生過的輿情事件,需要做好總結歸納,謹防新的輿情產生。
結語
網絡輿情是互聯網上網民情緒的表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情民意和社會心理。從其誕生之日起,網絡輿情就對整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全媒體視域下,網絡輿情傳播的快速性和不可控性使得突發性事件頻頻發生,與傳統輿論生態相比,用戶主體、傳播方式、不確定性因素更多,形勢更加復雜,對涉事主體(政府、企業、機構、個人)的輿情處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要基于傳播主體、交流方式、溝通渠道、情緒表達和輿論場等變化特征,轉變輿情治理思路,基于輿情潛伏期、爆發期、蔓延期和消退期四個階段著手制定相應的對策,化“危”為“機”。■
注釋:
[1]張文英.康熙時期對“輿情”的使用及其研究[J].理論界,2010(09):120-123.
[2]中國傳媒科技.網絡輿情[J].中國傳媒科技,2022(06):6.
[3]邵德奇,馮超,王麗萍.新媒體視域下網絡輿情特點與治理[J].中國傳媒科技,2022(06):7-9.
[4]趙仁青,黃志斌.網絡輿情與非理性因素粘連的現實鏡鑒[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