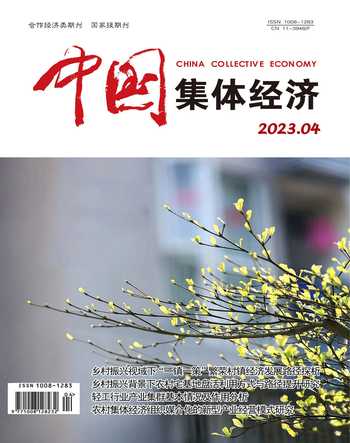創新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的耦合協調評價研究
杜躍平 羅云鶴







摘要:文章采用Super-SBM模型與耦合協調模型對中國30個省市和自治區2009~2018年創新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及其耦合協調度進行了評價分析。研究表明,從時間角度看,中國創新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整體呈不斷上升態勢,但綠色經濟效率低于創新效率;從空間趨勢看,各省市及四大區域效率耦合協調水平雖不斷增長,但內部差異仍然較大,創新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的耦合協調度有待進一步提高。最后根據評價分析結果提出對策建議。
關鍵詞:創新效率;綠色經濟效率;Super-SBM模型;耦合協調
一、引言
轉變增長方式,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首要任務。創新和綠色發展作為新發展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創新是轉變發展方式、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動力,綠色發展是建設美麗中國的主要內容及發展目標。要實現綠色發展,必須通過創新改變我國經濟發展模式,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和資源能源結構,提高資源能源使用效率。
二、 文獻綜述
創新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動力,創新所帶來的新工藝、新產品、新市場能夠為經濟發展帶來新方向。但自工業革命之后,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凸顯,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逐漸成為學者們關注的另一問題。把握創新、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發展關系,對于全面實現綠色協調可持續發展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一)創新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
創新效率作為衡量區域創新要素使用以及高效配置的重要指標,代表著產業結構水平、循環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生產要素利用效率。李婧等利用經費投入、專利等科技指標對中國各地區創新過程效率進行了實證分析;李政等認為創新效率的技術有效性和規模有效性呈現東、西、中不斷縮減的趨勢;李金滟等對湖北省各地級市歷年創新效率進行分析,認為創新效率在不同地區存在明顯差異。
綠色經濟是將資源利用與非期望產出綜合考慮在區域經濟效率評價分析中,是對原有經濟效率的修正,一般用綠色發展水平指數或綠色效率表示;Atakelty認為不考慮環境資源因素的經濟效率評價會對結果分析和政策制定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將環境成本考慮在綠色經濟效率分析中至關重要;錢爭鳴等認為與傳統經濟效率相比,東、中、西三大區域綠色經濟效率呈現不同的增長趨勢,且西部地區綠色經濟效率被低估;斑斕等認為在考慮了非合意產出之后,中國經濟效率水平整體下降,東部與南部地區綠色經濟效率水平處于全國首位;孫金嶺等采用DEA模型分析了“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綠色經濟效率演變趨勢,認為技術進步對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影響。
通過文獻梳理發現,學者們主要將區域創新效率和綠色經濟效率分開討論,鮮有兩者結合在一起分析其耦合協調關系,且較少涉及創新與經濟發展的效率動態演化規律與空間特征分析。因此本文在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構建效率評價指標體系,對中國30個省市和自治區的創新效率和綠色經濟效率耦合協調度及其空間演化特點進行測度研究,深入剖析不同地區創新與綠色經濟發展水平與空間差異,進而為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發展對策提供決策參考。
(二)創新與綠色經濟的耦合協調作用機理
耦合最初源于物理學,主要描述兩個及以上系統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復雜關系。耦合度反映系統內部要素之間關聯程度的大小,若系統內部關聯程度強,則兩者的耦合度就高,反之亦然;協調度主要反映系統內部各部分在相互關聯基礎上從無序轉向有序的一種趨勢。區域創新與綠色經濟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一方面,創新是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另一方面,綠色經濟發展能夠為創新提供優質資源,驅動創新進步,兩者同構成了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耦合協調關系。
1.創新驅動綠色經濟發展
創新是綠色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綠色經濟為創新指引方向。首先,創新能夠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先進的科學技術能夠減少環境污染物排放,釋放生態環境壓力;其次,創新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技術創新變革激發企業創新活力,提高生產效率與產業發展水平;而且在現代科學技術的支撐下,新一代綠色新興產業應運而生,驅使產業結構不斷朝著經濟高質量發展方向趨近。
2.綠色經濟發展為創新提供保障
創新驅動綠色經濟增長,綠色經濟為創新提供發展保障。首先,綠色經濟改善創新環境。經濟實力越強的地區其基礎設施越完善,發達的技術、交通、通信不僅促進了區域間的交流,同時也能夠吸引資金、人才的流入,培育良好的創新氛圍;其次,經濟發展激發創新活力。經濟進步在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同時,也激發了消費者對于新產品、新技術的需求,促使企業加大創新投入,不斷優化改進創新成果;最后,經濟發展為創新提供要素基礎。地區財政收入的增加會加大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夯實創新發展基礎。
3.改進創新效率可以提高綠色經濟發展效率
創新效率的提升加快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促進新興產業發展,提高區域經濟發展的擴散效應和集聚效應;其次創新已成為提高地區綜合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創新效率在提升資源優化配置的前提下,為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最后,創新效率的提升能夠降低產業發展污染物的排放,提升綠色發展水平。
三、模型選擇與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一)測度模型
1.Super-SBM模型
數據包絡分析法(DEA)用以評價多投入多產出決策單元的相對效率。隨后,Tone在傳統DEA模型基礎上提出Super-SBM模型,用以更好區分處于生產前沿面的決策單元。
假設具有n個決策單元(DMU),記為DMUj (j=1,2,…,n),每個DMU有m個投入,q個產出,分別用向量X∈Rm,Y∈Rq表示。矩陣X=[x1,x2,…,xn]∈Rm×n,Y=[y1,y2,…,yn]∈Rq×n,其中,xi、yi>0。
定義ρ如下:
minρ=
x≥∑xij λj,i=1,2,…n
y≥ ∑yijλj,i=1,2,…n
λj≥0,j=1,2,…n
≥xk,k=1,2,…,n
≥yq,q=1,2,…,s
ρ為各個系統的效率值,s-,s+分別代表投入、產出的松弛變量;λ是權重向量。目標函數ρ是關于s-,s+的嚴格單調遞減,且ρ≥0,對于DMU來說,若ρ=1,即s-,s+都為0,則決策單元有效,否則無效,需要在投入或者產出方面進行改進。
2. 耦合協調度模型
借鑒相關的研究成果,將模型定義如下:
(1)耦合度模型。
C=s*
C表示系統之間的耦合度(0≤C≤1),s為系統的個數,U為決策單元綜合評價值,i、j=1,……,s,且i≠j。
(2)耦合協調度 但在研究中發現,若兩系統之間評價值較為相近時,決策單元綜合評價值過高或過低都會有著較高的耦合度,無法對發展水平做出準確判斷,因而引入更為客觀的耦合協調度。
T=αU1+βU2
D=
T為系統U1和U2的綜合協調指數(在文章分析中,U1代表創新效率,U2代表綠色經濟效率),α,β∈(0,1)為待定系數,表示創新與綠色經濟的貢獻度,且α+β=1。但由于資源稟賦條件不同,各地區之間創新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明顯差異,給兩系統賦予相同權重將會影響各自效率協調性分析,因此在結合袁潔研究的基礎上,令α=U1/(U1+U2),β=U2/(U1+U2)。
D代表創新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的耦合協調度。由于超效率模型在計算中會出現效率值大于1的情形,因此僅限定D≥0;同時借鑒蘇宏枝、張青峰學者的研究成果,將區域創新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的耦合協調度等級劃分為四個等級,如表1所示。
(二)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創新與綠色經濟發展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為合理分析區域創新與綠色經濟發展間的耦合協調度,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結合國家“十四五”規劃指標體系,加入環境因素指標。如表2所示。
四、實證研究
(一)數據來源及說明
以中國30個省市和自治區為研究對象(西藏、港澳臺地區除外),研究數據來源于2009~2018年相關統計年鑒、各省市和自治區歷年相關統計公報,采用均值法與線性插值法補齊缺失值;同時考慮到價格因素影響,以2009年為基期,對部分指標進行平減處理。
(二)創新效率和綠色經濟效率分析
基于已有數據,結合Super-SBM模型測算各省市和自治區的創新效率、綠色經濟效率。由于篇幅限制,僅列舉2009年、2012年、2015年、2018年各地區效率值,具體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中國創新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水平不斷提升,但總體綠色經濟效率低于創新效率;且由于資源稟賦條件不同,同一時期效率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性,呈現東部、西部、東北、中部的遞減趨勢。2009~2018年全國整體創新效率均值提升了59%;綠色經濟效率均值提升了53%,但均未達到DEA有效。這表明自“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與“科技強國戰略”實施以來,中國創新資源配置和綜合驅動能力有著明顯提升,創新成效顯著;但各省份綠色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差異,創新、綠色發展思維意識不夠長遠,部分地區出現了創新轉化效率低、綠色經濟發展層次不夠高等問題,創新要素并未發揮其真正的質變作用。
(三)創新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耦合協調度評價
對各地區創新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耦合協調度進行計算,結果如表4所示。2009~2018年各省市效率耦合協調度均有著不同程度的提升,增長幅度較高的省份有青海、寧夏、江蘇、新疆、廣西、貴州、浙江。北京市創新與經濟發展水平高,一直處于優質協調狀態,整體提升幅度不明顯;而山西省一直在中度協調階段波動,整體協調水平低。這主要由于山西屬于資源依賴型發展省份,經濟增長更多憑借資源要素支撐,技術市場與各類創新產出未能真正發揮對經濟的驅動作用;同時在東部產業轉移過程中承接了大量高污染行業,單位GDP能耗高,進而影響其耦合協調度水平。
(四)創新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耦合協調度空間演變特點
2009~2018年全國整體創新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的耦合協調水平不斷提升,優質協調地區基本集中在東部沿海。從2009~2018年,北京、天津、上海、江蘇等省份已從低度協調上升至優質協調階段,山西、河南、河北、內蒙古一直介于低度協調與中度協調之間,整體耦合協調水平遠低于東西部地區;西部省市除西藏外,其他省份創新與綠色經濟的效率協調等級已從2009年低度協調上升到2018年的協調發展,充分使用了創新要素,對綠色經濟發展的驅動效果顯著。
五、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區域創新與綠色經濟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忽視任何一方都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從時間角度看,2009~2018年,全國創新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在不斷提升,創新驅動綠色經濟發展效果顯著,但整體創新發展遠超于綠色經濟,綠色經濟效率的提升依舊具有巨大空間,必須在強化創新驅動綠色經濟效率方面采取強有力的對策措施;其次,各省市創新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耦合協調水平在這十年間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耦合協調程度不深,尤其是中部地區創新與綠色經濟耦合協調水平有待進一步強化提升;最后,在空間上,創新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耦合協調水平不斷優化,耦合協調等級呈現東部、西部、中部依次遞減態勢,西部地區基本實現創新與綠色經濟協調發展。
(二)對策建議
1. 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斷提高科技創新實力及創新效率。首先,各地區應完善創新體制機制,吸引創新人才、資金、技術的流入,提高創新投入質量和產出效率;其次,加強政產學研用合作,提高創新成果的轉化能力和產業化水平;最后,強化對創新成果知識產權的保護,完善產權制度,構建良好的創新環境,提高創新效率。
2. 強化綠色發展理念,提高綠色經濟發展效率。首先,進一步發揮高新技術開發區綠色發展引領作用,結合地區實際情況積極引入各類綠色新興產業,激勵綠色高技術產業的發展,不斷優化高新區產業結構,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實現高新區高質量發展;其次,注重對生態環境保護以及自然資源利用,健全生態補償機制,提高企業在綠色經濟發展中的主體意識和主體作用,積極發展綠色企業、綠色生產、清潔生產,提高資源利用率。
3. 針對具有不同耦合協調水平的地區制定不同的提升路徑,全面提升創新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的耦合協調度。東部地區要進一步強化創新效率和綠色發展效率的提升,在體制機制創新、先進技術應用、數字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全國示范帶頭作用。中西部及東北地區,深入學習和借鑒東部地區的發展經驗,并深入剖析自身在創新和綠色經濟發展方面的不足,緊抓“一帶一路”建設、新一輪西部大開發和東北振興的國家重大戰略機遇,及時調整發展思路,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大力培育新產業、新業態與新模式,堅持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新路子.從實際出發,按照各地資源稟賦條件發展特色產業,宜水則水、宜農則農,加快提升創新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并促進兩者協調發展。
由于數據與篇幅限制,本文的研究未能從更廣泛的時間序列對創新與綠色經濟之間的耦合協調作用規律進行分析;其次,研究對象也不應僅局限于省份,為了研究更加深入,可以從各個產業以及省份內部進行分析,深入探討創新與綠色經濟的耦合作用機理。
參考文獻:
[1]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M].何畏,易家詳,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2-4.
[2]李婧,譚清美,白俊紅.中國區域創新效率及其影響因素[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19(06):142-147.
[3]李政,楊思瑩,何彬.FDI抑制還是提升了中國區域創新效率?——基于省際空間面板模型的分析[J].經濟管理,2017,39(04):6-19.
[4]李金滟,李超,李澤宇.城市綠色創新效率評價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統計與決策,2017(20):116-120.
[5]宋德勇,鄧捷,弓媛媛.我國環境規制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分析[J].學習與實踐,2017(03):23-33.
[6]ATAKELTY H,TERRENCE S V.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productivity analysis of the Canadian pulp and paper industry,1959~1994:An input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0,40(3):251-274.
[7]錢爭鳴,劉曉晨.中國綠色經濟效率的區域差異與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23(07):104-109.
[8]班斕,袁曉玲.中國八大區域綠色經濟效率的差異與空間影響機制[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36(03):22-30.
[9]孫金嶺,朱沛宇.基于SBM-Mal- mquist-Tobit的“一帶一路”重點省份綠色經濟效率評價及影響因素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12):230-237.
[10]KAORU T.A slacks-based measure of 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1,130:498-509.
[11]劉敏.山西省綠色經濟的效率測度及其影響因素實證分析[D].蘭州:蘭州財經大學,2020.
[12]袁潔. 中國綠色創新發展耦合協調度測算及其影響因素研究[D].南昌:江西財經大學,2020.
[13]蘇宏枝,吳宗杰,董會忠.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人口、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研究——基于主成分與耦合協調度模型[J].山東理工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8,32(02):21-25.
[14]張青峰,吳發啟,王力,王健.黃土高原生態與經濟系統耦合協調發展狀況[J].應用生態學報,2011,22(06):1531-1536.
[15]李雪松,曾宇航.中國區域創新型綠色發展效率測度及其影響因素[J].科技進步與對策,2020,37(03):33-42.
[16]王冉,孫濤.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環境規制對中國區域綠色經濟效率影響研究[J].生態經濟,2019,35(11):131-136.
[17]吳傳清,周西一敏.長江經濟帶綠色經濟效率的時空格局演變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宏觀質量研究,2020,8(03):120-128.
*本文系2020陜西省軟科學研究計劃資助項目(項目編號:2020ZLYJ-47)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單位: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