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標志須由專門法律重塑保護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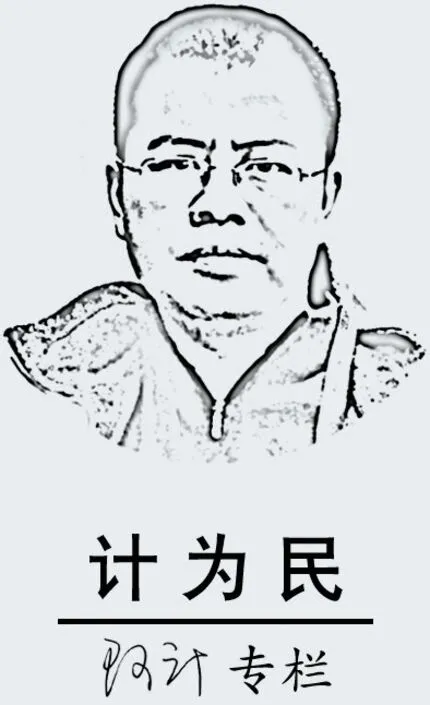
近期,《廣東省地理標志條例》經該省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成為全國首部地理標志地方性法規。這一開創之舉,不僅為保護廣東本地地理標志確立了全方位的法制安排,也為地理標志的國家立法變革提供了可參考的先行樣本。
令不少國人頗感陌生的“地理標志”一詞,其實早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貴州茅臺酒、西湖龍井茶、長白山人參、煙臺蘋果、五常大米、金華火腿、陽澄湖大閘蟹……諸多名聞遐遜的地理標志產品,標示著特定的產地,象征著質量和聲譽,也蘊含著自然印記、歷史傳承和人文積淀。可以說,遍布中華大地的地理標志資源,對于發展區域特色經濟、傳播中華傳統文化、助推鄉村產業振興、拓展對外貿易合作等等,奠定了先天的基石。
追溯起來,我國對地理標志的立法保護,是在本世紀初加入世貿組織的時代背景下快速推進的,并由此構建了商標保護和專門保護的雙軌模式,前者以集體商標或證明商標將地理標志納入保護,后者則分別對地理標志產品和農產品地理標志予以保護。其中,商標保護模式的主要依據是商標法及其實施條例,專門保護模式的主要依據則是《地理標志產品保護規定》和《農產品地理標志管理辦法》,其立法位級僅為部門規章。此外,反不正當競爭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也設置了間接性的保護條款。這種分散化的立法架構,固然滿足了當年快速立法的需求,但多法并行、效力不一的法制設計,不僅難以形成保護合力,還直接導致了地理標志稱謂不一、規范失調、交叉管理、權利沖突等問題。現實中,冒用地理標志的“搭便車”現象屢見不鮮,行業協會強收加盟費的“潼關肉夾饃”“逍遙鎮胡辣湯”風波等等,暴露的正是維權不力與權利濫用并存的困境。
破解地理標志保護、管理困局的關鍵舉措,在于扭轉目前散亂的立法狀態,以專門法律的形式,為地理標志量身打造統一的法律規范。從頂層設計看,民法典已將地理標志明確為與商標、專利等并列的一種知識產權,預留了地理標志單獨立法的制度空間;近年來中央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決策部署,亦明確強調“探索制定地理標志專門法律法規”。可以說,制訂地理標志專門法律的大方向已經明晰,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對具體制度作出科學設計和合理選擇,盡快推動立法的實質進展。
應當看到,地理標志專門法律并非是對既有法制的簡單整合,而是謀求管理機制的內在協調、保護模式的深度融合。這就要求對地理標志的概念界定、保護范圍、認定標準、權利內涵、侵權責任、救濟機制等等作出統一規范,進而構建起系統性的保護制度。如此,地理標志才能擺脫依附于其它立法的歷史局限,真正成為一種獨立的知識產權。
以地理標志的行政管理體制為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由于地理標志多法并行設置了不同的管理體制,進而形成工商、質檢、農業等部門各自為政、多頭管理的格局,不僅導致管理效率低下,也直接滋生了職責不明、執法抵牾、監管缺位等弊端。2018年機構改革后,工商、質檢部門的地理標志管理職責已明確劃歸國家知識產權局,但農產品地理標志仍然沿襲了由農業部門認定的傳統體制,并未徹底完成管理體制的最優化。地理標志專門法律理應以解決這一遺留問題為已任,進一步理順管理體制,以真正實現地理標志受理渠道、審查標準、保護監督等各環節的實質統一。
更應看到,與其它類型的知識產權相比,地理標志具有顯著的公共資源屬性,不僅凝聚了當地的自然血脈、鄉土記憶、歷史傳統、勞動智慧,也關乎當地的產業經濟和百姓權益,是一種集體私權和社會財富。因而,地理標志立法不能照搬其它知識產權的保護方式,而是應當創設更具公共服務特征的制度機制,并以助推產業發展、增進民眾福祉為終極目標。此次廣東地方立法就對此作出了可貴的探索,不僅引入了公益訴訟這一特別保護機制,其立法框架也未局限于傳統思維,而是構筑了貫穿地理標志的培育、使用、保護、服務、交流等全流程的制度體系。未來的地理標志專門法律,亦有必要以更多的制度創新,助推地理標志的潛在價值真正轉化為現實的經濟、民生等效益。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我國極為豐厚的地理標志資源,是彌足珍貴的知識產權長項,也是參與全球經濟博弈、文化競爭的優勢籌碼。正因此,從地理標志資源大國邁向知識產權強國、經濟強國和文化強國,是一條切實可行的突破路徑。而地理標志法制的更新改造,正是催動這一進程的關鍵所在。一言以蔽之,加快地理標志專門法律的立法步伐,勢在必行,功在長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