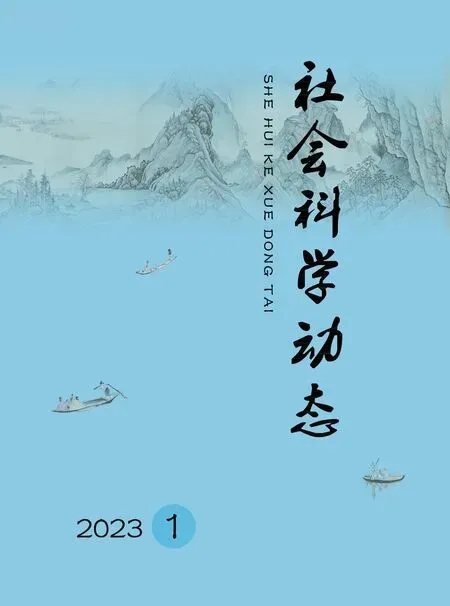恩格斯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問題研究述評
李 雯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是恩格斯歷史合力論思想中的一個根本或核心問題。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以及晚年數篇歷史唯物主義書信中都提到了這一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早已證實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 ,那么人們創造歷史的活動勢必含有人的目的和意志。然而,歷史結果往往不是從事活動的人們最初料想的那般,而是更多地體現為不盡人意甚至是適得其反。正如恩格斯所言, “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但是行動實際產生的結果并不是預期的,或者這種結果起初似乎還和預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卻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①人們不禁會問,為什么會出現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依恩格斯之見,這是因為社會歷史根本不同于自然歷史,人類史的存在、發展和規律性表現與人的意志、目的始終交織在一起。這一獨特性既表現在人類整體歷史發展進程中,也表現在每個個體的歷史活動中。既如此,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的解決也就轉化為對歷史規律與人的目的關系的探尋。
很明顯,對歷史規律與人的目的關系的正確把握,是我們破解恩格斯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難題的關鍵所在。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盡管一直經久未衰,但總體看來,國內外學界迄今仍未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解決方案。
一、國內關于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的相關研究
應該說,國內學界圍繞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問題,一些學者如葉澤雄、王南湜、林劍、左亞文、白利鵬、許恒兵、董新春等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索,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整體看來,目前國內研究仍然遺留了不少爭議性問題,有待進一步拓展與深化。具體來說,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否認問題的合法性
歷史規律與人的目的的關系問題實屬難解,稱其為歷史規律研究的 “瓶頸問題” 一點也不為過。面對其內在的邏輯悖論和理論困境,很多學者認為:歷史規律與人的目的由于各自分屬于兩個 “世界” “層面” 或 “層次” ,不能直接建構聯系。因而二者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一個 “真問題” ,沒有討論的必要和解決的可能。
1. “兩個世界說”
學者王南湜斷定這是一個 “虛假的問題” , “無論在何種意義上,我們都不能合理地談論歷史規律與人的能動作用的關系問題。”②他把世界二重化為 “理論世界” 與 “實踐世界” ,接著把歷史規律與人的能動性分別安置于這兩個根本不同的世界,由此認為二者之間的關系無論如何也不能予以合理討論。沿著這一思路解讀歷史規律與人的目的關系的學者還有許恒兵。在他看來,歷史規律并不同人的能動性一樣直接存在于社會現實,因而不能在邏輯一貫的意義上談論二者之間的關系問題。③
2. “兩個層面說”
學者王峰明認為,歷史規律與人的能動性具有不同的性質,分屬于社會歷史發展的兩個不同層面。其中,前者處于 “本質抽象” 層面,起著 “趨勢” 和 “結果” 的作用,后者處于 “現象具體” 層面,作為前者的現實基礎存在。④不同的是,王峰明強調人的能動性是歷史規律得以形成的現實基礎、實現的具體方式以及獨特的表現形式,又堅持了二者的統一。
3. “兩個層次說”
學者龔培河意識到歷史規律與人的能動性關系問題之所以難解,就在于二者不在同一層次。⑤他主張構建歷史規律與人的能動性之間立體式的互動邏輯,而不是傳統的平面式線性鏈接。
上述見解不乏深刻之處,事實上揭示了歷史規律的非直接現實性(或抽象性),即歷史規律不能像現實實在一樣直接呈現于主體面前,只有通過人們的抽象力才能予以把握。歷史規律 “沒有任何其他的現實性,而只是一種近似值,一種趨勢,一種平均數,但不是直接的現實。”⑥這符合對歷史規律的辯證理解,切近社會歷史現實。但只強調了 “兩個世界” “兩個層面” 或 “兩個層次” 之間的分離與異質性,對它們之間的融合與共性闡釋不夠充分,最終無益于 “矛盾” 難題的解決。
(二) “矛盾” 理解的不同闡釋
在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的理解上,學界主要有以下三種闡釋路徑。
1. “預期與非預期” 喻示歷史規律的客觀制約性
這類觀點在學界頗受歡迎。不少學者斷言,恩格斯之所以在闡發歷史合力論思想時提出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難題,只是為了論證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或意圖說明歷史客觀規律的存在。⑦這種觀點恪守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但僅僅停留在規律的客觀性與制約性的論證上,無力繼續朝歷史深處走去。
2. “預期與非預期” 表明歷史發展的無目的性
這種觀點在學界頗具權威,很多知名學者持此觀點。如學者林劍認為,歷史的 “非預期” 現象只能表明 “‘現實的個人’的活動是有目的的,而社會歷史的發展是無目的的。”⑧再如陳先達先生,他也同樣強調 “個人活動的目的” 與 “社會發展的目的” 之區別。⑨他在解釋社會歷史為何出現 “非預期” 時,強調人們創造活動的 “不由自主” 是因為創造活動的規律不是由人類自身而是由客觀事物及其相互關系所決定的。⑩他認為,根本沒有所謂的歷史目的。類似地,趙家祥和楊耕等學者也反對 “合目的性” 的論斷。依趙家祥之見, “合目的性” 的論斷意味著有某種 “目的” 外在于人類社會,需要社會去靠攏、實現這個 “目的” 。這是歷史唯心主義的表達。?楊耕也認為,盡管人的活動有目的,但這個目的的形成和實現,除了取決于人自身,更加取決于現實社會關系所蘊含的必然性。那些缺乏客觀依據的、不能體現歷史規律的目的,最終只能流于空想。?
就其暗含的價值取向而言,這種觀點實則為前一種觀點的變形。如果把握不好,就會有把歷史規律與人的目的割裂或孤立開來的傾向。既然斷定歷史發展的無目的性,那么,人類歷史就不免成為 “鐵的必然性” 客觀演繹的結果,人及其能動活動就可能被貶抑為工具或手段。如此一來,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就帶上了宿命論的色彩,最終歷史規律很可能會消解于歷史的無目的性之中。
3. “預期與非預期” 映現人類歷史發展的特殊性
這一觀點起初并不被接受,但隨著時代的個體化、多元化、差異化特征與日俱增,這種觀點日益受到學界認可與重視。就其發展趨勢來看, “目的” 闡釋成為一種主導性的闡釋路徑,或許是不可避免之事。學者葉澤雄認為,恩格斯提出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主要是為了進一步明確人的目的、意志因素在社會歷史進程及歷史規律生成與作用中的地位。?他較為深入和系統地研究了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強調只有人才是歷史的真正主體,社會歷史須臾不可離開人及其目的性活動,并以此作為人類史與自然史的根本區分。?當下,還有許多學者也開始變換視角,尋找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從人的主體性和目的性視角闡釋歷史規律。如學者吳宏政認為,歷史規律區別于自然規律的本質就在于歷史規律的 “價值先導” (即目的因素), “沒有目的就沒有規律,因為規律就是通向目的的必然性。”?再如學者陳新夏強調對歷史規律作主體性的闡釋。他指出,要正確理解歷史規律,除了客體方面的要求外,還應該有主體方面的要求,需要把人的價值、需要和利益提到應有位置。?
綜上可見,國內學界對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的幾種闡釋,愈發走近恩格斯歷史合力論思想的深處。這些都預示著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問題的研究將會綻放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三) “矛盾” 解決的不同思路
整體來看,國內學界關于 “矛盾” 難題的解決方案,除了兩種主流思路——實體性思路與主體性思路之外,還有其它一些 “非主流” 的思路。
1. 實體性思路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計劃經濟年代,實體性思路占據主流。受蘇聯影響,彼時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著重強調歷史規律的客觀性,將社會生活或人類歷史視為一種 “自然化” 的過程,造化出一個 “無人之境” ,抹煞了人的主體性或能動性。實體性思路把人及其能動作用排擠出社會歷史領域,缺陷是明顯的。
2. 主體性思路
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市場經濟年代,主體性思路逐漸代替實體性思路成為主流。主體性思路不再規避人及其能動作用,而是把人的目的與歷史規律共同納入理論思考范圍。歷史規律不再被認為是絕對的決定力量,只是被看作人類活動范圍、幅度的一種限定,在這個界限或 “可能性空間” 內,人們擁有選擇的權利和自由。 “可能性空間” 理論是主體性思路中最具創意的解答,它突顯了人在社會歷史中的能動性作用,反映了思維層次的轉換與提升,相對于實體性思路具有顯著的優越性、合理性。但是,它仍然沒能解決歷史規律與人的目的的統一問題。
3. 其它一些思路
除了兩大主流思路以外,國內有些學者還進行了其它一些嘗試。雖然沒有產生多么大的影響,但也給予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問題的研究以諸多有益啟示。比如中介理論。它承認歷史規律與人的目的之間具有統一性,但認為這種統一性需要以某種 “中介” 作為前提來建立。具體包括 “歷史趨勢中介論”?“認識中介論” “社會事物中介論”?“社會本能中介論”?“利益中介論”?等等。再如復雜性科學理論。它認為,復雜性觀念比規律性觀念更具解釋力, “可以內在地確立和說明人的能動作用的歷史作用”?,能夠更好地跨越傳統解釋中 “歷史規律與人的能動性” 之間的鴻溝。
上述思路為破解歷史規律與人的能動性之理論困境提供了多種可能性,極大拓寬了研究視角。近年來,還有一些學者嘗試尋求新的解決思路,以克服以往研究不足和遺留的難題。比如,學者葉澤雄基于實踐唯物主義提出的 “契合論” 。在他看來,人類實踐的雙重尺度內在規約了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之間相互靠攏的 “契合” 關系,而非彼此分離的 “對立” 或 “并列” 關系。?這理應成為我們思考的重點。
二、國外關于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的相關研究
現實生活中 “預期” 與 “非預期” 的相互嵌套和交錯,反映了人類歷史本身的極端復雜性,不斷挑戰著既有的關于歷史規律的獨斷論界說和硬性規定。在古代和中世紀,雖然沒有成形的歷史規律觀,但是人們的頭腦中已經萌生了決定性或必然性的觀念。誠然,這種認識是樸素、簡陋和粗糙的,但其意向卻十分清楚——用一種普遍本質解釋殊多和萬有(無論這種本質是源于人類理性自身的 “邏格斯” 或 “努斯” ,還是來自外部客觀精神的 “神諭” 或 “意旨” )。近代以來,由于思想家們各自理論前提、思想立場、考察方法和認識角度等多方面的差異,西方哲學形成了對歷史規律的多元化解讀。但有一點卻是殊途同歸的,即:詭譎復雜的人類歷史被賦予了一種必然性的本質,歷史規律甚至被看成是唯一或真正能夠解釋社會歷史的基礎。無論是近代啟蒙哲學以科學精神征服歷史,從而將機械必然性觀念注入歷史,抑或是德國古典哲學以目的論統攝歷史,它們都毫無二致地承認歷史本身有其內在的必然性或規律性。規律性思維的應用使得對人類整體歷史作貫通性理解或宏觀性透視成為可能。然而,上述觀點通常帶有客觀主義或本質主義的傾向,暴露出近代歷史哲學的不足與缺陷。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生活完全是不合理的和不人道的,理性主義已信譽掃地了。尼采的失望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虛無主義是這一時期思想狀況的絕妙反映。對任何進行深刻思考和具有深切感受的人來說,現實越來越不能被忍受了。”?
因而,現代西方哲學開始考究人們的歷史認識能力,反思歷史的前提、假設、性質和思想方法,開始致力于對歷史規律的普遍否定與歷史目的的熱情追尋,以打破近代哲學的必然性迷夢。
(一)普遍否認歷史規律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西方歷史哲學轉向批判的歷史哲學,否定歷史規律的傾向占據上風。在他們看來,社會歷史事件不具備自然事件那般重復性、客觀性與可預測性,也就不存在所謂的歷史規律。
1. 重復性問題
新康德主義者從歷史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學科劃分入手,以歷史事件不具有自然事件的重復性為根據,否定了歷史規律的存在。他們強調,只有具有重復性的、反復出現的東西才具有規律性。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都認為,歷史學是一門研究不具重復性的個別事件的學科,就是對 “歷史進程中的典型而獨特的事件進行概念分析”?,就是對 “一次性的、特殊的、個別的東西本身進行描述。”?故而,歷史不存在規律。他們做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的學科劃分,實際上是要求歷史學脫離自然科學束縛,而按照歷史學自己的方式去認識和研究歷史。?這實際上是對自然主義和實證主義思潮的反動與反撥,是歷史哲學領域的進步。但是,他們僅僅止步于社會歷史的現象層面,且混淆了歷史規律與歷史現象的區別。他們沒有看到 “規律” 與 “現象” 是全然不同的兩個概念,沒有看到若干不可重復的歷史事件表現出來的正是具有重復性的歷史規律。
2. 客觀性問題
新黑格爾主義者從自然與歷史的二元對立出發,以社會歷史不具有自然界的客觀性為根據,否定歷史規律的存在。他們認為,所謂規律是完全客觀的存在。自然界的一切不依賴于人及其意識,完全是自發地運動,所以自然界存在規律。然而,社會作為人的社會,由人的活動所構成,不存在獨立于人之外的客觀規律。克羅齊斷言, “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 “精神含有它的全部歷史,歷史和它本身是一致的。”?他認為歷史遺留下的知識都不是客觀的。每個人都從自己的 “當前興趣” 或價值需要出發去研究過去的事實,就把當代的價值觀滲透到歷史之中,使之帶上了主觀性。因而,歷史不存在規律。柯林伍德持類似觀點,他認為 “歷史學的題材并不是過去本身,而是我們對它掌握著歷史證據的那種過去。”?在客觀性的理解上,他們犯了嚴重錯誤。他們沒有意識到認識論意義上的客觀性與本體論意義上的客觀性之區別,而只是一味地把歷史認識的主體性和歷史性從其客觀性內涵中剔除干凈,從而把客觀性看成是超主體、超歷史的。可以說,克羅齊與柯林伍德都沒有理解真實的歷史,反而把客觀的歷史融化在他們的主觀主義論調之中,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盡管他們意識到了人類社會相對于自然界的特殊性。
3. 可預測性問題
分析哲學家波普爾從科學哲學立場出發,以社會預測的不精確性為由否定歷史規律。他認為,人們可以依據規律做出準確預言。在自然界,人們可以基于客觀規律對自然發展做出預測,不會對自然界產生影響。而在社會歷史領域, “預測可影響被預測事件。”?社會預測這種 “俄狄浦斯效應” 要么促進或阻止被預測事件發生,要么加速或延緩被預測事件發展。 “無論是科學的或任何別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預測人類歷史的未來進程。”?波普爾這種論斷,對馬克思主義來說極其不公正。原因在于,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科學(尤其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是對社會歷史本質及其規律的把握,當然具有預測功能。現代科技的突飛猛進更為這種預測的實現提供了方法保證與技術手段。事實上,波普爾據此來否定歷史規律的存在,不過是他的一個思想引子,他的真正目的是 “要‘摧毀’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理論”?,政治偏見十分明顯。
綜上,批判的歷史哲學家們對歷史規律的認識存在嚴重缺陷:他們用自然規律作為評判歷史規律的標尺,用自然現象的簡單類比來衡量社會歷史事件。應該說,歷史規律與自然規律具有差異性,不能簡單用自然規律觀硬套,而應根據社會歷史實際加以概括。此外,雖然他們在否定的具體進路上不盡相同,有思想家從歷史本身的特殊性入手,有思想家從歷史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劃分入手,有思想家從科學哲學立場出發,但他們均高度一致地否定歷史規律。如此一來,在歷史規律與人的目的關系問題上,由于消解了歷史規律的一極,實際上就取消了這一問題。 “原來矛盾著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沒有和它作對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否定歷史規律的做法不是對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的真正解決,而是一種消解 “矛盾” 或使之 “虛無化” 的手段。
(二)熱情追求歷史目的
目的論思維猶如西方傳統思想的基因,至今仍未消失,或者說不可能完全消失。從柏拉圖的 “理想國” 和亞里士多德的 “目的因” ,到奧古斯丁的 “上帝之城” 和維科的 “天神意旨” ,再到康德的 “大自然計劃” 和黑格爾的 “理性的狡計” ,都概莫能外地滲透著目的論思維。即便是在當今這個科學澄明的時代,目的與目的論依然是理論界熱議的話題。
在后現代主義那里,歷史不僅是 “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進步的和決定論的”?,同時也是 “目的論” 的, “有目的地朝著某種預先決定的目標運動。”?建設性后現代主義代表大衛·格里芬明確彰顯了他對目的的追尋: “如若沒有某種趨向于理想的可能性的目的因,理想、可能性、規范或價值便不能發生作用”?。他的后現代整體有機論包含了豐富的自然內在目的論思想。現代批判的歷史學家格魯內爾把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劃歸至 “千禧年論” ,界定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單一因果論(monocausal)唯物主義,即認為經濟條件決定全部社會生活。?與此同時,他又通過目的的設定來理解歷史。在格魯內爾看來,歷史的價值就在于它的目的本身;歷史的確定性在于它是不斷朝著某一目標的不斷接近。?當代知名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聲稱西方的自由民主是 “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 和 “人類政體的最后形式”?,同樣設定了歷史的 “定向性” 和 “歷史終結” 的目的。再如卡爾·洛維特的《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莫里斯·邁斯納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等等都在形形色色的意義上設定了歷史目的。
綜上可見,現代、后現代思想家們對歷史目的的熱情追尋,并沒有拋棄對歷史規律的言說。但是,他們卻往往以 “規律” 之名,行 “目的” 之實。他們認為,人類歷史既是被客觀規律決定的 “自然史” ,也是受最高目的指引通往圓滿的過程。在客觀歷史規律的嚴格規約下,必定有某個目的地在遠處等候著人們到達,無論是福山的 “歷史終結” 抑或是格魯內爾的 “千禧年” 都是如此。這些 “主觀主義者雖然承認歷史現象的規律性,但不能把這些現象的演進看作自然歷史過程,這是因為他們只限于指出人的社會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這些思想和目的歸結于物質的社會關系。”?他們沒有看到規律背后的社會現實,特別是經濟事實和物質基礎,因而是唯心主義的,對理論和實踐具有巨大的危害。就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本身的研究進展來看,這與近代哲學相比無疑是一種倒退。近代哲學尚且借助歷史辯證法,通過歷史運動去克服和解決矛盾。比如,維科的 “社會行動意外效果說” 、康德的 “大自然計劃說” 、黑格爾的 “行動附加說” 等。到了現當代思想家這里,辯證法反而被拋棄殆盡。從學術思想及其蘊含的政治傾向來看,西方學者基本上對此持詰難和批評態度,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成為他們攻擊唯物史觀的矛頭。應該說,國外研究者的詰難和批評,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跟他們的階級偏見、政治立場不無關系,但其中也不乏學術層面上的積極探索與思考。例如,他們對規律獨斷論的反叛以及對人的目的的尊重,給予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以創新性的研究視角和思路。同時,他們在詰難和批評過程中留下的諸多問題,如歷史本身是否有目的以及發展是否合目的;人及其意志沖動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如何,應如何評價;馬克思的思想與恩格斯的思想各有什么特色,等等。這些都是我們應該重視并予以解答的。
三、恩格斯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研究的評析與展望
從深層次上看,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實際上指向的是 “人類歷史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問題。”?因而,深入思考并尋求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的解決路徑,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身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當今社會實踐發展的客觀需要。
關于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的深層根源——歷史規律與人的目的之關系的研究一直是熱門話題。以我國研究歷史規律與人的目的關系的文獻統計分析為例。基于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以 “規律” 并含 “目的” 為主題檢索詞,設定期刊來源類別為 “核心” 和 “CSSCI” ,檢索出自1992年至2022年(近30年間)的相關文獻共有648篇。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整理并繪制出其發表年度趨勢圖、主題分布圖,參見圖1、圖2。從文獻計量的角度對 “規律與目的” 領域的研究現狀和主題分布做一歸納總結,并對CNKI數據庫中CSSCI與核心子庫的648篇學術論文進行挖掘,分析該領域論文的年度發表趨勢和主題分布的基本情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認識該領域研究的演化發展及其階段性特征。

圖1 學界關于規律和目的研究論文發表年度趨勢
1992—2022年的 “規律與目的” 研究論文發表年度如圖1所示。從中可知:其一,就發文數量來看,CSSCI期刊與核心期刊截至目前所刊發的 “規律與目的” 相關文獻共計648篇,高質量論文數量比較豐富。在近30余年來,相關研究的刊發數量除2019年外,每年從未低于10篇。其二,就整體趨勢來看,所有年份均有相關主題文獻刊發。這表明,該研究這些年來從未出現過間斷。實際上,近些年的發文量還有進一步上升的趨勢。發文量居高不下反映出這一問題尚未被徹底解決,仍有進一步深入和拓展的空間,將持續引發學界關注和思考。
1992—2022年的 “規律與目的” 研究論文主題分布如圖2所示。從中可知:文章數量位居前列的幾個主題詞依次為:(1) “合目的性” (45篇);(2) “合規律性” (35篇);(3) “高等職業教育” (32篇);(4) “馬克思” (32篇);(5) “新形態” (32篇);(6) “一體化教材” (30篇),等等。通過上述梳理可見,理論界對 “規律與目的” 問題較為重視,力求深入、全面地把握二者及其關系,確實取得了很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實事求是地講,既往研究也存在一些問題或值得商榷之處。其一,相關研究不均衡,存在一定的偏向性。具體來說,國內學界在歷史規律與人的目的關系的研究上,往往傾向于論證歷史規律的一端,而對于 “目的” 的另一端則較少提及。從國內研究主題分布情況來看,文獻比較集中的幾個主題分別是 “合規律性” “高等職業形態” 等,而以 “歷史目的” “人的實踐” 為主題的文獻相對來說要少很多。其二,該主題的研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 “重馬輕恩” 傾向。分析1992年以來CNKI上述特定數據庫中已有學術文獻的主題分布(見圖2),以 “馬克思” 為主題的文獻數量高達32篇,而以 “恩格斯” 為主題的文獻則只有9篇。在大多數情況下,恩格斯是以 “第二小提琴手” “馬克思的摯友與戰友” 的形象,或者說,是作為馬克思的 “陪襯” 出現在人們的研究視野中。相對于 “馬克思” 研究的厚重和扎實, “恩格斯” 的研究則稍顯薄弱。這反映出當今研究的不足與今后要努力的方向,在 “目的” “恩格斯” 等主題的研究深度、范圍和內容方面,需要進一步深化、細化與豐富。

圖2 學界關于規律和目的研究論文的主題分布
鑒于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問題的復雜性,我們 “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預期” 與 “非預期” 在社會歷史領域中既看不見,也摸不著,歷史規律與人的目的更不是什么有形、可見的物質實體。因而, “顯微鏡” 或 “化學試劑” 的實驗室方法在這里并不適用,只有科學的抽象法才能把握住 “非預期” 現象背后的規律。同時,我們還應注重邏輯與歷史的統一。既要注重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提出的時代背景和思想淵源,一切分析和結論應以彼時特定的主、客觀條件為前提,又要從邏輯上說明該問題提出的必然性。
注釋: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頁。
② 王南湜:《我們可以在何種意義上談論歷史規律與人的能動作用》,《學術月刊》2006年第5期。
③ 參見許恒兵:《蘇聯學者歷史規律與人的能動性關系論的范式轉變及困境——兼論一種可能性的解答方案》,《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學報》2016年第5期。
④ 參見王峰明:《歷史深處的漫步與遐思——陳先達先生的社會歷史規律觀述評》,《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
⑤ 參見龔培河、俞偉:《歷史規律研究邏輯困境與波普爾兩個論斷的啟示》,《長白學刊》2017年第6期。
⑥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4頁。
⑦ 參見王南湜:《追尋哲學的精神:走向實踐哲學之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頁。
⑧ 林劍:《論個人活動的有目的性與歷史發展的無目的性》,《哲學研究》2014年第11期。
⑨ 參見陳先達:《一個值得商榷的哲學命題——關于 “合規律與合目的” 問題質疑》,《學術研究》2009年第8期。
⑩ 參見陳先達:《歷史唯物主義的史學功能——論歷史事實·歷史現象·歷史規律》,《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2期。
? 參見趙家祥:《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57—358頁。
? 參見楊耕:《歷史規律研究中的三個重大問題》,《江蘇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
? 參見葉澤雄:《再論恩格斯歷史合力論研究中的幾個關系問題》,《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年第2期。
? 參見葉澤雄、趙鵬:《歷史合力論視域中的 “預期與非預期” 矛盾問題》,《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 吳宏政:《世界歷史規律的 “價值先導” 原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2021年第1期。
? 參見陳新夏:《歷史規律和趨勢的主體性闡釋》,《天津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
? 參見陳晏清、閆孟偉:《歷史規律·歷史趨勢·歷史預見——評波普〈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求是》2003年第18期。
? 參見田浩:《社會規律的客觀性與人的主觀能動性統一的中介》,《東岳論叢》1993年第4期。
? 參見劉福森:《人的社會本能和社會規律》,《哲學研究》1993年第3期。
? 參見穆懷中:《論利益在人的動機與歷史規律之間的中介作用——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哲學思考》,《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6年第2期。
? 白利鵬:《理解人類的命運:從規律性假設到復雜性假設——兼與王南湜教授商榷》,《學術月刊》2008年第11期。
? 參見葉澤雄:《論恩格斯對 “歷史” 本質的科學闡釋》,《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1年第1期。
? [法]約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紀法國思潮:從柏格森到萊維·施特勞斯》,吳永泉等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3—14頁。
? [德]文德爾班:《文德爾班哲學導論》,施璇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15頁。
? [德]李凱爾特:《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李超杰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68頁。
?? 參見[英]柯林伍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241—242、287—288頁。
?? [意]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博任敢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2、13頁。
? [英]波普:《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杜汝楫、邱仁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頁。
?? 韓震:《西方歷史哲學導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68、472頁。
?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頁。
?? [英]伊格爾頓:《后現代主義的幻象》,華明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55、55頁。
? [美]格里芬:《后現代科學——科學魅力的再現》,馬季方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第3頁。
?? 參見[英]格魯內爾:《歷史哲學:批判的論文》,隗仁蓮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4、15頁。
? [美]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陳高華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9頁。
? 《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頁。
? 左亞文、李棟:《論恩格斯晚年歷史合力論的根本問題》,《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2年第4期。
?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