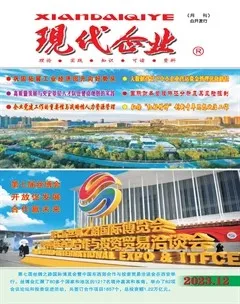健康型相對貧困風險防控與企業參與研究
□ 安徽蕪湖 陳愛如 張興民
2020年我國取得了脫貧攻堅戰的偉大勝利,實現了現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消除了絕對貧困,極大地提升了農村人口生活水準。但對農村貧困問題的探索并未結束,更加廣泛、隱秘的返貧問題還將長期嵌構于鄉村社會中,因疾病、健康因素造成的健康型返貧則是返貧問題的核心,并成為目前鄉村振興戰略亟待解決的問題。健康型相對貧困家庭應對外部風險沖擊具有顯著的脆弱性,大量貧困邊緣人口收入略高于國家貧困標準線,其生計策略單一,抗風險方式落后,健康資本存量不足,發生大病等意外事件容易造成斷崖式返貧。因此,梳理農村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貧困邊緣人口返貧的風險因素,并構建返貧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并對其進行預警,成為當前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重中之重。
一、國內貧困人口返貧風險評估研究綜述
1.關于風險評估標準的研究。在標準上,當前國內對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返貧的風險評估指標體系研究從以往單一靜態的標準轉向多維度動態的指標選取,這些指標的選取不局限于疾病因素,還強調考察脫貧戶與疾病相關的全方位社會因素。針對因病返貧的現象引入了“多維指標體系”,綜合分析了造成貧困的多重社會性因素和動態性特點,拓展了對貧困、返貧現象測量的范圍,構建了長期多維貧困指標體系。選取人均收入、健康狀況、受教育狀況、勞動能力等10個維度來計算多維貧困指數(MPI),綜合考慮脫貧戶返貧風險。防止返貧需構建一個新的貧困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對貧困問題進行全方位的評估。
2.關于風險預警機制的研究。在機制上,學術界還傾向于利用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建立因病返貧現象的預警機制,減少返貧現象產生。有學者認為應對當前因病返貧的現象進行“返貧預警機制”的構建,警源指標分為制度政策型、資源環境型、災禍風險型和能力習慣型4個準則層指標和16個具體指標。當貧困戶脫貧后,利用預警機制繼續對該戶的生產生活狀況進行追蹤,并依據上述指標體系對脫貧戶的動態信息進行監測,在返貧前進行預警干預。有學者等利用深度學習方法,計算返貧因子作為風險評估指標,推演特征空間要素與返貧率的映射關系,實現對返貧風險的評估與提前介入。
3.關于醫療保障政策執行效果的評估研究。在政策制度上,我國當前農村醫保政策主要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障制度、大病保險制度、民政醫療救助制度、健康扶貧政策等。還有部分是專門與相關企業對接開展健康產業扶貧。國內研究在上述政策框架下構建評估指標對其預防返貧效果進行評估。以貧困發生率、貧困總缺口貧困率等指標建立風險評估體系來對試點地區實施新農合初步階段緩解“健康型相對貧困”問題效果進行評估。運用健康型相對貧困緩解幅度、就醫經濟風險變化比例(RR下降幅度)作為指標體系來評價新農合健康型相對貧困的解決程度和風險共擔的實現程度。為考察我國基本醫療制度對緩解農村因病返貧的作用,陳文佼等從貧困醫療救助制度設計、經濟社會效益、醫療衛生利用情況和利用效率、制度的可持續性四個維度設計指標體系對我國貧困醫療救助制度的實行情況進行評估。
4.關于因病返貧風險理論的研究。形成因病返貧風險的研究理論框架要考慮理論與政策兩個維度。首先是學者對貧困理論的研究,貧困問題主要包含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兩個方面。所以,為了適應鄉村振興發展、推動鄉鎮企業發展,解決健康型相對貧困問題,我們的理論政策急需創新,最終目的是為構建一種“精準扶貧長效機制”,將農村扶貧的措施合理化、制度化和科學化。精準扶貧理念作為一種反貧困理論框架的提出,可以有效解釋和預防因病返貧現象。在精準扶貧理念框架下開展扶貧政策,部分地區將農村勞動力逐步轉移到企業中去,有效緩解了我國農村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返貧風險,有效推動我國農村反貧困工作。
二、國外健康型相對貧困返貧風險評估研究綜述
1.關于反貧困理論的研究。國外對貧困成因理論的研究頗多,早期國外學者傾向于將致貧現象的產生定義為經濟問題,用基本生產資料占用和經濟收入等基本生存需求指標衡量群體是否貧困。印度著名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在上世紀提出“能力貧困”的概念,他認為造成某類人群陷入貧困的原因并不是食物等商品的匱乏,而是缺少獲得達到社會平均生活條件的權利。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則從社會文化角度對貧困成因進行解釋,提出“貧困文化”理論。
2.關于返貧風險評估指標的研究。在考察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返貧問題上,國外研究者也進行了多維指標體系測量返貧風險的研究,如從人的“壽命、知識和生活水準”三個層次進行指標化的測量,并著重在“壽命”維度考察醫療對貧困的影響。用多維貧困測量方法和模型考察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返貧問題,通過分解多維貧困指標,測量每個貧困指標以判定在該指標上是否貧困。引入了“貧困脆弱性”的概念探討返貧問題,即公民受到自然社會疾病等方面的沖擊而使經濟降到貧困線下的概率。
3.關于醫療衛生政策防返貧效果的研究。這些研究主要側重于考察當地的衛生制度與醫療政策的運行情況并制定相應的健康型相對貧困風險評估指標。通過對衛生事業管理人員、醫療保險政策覆蓋率、衛生服務覆蓋率、人力資源發展和國家衛生信息系統等維度制定指標,考察因病返貧的風險率。通過從同一性、參加醫療保險的比率、醫療服務效果與預防等維度對危地馬拉的三種基本的醫療保險制度進行評估,構建評估指標。基于黎巴嫩衛生服務調查數據,運用多元回歸的方法對低收入國家醫療保障政策緩解災難性衛生支出的效用進行了定量分析。
三、研究評價
綜上所述,國內外研究者對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返貧風險的評估指標體系研究涉及廣泛,包括指標體系標準設立、預警機制建設和對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運行評估等。這些研究在各自的領域取得了矚目的研究成果,但同時也存在著需要進一步發掘之處。
1.已有研究取得的成果。目前,國內學者結合我國社會實際情況對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返貧風險的評估指標體系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其一,建立了多維、綜合的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返貧的風險評估指標體系,考察返貧現象的社會性和動態性因素;其二,利用返貧風險評估指標體系構建了一套完整的返貧預警機制,對因病返貧現象進行提前介入;其三,通過返貧風險評估指標體系來對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實施情況進行評估。國外學者也立足于本國國情,通過考察當地的衛生制度和醫療政策構建了一系列具體的返貧評估指標,這些研究很好地反映了當地醫療衛生的發展情況,能對當地的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的返貧風險進行評估,同時也對我國構建返貧風險評估指標具有借鑒意義。
2.已有研究存在的缺憾。國內學者的研究也存在問題:其一,對“因病而致貧”和“因病而返貧”這兩個現象過程的描述聚焦不夠,對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的返貧原因缺乏深入了解。其二,這些研究往往側重于某一方面,無法全面回答貧困問題形成的復雜成因。其三,在扶貧經驗政策研究上,我國扶貧政策依舊存在著“適應性問題”“精英俘獲”“懸浮扶貧”“扶貧主體單一”等缺陷,無法精準有效地解決因病貧困問題。國外研究者傾向于在本國的醫療制度下考察返貧問題,但由于體制的不同,這些研究重點是對醫療體系的評估,從企業發展等商業化角度尋找化解醫療貧困的途徑。而對構建防范農民因病返貧的有效指標的研究不多,無法反映本國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的實際特征。
四、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返貧風險評估指標體系構建
1.理論的選擇。在制定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返貧風險評估指標之前,必須先通過梳理風險理論來把握風險問題的內涵。風險存在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之中,具有廣泛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等特征,吉登斯認為,風險是一種表述可能性和潛在性的概念,是潛在并蘊含于事物發展之中。當前風險社會學界有兩大理論流派,一是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研究,二是盧曼的風險系統理論研究。雖然貝克和盧曼的風險理論都對現代性危機進行了批判,并從社會的制度結構層面指明了風險問題產生的根源,但是他們都忽略了風險問題的核心特征——資本性。資本的主體化、資本邏輯對社會生活的全面宰治,是現代性成為風險社會的具體歷史原因。所以本次風險評估指標制定在上述風險理論的指導下,再進一步結合布迪厄資本理論的內容考察這些群體的實際處境。布迪厄將社會中人們互動所使用的資本劃分為經濟、文化、社會和符號四大資本類型,具體落實到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的特征屬性上,正是醫療、經濟和教育等資本的匱乏導致其陷入返貧風險。解決貧困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對各類資本缺乏程度進行識別。因此,本文從布迪厄的資本理論出發,重點考察貧困人口的醫療健康資本,多維度綜合地構建評估指標。
2.指標體系設計的基本流程。第一,測量變量的確定。本風險評估指標在布迪厄資本理論框架基礎之上加以修改,并通過對上述文獻指標的梳理,重點測量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的醫療健康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等四個維度。第二,試調查問卷的制訂。通過制定上述需要測量的變量后,在各變量模塊之下詳設指標和題項,形成預調查問卷題項共36題,同時也構成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多維度、系統地對農民健康型相對貧困的風險做出詳盡評估。第三,調查問卷發放與收集情況。制定完成調查問卷后,采取預調查的方式,通過問卷星軟件在社交媒體發放問卷361份,問卷收集完畢后剔除廢卷、問題卷后得到有效問卷312份。最后將整理的問卷數據錄入SPSS軟件中,并對返貧風險指標的信度和效度進行分析。第四,指標信度與效度的分析。本次對調查問卷指標信度的測量采用的是SPSS22.0信度分析,并使用克朗巴哈系數法進行檢測。通過檢測,問卷中所有測量指標的Alpha值都大于0.7,即使最低值“醫療開銷”和“社會網絡”也達到了0.7548,這反映出本評估問卷的各項指標信度較高。對于指標效度的測量,本次測量采取探索性因素分析法(EFA)將問卷中復雜的變量整合為少數核心因子并對問卷題項間的相關矩陣檢測衡量工具的效度進行檢測。在EFA分析時以主成份分析和特征值大于1的條件進行因子萃取,并使用變異數最大法做直交轉軸,以達到簡化因素矩陣結構的目的并使各因素的意義更為準確。
五、基于企業參與的健康型相對貧困返貧風險防范策略
1.促進健康扶貧與農村醫療保障政策銜接。我國農村健康扶貧政策是在農村當地醫療保障基礎之上制定的,保障的對象主要為建檔立卡的貧困戶,但保障范圍之外存在著大量收入略高于貧困標準線的貧困邊緣戶以及省外就醫的貧困人口。針對保障范圍之外的貧困戶群體,預防因病返貧,政府應該將醫療保障政策與健康扶貧政策銜接起來,通過實施大病補充商業保險、大病醫療再救助和政府再救助等“補丁”政策,將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升級為“大健康扶貧”格局,從而切實緩解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返貧風險。
2.細化醫療報銷適用標準。我國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對預防因病貧困人口返貧有著積極作用,大病保險報銷制度能有效降低返貧風險。但我國目前大病報銷起付線標準一般根據當地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統一制定,這往往忽視低收入者等貧困人群的實際支付能力。所以在同一起付標準下,低收入人群更容易產生“疾病災難性支出”,陷入因病返貧的困境。因此需要對不同貧困人群的特征進行詳細評估,多維度、系統地制定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返貧風險評估指標體系。
3.擴大醫療資源供給渠道。基本醫療資源供給對防范因病貧困人口返貧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是發動民營醫院等愛心企業參與健康鄉村建設。要充分動員愛心企業,尤其是發展前景較好、對工作崗位專業性要求不高的企業參與慈善事業,積極參與第三次分配,從而夯實健康鄉村建設的資源基礎。一方面讓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另一方面豐富了農村基本醫療的資源,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二是農村醫保資金主要來源于城鄉居民醫保基金。一旦當地政府上一年資金沒有結余或者結余不足,醫保等大病保險的實施效果就會受到嚴重影響。因此,要積極和一些有能力有擔當的商業化保險企業合作,在良好的合作中既可以為企業發展提供基本的資金保障,還能為企業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塑造企業品牌發揮專業機構優勢,即堅持政府主導,商業化運營的原則,獲得穩定資金來源。這樣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推動社會發展上提供有力渠道。
4.完善基本醫療相關法律制度。要切實完善基本醫療相關法律制度,尤其要保障健康素養較弱的農民群體。一方面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運行需要相應的法律制度來保障,政府要進行分級診療法改革,通過法律等制度的安排明確各級醫療機構的職責與權限,規范基層醫療服務體系的建設;另一方面要對醫療機構的規范化運營相關法律進行完善。要積極發揮民營醫院等社會力量參與健康鄉村建設,同時也要出臺相關法律法規來規范和約束他們的醫療行為。
5.推進整體健康管理行動。整體健康管理行動要求更加關注人民的身體健康,也要關注人民的智力、情緒、精神、社交、職業和環境健康。對于收入在貧困線邊緣徘徊的身體不健康的人群要繼續加強兜底保障,避免使其因病返貧。在這個過程中要充分發揮企業的作用,在提供就業機會、提升家庭收入方面給予應有的幫助和支持,為鄉村振興提供企業支持。同時,將健康政策重點要轉移到病前的預防上,在政策上引導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對健康的重視,特別是要增加對健康、亞健康群體的健康管理,在這個過程中,鼓勵企業和相關醫院合作,為居民提供更好的健康保障。在具體推進該行動過程中要積極引入醫療企業參與,形成“政企社”分工與合作的局面,充分發揮企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動能。
在脫貧攻堅時期,主要通過提高醫療服務和超常規的醫療保障水平來解決患病農民的健康貧困問題。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反貧困政策體系具有目標上政治性、時間上的暫時性、水平上的兜底性和對象上的特殊性等特征,現階段無法防范大多數農民陷入健康相對貧困的風險。基于風險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本文構建了一套返貧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對健康型相對貧困人口的返貧風險進行評估,在評估的基礎上提出了促進健康扶貧與農村醫療保障政策銜接、細化醫療報銷適用標準、擴大醫療資源供給渠道、完善基本醫療相關法律制度、推進整體健康管理行動等防范策略。希望通過開展動態的評估,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可以提高農民的健康資本“存量”,進而提高勞動效率,實現防范與擺脫健康相對貧困困境的目標。[基金項目:安徽省社會科學創新發展研究課題攻關研究項目:安徽健康扶貧與健康鄉村建設的有機銜接及機制建設(2019CX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