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歸芍藥湯輔助治療盆腔炎性疾病后遺癥臨床觀察*
任芳穎 藺春艷 李媛媛
盆腔炎性疾病后遺癥(Sequelae of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SPID)是指發生于女性上生殖道及周圍結締組織的慢性感染性疾病,多為盆腔炎性疾病治療失當遷延而來的遺留病變,發病率4%~6%,臨床表現為小腹墜痛、腰骶酸脹、月經紊亂、帶下量多等癥狀,勞累、性生活及月經等刺激可加重病情[1]。SPID作為以增生病理改變為主的慢性炎癥,可出現盆腔腹膜的廣泛粘連、炎性包塊、輸卵管積水等變化,遠期引發不孕、異位妊娠、慢性盆腔痛等并發癥。SPID為女性婦科常見疾病,多見于性活躍期女性,其病程漫長、盆腔炎反復發作的特點嚴重影響女性生活質量。SPID的臨床治療多以抗菌藥物聯合應用殺滅病原體治療,由于存在病原體檢出率低、抗菌藥物難以滲入增生瘢痕組織內、長期應用產生耐藥性等不利因素,導致SPID總體療效欠佳。中醫理論中SPID屬“癥瘕”“帶下病”范疇,中醫婦科在整體調理臟腑、辨證施治和緩病緩治的治療原則下,采用清熱、活血、化瘀、補氣等的多種治法并舉,攻補兼施,在改善盆腔血液微循環、促進粘連吸收消散方面取得良好的治療效果[2]。本研究采用當歸芍藥湯聯合抗生素治療SPID濕熱瘀結證,觀察炎癥細胞因子及血液流變學指標的變化情況,評估其臨床療效。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2019年7月—2021年5月臨西縣人民醫院治療的SPID濕熱瘀結證患者共80例,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各40例。經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2組患者一般資料可比性良好(P>0.05)。見表1。

表1 2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例,
1.2 病例選擇標準納入標準:①符合《婦產科學》[3]中SPID相關診斷標準;②符合《中醫婦科學》[4]中慢性盆腔炎濕熱瘀結證的相關診斷和辨證標準;③年齡25~40歲。排除標準:①存在子宮內膜異位癥、子宮腺肌癥、結核性盆腔炎等盆腔疾病者;②2周內服用相關藥物或接受物理治療者;③妊娠、哺乳及備孕期女性;④存在重要臟器功能不全者。脫落標準:①依從性差,中途要求退出者;②私自加用其他治療藥物者。
1.3 方法2組患者均給予頭孢呋辛酯片(蘇州中化藥品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 H19990342)口服治療,每次0.5 g,每日2次;給予替硝唑片(浙江杭康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33020324)口服治療,每次1 g,每日1次。治療組在此基礎上給予當歸芍藥湯口服,組方:赤芍20 g,川芎、當歸、茯苓、白術各12 g,牡丹皮、瞿麥、三棱、莪術、澤瀉各6 g。每日1劑,濃煎至約200 ml,分早晚2次各100 ml溫服。2組患者均治療3周后評估療效。
1.4 觀察指標①炎癥細胞因子指標:檢測治療前后C反應蛋白(CRP)、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和白細胞介素-6(IL-6)的表達水平,均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②血液流變學指標:檢測治療前后全血黏度(高切、低切)、血漿黏度和紅細胞聚集指數等指標;③臨床療效 參考《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試行)》[5]對主要癥狀(少腹隱痛、腰骶酸脹、經行痛甚、帶下量多、胸悶納呆)進行量化評分,依嚴重程度記為0、2、4、6分,分值高代表癥狀重。擬定痊愈:癥狀及體征均消失,癥狀總積分減少≥95%;顯效:癥狀及體征明顯好轉,癥狀總積分減少≥70%且<95%;有效:癥狀及體征好轉,癥狀總積分減少≥30%且<70%;無效:癥狀及體征無好轉,癥狀總積分減少<30%。

2 結果
對照組2例因依從性差脫落,治療組1例因私自加用其他治療藥物脫落,77例患者順利完成治療。
2.1 炎癥細胞因子指標治療3周后,2組CRP、TNF-α和IL-6等炎癥細胞因子指標表達水平均較治療前明顯下降 (P<0.01),治療組低于對照組(P<0.01)。見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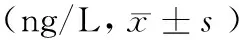
表2 2組患者炎癥細胞因子指標比較
2.2 血液流變學指標治療3周后,2組患者全血黏度(高切、低切)、血漿黏度和紅細胞聚集指數等指標均較治療前下降(P<0.01),且治療組諸指標低于對照組(P<0.01)。見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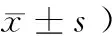
表3 2組患者血液流變學指標比較 (例,
2.3 臨床療效治療3周后,治療組治療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4。

表4 2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例,%)
3 討論
SPID是發生于女性上生殖道及周圍組織的以增生病變為主、持續時間長的慢性混合感染性疾病,長期的炎性浸潤狀態導致盆腔組織出現廣泛的粘連、增生及瘢痕形成,單純的抗菌藥物治療雖可殺滅敏感致病菌,部分改善臨床癥狀,但由于以增生為主的病理改變致盆腔血藥濃度偏低,抗生素有效利用率下降,表現為治療周期長、復發率高、病理損害吸收消散緩慢等缺點,因此單純的抗生素治療不能徹底殺滅致病菌,從根本上去除臨床癥狀[6]。及時中止炎性過度的炎癥反應和促進炎癥所致病理改變的吸收消散是SPID治療的關鍵。中醫對婦科慢性炎癥歷來有緩病緩治的觀念,采用扶正祛邪、活血化瘀、軟堅散結等多種診療思路,中藥方劑以多成分、多靶點、多途徑的協同作用方式,以高效低毒的治療特點,在SPID的治療取得良好的效果。聯合用藥是治療慢性炎癥的趨勢,在抗生素有效殺滅敏感致病菌的基礎上,輔以中藥辨證施治有助于炎癥反應的中止和增生性病理改變的吸收消散。
SPID依臨床特點歸屬中醫“癥瘕”“帶下病”范疇。婦人因攝生不慎或房事不節,濕熱之邪于胞門不閉之時乘虛而入,濕熱互結于沖任胞宮致癥瘕內生。如急性期誤治失治,或患者先天正氣不足,濕熱之邪郁積于胞宮,傷及帶脈氣血,纏綿日久不愈產生SPID諸癥。其病機為濕、熱、瘀互結,其病位為胞宮,表現為正氣已傷、濕邪留駐、邪正膠滯、病已入里等病機特點。濕熱瘀結證者濕熱與瘀血纏綿內結,帶脈失約,下焦氣機阻滯。濕毒為陰邪性趨下,易襲沖任胞宮,濕性重濁聚而成形,產生腹痛、下腹包塊等癥狀;經行或勞累耗氣傷血,正氣虛弱則病勢加重;濕邪致任脈損傷、帶脈失約,濕熱互結流注于下焦則帶下量多;熱邪消爍津液則大便秘結,小便黃赤[7]。治以清熱利濕、化瘀止痛為法。
當歸芍藥湯為東漢著名醫學家張仲景所撰《傷寒雜病論》中記載的理血劑,具有養肝血、補脾氣、利水濕之功效,是治療婦女妊娠期及婦科雜癥之中腹痛的常用方劑。方中重用赤芍瀉肝木、利陰塞以為君藥;以當歸補血止痛,以川芎活血行氣,二者共為臣藥,配以茯苓利水滲濕,澤瀉通淋消腫,白術健脾燥濕,三藥共為佐使。全方以血、氣、水為中心整體調治,方中血分用藥和氣分用藥各半,體現了肝脾兩調、血水同治的特點。本方伍以三棱活血行氣,伍以莪術破血行瘀,增強其活血行氣之功,補活血化瘀之力不足;伍以牡丹皮清熱涼血,瞿麥破血通經,以助化瘀消瘕、邪從里出。諸藥合用,化瘀滯之血、利蓄郁之濕則SPID諸證自消。炎癥的消退是多因素協同作用的結果,需多途徑聯合用藥,當歸芍藥湯由多種作用溫和的植物類藥物配伍而成,全方藥物作用廣泛,能多通道、多靶點抑制促炎細胞因子的表達,對因慢性炎癥導致的異常炎癥細胞因子表達起到調節作用,通過加速血液循環、利尿等機制將被炎癥破壞的組織和代謝廢物排出體外,通過抗擊氧自由基調節機體內環境氧化-抗氧化狀態促進受損組織的修復[8]。全方諸藥性味平和,每種藥物成分的濃度較低,能幫助機體的抗炎細胞因子調節內環境,不會因藥物濃度過高和積累干擾機體的正常代謝和全局環境。全方在扶持肝脾正氣的基礎上,培育機體自身的調節功能,促進病態臟腑的逐步恢復,體現了中醫藥調節機體生物環境治療慢性病的超前意識。
炎癥是機體對細菌、病毒等侵入或組織損傷、過敏反應等事件產生的保護性應答反應,但持續的、失控的炎癥反應可對組織產生損害,嚴重者可導致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炎癥反應的基本病理變化包括變質、滲出和增生,作為一種慢性炎癥,SPID以增生性病變為突出表現,炎癥細胞因子的異常表達代表持續炎癥反應對盆腔組織產生損害。本研究觀察所選炎癥細胞因子中CRP是全身性炎癥反應的非特異性標志物,過度表達提示存在較為嚴重的細菌感染;TNF-α過度表達會促進T細胞產生各種炎癥細胞因子,促進炎癥反應的發生和發展,加速組織的粘連與增生;IL-6在慢性炎癥反應中具有出現早、敏感度高的特點,其水平充分體現抗感染治療的效果[9]。本研究觀察到,對SPID濕熱瘀結證者給予當歸芍藥湯口服治療3周后,治療組炎癥細胞因子的水平低于對照組,說明當歸芍藥湯有效抑制了盆腔炎癥反應。血液流變學主要反映由于血液成分變化而帶來的血液流動性、凝滯性和血液黏度的變化情況。SPID患者中血液流變學指標的上升主要是由于炎癥損傷誘導趨化因子的富集,導致細胞的聚集性增加,血液的黏度隨之升高[10]。本研究觀察到,對SPID濕熱瘀結證者給予當歸芍藥湯口服治療3周后,治療組患者血液流變學指標低于對照組,說明當歸芍藥湯可明顯改善盆腔血液微循環,有助于增生性病變的吸收消散。從現代醫學角度分析,當歸芍藥湯治療SPID濕熱瘀結證的作用機制可能為:一方面通過下調炎癥細胞因子水平,改善盆腔炎性浸潤狀態,緩解臨床癥狀;另一方面,加速盆腔血液微循環,促進增生性病變的吸收消散。受條件所限,本研究納入樣本量偏少,為單中心研究,未能觀察治療的遠期療效,仍需擴大樣本量和延長隨訪時間進行臨床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