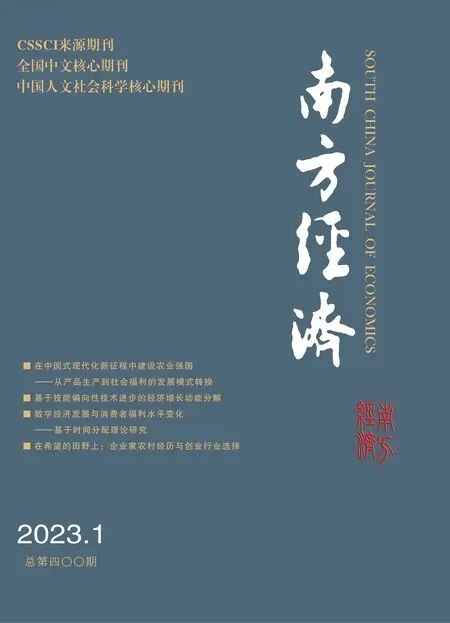基于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的經(jīng)濟(jì)增長動能分解
鄭江淮 荊 晶
一、引言
基于Solow(1956)構(gòu)建的基礎(chǔ)增長核算框架,可以將經(jīng)濟(jì)增長分解為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產(chǎn)率(TFP)貢獻(xiàn),早期的研究表明高收入國家經(jīng)濟(jì)增長的較大比例來自于TFP的增長,而中國主要依靠大量的要素投入推動經(jīng)濟(jì)增長,全要素生產(chǎn)率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有限,這種粗放型經(jīng)濟(jì)增長模式被認(rèn)為是不可持續(xù)的(Krugman,1994;Young,2003)。
中國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趨勢似乎印證了上述觀點(diǎn)。目前中國確實(shí)已進(jìn)入了經(jīng)濟(jì)增速換擋期,由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長逐步過渡至6%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并且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過程中面臨著許多新的困難,如資本回報(bào)率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地區(qū)發(fā)展結(jié)構(gòu)不平衡等問題,單純依靠要素投入驅(qū)動的粗放型經(jīng)濟(jì)增長模式難以維系。在這種背景下,黨的十九大報(bào)告指出,中國經(jīng)濟(jì)要轉(zhuǎn)向高質(zhì)量發(fā)展階段,需要轉(zhuǎn)變發(fā)展方式、優(yōu)化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轉(zhuǎn)換增長動力。那么,中國之前的經(jīng)濟(jì)增長依賴哪些動能,與其他國家相比又有什么不同,未來又能依賴哪些動能?為回答這些問題,需要進(jìn)一步對經(jīng)濟(jì)增長進(jìn)行分解,尤其需要打開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黑箱,厘清全要素生產(chǎn)率中包含了哪些動能因素,揭示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動的內(nèi)在機(jī)制以及驅(qū)動因素。
已有針對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核算的相關(guān)文獻(xiàn)大多認(rèn)可固定資本投入是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的主要?jiǎng)幽芤蛩兀谌厣a(chǎn)率在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過程中是否也是主要驅(qū)動因素方面則存在一定爭議。王小魯(2000)發(fā)現(xiàn)中國1979至1999年間全要素生產(chǎn)率平均增長率為1.46%,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率為14.9%;郭慶旺、賈俊雪(2005)估算中國1979至2004年全要素生產(chǎn)率平均增長率僅為0.891%,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率也只有9.46%;王小魯?shù)龋?009)估計(jì)中國1999至2007年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率為3.6%;白重恩、張瓊(2015)估計(jì)中國1978至2007年全要素生產(chǎn)率平均增速為3.9%,2008—2013年TFP年均增長率下降為1.8%。
也有很多文獻(xiàn)嘗試打開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黑箱。現(xiàn)有研究表明,全要素生產(chǎn)率包含了技術(shù)進(jìn)步、資源配置效率、設(shè)備使用率、規(guī)模經(jīng)濟(jì)、要素和管理質(zhì)量提升以及擴(kuò)散效應(yīng)等多種含義(Jorgenson and Griliches,1967;Maddison,1987;Aghion and Howitt,2007)。王小魯?shù)龋?009)實(shí)證發(fā)現(xiàn)中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主要來自于市場化和城市化改革,基礎(chǔ)設(shè)施改善以及人力資本效應(yīng);靳濤、陶新宇(2015)則強(qiáng)調(diào)科技進(jìn)步、城市化、對外開放、政府主導(dǎo)以及國有企業(yè)改革等對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的促進(jìn)作用;李平(2016)提出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主要來自技術(shù)進(jìn)步,技術(shù)效率改善以及結(jié)構(gòu)轉(zhuǎn)換等;張豪等(2017)發(fā)現(xiàn)中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主要來自于技術(shù)進(jìn)步,其次是規(guī)模效應(yīng);鄭江淮等(2018)提出資源再配置、全球價(jià)值鏈攀升等結(jié)構(gòu)動能是中國經(jīng)濟(jì)長期增長的重要?jiǎng)恿碓矗?008年后,人力資本以及創(chuàng)新投入等供給側(cè)動能貢獻(xiàn)不斷提高;郝大江、張榮(2018)提出要素在空間上的集聚效應(yīng)是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的長期動力;許憲春等(2020)則發(fā)現(xiàn)中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主要源于行業(yè)內(nèi)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以及行業(yè)間的勞動力再配置。
勞動力技能水平的提升也被認(rèn)為是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的重要驅(qū)動因素。Lucas(1988)發(fā)現(xiàn)教育和人力資本提高可以顯著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和技術(shù)進(jìn)步;Romer(1990)指出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進(jìn)社會整體生產(chǎn)率的提高;Fleisher et al.(2009)的實(shí)證研究也表明中國1978—2003年人力資本提高顯著提高了全要素生產(chǎn)率水平;程紅等(2016)基于中國企業(yè)-員工匹配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勞動技能結(jié)構(gòu)對企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具有較強(qiáng)的促進(jìn)作用;張勇(2020)針對中國1978—2017年的實(shí)證研究則表明中國人力資本投入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平均貢獻(xiàn)率為10.8%。
近年來,已有很多文獻(xiàn)發(fā)現(xiàn),技術(shù)進(jìn)步是有偏的,隨著技能勞動力占比的提升,技術(shù)進(jìn)步將相對提升技能勞動力的技術(shù)效率水平(Acemoglu,1998),然而目前很少有文獻(xiàn)將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因素納入經(jīng)濟(jì)增長核算框架中。
本文嘗試從供給側(cè)出發(fā),在基礎(chǔ)的增長核算框架內(nèi)引入異質(zhì)性勞動力投入以及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從而構(gòu)建一個(gè)新的經(jīng)濟(jì)增長動能分解框架,將經(jīng)濟(jì)增長分解為資本投入、勞動投入、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中性技術(shù)進(jìn)步及效率改進(jìn)等五種動能,分別計(jì)算了這五種動能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并對比了不同國家間的增長動能情況。本文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中國的經(jīng)濟(jì)增長由資本要素積累以及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共同驅(qū)動,其中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以及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是TFP增長的主要來源,而資源配置效率的變化則是導(dǎo)致全要素生產(chǎn)率波動的主要原因。
本文與現(xiàn)有文獻(xiàn)的差別及可能的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第一,本文將不同技能水平的勞動力作為直接投入的生產(chǎn)要素,而非以人力資本形式,這是因?yàn)椴煌愋蛣趧恿﹂g可能是不完全替代的,簡單的加總不能很好刻畫技能勞動投入對產(chǎn)出的實(shí)際貢獻(xiàn),同時(shí),人力資本積累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影響是非對稱的,提高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更多影響的是技能勞動力的生產(chǎn)率水平(Stokey,2021)。第二,本文考慮了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影響,不同技能水平勞動力可以使用不同的技術(shù),并且這些技術(shù)的增長率可能是不同的。第三,本文允許不同國家以及不同技能水平勞動力具有特定的技術(shù)進(jìn)步形式,并直接使用數(shù)據(jù)推得各國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形式。第四,本文在基礎(chǔ)的包含資本與勞動的C-D生產(chǎn)函數(shù)基礎(chǔ)上嵌套了一個(gè)包含異質(zhì)性勞動力投入以及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的CES函數(shù),從而將資本、低技能勞動力、高技能勞動力、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等因素均納入增長核算框架內(nèi),并且可以與現(xiàn)有增長核算文獻(xiàn)相關(guān)結(jié)果進(jìn)行比較。
本文的理論意義在于對基準(zhǔn)增長核算方法進(jìn)行了拓展,量化分析了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以及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這兩種新動能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本文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在于,通過對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的動能分解,并與其他國家相比較,揭示了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的奇跡背后,不僅僅是依靠大量的資本要素投入,技能勞動力培養(yǎng)以及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同樣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并且技能深化以及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于高收入國家而言也是重要的經(jīng)濟(jì)增長動能。本文的政策含義是在高質(zhì)量發(fā)展階段,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以及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將成為中國經(jīng)濟(jì)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的關(guān)鍵動能因素,政府要將促進(jìn)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以及技能勞動力供給側(cè)改革作為長期的發(fā)展戰(zhàn)略和政策取向。
二、文獻(xiàn)綜述
本文主要與兩類文獻(xiàn)密切相關(guān),首先是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理論。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理論的提出主要是用來解釋20世紀(jì)70年代以來發(fā)達(dá)國家的長期技能溢價(jià)現(xiàn)象(Autor et al.,1998;Acemoglu,2002)。針對中國的研究也發(fā)現(xiàn),中國同樣也存在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并且引致了技能溢價(jià)以及地區(qū)不平等問題(宋冬林等,2010;陸雪琴、文雁兵,2013;陳勇、柏喆,2018;郭凱明、羅敏,2021)。
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同樣也存在經(jīng)濟(jì)增長效應(yīng),目前大部分文獻(xiàn)都強(qiáng)調(diào)技術(shù)進(jìn)步方向與要素稟賦匹配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產(chǎn)率水平,發(fā)展中國家直接引進(jìn)、吸收和改進(jìn)發(fā)達(dá)國家的先進(jìn)技術(shù)與自身要素稟賦不匹配是導(dǎo)致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dá)國家間產(chǎn)生生產(chǎn)率差異的重要原因,因此要采用適宜性技術(shù)以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Basu and Weil,1998;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林毅夫、張鵬飛,2006;孔憲麗等,2015;余東華等,2019)。
第二類文獻(xiàn)是經(jīng)濟(jì)增長核算相關(guān)文獻(xiàn)。經(jīng)濟(jì)增長核算是基于生產(chǎn)函數(shù)對經(jīng)濟(jì)增長動力來源進(jìn)行近似分解,可以用來量化分析特定部門或新技術(shù)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進(jìn)而用來比較不同國家或部門經(jīng)濟(jì)增長表現(xiàn)的優(yōu)劣(Crafts and Woltjer,2021)。王家庭等(2019)、趙文(2021)以及李展(2022)等基于經(jīng)濟(jì)增長核算方法分析了中國勞動生產(chǎn)率增長的主要來源,他們的研究表明,資本投入以及部門間的結(jié)構(gòu)變化是中國長期以來勞動力生產(chǎn)率增長的主要驅(qū)動因素,技術(shù)進(jìn)步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正逐步提升。Cette et al.(2022)對1960至2019年30個(gè)發(fā)達(dá)國家的經(jīng)濟(jì)增長核算結(jié)果則表明,發(fā)達(dá)國家勞動生產(chǎn)率的主要增長來源是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同時(shí)資本深化以及教育同樣扮演了重要角色。
也有文獻(xiàn)進(jìn)一步分解核算了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馬洪福、郝壽義(2018)基于時(shí)變彈性生產(chǎn)函數(shù)框架,利用反事實(shí)分析方法發(fā)現(xiàn)有偏技術(shù)進(jìn)步可以通過改變要素產(chǎn)出彈性直接提高全要素生產(chǎn)率,但同時(shí)又會通過改變要素投入結(jié)構(gòu)而抑制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楊翔等(2019)運(yùn)用數(shù)據(jù)包絡(luò)分析法(DEA)度量了技術(shù)進(jìn)步的偏向性,并發(fā)現(xiàn)中國工業(yè)行業(yè)技術(shù)進(jìn)步以中性技術(shù)進(jìn)步為主,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技術(shù)進(jìn)步的貢獻(xiàn)率為12.5%。雷欽禮、徐家春(2015)、封永剛等(2017)、李小平、李小克(2018)、余東華等(2019)使用對數(shù)線性化方法展開CES生產(chǎn)函數(shù),從而對TFP增長率進(jìn)行分解,進(jìn)而得到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TFP增長率的影響,他們的研究表明資本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可以解釋中國宏觀以及大部分工業(yè)行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并且貢獻(xiàn)率是在逐年上升的。
然而現(xiàn)有研究存在三個(gè)問題,第一,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jì)增長核算框架通常將生產(chǎn)函數(shù)設(shè)定為固定產(chǎn)出彈性的C-D函數(shù)形式,而出于度量技術(shù)進(jìn)步偏向性的需要,現(xiàn)有研究中大多需要將生產(chǎn)函數(shù)設(shè)定為時(shí)變產(chǎn)出彈性生產(chǎn)函數(shù)或CES函數(shù)形式,這就使得在考慮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因素后得到的經(jīng)濟(jì)增長核算結(jié)果較難與現(xiàn)有研究結(jié)果進(jìn)行比較(Prados et al.,2021)。而本文則選擇在C-D生產(chǎn)函數(shù)基礎(chǔ)上嵌套一個(gè)包含兩種異質(zhì)性投入的CES函數(shù),使得本文分解得到的結(jié)果中既包含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中性技術(shù)進(jìn)步、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等新動能貢獻(xiàn),也包含資本、勞動投入等傳統(tǒng)動能貢獻(xiàn),從而可以與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增長核算框架下的研究結(jié)果相比較。
第二,現(xiàn)有分解核算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經(jīng)濟(jì)增長貢獻(xiàn)的文獻(xiàn)大多是對生產(chǎn)函數(shù)的不完全分解,更多強(qiáng)調(diào)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總體技術(shù)進(jìn)步或者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的貢獻(xiàn),較少提及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總體貢獻(xiàn),并且沒有與要素投入等傳統(tǒng)動能的貢獻(xiàn)進(jìn)行比較。
第三,現(xiàn)有實(shí)證研究大多著眼于資本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而在經(jīng)濟(jì)增長核算框架中考慮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的文獻(xiàn)相對較少,尤其缺少度量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貢獻(xiàn)的實(shí)證研究,本文將做出相應(yīng)補(bǔ)充,并通過跨國比較方式,指出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以及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將成為中國經(jīng)濟(jì)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的關(guān)鍵動能因素。
與本文結(jié)果密切相關(guān)的文獻(xiàn)為Rossi(2022),他們基于12個(gè)國家微觀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研究結(jié)果表明,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每提高1.11%可以促進(jìn)人均GDP提高1%。本文的實(shí)證分析結(jié)果同樣表明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可以顯著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并且本文進(jìn)一步通過增長核算方法分解得到了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及其變動趨勢。
此外,Barany and Siegel(2021)設(shè)定了一個(gè)與本文類似的增長核算框架以分析1960至2017年美國產(chǎn)品部門勞動率的驅(qū)動因素,他們的結(jié)果表明技術(shù)進(jìn)步在不同部門以及不同要素間均存在差異,而部門間生產(chǎn)率差異主要來源于技術(shù)進(jìn)步的方向以及技術(shù)進(jìn)步增長率。該結(jié)論也與本文基本結(jié)論較為相似,但本文的分析主要著眼于宏觀層面的經(jīng)濟(jì)增長動能分解,而非比較部門間經(jīng)濟(jì)增長驅(qū)動因素的差異。
三、經(jīng)濟(jì)增長動能分解框架
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jì)增長核算框架通常將生產(chǎn)函數(shù)設(shè)定為如下包含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投入的C-D函數(shù)

現(xiàn)有文獻(xiàn)在考慮勞動投入異質(zhì)性時(shí)通常是在(1)式的基礎(chǔ)上加入衡量勞動力投入質(zhì)量或人力資本的參數(shù),從而將勞動投入中的技能水平變化分離出來。而本文則將勞動要素投入分為技能勞動力和非技能勞動力兩種類型,并假定勞動產(chǎn)出為兩種異質(zhì)性勞動投入的CES函數(shù)。此外,本文還假定存在偏向性的技術(shù)進(jìn)步,從而將生產(chǎn)函數(shù)形式設(shè)定為

其中Y為最終產(chǎn)出,K、H、L分別為資本、技能勞動力和非技能勞動力投入,α和1-α分別為資本和勞動的產(chǎn)出彈性系數(shù),并且0<α<1。本文假定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間存在替代關(guān)系,替代彈性為σ>0。本文還假定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使用不同的技術(shù),技能勞動力使用的技術(shù)效率參數(shù)為非技能勞動力則為上述設(shè)定意味著技術(shù)進(jìn)步是非中性的,當(dāng)技能增強(qiáng)型技術(shù)進(jìn)步速度更快,即時(shí),技術(shù)進(jìn)步是技能偏向性的,反之則為非技能偏向性的。
如果在(2)式中不考慮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間的替代關(guān)系時(shí),本文設(shè)定的生產(chǎn)函數(shù)與傳統(tǒng)考慮勞動投入質(zhì)量或人力資本的生產(chǎn)函數(shù)是相似的,此時(shí)非技能勞動力技術(shù)效率參數(shù)的變化可看作是哈羅德中性技術(shù)進(jìn)步,而技能勞動力技術(shù)效率參數(shù)AH t的變化則包含哈羅德中性技術(shù)進(jìn)步以及人力資本積累帶來的生產(chǎn)效率提升。
對(2)式的生產(chǎn)函數(shù)兩邊取對數(shù)可得

假定Ht=?tNt,Lt=(1-?t)Nt,其中Nt為t期總的勞動力投入,?t為技能勞動力投入比例。從而可將(3)式改寫為

參照Kmenta(1967)和Thursby and Lovell(1978)對CES生產(chǎn)函數(shù)的近似方法,對函數(shù)

在f(0,0)處二階泰勒展開可得到(4)式的近似等式,并進(jìn)一步得到產(chǎn)出增長可近似分解為

與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jì)增長核算框架相比,本文的分解結(jié)果中同樣包含物質(zhì)資本投入增長貢獻(xiàn)αΔlnKt,以及勞動投入增長貢獻(xiàn)(1-α)ΔlnNt,二者可以視作經(jīng)濟(jì)增長的常規(guī)動能。因此,本文得到的分解結(jié)果可與現(xiàn)有經(jīng)濟(jì)增長核算結(jié)果相比較,區(qū)別主要在于本文對索洛余值的做出了新的分解與解釋。
在本文所使用的經(jīng)濟(jì)增長核算框架中,作為經(jīng)濟(jì)增長新動能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即索洛余值(tfp)由勞動力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中性技術(shù)進(jìn)步以及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三部分組成:

上式第一部分E1僅包含技能結(jié)構(gòu)因素,可以度量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第二部分E2中,技能增強(qiáng)型技術(shù)進(jìn)步與非技能增強(qiáng)型技術(shù)進(jìn)步的變化對兩種勞動要素的影響是中性的,因此該部分可以度量中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影響;第三部分E3中的變化會相對提高某種技能水平勞動力的生產(chǎn)率水平,即該部分中包含了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影響,同時(shí)該部分中還包含了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與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的協(xié)同效應(yīng),現(xiàn)有文獻(xiàn)大多將其獨(dú)立出來,而本文認(rèn)為,適宜性技術(shù)進(jìn)步是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研究中的一個(gè)重要領(lǐng)域,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與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的協(xié)同效應(yīng)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可以歸并于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貢獻(xiàn)之中。
與現(xiàn)有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研究相比,本文所列(6)式中并不包含資本以及勞動力投入要素,即改變要素投入大小不會影響全要素生產(chǎn)率,這與索洛余值的定義更為一致。同時(shí),本文在計(jì)算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時(shí)考慮了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之間不完全替代關(guān)系,而非簡單地計(jì)算勞動技能結(jié)構(gòu)變化,同時(shí)計(jì)算過程中僅需用到技能勞動力占比數(shù)據(jù),而無需估算人力資本投資流量以及折舊量,進(jìn)而估算得到人力資本存量數(shù)據(jù)。
四、模型設(shè)定、估計(jì)方法和數(shù)據(jù)說明
(一)估計(jì)模型設(shè)定
本文首先設(shè)定了以下實(shí)證模型以檢驗(yàn)勞動力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以及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全要素生產(chǎn)率水平是否具有提高效應(yīng),進(jìn)而驗(yàn)證本文所構(gòu)建的增長核算分解式的合理性:

其中Skilli,t是i國t時(shí)期技能結(jié)構(gòu)水平,SBTCi,t表示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水平,其計(jì)算表達(dá)式為:



此外,本文還控制了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資以及政府投入等可能會對國家全要素生產(chǎn)率水平產(chǎn)生影響的因素。同時(shí)本文在回歸中也加入了時(shí)間固定效應(yīng),以控制經(jīng)濟(jì)周期對本文回歸結(jié)果的影響。
(二)數(shù)據(jù)來源和變量說明
本文所使用數(shù)據(jù)均來自于2013版WIOD數(shù)據(jù)庫,時(shí)間跨度為1995—2009年,各變量數(shù)據(jù)處理方法如下。
增加值(Y):本文使用了WIOD數(shù)據(jù)庫提供的各國增加值數(shù)據(jù),并使用歷年增加值價(jià)格指數(shù)進(jìn)行平減。在此基礎(chǔ)上,也可以進(jìn)一步計(jì)算出歷年增加值實(shí)際增長。
資本投入(K):WIOD數(shù)據(jù)庫提供了各國歷年實(shí)際固定資本存量(1995年不變價(jià)),本文將其作為資本投入,資本投入的增長情況也由資本存量變化計(jì)算得到。
勞動力投入(N):從業(yè)人員人數(shù)和工作小時(shí)數(shù)均為常見的用來衡量勞動力投入的指標(biāo),WIOD數(shù)據(jù)庫同樣也提供了各國歷年從業(yè)人員人數(shù)數(shù)據(jù),但細(xì)分到技能勞動力和非技能勞動力投入時(shí),僅提供了從業(yè)人員工作小時(shí)數(shù)數(shù)據(jù),因此本文統(tǒng)一使用從業(yè)人員工作小時(shí)數(shù)衡量勞動力投入。
技能結(jié)構(gòu)(Skill):WIOD數(shù)據(jù)庫將勞動力分為高技能勞動力、中等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三類,本文參照Acemoglu(1998)的定義,將中等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統(tǒng)一歸類為非技能勞動力,并將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工作小時(shí)數(shù)之比作為技能結(jié)構(gòu)的代理變量。
資本報(bào)酬份額(πK):本文使用WIOD數(shù)據(jù)庫提供的資本報(bào)酬總額數(shù)據(jù)除以增加值得到了資本報(bào)酬份額。
技能勞動力報(bào)酬份額(πH)和非技能勞動力報(bào)酬份額(πL):分別使用技能勞動力和非技能勞動力在勞動報(bào)酬中所占比例乘以勞動報(bào)酬總額可以得到各類勞動力的報(bào)酬總額,再除以增加值可以得到各類勞動力在總體報(bào)酬分配中所占的份額。
利率(r)和勞動力工資(w):使用實(shí)際的資本報(bào)酬總額①統(tǒng)一使用增加值價(jià)格指數(shù)平減。除以固定資本存量可以得到資本利率,同樣使用各類勞動力的實(shí)際報(bào)酬總額除以工作小時(shí)數(shù)可以得到各類勞動力的實(shí)際小時(shí)工資。
蛋白定量采用Bradford法,波長595 nm測定蛋白濃度,用標(biāo)準(zhǔn)牛血清白蛋白繪制標(biāo)準(zhǔn)曲線,對制備樣品蛋白溶液定量。
控制變量。城市化水平(Urban)、外商投資(FDI)、政府投入(Gov)等變量數(shù)據(jù)均來自于世界銀行發(fā)展數(shù)據(jù)庫。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jì)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統(tǒng)計(jì)結(jié)果
五、實(shí)證結(jié)果及分析
(一)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估計(jì)結(jié)果
本文使用標(biāo)準(zhǔn)化供給面系統(tǒng)方程組分別估計(jì)了34個(gè)國家的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替代彈性,各參數(shù)估計(jì)結(jié)果如表2所示:

表2 替代彈性等參數(shù)估計(jì)結(jié)果
從參數(shù)回歸結(jié)果來看,各國規(guī)模報(bào)酬參數(shù)ξ均接近于1,沒有明顯的規(guī)模報(bào)酬遞增或遞減;成本加成率μ的估計(jì)結(jié)果則均接近于0,說明在考慮不同技能水平勞動力投入情況下,市場壟斷情況并不明顯。各國資本報(bào)酬份額α的估計(jì)結(jié)果則存在較大差異,大部分歐美發(fā)達(dá)國家的資本報(bào)酬份額居于0.3~0.4區(qū)間,中國等發(fā)展中國家的資本報(bào)酬份額則接近甚至大于0.5。
本文估計(jì)得到34個(gè)國家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替代彈性均值為1.77,不同國家的估計(jì)結(jié)果存在較大差異,這也意味著在做跨國比較研究中,使用統(tǒng)一的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彈性可能是不合適的,會導(dǎo)致最終結(jié)果出現(xiàn)誤差。現(xiàn)有文獻(xiàn)對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替代彈性大多居于1.4~2.0區(qū)間(Katz and Murphy,1992),本文估計(jì)得到的替代彈性均值也處于該區(qū)間。
由參數(shù)估計(jì)結(jié)果也能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國家在1995—2009年之間是呈現(xiàn)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的(γH-γL>0),但也有一部分國家技術(shù)進(jìn)步是非技能偏向性的,其中既有中低收入國家,如印尼、巴西等,也有加拿大等高收入國家。而由圖2可知,總體而言,人均GDP水平越高的國家,技術(shù)進(jìn)步越偏向于技能勞動力,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速度也越高。
中國在該時(shí)期內(nèi)的技術(shù)進(jìn)步是技能偏向性的,根據(jù)(8)式計(jì)算的技能偏向性指數(shù)SBTC的變化趨勢如圖2所示,可以看出,中國的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是相對穩(wěn)定的,尤其是在1996—2004年間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速度較快,而在2004年后技術(shù)進(jìn)步速度有所放緩。

圖2 中國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指數(shù)變動趨勢
(二)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經(jīng)濟(jì)增長回歸結(jié)果
在估算得到各參數(shù)情況下,利用(8)式可計(jì)算得到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指數(shù)(SBTC),并在此基礎(chǔ)上對(7)式的回歸方程進(jìn)步估計(jì)。本文分別使用了差分GMM(Diff-GMM)和系統(tǒng)GMM(SYS-GMM)兩種方法進(jìn)行估計(jì),具體結(jié)果如表3所示。

表3 基準(zhǔn)回歸結(jié)果
回歸結(jié)果表明,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即提高技能勞動力投入比例有助于促進(jìn)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技能勞動力生產(chǎn)效率更高,對新技術(shù)新設(shè)備的使用能力更強(qiáng),投入技能勞動力更利于企業(yè)模仿吸收前沿技術(shù),也是提升人力資本的主要方式。
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指數(shù)的回歸系數(shù)為負(fù),這與本文的預(yù)期完全相反。根據(jù)(6)式,由于各國技能勞動力占比均是不斷提高的,因此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指數(shù)對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邊際效應(yīng)正負(fù)性主要取決于替代彈性的大小,當(dāng)σ>1時(shí),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邊際效應(yīng)才會為正,反之則不然。而本文使用標(biāo)準(zhǔn)化供給面系統(tǒng)方程組估計(jì)的結(jié)果中,有多個(gè)國家的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替代彈性σ的估計(jì)值小于1,因此直接使用(8)式定義的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指數(shù)進(jìn)行回歸并不合理,需要進(jìn)一步考慮替代彈性的影響。而在考慮彈性系數(shù)影響,即使用(σ-1)/σ*ΔSBTC作為解釋變量后,回歸系數(shù)為正。這意味著,當(dāng)且僅當(dāng)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間是替代關(guān)系時(shí),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才會顯著促進(jìn)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而當(dāng)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間是互補(bǔ)關(guān)系時(shí),非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更能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這與適宜性技術(shù)進(jìn)步的結(jié)論是一致的。
控制變量方面,城鎮(zhèn)化、FDI以及政府支出等都能顯著促進(jìn)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城鎮(zhèn)化水平提高,意味著剩余勞動力從低生產(chǎn)率的農(nóng)業(yè)部門轉(zhuǎn)移至生產(chǎn)率相對更高的城市非農(nóng)部門,提升了資源配置效率,從而帶動整體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高。FDI會帶來技術(shù)溢出效應(yīng),同樣也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產(chǎn)率。政府用于基礎(chǔ)設(shè)施改善以及基礎(chǔ)科技研發(fā)活動的支出,對于提高全要素生產(chǎn)率同樣有著顯著作用。
(三)穩(wěn)健性檢驗(yàn)
本文基準(zhǔn)回歸部分的結(jié)果可能會受到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間替代關(guān)系的影響,首先是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影響可能來自于替代彈性。現(xiàn)有對資本-勞動替代彈性的研究表明,資本-勞動替代彈性會受到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影響,同時(shí)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對經(jīng)濟(jì)增長率也會產(chǎn)生正向影響,替代彈性越大,經(jīng)濟(jì)增長率越高。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替代彈性同樣也可能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以及經(jīng)濟(jì)增長率相關(guān)。
圖3給出了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與不同技能水平勞動力替代彈性的關(guān)系,從中可以發(fā)現(xiàn)大部分國家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間是替代關(guān)系,34個(gè)樣本國家中僅有11個(gè)為互補(bǔ)關(guān)系。同時(shí),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與不同技能水平勞動力替代彈性間存在一定的正向聯(lián)系,即人均GDP越高的國家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間的替代彈性通常越大,人均GDP低于20000美元(2010年不變價(jià))的國家大部分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之間均為互補(bǔ)關(guān)系,高于20000美元的國家則大部分為替代關(guān)系。但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與不同技能水平勞動力替代彈性間的這種正向聯(lián)系并不是絕對的,如中國、印度等發(fā)展中國家不同技能水平勞動力替代彈性較大,而美國、芬蘭、加拿大等發(fā)達(dá)國家勞動力替代彈性則接近于1。

圖3 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與替代彈性
同樣,由圖4可知,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間的高替代彈性并不能引致更快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速度,反之也不成立。因此,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間的替代彈性大小并不會對全要素生產(chǎn)率以及經(jīng)濟(jì)增長產(chǎn)生正向影響。

圖4 替代彈性與全要素生產(chǎn)率
其次是本文對替代彈性的估計(jì)可能存在誤差,進(jìn)而對實(shí)證結(jié)果產(chǎn)生影響。為進(jìn)一步減少替代彈性對實(shí)證結(jié)果的影響,本文考慮使用固定的替代彈性值代替供給面方程組估計(jì)得到的結(jié)果。現(xiàn)有文獻(xiàn)中大多假定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間的替代彈性為1.4或2,在這兩種情形下,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間均為替代關(guān)系,而供給面方程組估計(jì)結(jié)果顯示部分國家異質(zhì)性勞動力間是互補(bǔ)關(guān)系,因此本文也考慮了替代彈性為0.5的情形。將各國異質(zhì)性勞動力間的替代彈性固定為上述三個(gè)值后,重新計(jì)算了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指標(biāo)(SBTC),并分別使用差分GMM方法做了回歸,回歸結(jié)果如表4所示。

表4 穩(wěn)健性回歸結(jié)果
表4的回歸結(jié)果表明,當(dāng)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間替代彈性被固定為1.4或2時(shí),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回歸系數(shù)仍然顯著為正,而當(dāng)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間替代彈性被固定為0.5時(shí),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回歸系數(shù)則變?yōu)樨?fù)。這意味著,當(dāng)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間為替代關(guān)系時(shí),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可以促進(jìn)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而當(dāng)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間為互補(bǔ)關(guān)系時(shí),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則會阻礙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這與基準(zhǔn)回歸得到的結(jié)論是一致的。此外,當(dāng)將(σ-1)/σ*ΔSBTC作為解釋變量后,回歸系數(shù)始終為正,且使用不同的固定彈性值不會對系數(shù)大小產(chǎn)生影響。使用系統(tǒng)GMM方法進(jìn)行回歸后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jié)論。因此,固定彈性的估計(jì)結(jié)果不會對本文結(jié)論產(chǎn)生影響,本文實(shí)證部分的結(jié)論是穩(wěn)健的①受篇幅限制,本文在穩(wěn)健性檢驗(yàn)部分僅報(bào)告了差分GMM回歸結(jié)果,系統(tǒng)GMM回歸結(jié)果與差分GMM回歸結(jié)果基本一致,僅在系數(shù)大小以及控制變量回歸系數(shù)顯著性上略有差別,但不影響本文總體結(jié)論。。
六、各國經(jīng)濟(jì)增長動能核算及分析
在驗(yàn)證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以及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高的促進(jìn)作用基礎(chǔ)上,本文將進(jìn)一步利用經(jīng)濟(jì)增長動能分解框架計(jì)算各國經(jīng)濟(jì)增長中各類因素的貢獻(xiàn)。
使用實(shí)證部分計(jì)算得到的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指數(shù)代入(4)式可以得到

其中εt是產(chǎn)出增長減去要素投入貢獻(xiàn)、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貢獻(xiàn)以及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貢獻(xiàn)后的余值項(xiàng),包含了中性技術(shù)進(jìn)步以及資源配置效率等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影響。本節(jié)在增長分解中將中性技術(shù)進(jìn)步因素與資源配置效率合并,并使用余值項(xiàng)代替,而不是分別進(jìn)行計(jì)算,是因?yàn)榈谝唬疚闹饕菫榱朔治黾寄芙Y(jié)構(gòu)以及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影響,第二,計(jì)算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指標(biāo)SBTC時(shí)僅需使用利潤最大化一階條件,而分別計(jì)算每年技能增強(qiáng)型技術(shù)進(jìn)步率以及非技能增強(qiáng)型技術(shù)進(jìn)步率以加總得到中性技術(shù)進(jìn)步率則需要額外的假設(shè),使用標(biāo)準(zhǔn)化供給面系統(tǒng)方程組中得到的γH+γL代替則不能很好地反映中性技術(shù)進(jìn)步每年的變化情況。當(dāng)然這種處理方式并不會影響本文對于技能結(jié)構(gòu)以及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經(jīng)濟(jì)增長貢獻(xiàn)的分析。
根據(jù)(9)式可計(jì)算1995—2018年各國新舊動能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年均貢獻(xiàn)。由于2013版WIOD數(shù)據(jù)庫僅提供了1995—2009年各國不同技能水平勞動力投入以及收入數(shù)據(jù),僅使用該數(shù)據(jù)庫分析各動能對經(jīng)濟(jì)增長貢獻(xiàn)存在年限較短且時(shí)效性較差等問題。因此本文需要引入其他數(shù)據(jù)以將分析結(jié)果拓展至2018年①本文在回歸分析部分僅使用了1995至2009年樣本數(shù)據(jù),主要是因?yàn)?010至2018年數(shù)據(jù)缺失較為嚴(yán)重,需要使用插值法補(bǔ)充數(shù)據(jù),數(shù)據(jù)質(zhì)量相對較差。同時(shí)當(dāng)將樣本數(shù)據(jù)拓展到2018年時(shí),得到的是一個(gè)長面板數(shù)據(jù),此時(shí)兩階段GMM回歸估計(jì)是無效的。而在動能分解分析部分為了能保證分析具有時(shí)效性,將樣本數(shù)據(jù)拓展至2018年是有必要的,而且使用插值法并不會改變總體的動能貢獻(xiàn)變動趨勢。當(dāng)然本文在使用14個(gè)國家2010至2018年面板數(shù)據(jù)的回歸結(jié)果與本文回歸分析部分結(jié)果基本是一致的,因此回歸分析部分的樣本年份選擇并不會改變本文的基本結(jié)論。,新的數(shù)據(jù)來源及處理方法如下。
固定資本投入:世界銀行發(fā)展數(shù)據(jù)庫(WDI)提供了各國歷年實(shí)際固定資本形成額(2010年不變價(jià)),本文將折舊率統(tǒng)一設(shè)定為4%,并在此基礎(chǔ)上采用永續(xù)存盤法計(jì)算了固定資本存量。該數(shù)據(jù)庫中僅提供了2010年中國實(shí)際固定資本形成額,其他年份數(shù)據(jù)來自歷年中國統(tǒng)計(jì)年鑒,并以2010年為基期使用歷年固定資產(chǎn)投資價(jià)格指數(shù)進(jìn)行平減。
勞動投入:世界銀行發(fā)展數(shù)據(jù)庫(WDI)提供了各國勞動力規(guī)模以及國家層面估計(jì)的失業(yè)率數(shù)據(jù),在此基礎(chǔ)上,本文計(jì)算得到實(shí)際投入的勞動力規(guī)模。
技能勞動力投入:世界銀行發(fā)展數(shù)據(jù)庫(WDI)并未提供勞動力投入中技能勞動力比例數(shù)據(jù),參照Barro and Lee(1993,2013),本文采用25歲人口中至少接受過短期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指標(biāo)作為代替。該指標(biāo)存在數(shù)據(jù)缺失的情況,本文使用2013版WIOD數(shù)據(jù)庫補(bǔ)充了1995—2009年的缺失數(shù)據(jù),由于WIOD數(shù)據(jù)庫中報(bào)告的技能勞動力投入為投入時(shí)間,而世界銀行發(fā)展數(shù)據(jù)庫僅提供了技能勞動力人數(shù)比例,因此在補(bǔ)充數(shù)據(jù)過程中需要先根據(jù)現(xiàn)有數(shù)據(jù)估算兩個(gè)數(shù)據(jù)庫中指標(biāo)間的比例關(guān)系,再對數(shù)據(jù)進(jìn)行調(diào)整補(bǔ)充。2010年及之后的缺失數(shù)據(jù)則使用插值法進(jìn)行補(bǔ)充。中國的技能勞動力投入數(shù)據(jù)則來使用歷年勞動統(tǒng)計(jì)年鑒提供的大專及以上勞動力投入比例指標(biāo),部分缺失年份數(shù)據(jù)同樣使用插值法進(jìn)行補(bǔ)充。
技能溢價(jià):根據(jù)WIOD數(shù)據(jù)庫相關(guān)指標(biāo)可計(jì)算得到1995—2009年各國技能溢價(jià)水平。而OECD數(shù)據(jù)庫提供了部分OECD國家2010—2018年受過不同教育的勞動力的平均工資水平,本文首先根據(jù)WIOD數(shù)據(jù)庫中的相關(guān)指標(biāo)計(jì)算得到各國低技能勞動力與中等技能勞動力投入比例,進(jìn)而計(jì)算各國2010—2018年中等及以下技能水平勞動力的平均工資(低技能勞動力比例*低技能勞動力平均工資水平+中等技能勞動力比例*中等技能勞動力平均工資水平),最后在此基礎(chǔ)上可計(jì)算得到技能溢價(jià)水平(高技能勞動力平均工資/中等及以下技能水平勞動力平均工資)。中國1995—2009年技能溢價(jià)數(shù)據(jù)同樣來自于WIOD數(shù)據(jù)庫,2011年及2015年技能溢價(jià)數(shù)據(jù)則根據(jù)中國健康與營養(yǎng)調(diào)查(CHNS)提供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計(jì)算得到,其余年份使用插值法進(jìn)行補(bǔ)充。
受到數(shù)據(jù)可得性限制,本文僅計(jì)算得到14個(gè)國家1995—2018年各動能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情況②其余國家則可以利用WIOD數(shù)據(jù)庫提供的數(shù)據(jù)分解得到1995至2009年各動能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受篇幅限制,本文未列出相關(guān)結(jié)果。,其均值如表5所示。

表5 1995至2018年14個(gè)國家經(jīng)濟(jì)增長動能分解結(jié)果
典型事實(shí)一:資本投入增長是各國經(jīng)濟(jì)增長主要的動力來源之一,高收入國家資本投入增長主要來自于內(nèi)生資本積累,中低收入國家則主要來自額外資本投入。
中國1995至2018年GDP年均增長率為8.68%,其中資本投入增長年均貢獻(xiàn)為5.35%,貢獻(xiàn)率達(dá)到了61.64%,是經(jīng)濟(jì)增長的最主要驅(qū)動因素。本文動能分解所使用的樣本中另一個(gè)處于中低收入階段的國家,墨西哥GDP年均增長率為2.68%,其中資本投入增長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率是達(dá)到了99.08%,即墨西哥在1995至2018年的經(jīng)濟(jì)增長幾乎完全可以用資本投入增長來解釋。高收入國家中資本投入增長貢獻(xiàn)率則相對較低,其中美國資本投入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率為46.99%,其他國家的資本投入增長貢獻(xiàn)率則在30%左右。
進(jìn)一步考慮固定資本投入增長的機(jī)制,在索洛經(jīng)濟(jì)增長模型中,當(dāng)經(jīng)濟(jì)體處于均衡增長路徑上,人均資本增長率等于外生的技術(shù)進(jìn)步速度,從而可以得到均衡增長路徑上固定資本增長率為ΔlnK*=ΔlnL+tfp。因此,固定資本投入增長可以分為均衡增長路徑上勞動力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引致的固定資本積累,以及向均衡增長路徑轉(zhuǎn)移過程中額外的固定資本積累三個(gè)部分。通過進(jìn)一步分解可以發(fā)現(xiàn),中低收入國家資本投入增長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更多是來源于向均衡增長路徑轉(zhuǎn)移過程中額外的固定資本積累,而高收入國家資本投入增長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則更多來源于均衡增長路徑上技術(shù)進(jìn)步引致的固定資本積累。
如圖5所示,從資本投入貢獻(xiàn)變動趨勢來看,固定資本投入增長在大部分年份都是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的主要來源,其變動趨勢可以大致分為四個(gè)階段。第一階段,1995至2000年間,固定資本投入增長對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貢獻(xiàn)持續(xù)下降,由1996年的5.64%降至2000年的4.48%;第二階段,2000年至2004年固定資本投入增長貢獻(xiàn)快速增大,并在2004年達(dá)到了5.87%;第三階段,2004年至2010年,資本投入貢獻(xiàn)在緩慢增長,2010年時(shí)達(dá)到6.55%;第四階段,2010年至2018年,資本投入貢獻(xiàn)快速下降,2018年資本投入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僅為4.36%。而通過對固定資本投入貢獻(xiàn)再分解可以發(fā)現(xiàn),2000年至2007年固定資本投入增長主要來源于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引致的固定資本內(nèi)生積累增加,而在2008年后,中國政府大幅增加了公共投資,導(dǎo)致額外固定資本投入大幅增長,對經(jīng)濟(jì)增長貢獻(xiàn)也大幅提高。然而額外資本投入并不具有持續(xù)性,其在2010后的持續(xù)下降也是導(dǎo)致資本投入貢獻(xiàn)快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圖5 資本投入貢獻(xiàn)變動趨勢
其他各國資本投入貢獻(xiàn)變動趨勢與中國存在較大差異。其中墨西哥的資本投入貢獻(xiàn)在1995至2000年間是在不斷提高的,但2000年后的大部分年份中資本投入貢獻(xiàn)都是在減少的,有效資本投入不足也是其經(jīng)濟(jì)增長速度下滑,遲遲沒有跨過中等收入階段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及其他部分OECD高收入國家的資本投入貢獻(xiàn)則在2007年經(jīng)濟(jì)危機(jī)沖擊后出現(xiàn)下滑態(tài)勢,隨后在2010年前后恢復(fù)增長。
典型事實(shí)二:全要素生產(chǎn)率是經(jīng)濟(jì)增長的另一個(gè)主要來源,TFP快速提升是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速度高于其他中低收入國家的主要原因。
根據(jù)本文計(jì)算結(jié)果,中國1995至2018年全要素生產(chǎn)率平均增長率為3.10%,即使在不考慮技術(shù)進(jìn)步對資本積累的內(nèi)生促進(jìn)作用情況下,TFP增長對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的年均貢獻(xiàn)率也達(dá)到35.66%。美國及其他高收入國家中,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也在經(jīng)濟(jì)增長過程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其貢獻(xiàn)率也普遍高于30%。與之相對應(yīng)的,墨西哥全要素生產(chǎn)率呈現(xiàn)負(fù)增長態(tài)勢,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平均貢獻(xiàn)率為-28.63%,是其無法走出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重要原因。
本文計(jì)算得到的各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對經(jīng)濟(jì)增長貢獻(xiàn)的變動趨勢如圖8所示。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對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僅次于固定資本投入增長,其變動趨勢可以大致分為五個(gè)階段。第一階段,1995年至2000年間,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對經(jīng)濟(jì)增長貢獻(xiàn)緩慢下降;第二階段,2000年至2004年間,全要素生產(chǎn)率緩慢提升;第三階段,2004至2007年間,全要素生產(chǎn)率快速提升,并且其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在2006年以及2007年分別達(dá)到6.06%以及7.15%,超過了資本投入增長貢獻(xiàn);第四階段,2007至2012年,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對經(jīng)濟(jì)增長貢獻(xiàn)快速下降,在2012年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貢獻(xiàn)僅為1.58%,是本文樣本期內(nèi)最低水平;第五階段,2012年以后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對經(jīng)濟(jì)增長貢獻(xiàn)緩慢增加,并在2018年達(dá)到了2.21%。

圖8 TFP增長貢獻(xiàn)變動趨勢
典型事實(shí)三: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是中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的主要驅(qū)動力,并且仍有較大潛力。
根據(jù)本文的計(jì)算結(jié)果,1995至2018年間,中國的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年均貢獻(xiàn)為2.78%,貢獻(xiàn)率為32.04%,是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的主要驅(qū)動力。1995至2004年,中國技能勞動力占比由2.30%快速提升至7.23%,對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以及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較大;2005至2008年間,中國技能勞動力占比總體變化不大,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也相對較小;2009至2017年間,中國技能勞動力占比再次快速提升,由7.43%提升至19.1%;而在2017年后,中國技能勞動力占比提升速度再度放緩。總體而言,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是中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保持較高提升速度的重要因素,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相對穩(wěn)定。
墨西哥1995年技能勞動力占比為12.39%,遠(yuǎn)高于中國同期水平,但在樣本期間內(nèi),墨西哥技能勞動力占比提升緩慢,2018年時(shí)僅達(dá)到16.45%,已經(jīng)低于中國同期水平。較為緩慢的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速度拉低了墨西哥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速度,進(jìn)而影響了墨西哥的經(jīng)濟(jì)增長速度。因此,持續(xù)穩(wěn)定的技能勞動力培養(yǎng)是中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速度遠(yuǎn)高于其他中低收入國家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中國在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方面仍具有較大潛力,盡管在1995至2018年間中國技能勞動力占比提升速度遠(yuǎn)高于其他國家,但是與高收入國家相比仍然有較大差距。2018年美國技能勞動力占比已經(jīng)達(dá)到了45.17%,本文樣本中的其他12個(gè)OECD國家技能勞動力平均占比也達(dá)到34.09%,均遠(yuǎn)高于中國,未來中國仍然可以通過加快技能勞動力培養(yǎng)帶動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并進(jìn)一步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
典型事實(shí)四: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是中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的另一個(gè)主要來源。
1995至2018年間,中國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年均貢獻(xiàn)為1.85%,貢獻(xiàn)率為21.27%,略低于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但仍然是樣本時(shí)期內(nèi)中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主要來源之一。如圖11所示,從歷年分解結(jié)果來看,中國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對經(jīng)濟(jì)增長貢獻(xiàn)的變動趨勢與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貢獻(xiàn)的變動趨勢基本一致,說明中國的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是適宜的。

圖1 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與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

圖11 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貢獻(xiàn)變動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在樣本期間內(nèi),美國技能勞動力占比增長較為緩慢,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平均每年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0.16%。而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平均每年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0.61%,可以解釋美國樣本期間內(nèi)大部分TFP增長,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總體貢獻(xiàn)也僅次于資本投入。因此,當(dāng)技能勞動力占比提升速度放緩時(shí),進(jìn)一步促進(jìn)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將成為促進(jìn)TFP持續(xù)增長的關(guān)鍵。
同時(shí)也可以發(fā)現(xiàn),對于本文樣本中的大部分高收入國家而言,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以及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均可以解釋大部分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不同的是,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過程中,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以及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均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美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主要來自于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而其他11個(gè)OECD國家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平均而言則主要來自于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
典型事實(shí)五: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過程中存在著效率損失,阻礙了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以及經(jīng)濟(jì)增長。
本文的動能分解結(jié)果表明,在樣本期內(nèi)的大部分年份中,中國都存在效率損失。總體而言,中性技術(shù)進(jìn)步及效率改進(jìn)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年均貢獻(xiàn)為-1.53%,貢獻(xiàn)率為-17.65%。從變動趨勢來看,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對外開放紅利逐步改善了中國的資源配置效率,中性技術(shù)進(jìn)步及效率改進(jìn)等因素在2004至2007年推動了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部分年份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甚至超過了技能結(jié)構(gòu)優(yōu)化以及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貢獻(xiàn)之和。然而在2008年之后,政府部門對基礎(chǔ)設(shè)施以及房地產(chǎn)等行業(yè)的額外投資導(dǎo)致資源配置效率惡化,阻礙了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也是導(dǎo)致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對經(jīng)濟(jì)增長貢獻(xiàn)快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資源配置效率的變化是中國全要素生產(chǎn)率波動的重要因素。
而從其他國家中性技術(shù)進(jìn)步及效率改進(jìn)變動趨勢來看,受經(jīng)濟(jì)危機(jī)沖擊影響,美國及其他11個(gè)OECD國家中性技術(shù)進(jìn)步及效率改進(jìn)對經(jīng)濟(jì)增長貢獻(xiàn)在2007年出現(xiàn)了大幅下滑,并在2010年后逐步恢復(fù),這與全要素生產(chǎn)率波動趨勢基本是一致的。因此,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波動主要受資源配置效率變化影響。

圖6 內(nèi)生資本積累貢獻(xiàn)變動趨勢

圖7 額外資本投入貢獻(xiàn)變動趨勢

圖9 技能勞動力占比變動趨勢

圖10 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貢獻(xiàn)變動趨勢

圖12 中性技術(shù)進(jìn)步及效率改進(jìn)貢獻(xiàn)變動趨勢
七、結(jié)論
本文從供給側(cè)出發(fā),將經(jīng)濟(jì)增長分解為資本、勞動這兩種要素投入為代表的舊動能,以及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中性技術(shù)進(jìn)步、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等新動能,并計(jì)算了1995至2018年14個(gè)國家各動能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本文的結(jié)果表明,第一,1995至2018年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主要依靠固定資本投入以及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共同驅(qū)動,其中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的主要來源為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以及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年均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2.78個(gè)百分點(diǎn),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率為32.04%,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年均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1.85個(gè)百分點(diǎn),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率為21.27%。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以及技能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同樣也是高收入國家經(jīng)濟(jì)增長的主要?jiǎng)幽埽^為緩慢的技能勞動力投入占比提升速度以及與自身要素稟賦不相匹配的偏向性技術(shù)進(jìn)步則是導(dǎo)致墨西哥等中低收入國家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緩慢,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基于以上結(jié)論,本文得出了以下促進(jìn)中國未來經(jīng)濟(jì)增長的啟示。第一,中國仍需保持較高的固定資本投資增長速度。盡管在高質(zhì)量發(fā)展階段,需要轉(zhuǎn)變以往依靠要素投入驅(qū)動經(jīng)濟(jì)增長的方式,但這并不意味著固定資本投資不再重要。當(dāng)然高質(zhì)量發(fā)展階段的固定資本投資應(yīng)更多為與新模式、新業(yè)態(tài)、新技術(shù)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的使用相關(guān)的新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以及新機(jī)器投資,從而持續(xù)推動經(jīng)濟(jì)增長。第二,中國需要進(jìn)一步培養(yǎng)技能勞動力隊(duì)伍,以應(yīng)對可能的老齡化問題。通過培養(yǎng)技能勞動力隊(duì)伍,提高技能深化程度,將“人口紅利”轉(zhuǎn)化為“技能紅利”,進(jìn)而持續(xù)推動經(jīng)濟(jì)增長。目前中國勞動力中技能勞動力比例與高收入國家間存在較大差距,技能結(jié)構(gòu)深化仍有很大潛力。第三,創(chuàng)新驅(qū)動對中國經(jīng)濟(jì)未來發(fā)展十分重要,需要保持較快的技術(shù)進(jìn)步速度。技術(shù)進(jìn)步是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高的主要來源,可以持續(xù)推動經(jīng)濟(jì)增長。由于資本收益遞減效應(yīng)的存在,未來固定資本投資增長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將不可避免地下降,此時(shí)需要較高的技術(shù)進(jìn)步速度以維持經(jīng)濟(jì)的中高速增長。
當(dāng)然,本文還存在很大改進(jìn)余地。首先是本文并未擺脫傳統(tǒng)的Solow增長核算框架,主要分解了供給端的要素投入以及技術(shù)進(jìn)步等動能,而并未考慮需求端動能,以及結(jié)構(gòu)轉(zhuǎn)換紅利等同樣會帶來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的動能。其次,本文并未考慮各動能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而僅僅核算了各動能變化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貢獻(xiàn)。最后,限于生產(chǎn)函數(shù)估計(jì)方法以及樣本期較短問題,本文并未考慮不同時(shí)期替代彈性的變化,也可能對具體核算結(jié)果造成影響。
- 南方經(jīng)濟(jì)的其它文章
- 在中國式現(xiàn)代化新征程中建設(shè)農(nóng)業(yè)強(qiáng)國
——從產(chǎn)品生產(chǎn)到社會福利的發(fā)展模式轉(zhuǎn)換 - 農(nóng)業(yè)社會化服務(wù)有助于提升農(nóng)業(yè)綠色生產(chǎn)率嗎?
- 創(chuàng)業(yè)者調(diào)節(jié)焦點(diǎn)、組織間信任與新企業(yè)資源識取
——有調(diào)節(jié)的中介效應(yīng) - 在希望的田野上:企業(yè)家農(nóng)村經(jīng)歷與創(chuàng)業(yè)行業(yè)選擇
- 數(shù)字經(jīng)濟(jì)、服務(wù)業(yè)效率提升與中國經(jīng)濟(jì)高質(zhì)量發(fā)展
- 數(shù)字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消費(fèi)者福利水平變化
——基于時(shí)間分配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