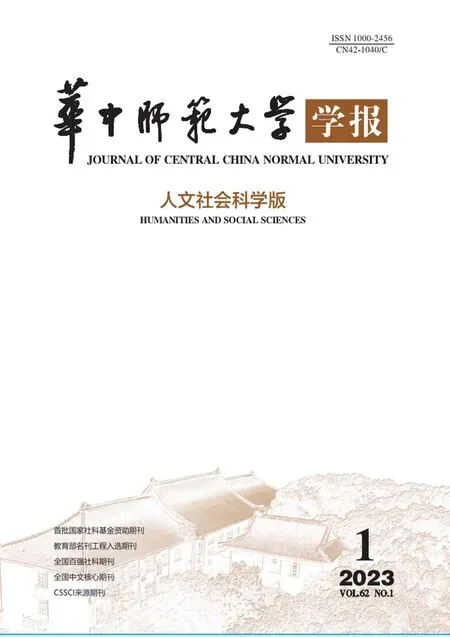影響焦慮、學科地位與空間競爭
——布爾迪厄對阿爾都塞主義的持久敵視
李鈞鵬 許松影
(華中師范大學 社會學院、湖北省社會發展與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湖北 武漢 430079)
導言:“只有不懷好意……”
每隔一段時間,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與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在思想上的關系問題就會浮現出來。布爾迪厄究竟是阿爾都塞主義者,還是反阿爾都塞主義者?這一問題近乎粗暴,其意義卻頗不平凡。“阿爾都塞主義”(l’althussérisme)(1)雖然阿爾都塞的部分追隨者反對“阿爾都塞主義”這種說法(參見James H. Kavanagh, Thomas E. Lewis, Etienne Balibar and Pierre Macherey, “Interview: Etienne Balibar and Pierre Macherey,” Diacritics, vol.12, no. 1, 1982, pp.46-51.),但這種表述在布爾迪厄的著述中屢有出現,主要是指阿爾都塞及其合作者所持有的理論主張和政治立場。濃縮了馬克思主義和結構主義這兩層含義,在當前的社會理論體系中基本等同于完全忽視行動者的極端結構主義。因此,布爾迪厄社會學與阿爾都塞主義的關系,可以說就是布爾迪厄社會學與決定論和結構主義的關系。布爾迪厄本人曾明言:“只有不懷好意或不知情者才會把我置于‘結構主義者’的行列中。”(2)皮埃爾·布爾迪厄:《自我分析綱要》,劉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79頁。不僅如此,為了將自身立場與阿爾都塞主義區分開來,布爾迪厄多次從理論著手,指控作為極端結構主義的阿爾都塞主義把行動者還原為結構的附帶現象或者承載物(3)參見皮埃爾·布爾迪厄:《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劉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353頁;皮耶·布赫迪厄:《所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會學文集》,陳逸淳譯,臺北: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36、54頁;Pierre Bourdieu, Jean-Claude Chamboredon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1, p.252; Pierre Bourdieu,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Literary Fie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79; Pierre Bourdieu,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9—1992, Cambridge: Polity, 2014, p.6,p.96,p.114; 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6, pp.168-169,p.234,p.445,p.500; Pierre Bourdieu, Manet: A Symbolic Revolu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98—2000, Cambridge: Polity, 2017, p.178; Pierre Bourdieu, Anthropologie économ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92—1993,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7, p.21,p.140; Pierre Bourdieu, Habitus and Field: General Sociology, Volume 2,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1982-1983, Cambridge: Polity, 2020, p.79.。然而,數十年來,對布爾迪厄的自我聲明有意無意視而不見的研究層出不窮,或新或舊的觀點一再浮現,而這些觀點所引發的紛爭也從未停歇。布爾迪厄在超過30年的時間里持久地敵視阿爾都塞主義,但學術界卻不斷發現他的社會學思想與阿爾都塞主義的相似之處。既然如此,我們就需要解釋以下問題:其一,如果布爾迪厄與阿爾都塞主義在理論上有異曲同工之妙,布爾迪厄為什么對阿爾都塞主義抱有強烈批判態度?其二,除了思想和理論層面的區分,布爾迪厄對阿爾都塞主義還提出了哪些指責?各種指責又出自何種原因?
在布爾迪厄與阿爾都塞主義的關系問題上,既有研究不約而同地采用了內部主義視角,只關注理論層面的相似和差異。然而,這種內部主義視角不僅忽視了社會背景和學術潮流,更徹底無視行動者的現實特征(4)參見Charles Camic and Neil Gross, “The New Sociology of Ideas,” in Judith R. Blau,ed.,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ology, Malden: Blackwell, 2001, pp.236-249.,特別是布爾迪厄的個人情感和習性——不應忘記,與學術思想一樣,學術批評同樣有具體的社會背景和個人特色(5)參見Anne Warfield Rawls, “The Wartime Narrative in US Sociology, 1940—1947,”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21, no. 4, 2018, pp.526-546.。本文從關注社會背景且行動邏輯多元化的多維理論視角出發,論證布爾迪厄并非沒有意識到他與阿爾都塞主義的理論相似性;而布爾迪厄之所以持久敵視阿爾都塞主義,除理論上的分歧外,更重要的是影響焦慮、學科地位抗爭和學術空間競爭等情感性和功利性原因。
本文主體內容包括以下五個部分:第一,梳理討論布爾迪厄社會學與阿爾都塞主義之間關系這一問題的既有文獻,從問題和方法兩個角度說明現有研究的進展,并在既有理論基礎上提出一種解釋學術評價的行動理論框架,明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目標;第二,利用一手和二手材料,呈現阿爾都塞學派成員(主要是阿爾都塞本人)與布爾迪厄的生平與交往等內容;第三,概述布爾迪厄與阿爾都塞主義的理論相似之處,并說明評論界將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等同于阿爾都塞式馬克思主義的做法,在此基礎上,指出布爾迪厄在呈現阿爾都塞思想時表現出“影響焦慮”的諸多特征;第四,說明20世紀法國的哲學和社會學的代際演變與相互關系,指出布爾迪厄不僅對哲學或純理論研究的支配地位極為敏感,而且在積極對抗哲學對社會學的支配姿態的意圖下,指認阿爾都塞思想為“認識論貴族主義”,將阿爾都塞視為哲人王,從而提出一種道德和政治指控;第五,概括20世紀60—70年代法國學術場域中布爾迪厄社會學和阿爾都塞式馬克思主義的競爭關系,闡述阿爾都塞學派重要成員對社會學和布爾迪厄社會學的批評,辨認出布爾迪厄的四種回應。最后,總結全文主要內容,說明擺脫純粹內部主義、構建多維理論視角對學術評價研究的必要性。
有必要說明,本文完全無意于否認布爾迪厄社會學的原創性,更無意從道德角度貶低和指責布爾迪厄。換言之,目前這項研究并非意在反駁布爾迪厄對阿爾都塞的諸多定位和批判,而是希望以更加完整的方式理解布爾迪厄對阿爾都塞主義的持久敵視。
一、理解學術評價:從內部主義到多維視角
考察布爾迪厄與阿爾都塞主義關系的研究最早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此后盡管文獻層出不窮,核心思路卻都是關注理論分歧的內部主義,因而基本觀點也只有兩種。然而,從學術評價研究的角度看,要理解布爾迪厄對阿爾都塞主義的持久敵視,應當采取更多關注社會化的行動者和歷史背景的外部主義視角。
(一)既有研究的內部主義視角及其問題
20世紀70年代,也就是布爾迪厄剛剛成名的時候,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便注意到布爾迪厄與阿爾都塞兩人思想的相似性,認為他們都持有專家掌握特殊真理并有權指導大眾的知識和政治觀點(6)參見Jacques Rancière, The Philosopher and His Poo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80年代,呂克·費里(Luc Ferry)和阿倫·雷諾(Alain Renaut)舍棄阿爾都塞,直接將布爾迪厄視為馬克思主義的代表,并且聲稱布爾迪厄與阿爾都塞的差別只是表達的公開與否而已(7)參見Luc Ferry and Alain Renaut, 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 An Essay on Antihumanis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0, p.162.。90年代,杰弗里·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更加明確地指出布爾迪厄思想發展中的“阿爾都塞主義階段”(8)杰夫瑞·亞歷山大:《世紀末社會理論》,張旅平、霍桂恒、渠敬東、應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3-304頁。。世紀之交,珍妮·維迪-勒魯(Jeannine Verdés-Leroux)公開斥責布爾迪厄像包括阿爾都塞在內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扮演了模糊和蒙蔽他人頭腦的角色”(9)Jeannine Verdés-Leroux, Deconstructing Pierre Bourdieu: Against Sociological Terrorism from the Left, New York: Algora, 2001, p.264.。同期,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承認布爾迪厄在提供答案上的原創性,卻堅稱他共享了阿爾都塞等結構主義者的主題,即“人類注定會成為支配結構的囚徒”(10)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社會理論思想史導論》,簡守邦譯,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404頁。。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盡管理解布爾迪厄對“機器”(apparatuses)概念所內含的功能主義觀的不滿,但依舊認為他有關教育制度等分類“機器”(machine)的研究,與阿爾都塞的觀點不存在本質差異(11)參見Jacques Bidet, “Bourdieu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Jacques Bidet and Stathis Kouvelakis, eds., Critical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Marxism, Leiden: Brill, 2008, pp.587-603.。在第二個十年,研究者的觀點更加慎重。例如,布萊恩·特納(Bryan Turner)認為,布爾迪厄有關宗教的看法同時有賴于韋伯和阿爾都塞的主張,也就是后者有關意識形態的看法。然而,他同時又認為,這并不表示布爾迪厄繼承了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而只是說明布爾迪厄的宗教解讀(以及更為重要的習性概念)和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存在“分析上的相似性”(analytical similarity)(12)Bryan S.Turner, “Pierre 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in Simon Susen and Bryan S. Turner, eds., The Legacy of Pierre Bourdieu: Critical Essays, London: Anthem, 2011, p.228, pp.231-232.。近來,迪迪埃·埃里蓬(Didder Eribon)也在其暢銷著作《回歸故里》中指出:“布爾迪厄批評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概念……不能否認,阿爾都塞的理論將我們帶至一出老舊的馬克思主義戲劇(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出老舊的論戰)臺上,各種社會實體就像演出戲劇(純粹是學術性的)一般互相對峙。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布爾迪厄的一些表達方式驚人地與他自己極力避免使用的概念非常接近”(13)迪迪埃·埃里蓬:《回歸故里》,王獻譯,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84頁。。此外,在階級、國家、再生產等問題上,認為布爾迪厄與阿爾都塞觀點一致的看法仍舊不斷出現(14)參見Julien Pallotta, “Bourdieu’s Engagement with Althusserian Marxism: The Question of the State,” Actuel Marx, vol. 58, no. 2, 2015, pp.130-143; Julien Pallotta, “Le moment 1970 sur la reproduction: Althusser et Bourdieu,” Actuel Marx, vol. 70, no. 2, 2021, pp.96-110; Dylan Riley, “Bourdieu’s Class Theory: The Academic as Revolutionary,” Catalyst, vol. 1, no. 2, 2017, pp.107-136; Michael Burawoy,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Marx Meets Bourdieu,” in Thomas Medvetz and Jeffrey J. Sallaz,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ierre Bourdieu,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466; Robert Dingwall,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Edition,” in Jean Peneff and Howard S. Becker, eds., Sociology and Music in the Chicago School, London: Routledge, 2018, p.xx.。

作為布爾迪厄的學生,讓-路易·法比亞尼(Jean-Louis Fabiani)做出如下斷言:“與一般保守派批評相左的是,布爾迪厄不曾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本人也從不隱瞞這一點。”(23)讓-路易·法比亞尼:《布爾迪厄傳》,陳秀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第59頁。就資本概念而言,布爾迪厄的資本理論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擴展”;就教育論題而言,阿爾都塞主義者實際上批評《再生產》一書對階級強調不夠;在文化理論上,“馬克思主義學派學者很早就發展出一套文化理論,其基礎,早已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得清清楚楚。他們并不需要吸收布爾迪厄。他們的裝備已經相當充實,甚至,用以解析這繁復的人間社會也已綽綽有余”。因此,“布爾迪厄的研究計劃并非為了改革馬克思主義,亦非為了將之延伸到社會整體,而是以另一套整體理論來代替馬克思學說”(24)讓-路易·法比亞尼:《布爾迪厄傳》,第61-68、70-71、76頁。。
整體來看,盡管維迪-勒魯和法比亞尼的某些論述超出了理論范圍(25)參見讓-路易·法比亞尼:《布爾迪厄傳》,第3-4頁;Jeannine Verdés-Leroux, Deconstructing Pierre Bourdieu: Against Sociological Terrorism from the Left, p.264.,但既有研究無不遵循學術評價的內部主義視角。這種視角認為,一位思想家對另一位思想家的評價只能出自理論內部,也就是說,學術評價只是遵循一套既有的或清晰或模糊的理論衡量標準。因此,只要思想家嚴格界定概念內涵并且遵守邏輯規則,這些二元范疇總能有效地衡量待評價思想,區分開不同的思想,其結果并不因使用者的不同而不同。而后續的研究者通過同一套衡量標準,也就能夠重現思想家自身的評判結果。
(二)基于DBO理論的修正模型:一種解釋學術評價的多維視角
誠然,學術評價,亦即學術從業者用一套標準來衡量其他思想并做出定性和定位等判斷,作為社會學自然包含的一種現象,其背后必然存在一套潛在的話語倉庫,或說“話語劇目”和“概念工具箱”,它是行動者做出判斷的理論參考。如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所說,這些話語集中體現在教科書、研究指南、讀本、書評等地方(26)參見托馬斯·庫恩:《必要的張力——科學的傳統和變革論文選》,范岱年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25-227頁。。盡管研究者可以根據上述范疇理解布爾迪厄對阿爾都塞的理論批判,然而,學術評價卻不單純取決于這一套客觀存在的理論范疇:學術評價的話語劇目固然限定了可選擇的表達,但做出學術評價的原因以及究竟選擇何種表達形式,都不是話語劇目本身所能決定的。
內部主義視角的另一個問題是將行動者假設為邏輯理性的個體。也就是說,針對“布爾迪厄與阿爾都塞主義基本立場相似”這一論斷,支持者和反對者都假定布爾迪厄是一位純粹理性的個體,只會根據他所受到的學術訓練來思考問題,也只會按照基本的邏輯原則選擇立場。依據這一假設,布爾迪厄的性格及其作品中所有帶有個人情感的討論,從一開始就要排除在外。然而,一旦這樣做,研究者便依據一套既有的規范裁剪了布爾迪厄本人和他的作品,從一開始就采納了偏頗的理論視角。因此,這一假設不僅現實性和普遍性程度較低,而且實際上暗中將研究者的注意力從布爾迪厄的生活和文本上轉移開了。
當前的社會學研究中,若要充分解釋學術評價,研究者的最佳選擇,仍是將學術評價視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行動,從而沿著行動理論的脈絡(27)參見Hans Joas and Jens Beckert, “Action Theory,” in Jonathan H. Turn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2001, pp.269-285.,選擇既有理論框架或稍加調整以使其符合研究對象與研究問題,再進行針對性的考察。而從研究對象的契合性與理論工具的可操作性兩方面看,彼得·赫斯特羅姆(Peter Hedstr?m)以期望(Desires)、信念(Beliefs)和機會(Opportunities)為核心的行動理論(簡稱DBO理論)是一個相對恰當的起點。DBO理論的核心在于:“一個行動者的期望、信念和機會是行動者付諸行動的最直接的原因。……行動的原因,就是一系列的使行動顯得有理由的期望、信念和機會的組合。”(28)彼得·赫斯特羅姆:《解析社會:分析社會學原理》,陳云松、范曉光、朱彥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第41-42頁。該理論的基本解釋邏輯如圖1所示。

圖1 DBO理論的核心(29)參見彼得·赫斯特羅姆:《解析社會:分析社會學原理》,第41頁。
DBO理論在簡潔性和解釋力之間達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但并非完美無缺,其至少存在以下四點問題:第一,關鍵概念的定義存在混亂,特別是期望和機會,期望實際上也被定義為機會,而機會根本沒有定義;第二,分類標準不清晰,機會究竟是主觀感知還是客觀結構未予清楚說明(30)參見彼得·赫斯特羅姆:《解析社會:分析社會學原理》,第41-42頁。;第三,行動者假設存在問題,盡管承認行動者的“不透明性”(31)彼得·赫斯特羅姆:《解析社會:分析社會學原理》,第43頁。,卻依然堅持期望、信念和機會能夠充分解釋行動,而忽視了行動者的創造性、身體和情感等特性;第四,錯誤的行動者存在狀態假設,DBO理論中的行動者是獨白式的,缺少對話和交流的視野,集中關注行動的微觀基礎而忽視了行動的中層影響因素(32)參見馬克·格蘭諾維特:《社會與經濟:信任、權力與制度》,王水雄、羅家德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第18-30頁。。
由于存在上述問題,結合其他行動理論修正DBO理論就顯得十分必要。首先,必須找回DBO理論輕視的個體和行動之外的存在,亦即通常以“社會”籠統稱之的物質和觀念部分,由此在理論上區分社會、行動者和行動;其次,進一步精細化社會概念,區分規范(文化或共享價值)、結構(獨立于個體的模式與格局)和網絡(動態的人際互動及其結果),并且采取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吉登斯和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的觀點,將每一種社會存在都視為二重化的,即既是資源又是約束(33)參見安·斯威德勒:《行動中的文化》,王化險譯,見周怡主編:《文化社會學:經典與前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3-31頁;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綱要》,李康、李猛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3-26頁;馬克·格蘭諾維特:《鑲嵌:社會網與經濟行動》,羅家德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17-31頁。;再次,盡管行動者存在于規范、結構和網絡之中,并且這三者都不是完全消極的約束性因素,但行動者仍然是高度“不透明的”,其習性、創造性、身體和情感等特性無法全部還原為社會存在,因此,行動者是否付諸行動所具有的偶然性遠超DBO理論的假設;最后,經由互動和反饋,行動顯然對行動者和社會有反作用(34)參見諾貝特·埃利亞斯:《論文明、權力與知識——諾貝特·埃利亞斯文選》,劉佳林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09-130頁。,限于研究內容,這一點不再過多展開。基于DBO理論的修正模型如圖2所示。

圖2 基于DBO理論的修正模型
基于DBO理論的修正模型雖然提供了一個考察社會行動的一般性框架,但在應用于學術評價時,應注意到學術評價的若干特殊性。例如,直接影響學術評價的社會存在中,規范、結構和網絡都帶有獨特的學術色彩。廣義上,學術規范不僅包括寫作和研究準則(例如禁止抄襲和被研究者的知情權),也包括主導性的理論、方法、評價標準、教學內容和方式等,它們共同構成了某個學術領域中研究人員的共識價值。學術結構同樣含有兩方面內容,一是涉及全部學科或單獨學科內從業人員的地域、性別、代際、權力、資金等的分布模式,二是不同學科之間的關系,例如高等/低等、交流/隔絕等模式。學術網絡則是指研究者彼此之間相對穩定的關系格局,其中既有聯系相對松散的學術群體,也有聯系緊密的學術派別。
綜合以上討論,圖3展示了一個針對學術評價行動的、基于DBO理論但又更加具體的修正模型。

圖3 修正模型視角下的學術評價
而上述模型不僅構成了本文解釋布爾迪厄對阿爾都塞主義批評的基本框架,也令本文的兩個主要研究目標更加清晰可見:(1)清楚且全面地總結布爾迪厄針對阿爾都塞主義的學術評價,闡明其中除理論性的反思和指責外,還包含哪些內容;(2)打開從社會到行動者再到行動的“黑箱式”過程,說明這一過程究竟展現了怎樣的因果機制。
二、布爾迪厄與阿爾都塞的人生軌跡和私人關系
作為享有世界性聲譽的思想家,阿爾都塞和布爾迪厄的生平已經眾所周知,無須我們做過多說明(35)參見路易·阿爾都塞:《來日方長:阿爾都塞自傳》,蔡鴻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弗朗索瓦·多斯:《從結構到解構:法國20世紀思想主潮》(上),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381-420頁;皮埃爾·布爾迪厄:《自我分析綱要》,2017年;邁克爾·格倫菲爾編:《布迪厄:關鍵概念》,林云柯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3-30頁;l’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 Inventaire des Archives de Louis Althusser Deposees a l'IMEC, 1997。。從兩人的生平與聲譽來看,總體而言,阿爾都塞和布爾迪厄在20世紀下半葉的經歷,大致形成四個對比鮮明的階段,即:(1)1951—1964年,無名教師與青年學生;(2)1965—1980年,阿爾都塞時刻與布爾迪厄的攀升;(3)1980—1990年,殺妻犯人與法國社會學家王;(4)1990年之后,學術聲譽平緩恢復和譽滿天下。與兩人的人生軌跡相比,阿爾都塞與布爾迪厄的私人關系則相對明確地切分為相交與失和兩個階段。
布爾迪厄的學生時代與阿爾都塞交集不多。從阿爾及利亞返回巴黎后,應阿爾都塞之邀,布爾迪厄于1963年12月到次年4月,與帕瑟隆在巴黎高等師范學校講授“當代科學社會學”,同時向聽眾講解他們當時已經完成和正在做的社會學研究。阿爾都塞本人于1963年12月6日晚,在這場題為“人文科學中的理論與方法”的研討班上致辭,向聽眾引介了布爾迪厄和帕瑟隆兩人(36)參見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ntroducing Bourdieu and Passero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36, no. 7-8, 2019, pp.5-21.。
盡管這場研討班中間出現爭論(37)參見Gisèle Sapiro, Fran?ois Denord, Julien Duval, Mathieu Hauchecorne, Johan Heilbron, and Franck Poupeau, eds., Dictionnaire International Bourdieu, p.20; Jacques Rancière and Peter Hallward, “Only in the Form of Rupture: An Interview with Jacques Rancière,” in Peter Hallward and Knox Peden, eds., Concept and Form, Volume 2: Interviews and Essays on the Cahiers pour l’Analyse, London: Verso, 2012, p.260; Jacques Rancière, Althusser’s Lesson, p.40,p.171.,但阿爾都塞與布爾迪厄的關系并未因此受到破壞。1965年,《保衛馬克思》和《閱讀〈資本論〉》出版后,阿爾都塞向布爾迪厄寄贈新書,而布爾迪厄則回信答謝(38)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等人也向阿爾都塞贈書表示感謝,見l’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 Inventaire des Archives de Louis Althusser Deposees a l'IMEC, p.16; Fran?ois Dosse, “Deleuze and Structuralism,” in Daniel W. Smith and Henry Somers-Hall,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eleuz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31.。1966年,布爾迪厄在《現代》(LesTempsModernes)雜志發表《知識場域和創作計劃》一文,文中正面引用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兩次(39)參見麥克·F. D. 揚編:《知識與控制——教育社會學新探》,謝維和、朱旭東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06-207、223頁。。
1968年4月15日,阿爾都塞在給意大利共產黨員瑪麗亞·安東涅塔·馬西奧奇(Maria Antonietta Macciocchi)的信中說道:“正是這一系統延緩了半無產階級的徹底社會瓦解。布爾迪厄已經令人信服地指出,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阿爾及利亞的半無產階級中。”(40)Louis Althusser and Maria Antonietta Macciocchi, Letters from the Insid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to Louis Althuss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p.56.同年,布爾迪厄與帕瑟隆等人合編的《社會學的技藝》(LeMétierdesociologue)初版,“從阿爾都塞在1965年出版的合著《閱讀〈資本論〉》的前言中節選了一部分”(41)Gisèle Sapiro, Fran?ois Denord, Julien Duval, Mathieu Hauchecorne, Johan Heilbron, and Franck Poupeau, eds., Dictionnaire International Bourdieu, p.21.。因此,該書出版后也寄給阿爾都塞,阿爾都塞為該書寫作了一篇6頁的短評(42)參見l’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 Inventaire des Archives de Louis Althusser Deposees a l’IMEC, p.21.。
然而,從1968年開始,雙方的關系便開始有所變化。一方面,布爾迪厄并不喜歡阿爾都塞1968年出版的《列寧和哲學》;另一方面,1968年的“五月事件”之后,阿爾都塞本人一段時間內仍舊沉浸在事件余波中,在1969年完成的《論再生產》手稿中,阿爾都塞再次正面提及布爾迪厄:“……教育系統,它通過我們將要研究的那些機制,根據個人的出身,對他們進行或多或少的‘教育’,并強化著實踐的、經濟的和意識形態的禁令(‘文化’:這些都由布爾迪厄和帕瑟隆研究過了)……”(43)路易·阿爾都塞:《論再生產》,吳子楓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06頁。
1970年6月,阿爾都塞從《論再生產》手稿中抽出一部分,發表在法共的機關刊物《思想》(LaPensée)雜志,是為《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這篇文本引發巨大反響,也啟發了諸多后續研究:“阿爾都塞給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所下的定義,催生了許多特定的研究領域,這些領域可以更為廣泛地闡明社會現實。”(44)弗朗索瓦·多斯:《從結構到解構:法國20世紀思想主潮》(下),第227頁。但是,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布爾迪厄本人對它卻頗為反感:“這個文本反響很大,但布爾迪厄一直都不贊同。在《論國家》和《反思社會學導引》中,布爾迪厄認為‘機器’這個詞是功能主義的,甚至是有著‘陰謀論的臆想,好像有一股邪惡的力量為世間的萬事萬物負責’。”(45)Gisèle Sapiro, Fran?ois Denord, Julien Duval, Mathieu Hauchecorne, Johan Heilbron, and Franck Poupeau, eds., Dictionnaire International Bourdieu, p.21.
1972年,《社會學的技藝》再版,布爾迪厄刪掉了阿爾都塞的選段。1973年,阿爾都塞的學生、也是《閱讀〈資本論〉》一書的合作者艾蒂安·巴利巴爾(étienne Balibar)在《思想》發表《論歷史辯證法:關于〈閱讀資本論〉的若干批判性評論》,次年,巴利巴爾將這篇文章作為《歷史唯物主義五講》(Cinqétudesdematérialismehistorique)一書第四章重新出版。布爾迪厄于1975年在其創辦的刊物上回應巴利巴爾,發表《有關馬克思的講座:關于“關于〈閱讀資本論〉的若干批判性評論”的若干批判性評論》,標題顯然是對巴利巴爾文章的戲仿,其內容則是批判阿爾都塞和巴利巴爾作為哲學家的認識論貴族主義,以及作為共產黨哲學家只會援引大師文本的教條主義(46)參見皮埃爾·布爾迪厄:《言語意味著什么:語言交換的經濟》,劉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71-187頁。。2001年,此文又被布爾迪厄收入《語言與符號權力》(Langageetpouvoirsymbolique)一書,標題改為《宏大話語:關于“關于〈閱讀資本論〉的若干批判性評論”的若干批判性評論》。這篇文章使得雙方關系徹底破裂,如法比亞尼所說:“布爾迪厄……教訓競爭對手時毫不留情,于是彼此很快就變成仇敵。”(47)讓-路易·法比亞尼:《布爾迪厄傳》,第76頁。
阿爾都塞顯然知道布爾迪厄這篇嘲諷性文章,在1976年撰寫的手稿中,阿爾都塞簡短而高度政治性地考察了馬克思與社會學的關系,將社會學看作一種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理論,并對布爾迪厄做出含蓄的回應:“某些法國社會學學派,把習性概念看作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鑰匙,還要給盡力參與政治活動的人上修辭課。”(48)Louis Althusser, Les vaches noires: Interview imaginaire (le malaise du XXIIe Congrès) Ce qui ne va pas, camarad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6, p.59.在阿爾都塞看來,布爾迪厄僅從寫作風格上入手揶揄他人,相對于巴利巴爾學校內外的政治行動,布爾迪厄的諷刺性態度表明他在政治問題上并不嚴肅。
概言之,布爾迪厄比阿爾都塞眾所周知的幾位學生(如巴利巴爾和朗西埃)年紀大,但布爾迪厄與阿爾都塞仍然分屬兩代人:接近20年的年齡差距分開了老師和學生,但10年卻是一個更加敏感的距離,無法感受同樣的思想與社會氛圍,也無法為教導關系奠定基礎。這些獨特的外部條件和相似又相異的人物性格結合在一起,促使布爾迪厄反對所謂的“阿爾都塞主義”。當然,他們在理論上的確也存在不少分歧。
三、影響焦慮:強者、雙重影響和消解焦慮
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曾指出,詩歌的歷史無非是詩人中的強者“為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間而相互‘誤讀’對方”的歷史:“所謂詩人中的強者,就是以堅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顯赫的前代巨擘進行至死方休的挑戰的詩壇主將們。天賦較遜者把前人理想化,而具有較豐富想象力者則取前人之所有為己用。然而……取前人之所有為己用會引起由于受人恩惠而產生的負債之焦慮。試想,哪一位強者詩人希望意識到,他并沒有能夠創造出自己的獨特風格?”(49)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徐文博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3-4頁。易言之,每一位哀嘆自己來得太晚的強者詩人,越是想象豐富和意志堅強,越是希望構造出原創的思想成果,也就越會直面和利用前人的創造,面對由此而來的“影響焦慮”,強者詩人往往有意無意地采取各種寫作方式修正前人,以此削弱前人而壯大自己(50)參見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2019年。。
布魯姆的理論顯然不止適用于詩人。柯林尼可斯在為布爾迪厄所寫的悼詞中曾說道:“很難不把他(指布爾迪厄)在自己的著作中針對馬克思(事實上還有其他人物,如涂爾干、韋伯)的原創性聲明看作哈羅德·布魯姆所謂‘影響的焦慮’的一個實例。”(51)Alex Callinicos, “Pierre Bourdieu and the Revival of Social Critique,” Radical Philosophy, 2002, pp.5-7.盡管柯林尼可斯的討論過于簡略,然而,他敏銳地注意到布爾迪厄的性格對其創作和評論(針對自身和針對他人)的意義。布爾迪厄在政治上的獨立立場和學術上的原創性宣告均證明其社會學中的“強者”習性;而他與阿爾都塞主義在理論上的相似之處(無論主觀上借用還是客觀上相似),以及阿爾都塞主義在20世紀60—70年代的巨大影響力所導致的“布爾迪厄只是阿爾都塞主義翻版”的外界評論意見,又一再引起他的焦慮感。因此,正如邁克爾·布洛維(Michael Burawoy)所說,修正阿爾都塞主義就成為布爾迪厄消解焦慮的一種方式(52)參見Michael Burawoy, “Making Sense of Bourdieu,” Catalyst, vol. 2, 2018, pp.51-87.。就此而言,布爾迪厄與強者詩人的區別只在于他采用了不同的修正技巧。
(一)社會學中的“強者”
如果說詩人中的強者“是以堅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顯赫的前代巨擘進行至死方休的挑戰的詩壇主將們”,是想象力豐富、思想獨立和意志堅韌的人物,社會學中的“強者”與此并無二致,而且不單單表現在作品創作上,也不只表現為正面的舉動。布爾迪厄自學生時代起便從不隨波逐流,“他出生于‘外省和民間’,置身于學院的高墻里令他感到不自在。盡管也有其他的學生與他情況相同,他還是感到自己能僥幸通過嚴格的入學篩選是一個奇跡。他并沒有沾沾自喜,卻總感到一種隱隱的怒氣……他被一種不尋常的報復欲所激動”(53)弗朗索瓦·杜費、皮埃爾-貝特朗·杜福爾:《巴黎高師史》,程小牧、孫建平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14頁。。政治上,在共產主義席卷巴黎高等師范學校乃至整個巴黎思想界的時候,布爾迪厄與德里達等人一起,拒不追隨流行趨勢。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法比亞尼、維迪-勒魯與米歇爾·拉蒙特(Michèle Lamont)等人不約而同地關注到布爾迪厄堅持己見和抗拒批判的頑強性格(54)參見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憶錄》,楊祖功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435頁;讓-路易·法比尼亞:《布爾迪厄傳》,第5頁;Jeannine Verdés-Leroux, Deconstructing Pierre Bourdieu: Against Sociological Terrorism from the Left, pp.30-31; Michèle Lamont, “Looking back at Bourdieu,” in Elizabeth Silva and Alan Warde, eds., Cultural Analysis and Bourdieu's Legacy: Settling Accounts and Developing Alterna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10, p.133.。
在最近的一場辯論中,布洛維盡管側重于現象描述,卻無意中延續了此種觀點,且更為清楚地指出:“布爾迪厄發展出了一套引用和不引用的策略,以此作為他承認或不承認競爭對手的一個標志,由此,對抗成為他學術習性的一部分。塔爾科特·帕森斯或于爾根·哈貝馬斯更樂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與他們相比,布爾迪厄傾向于掩蓋他所站立的肩膀,從而使他自己看起來就是自身天才的源泉。布爾迪厄是借用競爭對手觀點卻不公開承認的知名人士。如果原作者很有名,他就把他們樹立為敵人,扭曲他們的觀點,使其站不住腳,由此,他本人則作為一名優勝的思想家形象出現。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布爾迪厄尤其如此。所以,他盡力隱藏自己對阿爾都塞式結構主義的利用……而這種隱藏的方式則是,要么拒不指出來源,要么粗暴地攻擊阿爾都塞及其追隨者。”(55)Michael Burawoy, “Making Sense of Bourdieu,” Catalyst, vol. 2, 2018, pp.86-87.
(二)主動與被動的雙重影響
在布爾迪厄主觀方面,盡管批判結構主義傳統的次數更多,但他絕非全不認可結構主義的理論主張,更沒有徹底切斷他與結構主義的理論關聯,如他本人所說:“我和‘結構主義’世代(包括阿爾都塞,還有尤其是福柯)有許多知識上的共通之處——不過,我并不認為自己屬于其中。首先是因為我和他們在學校中相差了一個世代(我聽過他們的課)。在這也因為我排斥那些讓我覺得是時尚的事物,可以這么解釋,我和他們的共通之處,是都企圖反抗存在主義為這個世代所展現出來的東西:當時正流行著萎靡不振的‘人道主義’,并鼓吹‘真實體驗’;而這種政治道德主義,至今仍在期刊《精神》中殘存著。”(56)皮耶·布赫迪厄:《所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會學文集》,第28頁。
此外,布爾迪厄也絕不排斥學習,包括向自己的同輩人學習。1974年,德里達那排版極其怪異出格的《喪鐘》(Glas)出版后,布爾迪厄反響十分熱烈,在給德里達的回信中他說道:“我想十分真誠地感謝你的《喪鐘》,我很快樂地讀了它。除了別的東西意外,你的構圖追求讓我很感興趣。我也在以另外的邏輯打破傳統的修辭法,而你的成就在這個意義上讓我深受鼓舞。”(57)伯努瓦·皮特斯:《德里達傳》,魏柯玲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33-234頁。在很多文本中,布爾迪厄有意用夾在文中的小字號文字書寫個人看法和做推論,這種情況在他1975年評論巴利巴爾的那篇文章中十分明顯,文章的排版從一開始就是整篇文章的有機構成部分(58)參見Pierre Bourdieu, “La lecture de Marx. Quelques remarques critiques à propos de ‘Quelques remarques critiques à propos de Lire Le Capital’,”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o. 5-6, 1975, pp.65-79.。
考慮到這些內容,布爾迪厄思想中存在與阿爾都塞主義類似的觀點,甚至主動學習和接受阿爾都塞主義的某些成分,并非完全不可想象之事(如前文所說,布爾迪厄對阿爾都塞主義的敵視是持久的,卻并非始終如一的)。這些理論上或多或少的相似之處,除前述已經被辨認出的有關教育、符號暴力與意識形態、社會科學哲學、知識、宗教、客觀關系優先性等議題上的討論,至少還包含結構因果性(59)參見路易·阿爾都塞、艾蒂安·巴利巴爾:《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第219頁;今村仁司:《阿爾都塞——認識論的斷裂》,牛建科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9-218頁;皮埃爾·布爾迪厄:《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第178頁。、認識論斷裂(60)參見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第370頁。、經濟的最終決定作用(61)參見路易·阿爾都塞、艾蒂安·巴利巴爾:《讀〈資本論〉》,第59頁;路易·阿爾都塞:《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陳越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6-157頁;皮埃爾·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8頁。等理論要點。其中,尤為顯著的是“過度決定”(surdétermination/overdetermination)這一概念。過度決定,即所謂多元決定(另有超越決定和超定等譯法),源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阿爾都塞將其定義為:作為復雜的結構化整體,社會形態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在于不同結構之間的不平衡,經濟結構既限定了社會形態的不平衡發展,其最終決定作用也取決于這種結構的不平衡(62)參見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第180-185頁。。概言之,過度決定包含了垂直的最終決定和水平的相互決定兩方面含義。布爾迪厄也在其個人研究中使用了阿爾都塞所定義的這一概念:“在哲學場域中進行的爭斗,盡管包含在權力場域中,但這些爭斗始終是多元決定的(overdetermined),并且傾向于以雙重邏輯來運作。”(63)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第133頁。
然而,與阿爾都塞主義有關的“影響”還不只限于著作和理論,更來源于不斷出現的外部評論,后者帶給布爾迪厄的焦慮和反感更甚于前者。最晚到1980年,評論家們便已經得出了今天仍廣為流行的判斷:“如果在法國思想中定位皮埃爾·布爾迪厄的最初處境,那么我們可以說他嘗試對幾種思想做原創性的綜合: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作為對支配的批判和一種意識形態理論)以及1955—1965這一代(法國)哲學家所理解的巴什拉認識論。”然而,布爾迪厄對此嗤之以鼻,在他看來,諸多“布爾迪厄=馬克思+(阿爾都塞等人理解的)巴什拉”的看法,實際上是把未知還原為已知,把原創還原為既有,這些公式化做法還會補充一些在學術評價上被污名化的人物或理論(比如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來進一步污蔑自己,是“理解原創性的典型教授視角”(64)Pierre Bourdieu, Interventions, 1961-2001: Science sociale et action politique, Paris: Agone, 2002, p.112.。此外,費里和雷諾的《68思想:論反人道主義》一書于1985年出版并迅速引發熱議(65)參見伯努瓦·皮特斯:《德里達傳》,第327-328頁。,盧迪內斯庫和德里達在談話中提到了(66)參見雅克·德里達、伊麗莎白·盧迪內斯庫:《明天會怎樣:雅克·德里達與伊麗莎白·盧迪內斯庫對話錄》,第3頁。,布爾迪厄在和漢斯·哈克(Hans Haacke)的交流中也提到了(67)參見皮埃爾·布爾迪厄、漢斯·哈克:《自由交流》,桂裕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2頁。。《68思想:論反人道主義》從內容上看不乏問題,然而它的流行再度放大了人們認為布爾迪厄與阿爾都塞思想上十分接近的看法。也就是說,布爾迪厄社會理論與阿爾都塞馬克思主義的相似,不僅在于理論本身的某些或重要或不重要的一致,還在于評論家和社會公眾對這兩種理論體系的看法,后者往往出于簡化的目的或至少是遵從簡化的邏輯,將兩者直接等同。
如果說布爾迪厄的確有意無意地接受和內化了若干阿爾都塞主義的立場,由此產生出布魯姆所說的取前人之所有為己用而產生的“焦慮”,而且布爾迪厄的性格越是強勢,越是追求原創性,這種焦慮感就越強,那么,外部評論把他和阿爾都塞主義等同的做法,就更進一步地激化了他的感覺和反應,促使他以自己的方式消解焦慮。
(三)消解焦慮的三種修正技巧
斯沃茨在其經典研究一個很不起眼的注釋中寫道:“雖然不是高師的阿爾都塞圈子中的成員,布爾迪厄卻從來不公開地評判阿爾都塞。”(68)戴維·斯沃茨:《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第23頁。盡管他立即提出了布爾迪厄在訪談中對阿爾都塞的正面評價,但斯沃茨的這一判斷無疑是錯誤的,事實遠非如此。布爾迪厄不僅多次抨擊阿爾都塞,其對阿爾都塞主義的修正也不一而足,主要是通過以下三種技巧:
1.自說自話:批判時只點名和貼標簽而不分析文本
1970年起,阿爾都塞主義在布爾迪厄的著述中有兩種形象:研究對象和對話對象。作為研究對象,布爾迪厄多次提及阿爾都塞和福柯等人在知識場域和大學場域中不平衡的位置:“我們越接近研究端,就越看到象征性資本和大學身份地位之間的間距可能性增加,某些最有威望的知識分子能占據完全是次要的大學位置,例如在調查進行當時的路易·阿圖塞、羅蘭·巴特、米歇爾·傅柯。”(69)皮耶·布赫迪厄:《學術人》,李沅洳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184頁。類似的看法在《學術人》一書英譯本前言中更加清楚:“福柯是這個位置的最好代表,因為直到成為法蘭西公學院的教授,他都沒有掌握特別的學術或科學權力,也沒有那些學術權威所能提供的庇護,盡管他的名氣使他對出版界,乃至于整個文化生產場域有著可觀的影響力。這種位置的邊緣屬性,在阿爾都塞和德里達那里更是令人驚訝:他們的職位很低(高師的輔導老師)……”(70)Pierre Bourdieu, Homo Academicu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xix.也只有在將阿爾都塞主義視為研究對象的情況下,1970年之后的布爾迪厄才唯一一次大量引用對方的詞句,也就是1975年戲仿巴利巴爾的文章。然而,這篇一再被布爾迪厄提及的論文(71)參見Pierre Bourdieu,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Martin Heidegg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22.,實際上只是從修辭角度出發的外部主義或說社會學分析,而不是理論對話和批評(72)參見皮埃爾·布爾迪厄:《言語意味著什么:語言交換的經濟》,第171-187頁。。
一旦將阿爾都塞主義確定為受批判的對話對象,布爾迪厄除單個字詞或概念外便不再引用對方原文,更不做任何深入分析。因此,盡管阿爾都塞主義是布爾迪厄批評最尖銳的對象之一,布爾迪厄的作品中卻找不到對后者理論的深入解讀,也極少引用阿爾都塞主義者的原話,并不清晰地呈現自己的文本證據何在,而只是通過點名和貼標簽的形式不斷地重復以下三種批評:(1)阿爾都塞主義是學究理性主義,不重視經驗和實踐,只會耍理論的把戲(73)參見皮埃爾·布爾迪厄:《帕斯卡爾式的沉思》,劉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9-10頁;Pierre Bourdieu,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9—1992, p.77; Pierre Bourdieu, Interventions, 1961—2001: Science sociale et action politique, p.45.;(2)阿爾都塞主義否定人的能動性,將行動者還原為結構的“承載物”,是極端的結構主義;(3)阿爾都塞主義是悲觀功能主義,將國家視為一套“邪惡機器”,有陰謀論傾向(74)參見Pierre Bourdieu,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9—1992, p.77; 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445.。在提出上述三種批評時,布爾迪厄沒有一次在引用阿爾都塞主義者原文的基礎上展開深入解讀,更沒有深入對話的意圖。
布爾迪厄曾在對話中聲稱:“我也是速讀的受害者。在看到我的書被引用時,簡直不能相信,我看不出他們從我這里得到了什么,好像所有的話都是我說的……這種速讀文化是一場災難,因為它扼殺了緩慢的思考。就我自己而言,我花了很多很多個月的時間逐行閱讀韋伯,更不用說胡塞爾了。這是一個孕育的過程。我永遠也寫不出‘Weber (1913)’這種糟糕透頂的引文方式。”(75)Pierre Bourdieu and Michael Grenfell, Encounter I: Pierre Bourdieu in Conversation with Michael Grenfell, ACT: Recent Work Press, 2019, p.17.然而,他的文字和言語遠不是一回事,在《法律的力量:邁向司法場域的社會學》這篇長文涉及阿爾都塞的地方(76)參見皮埃爾·布迪厄:《法律的力量:邁向司法場域的社會學》,見《北大法律評論》編委會編:《北大法律評論》第2卷·第2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97-498頁。,布爾迪厄把自己嚴厲批評并且聲明不會采用的方式展現得淋漓盡致:首先,布爾迪厄實際上沒有引用阿爾都塞的任何作品,只是提到“機器”(Apparatuses)這個典型的阿爾都塞主義詞匯,更沒有展開任何精細的分析;其次,指控阿爾都塞把法律還原為統治階級的工具,然而,布爾迪厄不僅讀過《保衛馬克思》和《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也引用過,甚至將“過度決定”作為反還原論的概念正面使用(77)參見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第133頁。,但他依然把根本不屬于阿爾都塞的觀點強加給阿爾都塞,完全沒有討論阿爾都塞究竟說了什么。
又如1986年5月15日的法蘭西公學院講座,布爾迪厄在其中指責阿爾都塞主義在國家理論上是極端結構主義且帶有陰謀論色彩,盡管聲稱自己能舉出諸多例證,然而最終一個引文都沒有出現:“因此,大聲斥責權力……實則令他們陷入了支配—操縱和自愿奴役的話語傳統中(可見阿爾都塞、工具邏輯、被操縱的、邪惡國家等等)。(我幾乎沒有夸大,如果我愿意,我能引用一大堆文獻……)”(78)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445.
2. 正面使用對方的觀點時不點名
正如布洛維所說,“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布爾迪厄尤其如此。所以,他盡力隱藏自己對阿爾都塞式結構主義的利用……而這種隱藏的方式則是,要么拒不指出來源,要么粗暴地攻擊阿爾都塞及其追隨者”(79)Michael Burawoy, “Making Sense of Bourdieu,” Catalyst, vol. 2, 2018,pp.86-87.。如果說只點名不分析是為了批判,那么只使用而不點名就無疑是宣揚自身的原創性了。
例如“多元決定”(即“過度決定”)概念,在1991年2月21日的法蘭西公學院講座中,布爾迪厄也指出這一概念與阿爾都塞主義的關聯:“對涂爾干來說,原始社會的所有東西混雜在一起:宗教、科學、經濟、儀式、政治等等;人的所有行動都是‘多功能的’,或用阿爾都塞的術語說‘多元決定的’(多功能這個表達更好)。”(80)Pierre Bourdieu,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9—1992, p.201.然而,在正式出版的著作《反思社會學導引》中,布爾迪厄雖然正面使用了這一概念(81)參見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第133頁。,并且多次提及阿爾都塞主義(82)參見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第7、18、196、201、294、370頁。,但沒有一個地方給出阿爾都塞的原話,甚至參考文獻中連一個特定的參考文本都沒有。這種情況在布爾迪厄及其追隨者的寫作中并非個案。
在1985年3月1日的法蘭西公學院講座中,布爾迪厄聲明要繼續發展他所提出的理論,也就是一整套內部融貫且對于建構社會事實和科學對象來說至關重要的概念體系。在他看來,“這些概念尚未通過理論工作(travailthéorique)制造出來”(83)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19.。同年5月30日的講座中,布爾迪厄又提出:“實際上,我并不是要做理論工作,如果我最后說出的是其他人一開始就想說的東西,那這也正是因為理論話語是經由斗爭而來的……如果這種理論話語并不是‘理論工作’(正如某人在某時曾說過的那樣)……”(84)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378.撇開“理論和概念體系構造社會事實和科學對象”這一阿爾都塞在《閱讀〈資本論〉》中清楚表達的觀點(阿爾都塞的相關文本被收錄在《社會學的技藝》的初版中)不談,在以上沒有提及任何姓名的兩處引文中,阿爾都塞主義的色彩無處不在,以至于布爾迪厄講座的編者在這兩處都加上注釋,說明阿爾都塞主義和“理論工作”的關聯,特別是阿爾都塞本人在1967年發表的文章《論理論工作》(Surletravailthéorique),并且指明布爾迪厄所說“正如某人在某時曾說過的那樣”是指向阿爾都塞主義者的(85)參見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36, p.394.。而布爾迪厄在這兩處明顯的自相矛盾,也就是既聲明要繼續“理論工作”,又聲稱自己做的不是“理論工作”,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既接受部分阿爾都塞主義觀點但又拒絕承認受惠于對方的心理。
3. 脫離語境,刻意誤讀
作為理論評論家的布爾迪厄,在討論到阿爾都塞主義時,并不是從文本和作者意圖出發提出批評,而是從自己希望強調的方面出發,無視文本或概念的原本意涵,為其附加上完全不相干的內容,在此基礎上大肆批判。上述第一種修正技巧便包含多種這類情況,除此之外,布爾迪厄的刻意誤讀還表現在下述兩點上。
第一,針對阿爾都塞所謂“保衛馬克思”的說法,布爾迪厄在1983年接受訪談時曾說道:“要不是像阿爾都塞所說的保衛馬克思,就是反對馬克思。但我認為,我們可以用馬克思來進行思考并與馬克思對抗,或者是用涂爾干來進行思考并與涂爾干對抗……這就是科學運作的方式。”(86)皮耶·布赫迪厄:《所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會學文集》,第103頁。這種說法在接近20年的時間里絲毫不變,又一次出現在1999年的訪談中,甚至詞句都幾乎完全一樣:“是像阿爾都塞那樣‘保衛馬克思’,還是‘反對馬克思’。我相信,在思想上有可能用馬克思反對馬克思,或者用涂爾干反對涂爾干,當然,也能用馬克思和涂爾干反對韋伯,但反過來也可以。”(87)Simon Susen and Bryan S. Turner, eds., The Legacy of Pierre Bourdieu: Critical Essays, London: Anthem, 2011, p.114.然而,布爾迪厄的這一說法完全脫離了阿爾都塞著述的語境。一方面,阿爾都塞1965年之所以選用“保衛馬克思”(PourMarx)作為書名,主要是出于理論和政治對話,有著具體的社會背景(法國的理論貧困等)與對話對象(“青年馬克思”和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阿爾都塞對馬克思絕不是毫無批評,用布爾迪厄的話說,“認識論斷裂”本身就是“用(成熟)馬克思反對(青年)馬克思”(88)James H. Kavanagh, Thomas E. Lewis, Etienne Balibar and Pierre Macherey, “Interview: Etienne Balibar and Pierre Macherey,” Diacritics, vol.12, no.1, 1982, pp.46-51.。
第二,針對“認識論斷裂”這一概念,布爾迪厄完全無視阿爾都塞主義的理解,認為:“正是從第一次修改中我們可以吸取下面的教訓,這種教訓對那些津津樂道‘斷裂’的人來說尤其重要:科學斷裂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像在創始哲學(initiatory philosophy)(和阿爾都塞式的馬克思主義)那里的一種原創性行為。它有可能要花費30年的功夫。因此,我們有時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回到同一個對象上,即使批評家有可能抱怨我們是在一再重復同一件事情。”(89)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第201頁。也就是說,阿爾都塞主義者將“認識論斷裂”視為一次性、沒有周折和往復的思想創造(90)參見Pierre Bourdieu,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Martin Heidegger, p.127.。在這一問題上,布爾迪厄的追隨者對布爾迪厄的看法亦步亦趨(91)參見Niilo Kauppi, French Intellectual Nobility: Institutional and Symbolic Transformations in the Post-Sartrian Er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p.43.。然而,由于沒有引用任何文本做分析,布爾迪厄及其追隨者的理解同樣是自我想象的。阿爾都塞的“認識論斷裂”概念的確區分了科學與意識形態,但阿爾都塞并沒有聲稱從意識形態到科學的實際過程是一勞永逸的。相反,阿爾都塞不僅認為擺脫意識形態是一個極為艱難的過程(92)參見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第63-64頁。,而且科學在誕生后依然會不斷受到意識形態的侵擾,時刻有遺忘和退化的危險(93)參見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and the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tist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Verso, 1990, pp.29-30.,正因如此才必須進行艱苦的理論工作。
四、學科地位:哲學家及其貴族主義
布爾迪厄學生時代接受的是哲學教育,不過,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早期的阿爾及利亞社會調研經歷促使他轉向民族學和社會學(94)參見Lo?c Wacquant, “Pierre Bourdieu,” pp.215-216;伯努瓦·皮特斯:《德里達傳》,第79頁。。此后,盡管布爾迪厄仍然重視社會學研究的認識論條件,但他并不認為哲學享有任何高等地位——無論是學科上的高等,還是認識上的高等。然而,如果說布爾迪厄的確將阿爾都塞主義視為宣揚哲學高等地位代表的話,他的看法卻并不是純粹的個人情感或個人臆測,相反,這一觀點不僅有現實的和歷史的社會背景,而且作為批判,更采取了頗為不同的表達方式。
(一)被哲學支配的社會學
20世紀法國社會學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的發展:(1)世紀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時期主要見證了涂爾干學派的崛起與衰落,一戰對該學派造成重大打擊,羅伯特·赫爾茲(Robert Hertz)等新一代成員在戰爭中犧牲。(2)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法國社會學的危機階段。勒內·沃爾姆斯(Renè Worms)后繼無人,勒普雷學派(l'école de Le Play)聲名更高,但因與納粹合作而聲譽受損(95)參見夏爾·亨利·屈安、弗朗索瓦·格雷勒、洛南·埃爾武埃:《社會學史》,唐俊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115-126頁。。盡管涂爾干學派的建制化并未完成,但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喬治·達維(Georges Davy)、塞勒斯坦·布格勒(Célestin Bouglé)等涂爾干學派的成員仍是法國社會學的有生力量。此外,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和羅杰·凱盧瓦(Roger Caillois)等人在30年代創建“社會學學院”,也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代表。(3)二戰后到60年代末,法國社會學的重建時期。其中,阿隆、喬治·古爾維奇(Georges Gurvitch)、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喬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讓·斯托策(Jean Stoetzel)等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大量的組織和刊物相繼創辦起來,這一時期也是法國社會學第二個建制化高峰的開端(96)參見皮埃爾·布爾迪厄:《自我分析綱要》,第30-37頁;Johan Heilbron, French Sociolo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0.。(4)70年代到90年代早期,法國社會學快速且多元發展時期。布爾迪厄、阿蘭·圖海納(Alain Touraine)、雷蒙·布東(Raymond Boudon)、米歇爾·克羅齊埃(Michel Crozier)是這一時期最知名的人物,他們代表了相當不同的研究路徑(97)參見朋尼維茲:《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孫智綺譯,臺北: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20-23頁。。(5)90年代起,法國社會學的發展徹底多元乃至碎片化,各種主題和取向均有涉及,“往昔圍繞幾位巨匠構建起來的社會學,裂變成多種學派”,并且“受到外國同行的影響,這些學派大都帶有建構主義和互動主義觀念的特征”(98)菲利普·卡班、讓-弗朗索瓦·多爾蒂耶:《法國視角下的社會學史與社會學思想》,吳紹宜、夏其敏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98頁。,代表人物有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和弗朗索瓦·迪貝(Fran?ois Dubet)。
法國哲學在20世紀主要體現為意識哲學和概念哲學兩種形式,但與社會學狀況不無類似,它也同樣經歷了大致五個發展階段。30年代之前,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思想與新康德主義統率著法國。30年代之后,黑格爾哲學、胡塞爾(Edmund Husserl)現象學和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哲學相繼進入法國;同期,以讓·卡瓦耶斯(Jean Cavailles)等人為代表的法國科學認識論哲學也不斷發展。50到60年代早期,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等人帶來了存在主義和現象學的鼎盛時代;然而,從60年代中期開始,列維-斯特勞斯、拉康、阿爾都塞、福柯、巴特等人所代表的結構主義思想占據思想舞臺,德里達基本同時期的解構主義既攻擊又推動了結構主義的發展。80年代后,除結構主義明顯衰落外,法國哲學也呈現出多元化的局面,德國古典哲學、笛卡爾哲學、現象學、尼采哲學、海德格爾哲學和分析哲學均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20世紀法國哲學與社會學的發展,可以概括性地總結如表1:

表1 20世紀法國哲學與社會學代際表
然而,與兩門學科內部思想動向在20世紀都不斷發展變化不同的是,兩門學科的地位相差甚遠。
首先,從建制上看,不同于哲學的源遠流長,法國社會學的學科地位直到50年代末才確立起來。在1910年,法國只有兩個社會學教席,總共也只有四所大學開設社會學課程。一戰到二戰之間,法國社會學遭受重創,在戰后的重建中,一開始只有古爾維奇和達維兩人擁有通過社會學博士的教授資格,阿隆和斯托策直到1955年才獲得這一資格。50年代早期,社會學在法國仍然只是哲學教育的一部分,法國社會學家的數量不超過100人,正式的大學教職工更是只有25人,直到1958年,第一批本科學位點才在巴黎大學和波爾多大學創立。由于60年代社會學才迎來快速發展,因而法國的著名社會學家往往都是哲學教育出身,從涂爾干到布爾迪厄再到拉圖爾,這反而是一般情況(99)參見Robert Dingwall,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Edition,” pp.ix-xvi.。在大學場域中,“除政治科學和經濟學外,其他的社會科學(社會學、民族學和心理學)的建制化都在文學系之內,這就導致它們長久地依賴著人文科學與哲學——后者如法比亞尼所說,是‘學科之王’。”(100)Johan Heilbron, French Sociology, p.8.
其次,從思想上看,哲學家作為有勇氣思考世界的人,他們沒有利害關系的思考不僅是日常生活的指導,更是其他學科的認識論基礎,其他學科只有遵從這些基本的認識原則,方能取得進步。由于哲學所具有的這些思想優越性,通常說來,哲學家總是以傲慢姿態對待社會學家,一邊教導社會學家應該如何做,一邊抗拒后者對哲學的“外部主義”研究(101)參見Gisèle Sapiro, Fran?ois Denord, Julien Duval, Mathieu Hauchecorne, Johan Heilbron, and Franck Poupeau, eds., Dictionnaire International Bourdieu, p.673.。總而言之,“哲學是享有威望的學科”(102)皮埃爾·布爾迪厄:《自我分析綱要》,第69頁。。對此,阿隆和列維-斯特勞斯也做出了個人化但又完全一致的判斷(103)參見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憶錄》,第440、598頁;雷蒙·艾宏:《雷蒙·艾宏:入戲的觀眾》,賴建誠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年,第19頁;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迪迪埃·埃里蓬:《亦近,亦遠——列維-斯特勞斯談話錄》,汪沉沉譯,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年,第191頁。。
正是觀察到這種學科地位不平等,布爾迪厄不僅看重列維-斯特勞斯(104)參見帕特里克·威肯:《列維-斯特勞斯:實驗室里的詩人》,梁永安譯,廣州:新世紀出版社,2012年,第296-297頁。,更是直接寫道:“我們必須將社會科學重新置入它們多少都會參與的兩個空間中,亦即文學院和自然科學學院……社會科學位居雙重被支配位置,一是在自然科學越來越占支配地位的分級里,二是在舊有的分級中……這解釋了為何這些學科仍舊是成績不佳或者成績中等之布爾喬亞階級孩童的避難所。”(105)皮耶·布赫迪厄:《學術人》,第215-216頁。
(二)阿爾都塞主義的認識論貴族主義
布爾迪厄對阿爾都塞主義的哲學理性或說認識論貴族主義批判,首先集中在后者的“認識論斷裂”這一概念上。阿爾都塞將這一概念應用于馬克思思想研究,認為1845年之前的馬克思處在人道主義的意識形態中,而此后馬克思則逐漸進入一套科學的社會理論中。在阿爾都塞的著作中,“認識論斷裂”的意思是科學思想從意識形態中掙扎而出的過程,因而僅僅涉及認識在客觀上的對錯(106)參見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第61-63頁;阿圖塞:《自我批評論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28-138頁;阿圖塞:《自我批評論文集》(補卷),林泣明、許俊達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113-116頁。。然而,布爾迪厄擴展了這個詞的意涵,將之轉移到道德領域中,認為這一概念有意炫耀一種精英立場,甚至暗示“斷裂”類似于宗教“悔過”(107)參見Pierre Bourdieu,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9—1992, p.229.。在布爾迪厄的作品和談話中,這一話題出現得非常頻繁。
在1985年3月28日的法蘭西公學院講座中,布爾迪厄最為明確地表達了這一點:“很明顯,認識論斷裂的主題確立了普通人和學者之間的斷裂,因此,阿爾都塞主義實際上是一種認識論貴族主義(épistémocratisme)。盡管哲學傳統經常有這種傾向(所以我不喜歡),但阿爾都塞主義格外熱衷于這種掌握另一重本質或本性的感覺:群氓身處幻覺和錯誤之中,無力看清真相,而另一些人能夠悔過,能夠與虛假斷裂,因此看清楚世界的本來面目,同時,也看清其他人不過是假象的傀儡。”(108)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252.
同年,在接受阿克塞爾·霍耐特(Axel Honneth)等人的訪談時,布爾迪厄再次指責阿爾都塞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卻總是帶有哲學家的傲慢,認為自己掌握了不受歷史影響的永恒真理,并且能夠以此來指導其他學科和其他人:“如果有什么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使人接納的,那就是對于概念的歷史(或概念的歷史性)的關注,這正是我們用來思考歷史的東西。然而,哲學的優越感使我們忘了去服膺于概念的歷史批判,而這些概念乃是由其生產及使用的歷史背景所清楚標示出來的(阿爾都塞學派在這方面是出類拔萃的)。”(109)皮耶·布赫迪厄:《所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會學文集》,第50頁。在布爾迪厄看來,法蘭克福學派也有阿爾都塞主義的這種問題:“我許多的研究策略都受到以下關懷的啟發:拒斥哲學中常見的整體性企圖。同樣的,我也一直與法蘭克福學派維持著一種相當矛盾的關系,我們的共通點很明確,然而,該學派的整體性批判卻保留了所有大理論的特征,亦即他們不想在實證研究的廚房里頭把手弄臟。而這種優越感讓我感到某種程度的惱火。阿爾都塞學派也是一樣;正是因為哲學所具有的高度,才使得那種過于簡單卻又專斷的介入有了其借口。”(110)皮耶·布赫迪厄:《所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會學文集》,第53頁。
1988年,《社會學的技藝》首次翻譯為英文,在為該書專門準備的訪談中,布爾迪厄以高度譏諷性的語言再次指責阿爾都塞主義者:“另一方面,也有遠離現實和人類的理論家,阿爾都塞主義者就是典型。這些高師生,往往來自于資產階級,從沒見過一個工人,一個農民,或者其他人,制造出一套沒有能動者的宏大理論。《社會學的技藝》出版后,這些理論家蜂擁而至……我的很多作品,例如說《實踐感》,都在激烈反對這種科學家的優越感,他們宣稱自己知道有關(普通)民眾的真理,比民眾知道得更好。”(111)Pierre Bourdieu, Jean-Claude Chamboredon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p.252.
1991年5月15日,布爾迪厄在與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的對話中說道:“理論家(仿佛)有資格說‘你就是個意識形態分子’。舉個例子,阿爾都塞就輕蔑地提到‘所謂社會科學’……我認為,這種做法貴族氣實在太重,說實話,我不喜歡‘意識形態’這個詞的一個原因,正是阿爾都塞的貴族氣思維。”(112)Pierre Bourdieu and Terry Eagleton, “Doxa and Common Life,” New Left Review, vol. 191, 1992, p.113.
1993年,在一篇有關薩特的文章中,布爾迪厄回溯了自己60年代早期的社會調研,并且再度宣稱:“去近距離考察阿爾及利亞的工人,以及非工人、失業的人、半無產階級、失地農民等等,也就是與大寫的話語決裂——這些話語后來又在阿爾都塞和高師學生身上復活了。”(113)Pierre Bourdieu, Interventions, 1961—2001: Science sociale et action politique, p.45.
1996年10月27日,布爾迪厄在與好友雅克·布弗雷斯(Jacques Bouveresse)的交談中再度以譏諷的語調說道:“雖然閱讀馬克思的哲學家宣稱自己比工人自己更好地理解他們,但是一旦把統計學用到哲學家身上,他們就覺得這是犯罪了。所以,你是反動派,我是庸俗分子。”(114)Jacques Bouveresse, Bourdieu, Savant & Politique, Paris: Agone, 2004, p.55.
在生前最后一次法蘭西公學院講座《科學之科學與反思性》中,布爾迪厄依舊念念不忘阿爾都塞主義的哲學家傲慢:“可是我也堅決反對哲學,亦即反對旨在捍衛小團體及其陳舊的程序的體制型的哲學,尤其是堅決反對傾向于提倡具有優越本質的特權階級的哲學中的貴族哲學,反對所有這類哲學家,不論他們的反體制的品格如何;盡管他們中的某些人打著與‘主體性的一類哲學’決裂的旗號,他們還是繼續主張對社會科學采取特權階級所慣于采取的藐視的態度,這種態度也是傳統哲學信條的基石。……他們都把社會科學的地位排列于‘學識’之下,即不如諸多的‘學識’。”(115)皮埃爾·布爾迪厄:《科學之科學與反觀性:法蘭西學院專題講座(2000—2001學年)》,陳圣生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77頁。
如果說作為中間一代的阿隆還能平心靜氣地接受哲學和哲學家的傲慢姿態,已經完成轉向并且要更徹底地推進社會學獨立的布爾迪厄,就完全無法忍受哲學的優越地位了,特別是阿爾都塞主義所代表的、在他看來更加極端的哲學學究理性(或說認識論貴族主義)了。更為糟糕的是,布爾迪厄認為這種哲學家的傲慢還染上了不良政治意圖,也就是自柏拉圖以來就從未停歇的“哲人王”理想。
(三)阿爾都塞主義與哲人王的古老夢想
按照布爾迪厄的定義,認識論貴族主義往往特指哲學家自認為掌握他人所不具有的真理,因而表示對普通人和社會科學家的傲慢。在某些場合,布爾迪厄進一步推演其內涵,指出哲學家這一傲慢態度與政治目的結合,便會成為“哲人王”的古老夢想。針對阿爾都塞主義,盡管這一主題出現的次數并不多,但是布爾迪厄至少從兩個方面提出批判,分別涉及:(1)阿爾都塞主義的政治意圖;(2)阿爾都塞主義為實現該意圖而采取的政治策略。
首先,針對阿爾都塞的《列寧和哲學》(116)參見阿圖塞:《列寧和哲學》,杜章智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53-64頁。,布爾迪厄在1986年5月29日的法蘭西公學院講座中說道:“科學家真正理解世界,因此,他在某種程度上也應該統治世界。這就是在哲學家不斷出現的哲人王神話,從柏拉圖到列寧再到阿爾都塞:哲學家能夠看清楚世界的本來面目,他與觀看世界的普通人視角一刀兩斷,科學區分開了專家和普通人,在某種程度上,普通人被剝奪了有關世界的真理。”(117)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485.類似的指責也出現在1988年布爾迪厄與比特·克拉斯(Beate Krais)就《社會學的技藝》英譯本出版而作的訪談中:“我的很多作品,例如說《實踐感》,都在激烈反對這種科學家的優越感,他們宣稱自己知道有關(普通)民眾的真理,比民眾知道得更好,能讓民眾幸福,這種優越感與哲人王這一古老的柏拉圖神話完全一致(其現代形式就是列寧崇拜)。”(118)Pierre Bourdieu, Jean-Claude Chamboredon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p.252.
其次,布爾迪厄認為阿爾都塞不僅僅在觀念上懷有“哲人王”的夢想,他更是將這種夢想具體實現在日常生活中,特別體現在阿爾都塞的某些政治舉措上。在1977年完成的《帕斯卡爾式的沉思》中,布爾迪厄說道:“我的一部分研究就是為了推翻在對社會世界的分析中通用的許多思想模式(從一種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殘余開始,這種經典除了導致政治聯合之外,還模糊和蒙蔽了不止一代人的頭腦……)。”(119)皮埃爾·布爾迪厄:《帕斯卡爾式的沉思》,第9-10頁。而在最后出版的《自我分析綱要》中,布爾迪厄則直接點名,攻擊阿爾都塞的政治行為或其表現:“集中在《新批評》周圍的共產黨知識分子如何在他們表面上對整個世界廣泛開放的討論中,再生產文科預備班和高等師范學校這個封閉小世界的對立和等級,路易·阿爾都塞無疑是這個小世界的典型形象。”(120)Pierre Bourdieu, Sketch for a Self-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35.此外還有更加尖銳的措辭:“這些學生是共產黨支部骨干,阿爾都塞喜歡在這個支部中發揮他的政治戰略家才能,尤其是打擊非共產黨學生的積極性……”(121)Pierre Bourdieu, Sketch for a Self-Analysis, p.87. 類似批評見理查德·沃林:《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董樹寶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220-221頁。
由此可見,布爾迪厄對阿爾都塞主義的批判,遠不是單純的理論分歧,而是身份、道德和政治的全方位對抗。
五、空間競爭:社會學家與馬克思主義者
德里克·羅賓斯(Derek Robbins)在提及布爾迪厄社會學與阿爾都塞主義相似之處時,曾不無深意地寫道:“布爾迪厄清楚地澄清了他所謂實踐的理論不是什么,但是鑒于他拒絕與馬克思主義發生任何干系,他沒有承認他的觀點與阿爾都塞在1960年代所表達的那些觀點之間的相似性。”(122)邁克爾·格倫菲爾:《布迪厄:關鍵概念》,第48頁。與此類似,法比亞尼在專研布爾迪厄的作品中寫道:“布爾迪厄身為‘馬克思拜讀巴利巴爾’的始作俑者,教訓競爭對手毫不留情,于是彼此很快就變成仇敵。”(123)讓-路易·法比亞尼:《布爾迪厄傳》,第76頁。然而,為什么“他拒絕與馬克思主義發生任何干系”?又為什么是“競爭對手”?要理解布爾迪厄對阿爾都塞主義的持久敵視,必須把后者深具黨派色彩的“馬克思主義”身份考慮在內。因為自視為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阿爾都塞主義,一邊帶有馬克思主義傳統上對社會學的貶低,另一邊又不斷開展性質類似的研究與社會學競爭,這種雙重的“霸凌”最終導致和激化了布爾迪厄的對抗姿態。
(一)貶低和競爭:阿爾都塞主義與社會學
盡管布爾迪厄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把社會學視為反學院體制的武器(124)參見弗朗索瓦·杜費、皮埃爾-貝特朗·杜福爾:《巴黎高師史》,第114頁。,但在30年代之后,社會學在法國已經被定性為保守的學問,是既存體制的一部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以下兩個原因: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十年左右,盡管涂爾干學派遭受嚴重打擊,但該學派仍在推進這門學科在研究上的深化和體制化。較為嚴重的分裂出現在學科內部,特別是大學教授和研究人員之間:“大學教授將‘新精神主義’和共和國的建立聯系在一起;而研究人員則秉承理性經驗主義,強調對‘社會形態’的研究。”(125)夏爾·亨利·屈安、弗朗索瓦·格雷勒、洛南·埃爾武埃:《社會學史》,第117頁。由于前者地位更高,產出成果也更多,導致社會學與官方立場越來越接近。因此,新一代思想家強烈抨擊占據大學高位的社會學大師,典型如保羅·尼贊(Paul Nizan)。在1932年出版的頗受好評的小說《看門狗》(LesChiensdegarde)中,尼贊以涂爾干為對象,實則將整個社會學都視為官方的“看門狗”:“涂爾干窮其一生都以捍衛資產階級為使命。他的文本都是宣傳品。涂爾干的成功正是來自道德宣傳,也因為他是第一個正面捍衛社會的學者。”(126)夏爾·亨利·屈安、弗朗索瓦·格雷勒、洛南·埃爾武埃:《社會學史》,第122頁。
其次,二戰期間及之后,共產黨在法國政治和思想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傳統上,馬克思主義者總是傾向于敵視社會學,認為社會學是資產階級的學問,是維護舊體制并且和馬克思主義對抗的思想武器。法國共產黨的懷疑并非全然沒有道理,因為緊隨二戰而來的冷戰促使美國的各種基金會和組織主動與法國社會學進行聯絡,法國社會學不僅接受研究資助,向自由主義靠攏,而且與美國東部地區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建立起密切的學術網絡。在此狀況下,“法國共產黨排斥社會學研究,認為在代表工人階級發聲這方面,社會學是自己潛在的敵手”(127)Robert Dingwall,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Edition,” p.xii.。結合以上兩方面原因,馬克思主義者開展自己與社會學實際上不乏相似之處的研究,同時也不斷攻擊作為“資產階級科學”的社會學,幾乎享有必然的正當性。
60到70年代,在諸多馬克思主義群體中,阿爾都塞及其弟子的研究尤為眾人所知,阿爾都塞的影響不僅僅針對廣義上的學術界(或說巴黎的學者群體),而是深入到社會學中:“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法國思想生活中有著比英國和北美高得多的支配地位。戰后階段,社會學的爭論也受到阿爾都塞和普蘭查斯的形塑,這兩人都在馬克思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主張,要求取代‘資產階級社會學’。”(128)Simon Susen and Bryan S. Turner, The Legacy of Pierre Bourdieu: Critical Essays, p.xvi.與此類似,法比亞尼也在《社會學:歷史、觀念和潮流》中說道:“路易·阿爾都塞……對社會科學的重要性有所保留,但他的作品的確影響了若干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的職業,包括克里斯蒂安·博德洛(Christian Baudelot)、羅杰·埃斯塔布萊(Roger Establet)和伊曼努爾·特雷埃(Emmanuel Terray)。”(129)Jean-Louis Fabiani, La sociologie: Histoire, idées et courants, Paris: Sciences Humaines, 2021, p.15.事實上,阿爾都塞的思想在60到70年代,不僅在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研究中有影響,而且滲透到了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語言學和經濟學之中(130)參見弗朗索瓦·多斯:《從結構到解構:法國20世紀思想主潮》(下),第222-239頁;弗朗索瓦·多斯:《結構主義史》(修訂版),季廣茂譯,北京:金城出版社,第385-391頁。。
然而在思想上,阿爾都塞盡管偶爾高度評價孔德和涂爾干(131)參見路易·阿爾都塞:《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第111頁;路易·阿爾都塞:《哲學的形勢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第1期。博德洛對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研究很感興趣,但依然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提出諸多批評,見弗朗索瓦·多斯:《從結構到解構:法國20世紀思想主潮》(下),第226-227頁;Ana Maria F. Almeida, “Entrevista com Christian Baudelot e Roger Establet,” Tempo Social, vol. 20, no. 1, 2008, p.183.,但他及其弟子從未真正接近社會學,反而多次嚴厲批評社會學(132)參見阿圖塞:《列寧和哲學》,第23、25、212-213、219、235頁。,而且試圖更新乃至替代社會學。從50年代末到60年代早期,阿爾都塞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在于“科學”的本質,也就是一種思想具有何種性質才能說是“科學的”,這個概念是之后確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為科學的必需步驟(133)參見路易·阿爾都塞:《黑格爾的幽靈》,唐正東、吳靜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21-342頁;路易·阿爾都塞:《孟德斯鳩:政治與歷史》,霍炬、陳越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9-25、60頁。。阿爾都塞1963年對布爾迪厄和帕瑟隆的引介,同樣反映了他在這方面的思索,以至于盡管他在理解60年代法國社會學的形態方面不乏洞見,但整篇引介卻沒有集中在社會學和布爾迪厄等人身上,而是不斷探究社會學究竟在何種意義上是科學的和不科學的(134)參見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ntroducing Bourdieu and Passeron, pp.5-21.。多斯非常恰當地總結了這一時期阿爾都塞為自己設定的主要理論任務之一:“在‘概念哲學’的基礎上,檢驗不同社會科學的有效性。”(135)弗朗索瓦·多斯:《結構主義史》,第355頁。簡而言之,60年代早期的阿爾都塞認為,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科學,因而也享有評價其他學科和學問的優越性。
巴利巴爾批評布爾迪厄原創性不足,認為后者的很多概念與想法馬克思主義也有(136)參見étienne Balibar and Charles Barthold, “Etienne Balibar in Conversation: Revisiting European Marxism,”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36, no. 7-8, 2019, p.239.。此外,尼科斯·波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同樣深受阿爾都塞影響,且與阿爾都塞關系密切,他明確表示不贊同布爾迪厄的諸多觀點。例如,波朗查斯以典型的阿爾都塞主義觀點,集中攻擊布爾迪厄“階級”概念的“多元論”定義:
在確定階級定義時使用多種標準的問題值得注意。……然而這并不包含任何一類多元標準(六種,八種或十四種),而完全只有一種確定的標準,它是一個與結構各個方面的復雜關系,這些方面本身的定義也完全是確定了的。例如在意識形態方面提出任何一種“多元論”都是錯誤的,好比教育方面、階級意識方面、對待勞動的“合理化”或“非合理化”方面等等——我主要想的是布爾迪厄那些人所共知的著作。它之所以錯誤,是在這樣的意義上……(137)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葉林、王宏周、馬清文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98-99頁。
可以設想的是,阿爾都塞主義者針對社會學、針對布爾迪厄本人的批評態度(138)參見Johan Heilbron, French Sociology, p.156.,混合波朗查斯等人的社會學家身份,再加上他們60到70年代的聲譽(139)參見弗朗索瓦·多斯:《從結構到解構:法國20世紀思想主潮》(下),第234頁。,顯然有可能激怒布爾迪厄。在1988年的訪談中,布爾迪厄極其少見地將這種復雜的競爭關系和盤托出:“《社會學的技藝》出版后,這些理論家蜂擁而至。在不同時期,《技藝》寫出來也會不同。認識論前提由科學實踐的反思推動,這種反思在那個時候最為急迫。因為危險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所以話語所強調的內容也必須改變。在寫作《技藝》的那個時候,側重于理論一極以反對實證主義是必要的。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當阿爾都塞主義的浪潮橫掃法國時,我就更想強調經驗一極以對抗這種理論主義,這種理論主義把能動者還原為結構的‘承載物’。”(140)Pierre Bourdieu, Jean-Claude Chamboredon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p.252.
(二)無知和虛偽:布爾迪厄的回應
如上所說,布爾迪厄事實上非常清楚阿爾都塞主義的影響力,以至于認為要站在這種影響的對立面以平衡知識界的取向。針對阿爾都塞主義在社會學的影響力,借助《再生產》英譯本的出版,布爾迪厄也直接挑明,要求英語世界的讀者把自己的研究與阿爾都塞主義區分開:“由于當時的哲學氛圍,這種‘政治’解讀也經常混合著‘理論’解讀,或更準確說是理論主義的解讀:《再生產》的英譯本首次出版時(差不多是法語首版的10年后了),英國知識界正處在阿爾都塞主義哲學家的宏大理論的掃蕩下,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套習語之下,他們更加‘一般性’地簡化了在《繼承人》和《再生產》中讀到的‘命題’。”(141)Pierre Bourdieu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p.viii.除開這種直接的區分,對于阿爾都塞主義既從政治上貶低社會學,又在理論上輕視社會學的做法,布爾迪厄至少采取了四種不盡相同的回應方式。
第一,在政治立場上保持距離,認為阿爾都塞主義是偽激進主義,也就是并不真的反對體制。布爾迪厄從未加入共產黨,甚至不情愿與馬克思主義發生過多關聯,如法比亞尼所說:“在他那篇非常著名的關于社會空間與階級來源的文章里,布爾迪厄毫不遲疑地聲明:‘一種社會空間理論的建構,便假定著與馬克思學說的一連串決裂。’他甚至斷言,在使社會空間理論能更適切的努力中,馬克思學說是妨礙進步的最大阻力。”(142)讓-路易·法比亞尼:《布爾迪厄傳》,第69頁。
但布爾迪厄的反對還不只停留在理論上。1996年,布弗雷斯在和布爾迪厄的談話中說道:“先說清楚,我對既存秩序的同情,并不比(校園激進主義)更多。而且對哲學體制和傳統大學體系的反叛,肯定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更多。我當時很快就產生懷疑,特別是針對阿爾都塞:他融入既存秩序如此之深,以至于我很難相信他是要真的改變它。很多‘顛覆型’哲學家都給我這種印象……”布爾迪厄對這一說法表示贊同,并且譏諷地說道:“哲學家的特性之一就是他認為再沒有別人比自己更有反思精神了。”(143)Jacques Bouveresse, Bourdieu, Savant & Politique, Paris: Agone, 2004, pp.53-55. 對阿爾都塞的類似批評,見伊麗莎白·盧迪內斯庫:《拉康傳》,王晨陽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年,第379-380頁;伯努瓦·皮特斯:《德里達傳》,第187頁。
第二,嚴厲批評阿爾都塞主義者的社會學素養。一方面,布爾迪厄認為阿爾都塞主義者實際上并不懂社會學,甚至沒有讀過多少社會學著作。1999年,布爾迪厄在訪談中說道:
在馬克思主義者以及當時很多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中間,讀韋伯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經常說如果不了解韋伯,幾乎就沒辦法做社會學。……阿爾都塞也同意,他不僅承認馬克思主義者沒有認真對待韋伯,也承認他自己并沒有讀過韋伯的作品。韋伯被看成是“右派分子”……(144)Simon Susen and Bryan S. Turner, The Legacy of Pierre Bourdieu: Critical Essays, pp.113-114.
另一方面,布爾迪厄也不斷指責阿爾都塞主義者對馬克思的態度也算不上“科學”,因為他們不是把馬克思的學說作為有正確也有錯誤的待檢驗思想,而是當作不變的真理來供奉,以至于采取一種二元對立的宗教式態度(145)參見皮埃爾·布爾迪厄:《自我分析綱要》,第104-105頁。。在他看來,阿爾都塞主義為“馬克思主義的宗教—先知一派”,要壟斷對馬克思的解讀(146)參見Pierre Bourdieu,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Martin Heidegger, p.127; Pierre Bourdieu,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9—1992, p.229.。在這種心理作用下,阿爾都塞主義者對馬克思關鍵概念的理解也不可能正確,也就是說,他們甚至可能根本不懂馬克思,如布爾迪厄所說:“的確,我不斷返回到一些被認為已有定論的基礎事物上。比如資本,我們都知道它是什么……你只要讀一讀《資本論》,或者更好是讀一讀《閱讀〈資本論〉》(等等)。如果資本是他們說的那樣,那很好,但在我看來并不是。”(147)Pierre Bourdieu, Sociology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1993, p.32.這一批評有時候更加激烈,以至于布爾迪厄指控阿爾都塞主義者(也包括福柯和德勒茲)存在學風問題,都是偏好夸夸其談的人(148)參見皮埃爾·布爾迪厄:《科學之科學與反觀性:法蘭西學院專題講座(2000—2001學年)》,第183-184頁。。
第三,指控阿爾都塞主義者輕視社會學但又抄襲社會學思想的雙面行徑。這種指控最早出現在1984年出版的《學術人》中,之后被一再重復(149)參見Pierre Bourdieu,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p.104.。例如,布爾迪厄在《反思社會學導引》中論述道:
60年代以來……大學和知識分子的場域第一次被人文科學方面的專家(由列維-斯特勞斯、杜梅澤爾和布羅代爾等人領軍)所支配。一時間,所有討論的核心焦點都轉向了語言學,語言學被建構成為所有人文科學的范例,甚至像福柯這樣從事哲學工作的學者也把語言學作為自己的范例。這正是我以前稱之為‘某某學效應’(-logy effect)的緣起,我用這個詞來指許多哲學家竭力從各門社會科學中搬用方法,并模仿這些社會科學的科學性特征,但與此同時,他們卻不肯放棄‘自由思想家’的特權地位,比如:巴特的符號學,福柯的考古學,德里達的書寫學,或阿爾都塞式的企圖——他想把對馬克思進行的所謂‘科學’閱讀假冒為一種獨立自足的科學,并且充當所有科學的標尺。(150)皮埃爾·布爾迪厄:《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第191頁。
同樣的批判也出現在《自我分析綱要》中,盡管置放在哲學與社會學競爭的背景中(151)參見Pierre Bourdieu, Sketch for a Self-Analysis, pp.13-14.。
第四,在馬克思主義內部尋找阿爾都塞主義的替代物,特別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E. P.湯普森。湯普森對阿爾都塞在英國的流行尤其不滿,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湯普森說道:“對于阿爾都塞的著作,我從形式上完全拒絕,從內容上絕大部分拒絕。”最晚從1974年開始,湯普森就醞釀寫一篇反對阿爾都塞的文章(152)參見斯科特·漢密爾頓:《理論的危機:E. P.湯普森、新左派和戰后英國政治》,第93頁;E. 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London: Merlin, 1996, p.xi.。文章寫作期間,湯普森于1975年造訪巴黎,在法國科學院組織的歐洲社會史討論會上遇到布爾迪厄(153)參見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第272頁。,隨即被后者及其團隊的研究打動。1978年,湯普森原本意在反駁阿爾都塞的文章最終以著作的形式出版,即著名的《理論的貧困》。在這部激烈抨擊阿爾都塞主義的著作中,湯普森除了向英國的讀者告誡阿爾都塞主義的危害,還推薦了用以替代的人物:“他們(指阿爾都塞主義者)可以仔細閱讀皮埃爾·布爾迪厄的作品,以完成自己的再教育。”(154)E. 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p.235.
另一方面,盡管布爾迪厄在某些地方也對湯普森提出批評(155)參見皮埃爾·布迪厄:《法律的力量:邁向司法場域的社會學》,第498頁。,但絕大多數時候,布爾迪厄對湯普森均持贊揚和肯定的態度。除了于1976年在自己主編的刊物上發表湯普森的文章,布爾迪厄不僅多次高度評價湯普森的歷史研究,也非常正面地看待湯普森對阿爾都塞主義的批判,更是多次援引湯普森對阿爾都塞主義流行的貶稱“法國熱”(French flu)(156)參見皮埃爾·布爾迪厄:《帕斯卡爾式的沉思》,第107頁;皮耶·布赫迪厄:《所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會學文集》,第105頁;Pierre Bourdieu,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9—1992, p.64,p.141,pp.143-144,p.148,p.310; 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256.。不可否認,布爾迪厄推崇湯普森的主要理由顯然在于理論和學術上,特別是后者對馬克思主義的靈活理解、歷史主義取向(與阿爾都塞主義的理論主義取向截然對立)以及對極端結構主義立場的反感(157)參見Richard Harker, Cheleen Mahar and Chris Wilkes, e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The Practice of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0, p.21.。然而客觀上,正如布爾迪厄所說,占有一個立場就是提出一種觀點,而提出一種觀點也是占有一個立場(158)參見Jacques Bouveresse, Bourdieu, Savant & Politique,p.53.。因此,布爾迪厄對湯普森的支持,實際上區分出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因而成為針對阿爾都塞主義的替代性批判,不僅在馬克思學說的解讀和使用上再度與阿爾都塞主義構成競爭關系,而且這種批判在形式上無須反對馬克思主義本身。
結 語
為什么布爾迪厄的社會學與阿爾都塞主義存在理論上的相似性,甚至的確受到阿爾都塞的影響卻激烈否認,在從1970年到2002年長達30年的時間中,持久地敵視阿爾都塞主義?既有研究一致采取了內部主義視角,其潛臺詞是“布爾迪厄本不應當如此”或“布爾迪厄大可不必如此”,這種視角從未真正揭示出復雜的實際過程如何以及為何。與此不同,我們認為盡管布爾迪厄與阿爾都塞的確存在重要的理論分歧,但完全從理論層面來理解這一理論分歧卻是片面的,也不足以解釋布爾迪厄的持久敵視態度。
要充分理解布爾迪厄對阿爾都塞主義的批判,必須回返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由此不難看到,布爾迪厄對阿爾都塞主義的理論批評,只是他對阿爾都塞主義整體性指控的一個部分。這一整體性指控除理論性質外,還有以下三個理論分歧之外的原因:(1)消解影響焦慮:作為布魯姆意義上看重自身思想原創性的學者,布爾迪厄對源于阿爾都塞和其他評論者的影響產生焦慮感,而為了消解焦慮,布爾迪厄選擇以自說自話、省略出處和刻意誤讀的方式對待阿爾都塞主義,由此表現為強烈的批判態度;(2)學科地位抗拒:由于法國的哲學長期凌駕在社會學之上,且布爾迪厄認為阿爾都塞主義對普通人、社會學乃至他本人也存在由此而來的優越感,因此,布爾迪厄將阿爾都塞主義辨認為“認識論貴族主義”,從道德和政治的角度提出批判;(3)學術空間競爭:由于阿爾都塞主義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既從階級屬性上貶低社會學,又在同一個學術空間中展開相似研究,還不斷對布爾迪厄提出批評,因此,布爾迪厄從阿爾都塞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身份認同入手,批評阿爾都塞主義是偽激進主義、缺乏社會學素養、有著貶低社會學又利用社會學的雙面行徑以及無法代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如圖4所示:

圖4 修正模型視角下布爾迪厄對阿爾都塞主義的批判
考慮到研究目標,我們盡可能準確和充分地還原與布爾迪厄和阿爾都塞相互評價有關的社會背景(主要是學術和學科背景),也盡可能以原文引文的形式讓布爾迪厄本人說話,以客觀呈現他的個人態度。盡管依舊受限于材料,但在布爾迪厄的社會學與阿爾都塞主義的關系上,我們已邁出了或許仍不乏問題的一小步。與此同時,我們希望在更加深入、更加一般性地理解社會學的學術評價上邁出嘗試性的一小步:學術評價研究除了采取側重于理論評價標準的內部主義路線,也有必要考慮更多關注社會化的行動者和歷史背景,從而在學術評價研究中采取多維視角,而基于DBO理論的修正模型僅僅是一個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