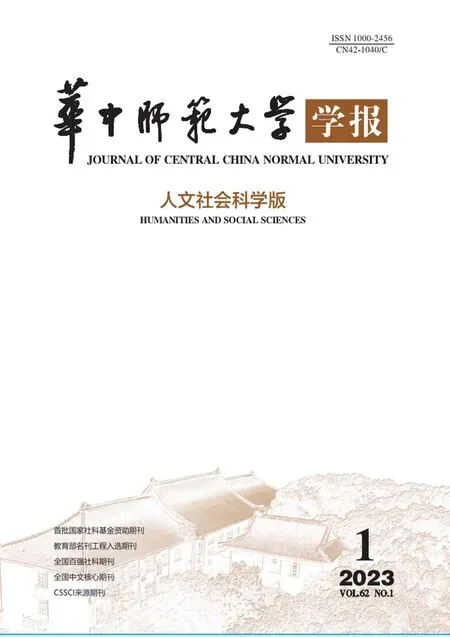論民國時期北京總商會會長安迪生被拘案
朱 英
(華中師范大學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湖北 武漢 430079)
辛亥革命肇建了中華民國,各種實業團體在民初層出不窮,一度出現發展實業的熱潮。清末即開始籌備的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也于民國元年創立,使商會擁有了全國性領導機構,其能量與影響更加令人矚目。當時的工商界人士甚至將商會與國會兩相比較,認為“國會雖可解散,而解散商會”,政府卻無此力量(1)參見《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在上海開第一次大會紀事》,《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會報》第1年,第9號,1914年6月,“紀事”,第41頁。。農商部官員也承認:“商會為社會之中堅,又為經濟之樞紐,關系于一國之強弱存亡者甚大。”(2)《全國商會聯合會開會記》,《申報》1914年3月16日,第10版。民國北京政府隨后頒行《商會法》及其施行細則,以法律形式進一步確認商會的社團“法人”性質。種種情況似乎都表明,商會的社會地位不斷得到提升,商會領導人的威望也隨之越來越高。然而,數年后發生的北京總商會正副會長被拘案,卻表明在官廳眼中作為民間團體的商會及其領導人,實際上不僅沒有什么值得尊敬的社會地位,而且仍然可以隨意捏造罪名予以拘押,這一殘酷現實不能不令工商業者大失所望。迄今為止,該案尚未引起商會史研究者的注意,沒有相關研究成果問世,本文擬就此問題作初步探討,以促進商會史研究的發展(3)研究北京商會的成果主要有劉娟:《近代北京的商會》,《北京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張淑生:《政治漩渦中的北京總商會研究(1916—1938)》,南京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年;白玉:《北京商會研究(1903-1909)》,北京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敖凱:《京師總商會研究(1906—1928)》,首都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等等,但這些成果都沒有論及1920年北京總商會正副會長被拘案。。
一、北京總商會會長安迪生被拘案的發生
在商會地位日益提高之際,位于京師的總商會正副會長安迪生、殷文煜在1920年3月6日突然被警察廳拘押。該事件在當時稱得上是一大新聞,故不僅當地報紙多有報道,而且上海發行全國的各大報也都及時跟進予以報道。北京《晨報》率先發表的報道內容如下:
京師總商會會長安迪生等以有侵吞公款嫌疑,為各行商董等在國務院、內務部、農商部、警察廳等處遞呈舉發,并請警廳派員至總商會接收彼等已交之款,因此警察廳于前日下午一時派督察長李景君會同該區署長前往總商會接收,安氏與煤行商董殷海陽等不肯將款交出,且不許警廳特派員閱看賬簿。兩方交涉至六時余,仍無結果,李督察長因請其到廳見吳總監解決此事。及到警廳,吳總監延安、殷等至客廳內,仍以事關貧民生計,勸其襄贊此舉,安、殷等堅持警廳無干涉此事之權,態度極其強硬,遂被拘留廳內,責令將此公款賬簿交出檢閱,并聞此案辦理方法,將由地方檢察廳提出公訴。(4)《北京商會長安迪生被拘》,《晨報》1920年3月9日,第3版。
這篇報道只是非常簡略地介紹了安迪生等被警察廳拘押的原因及情形,因未有具體闡述,諸多細節令讀者不明所以。報道中提到的煤行商董殷海陽,即為時任北京總商會副會長的殷文煜(又稱殷文玉)。上海《新聞報》和《時報》報道的內容與《晨報》大體相似,《申報》于次日發表“京師總商會長安迪生等昨日突被警廳拘押”的報道,附有京師警察廳致各省通電說明拘押安迪生緣由(5)參見《京警廳與總商會之交涉》,《申報》1920年3月10日,第7版。。與各報略有不同的是《民國日報》的報道,該報除發表相似內容的報道之外,還透露了各報所沒有的如下內容:
茲聞安、殷二人被拘留之消息傳出后,其朋比為奸之石某李某韓某關某等人,頗為憤懣,遂在秘密處所集議,擬先慫恿京內商界起而向警廳抗爭,將安、殷二人索出,否則即以罷市對待。不料石某等奔走多處,大碰釘子。原來各行商董素日因安、殷等把持會務,遇事武斷,已大傷感情。此次被拘,不但與商界公益無關,且以堂堂總商會之會長,因肥己利私之事,被拘官廳,實屬有損商界體面,除不與援助外,并已有人主張另選會長之舉,因此石某等大為懊喪,惟有另想妙策而已。(6)《北京商會長被拘情形》,《民國日報》1920年3月11日,第6版。
這一報道顯然對安迪生很不利,《民國日報》也是當時唯一肯定京師警察廳拘押安迪生行動的報紙。從相關史料記載以及后來的事實看,該報道所說只是反映了一方面情形,并不全面也不客觀。在此前后,上海《民國日報》一直對商會的評價不高,甚至持否定態度,尤其是后來商民運動期間出現商會存廢之爭,該報作為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的喉舌,更力主商會是反對革命的舊式商人團體,應予廢除,由商民協會取而代之。
人們不禁要問,堂堂京師總商會正副會長,為何警察廳能夠隨意拘押?當時的輿論也十分關注總商會正副會長被拘押究竟緣于什么原因?分析各方面史料的記載,概而言之,北京總商會正副會長之所以被拘押,既有遠因,又有近因;近因中不僅有外因,而且有內因。
所謂遠因,與辛亥革命不無關聯。警察廳拘押總商會正副會長之后,顯然也意識到此案與拘押普通百姓不可等同,遂向全國各督軍、省長通電說明“清理商會公款情形”與緣由,對其拘押商會正副會長的行為加以解釋。該通電首先即說明:“辛亥秋,京城市面恐慌,經前內外城巡警總廳申請前度支部撥官款百余萬兩,交總商會轉發各商承借,以資接濟。”(7)《京師警察廳之通電》,《新聞報》1920年3月11日,第2張第2版。約定六個月后歸還。而該款即是京師警察廳欲清理的商會公款,也是有些報道所說的導致此案發生的遠因。
武昌起義爆發后,一度在全國引起短暫的金融恐慌,“人心惶惑,紛提現款”,導致銀根奇緊,商業衰敗。為勉力維持,各地商會都不得不緊急呈請地方官府劃撥官款,轉由商會息借商家周轉,以免閉門歇業。北京雖為都城,在武昌起義后同樣陷于金融動蕩局面。北京總商會請求官府劃撥官款,幫助商家渡過金融危機:
辛亥武漢起義,至九十月間京師金融頓形停滯,市面忽起極大恐慌。清廷以京都根本之地,深恐人心搖惑,國本動搖,爰發內帑銀一百二十五萬兩,交由商會轉給各商,以備維持市面之用。商會于收到此款,即按放賬辦法,由各商號提出擔保息借,約期歸還。(8)《北京通信·京師總商會會長被捕詳情》,《申報》1920年3月12日,第6版。
但這筆官款后來卻成為京師警察廳與北京總商會會長安迪生發生矛盾甚至是沖突的遠因。“據警察廳之文告,謂其經手壬子接濟市面款項,報銷不清,顯犯刑律上之侵占罪。”實際上,這只是警察廳為拘押總商會正副會長尋找的借口。在歸還這筆官款的約期屆臨之前,京師又突發兵變事件,使受該款接濟的商家遭受較大損失,遂申請延遲歸還。據報載,辛亥金融動蕩后,“歷時未久,忽有壬子正月十三兵變之禍,凡被焚劫者,大抵均系前時借用接濟款項之戶(受接濟者都系銀號當鋪),而各戶被焚劫之損失,其總數且有一千五百余萬之多,因之是項接濟市面款項,迄今未能收回。對于官家,當然不能償還”,延至1919年,財政部于當年九、十月間“曾有要償此款之令,旋經商會分向府院遞呈,以壬子兵燹撫恤迄未蒙發,請求緩還接濟之款,當經國務會議通過,批準在案”(9)《北京通信·京師總商會會長被捕詳情》,《申報》1920年3月12日,第6版。。可見,辛亥年間官撥接濟款之所以未能按約期歸還,系事出有因,在財政部要求歸還此款時,北京總商會向府院呈明緣由,請求暫緩歸還,獲國務會議通過批準在案,并非警察廳所指控之數年拒不清理,更不應成為警察廳拘押總商會正副會長的理由。
辛亥年的此項官款又稱息借商款,雖拖延近十年未能償還,但北京總商會也并非如警察廳所指控的那樣根本不愿清理。實際上,總商會先前即設立清理息借商款的專門機構。“前會長陳陞繼任時,以賬目焚如,組織清理公款股,以專責成”,安迪生繼任會長后,“復定辦法,凡歸借款各事,均由清理股主任及清理各員專司其事”。因此,辛亥年間的這筆息借商款,實則并非真正構成此案之肇因,只是京師警察廳拘押總商會正副會長的托詞,至于個中奧妙,還需探尋其他方面的原因。
輿論也曾指出,“惟辛壬間之會長則非安迪生與殷文玉二人,乃此次竟將安、殷二人拘留者,蓋尚有近因焉”(10)《北京通信·京師總商會會長被捕詳情》,《申報》1920年3月12日,第6版。。如前所說,對北京總商會而言,近因中是既有外因,又有內因。所謂外因,乃是總商會以及會長安迪生與警察廳之間的關系日趨惡化。據報道,隨著市面的恢復,各商家陸續將接濟款交還商會,但隨后又“遭復辟之變,商人損失甚巨,商會即擬將此款償還商人損失,未經政府核準”。京師警察廳則希望將此款“移作維持平民重整旗鼓之用”。但總商會仍“復持前議,逕呈總統批準,以此款抵償復辟時商人所被之損失。警廳知總統批準,已無可挽回,遂與商會長暨會董等情商,勸其襄助盛舉,會長安迪生等以此事既經總統批準抵償商會損失,警廳無干涉之權答之”(11)《安迪生被拘之原因》,《新聞報》1920年3月12日,第2張第1版。。警察廳對總商會的這一做法十分不滿,兩者之間遂由此而產生矛盾。1919年,警察廳又有“請提該項官款為貧民工廠經費之議”。據警察廳稱,“以八旗生計維艱,困苦情狀不堪言喻,擬籌設工廠,提倡工藝”,并請由財政部批準以總商會歸還之官款為辦廠經費。與此同時,警察廳向總商會提出清查該款要求:“聲明目前僅屬清查,將來體察市面,再酌令繳款。乃該會竟一再支吾,傳聞該會內一部分商人把持挪用,并有私行接濟個人之事,報紙登載,嘖有煩言。”(12)《京師警察廳之通電》,《新聞報》1920年3月11日,第2張第2版。但總商會仍堅持認為財政部和大總統已批準暫緩還款,再次拒絕警察廳的要求,并且拒不配合警察廳清查該款。
不僅如此,在其他一些問題上總商會會長與警察廳也多有矛盾,且愈積愈深,最終導致會長被拘案發生。安迪生事后曾發表通電坦言被拘原委:“迪生賦性憨直,遇事每多開罪奸派,實為今日召禍之端。”具體說來,安迪生此前從事的一系列活動,都不同程度地得罪了警察廳總監吳炳湘。例如《益世報》(北京)報道:
和平聯合會之發起也,反對金幣借款兌取日金也,而拒絕吳炳湘面囑登報解釋軍事協訂與日本密約一事,尤為奸人所切齒。迨天安門國民大會之風潮,迪生主席宣誓抵制劣貨,而吳炳湘之怒愈不可遏,誓必報復以快彼黨之心。他若吳炳湘佯請辭職,授意商會挽留,而迪生不聽其主使,更為彼難言之隱。(13)《安迪生出獄后行動》,《益世報》(北京)1920年10月17日,第6版。
因此,吳炳湘對安迪生一直懷恨在心,遇有機會必予報復。
另還應說明,1918年安迪生當選北京總商會會長時,正值擔任國務總理的皖系段祺瑞為首的安福系大肆擴張勢力,甚至操縱國會選舉,左右北方政局。徐世昌出任大總統后,段祺瑞雖被免職,但安福系勢力仍很強大,尤其是在參眾兩院擁有多數議席,很大程度上能夠左右當時的北京政府。所以,在政治、經濟乃至社會等許多領域都不難見到安福系勢力的身影。擔任京師警察廳總監的吳炳湘,也是安福系的骨干成員。由此不難理解,在安福系勢力強大之時,吳炳湘雖然只是警察廳總監,但也不會將總商會會長放在眼里。他不僅敢于拘押總商會正副會長,甚至還越權將合法選舉的北京總商會正副會長和全體會董解職,重新選舉新會董和會長,并安排安福系的成員擔任總商會副會長。這一特殊背景,也可以稱得上是導致本案發生的外在原因。連安迪生也意識到,“迪生自民國七年被選會長,正安福盤踞膨脹勢力之時”(14)《安迪生出獄后行動》,《益世報》(北京)1920年10月17日,第6版。,故總商會在很多問題上都受到安福系牽制,直至發生被拘案。有商董也指出,警察廳總監吳炳湘對辛亥年商會息借官款一直垂涎欲滴,“欲攫為安福部非常經費,乃藉設立貧民習藝工廠之名,遽行提取。是時安迪生適充京師總商會會長,不自量力,呈請大總統準予暫緩歸還,與彼吳氏相對抗,以致結怨甚深”。由此可見,安迪生被警察廳拘押的內幕實際上廣為人知,并非什么秘密,“其冤抑聞者無不知之,乃查安福氣焰正盛之時,人皆敢怒而不敢言”(15)《保釋安迪生之呼吁》,《申報》1920年8月7日,第6版。。
可以說,京師警察廳拘押安迪生的行為具有相當大的隨意性,根本沒有將作為社團“法人”的商會及領導人放在眼里。從相關報道中可知,警察廳起初委派督察長赴商會,并無拘押安迪生之意,只是希望接收商家已交之款,但安迪生明確拒絕,也不讓督察長查閱賬簿。僵持數小時無果,督察長請安迪生、殷文玉二人至警察廳,其目的也并非實施拘押行動,而是希望由警察廳總監吳炳湘出面說服安迪生。到警察廳后,吳炳湘總監表面上客氣地將安、殷二人請至客廳,“仍以事關貧民生計,勸其襄贊此舉”,結果“安、殷等堅持警廳無干涉此事之權,態度極其強硬”,導致吳炳湘惱羞成怒,安、殷二人“遂被拘留廳內”。可知在此前并無拘押令的情形下,完全是由于警察廳總監勸說不成,才氣急敗壞地臨時下令拘押安、殷二人,其隨意性不言而喻。可以肯定,警察廳拘押安迪生實則緣于對其不滿與憤恨,這種不滿和憤恨又是因為安氏沒有應允警察廳向商會提出的一系列要求。而警察廳作為執法機關,可謂隨意執法,甚至知法違法,反映了近代中國法制在實施過程中存在的隨意性。
在安迪生出任會長之前,北京總商會與官廳的關系十分曖昧。輿論有稱:“北京商會處于行政薈萃之區,居于官僚集眾之地,常為行政方面所左右。選舉會長董事,屢帶有官僚彩色,而非純粹商人性質。洪憲帝制,會長馮云沛首先勸進,上表稱臣,中交兩行停止兌現,北京商會不能同外省協力抗爭,其明證也。”但自安迪生、殷文煜出任正副會長之后,北京總商會在這方面發生明顯改變。“安迪生以金珠店營業,殷文煜以燒煤商營業,皆非大資本家,被舉為商會會長副會長以來,遇有妨害商業者,如公債票、如紙幣久不兌現,竭力抗議,無論有效無效,其純為商人行徑,毫無官僚氣味,為行政方面所嫉視,可斷言也。”安、殷二人之所以被拘押,對于警察廳所稱之官款一節,輿論也指出:“當時安、殷二氏未為會長,其支配方法,未必系出于其手,今雖不無關,然其屢與官僚沖突,為各方面所嫉視,實為一大原因也。”(16)本段引文均出自窺天:《北京商會》,《益世報》(北京)1920年4月22日,第7版。很顯然,輿論也知悉總商會正副會長被拘押主要是與官廳發生矛盾沖突所致。
至于北京總商會會長被拘案發生的近因中的內因,則是總商會內部因權力與利益紛爭,有會董聯名向警察廳舉報安迪生,從而為警察廳拘押正副會長提供了口實。
1920年2月,北京總商會依據《商會法》的規定舉行換屆改選。在選出新一屆會董后,接著由全體會董選舉正副會長。選舉結果為安迪生得38票,當選連任會長,殷文煜得20票,當選為副會長(17)參見《北京商會選舉結果》,《益世報》(北京)1920年2月11日,第3版。。其實安迪生并不希望連任總商會會長,甚至在1919年6月就曾提出過辭職,總商會呈請農商部挽留,農商部批示“查該會長就職以來,辦事尚屬認真,未便遽易生手”(18)《農部批留安迪生》,《京報》1919年7月3日,第3版。,他才勉強留任。本次換屆改選結果公布后,無意留任的安迪生辭不就任。其辭職函稱:
前承諸君雅愛,推為會長,三載之中,勉膺艱巨,材力短絀,愧會務發展之未能欲盡職責,又為經濟之所限,困難迭經,深自愧恧。今屆改選,正擬藉此息肩,不意復承推弟聯任,當此會務諸待進行,似弟無才,萬難勝任,況時艱孔亟,若再以病軀戀棧,深恐因應失宜,關系會務甚巨,惟有據情懇請另行推選賢能,以重會務,而利進行,不勝感禱。(19)《安迪生辭職》,《益世報》(北京)1920年2月14日,第3版。
報章刊登安迪生的這封辭職函時附加按語表示:“聞安君任內所辦各事,甚著成績,此番因困難而辭職,深為商界之不幸。”(20)《安迪生辭職》,《益世報》(北京)1920年2月14日,第3版。北京總商會的絕大多數會董也認為安迪生在上屆會長任內盡職盡責,使總商會聲譽有所改觀,遂竭力挽留他連任。
就在安迪生堅決要求辭職,多數會董盛情挽留時,上屆會董兼清理公款股清理委員的高德隆,聯同他人向警察廳舉報總商會在安迪生主導下存在換屆改選違法情形,并稱公款清理已完成,請警察廳前往接收。實際上,其舉報行為主要緣于自己沒能當選連任會董,而安迪生卻當選連任會長。根據《商會法》第24條規定,“會長、副會長及會董均以二年為一任期”,“會長、副會長及會董任期滿后,再被選者得連任,但以一次為限”(21)天津市檔案館等編:《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12—1928)》(第1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04頁。。依據以上規定,北京總商會在換屆改選前,將高德隆等連任已屆四年,依商會法不能再當選的四人名單列出,結果引起高氏等人的不滿,認為“安迪生亦已四年”,卻仍當選會長。事實上安雖連任已屆四年,“然二年董事,二年會長,依法不在不許連任限制之列”(22)《北京通信·京師總商會會長被捕詳情》,《申報》1920年3月12日,第6版。。需要說明的是,《商會法》中的此條規定,并未具體說明正副會長及會董任期分別計算,在執行過程中確實容易引起爭議。農商部后曾明確解釋,連任會董雖不能再當選會董,但可當選正副會長,而正副會長需在會董中選出,所以在初選時不應剝奪連任會董的被選權,如果仍當選會董,最終未當選正副會長,則其新選會董資格自然取消,由得票數多者遞補。為此,農商部還針對北京總商會換屆改選出現的爭議,于1920年3月發布訓令:
查商會會長、副會長連任問題,各商會因會長、副會長均由會董內選出,與會董任期合算者居多,亦有因合算致起爭執者,自應明定辦法,以昭劃一。會長、副會長與會董名稱既殊,職務權限亦各不同,依商會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其任期當然不能合算。嗣后各商會于改選之時,所有會長、副會長與會董任期,應即各歸各算。從前有因合算爭執,尚未另行選定者,亦應照此辦理,以歸一律,而免爭端。(23)天津市檔案館等編:《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12—1928)》(第1冊),第66-67頁。
由此可知,北京總商會在改選前將連任會董名單單獨列出,以示不能當選,確有不當,但農商部并不認其違法,只認為是對《商會法》相關條文理解不準確,要求各商會今后改選時統一按訓令辦理。所以,這方面的指控并不足以對安迪生構成威脅,警察廳也不會糾結于此。
高德隆等人對安迪生的另一指控,是把持挪用未還官款,而這正是警察廳之前與安迪生發生矛盾的癥結。顯而易見,總商會前會董的這一指控,使早就對安迪生懷恨在心的警察廳總監吳炳湘獲得了下手機會。高德隆等人向警察廳呈稱:“此項官款清理完竣,請派員監查。”吳炳湘隨即“派員再赴該會查核賬目……詎該會長安迪生殷文煜恃符抗拒,百方勸導,堅不肯將賬簿交出,致官廳不能清查官款,誠不知該安迪生等遵何法律,具何理由?人謂其把持挪用,不敢將賬簿交出,豈盡無因”。于是,警察廳以“侵占公務上管有財物,刑律規定綦嚴,該安迪生等既有侵占嫌疑,自未便再事放棄”(24)《京師警察廳之通電》,《新聞報》1920年3月11日,第2張第2版。,遂將總商會正副會長雙雙拘押。
正是由于上述之遠因與近因,以及近因中的外部原因與內部原因等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與北京總商會多有矛盾的京師警察廳在并無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僅憑別有用心者之不實舉報,即對北京總商會正副會長輕易實施拘押,并提出公訴,人為制造了一大冤案。該案的發生,既說明《商會法》頒行后商會社會地位的提高與所謂法律保障,在實施過程中難以落地,同時也證明近代中國法規的建設與執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為因素的影響與制約,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和隨意性。
二、對北京總商會會長安迪生的起訴與判決
京師警察廳在拘押安迪生和殷文煜后,其目的并不只是對總商會給予一般性警告,而是一心想向檢察廳提出公訴,以判處違法犯罪之名將總商會會長關進牢房,但其針對的主要是先前屢次與警察廳對抗的安迪生。殷文煜因剛當選為副會長,而且尚未正式就任,也未參與以前抗衡警察廳的行動,只是因安迪生而一起被拘,最后被提起公訴的罪名也不是貪污公款,而是吸食鴉片煙。
為了獲得輿論的諒解與支持,京師警察廳在拘押安、殷二人的次日,即向《晨報》館致送公函,歷數“該會長等竟深藏固拒,倘非別有情弊,何至延抗若此,其把持挪用,人言不為然,因查刑律第三百九十二條關于侵占公務上管有財物規定綦嚴,該會長拒絕查賬,顯有侵占嫌疑,自未便再事放棄”。該函還指出此案必須“依法辦理,除函農商部查辦外,誠恐有不逞之徒,造謠煽惑,用將始末詳情,函達貴報館,即希將原函登之報端,以便周知,而免淆惑”(25)《京師警察廳公函》,《晨報》1920年3月9日,第6版。。《晨報》對警察廳可謂言聽計從,不僅照登其公函,隨后還報道:
京師警察廳近日清算商會會長吞沒公款一案,現在已有頭緒。昨據內左四區查復東城確有兩家使過辛亥接濟市面借款,一為義豐號,一為天益泰,業已歸還,而商會并未注銷此款。又聞日前八埠已公舉代表吳鴻昌赴警廳,遞稟控告商會吞沒花界公益捐款,請為追究等語,聞警廳刻已派員調查矣。(26)《安迪生吞款昨聞》,《晨報》1920年4月5日,第3版。
安迪生一案尚未開庭審理,《晨報》的報道即與警察廳口徑一致,斷定安氏侵吞公款,從報道所用標題及內容即可看出其明顯傾向。拘押安、殷二人后,京師警察廳不斷向報章放出不實訊息,暗示二人有罪,將提起公訴。有報道謂:“安迪生被拘后,現托某要人說項,愿將賬簿交出核算。”(27)《國內特約電》,《時報》1920年3月13日,第2版。另有消息稱:“北京商會長安(迪生)仍押警廳,現查出侵吞公款四十余萬。”(28)《北京專電》,《時報》1920年3月23日,第2版。然而實際情況是京師警察廳強行將總商會“賬簿冊表及現款抵押抄去,在廳清查三月有余,迄無罪證可指,不得已以牽強假借之理由,越權擅請前大理院院長姚震解釋,始移送法廳起訴。原訊之檢察官認為無罪,擬即免訴,吳炳湘復商同前司法總長朱深及前大理院長姚震,授意改派檢察官,始以提起訴訟”(29)《安迪生自述之代電》,《益世報》(北京)1920年9月17日,第3版。。
在此之前,北京總商會首飾業等業會董,聯名“具呈請保釋總商會會長安迪生等,而京師警察總廳以總商會會長安迪生等,既有侵吞公款嫌疑,拘留警廳,現正在清理賬目,調查證據”為由,不允許保釋,并聲稱安迪生“不宜再充當會長,應即令其退職”(30)《安迪生被拘續聞》,《新聞報》1920年3月16日,第2張第2版。。6月,曾一度傳聞安迪生行將釋放:“商會會長安迪生被警廳拘禁已兩月余,曾經警署訊實,安氏雖有短欠公款之事,皆系為地方公事支用,并非侵吞公款。因此,當局擬將安氏開釋。然恐安氏出后有何舉動,聞須得有確實保證,方能開釋云。”(31)《安迪生行將釋放》,《益世報》(北京)1920年6月5日,第3版。事實上,安、殷二人不僅沒有被釋放,甚至連保釋也不允許。
安、殷二人從3月初被拘押,一直沒有開庭審理,直至五個月之后才被地方檢察廳向審判廳提起公訴。被告共3人,第一被告自然是安迪生,第二被告并非殷文煜,而是北京總商會會計胡俊舫,安、胡二人均以違法偽造文書詐財被起訴。殷文煜被列為第三被告,系以違法吸食鴉片煙而被起訴,可見他確實是受到連累而卷入了這場不應有的官司。安、胡二人各自聘請律師作為辯護人,殷文煜則沒有聘請辯護律師。
8月3日第一次開庭審理。不知何故各報均無首次開庭的詳細報道,只說“安迪生經各商家保釋一節,已志昨報。聞昨日第一次開庭,所有紳商赴廳旁聽者,人數頗多,咸望宣告無罪。惟據某方面仍欲判以輕微罪名,以顧全司法面子,此說不知確否”(32)《安迪生案昨已開庭》,《益世報》(北京)1920年8月4日,第3版。。4日第二次開庭,因首次開庭時總商會會董到案者寥寥,且口供頗不一致,“故今日添傳商會書記薛某并前任會長馬潤田到案,于上午十余鐘繼續開庭”。法庭先向薛某詢問:“各項借的公款,安迪生曾在會報告否?答:報過。”又問:“在大會抑職員會報告?答:開會次數太多,記憶不清。”隨后,馮潤田接受法庭詢問,告以辛亥年接濟公款共計125萬兩,由大清銀行交付商會,六個月為期,行息六厘,商會息借后再照此借給各商號。到期后,“嗣因國體改建共和及壬子兵變,未能交還”。法庭還詢問,如有接濟款未借與商號,商會是否仍出利息?回答是“仍出利息”。最后,法庭喚安迪生、胡駿舫到庭,“胡先將賬簿交齊推事,遂對安、胡二人宣告:本案須待調查,今日辯論中止”(33)《安迪生二次開庭》,《益世報》(北京)1920年8月5日,第3版。。
從報道看,安迪生案的前兩次開庭似乎都比較簡單,并沒有說明究竟以何種罪名起訴安迪生,直至第三次開庭,才獲悉是以偽造私文書詐財提起公訴,共計六條,分別是:撥借國貨維持會洋二萬元,另還有補助商事公斷處及商業夜班傳習所經費,報館廣告費,赴上海聯合會旅費,建筑商會樓房用款,以公款移作商會經費。法庭宣讀后,安迪生之辯護人發言,強調“此案有最要原因,就是前京師警察廳意欲提取前項借款,當時會長安迪生因北京市面諸待維持,有從緩歸還之必要,是以曾向總統求從緩歸還,曾經指令照準,雙方意見緣此而起,而高德隆等認為警廳與商會會長各走極端,恐將來累及自身,因向警廳遞稟聲明,并非告發,此為最初原因”。辯護人之所以強調這一背景,無非是向法庭闡明此案絕非一般案件,系由警察廳與商會會長之間的矛盾而起,高德隆只是向警察廳予以聲明,并不是要告發安迪生,故而根本不應有此公案之起訴。此外,辯護人還對有爭議的這筆借款的性質進行了闡述,認為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商會致大清銀行復函,并度支部照會以及前馮會長庭上證詞等,都足以證實“此款純為借貸性質”,“既是借貸性質,毫無刑事之可言”。對于公訴方提出的六條起訴理由,辯護人也“逐一駁辯,大致謂證據理由均不充足,當然宣告無罪”。聽了辯護詞之后,檢察官表示:“此案是否為借貸性質,或為保管性質,請審判長主持。并謂安迪生系屬商人,容或缺欠法律知識,亦可圓通辦理。”在三次庭審過程中,殷文煜都很少被提及,只是陪同安迪生被提起公訴者。第三次庭審結束前,法官問殷文煜是否有話要說,殷氏感覺十分冤屈,只說了三句話:“一非現刑犯,二未經人告發,三自請戒煙,當然無罪云。”(34)本段引文均出自《安迪生案三次開庭》,《益世報》(北京)1920年8月8日,第3版。
安迪生案三次開庭后,等待審判廳判決。在此期間,北京政局發生重要變動。1920年7月14日直皖戰爭爆發,皖系很快全線潰敗,19日段祺瑞通電自請罷免全部官職,隨后由直奉兩系控制了北京政府。與此相應,以皖系為靠山的安福系也受到致命打擊,先前的強大勢力和影響即刻土崩瓦解。由于安迪生案與安福系骨干成員警察廳總監吳炳湘密切相關,可以說是其一手制造的冤案,此時安福系已經垮臺,不僅不再有控制力,而且還會受到清算,這一政局變動對安迪生案的宣判自然會產生影響。
另外,在安迪生案第三次開庭之際,北京百余商家聯名呈文地方審判廳,認為“近者安福既倒,安君亦宜以時釋放”,并闡明“安迪生因公受累,無辜被誣,請求準予保釋,在外候審”。呈文還說明檢察廳起訴安迪生的罪名不能成立:
支用各款,既經明白記載,毫無捏飾,一望而知為商會所挪用,決不至使人認為公記項下之借用,則安迪生為商會動用該款,自系暫時挪用之性質,亦無圖利第三人之心可言。商等際茲陰霾消散,竊憫安迪生無辜受累,尤幸我法庭秦鏡高懸,用敢不揣冒昧,直率陳詞,請將安迪生暫行保釋,在外候審,隨傳隨到,以免無辜之人,溽暑之中,久羈縲紲,實為公德兩便。(35)《保釋安迪生之呼吁》,《申報》1920年8月7日,第6版。
第三次開庭之后,此案之判決并未拖延很久。數日后,報章登載的消息即透露:“京師總商會會長安迪生、副會長殷文煜因不為黨派利用,前被吳炳湘以清查前清借款為名,將安、殷拘留警廳數月有余,并商同前大理院院長解釋法律,假借陷害,幾自冤沉海底。茲幸安福失敗,司法稍得自由,遂調查此中真像,三次開庭,昨已宣告非罪矣。”(36)《安迪生等宣告無罪》,《益世報》(北京)1920年8月12日,第3版。
8月20日,北京地方審判廳將安迪生一案的判決書在報上公布。這份判決書的編號為“京師地方審判廳刑事二庭判決副本九年辰字第三六三號”,因篇幅較長,《益世報》(北京)以連載方式分兩日刊登。判決書首先簡明扼要地宣布對安迪生、胡俊舫、殷文煜三人的判決:“右列被告人等因偽造文書詐財、吸食鴉片煙等案件,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提起公訴,本廳審理判決如左:主文,安迪生無罪,胡俊舫無罪,殷文煜吸食鴉片煙之所為處罰金八十元。”關于辛亥年接濟款的后續變動情形,判決書詳述法庭調查審理結果,指出該款確因壬子年兵變劫掠焚燒,借款各商家損失慘重,無法如期歸還,北京總商會曾解部8萬兩,信成銀行倒閉后,將該行21萬余兩抵押品逕行撥部,余款仍達90余萬兩,“該商會迭以體恤商艱,暫緩歸還,呈請政府照準”。安迪生擔任會長之后,設立清理官款股清理該款,議定除有力償還者仍收現金外,“其余酌收公債票儲蓄票中交京鈔,按照票面價格,作為現金,一面向政府請求緩償,而以所收各款及房產轉放各商家及銀行生息,以補票價之不足”。判決書認定總商會及附屬機關有時因經費不足,亦有暫在所存款項內挪借者,具體情況是:補助商事公斷處800元,夜班傳習所948.71元,各報館廣告費247.1元,群強報館200元,赴滬旅費868元,商會建筑樓房4087.3元。向國貨維持會借款2萬元,“前曾與農商部口頭接洽,得其允許始行撥款,因維持會無處存放,仍存商會,所以在賬上先交一筆,復存一筆,并非虛偽登載”。法庭認為本案被告是否構成犯罪,關鍵是需要確定兩點:“第一,該商會辛亥年由政府借到接濟市面之款,究竟借貸關系,抑系管理關系?第二,公記賬內所載國貨維持會洋二萬元及利息八百元之款,是否實有其事?”(37)本段引文均出自《安迪生案判決書》,《益世報》(北京)1920年8月20日,第3版。
法庭經多方核查商會與大清銀行往返文牘,尤其是“是年十月初十日大清銀行致該會函稱:前由度支部咨照敝行轉行撥借貴會銀一百二十五萬兩,以為市面接濟之需,言明由貴會出立借據為憑,即請查照前議即日繕立”。由此可以證實,“該商會原立于債務人之地位,否則何以須該會出立借據,此足以證明其為借貸關系”。借貸關系的確定對本案判決有著重要影響,因“按照民事上債務人對于所借之款,縱令借款當時結有指定用途之特約,亦只負民事上責任,不生刑事問題”,故安迪生并不存在刑事犯罪嫌疑。判決書進而指出:
安迪生為京師總商會會長,既未將該款侵占入己,而其所移用者,如前列商事公斷處各款,或系該會附屬機關,或系該會經常特別各費,即使逕行支用,不過與借款時原定接濟市面之特約稍有違背,原無犯罪之可言。況據到案各證人均稱系暫時借用,就該會決算報告表及公款對照表,八年十一月份挪用公款七千余元,至十二月份經費充裕,歸還五千余元之點以觀,縱令認為管理關系,旋借旋還,且未還者均系有賬可稽,亦無損害公款之可言。(38)《安迪生案判決書(續)》,《益世報》(北京)1920年8月21日,第3版。
不得不說的是,該判決書雖為安迪生洗清了冤屈,但他仍被無端拘押五個多月,身心疲憊不堪,名譽也一度受到很大傷害,類似情形在其他地區的商會中都未曾發生,可見當時的京師重地絕非什么首善之區。
三、安迪生被拘案對北京總商會的影響
北京總商會先前在輿論中的形象并不好,甚或常常受到批評,但安迪生擔任會長之后,因與各政派無私人瓜葛與利益勾連,盡量不受各政派利用,只是作為一名純粹的商董,全心全意站在商人立場上,發揮商會促進工商業發展,維護工商業者利益的功能與作用,故受到工商界歡迎。同時,在維護國家主權,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奴役等方面,北京總商會也有積極表現,為輿論所肯定。例如1919年11月日本軍警打死打傷愛國學生的福州慘案發生,全國反日浪潮高漲。12月7日北京各界在天安門舉行大規模國民大會,約5萬人出席,安迪生率商界千余人參加,并率先在會上致辭,闡明“抵制日貨一事,商會極端贊成,愿隨諸君之后,切實奉行”。為表示決心,安迪生還當眾簽字:“北京商界在商會商號本會長負永久抵制日貨日幣完全責任。安迪生中華民國八年十二月七日在國民大會簽字。”(39)《昨日空前之國民大會》,《晨報》1919年12月8日,第2版。隨后,北京總商會宣布抵制日貨的四項具體辦法,“各商家一律宣誓,自民國八年十二月七日后,永遠不進日貨,其已存之日貨則暫行擱置”。對于北京總商會和廣大商人的愛國行動,報章罕見地以《可敬戴北京之商人》為題予以報道,稱贊“北京商人愛國之熱心已不讓于他省矣”(40)《可敬戴北京之商人》,《益世報》(北京)1919年12月10日,第2版。。在安迪生率領下總商會抵制日貨的行動不僅受到各界歡迎,還被輿論寄予厚望,希望總商會出面多辦工廠,生產國貨,從根本上阻止外貨的輸入。“此事最好由總商會提倡辦理,不單是社會國家受惠,就是商人自身亦將獲利于無窮也。”(41)《我所希望于總商會者》,《晨報》1919年12月14日,第7版。正因如此,1920年2月北京總商會舉行換屆改選,安迪生得以高票當選連任會長。然而,正當北京總商會在輿論中的形象逐漸有所改觀之時,其新選出的正副會長卻突然被京師警察廳無端拘押長達五個多月,受到這樣一個沉重的致命打擊,北京總商會立即陷于癱瘓狀態。
由于剛剛換屆改選不久,安、殷二人被拘后,北京總商會頓時喪失了主心骨,無法正常運轉。部分會董曾開會商議,“以正副會長尚押警廳,推金世藻代理”(42)《國內專電》,《時報》1920年3月13日,第1版。。金是上屆總商會輔佐安迪生的副會長,由其代理會務應為合適人選。但高德隆等未能再當選連任的上屆會董,以新選會董不熟悉會務為借口,在京師警察廳的支持下,用到會幫理會務的名義,實際上控制了非常時期的北京總商會。據報道:
因會長副會長被拘,不能到會,會中一切事務,全行擱淺,新選會董,甫經到會,一切公事,均未能悉其端緒,遂公同議定,擬請前任會董陳陞、高德隆、孫學仕、王元貞、高金釗等,到會暫行幫理會事,以維現狀,俾資熟手。日前已具呈農商部,請準予備案,現尚未經批準(43)《安迪生被拘續聞》,《新聞報》1920年3月16日,第2張第1-2版。。
這個報道只是對北京總商會的表面變動情況給予了說明,并沒有揭示出暗藏其中的內幕。商會在正副會長均無法履職的特殊情況下,推舉數名聲望素孚的會董主理會務,應無可厚非。問題在于,為何不是在現任會董中推舉人選,而是在前任會董中推選?而且推選之人為何又主要是在本次換屆改選中未能連任,隨后向警察廳舉報安迪生的高德隆等上屆會董?這絕非偶然,而是幕后的精心安排。所謂新選會董甫經到會,不熟悉會務的理由,事實上也不能成立。因為在新當選的會董中,有不少是上屆會董再次當選連任者,按照《商會法》規定會董不能連任三屆,但可連任兩屆。而連任者應屬老會董,并不存在對會務很陌生而不能幫理的情形。這種反常的安排,顯然不是出于北京總商會全體現任會董的討論決定,而且呈請農商部備案也未獲批準。但在安迪生案發生后,作為商會最高管理機關的農商部似乎一直在玩弄隱身術,對于各方面針對該案的呈文或呼吁都保持沉默,基本上沒有發聲。
其實,在安福系勢力膨脹之時,京師警察廳針對北京總商會的一系列強行舉措,也根本不需要獲得農商部的批準。由安福系骨干分子控制的警察廳,拘押總商會正副會長的目的,除了打擊報復其不聽從吩咐,而且還意圖借此撤換總商會正副會長和會董,使之成為安福系的工具。所以,在拘押安、殷二人后,警察廳馬上就放出了風聲,稱安迪生等有明顯的違法犯罪嫌疑,現已被拘,當然“不宜再充當會長,應即令退職”。對于警察廳的這一說法,輿論指出:“會長退職,須經全體會董議決,并呈請農商部核準,再行改選新會長等。現警察總廳令安迪生等退職,未識仍應經過各種手續否,抑即遵廳令執行,尚未有明白宣言。”(44)《安迪生被拘續聞》,《新聞報》1920年3月16日,第2張第2版。很顯然,輿論對警察廳的這種反常之舉也無法理解。
即使如此,京師警察廳仍不顧工商界反對和輿論質疑,在未獲得農商部同意的情況下,授意非法主持總商會會務的高德隆等人,廢除按《商會法》相關規定合法選舉的北京總商會正副會長和會董,重新進行選舉。1920年4月6日,在警察廳操縱下迫不及待地進行了總商會的選舉。當選會董共計60人,袁鑒被選為會長,周作民當選為副會長(45)參見《京師總商會之選舉》,《益世報》(北京)1920年4月8日,第3版。。其中袁鑒尚屬“聽話”的商董,而周作民則是與安福系有密切關系的成員,甚至在當選前并不是總商會會員,根本不具備當選副會長資格。對于這次選舉,安迪生憤怒地表示,此次所謂選舉完全是安福系吳炳湘“強迫京師總商會改選,并指定袁某為正會長,與安福系有關系之周作民為副會長。而迪生會長之資格及前選數十會董,竟至強迫全體取消……依法組成之商會因摧殘而橫被解散,捫心清夜,愧憤難名。雖一人之犧牲尚微,而團體之誣蔑實甚”(46)《安迪生自述之代電》,《益世報》(北京)1920年9月17日,第3版。。
當時的輿論與工商界都懾于安福系的強大權勢,擔心受到報復,對這次非法選舉敢怒而不敢言。在安福系權勢衰敗之后,立即紛紛表示總商會這次選舉明顯違法,有報章評論指出:“警察廳以維持地方之職責,未經內務、農商部之指令,未經控訴之手續,逮捕法定機關之會長,實屬違法。在商會方面,安迪生之會長,未經農商部之取消,袁周之正副會長,未經農商部之承認,僅憑警廳之指揮,非法選舉,無異指派,于理不順,于法不合。”(47)窺天:《京師總商會會長袁周宜辭職說》,《益世報》(北京)1920年9月11日,第5版。部分現任會董與會員后來也聯名上書農商部,闡明:
京師總商會為法定機關,自設立以來,關于會務等項,歷經直接呈請大部核辦,有案可考。雖警察為京師行政官廳,然以沿革論,對于總商會決無解散職員之權。即曰安迪生有犯法行為,亦須法廳確定罪名后,方失會長資格,繼任會長應由會董中補選接充,呈候大部核定,乃無端硬將會長取消,復將明令認定之會董全體推翻,另行指派,致使正確民意機關壓斃于強權之下,黑暗已甚,法律何存?非法改選之始,先分函各行商會,各送會董一名為總商會當選之人,原函具在,可為指派明證。蓋周作民不在商會會員之列,既無其名,何從投選,所以必用各行函送者,即為制造會長之階梯,更為收入安福之導線。(48)《京商會上農商部書》,《益世報》(北京)1920年10月31日,第3版。
這份上書從各個方面詳細說明了此次選舉違反《商會法》的種種表現,但農商部卻懾于安福系余威不敢明確表明否認態度。
經過這次所謂的選舉,北京總商會已是面目全非,“尤奇者,舉一切促進商業各專股等,概行廢止,令人莫解是何居心”(49)《京師總商會之今昔觀》,《益世報》(北京)1920年9月21日,第3版。,這樣的總商會當然不可能真正發揮應有的職能。自違法選舉的會長和會董“就職以來,對于會務任意變更,已將《商會法》置諸腦后。前見議案,竟于指定會董八人專司議事之宣告,似此箝制眾口,以致到會寥若晨星。而會董中有古玩行郭保卿者,托病辭職,竟函致該行派人補充,并決定此后以此為例等語。似此盲人瞎馬,實將京師總商會陷于退化之境,而法定云者,將剝削以盡矣”(50)《京商會上農商部書》,《益世報》(北京)1920年10月31日,第3版。。廣大工商界人士與商會會員對這個總商會已不抱任何希望,輿論也多有批評。《益世報》(北京)的評論將前后截然不同的北京總商會進行了對比,感慨“京師總商會為北京商業之樞紐,全國商會之表率,舉所措置,關系于商業者至重且巨。在安迪生充作會長時,抱定發展商業之宗旨,凡職責上之任務,無不力求整頓。如文書科、書記科、庶務科、會計科、交際股、調查股、籌備股、清理股、圖書室、編輯室、商事月報等,各有專司,此外有商業夜校、傳習所、家庭工藝售品所,擬訂未辦者考工陳列所、內外城商業學校”。如此種種,呈現出井井有條和蒸蒸日上的氣象。然而,“適值安福派摧殘商會,袁鑒、周作民登臺,舉以上種種之設備,一律廢止。袁鑒媚人以自殘,已為奇事,而不意竟將法規制定之會議濫行廢置,如減少開會次數,指定八人到會議事,且竟通函各會董,有若遇事召集董事會,未免過煩。嗚呼!民主國家民意團體而有如是之怪現象,誠奇觀也”(51)《京師商會整頓近訊》,《益世報》(北京)1920年10月1日,第3版。。由于此期的總商會已失卻工商界代表機關的性質,在各界參加的重要社會活動中,再也看不到北京總商會的身影。最為鮮明的對比是1919年舉行的國民大會,安迪生代表工商界在大會扮演了重要角色,率先致辭并當場簽字抵制日貨,而1920年9月9日北京各界組織聯合會,籌備舉行國民大會,教育會、教職員公會、教職員聯合會、農會、律師公會、基督教救國團、報界聯合會、女學界聯合會、學生聯合會等九團體,均派代表出席,唯獨沒有總商會的代表(52)參見《昨日北京各界之大會議》,《晨報》1920年9月10日,第3版。。18日,“以發展民治主義為宗旨”,“由北京各公正國民團體組織之”北京各界聯合會正式成立,在發起籌備團體中也看不到總商會的蹤影(53)參見《北京各界聯合會成立》,《晨報》1920年9月19日,第3版。。
安迪生被宣判無罪時,安福系的權勢已趨于衰微,但非法選舉的會長和會董仍把持著北京總商會,使安迪生一直未能恢復會長職務,北京總商會也沒能走上正軌。當時的輿論普遍認為,安迪生既已判決無罪,理應恢復原職。有評論發出質問:“皖派失敗,安福傾倒,司法界不受勢力方面之牽制,安迪生經法庭裁判,宣告無罪,恢復其自由,而商會不恢復其會長何也?”該評論同時還尖銳地指出:“吾以為安迪生會長之不復,在非法選舉者有意把持,在商會無自立資格,是軍閥雖敗,安系雖傾,其勢力雖不及于司法,其威權猶能施于商界也。京師總商會為全國觀瞻所系,終于違法不敗,未免墮毀北京商界之人格矣。”(54)窺天:《安迪生宜復京總商會會長說》,《益世報》(北京)1920年9月1日,第5版。稍后,報紙又接連發表評論,明確表示非法選舉的正副會長袁鑒和周作民應該立即辭職,恢復安迪生會長職務:“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之京師總商會正副會長,乘安迪生被逮之際,非法選舉,名不正,言不順,何足以領袖群商而集事乎!”因此,“安迪生之會長當然恢復,袁周之會長當然消滅,無待辭說者也”。現在安迪生已宣告無罪,釋出月余,會長一職猶未恢復,袁、周之會長,猶未取消,“豈以官僚安福之氣焰威勢,尚及于商會耶?抑商董以法庭之裁判,猶未合法耶?吾必以為不然也”(55)窺天:《京師總商會會長袁周宜辭職說》,《益世報》(北京)1920年9月11日,第5版。。
與此同時,北京工商界也在努力爭取安迪生復職,以使總商會能正常發揮作用。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和北京總商會會董、會員計八百余人,先后呈請農商部恢復安迪生原職,但未獲答復。全國商會聯合會各省代表向農商部上書闡明:“商會為法定機關,凡商會中人為法人。自會長以及會董依法改選,呈請鈞部批準,正式就職,應享法律之保障。若以警察侵越司法權限,蹂躪法人,置商會法于不顧,匪特損失鈞部之尊嚴,為法律所不容,即全國商會會員中一份子,亦難安于緘默不言者。”京師警察廳令袁、周履行會長職務,顯系嚴重違法行為。“若不令安迪生復職,是認前警察廳總監吳炳湘以警察侵越司法權限,蹂躪法人,置商會法于不顧,雖屬違法,不妨敷衍遷就,鈞部之尊嚴何存?商會前途更不堪設想”(56)《安迪生復職之呈文》,《益世報》(北京)1920年10月23日,第3版。。在安福系權勢囂張之時,農商部不敢對安迪生案,以及京師警察廳對北京總商會違法強行改選明確表態,尚可理解,但現在仍然對商會的呼吁置若罔聞,則不可理喻。袁、周會長職務之取消與安迪生之復職,照理僅由農商部一道批示即可解決問題。正如輿論所說:“法庭宣告于前,其行之者,則在農商部。”(57)莞爾:《商會之無罪人》,《益世報》(北京)1920年11月1日,第5版。但農商部卻無所作為,著實令人費解。有人認為是因為當時農商部總長易人所致,1920年8月12日王迺斌署農商總長之職,上任伊始,千頭萬緒,一時難以顧及安迪生復職之事。隨后,農商部又傳聞將大量裁員,致使人心惶惶,直接影響到公務處置。“聞農商部總長王迺斌對于該部冗員亦擬大加裁汰,正在開列被裁各員之名單,計共有百余名之多,事先嚴守秘密,以杜夤緣之弊……該部職員均大起恐慌。”(58)《農商部裁員消息》,《民意日報》1920年10月3日,第3版。但至當年10月,農商部裁員已經公布,共計裁撤了五類職員,不應該再因此影響公務,但卻對安迪生復職之事仍無批復。11月,報章透露農商部賄托案曝光,“王迺斌總長赫然震怒,遂派某某等對于此案為徹底之查究矣”(59)《農商部發現賄托案》,《晨報》1920年11月15日,第3版。。次年1月,又傳聞農商部工商司司長陳承修提出辭呈,“其繼任人物,已在秘密競爭之中”(60)《農商部司長易人消息》,《晨報》1921年1月21日,第3版。。可見當時的農商部十分混亂,不斷發生意外之事,人員人心均不穩定。其實,農商部出現這種狀況仍與安福系的影響不無關系。是年初,教育部和農商部的總長人選安排引起爭奪,最后安福系與政府達成妥協。“政府方面連日與安福部接洽,結果頗為圓滿,其辦法系將農教兩席平均分配,農長由安福部舉人充任,教長由政府自行遴選,各占其一,兩無間言”(61)《教農兩部又有正式提人說》,《晨報》1920年1月20日,第3版。,于是農商部遂由安福系直接控制。安福系失勢后,農商總長雖然易人,但農商部中安福系的殘余勢力仍然盤根錯節,對于由安福系造成的安迪生案,自然不會積極予以平反并恢復安的職務。
10月底,北京總商會會董和會員李堪、韓成立、石繼錦、李恩坼等,“為恢復京師總商會面謁農商部次長,當經次長高凌蔚接見”。會見時李堪等向高次長詳述安迪生蒙受冤屈,以及警察廳強行對總商會進行非法選舉的情節,強調現在沉冤已得昭雪,“安迪生、殷文煜既經法庭宣告無罪,其會長資格當然存在,而依法成立之董事會橫被解散,尤屬法所不容。應呈請大部主持公道,一律依法恢復,以維法紀”。高聲稱有關情形已見諸報章,當場詢問商會借給商號之款有無契據,警察廳取消安迪生會長資格據何理由,安迪生當選連任會長是否報部批準等,李堪等一一作答。最后,高表示:“諸君所談極是,本部自當依據法律公平主持,安迪生會長之恢復與否,應以法庭判決是否犯有刑事罪為斷,當由本部調取法庭案卷,審核決定,其董事會無故解散,當然恢復,請諸君靜候可也。”(62)《商董與農次長談話》,《益世報》(北京)1920年11月1日,第3版。從表面上看,農商部次長的態度比較積極,安迪生復職似乎已無障礙,但農商部隨后仍無實際行動。
于是,有報章為此專門發表題為《敬告農商部》的評論,說明“京師總商會會長安迪生,經法庭宣告無罪,理應復職,全國商會聯合會各省代表,暨京師總商會新舊會董會員等八百余人,先后呈請農商部,取消違法之選舉,使安迪生復職,乃至今旬余,迄未見部批準,誠令人不無異議”。該評論還指明違法選舉不取消,安迪生不復職,北京總商會的亂象就無法制止:“近來京師商會,諸事停頓,開會不成,商人之心理,可見一斑。況一般會董會員,為爭人格爭公道,請求于農商部,則農商部即應俯察輿情,主張正義,急速取消違法之選舉,以慰商民,否則商民因公理未能伸,不幸而發生誤會,激起惡感,農商部實不得辭其責也。”(63)諤諤:《敬告農商部》,《益世報》(北京)1920年11月16日,第2版。為了獲得各地商會援助,北京總商會會董李恩坼、魏登甲等人,還曾聯名致函全國各大商會,闡明:
京師總商會前被強權解散,非法改選,凡我商界,無不痛心疾首,莫可誰何。雖正副會長等嗣經法庭宣告無罪,公理已伸,而職權未復,其經全國商會聯合會,及鄙等會董會員八百四十人,先后呈請農商部,恢復原狀,迄未奉有批示,倘竟不生效力,是京師總商會已無法定之可言,關系全國商會前途,至深且巨,用將呈稿另紙呈請質之高明,定獲痛癢相關,后援是助也,無盡私衷,諸維鏡覽。(64)《京師總商會函請援助》,《益世報》(天津)1920年12月6日,第10版。
類似的求助方式,是當時各商會遭遇重要變故,尤其是受到官廳打壓時所普遍采用的一種措施,雖不能立即解決問題,但卻可以得到各商會聲援而對官廳形成一定的壓力。另外,在安迪生無罪獲釋后,北京總商會原會董乃至全體會員接連舉行各種儀式,歡迎他歸來,實際上也是希望通過這一行動向官廳以及社會表明支持安迪生恢復原職的態度。“京師商會各商董,在福興居,公宴安君,為公受屈,沉冤昭雪,于以見安君,與眾商董平素之情洽也。”(65)《商界新聞》,《益世報》(北京)1920年9月10日,第6版。同時,對非法當選的袁、周等人,則可以產生較大的壓力。據報道,“近日京師總會會長安、殷等經法庭判告無罪后,京中商學各界開會歡迎。近日更有商會多數會員發起全體歡迎大會,并決定恢復商會辦法。袁、周等以各方不佳形勢相逼而來,均極恐慌。聞周作民因風頭不順,昨日已正式致函商會,請假一月,以為善退地步云”(66)《京師總商會之近聞》,《新華日報》1920年9月22日,第3版。。
由于農商部態度曖昧,盡管安迪生宣告無罪,全國商聯會與北京工商界一致要求恢復其會長職務,但卻一直未能實現。受其影響,北京總商會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也沒能恢復正常運轉,很少開展活動和發揮作用。直至1922年2月北京總商會又面臨換屆改選,有人繼續暗地活動,希望袁鑒、周作民“仍行繼任,以免一番推選交接”,并聲稱“即選舉,亦無相當人物”(67)《北京商務總會選舉會長之近聞》,《益世報》(北京)1922年1月24日,第7版。,而袁、周二人深知在工商界不得人心,表示不愿繼任。于是,北京總商會如期進行了改選。先選舉60名會董,隨后在會董中選舉正副會長,結果孫學仕當選為會長,安迪生當選為副會長(68)參見《商會重選正副會長之結果》,《益世報》(北京)1922年2月14日,第7版。。此次改選之后,京兆同鄉聯合會等五團體及各界士紳擬開會歡迎安迪生復出,但安迪生“因前遭冤獄,力抱消極態度”(69)《安迪生辭商會副會長》,《北京晚報》1922年3月19日,第2版。,向總商會聲明辭職,總商會則竭力挽留,形成安迪生“一再辭職不就,總商會更一再挽留”(70)《京師總商會一再挽留安迪生》,《益世報》(北京)1922年3月26日,第3版。的局面。可見,此次冤案不僅給北京總商會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而且對安迪生本人也是一次十分沉重的打擊。至當年5月,安迪生又向總商會再辭副會長一職,表示:“迪生不才,既蒙貴會厚愛,更何容過事推辭,無如才短能薄,益以多病,實難勝此重任,與其貽誤于后,寧若審慎于前,況際多事之會,此職猶未便任其久懸,庸請貴會另選賢能,以免貽誤要公,是為至盼。”(71)《安迪生再辭京商會會長》,《益世報》(北京)1922年5月6日,第3版。最后,北京總商會只得重新選舉副會長,由高保卿當選。本次改選與上次非正常選舉的相似之處,是“令各行舉出一人為會董”,違反了《商會法》第18條會董由會員投票選舉的規定,首飾行商會致函總商會指出:“貴總會所開各節,顯與商會法不合……貴總會開會,到會人數僅二十余人,不足法定人數,不能效力,即使已足法定人數,試問能否變更法律?敝會為護法起見,實不敢聽從亂命,貽商界之羞。”(72)《總商會違法選舉之又一反響》,《益世報》(北京)1922年2月8日,第7版。不難發現,安迪生案對北京總商會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兩年之后仍斷續可見。
結 語
商會是純經濟性質的民間社會團體,其領導人和會員都是工商業者。在清末和民初,除曾開展調和黨爭的活動之外,商會與政治基本上沒有發生直接聯系,在商會內部也很少發生與經濟問題無關的各種意外事件。不僅是商會,清末民初的農會、教育會等民間社會團體也大體如此。這一情況表明,該時期政治勢力的影響尚未擴展到經濟與社會領域的諸多具體環節。但至20世紀20年代以后這一情況出現明顯改變。商會的經濟性質雖無變化,但卻開始與政治勢力發生各種聯系。由于商會在經濟上有實力有影響,享有社團“法人”地位,所以常為政派所倚重和利用。同時,有個別商董為謀取商會領導職務,主動投靠政派或軍閥。例如上海總商會會董傅筱庵,為攫取會長寶座,尋求軍閥孫傳芳的支持,引發上海總商會兩次換屆改選風潮。第一次未得逞,兩年后卷土重來,終于當選為上海總商會會長。因此,進入20世紀20年代,許多商會都出現了換屆改選糾紛,并發生前所未有的各種意外事件。北京總商會正副會長被拘案,也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發生的一次意外事件。該案的發生、發展以及最后的結局,均與安福系勢力的膨脹與瓦解密切相關。而與政治發生日益密切的勾連,對類似商會這樣的民間經濟社團來說大多產生了負面影響,這在北京總商會正副會長被拘一案中有集中反映。隨后國民革命興起,國民黨大力開展民眾運動,政治對民眾團體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商會甚至被視為反革命團體而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經多年努力抗爭才得以避免被廢除的厄運。
在清末民初林林總總的民間社團中,商會在某些方面享有優于其他社團的待遇,也顯示出較高的社會地位。例如在商會的要求下,清朝農工商部曾制定商會與地方官衙門行文章程,規定商務總會對督撫行文用下對上的“呈”,對司道及以下各級衙門均用平級的“移”。當時曾有地方官員對此規定大惑不解,認為由普通商民組成的商會何以能獨享與府廳州縣平級的尊崇。民國建立后,農會等其他民間社團也希望一體享受這種待遇,農商部認為不妥,決定取消商會的這一待遇,全國商會聯合會和各地商會都據理力爭,使這個待遇得以保留。《商會法》頒布之后,商會更擁有了不同于其他民間社團的“法人”地位。種種情況表明,商會的地位與影響確實不同于其他民間社團,而且有《商會法》作為保障。但是,在近代中國的歷史條件下,不能簡單地以為商會從此即享有穩固的社會地位,更非工商界人士所說之“國會雖可解散,而解散商會”,政府無此力量。北京總商會正副會長被拘案以及總商會因此而被強制重新改選,說明不僅是政府,就是警察廳也可隨意拘押總商會正副會長,并對總商會予以改組。
北京總商會正副會長被拘案其實并不復雜,最終經過審判廳開庭,只進行了簡單的審理即宣告無罪釋放。因為事實十分清楚,總商會會長安迪生并未侵占公款,這只是京師警察廳給安迪生羅列的罪名。開庭審理時,各方面證據都表明辛亥年的這筆接濟官款,對總商會而言在性質上是借貸關系,而非管理關系,而借貸關系“只負民事上責任,不生刑事問題”,安迪生當然無罪。但安迪生宣判無罪之后,一手制造這一冤案的京師警察廳,事后并無任何形式的道歉,更無人因此受到處罰,近代中國執法的混亂由此可見一斑。
京師警察廳自身是執法機構,但卻知法犯法。除了隨意拘押正副會長之外,警察廳還有明顯違反《商會法》的行為。具體而言,警察廳違法罷免按法定程序選舉的會長和會董,而且不經商會所在地方和中央主管機關同意,違法重新進行選舉,選舉的形式也有違反《商會法》規定,例如由各業指定一人為會董,而不是由會員選舉產生,以致非會員竟然也能擔任會董,進而當上了副會長。此案表明,中華民國建立后,法律法規在清末初建的基礎上雖得到進一步完善,但執行法律的制度性保障體系卻付之闕如,致使很多法律法規實際上只是一紙空文,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