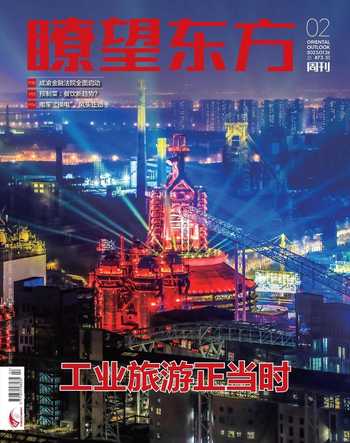中軸線上新鴿籠

養鴿戶站在改造后的新鴿籠前(張驁/ 攝)
說起北京中軸線,你會想到什么?正陽門、天安門、紫禁城、鳥巢、水立方、奧森公園……串起它們的就是中軸線。這條南起永定門,北到鐘鼓樓,縱貫北京老城,全長約7.8公里的軸線如首都北京的脊梁,跨越700余年,見證歷史變遷與京華煙云。我國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曾這樣形容它:“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的建立而產生。”
2022年8月,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表示,將推薦“北京中軸線”作為我國2024年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項目。眼下,中軸線申遺進入最后的沖刺階段,2023年2月1日前將正式提交申遺文本。
為了再現北京中軸線的壯美秩序,多年來,北京在文物騰退、修繕保護和周邊環境整治提升上步履不停。可登上鼓樓眺望時,依舊有些“不和諧”的元素映入眼簾,那就是位于第五立面,家家戶戶房頂上樣式各異、雜亂無章的鴿籠。
“為了讓它們與古香古色的中軸線景觀視廊相匹配、協調,鴿籠治理成為第五立面修繕的重要內容。而這,是一個生動的故事。”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規劃所所長、負責中軸線風貌管控城市設計導則編制的龐書經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雨燕、鴿子都是中軸線上的“原住民”, 龐書經團隊深知,最好的提升和保護是盡可能地保留中軸風貌的原汁原味。因此,他們打算給鴿子們置辦新家。
所謂第五立面即建筑物的屋頂,其作為中國古代建筑最典型的符號代表,形式豐富,造型精美,是中國建筑文化的重要瑰寶,有極大的藝術與實用價值。一個個屋頂,俯瞰之下,形成了空中的景觀視廊。
隨著北京老城第五立面整治工作的開展,如何保證鐘鼓樓周邊第五立面環境品質符合中軸線申遺標準,又要保留住屬于老北京的鴿哨聲,鴿籠的改造成為重要議題之一。
“鴿籠是鴿子的家,每天鴿子主人開籠放飛,鴿子在鐘鼓樓間盤旋,鴿哨聲悠揚,是一種活態的中軸線文化。”龐書經說。
多年來,龐書經和團隊成員深度參與了中軸線保護和治理工作。在他眼中,理想中的中軸線生活就是有人的活力和煙火氣,有美食、咖啡和展覽,能跟老居民聊聊天,概括起來就一個字:活。
因此,當鐘鼓樓周邊景觀視廊提升任務落到他手中時,龐書經覺得這是一件有意思、有挑戰性的事。
要提升,得從最顯眼的問題抓起,解決雜亂鴿籠就此提上日程。在觀察過程中他發現,主人對鴿籠的顏色各憑喜好,藍、綠、灰、白各色都有。鴿籠的用料也不相同,有的是用粗劣的鐵絲制成,有的是加蓋了石棉瓦的簡易房。
為了解決鴿籠問題,他們首先進行了歷史溯源。“據史料記載,盤鴿賞鴿盛行于明清兩代,以北京為中心。明代皇族、官員、商賈都有蓄鴿的愛好,甚至有了《鴿經》這樣的著作。清代皇族及八旗貴胄則承襲了這個雅好。直到清末,鴿子飛入尋常百姓家,盤鴿聽哨逐漸成為老北京人生活休閑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龐書經說。
在故紙堆中,龐書經看到了在正陽門筑巢600多年的北京雨燕,了解到鐘鼓樓的飛檐翹角也曾是野生鴿子的樂園,“樓鴿翔集”更是中軸線的歷史記憶。
雨燕、鴿子都是中軸線上的“原住民”,因此龐書經團隊打算給鴿子們置辦新家。
“為了讓它們與古香古色的中軸線景觀視廊相匹配、協調,我們需要設計統一規格和制式的新鴿籠。”龐書經說。
根據2019年5月出臺的《北京市責任規劃師制度實施辦法(試行)》,責任規劃師由北京市各區政府選聘,作為獨立第三方人員,為責任范圍內的規劃、建設、管理提供專業指導和技術服務。
簡單來說,按照工作程序,作為責任規劃師的龐書經只需要提交一張鴿籠設計圖和樣品,即可收工。他和團隊也按照“高不過脊”“寬不過屋”的原則,設計出挑高不超過1.4米的鴿籠圖紙和樣品。就在龐書經滿懷信心等待養鴿人檢查的時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我情愿每月開1萬塊錢工資,請他幫我打掃鴿子籠。”第一次看到龐書經的新鴿籠時,養鴿大戶史勇濤脫口而出。盡管做好了心理準備,但養鴿大戶的話,還是讓龐書經有些不知所措。
如今,這個鴿子籠還放在什剎海阜景街指揮部里,仔細觀察,它高1.4米,分為上下兩層,邊角處略帶弧度,精致而美觀。鴿籠設計用了心,會不會是史大哥一時沒轉過彎來,說的氣話呢?龐書經狐疑之間,打擊和否定接踵而至。
“一戶都不同意,大家全說不行,我都懵了。”龐書經講原理、聊思路,卻絲毫沒有引起共情,大家的一致否決讓他下決心親自入戶,了解究竟哪里出了問題。

鴿子在鼓樓前飛翔,展現活態中軸之美(張驁/ 攝)
設計也好,規劃也罷,只有空間和圖紙遠遠不夠,核心永遠是人。
2020年底,龐書經和團隊成員們第一次敲開了舊鼓樓大街周邊胡同里一戶人家的大門。一進院子,大大小小的鴿子籠讓他吃了一驚。粗略一數,院中鴿子超過200羽,大大小小,黑白花色俱全,咕咕的聲音交織出特殊的“旋律”。
“史大哥,我們是設計團隊,來找您商量鴿子籠改造的事。”龐書經仰著頭,和屋頂的“籠中人”搭話。他個頭不高,身體清瘦,正熟練伺候著身邊的鴿子:一手輕撫羽毛,一手送上美餐,任憑鴿兒在手心啄食。
這位“飼養員”就是史勇濤,龐書經碰到的第一塊“硬骨頭”。
“其實我沒別的意思,就是覺得你們這個設計太外行了。”史勇濤說,他是什剎海地區有名的養鴿人,養鴿已有40年的歷史,是位地道的行家。
龐書經把設計圖遞給史勇濤。沒想到,他掃了幾眼,連連搖頭:“你這籠子太矮了,看看我這個。”
登梯上房,身在籠中,哪怕身高超過一米八,在老史家的鴿子籠里也能挺直腰桿。鴿籠超過兩米的高度讓一人與群鴿絲毫不顯擁擠,悠然而有野趣。
“得給人和鴿子都留足空間。”一番攀談下來,龐書經開竅了,筆記本上記錄下的一條又一條,都是這位40年養鴿人的經驗和需求。
“除了高度,我知道了老城區的鴿子籠沒法直接采購,而是要像拼積木一樣采買零件自己組裝。而且,和咱們人住的房子一樣,需要很多功能分區。”有了老史的指點,設計團隊逐個入戶,陸續在設計方案上添上了網籠區、跳籠區、朝籠區,給鴿子增加“陽臺”和“健身房”。
明確了方向,調整了設計,龐書經又有了新想法。他想邀請養鴿人參與到自家鴿子籠的改造和設計中,在符合第五立面整體風貌要求的前提下,最大程度滿足大家的愿望。
聽到這個消息,史勇濤帶頭參與,親自設計了自家鴿籠的“陽臺”。再見到龐書經,老史連聲道謝,豎起了大拇指。
“不僅在檐口高度、鴿籠格局等方面優先滿足我們養鴿人的要求,還能最大限度保留各家鴿籠的特色,真是太貼心了。”他說。
值得一提的是,在鴿子籠改造中,設計團隊將材質更換為灰色鋼絲網。同時修繕屋面,將平頂改為鴿籠坡屋頂,實現了擾動小、代價少、居民都滿意的效果。
如今,站在鼓樓眺望,老史家的屋頂鴿子籠已經和中軸線第五立面融為一體。每當旭日東升,鴿群伴著鴿哨聲在鐘鼓樓間盤旋,勾勒出一條“活”的中軸線。
這次經歷,讓龐書經成了半個“鴿子通”,然而,養鴿人的認可并沒有讓他停下來。
“第五立面景觀視廊提升并非一蹴而就,后續的鴿籠養護仍舊值得關注。希望伴隨北京中軸線申遺,能推動老城基礎生活設施不斷改善,物業管理品質持續提升。”龐書經說。
鴿籠改造只是鐘鼓樓周邊環境品質整體提升的縮影,在胡同內,已經有退租后騰出的直管公房在等待新的“主人”。他們或許是社區新建的黨群文化中心,也有可能是便民菜店,還有望變身共生院,與原住民們一起迎來新生活。
在中軸線風貌管控城市設計導則編制過程中,龐書經和同事們把目光集中于長效、深層、利民,以求借助申遺項目從全局進行整治和改善。
在導則指導下,南鑼鼓巷四條胡同改造一院一方案、一戶一設計。雨兒胡同20號院,是歷史上逐漸演變形成的邊角雜院,無傳統規制,留住居民較多。為此,設計師圍繞留住居民需求,植入廚房、衛生間,改排水,實施強弱電入地,修繕破損房屋,并發動居民營造園林小品,讓院落更加宜居。雨兒胡同4號院,名為“乾井院兒”,因在院落改造中發現了乾隆年間的一口井而得名。在留住歷史、保留原物件的原則下,這口井被原地保存下來。如今,這座院子的居民全部騰退,全院改造為中式復古風建筑,落地玻璃窗、深棕色窗欞,槐樹、山楂樹自由生長,是胡同里最幽然靜美之處。
“若汝念我,只需環顧四周。”這是龐書經經常說的一句話,那張一米四高鴿籠的圖紙,他已經收藏起來,并且要收藏一輩子——只為提醒自己,設計也好,規劃也罷,只有空間和圖紙遠遠不夠,核心永遠是人。
“生活在老城胡同里的人首先得有生活幸福感。”龐書經認為,在北京中軸線申遺的沖刺階段,把民生擺在第一位,已經成為一致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