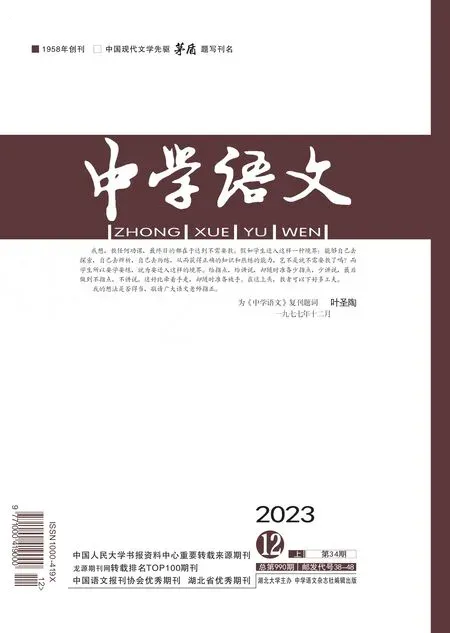回歸語文本體 構建生命課堂
——評曹明海《語文課程的根與本》
郭仁超
一、探源析本 廓清概念
曹明海教授的《語文課程的根與本》,探究的是語文課程的本質。而厘清語文課程的本質,也是開展語文教學活動的第一步。曹明海教授看到了語文教學有游離在教學本質之外的現象,語文課程所特有的詩意的一面、蘊含著民族文化世界的一面被遮蔽,因此大力倡導語文本體性的回歸,即語用的回歸。在曹明海教授看來,語文教學的本質就是語用教學,語用教學指向的是《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 年版2020 年修訂)》(以下簡稱“新課標”)中的“語言建構與運用”,這是語文課程教學活動與教學設計的核心指向與基本立足點。與以往對語文的相對單一界定不同,曹明海教授認為語文的概念是復合性的,具有文章的、文學的、文化的、語體的、文言的等多重內涵。復合性下的語文概念是豐富的,具有不同層次與角度,但基質是語言文字,語言文字是構成文章、文學、文化的最基本元素。這樣的做法厘清了語用或者說語文的概念。語文不再是各種觀點交鋒的角斗場,而是以語言文字為基質的復合性概念。對施教者來說,如果說語文概念的界定是“從哪里來”,那么由此出發明確的教學目標則是“到哪里去”。
曹明海教授創造性地將語文課程目標分成兩方面:一是語用能力目標;二是語用素養目標。語用能力目標指向的是培養學生語言運用能力,包括語用基本能力、語用思維能力、語用審美能力。語用素養目標指向的是提高學生語言文字素養,包括語用知識素養、實用文章素養、文學藝術修養、語言文化素養等。[1]能力目標是基礎性的,而素養目標是基礎之上的發展與升華。“能力—素養”兩種層次教學目標的制定,回應了僅僅將語文教學目標界定為識文斷字的“工具性”的觀點;將素養目標概括為語用知識、實用文章、文學藝術、語言文化素養,是從語文是語言文字的本體論出發,剔除“非語文”的教學目標,劃定語文“人文性”的邊界,防止將語文教學目標泛化,讓語文教學真正具有“語文味”。
由本體出發,最終達到的目的是生命化的語文教學,將語文作為主體生命形式來把握,是曹明海教授對于語文本體重要的價值探索。在他看來,語文教學要走向詩性、陶冶與人文,讓學生真正能夠在語言的世界里展現和延續自身的生命。這是以一種宏觀的視野,超越語言文字本身,是對語文課程目標的審視。詩性是語文課程一以貫之的求得智識的態度。陶冶區別于其他課程,是語文獨有的實現教育的方式。陶冶與詩性是一脈相承的。語文的詩性特質,能讓學生在對文本的涵泳中,實現自我品性、氣質、人生境界的提高。人文,即人文素養,“不是語文教學的泛化,而是語文本體構成的功能最大化”[2]。換句話說,提升學生人文素養,是語文課程最大的價值追求。
語文的概念是復雜的。何為語文本體?語文教學目標要去向何處?該以什么樣的方式到達?這些問題,是施教者在打開語文教材前必須要思考清楚的。曹明海教授在書中對語文本體的思考、對課程目標的分析、對教學手段的把握,讓施教者更加清醒地前行。
二、綱舉目張 條分縷析
如果說對語文本體、課程目標、教學手段的思考是宏觀的,那么對于文本解讀方法與不同文體特征的辨析,則是指向文本的具體思考。探索教學文本解讀方法是該書的重要一環,主要包含文本、學生與文本之間的關系、文體三方面內容。
1.立足文本
在曹明海教授看來,語文教學文本應以教材中的文本資源為范例,將一切的教學活動建立在教材的文本基礎之上,對教材中文本資源的解讀是確立教學內容的關鍵。教材文本是一個“多層次結構”,包含形式層、再現層與表現層。形式層是文本的語體層,包含了語音、語段、句段、結構及整體營構的秩序與形態;再現層是文本的語象”,指的是教材文本語言構出的物象與事象、場景與畫面、氣象與景境等;表現層是文本的語義層,即文本負載的情感與理思、精神與思想、靈魂與生命,是教材文本的深層意蘊。[3]對教材文本的多層次的理解,厘清了不同層次的教學內容。施教者在教材文本解讀過程中,不僅要看到文本的語音、語段,也要看到教材文本所具有的景境、情節,以及背后的情感、思想與意義。施教者不能只重視作品思想內容的把握,也不能只注重對語言語體層的解析,而是要從文本出發,不斷發掘教材文本的深層語義內蘊,由淺入深,入乎其內,出乎其外,讓教材文本解讀有層次,也讓教學內容更富有層次。
2.學生主體
如果說對教材文本的分析是著眼于文本,解讀教材文本后教學內容的確立是著眼于施教者,那么,分析讀者接受文本的心理以及對讀者與文本關系的探討,則是著眼于學生。在文本解讀過程中,曹明海教授創造性地將教材文本與學生之間的“不對稱關系”進行了修正和說明,認為文本具有未定性和空白,在向讀者發出召喚,讀者應積極填充空白,從而實現積極交流,這使學生在文本閱讀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得到了肯定。學生不是被動地接受教材文本的內涵,而是通過不同的方式,對教材文本進行創造性的分析與解讀,成為文本的建構者。這樣看來,曹明海教授將施教者與學生均作為平等的讀者看待。施教者在備課階段實現深悟,在課堂上,則是以學生為主體,從學生的“初感”出發,以詩性的方式實現讀者與讀者思想上的碰撞,從而促使學生深悟,實現語文課程價值。
3.審識文體
曹明海教授在書中著重分析了詩歌、散文、小說、戲劇這四種文體的特征,并采取相應的教學策略,以發現不同文體解讀的具體問題,指明具體對策,實操性相當強。他對文體教學的重視,也是在回應近些年語文教學活動表現出來的現象——文體意識模糊、文體“淡化”,各類文體呈現出類似的教學思路、教學設計和教學模式,直接影響教學質量。文體意識的確立具有重要的意義。文體意識能夠幫助施教者明晰各文體的主要特征,即各文體最鮮明、最有意味的地方。只有這樣,施教者才能真正把握“這一篇”的精髓并進入文本解讀。
曹明海教授的教材文本解讀觀,從文本的基本層次出發確立教學內容,在整體觀照的視野下,分析教材文本中的各項元素及其與整體的關系,在教學解讀過程中堅持以學生為主體,將教學活動中的“教師—文本—學生”三者有機聯系起來,富有創見性,對于一線教師實施教學活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史觀視野 回應現實
曹明海教授在我國語文教育史的視野下把握語文課程本質,書中對于語文本體的分析是基于長期以來語言學爭論的問題。但他沒有囿于爭論本身,而是看到了語言與本體之間的密切關系,得出語言文字是語文本體的結論。語言文字運用并不是近些年的提法,我國基礎教育的先行者、奠基者葉圣陶已對此有過深入的探討。葉圣陶在《略談學習國文》中提到,“語言文字的學習,出發點在‘知’,而終極點在‘行’,能夠達到‘行’的地步才算具有這種生活的能力”[4],由此明確了“知”與“行”的關系,以及語文學習的過程就是知而后行。學生是“知”的主體,也是“行”的真正實踐者,教材文本就是學生獲取“知”的重要來源。因此,曹明海教授對于語文本體的呼吁,對于學生主體的強調,以及對教材文本多層次、深入的分析,正是在宏觀的語文教育史視野下,對前輩學人的繼承與發展和對語文本質的把握。
隨著我國教育改革不斷深入,新課標從學科本體出發,確立了較為具體的課程目標,形成了以學習任務群為主體的課程組織形式,推動了包括任務群、情境化、項目化在內的教學方式的變革。教學方式的變革是基于時代發展的新形勢,但這并不意味著教學基礎內容的偏移,也不會造成語文課程基本內核的缺失以及“泛語文”“非語文”“假語文”等教學現象的形成。施教者立足于新時代教學方式的變革,必須突出學生語文素養本位。曹明海教授在書中對教學文本的多層次分析,對學生主體的確立,以及更為細部的文體分析,正是回應了當下語文教育中出現的一些偏差。語文課堂“語文味”的疏離,是施教者沒有認清語文課程的核心本質,對以語言文字為基質的教學文本沒有深入的思索,背離了對傳統語文陶冶性的追求;施教者更看重圖像表達,而忽視了最為基本的語言文字的涵泳,學生成為知識接受的客體,卻沒有真正參與教學文本的構建。這些現象的出現,無不引起包括曹明海教授在內的老一輩學人的憂慮。
新課標總結了語文課程的特質:“語文課程是一門學習祖國語言文字運用的綜合性、實踐性課程。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5],并進一步強調了以學生為主的理念和學生自主學習實踐活動,明確了具有完整結構的學習任務群是語文課程組織形式。學習任務群承載了語文學科核心素養,是課程構架的核心元素。學習任務群的建立,就是要引領教學方式的變革,凸顯學生的主體性,呈現學生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探究學習的學習方式。可見,曹明海教授強調學生主體,并將學生視為文本的建構者,與新課標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
總而言之,曹明海教授的《語文課程的根與本》可以說是一本結構嚴謹的書,一本有溫度的書。全書具有高度的理論視野,能夠從語文本體出發,通過分析語文的本體、語文的特質,形成較為科學的教學目標;能夠在教學方法論上結合西方接受美學、解釋學等相關理論,對文本、文本與學生關系、文體等相關內容進行細致的分析,真正解答施教者該如何做的問題。同時,曹明海教授對于詩意、語文味、生命語文的倡導,不僅呈現了一個有溫度的語文教學,還展現了一個有溫度的學者形象。正如書的《后記》中說的一樣:“那是一些純真的人,純真的事,純真的感情,純真的思維,純真的氣場,純真的環境,純真的交往,這些給我的‘解讀學’融注了純真的性格。”純真是難得的態度,以純真待語文,才能真正回歸語文本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