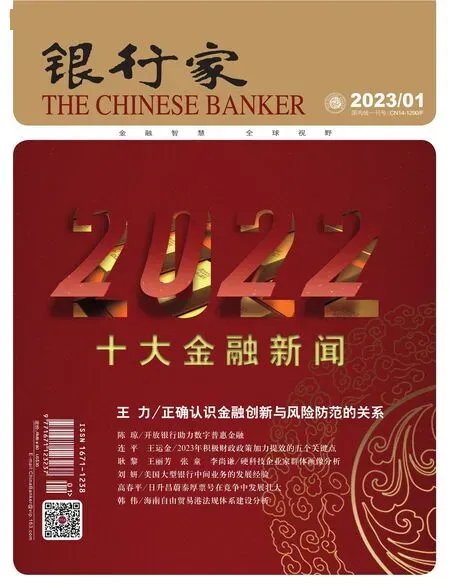美國即將陷入的衰退或是長期低增長的開端
楊博涵 徐奇淵
2022年美國經濟增速迅速放緩,2023年大概率進一步陷入衰退。然而,在美國經濟增速已經連續多個季度持續走弱的情況下,美國的勞動力市場持續過熱,通脹率仍然處于較高水平,IMF預估美國2022年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為8%,2023年通脹率仍將明顯高于目標水平。勞動力市場過熱、職位空缺率高,這說明美國現有的就業情況已經超過了充分就業狀態。高通脹率的持續也似乎進一步驗證了經濟正處于過熱狀態。美國當前的經濟增速本身就已經偏低,而勞動力市場、通脹率的表現似乎表明,即便是這個偏低的經濟增速,其很可能也已明顯高于潛在增速水平,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當前美國面臨的低增長、低失業和高通脹局面。本文將側重從美國勞動力市場的變化趨勢及保護主義興起的角度,指出美國潛在增速將在更長時間保持在低位。由此我們將看到,美國在2023年陷入衰退,很有可能是美國長期低增長時代的序幕。
美國經濟增速下滑的直接原因是潛在增速下降

2022年以來,美國經濟增速顯著走低。2022年一季度,美國GDP季調環比折年率增速為-1.6%,二季度為-0.6%,三季度增速雖然超出市場預期,暫時上升到了2.9%,但多個關鍵指標正顯示出疲軟跡象。從2022年全年來看,IMF預估美國的GDP增速將下降至1.6%,且IMF進一步預測,美國在2023年的增速將下降至1%。相比之下,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2010——2019年,美國經濟增速最低為2011年的1.5%。而2022年1.6%的預估增速已非常接近2011年的水平,2023年的預測增速甚至將明顯低于2011年的水平。
令人費解的是,在美國經濟增速大幅放緩的同時,美國的失業率早已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同時通貨膨脹率卻快速上升。2022年6月,美國CPI指數同比上漲9.1%,這是1982年至今的最高水平。一方面是過高的通貨膨脹率,另一方面是過熱的勞動力市場,這意味著當前經濟增速雖然已經處于歷史較低水平,但很可能仍然顯著高于潛在增速水平。
從20世紀末至今,美國經濟的潛在增速一直呈現下降趨勢。據OECD的估算,在進入21世紀以后,美國潛在增長率從3%下降至2%左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潛在經濟增速一度下降到1.5%左右,并常年保持在2%以下。IMF預估,美國2022年經濟增速和CPI通脹率分別為1.6%和8%,2023年這兩個指標增速則分別為1%和3.5%。如果只從通脹率來看,2023年作為預測值的3.5%通脹率仍然高于美聯儲的平均通脹率目標(2%),因此,對應的1%的GDP增速仍然可能是一個高于潛在增速的水平。如果美國的潛在增速較疫情之前有顯著下降,那么在此背景下,假設美聯儲仍然以疫情之前的失業率和經濟增速為參照,并試圖維持不切實際的目標,那美國就不得不面臨相對更高的通貨膨脹率。或者對應地,美聯儲要實現之前確定的平均通脹率目標(2%),那就將面臨更低的經濟增速和更為嚴重的失業率。此時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本輪美國的潛在經濟增速下降是長期的還是短期的,這個問題不但關系到我們理解美國未來的增長前景,而且也關系到我們如何理解美國的貨幣政策甚至更大框架下宏觀政策的取向。
美國潛在增速下降的原因
本輪美國通脹居高不下的同時經濟增速顯著下滑,這說明除需求端沖擊之外,也存在著負向的供給端沖擊。美聯儲從2022年3月到11月進行了史無前例的連續六次加息,這使得通脹壓力有所減緩。但與此同時,商品價格和服務價格走勢出現了明顯分化。2022年10月,美國核心CPI環比下降0.3%,二手汽車和服裝等商品價格環比下降明顯,但整體CPI環比上漲0.4%,尤其是占據消費支出更大比重的服務業保持著0.5%的環比增速。這意味著緊縮的貨幣政策可降低總需求,從而壓低商品價格,但對于勞動力供給不足導致服務業價格上漲的抑制效果較弱。由于服務業價格上漲主要來自供給端的負面沖擊,特別是勞動力供給不足。因此,依靠需求政策的緊縮無法解決供給端的負向沖擊問題。從供給端來看,供給端的負面沖擊甚至損害了美國經濟的潛在增速。從生產的角度來看,潛在增速主要由勞動力增速、資本回報增速及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三部分構成。在資本回報增速基本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和勞動力增速的下降是美國潛在經濟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疫情之前,研發效能下降和保護主義盛行共同壓低了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據Jones(2022)①Jones, C. I. (2022). The past and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A semi-endogenous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14, 125–152.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conomics-080521-012458測算,從1950年至今,美國經濟增長超過60%的部分來自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而科技進步又占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一半以上。可見科技進步是美國經濟增長的核心推動力。科技進步帶來的經濟增長率由科研人員人數和研發效能的乘積決定②Bloom, N. (2020). Are Ideas Getting Harder to Fi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4), 41. https://doi.org/10.1257/aer.20180338。從20世紀末至今,美國研發效能的下降對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下降起了決定性作用。以計算機行業為例,20世紀70年代,該產業的年增速高達35%。但進入21世紀后,年平均增速則為7%。從芯片領域的摩爾定律來看,要使兩年晶體管數增加一倍,需要的研究人員數是20世紀70年代的18倍。結果是,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在2000年到2019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里都保持較低水平,但這段時間里美國科研人員人數的投入增長了60%,這說明美國研發效能的下降。此外,美國從2017年特朗普上臺以來的貿易保護主義上升也阻礙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改善。在保護主義盛行的背景下,美國提升關稅,減少科技交流合作,這些措施保護了生產效率最低的企業,傷害了創新最為活躍的企業,從而使技術進步更加放緩,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進一步下降。根據紐約聯儲的經濟學家估計③Amiti, M., Kong, S. H., & Weinstein, D. (2021). Trade Protection, Stock-Market Returns, and Welfar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s://doi.org/10.3386/w28758,特朗普時期對中國加征的關稅會使美國全要素生產率下降4.5%,實際工資下降4.3%。
疫情暴發之后,美國勞動力供給受到顯著影響,這是當前美國潛在增速下降的關鍵因素。根據Jones(2022)的測算,1950年至今,勞動力供給增速對經濟增速的貢獻率為25%。而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了勞動力供給,并拉低了潛在增速。疫情中美國出現了大退休潮,根據美聯儲經濟學家的估計④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econres/feds/the-great-retirement-boom.htm,疫情期間有接近350萬人提前退休,這基本就對應了美國勞動力減少的數量。在這些提前退休的勞動力中,有三分之一的年齡在55——64歲。美國平均退休年齡男性為65歲、女性為62歲⑤根據波士頓學院退休研究中心數據,https://crr.bc.edu/data/frd/,而且55——64歲的勞動力一旦退出,其返回勞動力市場的適應能力較弱。因此,這部分提前退休的勞動力中,大部分是完全退出了勞動力市場,只有小部分可能會緩慢回歸。美國的退休人口比率在較長一段時間內都會高于疫情前水平,這將拖累勞動力供給的恢復。同時,在保護主義背景下,新進入的移民人數有所減少,且人口老齡化仍在繼續,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美國勞動力市場持續緊張。2022年,美國職位空缺率維持在6%以上,這是1950年以來的歷史最高水平。勞動力供給恢復緩慢不僅拉低了美國經濟增速,也會帶來工資上漲,并觸發“工資——價格”螺旋上升的壓力。
美國宏觀政策的出路在哪里
在潛在增速下降的背景下,美聯儲要實現相同的通脹目標,就必須被迫選擇更低的經濟增速。例如,美聯儲通過提升利率壓低總需求,從而恢復供需平衡、控制通貨膨脹。由于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恢復緩慢,美聯儲甚至需要更加緊縮貨幣政策,將總需求壓得更低,以等待供給恢復。這也意味著美國經濟增速將進一步放緩。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2022年11月30日的講話中承認,由于重返勞動力市場的退休人員有限及老齡化兩個原因,勞動力市場的供給還會持續不足,因此,美聯儲需要采取更高的利率才能將總需求壓到足夠低,這意味著恢復經濟供需平衡將需要經濟增速放緩較長一段時間。根據歷史經驗,通過需求政策來應對供給沖擊的代價較大。在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后,美聯儲在1980年12月將政策利率提高到22%,美國隨后在1981——1982年陷入衰退,1982年美國經濟收縮1.8%。如果美國不能成功應對本次供給端的負面沖擊,控制通貨膨脹率將意味著增速進一步下降。
當然,美聯儲也可以認為,當前通脹的壓力更多地來自供給因素的負面沖擊,因此可以進一步將平均通脹目標率提高到大于2%的水平,比如3%甚至4%,這當然可以擴大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選擇空間,但這也將使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聲譽再次受到質疑。2021年下半年,尤其是2022年上半年以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聲譽已經受到了較多的批評和質疑。因此,對于美聯儲來說,對于通脹目標保持謹慎態度可能仍然是有必要的。
因此,美國現在最大的政策挑戰還是負向的供給沖擊。推動勞動力市場恢復供需平衡是中期內政策的重點。一旦勞動力市場持續緊張,出現“工資——價格”螺旋上升,控制通脹的成本將變得非常大。因此,當前美國最迫切、也最有效的政策是推動勞動力市場供給面的改善,從而修復潛在增速,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超出了美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作為總需求調控政策的功能。從疫情后“大退休潮”的影響來看,該因素導致的高年齡段人口勞動參與率下降,將會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恢復。但是,一方面,這種自然修復需要較長時間;另一方面,美國持續的老齡化過程會減緩勞動力供給的增速。從政策選擇來看,重新放開移民限制有助于高度依賴移民勞動力的行業(如建筑業)減少職位空缺率。此外,提升疫苗接種率及增加醫療投資也可以減少“Long-Covid”帶來的勞動力損失。但總體而言,這些措施起到的作用可能有限或者這些措施本身就面臨各種困難。
從中長期來看,美國需要恢復潛在增速,更加需要放棄保護主義,拆掉貿易、投資和科技合作方面的藩籬。如果美國降低關稅,進口商品的價格會直接下降,可以減輕美國國內的通脹壓力,這將在較大程度上改善美聯儲在通脹與增長之間的權衡難度,使得貨幣政策的空間明顯擴大。同時,美國放棄貿易保護主義也可以促進國際市場上的企業競爭,以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從而讓美國的潛在增速有所恢復。但鑒于美國國內的政治環境和輿論氛圍,這方面政策面臨很大阻力。
綜上所述,從經濟周期的角度來看,美國在2023年大概率將進入溫和衰退。但從潛在增速的角度來看,科研研發效能下降、勞動力供給受限和保護主義上升等因素將使美國經濟的潛在增速持續在低位徘徊,且這種狀態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期。因此,2023年即將到來的溫和衰退有可能是美國低增長時代的一個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