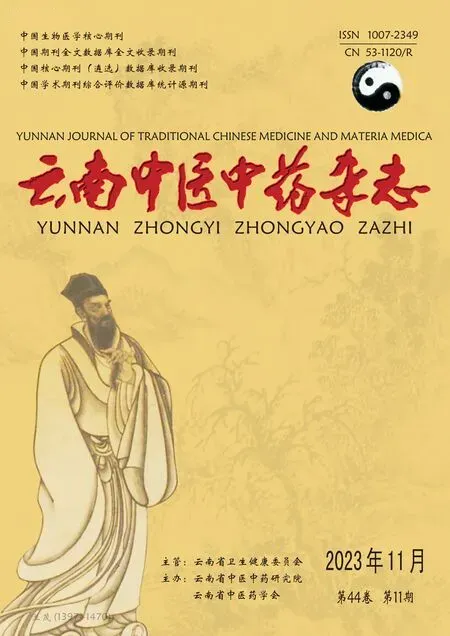基于新安醫學固本培元思想分期論治運動神經元病的理論探討*
談 露,方 向
(1.安徽中醫藥大學,安徽 合肥 230038;2.安徽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安徽 合肥 230031)
運動神經元病(MND)是一種神經系統變性疾病,分為原發性側索硬化(PLS)、進行性延髓麻痹(PBA)、進行性脊肌萎縮(PSMA)和肌萎縮側索硬化(ALS)4類。主要臨床表現為逐漸加重的軀體無力及全身肌肉萎縮[1]。且約有半數患者會因為發生吞咽功能障礙和呼吸肌無力,在3~4年內死亡,目前世界范圍內對MND仍然沒有被證明有效的治療方法[2]。MND在中醫現有的文獻記載中未發現相對應的病名,但由于其臨床表現多為肢體筋脈痿軟、無力,后出現肌肉萎縮、肢體癱瘓,所以將其納入“痿證”的范圍[3]。臨證大多從虛從瘀論治,但療效欠佳[4]。新安醫學作為特色鮮明的地方醫學流派,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很高應用價值的學術思想,深遠的影響了中醫學的發展[5]。其中的固本培元思想,以強健脾腎,滋養元氣,從而調節自身氣機,提高治病能力的思想,對指導許多慢性虛損性病癥的治療具有重要價值[6]。MND發生發展是多種病因病機相互作用積累的結果,雖在疾病發展過程中病變臟腑各有側重,但各臟腑病變都以不同程度的虛損為主,故根據患者不同時期的臨床表現和病變特點,可遵循新安醫學固本培元思想,對MND進行分期論治。
1 固本培元思想歷史源流
新安醫學作為地域特點明顯的中醫學術流派,分支繁雜,固本培元派就屬于其中傳播范圍最廣、影響最大的分支[7]。新安固本培元派在16世紀中葉的明朝時期逐漸興起,起初以批判當時濫用苦味、寒涼及降瀉藥的風氣為主。隨后明清眾多的新安名醫,充實發展了這一學派,他們主張減少苦寒降瀉的藥物使用,提倡溫補培元藥物為主的治療方法,逐步形成了以固本培元為治療思路,培補脾腎先天之氣、溫養氣血等方劑為治療基礎,臨床上使用人參、黃芪、白術或以附子、干姜、當歸為基本藥物的用藥特點的醫學流派[8]。尤其擅治肺脹、不寐、痹證、痿證、消渴等慢性虛損性疾病,治療時多采取中藥湯劑、針灸、食養等多種方式聯合使用[9],臨床療效顯著。
2 固本培元思想內涵
中醫的基礎理論里認為,本,即人體的根本,可分為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腎為先天之本,決定人體先天稟賦強弱、內臟功能和生長發育速度的根本是腎臟的功能。脾為后天之本,脾的功能為出生后所有的生命活動提供能量[10]。元,即元為元氣。是人體生命的初始來源,在人一生之中不斷被消耗,又可接受后天藥食、呼吸之氣的充養[11]。《素問·舉痛論》曰:“百病生于氣”,即由于人體所有疾病均起源于氣的生成和運行,故培元需扶先后天脾腎之正氣,即人體的正氣。
新安固本培元思想以脾胃化生氣血,榮養周身的理論為基礎,確立了主以調補脾胃,滋其化源,以后天水谷精氣充養先天元氣的思路,通過重視脾胃與腎的調理補養、化生精血,同時充養后天有形臟腑,從而使后天脾胃與腎補養先天,激發人體先天生命力。形成了治療上通過扶助人體本元正氣,來祛除病邪以治愈疾病或養生防病的思維方式。其特色在于與病邪相對而言,更加重視人體本身的抗邪能力,而這種能力根源于先天元氣,五臟之中又以脾腎最為關鍵。無論元氣或脾腎,其均強調的是生化之源的作用。因人參有甘能生血、陽生陰長之義,故取其作為固本培元首要用藥,并多配伍黃芪等補氣之藥,當歸、甘草、麥冬等補血滋陰之品,以達到氣血并調,脾腎同補,同時慎用寒涼攻利之劑,時時處處以護養元氣為先,從而治療各類臟腑虛損之病。
根據MND患者的臨床表現,其主要病機多為五臟虧損,精液不足,氣血虧虛,筋骨失養,不同時期臟腑受累各有側重。所以在固本培元思想指導下采用益氣健脾、補腎益精的方法對MND進行分期治療,可以通過早期補肺健脾、中期溫補脾腎、晚期補益肝腎,培補一身正氣,使疾病得到更好的療效。
3 MND分期論治
3.1 早期-肺脾氣虛,補肺健脾 發病早期的MND,癥狀輕微,大多數患者僅表現為肢體無力、肉跳、神疲倦怠、乏力氣短、畏風自汗等癥狀,大多可見舌淡,苔薄白,脈細弱。此期患者中以肺脾之證較為多見[12]。由于肺主氣,促使氣血津液敷布全身。衛氣賴肺氣宣發而敷布全身,抗御外邪。肺氣充盛,則衛氣強盛,肺氣虛弱則導致神疲倦怠、少氣乏力、惡風自汗。脾臟是后天的基礎。它是氣血生化之源。脾是四肢以及身體肌肉的主宰。身體的肌肉由脾臟輸送的水谷精微和氣血生化之源滋養,以維持其生理活動。脾臟負責升清。氣血向四肢的運輸取決于清陽的充實程度。如果氣不足,身體就不能發揮其功能,清陽就不能上升。四肢得不到清陽的充實,就會變得痿軟和無力。此期多從補益肺脾著手,以補氣生血,調補陰陽。由于補肺補脾在于補營,補肺脾氣就是補營氣。所以臨床上治療MND早期,肺脾虛弱表現為主的,擬方治療時可將參、芪設為君藥或加大劑量。參、芪補營,不僅能養肺脾,還能滋養陰血,因為人參、黃芪性味甘溫,不是尖銳溫陽之品,且甘能生血,所以沒有耗氣傷陰的缺點[13]。治療上在運用清熱祛濕、熄風、祛瘀等治法同時,針對不同患者的證候差異[14],常配伍參、芪以及山藥、茯苓、白術等補肺健脾藥,以達到延緩MND疾病發展速度的目的。
3.2 中期-脾腎陽虛,溫補脾腎 中期的MND患者,肢體無力的癥狀明顯加重,開始逐漸出現形體痿廢,骨瘦如柴、肌肉顫抖、畏寒、四肢冰冷、面色發白、腰膝酸軟或冷痛,并伴隨言語不利、舌肌萎縮等癥狀,大多舌淡胖,苔白,脈細。此期患者中以脾腎陽虛較為多見。因脾臟和腎臟與先天和后天的營養有相互關系。脾之陽氣根源于腎,脾臟陽虛,則脾腎陽虛。同樣,脾陽虧虛則腎之陽氣無以充養,任何一方虛弱則易導致脾腎俱虛。脾腎陽虛的結果是無法攜帶和接受氣,無法滋養和補充肌肉,導致肌肉萎縮持續增加。由于腎主骨,吸收氣血,所以臨床上不僅表現為肌肉無力,萎縮加重,還表現為頸部轉動不利,頭歪眼斜,呼吸困難,腰膝疼痛無力,不能久站等。治當溫補脾腎為主,治療上可使用新安醫家孫一奎創立的溫補下元名方“壯元湯”,主張用人參、黃芪治療虛證,補腎益氣,強壯培元,將益氣藥與溫陽藥共同使用[15],通過培補腎陽與命門元氣使固本培元得以實現,方中作為益氣藥的人參、黃芪等與溫陽藥的附子、肉桂、生姜等配合使用,附子溫補下元,人參、附子健脾行氣,諸藥合用,達到先后天并補之功。若伴肌束顫動者,加天麻、鉤藤;正虛易感者,加甘草、大棗。辨證施治,以改善中期MND患者臨床癥狀,提高生存質量。
3.3 晚期-肝腎陰虛,肝腎同治 晚期的MND患者,此時肢體無力、肌肉萎縮持續加重,甚至四肢痿廢、大肉漸脫,或言語不清、吞咽不利、呼吸受限、舌肌僵硬萎縮,肢體麻木、肢體酸痛、痰黏難咯等,大多舌淡紅,少苔或無苔,脈弦細。此期患者多為肝腎陰虛,病位有從肺脾、脾腎演變至肝腎的趨勢。脾胃病久也必然累及下焦肝腎[16]。長期的疾病耗費人體精血,腎臟的精氣不能產生肝血,肝為筋之所主,肌腱沒有得到滋養,這導致了四肢僵硬和肌肉運動。長期生病情志不暢,郁而化火消耗了血液,水不含木,肝臟失去營養。后肝陽上亢,導致肝風的內動,使肢體僵硬,肌肉運動更加困難,治宜滋補肝腎。所以在前期治療的基礎上,可遵循新安醫家孫一奎所著《赤水玄珠》中強調的治痿不專于陽明,宜養肝滋腎[17],可臨床上滋補腎陰可選用熟地黃、山藥、山茱萸、枸杞子、女貞子、黃精等,這些藥物溫而不燥、補而不滯,可達到肝腎并補;溫補腎陽可選用巴戟天、肉蓯蓉、淫羊藿、桑寄生等,這些藥物性多溫潤,溫而不燥,滋而不澀,可達到陰陽雙補[18]。亦多增用平補陰陽的紫河車、龜板、鹿角膠、鱉甲等血肉有情之品,使晚期患者病情平穩,達到帶病延年的效果。
除根據分期特點辨證施治外,固本培元思想在MND臨床治療上的并不局限于湯藥。常認為通過內服中藥與針刺、艾灸、食養配合常能發揮更優效果[19]。所以在MND早期,多將局部取穴與循經取穴配合使用,使營衛運行有序,從而達到健運肺脾、調和營衛的功能。可通過針刺阿是穴,疏通局部的氣血,邪氣消散,正氣隨之恢復。在MND中期,脾腎陽虛,針刺溫補力量有限,正所謂“針所不為,灸之所宜”[20],則可通過溫針灸辛溫助陽腎經及督脈。陽氣之根為腎,陽脈之海為督脈,人體陽氣不足時,則寒邪無從溫補,故通過艾灸陽熱溫補之力,由督脈主導有機融合全身陽氣,迅速貫通全身的陽氣,使陽熱之氣運行于經絡,從而達到溫腎暖脾,脾腎同補的目的。在MND晚期,病情遷延,肝腎陰虛,多針刺、艾灸肝腎二經,并配伍督脈穴位和背俞穴去補養機體,以溫腎壯督、溫補元氣。除此之外,食療作為MND的配合治療,可采用新安養生專著《老老余編·養生余錄》中記載的羊肉粥[21],強壯筋骨。其中含黃芪、人參、茯苓、大棗、粳米等。粳米煮粥可滋養脾胃,黃芪歸脾肺經,有益氣升陽之功,人參、大棗健脾調中,五者與羊肉搭配,加工成滋補藥膳,以期改善MND患者臨床癥狀,提高其生存質量。
4 小結
固本培元思想重視脾、腎在疾病發生發展中的作用,主張培護人體元氣,強調人體生化之源的作用,擅長重用人參、白術、黃芪行溫補之力,提倡湯藥、針灸、食養等多種治療手段聯合使用。五臟虛損、人體元氣虧虛是MND致病的病機要點所在,根據新安醫學固本培元思想,在其發病的早、中、晚期分別采取補肺健脾、溫補脾腎、肝腎同治的治療方法,應用壯元湯等代表方劑,配合針灸、食養等進行綜合調理,多種治療手段聯合應用,為MND患者的治療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