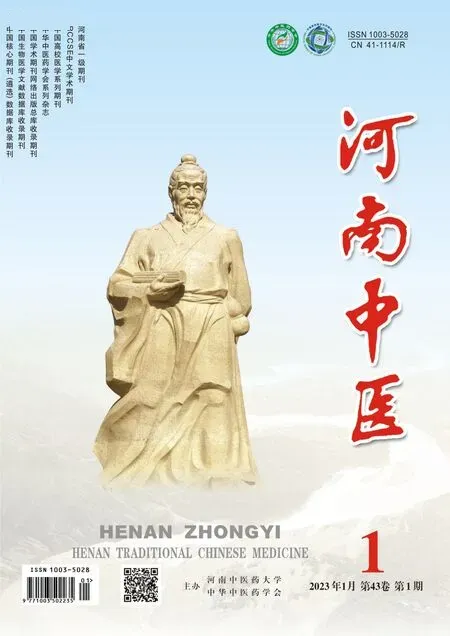茵陳五苓散治療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自發性細菌性腹膜炎臨床研究*
章璐
珠海市人民醫院,暨南大學附屬珠海醫院,廣東 珠海 519000
我國是世界上乙型肝炎(簡稱乙肝)感染者最多的國家[1],雖然有疫苗與治療藥物,但是乙肝病情發展終將導致肝纖維化、肝硬化、肝細胞癌等并發癥[2]。肝硬化患者中有25%~35%在入院時或住院期間出現細菌感染,死亡率較高。感染是失代償性肝硬化患者最重要的死亡原因,與未感染的肝硬化患者相比,死亡風險增加了4倍[3]。自發性細菌性腹膜炎(spontaneous bacterial peritonitis,SBP)是在肝硬化基礎上發生的無明確腹腔內病變來源的腹腔感染,肝硬化合并SBP可迅速進展為肝腎功能衰竭,甚至導致死亡[4]。近年來,中醫對SBP的研究越來越多[5-7],SBP常見證型有脾虛證及濕熱證,茵陳五苓散治療SBP的效果顯著,但臨床報道較少。本研究觀察茵陳五苓散治療脾虛濕熱證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的臨床療效,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2017年6月至2020年5月珠海市人民醫院收治的脾虛濕熱型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自發性細菌性腹膜炎患者80例,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觀察組與對照組,每組各40例。對照組男25例,女15例;年齡34~75(53.63±8.24)歲;病程5~18(8.26±3.14)年;病因:乙肝24例、丙肝10例、酒精性肝病1例、其他原因5例;疾病首發13例,復發或多發27例。觀察組男26例,女14例;年齡35~74(52.64±8.13)歲;病程5~18(8.12±3.09)年;病因:乙肝23例、丙肝11例、酒精性肝病2例、其他原因4例;疾病首發10例,復發或多發30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納入標準根據《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8]和《美國肝臟研究協會成人患者肝硬化腹水處理實踐指南(2012修訂版)》[9]中的乙型肝炎和肝硬化腹水的西醫診斷標準。自發性腹膜炎的診斷標準:①腹腔內存在感染癥狀和體征;②腹水細菌培養陽性;③腹水中多形核白細胞計數>0.25×109L-1;④非繼發性感染[10]。肝硬化中醫辨證標準[11]:脾虛濕熱證分為三個階段:①濕熱蘊結證,此證為脾虛水濕內蓄而熱化。腹大堅滿拒按,脘腹撐脹,煩熱口渴,目膚發黃,小便黃赤短少,大便秘結,不欲飲食,嗜臥,舌紅苔黃糙,脈弦數。②熱毒熾盛證,臨床表現為黃疸發作,快速加深,鮮黃色,體溫過高,多飲,頻繁嘔吐,腹脹,疼痛和拒絕按壓力,便秘,黃紅色的尿液,尿急,躁動,舌質深紅色,舌苔黃色、粗糙或有刺,脈沖泛濫和濕滑。③痰瘀互結證,臨床表現包括惡心,嘔吐,痰多,口腔黏稠,胸悶,腹脹,或伴有目黃,舌苔白厚或黃厚,脈滑或澀。
1.3 病例排除標準有嚴重心血管、腎臟或精神疾病;凝血功能障礙;妊娠期或哺乳期婦女;對本次研究藥物過敏。
1.4 治療方法所有患者均給予常規抗病毒治療,保肝、利尿,定期穿刺引流腹水。對照組給予頭孢噻肟(安徽威爾曼制藥有限公司,批準文號:國藥準字H20043299,規格:3.0 g)靜脈注射,每日 6 g,分3次給藥。觀察組在對照組治療的基礎上給予茵陳五苓散治療,方藥組成:茵陳160 g,澤瀉 30 g,豬苓9 g,茯苓9 g,白術9 g,桂枝6 g,水煎服,每日1劑,早晚服用。兩組均治療2個療程,7 d為1個療程。
1.5 觀察指標分別于治療前后清晨空腹抽取患者靜脈血3 mL,3 000 r·min-1離心,取上清液,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測定血清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檢測試劑盒由Abnova公司提供,貨號:KA1227)、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檢測試劑盒由QIYBO公司提供,貨號:QY-H10038)、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檢測試劑盒由Elabscience公司提供,貨號:E-ELN-H0102c);使用由南京貝登醫療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邁瑞BS-28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C反應蛋白(C reactive protein,CRP)、Ⅲ型前膠原(procollagen type procollagen type III,PCⅢ)、血清Ⅳ型膠原(type IV collagen,Ⅳ-C)、層黏連蛋白(laminin,LN)和透明質酸(hyaluronic acid,HA)。觀察并記錄治療前后兩組肝纖維化指標(PCⅢ、Ⅳ-C、LN、HA)、細菌感染標記物(PCT、CRP)以及炎性因子(IL-6、TNF-α)變化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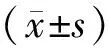
2 結果
2.1 兩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治療前后肝纖維化指標比較具體結果見表1。

表1 兩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治療前后肝纖維化指標比較
2.2 兩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治療前后細菌感染標記物水平比較具體結果見表2。

表2 兩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治療前后細菌感染標記物水平比較
2.3 兩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治療前后炎性因子水平比較具體結果見表3。

表3 兩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治療前后炎性因子水平比較
2.4 兩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臨床癥狀改善時間比較具體結果見表4。

表4 兩組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臨床癥狀改善時間比較
3 討論
肝功能衰竭、肝功能失代償期肝硬化以及肝臟惡性腫瘤的患者極易合并SBP。肝臟庫普弗細胞的功能降低,使得患者的身體抵抗力下降,細菌入腹腔導致SBP。SBP的發生可能與門靜脈血液瘀滯、腸黏膜屏障功能障礙以及毛細血管通透性增加存在密切關系,細菌進入血液引發周身感染,其中,腹腔是最容易感染的部位。SBP沒有明顯的腹腔內病灶,當腹水中的中性粒細胞計數高于250 μL時,應考慮為此病癥[12]。在住院期間存在腹水的肝硬化患者中,SBP的發生率為5%~25%[13-14]。細菌感染是肝硬化十分常見的并發癥,并且肝硬化患者發生感染的病因很多:肝功能不全、腸道營養不良、細菌易位、體液免疫和細胞介導免疫力下降、門靜脈高壓加劇、遺傳因素等均為肝硬化患者感染的影響因素[15]。SBP患者預后較差,死亡率為20%~30%。目前,治療SBP的方式主要有抗生素和白蛋白輸入治療。因此,早期診斷、合理選用安全有效的藥物治療對改善預后非常重要。作為第3代頭孢菌素類的頭孢噻肟,具有抗菌譜廣、強大的對抗革蘭陰性桿菌的作用,且腎毒性小,不易并發二重感染,能迅速進入腹腔內起到殺菌作用,臨床效果顯著,已廣泛應用于SBP的抗菌治療中。
肝硬化合并SBP屬于中醫學“臌脹”的范疇,是中醫“風、癆、臌、膈”四大重癥之一。肝硬化的病位在肝,乃邪毒未清,導致肝郁血停,久而耗傷氣血,結而成痞。本研究采用茵陳五苓散,茵陳清熱利濕、疏肝退黃,合以五苓散利水滲濕,佐以桂枝,增強除水濕之力,發揮溫陽化氣、利濕行水之功效,溫腎陽、調肝氣、健脾利濕則臌脹除。目前,肝硬化合并SBP的發生機制尚未明確,大量研究表明,炎性病變以及免疫系統被激活對SBP的疾病進展意義重大,腹水中的促炎細胞因子表達增多也是其中關鍵的環節。同時,抗炎細胞因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炎性病變的發生發展中參與重要的調控,因此促炎細胞因子和抗炎細胞因子的動態變化決定SBP發展的預后和方向。肝硬化合并門靜脈高壓患者容易出現機體抵抗能力下降,腸黏膜屏障功能受損,腸壁瘀血,水腫,通透性增高,腸道細菌大量繁殖、擴散、移位,導致腹腔發生細菌感染[16],上述情況與SBP的發生具有密切相關性。血液中的單核-巨噬細胞以及腹腔中的巨噬細胞被移位的細菌及其釋放的毒素持續激活,導致TNF-α高表達,誘發免疫活性細胞激活釋放炎性介質,繼而參與抗感染過程,導致促炎細胞因子表達水平升高,且與機體產生的抗炎細胞因子發生拮抗。國內研究對比肝硬化腹水合并SBP與不合并SBP,發現合并SBP患者腹水中IL-10的水平較不合并SBP低,IL-18水平較不合并SBP高,說明合并SBP患者中抗炎細胞因子相比促炎細胞因子更有優勢,這可能是引發SBP的原因之一[17-18]。隨著癥狀改善,兩項指標均發生顯著變化,同時腹水中的兩項指標改變最明顯。陳勇等[19]發現,肝硬化合并SBP的患者腹水中白細胞介素水平高于血清,其機體腹水中大量中性粒細胞聚集引發了細胞因子級聯反應,促炎細胞因子和抗炎細胞因子高表達,導致腹水中白細胞介素的水平高于血清,提示血清中白細胞介素可能來自腹水。故在臨床對腹水中的相關指標進行動態監測可作為療效觀察指標。
有研究表明,TNF-α對IL-6的產生起到正調節作用,TNF-α、IL-6增高與內毒素刺激巨噬細胞導致過量分泌密切相關。PCT對肝硬化合并SBP的早期診斷相對于傳統標記物(如C反應蛋白、白細胞、紅細胞沉降率等)具有較高的特異度和敏感度。IL-6屬于一種炎性因子,當機體受損后,血清中 IL-6 水平迅速升高。PCT屬于一種常見的感染指標,其正常狀態下水平極低,一旦發生細菌感染,通過炎癥機制,肝細胞、神經元的PCT分泌量上升,繼而血清中的PCT水平升高。PCT的穩定性較佳,易檢出,若感染得到控制,2 d內血清PCT水平會迅速降低,故臨床上經常將PCT作為感染指標。PCT是一種糖蛋白,不具備激素活性,主要是甲狀腺C細胞分泌而來,在正常狀態下其值極低,檢測血清中是否存在PCT較困難,一旦機體發生細菌感染尤其是感染嚴重或周身感染,其水平異常升高。PCT對細胞因子級聯反應的調控十分關鍵,在一些感染疾病中其值較高,原因可能在于其與IL-6、TNF-α等炎性因子的刺激存在一定關系。PCT在機體發生感染后會迅速升高,此時可在血清中檢出,其在機體中較為穩定。相比其他感染指標,未發生細菌感染其水平不會升高,并且在一些慢性或局部非特異性感染疾病中其水平升高程度較小,因此針對感染嚴重的SBP其具有較高的檢測價值[20-22]。
乙型肝炎十分常見,WHO統計數據顯示,每年死于HBV導致的肝功能衰竭、肝硬化以及肝臟惡性腫瘤的患者高達百萬人數,乙型肝炎的預防和治療已成為當前十分重要的公衛問題。乙型肝炎的發生與機體的免疫存在緊密的關系,HBV復制以及因此引發的免疫反應是引發肝臟受損和疾病惡化的重要原因。乙型肝炎治療的目的在于制止HBV復制以及清除HBV,中醫學中沒有乙型肝炎的病名,此病在中醫學中屬于“脅痛”等范疇,中醫認為,此病多因濕熱疫毒蘊結腸腑,病發之初邪毒內盛,如果病情嚴重,用藥劑量不足,導致機體內仍存在余邪,加之使用苦寒藥,藥物配伍不合理,脾胃受損,脾運化功能失常,脾氣虧虛,從而出現水液運化障礙,導致胸悶、飲食下降、舌苔厚膩等。濕熱邪毒郁積于肝脾,因此引發乙型肝炎,故乙型肝炎的中醫證型為肝膽濕熱證。中醫學認為,此病多是因肝火亢盛、濕熱稽留脅痛,日久耗陰傷血,導致陰虛血燥。由于肝臟和腎臟本是同根同源,肝腎陰液虧虛,虛熱內擾,肝病傳至脾導致脾腎虧虛。脾臟運化水液的功能出現問題,水濕停滯形成腹水,臟氣內虛,功能失調,寒凝氣滯。
五苓散出自《傷寒論》,適用于陽氣不足,氣化不利,津液不布,水飲內停之病機,病位涉及上中下三焦。因水飲之邪停留部位不同,臨床病癥變化多端,該方可用于心腦血管疾病、肝硬化腹水、慢性腹瀉、腸炎、各類泌尿系統疾病、特發性水腫、尿潴留等。肝硬化合并SBP患者屬脾虛濕熱內盛、中焦氣化不利,水氣內停之病機,正合五苓散健脾除濕利水之功,故用之療效良好。五苓散加茵陳為茵陳五苓散,全方六味,出自《金匱要略》,適用于內生濕熱、氣化不利為基本病機的黃疸、脅痛、陽痿、眩暈、痹證、不寐等疾病。該方以綿茵陳為君藥,茵陳苦寒,苦能燥濕,寒能清熱,其氣清芬,善于滲濕而利小便。臣以澤瀉、茯苓、豬苓,取其甘淡滲利之性,輔以君藥,加強利水之功,且水散熱亦消也。葉天士謂:“滲濕于熱下,不與熱相搏”。佐以炒白術健脾利濕,桂枝助陽化氣,俾土實氣行,則水濕化矣。方中茵陳是治療濕熱的主藥,現代研究已證實,其具有保肝利尿的功效,茯苓、澤瀉具有利濕行水的功效。《藥品化義》認為,茯苓“最為利水滲濕要藥”。《用藥心法》云:“茯苓,淡能利竅,甘以助陽,除濕之圣藥也。味甘平補陽,益脾逐水,生津導氣”。《本草匯言》中提到:“澤瀉有固腎治水之功,然與豬苓又有不同者,蓋豬苓利水,能分泄表間之邪;澤瀉利水,能宣通內臟之濕。白術甘溫苦燥,善于補脾氣,燥化水濕,與脾喜燥惡濕之性相合,治療脾虛濕滯有標本兼顧之效。”白術可改善消化系統癥狀。此方中桂枝具有發汗解肌,溫通經脈,助陽化氣的功效,與茯苓、豬苓、澤瀉同用可治療水濕內停病證[23]。本研究以茵陳五苓散治療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此方溫陽化氣,利濕行水,清除濕熱邪毒,水濕下行從尿道排出,具有清除患者機體內的濕熱邪毒,清熱解毒的功效。
綜上所述,茵陳五苓散辨證治療可有效降低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SBP患者的肝纖維化指標、細菌感染標記物、炎性因子的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