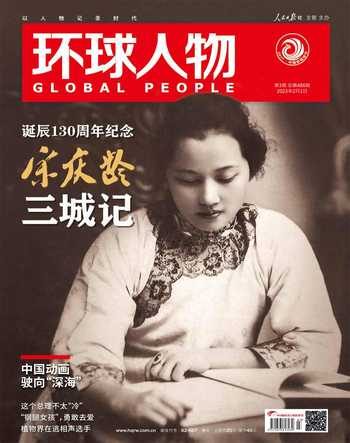李氏,回山轉海不作難
周白之白
在動輒千百年的歷史長河中,墓志是古人留給后人的“時間膠囊”。那些長期深埋于地下的墓志,在種種偶然因素的作用下,部分會被后人發掘、識讀。在這種極其幸運的偶然之下,那些本該湮滅無聞的人物和故事就這樣闖進了我們的視野,那些曾真實存在過的鮮活人生,在千百年之后,似乎仍有某種擊中胸膛的力量,讓人感受到那個時代的力量。
如果不是60多年前于陜西乾陵(唐高宗李治與皇后武則天合葬墓)偶然發現的《大唐故劉府君墓志銘》,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唐朝女性李氏,以及她那趟蕩氣回腸、艱難而堅韌的人生旅程。
李氏是墓主劉浚(同濬)的發妻,劉浚則是唐朝宰相劉仁軌之子。劉仁軌因在百濟(朝鮮三國時代政權之一)之戰中斬獲戰功,頗受高宗與武則天重用,84歲卒于宰相之位,陪葬乾陵。
李氏的丈夫劉浚亦非等閑之輩,他17歲隨父征伐,屢屢立下戰功,平李敬業之反時又以江左五州簡募宣勞使的身份大放異彩,累遷至太子中舍人。
劉家父子的生平,新舊唐書《劉仁軌本傳》均有載,而李氏則不見于史籍。
換言之,重見天日的《大唐故劉府君墓志銘》,是李氏曾來過人間的證明。
唐高宗尚在人世的時候,武則天就已經成為“雙圣”之一,等到唐高宗去世以后,武則天的權勢自然達到了頂峰。
面對如此情形,野心勃勃的武則天不甘放權做一個盡心盡力輔佐新皇的太后。為此,武則天想出一個辦法來試探朝中大臣的心思。
她讓朝堂上的所有大臣去寫一份勸進表,其目的就是為了讓自己的皇帝之位變得名正言順,并同時告訴天下人:我本來是不想當皇帝的,但大家都勸我當皇帝,那我也只能勉為其難地帶領大家走上繁榮昌盛的道路。
如果大臣愿寫,那就說明他可為自己所用;若不愿意寫,想辦法打壓即可。
劉仁軌生前即勸誡武則天吸取西漢呂后之禍的教訓,及早讓權抽身。可能是受其父的影響,劉浚堅決反對武則天稱帝,所以劉浚對那份勸進表的態度可想而知。
最終,劉浚為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由于受到誣陷,劉浚被流放嶺南,載初元年(公元690年)被酷吏殺害于廣州,年僅四十七歲。

李氏決定接回丈夫遺體。
據墓志推算,丈夫劉浚客死他鄉那年,李氏剛好40歲。
有關李氏40歲之前的人生,墓志上所言不多。只知道她來自隴西李氏家族,是隋絳郡公李禮成六代孫、右衛將軍李揚休長女。她“麗如朝蕣(因同舜)”而“操若寒筠”,年初及笄(約15歲)便早早地嫁到劉家。
幸運的是,因出眾的德操行能,李氏得到了丈夫全家人的認可。婆婆文獻夫人年老多疾,李氏與丈夫劉濬親侍湯藥,十數年如一日。夫妻二人的至孝之行甚至一度受到高宗的表揚,來自朝廷的欽賞也被劉家引以為榮。
40歲之前,李氏的人生雖不乏高光時刻,但其行動軌跡仍不外乎廳堂之間,所付出的辛勞勤勉,亦不過想要全力做好一位妻子和兒媳而已。
李氏40歲之前的人生,即使談不上養尊處優,也畢竟是高門貴婦,總體而言還算平靜、閑適。如無意外,她會繼續平靜地生活下去,最終以一位飽受尊重的夫人身份過完心滿意足的一生。
但40歲那年,丈夫枉死嶺南的噩耗突然傳來,李氏的人生就此被徹底打亂。巨大的悲痛之中,她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她要帶著幼子,親自從遙遠的廣東接回亡夫劉浚的遺體,讓其落葉歸根。
在當時的條件下,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更何況,李氏還是一位大概率從未出過遠門的悲痛中的女子。
“山長海闊,萬無一回。”墓志銘用這八個字形容了李氏那趟旅程的艱險,感覺也像在寫每個人的一生。
關于李氏此舉的艱難與悲壯,墓志寫得蕩氣回腸:
及公枉歿南荒,夫人攜幼度嶺,行哭徒跣,扶櫬還鄉,寒暑四年,江山萬里,一朝至止,誰不嗟伏!
在唐朝,長途旅行的艱難遠非今人所能想象。據學者統計,唐朝旅行者的不幸遭遇大概有虎殺、鬼擊(突發疾病)、南方的毒蟲與瘴氣等若干種原因,任何一種都足以輕易奪人性命。
與玄奘、鑒真這樣心懷虔誠信仰的旅行者相比,支撐李氏踏上那段旅程的信念又是什么呢?她可能是出于成婚20多年來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的伉儷情深,也可能是出于對丈夫在嶺南異鄉枉死于酷吏之手的痛惜。
總之,在穿越四個春夏秋冬、往返萬里之后,劉浚的遺體奇跡般地回到了故鄉。
劉浚墓志后有銘,極力渲染了李氏的壯舉,其辭精煉清麗、悲壯痛切,讀來深受震撼。
生妻稚子,既少且孩。
他鄉異縣,誰不哀哉。
山長海闊,萬無一回。
卓哉夫人,貞操絕倫。
涉水萬里,乘舟四春。
扶櫬攜幼,來歸洛濱。
“山長海闊,萬無一回。”墓志銘用這八個字形容了李氏那趟旅程的艱險,感覺也像在寫每個人的一生。

《大唐故劉府君墓志銘》。
隨著年齡的增長,那趟艱險旅程的后果逐漸顯露出來:“屬以往纏瘴癘,患漸膏肓。”南方的瘴癘之毒還是侵蝕了李氏的健康,并逐漸發展成難愈之疾。皇帝特賜金丹、親題藥法,名醫不絕、中使相望,然而,“生也有涯,命不可贖”。
開元十七年(公元729年),李氏“薨于道政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九”。
李氏的臨終遺言之中,“吾內省無違”五個字格外值得玩味。用今天的話說,李氏自認為她這一生拼盡了全力、絲毫無愧于心。任何朝代、任何身份的人,若臨終前能有這樣的感悟涌上心頭,大概都會令人羨慕吧。
李氏臨終之前,還想著身體力行改革葬禮習俗,那就是死者“用物覆面”。李氏認為,“用物覆面”本是古時失行者因恥見亡靈而作出的舉動,后人無知,相習成例而已,革除此弊習俗成為李氏在人間的最后一個愿望。以李氏之志行,她顯然無須恥見任何亡靈。
值得欣慰的是,在李氏的悉心撫養教導之下,劉浚與李氏所生之兩子皆順利長大成材。長子劉晃一度受到玄宗賞識,且寫得一手好詩,曾與宰相張說唱和;次子劉昂,官至京兆少尹。
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時當春末夏初,李氏與丈夫劉浚合葬于乾陵陪葬墓地。巧合的是,這年的春末夏初,李氏的同宗——時年三十整的李白第一次來到長安。
也許是受墓志銘里“山長海闊,萬無一回”八個字的影響,每次當讀到李白那句“回山轉海不作難,傾情倒意無所惜”,筆者總忍不住想起李氏的故事。
銘像來勢洶洶的提問,詩則是一個干脆利落的回答。
至少,無論連名字都沒能留下的李氏,還是名滿天下的李太白,都是這么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