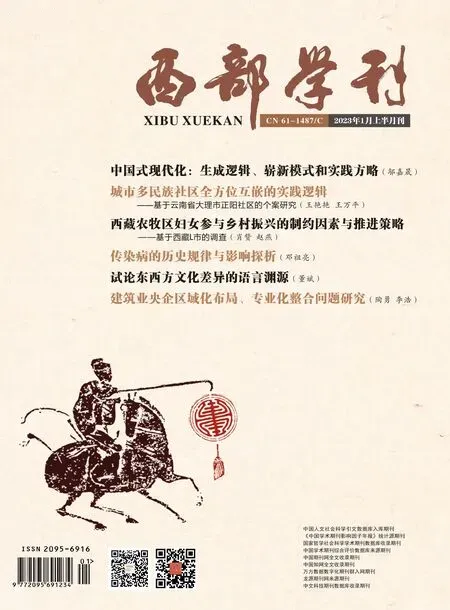赤子之心與孩童之心
——老子與李贄二心之解析
張 潔
在老子《道德經》五千言中,老子提到“赤子”或“嬰兒”的地方共有五處:“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圣人皆孩之。”“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在書中多次提及赤子或嬰兒是希望人們能夠返璞歸真,時刻保持一顆“赤子之心”。嬰兒的天真無邪、淳樸自然不免讓人聯想到自然成長的孩童,“孩童之心”是真心、是本心,是人的心靈最自然地發散流溢出的狀態。不論是“夫童心者,真心也”,還是“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都體現出“孩童之心”在李贄理想人格和價值準則中所占據的主導地位。擁有“孩童之心”,就是保持未被污染的本真之心。本文將闡釋“赤子之心”與“孩童之心”的思想內涵,并力圖從二心的復歸與深化兩個方面對其進行比較,以求得出二心之間的相互辯證關系。
一、何謂“赤子之心”?
“赤子”一詞最早出現于《尚書·康誥》:“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孔穎達疏:“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天生赤色,故曰赤子,可見“赤子”即為剛出生的嬰兒。與嬰兒語義相近的還有“孩”“孺子”,等等。春秋時期戰火不熄,動蕩不止,諸侯兼并,民眾流離失所。混亂的社會環境、尖銳的社會矛盾,給民眾帶來數不清的災難。在這個社會的變革與轉型時期,奴隸主貴族式微,封建因素蓬勃發展,老子提出“赤子之心”,希望人們回歸到樸素自然的狀態中,意圖緩解人們之間的爭奪與殺戮。
為何“赤子之心”被老子所提倡,其背后根本原因是老子認為“赤子之心”之中有著一種“大德”,天地大德曰之生,“德”正是從“道”中所來,是形而上本體永恒之“道”在人世間的切實體現。老子說:“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擁有深厚道德之人,就好比初生的嬰孩,毒蟲、雄鳥、猛獸都不會主動去傷害他,整日大聲啼哭,但嗓子不會沙啞,這都是因為他精神狀態飽滿、和氣淳厚的緣故,這也是“含德”的緣故。同樣講“德”的還有“常德不離”。如果“道”作為老子哲學體系的根本原則,那么“德”就是無形無體、恍忽幽深的“道”內化于萬物的顯現。初生的“赤子”或“嬰兒”體現了“含德之厚”這種理想的完滿狀態。因為其保持著這種完滿狀態,所以“赤子”無知無欲,如王弼注:“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嘎也。”正因為自身圓滿無所欲求,無所求之即無所奪之,無所奪則不犯萬物,所以蛇蟲鼠蟻、飛禽走獸都不會“損其全”,“益生曰詳,心使氣曰強”要求人不能有縱欲貪生、心使氣強的做法,事物過于壯盛了就一定會衰敗。從這里可以聯系到老子的“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水善于滋潤萬物而不與萬物相爭,停留在眾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因此最接近于“道”,最近于道的水的特征就是利萬物而“不爭”。最善的人選擇居住最卑微惡劣的地方,而心胸卻保持深不可測的沉靜。“心,善淵”的“淵”字,亦有保持沉靜之義。心如果不爭、不動,不支配氣,就不會破壞和順的狀態,否則有心強求“謂之不道”,不合乎道就會滅亡,那么就不能如“赤子之心”一般得道而活。赤子是“含德之厚”的存在,而“赤子之心”也必須謂之有道。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是老子以及道家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是“道”作用于萬事萬物的一種自然狀態。“樸”有質樸、素樸之意,是一種未經干擾的原始狀態。“樸散則為器”,與“樸”相背的就是人為的雕琢。王弼注:“真也,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真樸已散,成為萬物之器。”“器”與“道”相對應,形而下者謂之器,是真樸這種狀態被打破后的產物。“嬰兒”與“樸”正是有著這種天然去雕飾的初生狀態,一種渾然天成、未加修飾的自然本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鎮之以無名之樸,夫將不欲。”貪欲滋長,那我就要用“道”的真樸來鎮住它,這樣就不會產生貪欲之心了。在“樸”的狀態下,人性的欲望不會過分滋長,這樣狀態下的人性是真的、自然的,始終保持本真的狀態,宛如初生的“嬰兒”。無法否認的是,嬰兒會成長為大人,人性的私欲也會從無到有,那么最為重要的無非要善于保持這種自然的狀態。“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鑒,能無疵乎?”精神和形體合一,聚結精氣以致柔和溫順,那么人心靈深處明澈如鏡、深邃靈妙。“嬰兒”能保持其“樸”的狀態,在于“抱一”與“專氣”。身體與精神合而為一,自然之氣聚合,始終保持這種本能狀態。老子認為,像“嬰兒”或“赤子”這種其心保持質樸、專一的狀態才是人應當追求的。
二、孰是“孩童之心”?
李贄所處的晚明時代,封建制度逐步走向衰落,而統治階級為了加強統治,使得經濟、政治、思想上的禁錮加劇。但是隨著新經濟萌芽的開始,刺激產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家,李贄就是其中之一。李贄提出“孩童之心”的思想,希望人們保有自然之童心,童心也就是“孩童之心”,孩童的心是純真無暇、自然而然的。李贄關于“孩童之心”的主張主要集中在《童心說》中。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也就是“真心”,孩童的心是純潔、天真無邪的,是一種純任自然的狀態,是心的自然之性。李贄這里的“真”吸收了道家的思想,道家的“真”,有自然之意,崇尚自然,反對人為的雕琢。“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真”受于天,是自然的不可更易的,“真”中含有的自然之序,反對任何阻礙精神形體自由之事物。李贄提倡的“真”,在此基礎上更強調人發于內心之真情實感的現實表達。與“真”相對的也就是“假”,“真”即“絕假純真”。“夫既以聞見道理為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于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如果一切以聞見道理為主,那么說的話就變成了刻意為之,而不是內心的真實表達。人一旦以虛假為本,所知所行無不虛假,人人虛假則難以辯真。“真心”與“假心”相對應,表現的是真自我、真性情,一旦“童心”被障,取代“真心”“真言”的就變成了“假心”“假言”。
“本心”是樸素、原始、未受社會世俗氣息沾染的純凈孩童之心。李贄認為“童心”即“最初一念之本心”,這里提到的“本心”是禪宗術語,禪宗的佛性論以“心”為本體。高僧慧能云:“若識本心,即是解脫。”人要保持“本心”的清凈無染,摒除俗世的紛擾、誘惑,堅守本性,這樣才能明心見性、成圣成佛。慧能認為任何人都有佛性,“眾生即佛,佛即眾生。”但世人往往貪戀塵世的紛擾,容易失去本心、迷失心智,所以佛性的保持就在于內心的清凈無染。“孩童之心”在父母未生之前是空無的,在降生之后也未曾沾染外物,是純凈無瑕的,所以“童心”具有“本心”的特征。李贄認為“孩童之心”本來就是清凈的,之所以失去清凈的本體,原因在于“童心”被“障”。“童心既障,于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造成“童心”被障的是“聞見道理”。如果后天得來的感性聞見和理性道理一旦入主人的心靈,“童心”也就壅塞了,說出的話言不由衷,寫出的文章并非真情實感。這里的“障”字出自禪宗“理障”這一概念,解釋為當下解脫的障礙,它也是禪宗的核心思想。真正的解脫只能通過自心自性的體悟實現,并不是通過語言和聞見這些外在的形式達到,這與李贄“童心說”中關于“童心被障”的看法不謀而合。“童心”是斷絕虛假的根源,成為圣賢的根本,而“本心”更是獲得佛性的關鍵。李贄的“孩童之心”是他對佛家“本心”的借鑒與運用,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
李贄在《藏書》中寫道:“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李贄的“童心”包括人的私心,并且這種私心是人皆有之的,即使是圣人也不例外。人人都有趨利避害的利己之心,“私”是“人之心也”,是人所共有的天性。私欲是人們在日常生產活動中追求物質利益和精神需求的來源和動力,李贄從百姓日用的角度,肯定了私心的合理性:“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并且親身體驗百姓的勞苦生活和傾聽廣大勞動人民肺腑之言。李贄認為“人必有私”,肯定勞苦人民擁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擁有自己合理的私人利益是天經地義的,同時批判了專制統治者以仁義道德為借口剝削人民的事實。
三、“心”之復歸與深化
(一)“赤子之心”與“孩童之心”的復歸
老子的“赤子之心”和李贄的“孩童之心”雖然年代相隔久遠,但是兩者之間存在著共通之處。李贄受老子思想由來已久,曾作《老子解》。李贄的“孩童之心”思想深受老子“赤子之心”的影響,赤子的“復歸于樸”與孩童的“真心”都崇尚一種渾然天成、未加修飾的原始自然狀態。“樸”的狀態因欲望而打破與“聞見道理”導致的童心被“障”都突顯了“二心”的失落;老子的“復歸于嬰兒”以及李贄對“天下之至文”的追求與呼喊都體現出“二心”回歸的必然,而這些都可以歸結為“二心”的復歸。
首先,“赤子之心”和“孩童之心”的復歸意味著二心的失落。老子“赤子之心”的失落在社會層面,表現為“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統治者“強為”,干預的越多越刺激人們欲求的瘋長,從而導致“赤子之心”的失落,而心的失落又加劇了民眾的罪惡、社會的混亂。在個人層面因“聞見道理”入主心靈,“童心”因被其所替代而喪失,“童心”喪失,一切皆假,不是出自“童心”的話,即使再動聽,也是毫無意義可言的。只有發自“童心”的作品,才能成為“天下之至文”,但因為“假人”“假事”,尤其是“假文”的盛行,又進一步加劇了“孩童之心”的喪失,從而陷入惡性循環。
其次,“赤子之心”和“孩童之心”都是老子和李贄對其理想人格的追求,是通往理想人格所需的內在的道德與性情修養。“復歸于嬰兒”“圣人皆孩之”因為嬰兒是含德之厚、無欲無知、自然圓滿的存在,因此得道要“復歸于嬰兒”,得道成圣即是保持赤子的本性,復歸于赤子純真自然的狀態,圣人不為外物所累,順乎自然,這種狀態也正是老子最為推崇、追求的理想狀態。“古之圣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在李贄看來,圣人們不讀書時,童心自然存而不失,縱使多讀書,他們也能守護童心,“童心”在此成為評判的標準,圣人也就是童心未失的人。“二心”的復歸是達到圣人理想人格的內在途徑,是原初理想狀態的復位與回歸。
最后,“赤子之心”與“孩童之心”都具有存在、失落與回歸的運動過程,但二心在復歸程度上存在一定差別。老子“赤子之心”復歸的終點在于消解人的欲望,并使之抽離喧鬧的世俗,讓掩蓋在欲望與世俗下的人性得以顯現,從而復歸人自然之本性,復歸于“赤子”,最后復歸于最高之境界——“道”。“孩童之心”在復歸的同時考慮了生存的現實性,在圓滿的理想狀態與殘酷的現實之間拉扯,在復歸與生存之間找到平衡的出口。因此,老子的“赤子之心”是李贄“孩童之心”復歸的方向與終點,而“孩童之心”是“赤子之心”在現實的土壤里得到的發展與延伸。
(二)“孩童之心”對“赤子之心”的深化
隨著時間的流逝,嬰兒總會長成孩童,“孩童之心”在保留原初“赤子之心”的同時緊扣時代發展。老子理想的社會是回歸到“小國寡民”的狀態,不追求知識和利益,老百姓各得其所,自然而然地生活,這是針對當時混亂的社會環境,追名逐利的社會風氣提出的主張。老子認為是“赤子之心”的丟棄,導致人私心私欲的泛濫,因此希望人民無欲無為,老死不相往來,從而在復雜的現實斗爭中遠離紛擾、保全自己。
李贄所處的時期市民階級壯大,他的社會經歷使其從市民階級的角度出發,肯定追求物質利益的合理性,李贄的“孩童之心”里不僅有“真心”也有“私心”,與老子的“赤子之心”不同的是他肯定了私心存在于人本性中的正當性,把“赤子之心”的出世拉入到“孩童之心”的入世。李贄的“私心”也體現了對人自身的關注,他在《焚書》里寫道:“士為貴己,務自適,如不自適而適人之適,雖伯夷、叔齊,同為淫癖;不知為己,惟務為人……”,做人貴在做自己,要肯為自己的“孩童之心”去斗爭以此感到自我安適,而不是去一味地遷就他人。這與老子“赤子之心”里強調“不爭”的觀點也是不同的。李贄對“赤子之心”思想進行了深化,“孩童之心”在保持“赤子之心”本真與質樸的同時,從自身的生存與幸福出發著眼于人本身的發展,順從自然之本性,在浮華喧囂中秉持自己內心的純真與自由。
李贄對“赤子之心”的發展還體現在文學創作中。他把“赤子之心”的自然本真運用到文學領域,把是否擁有“童心”看作是創作的關鍵,強調作者的原初自然之心,如追求“自然之為美”的“化工”境界。“致虛極,守靜篤”,但老子的“赤子之心”更向往擺脫外在的束縛和紛擾、致虛守靜的理想生活。與老子平淡不爭的心境不同,李贄在保留其心的情況下對“童心”的維護更為激進。屈原在《九章·惜誦》里“發憤以抒情”,李贄依據其觀點,提出了“發憤而作”:“不憤不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呻吟也,雖作,何觀乎?”他所說的憤是一種怨憤激昂的情感表達,要隨心所欲,不受任何約束,甚至“發狂大叫,流涕痛哭,不能自止”。創作不僅要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感,更要將這種情感強烈地表現出來。李贄在文學上這種情感的強烈噴發和具有時代性的觀點是對老子“赤子之心”的內在發展與深化。
四、結語
“赤子之心”和“孩童之心”是老子、李贄在各自時代背景下提出的理論觀點,雖相距甚遠但仍有異曲同工之妙,歸結為二心的復歸與深化。赤子終會長成孩童,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二心都是在人生漫長歷程中擺脫生存困境、邁向理想人格、呼喚理想家園的重要途徑。老子的“赤子之心”向往與原初世界合二為一,是其理想之追求,李贄的“赤子之心”珍視人間之煙火,是其現實之央浼。李贄的“孩童之心”是老子“赤子之心”自然而然的發散與流變,“赤子之心”與之同時也是“孩童之心”的指向與歸宿,二者相互交織,互為表里,以成就天地之大心,道德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