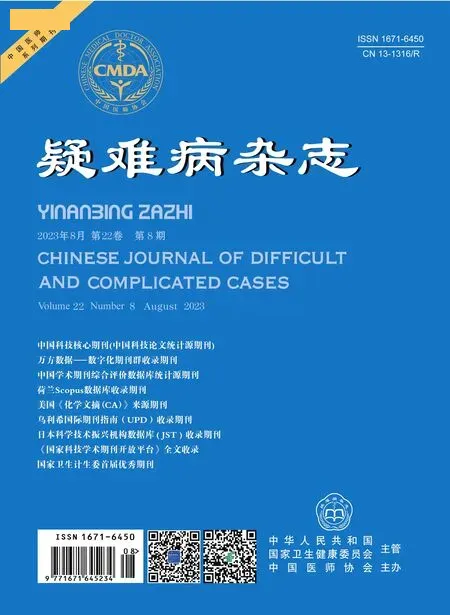腸道菌群與膽固醇結石、膽色素結石形成關系的研究進展
樊鳳良綜述 孫海軍審校
膽囊結石(cholecystolithiasis)作為人類消化系統最常見的疾病之一,隨著人們近些年來生活水平的提高,發病率也在逐年攀升。膽囊結石主要包括膽固醇類結石、膽色素類結石和以碳酸鈣與磷酸鈣為主的混合型結石,相比膽色素類結石,膽固醇類結石發病率要遠大于膽色素結石[1]。膽囊結石的發病主要與高脂飲食、肥胖及女性激素等因素造成膽汁濃縮和淤積密切相關[2]。近些年發現腸道菌群也參與膽囊結石的形成,并產生重要影響,探究清楚微生物菌群和膽囊結石的關系或許成為治療或干預膽囊結石的潛在選擇。
1 腸道及膽道菌群分類
微生物群落被認為是人體不可替代的成分,它們對于人體的特定生理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胃腸道中與人類共生著大量微生物,健康成年人的腸道微生物種群主要由細菌門厚壁菌門和擬桿菌門(90%)組成,其次是其他門,包括比例較低的放線菌(主要是雙歧桿菌)、變形桿菌、梭菌和疣微菌[3]。這些定植于人類胃腸道的微生物通過共生、共同進化,可以影響個體的生理、新陳代謝、營養和免疫功能,其正常比例維持著人體的正常功能,因而即使微生物種群微小變化也會引起菌群的生態失衡,從而導致人體的功能紊亂,繼而引發機體一系列疾病,如炎性腸病、癌癥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等[4]。
目前尚不清楚健康個體和非感染性疾病患者的膽管中是否存在微生物組,普遍認為健康個體的膽管中不存在微生物。但膽管已被證明在疾病條件下攜帶細菌,膽管結石的復發部分也歸因于細菌從小腸的遷移[5],其遷移存在2種途徑:一種是通過腸屏障,另一種是通過肝腸軸即Oddi括約肌直接回流。研究表明,膽道菌群與十二指腸相似,變形菌門(61.7%)、厚壁菌門(25.1%)、擬桿菌門(5.0%)、梭桿菌門(4.6%)和放線菌門(2.6%)是膽汁中最主要的門[6]。因此,腸道和膽道菌群失衡的關系也越來越被重視。
2 膽固醇結石與菌群關系
菌群參與膽固醇結石的形成主要可以通過調節膽汁酸代謝參與膽固醇結石的形成和微生物群代謝物參與膽囊中膽固醇結石形成2種機制進行[7]。
2.1 膽汁酸的腸肝循環 肝細胞是膽固醇合成膽汁酸的場所,其合成途徑包括由肝細胞中膽固醇7α-羥化酶(CYP7A1)介導的經典途徑,以及由肝細胞中甾醇27-羥化酶(CYP27A1)介導的替代途徑,研究表明CYP7A1和CYP27A1的表達可受到腸道微生物群的調節[8],膽固醇首先通過上述2種途徑合成游離的初級膽汁酸, 然后通過酰胺鍵與牛磺酸和甘氨酸結合形成結合膽汁酸。在進食時通過神經和體液調節刺激膽囊分泌儲存的結合型膽汁酸,其通過膽管分泌進入腸道,來幫助脂類的吸收。而有一部分結合膽汁酸進入腸道后被具有膽汁酸鹽水解酶(BSH)的細菌催化成為游離膽汁酸,進而被7α-脫羥基轉化為次級膽汁酸,最后由腸上皮細胞吸收經由門靜脈返回肝臟,完成膽汁酸的腸肝循環[9]。
2.2 HBS與游離膽汁酸 目前已知在腸道中的部分結合膽汁酸能被腸道中細菌產生的BSH水解成游離膽汁酸,這些細菌種類眾多,目前已知擬桿菌屬、梭菌屬、雙歧桿菌屬、乳酸桿菌以及腸球菌等菌屬具有BSH[10]。研究表明,小腸中的結合型膽汁酸被腸道微生物群產生的BSH代謝,通過C24酰胺鍵水解釋放非共軛BA[11]。游離膽汁酸代謝主要依賴法尼醇X受體(FXR)[12]和G蛋白偶聯受體(TGR5)2種關鍵的受體[13]。在肝臟和回腸中FXR表達最多,在肝臟中游離膽汁酸可作為信號分子激活 FXR,從而抑制7α-羥化酶的啟動子,進而抑制7α-羥化酶的表達,最終抑制游離膽汁酸的合成[12]。回腸中膽汁酸通過刺激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15/19 (FGF15/19)的表達,進而將FGF15/19釋放到門靜脈血中,再激活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4(FGFR4)的表達,FGF15/19調節膽汁酸合成,FGF19可通過門靜脈循環到達肝臟,通過抑制膽固醇7α-羥化酶(CYP7A1) 的活性來抑制肝細胞分泌Bas[14]。TGR5主要依賴次級膽汁酸來激活,作為腸道微生物種群和膽汁酸之間相互作用的另一個靶點,TGR5的激活會引起細胞內環磷酸腺苷(cAMP)增加,從而導致靶蛋白磷酸化的水平增加[15],最終引起腸道的運動活躍等變化。內源性β-葡萄糖醛酸酶可能會影響肝內膽管結石的形成,其表達和分泌增加可以通過脂多糖在PKC、NF-κB、c-myc通路在肝細胞和肝內膽管上皮細胞中級聯誘導實現[16]。而膽汁鹽的存在增加了細菌細胞的通透性,并且膽汁鹽可以顯著增強腸道中細菌的β-葡萄糖醛酸酶活性,從而影響結石的形成[17]。
2.3 7α-脫羥基與次級膽汁酸 腸道菌群還可以產生7α-脫羥基酶,其可將腸道中的游離膽汁酸轉變為次級膽汁酸[18]。和BSH不同的是,具有7α-脫羥基酶的細菌在腸道中占有極少的比例,僅在少數梭狀桿菌屬及鏈球菌科中發現了 7α-脫羥化酶,但這些含量相對較少的腸道菌群對宿主的影響卻可能很大,而且它們可以增加腸道中的次級膽汁酸,如石膽酸(LCA)和脫氧膽酸(DCA)[19]。
3 膽色素結石與菌群關系
膽色素結石是由細菌產生的β-葡萄糖醛酸酶使膽紅素解離并與鈣結合沉淀而形成的,然后膽紅酸鈣通過陰離子糖蛋白聚集成結石[20]。腸屏障是腸道結構和功能的總稱,它能阻止細菌和毒素等有害物質通過腸黏膜進入人體的組織、器官和血液循環,其功能障礙可能導致細菌易位、內毒素血癥和膽汁β-葡萄糖醛酸酶促進色素性膽結石的形成[21]。大多數色素性結石都與細菌有關,這些細菌可以產生β-葡萄糖醛酸苷酶黏液,其促進色素性結石形成的因素包括β-葡萄糖醛酸酶(bG)、磷脂酶(PhL)和黏液,黏液的產生比β-葡萄糖醛酸酶的產生與結石形成更相關[22]。
3.1 β-葡萄糖醛酸酶與膽色素結石 β-葡萄糖醛酸酶是一種水解酶,其能分解結合膽紅素并將其轉化為葡萄糖醛酸和非結合膽紅素,再與鈣離子結合形成鈣膽紅素結石,該過程歸因于腸道桿菌科細菌(如大腸桿菌和克雷伯菌)、梭菌屬的存在[23]。宿主和環境因素對β-葡萄糖醛酸苷酶活性的影響很大,研究表明一些藥物存在對β-葡萄糖醛酸酶活性的抑制作用,如吲哚的噻二唑衍生物 (1-22)等[24],β-葡萄糖醛酸苷酶在醫療等領域越來越受到重視, 已成為當今研究的熱點,通過抑制β-葡萄糖醛酸酶有望成為管理疾病和藥物治療的新方法。
3.2 細菌產生黏液和磷脂酶 大多數細菌會產生黏液,黏液是一種由細菌產生的陰離子糖蛋白,這些黏液可以促進結石形成[20]。體外條件下研究表明在膽結石形成過程中,細菌的黏液活動導致膽結石凝固,而其他活動加速膽結石形成的成核,從而增加疾病的嚴重程度[25]。當存在細菌感染時,膽道磷脂酶活性顯著升高。大部分從膽汁中分離出的菌株都具有磷脂酶 A1 和磷脂酶 A2 活性,由于膽結石中的脂肪酸主要是棕櫚酸,并且必須從膽汁磷脂酰膽堿分子中的第一個位置裂解,由此在棕色色素性結石棕櫚酸鈣的形成過程中細菌磷脂酶 A1可能起重要作用[26]。Ⅱ型磷脂酶 A2 (PLA2-Ⅱ)可能在黏膜炎性反應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進而可能產生原核劑,增加的膽道 PLA2-Ⅱ可能在多種膽固醇結石中具有重要的發病機制,可能是通過加強膽囊黏膜炎性反應以及有利于膽固醇晶體形成的相關膽道改變[27]。
4 腸道菌群對膽囊結石的影響
Liu等[28]研究表明L.christinae (LAE)水提物通過影響腸道菌群來預防模型動物體內膽固醇結石的能力。在致石飲食誘導的雄性C57BL/6J小鼠中LAE 治療后膽固醇結石的形成大大減少。此外,腸道菌群表現出顯著的變化,喂食生石飼料的模型組中,未分類的卟啉單胞菌屬、乳酸桿菌屬和別氏菌屬的豐度降低,而與正常飼料喂養的對照組相比,阿克曼氏菌的豐度顯著增加;LAE的管理扭轉了這些變化[28]。這些結果表明,LAE可以被認為是消除由高脂肪和高膽固醇飲食誘導的膽固醇結石的有效療法,這可以通過影響腸道菌群來實現[28]。此外,使用腸道益生菌可以最大限度地逆轉膽囊結石患者的膽汁成分,從而減少膽結石的形成[29]。
5 菌群參與膽囊結石治療
膽囊結石的中西醫結合治療越來越受到關注,其中腸道菌群在治療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腸道菌群通過調節膽汁酸代謝、抑制膽固醇合成影響膽囊結石的形成,其中腸道菌群可通過調節FXR信號分子影響膽汁酸代謝,因此可通過次級膽汁酸—熊去氧膽酸抑制肝臟膽固醇的合成,有利于結石中膽固醇逐漸溶解[30]。此外短鏈脂肪酸—丁酸可降低血清總膽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含量[31]。褐藻膳食纖維可調節腸道菌群的種類和數量,影響腸道菌群代謝產物,從而改善糖脂代謝紊亂,達到預防膽囊結石的效果[32]。菊粉作為一種膳食纖維,可修復菌群失調導致的膽汁酸含量變化[33]。此外合成微生物群落是有望對微生物群落進行精準調控和改造的人工微生物體系,從而達到治療膽囊結石的效果[34]。王素英等[35]推測具有清熱利濕作用的中藥具有調節腸道菌群失衡的作用,進而影響膽石癥的疾病進程。居永慧等[36]研究表明四妙永湯、大黃、黃連均可促進膽汁酸的生物合成。在動物模型中,發酵刺梨汁可通過活性酵母發酵,調節腸道微生物及其代謝物,改善腸道菌群紊亂,保護腸道屏障,調節豬去氧膽酸、石膽酸、脫氧膽酸等膽汁酸代謝物[37]。
6 小 結
膽囊結石患者越來越多,但對于膽囊結石的具體病因尚不十分清楚,目前對膽囊結石的治療僅僅通過外科手術來完成。研究表明腸道菌群失衡不僅與膽固醇結石相關,還與膽色素結石相關。此外,腸道菌群代謝產物對膽囊結石的影響機制越來越受到重視。這為膽囊結石的治療及預防提供了方向。但膽囊結石與腸道菌群具體機制尚待研究,未來有望通過基因測序和嚴格的臨床試驗來確定腸道菌群與膽囊結石的具體機制,進而通過生物療法代替外科手術對膽囊結石的治療。腸道微生物組組成的改變還可能導致免疫失調,促進慢性炎性反應和腫瘤的發展。腸道微生物及其代謝產物可能通過循環系統遷移到身體其他部位,導致宿主生理狀態失衡,并通過腸—腦軸、腸—肝軸分泌各種神經活性分子,影響特定器官的炎性反應和腫瘤發生。因此,腸道微生物群有望為腫瘤進展提供思路,并可能為惡性腫瘤的發病機制提供新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