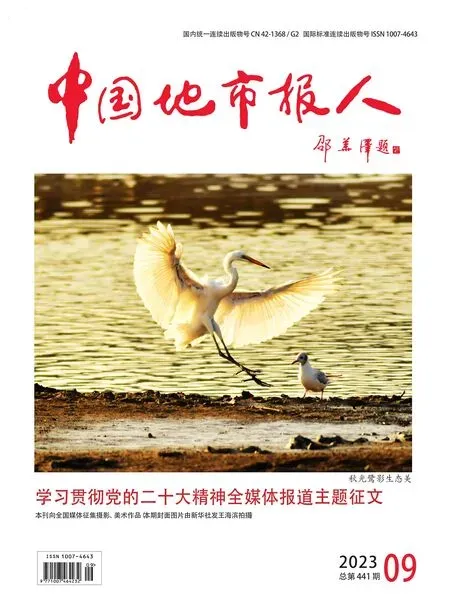傳媒題材影視作品創作熱現象淺析
卓朝興 陳菀鈴
近幾年,以傳媒為題材的影視作品數量逐年增加并呈現創作熱潮。傳媒題材影視作品創作熱的產生無疑是一種積極現象,這種現象背后的原因、發展現狀以及未來發展方向都值得我們探討深思。
一、創作熱的產生原因背景
(一)政策支持。任何作品的創作都與時代背景息息相關,官方政策的支持是催生一個行業、一類作品熱潮的重要條件之一。首先,在媒體建設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高度重視新聞輿論工作,作出重大決策部署。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加強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塑造主流輿論新格局。2022年8月中辦國辦印發的《“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中,提出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輿論導向和價值取向,構建網上網下一體、內宣外宣聯動的主流輿論格局,不斷增強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建立以內容建設為根本、先進技術為支撐、創新管理為保障的全媒體傳播體系。其次,在廣播電視內容建設方面,國家也頒布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例如2022年2月發布的《“十四五”中國電視劇發展規劃》詳盡地針對電視劇內容的選題規劃和創作指導作出指示,并推出電視劇創作生產全流程質量管理體系、綜合評價體系等多維度的內容衡量機制,為建設文化強國進一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兩大行業齊頭并進為傳媒主題的影視作品創作提供了良好的時代背景與生長土壤,緊跟政策必然能切中時代熱點。因此,傳媒與廣電兩大行業的雙支持催生了國內傳媒主題影視作品的創作熱。
(二)社會發展。近幾年在國內逐漸熱門起來的傳媒題材影視作品其實在國際上早有悠久的創作淵源,自20世紀起國際上(尤其是發達國家)便不乏以傳媒為題材進行創作的影視作品,并且此類作品在國外已經成熟。如1952年奧斯卡最佳編劇獎《倒扣的王牌》(美國)、2001年提名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的《戰地攝影師》(德國)、2006年的《頂級播音員》(日本)、2008年韓劇史上首部真實展現記者生活的傳媒專業題材電視劇《聚光燈》。國內傳媒題材影視作品創作的開頭應從21世紀初開始追溯,在中國改革開放初顯成效、加入WTO等一系列與國際接軌的時代背景下,同時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國家對媒體的日益重視、國內媒體自身的發展更新,國內同類型題材的影視創作蓬勃興起。
(三)題材的可塑性。傳媒自身的廣泛性為以傳媒為題材進行創作的影視作品帶來了創作的無限可能,也可稱此性質為可塑性,即傳媒題材可單獨成為主題,也可以多種形式融入各種大主題中。
目前中國的傳媒主題影視作品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傳媒工作者為主角、傳媒工作為主線劇情,通過刻畫主人公在工作時遇到的種種情況來揭露傳媒業內幕或歌頌傳媒業。例如由賈樟柯導演的電影《不止不休》,講述了主人公懷揣記者夢想進入報社,追蹤探訪非法賣血產業,意外發現了乙肝患者代檢這條灰色產業鏈,最終發出報道《一億人的反歧視主張》引發全社會的熱烈反響,間接促進了國家取消乙肝五項測試納入就業、入學的規定,體現調查記者與深度報道的力量之大。另一類則是以愛情、親情等其他類型劇情為主線,將主人公的職業設定為傳媒工作者,在劇情的發展中穿插與傳媒相關的題材。例如豆瓣9.5分的臺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以喪親、尋求真相與救贖為主線,將幾位主人公設定為新聞工作者,同時穿插大量新聞傳媒行業中的日常工作片段來折射“新聞倫理”這個次主題。
影視作品可利用傳媒題材來展現傳媒行業自身,也可借用傳媒題材來輔助展現其他主題。傳媒題材在影視作品創作中具有靈活的可塑性,這也是國內傳媒題材影視作品能夠出現創作熱的原因之一。
(四)媒介問題引起的社會反思。全媒體時代,除了權威的傳統媒體,近年來自媒體崛起并成為一大傳播主力。自媒體因不受官方機構審查監管,通常可發布更具娛樂屬性的傳播內容,這也為自媒體帶來了巨大的流量。但正因為不受監管、追求流量,自媒體成為制造流言的推手,導致整個媒體行業亂象叢生,產生諸多媒介問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問題便是網絡暴力。許多理性的受眾也逐漸平靜下來,去正視與反思這場“狂歡”遺留給社會的問題。受眾的重視加上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足以讓“傳媒”成為影視作品創作的新熱題材。
二、中國傳媒題材影視作品的現狀
(一)相關影視作品尚未達到預期的收視(票房)效果。在新媒體流行與傳統媒體迅速轉型的時代背景下,我國的傳媒產業日益壯大,傳播矩陣越發健全,但傳媒題材影視作品的發展程度卻不能與之匹配。不少傳媒題材影視作品不顧故事邏輯、沒有把握好劇情節奏、生搬硬套傳媒題材、違背現實事實,這樣的作品無法收獲良好口碑,自然也無法收獲理想的票房與收視率。近幾年來,以傳媒為主題創作的國產電視劇《浪淘沙》《巨浪》《突圍》都未能引起關注,收視率慘淡;豆瓣評分高達9.5的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也只在臺灣獲得了較好的收視率,在內地的傳播與收視效果平淡;據專業影視數據APP“燈塔”統計,2023年初在大陸上映的《不止不休》最終也只以5647.5萬元票房收場。
(二)相關作品的創作、市場、觀眾仍處于生長期。與國外傳媒題材影視作品創作相比,當前國內相關作品的創作仍處于待成熟階段。從歷史上來看,國外早在20世紀便生產了不少以傳媒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如《公民凱恩》(1941)、《總統班底》(1976)、《怪胎記者》(1980)、《驚爆內幕》(1999)。而國內直至21世紀初才逐漸生產關于傳媒話題的影視作品,如黃秋生與陳冠希主演的《A1頭條》(2004)、陳凱歌導演的以人肉搜索和網絡暴力為主題的《搜索》(2012)、對“流量至上”進行探討的《導火新聞線》(2016)。對比成片質量方面,近10年國外有獲得最佳影片的《聚焦》、查理茲·塞隆三提奧斯卡的《爆炸新聞》、入圍戛納主競賽的《法蘭西》、新晉戛納影后的《圣蛛》等。反觀國內傳媒題材影視作品,其地位仍處于初入影視市場的階段,傳媒題材影視作品在與紅色愛國主旋律、青春偶像、科幻科技等大熱題材影視作品競爭時仍顯無力,該類作品的觀眾群體仍然算不上“大眾”,達到預期收視(票房)效果依舊是其當務之急,保證質量、獲獎與否等目標需在解決上述痛點后才有余力實現。
三、關于傳媒題材影視作品創作及發展方向的建議
(一)遵循國內主流價值觀。中國本土作者在進行傳媒題材影視作品創作時應根植于本國文化土壤,遵循國內的主流價值觀,切不可盲目照抄國外優秀作品,畢竟國內外的價值觀存在差異,若不“因地制宜”則易“水土不服”。美國好萊塢夢工廠生產的影視作品多帶有“美國夢”“霸權主義”等意識形態,與此類比,國內在創作傳媒題材影視作品時,可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意識形態融入影視作品中。提及傳媒題材影視作品的創作觀念,就不可不涉及國家新聞觀,外國傳媒題材影片體現的是自由新聞主義,而國內在該類作品上則應體現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無論是傳媒題材還是其他題材的影視作品,把握正確的主流價值觀是往正確方向發展的第一要務。
(二)具有時代內核與思想高度。目前國內的傳媒題材影視作品劇情多呈現“懷著新聞理想—現實受挫—實現理想”的俗套化設定;而在人物設定方面,國產傳媒題材影視作品多將新聞工作者簡單設定為“理想主義者”或“不義”的角色。前者以電影《不止不休》為例便可印證;后者在新近的多部影視作品中都可得到印證,例如,在《歡樂頌》里,記者是堵在安迪家樓下的角色;在《開端》里,記者是刺激原本善良的人民教師“鍋姨”成為公交車爆炸案犯罪嫌疑人的角色。這些俗套的設定將原本能夠用來反映傳媒行業內核、折射時代重大新聞事件的傳媒題材變成了對真實傳媒行業的抹黑。
傳媒題材影視作品創作的出路定然不止于此,國內在進行相關作品的創作時可以借鑒國外經典作品的思路,例如英國1984年出品的《殺戮之地》則通過戰地記者主人公的視角去展現“‘紅色高棉’血洗柬埔寨”這一段沉重的歷史;又如提名第70屆金球獎電視類最佳劇情類劇集的《新聞編輯室》在第二季和第三季中通過新聞機構的視角呈現了“9·11事件”“占領華爾街運動”“美國2012年總統大選”“利比亞戰爭”“班加西事件”等值得探討的歷史與政治議題。從劇情和人物設定來看,仍有不少國產傳媒題材影視作品落入俗套化的境地。要想讓作品真正發揮傳媒題材的優勢與亮點,必然不可落于俗套,而應精心選擇、構思題材,跳脫出愛情劇、家庭倫理劇、職場劇的老舊范疇,呈現真實的新聞傳媒行業,展現媒體維系社會共識和平衡輿論、甚至推動社會某方面改革的特效,讓本身就與社會、歷史息息相關的傳媒題材發揮反映時代與社會議題、針砭時弊的效果。
結語:
近年來國內傳媒題材影視作品的生產數量逐年增多,傳媒元素也被越來越多運用在其他類型影視作品中,新聞工作者角色在國產影視作品中更是頻頻出場。國內也涌現了諸如《我們與惡的距離》《女不強大天不容》《不止不休》等口碑較好的傳媒題材影視作品。在中國愈發繁榮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環境以及相關行業和政策的支持下,傳媒題材影視作品的創作熱應運而生。在政策保障、行業引導、受眾關注、專業人士創作等多方因素的綜合孕育下,傳媒題材影視作品的創作趨勢正穩中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