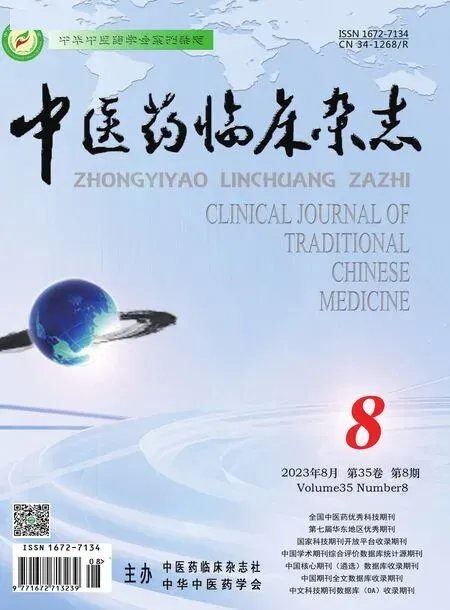淺談針灸對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的調治*
劉姍姍,陳星良,呂小鋒,夏興秀,周浩,王超
1 成都中醫藥大學 四川成都 610075
2 四川省中西醫結合醫院 四川成都 610041
亞健康狀態是處于健康與疾病之間的中間狀態,表現為特定時期的活動能力降低、適應能力下降等表現,通常不能滿足現代醫學對于慢性病的診斷及亞臨床診療要求[1]。世界衛生組織(WHO)2016年調查示全球亞健康狀態人數已超60億,占全球總人口的85%左右,我國報告指出,國內亞健康狀態人數占比雖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卻也達總人數的70%[2]由于亞健康狀態對一個國家的民眾生活健康安全將產生巨大危害,故防止由亞健康狀態向慢性病態的傳變,進行亞健康狀態調治也成為了當今健康中國行動的重要內容。
研究顯示,亞健康狀態以虛證為主,包括肝郁脾虛、心腎不交、腎陽不足、氣虛和腎陰虛五大證型[3]。綜合可見肝郁脾虛型亞健康人群占比最大[4-7],超過50%,且女性發病率高。目前對于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的調治有著多種治療方案:現代醫學常運用能量合劑改善器官功能,維生素調節物質代謝及維持人體正常生理功能,物理因子療法調節生理功能,抗焦慮類止痛藥等對癥處理;傳統醫學則常運用口服中藥、針灸推拿、傳統養生功法、五行音樂等方法進行治未病即未病先防。作為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針灸簡便效速、不良反應少等特點在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的干預中發揮著重大作用。本文就針灸對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的調治進行簡要論述。
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的臨床表現
中華中醫藥學會在2006年頒布的《亞健康中醫臨床指南》示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主要表現為疲勞、急躁易怒、喜太息、情志抑郁、食后胃脹等5大癥狀[8]。具體表現為:第一頭面軀干方面:神疲乏力,周身倦怠,四肢困重,也可見頭痛、頭暈、面色萎黃、痤瘡等,有的咽部異物感,兩脅竄痛且疲勞或遇怒加重等。第二消化功能方面:常見噯氣吞酸,食欲不振,口中甜膩或口干口苦等,脘腹脹滿痞悶,排便不暢,大便秘結或便質稀溏,亦可見腹痛欲泄,泄后痛減等情況;第三精神情志方面:精神緊張、情緒低落,或易怒,或情志低落、抑郁、焦慮不安、睡眠質量下降等;第四表現在社會適應能力方面:反應遲鈍,社交能力下降。此外女子以肝為先天,肝郁脾虛對女性影響尤為顯著,表現為白帶增多及月經周期、色、量、質的異常。
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的中醫病因病機
臟腑經絡失和,氣血陰陽失調是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基本病機。《丹溪心法·六郁》曰:“氣血沖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諸病生焉”。肝主疏泄是肝臟最核心的功能,氣機調暢可促進情志調暢、血液運行、排泄膽汁、疏利三焦水道、脾胃運化等。肝氣疏泄正常是脾胃正常升降的前提,只有肝氣條達,氣血運行通暢,才能使臟腑功能協調,機體陰陽平衡。
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以情志不暢、起居無常、勞逸失度、飲食不節等為主要病因[9-10]。
情志不暢。現代社會信息量快速膨脹,社會責任與家庭責任并重,人們工作強度高,精神壓力大,相當一部分人因此而情志不暢。《素問·舉痛論篇》云:“百病生于氣也,怒則氣上……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又曰“土疏泄,蒼氣達,陽和布化,陰氣乃隨,生氣淳化,萬物以榮”。可見“百病皆生于氣”“諸郁源于肝”,情志不遂易造成氣機升降失衡,若肝氣疏泄不及則肝氣郁結不解而抑郁,焦慮不安,若肝氣疏泄太過致肝氣上逆又會導致情志亢奮或精神渙散。“太過”與“不及”皆使七情不調而“病”從中生,肝木乘土,影響后天之氣,脾胃氣虛致氣不布津、木不疏土。
起居無常。隨著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相當一部分人主動或被動熬夜。《素問·五藏生成篇》云:“人臥則血歸于肝”。經常勞神熬夜之人耗氣傷血,人體氣血虧虛,肝失濡養,陰陽失調,氣血紊亂,出現全身乏力、困倦、睡眠質量下降等表現。
勞逸失度。《素問·宣明五氣篇》云:“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脾主肉”,現代部分學生、公司員工長時間學習、工作而久坐、久視,體力及腦力過度消耗而損傷元氣;另也有部分人長時間臥床,睡覺、看電視等,因長期缺乏運動引起脾氣失運、氣血瘀滯,致四肢困重、頭痛、頭暈等。
飲食不節。人們工作應酬,疲于奔波,常不知饑飽。《素問·痹論篇》云:“飲食自倍,腸胃乃傷”。五味入五臟,現代人愛食肥甘厚膩,冷飲甜食等滋膩傷脾之物,正如《素問·奇病論篇第四十七》云:“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若出現飲食偏嗜易破壞膳食結構可致機體陰陽失調;而若飲食攝入過少又將引起后天不足,臟腑失于濡養,臟腑機能偏盛偏衰,出現一些消化道癥狀。
針灸調治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的作用機理
古人將治療亞健康狀態稱為“治未病”,而運用針灸來調治未病的方法被稱為“逆針灸”,即在機體無病或發病之前便選用針灸療法以激發經氣,調理身體。正如《靈樞·根結》所言:“用針之要,在于知調陰與陽”。臟腑氣血功能紊亂是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發生的病理基礎,針灸治以疏肝解郁、健脾和胃、疏通經絡和協調陰陽。經絡是機體在生理和病理情況下臟腑組織相互聯系溝通的途徑。楊永清等[11]認為“針灸的調節作用具有多環節和多靶向的特點”:針灸信息經外周神經傳送到中樞神經后,調控內分泌系統及免疫功能,形成神經—內分泌—免疫調節網絡。因患者體質不同,通過中醫辨證論治,施以不同針灸治療方法,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協調陰陽,達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的目標。
針灸對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的調節作用
1 針刺對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的調節作用
針刺是通過選用不同針具,作用于不同穴位,施以不同補瀉手法,來激發人體的正氣,調和經絡氣血,達到臟腑經絡、氣血陰陽平衡的效果,提高機體免疫功能。對于肝郁脾虛型亞健康,常選用肝經、脾經、胃經、膀胱經、任脈及督脈進行針刺治療[12]。姜英[13]等對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受試人群行針刺調理,將雙內關、水溝、百會、雙三陰交、四神聰選作主穴,另配以雙太陽、雙太沖、雙陰陵泉,得氣后留針 30min,1次/d,治療15d后間隔7d,此為1個療程,治療3個療程后發現總有效達率96.6%,受試者主訴癥狀及精神狀態明顯好轉。研究者[14-15]發現肝俞“龍虎交戰”針法可以較大程度地改善亞健康失眠患者的睡眠質量和效率及肝郁氣滯癥狀,并且對亞健康失眠遠期療效顯著,復發率低,不良反應小。陳婷[16]發現電針結合重復經顱磁刺激治療肝郁型亞健康失眠療效顯著。此外韋光等[17]把120例肝郁脾虛亞健康青年患者隨機分為兩組,對照組選以針刺百會穴、雙足三里、雙三陰交等,每次留針30min/次,隔日1次;治療組予以推拿聯合針刺方法,發現臨床治愈率治療組優于對照組(P<0.05)。可見針刺方法能安神養心、健脾和胃、補中益氣、疏通臟腑精氣,能有效改善各項肝郁脾虛慢性疲勞綜合征倦怠、身重、四肢勞倦、急躁易怒、恐懼焦慮等癥狀,療效佳且無不良反應。
2 穴位埋線對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的調節作用
穴位埋線是把經絡理論和物理治療相結合后形成的一種現代治療方法,與普通針刺相比,其不僅能在操作時產生即刻效應,更能在機體吸收羊腸線時產生變態反應及化學刺激效應達到長效的效果[18]。冷安明等[19]將140例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患者分為兩組,對照組進行心理疏導治療,治療組除了心理疏導治療外,還選用雙肝俞穴、脾俞穴、腎俞穴、心俞穴、足三里穴、太沖穴等進行埋線治療,最終發現治療組治療效果更優,患者生活質量更佳。同樣陳君[20]對36例肝郁脾虛型亞健康態患者在中脘穴、雙肝俞穴、脾俞穴、足三里穴處行埋線以補益脾胃、疏肝解郁,結果治療有效率為94.4%。可見穴位注射不需行針,操作時間短,簡便易行,作用時間長,并能有效改善患者生活質量,可臨床推廣。
3 耳穴對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的調節作用
根據《中醫治未病指南》,有研究人員[21]對不同體質患者進行了標準化耳穴治療的回顧性研究,最終發現標準化耳穴療法對肝郁氣滯有效率最高,達92.31%。何亞玲[22]認為耳穴撳針能夠有效改善氣郁質亞健康態失眠,且遠期療效佳,且在改善入睡時間、睡眠時間、日間功能等方面,比普通針刺更具優勢,值得在臨床上進一步推廣。蔡黎等[23]研究發現耳穴壓豆法能夠較好地緩解亞健康診斷中如胸部漲滿不適、腹脹、疼痛等氣郁的癥狀,肺功能有所改善,確有療效,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
4 罐法對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的調節作用
罐法是依靠罐內外壓力差將罐吸附在皮膚表面,使局部毛細血管充血,并使機體產生一種組胺和類組胺物質,刺激機體器官,增強機體功能活動;還可加深呼吸,促進胃腸蠕動,改善消化功能;并可加速血液回流,調節微循環,淋巴液循環,提高免疫功能;可直接殺死病原體或修復損傷或病變組織,通過對機體的整體調節,提高體內免疫力等多個系統的功能[24]。姜英[13]等發現對肝郁脾虛型患者在膈俞至膽俞雙側用閃火法拔罐進行緩推,即留罐后作短距離單向移動后,稍加力快速取下,反復操作致皮膚紅潤,配合針刺,隔日進行一次,治療7次后休息7d,此為一個療程,治療三個療程后軀體化、抑郁焦慮等因子分多明顯下降(P<0.05或P<0.01)。宋守江[25]選取亞健康狀態患者36例,經過背部督脈走罐、陽性反應部位及臟腑對應腧穴刺絡拔罐后發現疲勞及其他伴隨體征明顯緩解,甚至消失,總有效率達94.4%。罐法對人體免疫機能產生了雙向調節效果,能增強機體的免疫機能,調治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軀體化、抑郁、不安的表現,從而改善了人體亞健康狀況。
5 中藥臍貼對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的調節
中藥臍貼是將藥物貼敷貼于神闕處,因臍孔肌膚角質層較薄,屏障功能弱,促進了機體對藥品的直接吸收,從而減少了藥品對消化系統的影響和肝臟代謝過程對藥品成份的損害,也可使藥品更佳地發揮效果。歐洋等[26]將80例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患者分為兩組,對照組予以逍遙丸,治療組予以逍遙丸合中藥臍貼,治療2月后發現治療組量表評分較對照組低,且中醫證候改善明顯,可見逍遙丸聯合中藥臍貼后疏肝解郁養血調理亞健康狀態的效果更佳。鐘堅娥等[27]將100例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人群施以臍療聯合耳穴壓丸治療,結果治療后患者的癥狀明顯緩解。趙娜等[28]將68例患者隨機分為2組,治療組睡前半小時在神闕等處予安眠貼,對照組在相應位置貼敷安慰貼,治療40d,隨訪半年后發現,治療組總有效率為72.7%,對比對照組9.4%可見治療組睡眠改善情況明顯優于對照組。中藥臍貼能有效調節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失眠、抑郁、不安等表現,改善臨床癥狀,提高生活質量,對保健意義重大。
6 艾灸對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的調節
灸法治療適用于[29]經絡不通、氣血不暢之寒、熱、虛、實諸證,通補互用,常用于陽虛型亞健康狀態的調節,以溫促通、以溫達補、以通促補,主要作用部位是皮部、絡脈。艾灸溫通溫補效應的作用機制[30]為艾灸激活穴位以推動氣血運行達到調節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臟腑功能的作用。對于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的治療常用于脾胃不適,如腸應激綜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等。肖靚宜等[31]采用通過糾正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中樞相關受體及激素的異常表達,抑制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功能亢進,改善胃腸動力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李奎武等[32]發現懸灸“天樞”“上巨虛”可降低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大鼠內臟高敏感性,改善其腹痛、腹瀉等癥狀,改善其免疫功能狀態。邱菊等[33]基于“調氣法”針刺結合艾炷灸雙側心俞、肝俞、脾俞能有效改善肝郁脾虛型原發性失眠患者的中醫證候、睡眠及生活質量。
討 論
對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的研究,已有許多學者涉及,并取得的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針灸可能通過調控多方面中樞機制,調節神經內分泌系統,包括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和應激激素、單胺類神經遞質和阿片肽[34];影響腸道菌群多樣性與數量[35],改善腸道屏障功能,調控腦腸肽實現抗疲勞作用;通過降低丙二醛、上調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活性來提高抗氧化應激能力[36]等改善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患者臨床癥狀。在進行相關研究時可使用多模態神經影像技術對肝郁脾虛型患者進行分析,并從結構、功能、代謝等多角度,相互印證針灸治療慢性疲勞綜合征的中樞機制。總之針刺具有全面調節的優勢,且安全、方便、無毒副作用,值得更廣泛的臨床應用。針灸治療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療效確切,然而當前針灸治療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的臨床研究也存在不少問題。
首先,對于亞健康狀態的概念至今仍未統一,缺乏國內、國際統一的診斷標準,傳統的癥狀標準檢測和量表評估有一定局限性,實驗室指標可以更加精準客觀地反映人體內在變化,最大限度地消除人為因素的影響,能夠更早、更全面得認識亞健康,精準把握亞健康狀態,識別并干預亞健康狀態。目前尚有大量學者在進行亞健康狀態的現代醫學相關研究,但因其涉及自主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消化系統、免疫系統等多系統臨床表現,所以也需要從多層次、多角度來詮釋其臨床變化的物質基礎。
其次,筆者查閱相關文獻后發現目前大量文獻只著眼于對不同針灸療法治療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進行療效分析,但何時為恰當的干預時間未曾提及,是否一定要盡早干預?過早地干預是否會影響機體自身的自我調節功能?此外,當前大多數研究僅關注臨床療效觀察,較少對針灸具體作用機制進行闡述和研究,這無疑降低了相關文獻的科學性。
再者,鮮有文獻提及針灸治療肝郁脾虛型亞健康后的跟蹤和隨訪,或隨訪時間短,極少報道患者治療后的生活質量及不良反應。針對當前針灸治療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的作用機制仍未完全明確的前提下,干預治療后的跟蹤和隨訪則顯得尤為重要,遠期療效有利于進一步論證針灸的作用機制,有利于進一步深入探索最佳的治療方案和聯合治療策略,其可為推動針灸的臨床應用提供更可靠的證據。
最后,針灸是中醫治療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的一種重要手段,而各家針灸手法各異,對補瀉方法、刺激量、刺激頻率仍缺乏統一的量化標準。一直以來針灸便具有“簡便驗廉”的優點,現在其效廉、經濟、安全等優點在調治亞健康狀態上仍具有獨特的優勢,但對于當代青年人,其“簡便性”已褪去不少,筆者在臨床實踐中感受現有不少人不能接受針刺之“痛”,艾灸之“氣”,拔罐之“印”,如何讓更多人接受針灸治療也是我們這一輩針灸人的使命,我們應不斷發掘針灸在調治肝郁脾虛型亞健康狀態方面的潛在優勢和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