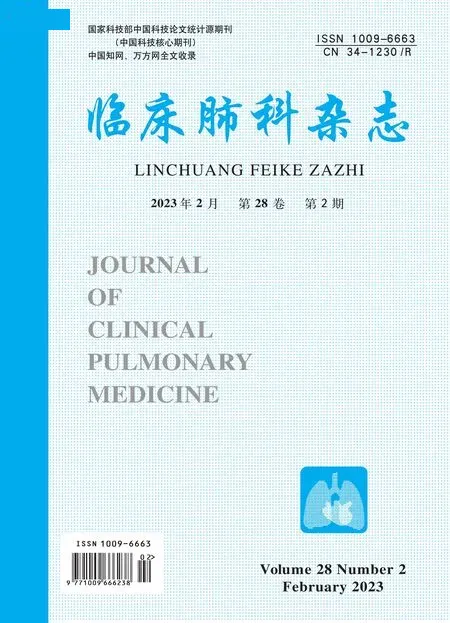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與腸道菌群的研究進展
宋佩佩 岳紅梅,2 劉南玉 魏繼芳 王嘉琪 謝瑩瑩 魏雅倩
由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引起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已引起全球關注,最常見的癥狀是發燒和咳嗽,幾項研究報告稱,受感染的患者患有胃腸道癥狀。人體腸道被大量微生物定植,包括數萬億種細菌,這些細菌統稱為腸道微生物群。現有數據結果顯示有相當比例的COVID-19患者存在腸道微生物群失調問題并在病毒清除后持續存在,因此,腸道微生物與SARS-CoV-2病毒感染之間可能存在密切關系。本文綜述了評估COVID-19患者與健康個體相比的腸道微生物群的組成,可能具有作為該疾病的診斷和/或預后生物標志物的潛在價值,通過飲食、益生菌干預調整腸道菌群作為COVID-19的潛在治療靶點。
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胃腸道癥狀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由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感染引起,其臨床表現大多為非特異性癥狀[1],最常見的癥狀是發燒和呼吸道癥狀,但許多患者也會出現胃腸道(GI)癥狀,包括腹瀉、惡心、嘔吐和腹痛[2-3]。Pan[2]等首先把胃腸道癥狀與新冠肺炎聯系起來,該研究分析了三家醫院收治的204例新冠肺炎患者的臨床資料,高達50.5%患者有消化系統癥狀,排除食欲不振,則總共18.6%的患者出現胃腸道特異性癥狀,同樣最近的一項薈萃分析報告稱,20%的患者有胃腸道癥狀[3]。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持SARS-CoV-2感染中的胃腸道病毒感染。
雖然肺部感染的機制已被廣泛研究,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SARS-CoV-2為何以及如何誘發胃腸道癥狀。血管緊張素轉換酶2(ACE2)受體是一種已知的進入宿主細胞的SARS-CoV-2受體[4]。ACE2廣泛表達于肺、腸、心臟、血管內皮細胞、腎臟和肝臟的纖毛、杯狀和產生表面活性物質的2型肺泡細胞。SARS-CoV-2病毒的成功進入不僅取決于細胞受體ACE2的存在,其入侵過程尚需通過黏膜特異性Ⅱ型跨膜絲氨酸蛋白酶(TMPRSS2)的介導,它介導了SARS-COV-2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與細胞的融合,促進了病毒的感染,這兩者對于病毒和細胞膜的融合至關重要[5-6]。ACE2和TMPRSS2不僅在肺組織中表達,而且在胃腸道上皮,特別是小腸和結腸中高表達,因此有利于SARS-CoV-2的感染[7]。從糞便標本分離的小腸上皮細胞中檢測到SARS-CoV-2病毒的活躍復制[8],且可在患者的糞便樣本中檢測到[9-10]。此外Lu[11]等人的研究中,對受試者進行了內窺鏡檢查,可以在不同的胃腸道位置檢測到SARS-CoV-2。以上證據說明胃腸道癥狀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腸道上皮細胞的直接感染,且在腸道上皮細胞中病毒的高度復制,所以SARS-CoV-2在胃腸系統的作用導致惡心、嘔吐、腹瀉和腹痛的發生增加。
胃腸道癥狀的潛在機制可能涉及腸道黏膜屏障的損傷并促進炎癥因子的產生,胃腸道癥狀伴隨著炎癥或腸道損傷,腸道屏障完整性喪失,腸道微生物可以激活先天和適應性免疫細胞,把促炎細胞因子釋放到循環系統,導致全身炎癥。這些炎癥介質促進中性粒細胞、巨噬細胞和T細胞進入腸道黏膜,導致腸道炎癥,可能導致腹瀉和其他胃腸道癥狀[12-13]。此外新冠肺炎有腹瀉癥狀且血清白介素6水平升高的患者顯示出較高的鈣衛蛋白濃度[14-15],鈣衛蛋白(一種主要由中性粒細胞表達的標志性蛋白)是炎癥性腸病的臨床生物標志物,具有免疫調節功能,在新冠肺炎相關性腹瀉的診斷,特別是隨訪中可能起到潛在的監測作用[12]。
二、腸道菌群與COVID-19
人體腸道中含有數以萬億計的微生物,統稱為腸道微生物群,與機體免疫穩態調控密切相關[16-17],已經報道了不同肺部疾病中的腸道微生物群變化[18-19]。Zuo[20]等人用霰彈槍宏基因組測序報告了COVID-19患者腸道微生物群的改變,提示以肺損害為主的新冠肺炎也可導致腸道微生態失調,研究顯示住院期間COVID-19病例的糞便微生物組發生了顯著變化,其特征在于機會致病菌富集(包括哈氏梭狀芽胞桿菌Clostridium hathewayi、諾氏擬桿菌Bacteroides nordii、粘液放線菌Actinomyces viscosus)和有益共生菌減少(包括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毛螺菌屬Lachnospiraceae bacterium 5_1_63FAA、真桿菌屬Eubacterium rectale和卵瘤胃球菌Ruminococcus obeum)。在另一項研究中比較了新冠肺炎患者、甲型H1N1流感患者和健康對照組,以了解腸道微生物群的變化,研究中也觀察到了相同的結果[21]。在此基礎上Sencio[22]等人在COVID-19敘利亞倉鼠實驗模型中發現,SARS-CoV-2感染導致腸道微生物區系有害細菌分類群(如腸桿菌科Enterobacteriaceae和脫硫弧菌科Desulfovibrionaceae)的相對豐度較高,SCFA生產者(瘤胃球菌科Ruminococcaceae和毛螺菌科Lachnospiraceae)的相對豐度降低,血液中SCFA的濃度降低。以上表明,與對照組相比,COVID-19患者腸道生態失調伴致病菌富集和有益共生體耗盡。而且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腸道生態失調與COVID-19感染的嚴重程度有關,并在病毒清除后持續存在。因此腸道微生物群的組成可能具有作為該疾病的診斷和/或預后生物標志物的潛在價值,通過飲食、益生菌干預調整腸道菌群可以作為COVID-19的潛在治療方法。
(一)腸道菌群失調與COVID-19嚴重程度
如前所述,COVID-19患者的腸道微生物群組成發生了變化,據報道,微生物組成的改變與新冠肺炎疾病的嚴重程度和對疾病的炎癥反應有關。Zuo[20]等人發現,來自厚壁菌門的糞芽孢菌屬Coprobacillus、多枝梭菌Clostridium ramosum、哈氏梭狀芽胞桿菌Clostridium hathewayi與疾病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糞芽孢桿菌已被證明可以強烈上調小鼠腸道中ACE2的結腸表達,而多枝梭菌與哈氏梭狀芽胞桿菌與菌血癥和感染相關,而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是與COVID-19嚴重程度呈負相關的主要細菌,是腸道中短鏈脂肪酸(SCFAs)的主要生產者,由于誘導IL-10的產生而具有抗炎潛力[23]。Yeoh[24]等人進一步強調,腸道微生物區系組成可能參與決定SARS-CoV-2感染嚴重程度的程度,在胃腸道發揮免疫調節作用的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普拉梭菌和 Bifidobacterium bifidum-兩歧乳桿菌與新冠肺炎的嚴重程度呈負相關。Cao[25]等人證明,與輕度至中度病例相比,COVID-19重癥病例產生丁酸鹽的細菌群(包括真菌)幾乎被耗盡,而機會致病菌更豐富,而糞丁酸鹽水平下降與血漿促炎細胞因子IL-10和趨化因子CXCL-10水平升高相關[26]。這突顯了SCFA在新冠肺炎發病機制和疾病嚴重程度中的重要性,補充SCFA或產生SCFA的益生菌可能具有改善疾病結局的潛力。以上發現表明,腸道菌群失調伴致病菌富集和有益共生體耗盡與COVID-19的疾病嚴重程度密切相關,再次強調了維持腸道內穩態對COVID-19預后具有重要意義。
(二)腸道菌群與COVID-19急性期后新冠綜合征(PACS)
雖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已得到緩慢控制,現在又面對另一個問題,COVID-19急性期后新冠綜合征(PACS),其特征是SARS-CoV-2病毒清除4周后至少一個持續性癥狀[27]。據報道,急性新冠肺炎6個月后76%的患者出現了PACS,而入院時腸道微生物區系組成與PACS的發生有關,PACS患者腸道微生物群的特征是較高水平的活潑瘤胃球菌Ruminococcus gnavus、普通擬桿菌Bacteroides vulgatus和較低水平的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產丁酸鹽的細菌,包括假小鏈雙歧桿菌Bifidobacterium pseudocatenulatum和普拉梭菌群與PACS呈最大的負相關[28]。以上研究表明,盡管病毒清除,但COVID-19患者長期菌群失調可能導致持續性癥狀,因此基于腸道微生物組的分析可作為PACS發生的早期風險分層的一種工具。
(三)SARS-CoV-2感染與腸道菌群之間的互相作用
已知SARS-CoV-2可以通過血管緊張素轉換酶2(ACE2)受體入侵人體細胞,在腸道中,ACE2在生理上調節氨基酸運輸,并且與腸道免疫和微生物穩態有關。研究表明[29],小鼠缺乏ACE2會破壞局部色氨酸的穩態,改變腸道微生物組,使動物更容易受到炎癥的影響,導致彌漫性肺泡損傷和腸道中細菌負荷急劇增加,如急性肺損傷。據報道,SARS-CoV-2可以下調ACE2的表達[30],從而進一步限制ACE2的功能,降低了腸道對色氨酸的吸收,導致抗菌肽分泌減少,并改變了腸道微生物的組成。ACE2的減少使其配體血管緊張素Ⅱ和RAS失衡,導致腸道通透性增強和腸漏綜合征[31]。隨著腸道屏障的破壞,細菌和內毒素可以進入體循環,導致細胞因子的過度產生,最終引發內毒素血癥和炎癥。
已知在COVID-19患者中耗盡的普拉梭菌具有免疫調節特性,并有助于宿主防御,包括通過抑制NF-κB途徑[32],誘導IL-10的產生而具有抗炎潛力[23]。此外,有研究發現,普拉梭菌的消耗主要導致COVID-19患者SCFA和L-異亮氨酸生物合成的能力受損,而且持續時間超過30天[21]。單鏈脂肪酸(SCFAs)包括丁酸鹽、丙酸和醋酸鹽,是調節宿主-腸道微生物區系相互作用的關鍵分子。它們在腸道中發揮重要的調節功能,包括在抗菌反應和粘液分泌、腸道通透性和激活黏膜免疫系統方面發揮作用[33-34],它們還可以遠端調節肺部炎癥[35-36]。上述提到COVID-19重癥病例產生丁酸鹽的菌群幾乎耗盡,丁酸鹽可以維持腸道屏障的完整性,防止腸道內毒素和細菌的移位和循環,從而減少全身炎癥反應[31]。而L-異亮氨酸可以誘導宿主防御肽(即β-防御素)的表達,從而調節宿主的先天免疫和獲得性免疫,減輕病原體對人體的不利影響[37]。總的來說,SARS-CoV-2通過ACE2侵入腸道腸細胞,導致腸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謝物的改變以及屏障功能受損,而腸道屏障功能障礙會增加微生物向血液中的移位,細菌易位進入循環,導致全身炎癥加重和多器官受累。這提示加強在COVID-19中耗盡的有益腸道物種或許可以成為減輕嚴重疾病的新途徑,強調在COVID-19期間和之后管理患者腸道菌群的重要性。
三、腸道菌群調節作為COVID-19的潛在治療靶點
鑒于腸道菌群失調與COVID-19嚴重程度以及預后之間的關聯,調節腸道菌群以改變疾病結果的治療潛力是有希望的。
(一)飲食的影響
植物纖維通過促進腸道微生物區系中有益微生物(如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的生長,同時降低有害物種(如梭狀芽胞桿菌)的比例,發揮益生作用[38]。此外,某些細菌對可溶性膳食纖維的發酵產生了幾種有益的代謝物,如SCFAs,它們有助于維持結腸黏膜的完整性并調節免疫系統[39]。膳食纖維對腸道屏障具有保護作用,并可限制細菌易位進入體循環,而高脂肪和高蛋白飲食與黏膜屏障功能障礙有關[40]。一項病例對照研究調查了來自六個國家(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英國、美國)的2884名一線醫護人員(有568例COVID-19病例和2316例對照)的飲食模式與COVID-19之間的關聯,這些醫護人員根據大量接觸COVID-19患者接受了篩查。報告食用植物性飲食或魚素飲食(包括益生元食品)的個體與中度至重度COVID-19的幾率較低有關[41]。但這項研究依賴于主要由男性醫生組成的自我報告人群,而沒有包括受最嚴重COVID-19病例影響的個人,且超過70%的研究參與者是男性,所以有必要有在女性和非健康專業人員中重復這項研究,并提供宏量和微量營養素攝入量的詳細數據,以闡明植物性飲食和魚素飲食與新冠肺炎嚴重程度的關系。
(二)益生菌的影響

四、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COVID-19患者伴發胃腸道癥狀的可能原因是病毒顆粒在腸道感染高度復制,潛在機制可能涉及腸道黏膜屏障的損傷。人體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后腸道菌群多樣性下降,其特征是有益菌群減少,機會性致病菌富集,并與COVID-19嚴重程度與預后相關。高膳食纖維飲食及腸道益生菌制劑有利于促進宿主免疫反應提高,這已成為一個新興的臨床研究視角,必將為COVID-19的治療帶來新的思路。但目前為止已發表的支持在COVID-19中使用益生菌的臨床試驗數據很少,突出的挑戰包括確定最佳菌株,給藥方案和干預持續時間以及選擇適當的臨床和機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