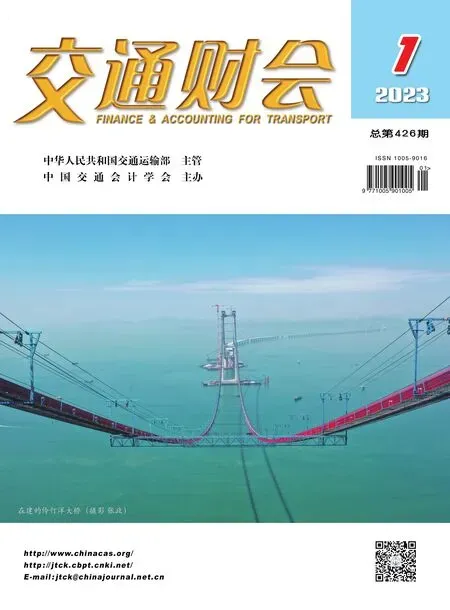關于BOT高速公路建設期收入會計處理的探討
尹崇懿
(蜀道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四川 成都 610095)
一、背景介紹
截至“十三五”末,我國公路通車里程近520萬公里,按照“十四五”綜合立體交通網“6軸7廊8通道”主骨架布局,我國將構建完善以“十縱十橫”綜合運輸大通道為骨干,以綜合交通樞紐為支點,以快速網、干線網、基礎網多層次網絡為依托的綜合交通網絡,到2025年,我國公路通車里程將達到550萬公里。BOT模式作為工程項目投資、建設和經營的主要合作模式之一,在過去為我國高速公路的蓬勃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當前,在交通強國戰略引領下,建設現代化高質量綜合立體交通網絡工作持續大力推進,BOT高速公路模式勢必在未來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研究對象
各BOT高速公路的投資建設運營環節在流程細節上存在各式差異,差異的存在也對其會計處理產生了不同的影響。BOT高速公路的主要模式包括使用者付費的BOT高速公路、政府付費的BOT高速公路和使用者付費與政府補助相結合的BOT高速公路。本文僅選取了BOT高速公路中較為主流的模式,以處于在建期的使用者付費BOT高速公路為研究對象,結合相關文件對BOT高速公路收入的會計處理進行剖析探討。該模式具體流程為:企業通過施工或外包等方式完成高速公路的建設,在完善相關配套工程和必要審批流程后,取得特許經營權,再通過高速公路的運營實現收入和利潤。
三、主要問題
針對該類BOT高速公路,由于各企業對相關規定和業務流程的理解存在差異,導致實際操作過程中主要存在兩種處理方案,方案一分別于在建期和運營期確認收入和成本,方案二僅在運營期確認收入和成本。不同的處理方式將使BOT高速公路企業的收入、成本、成本費用占收入比、成本費用利潤率等關鍵指標產生巨大差異,導致數據失真、誤導決策等嚴重后果,對信息使用者產生不利影響。
以在建BOT高速公路A項目為例,A項目概算總投資87億元,預計建設期3年。該項目的業主公司為A公司,A公司的母公司為B公司。由于A項目無形資產的公允價值無法合理估計,2021年A公司根據工程計量情況,預計建造收入與成本一致,皆為4.53億元。
站在A公司的角度考慮A項目的影響。按方案一,則A公司應于2021年度確認營業收入4.53億元,確認營業成本4.53億元;按方案二,則不應于在建期確認收入和成本,待A項目正式通車運營后,再確認相關財務指標。

表1 2021年A公司財務情況 單位:億元
站在B公司的角度考慮A項目帶來的影響。如按方案一,則B公司應于2021年度確認營業收入90.95億元,確認成本費用77.68億元,成本費用占收入比85.41%,成本費用利潤率29.39%;如按方案二,則B公司應于2021年度確認營業收入86.42億元,確認成本費用73.15億元,成本費用占收入比84.64%,成本費用利潤率31.21%。

表2 2021年B公司財務情況 單位:億元/%
可以看出,兩種方案對相關企業的營業收入、營業成本、成本費用占收入比和成本費用利潤率等指標的計算影響較大。不同的BOT高速公路如果采用不同的方式統計數據,將使相關財務數據不具備可比性,建議對相關會計處理進行統一。針對以上兩種方式,本文將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是BOT高速公路企業是否適用于《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14號》;二是BOT高速公路企業身份的認定;三是BOT高速公路企業履約義務的認定。
四、分析探討
(一)BOT高速公路企業準則適用分析
BOT高速公路業主公司(以下簡稱業主方)在合同約定期間代表政府提供高速公路的建造和運營服務,并在運營期通過收費進行補償,滿足《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14號》中的“雙特征”要求。BOT高速公路的類型、對象在政府招標時已確定,雖然其價格暫未明確,不構成無條件收取現金的權利,但也有交通運輸部門和發展改革委的相關規定作為管控標準,符合“管控”定義,適用于《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14號》第一部分中第4條的無形資產模式。在BOT高速公路特許經營權到期時,企業將按協議進行移交,政府將享有項目資產剩余的經濟利益流入,符合“控制PPP項目資產重大剩余權益”的定義,滿足“雙控制”要求。
根據上述分析,BOT高速公路符合“雙特征”、“雙控制”要求,應根據《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14號》文件,參照《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對收入進行會計處理。
(二)BOT高速公路企業身份判定
按照《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14號》要求,首先應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文件,判斷業主方身份為主要責任人還是代理人。目前,在對業主方的身份進行判定的環節,業界普遍存在一定的爭議。筆者認為,宜將業主方認定為主要責任人而非代理人,應按照總額法確認相關收入,具體分析如下:
1.業主方作為簽約主體。部分BOT高速公路項目由業主方直接參與招投標,在中標后,由業主方與政府相關方簽訂投資協議,對權利義務進行約定。在該情況下,業主方理應作為主要責任人,按總額法對相關收入進行確認。
2.投資方作為簽約主體。部分BOT高速公路項目由交通投資企業作為主體參與招投標,在中標之后,由交通投資企業直接與政府相關方簽訂投資協議,對各方權利義務進行約定。需注意的是,由于該時間節點業主企業可能尚未成立,簽訂投資協議的責任主體是交通投資企業,僅從協議約定來看則應當認定交通投資企業為主要責任人。但根據行業慣例,相關責任及風險在業主公司成立之后則由交通投資企業轉移至業主方。BOT高速公路項目的融資、預算、施工、計量、安全、質量、運營、養護等諸多關鍵方面皆是由業主方負責。因此,根據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宜認定業主公司為主要責任人而非代理人,按照總額法對相關收入進行確認。
(三)BOT高速公路企業單項履約義務判定
按照《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14號》要求,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利用五步法對收入進行確認,其主要爭議點在于單項履約義務的識別。按準則要求,應對合同中的單項履約義務進行識別,將交易價格按照各履約義務單獨售價的相對比例分攤至各項履約義務。在BOT高速公路項目合同的履行中,通常可以識別項目建設和項目運營兩個重要環節,應將兩個環節識別為一個單項履約義務還是兩個單項履約義務還存在一定爭議,具體分析如下:
1.將項目建設和項目運營識別為兩項履約義務。部分企業將項目建設和項目運營視作一個合同中的兩個獨立環節,將項目建設單獨確認為一項履約義務。相關企業在項目建設期根據項目施工進度確認施工收入,在項目運營期根據通行費收取情況確認運營收入。該處理方式將項目建設和項目運營分開,其處理依據主要有以下三點:(1)在項目建成完工后,業主方可從中受益,取得特許經營權;(2)BOT高速公路的建設環節和運營環節存在清晰的時間節點,可進行明確的區分;(3)BOT高速公路按施工履約進度確認收入的方式切實可操作。
2.將項目建設和項目運營識別為一項履約義務。部分企業將項目建設和項目運營視作為達成一個目的所需經歷的兩個緊密相關的環節,將建設和運營確認為一項履約義務。相關企業在建設期不確認收入成本,僅在項目運營期根據項目運營情況確認通行費收入。其處理依據主要有以下四點:(1)BOT高速公路建成完工后并未從政府取得相應對價。BOT高速公路建成完工是業主方取得特許經營權的必要不充分條件,在項目建成后,業主方還需完善機電、綠化等道路相關配套工程,并提供高速公路收費里程表、車輛通行費收費標準等相關資料,履行必要手續流程后通過交通主管部門許可,方可取得收費批文,獲取特許經營權;(2)從本質來講,業主方對高速公路的建設是為了獲取高速公路的經營權,以便從高速公路的運營中獲取收益。因此,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可將建設視作經營的前期鋪墊活動,根據收入準則要求,企業為履行合同而開展的初始活動不構成履約義務,除非該活動向客戶轉讓了承諾的商品。而對于業主方來說,在BOT高速公路的建設階段并未向政府轉讓任何商品,甚至在建成之后也未向政府轉讓相應的商品,需待特許經營權到期時才將相應商品進行移交;(3)根據收入準則要求,如果該商品與其他商品具有高度關聯性,則企業向客戶轉讓該商品的承諾與合同中其他承諾不可單獨區分。BOT高速公路的建設環節和運營環節雖然從客觀上能夠單獨區分,但建設是為了運營,兩者高度關聯,不應單獨區分;(4)在建設期,業主方根據施工進度所確認的特許經營權需通過日常經營才能實現收益,項目建設本身無法為業主方帶來實質收益,如果在建設期和運營期分別確認收入,其實質是對高速公路通行收費業務帶來的收益進行重復確認。
總的來說,兩種處理方式對業主方的利潤不產生實質影響,但對收入、成本等財務指標的影響較大。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履行項目建設義務無法獲取政府相關方的相應對價,且BOT高速公路的建設、運營和移交三個環節緊密關聯、缺一不可,將建設環節單獨作為一個單項履約義務將失去意義,項目的建設和運營是連貫一體的過程,宜將建設和運營識別為一個連貫的單項履約義務而非兩個獨立的單項履約義務。
結語
在交通強國的時代背景下,BOT高速公路在我國基礎設施建設中扮演著愈發重要的角色。本文聚焦會計準則的適用、業主身份的判定和單項履約義務的確認等幾個爭議點,站在業主角度對BOT高速公路企業收入的賬務處理進行了分析和建議。希望相關處理盡快規范,相關問題得到解決,使財務處理合規統一、統計分析準確可靠、相關報告科學有效,打好扎實財務基礎,為交通強國戰略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