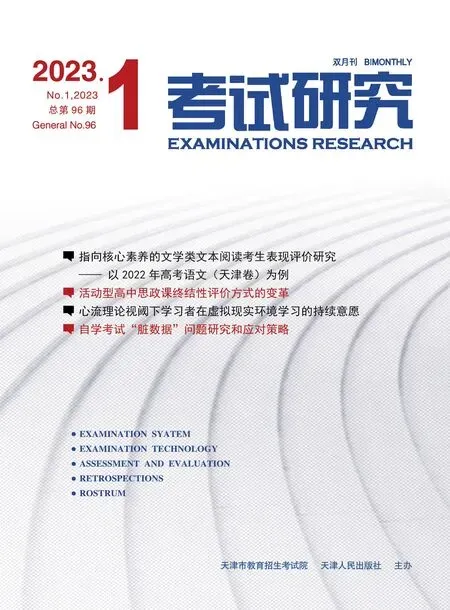自學考試社會助學熱點領域及前沿路徑探析
——基于CiteSpace計量分析
高川
一、引言
當前我國已經開啟了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篇章,踏上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新征程。教育作為重要的民心工程,是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重要內容,具有基礎、先導和全局的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1]。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民群眾提升素質技能的主渠道。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改革轉型是建設現代化教育強國的重要支撐。
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以下簡稱“自考”)是我國法定的基本教育制度,是國家認定的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主要形式,并且要在繼續教育領域發揮檢驗功能[2-3]。社會助學是連接個人自學與國家考試之間的橋梁和紐帶,是自考制度的必然產物和有機組成部分。自考助學的提質增效可以推進自考制度不斷完善發展,進而為促進高等學歷繼續教育高質量發展助力賦能。
自考助學的研究和實踐工作在自考制度建立之初就已經起步,目前已走過近40 年的發展歷程,形成了很多優秀的研究成果。為了全面系統掌握自考助學的研究現狀和發展動態,本文采用CiteSpace.5.8.R3 軟件,對CNKI 收錄的國內學術期刊相關文獻的知識結構進行可視化圖譜分析,旨在揭示自考助學領域的研究脈絡,進而為新時代開展自考助學相關研究提供借鑒與參考。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文獻數據來自中國知網CNKI 數據庫,以主題=“自學考試”AND 篇關摘=“助學”為檢索表達式,將“全部出版年”設定為檢索時間,將“全部期刊”設定為檢索來源。經過精確匹配,共檢索到934 篇期刊文獻,在剔除無效文獻(即無作者、無年份、重復、相關度不高、會議通知、專家訪談等文獻)以后,最終將1986年至2021年發表的612篇相關文獻確定為研究對象。
采用美國德雷塞爾大學計算機與情報學院陳超美博士開發的CiteSpace 可視化分析軟件,對上述經過數據清洗所得到的612 篇CNKI 期刊文獻進行數據分析,包括年發文量統計以及對作者、發文機構、關鍵詞、主題突現詞等的可視化圖譜分析,并以此為依據對自考助學領域的研究現狀、熱點和未來趨勢進行梳理和分析。
三、研究現狀分析
(一)年發文量分析
對特定研究領域的CNKI 學術期刊年度發文進行定量統計分析,對全面分析全國相關工作者和研究者在不同年份的研究總體情況具有重要作用。以年份為橫軸、發文數量為縱軸,利用EXCEL2019 軟件對篩選出的自考助學領域612 篇文獻進行統計與趨勢擬合分析,如圖1 所示。由圖1 可知,自考助學領域在自考制度建立之初(即1986年)就出現了1篇學術論文,說明本領域很早就受到關注。總體上看,在1986年至2015年,涉及自考助學的發文量呈現增長趨勢,2016年至今相關研究成果卻急劇下降,其發展歷程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圖1 自學考試助學領域發文量年度分布
第一階段,1986 年至 1999 年。由于 1983 年“社會助學”概念剛剛被教育部(原國家教委)正式提出[4],故此時的社會助學研究與實踐工作還處在自然狀態,相關研究成果稀少。1995年,自學考試進入高速發展快車道,自考助學市場也隨之進入高度活躍狀態,相關研究成果數量迅速增長。綜合來看,此階段發文總量呈現指數增長態勢。
第二階段,2000 年至2006 年。由于各種辦學主體持續進入自考助學領域,并極力爭奪市場份額,故國家加強了對社會助學工作的指導。教育部(原國家教委)于1995 年印發《關于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社會助學工作的意見》,原國家教委成人教育司分別于1997 年和2000 年印發了《關于加強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社會助學管理工作的通知》和《關于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社會助學工作考核評估意見》。自考助學市場進入了平穩的發展階段,相關研究發文量進入緩慢上升且小有波動的階段。
第三階段,2007 年至2015 年。此階段發文量呈現以2011 年為中心的正態分布走向。分析原因,是由于2010 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出臺導致的。在綱要的起草和醞釀時期,必然會組織專家進行調研考察,這會很大程度激發研究者的研究熱情。在綱要正式發布后,研究者結合綱要精神,也必然會掀起研究熱潮。同時,全國自考委自2011 年開始指導各省建立自考學習服務中心,并于2012 年開始評選全國示范性學習服務中心,這也進一步維持了自考助學的研究熱度。因此,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此階段的研究呈現出圖表中的走勢。
第四階段,2016 年至2021 年。此階段初期,隨著各省自考學習服務中心相繼建立,社會助學工作進入相對平穩時期。然而,此階段后期隨著許多頭部高校退出自考,自考助學市場受到較大打擊,因此近3年的自考助學發文量呈現急劇下降走勢。
(二)期刊發文量統計
對1986 年至2021 年CNKI 學術期刊收錄的涉及自考助學的612 篇學術論文進行匯總統計,可以發現,共265 種學術期刊發表過自考助學的論文。表1對發文量排名Top10 的期刊進行梳理,發文總量為274篇,占全部研究文獻的44.77%。發文Top10的期刊大多數為成人教育、招生考試、繼續教育領域的學術期刊,其中,《中國成人教育》發文量位居首位,共刊發相關文獻63 篇,占全部發文總量的10.29%;《中國考試》發文量位居次席,共刊發相關文獻45 篇,占全部發文總量的6.37%。發文量排名前7 的期刊均發表超過10 篇文章,表明這些期刊都是自考助學領域研究的主陣地。
從表1中還可以看出,發文量排位第1的《中國成人教育》在2008年至2017年入編北大核心期刊,排位第2的《中國考試》在2020年入編北大核心期刊,排位第3 和第8 的《成人教育》和《教育與職業》從2008 年至今一直入編北大核心期刊,排名第4 的《繼續教育研究》在2008年至2017年入編北大核心期刊,排名第9的《現代遠距離教育》在2017年至2020年入編北大核心并且入編CSSCI(2014-2016年版),排名第10的《現代教育管理》從2014年至今一直入編北大核心期刊。此外,福建教育考試院主辦的《教育與考試》、湖北大學主辦的《當代繼續教育》也都是在教育考試領域具有極大影響力的重要學術刊物。這說明,自考助學領域的研究水平和成果質量一直處在較高層次。

表1 自考助學領域發文量Top10的期刊
(三)發文作者分析
對特定研究領域中的高發文量作者進行篩選,并梳理不同作者之間的合作關系網絡,對于定位核心作者及作者群具有重要意義,也是文獻計量研究中的關鍵內容。
普賴斯定律是衡量各個學科領域文獻作者分布規律的重要研究手段,高產作者的計算公式為,其中Nmax為所分析領域的最多發文量作者的發文總數,Nmin的數值是被認定為高產作者的發文量最低標準[5]。根據數據統計,并由公式計算得出Nmin≈1.98,即發文量2 篇及以上的作者將被認定為自考助學研究領域的高產作者。以此為標準,共有100 位作者達到了標準。將這個標準翻倍,可以看出發表4 篇及以上的超高產作者數量驟減為12人。其中江蘇省教育考試院自考處的仲海寧發文量最大,共7 篇文獻,主要涉及自考生學習滿意度、農村自考教育、自考“專接本”、網絡化自考助學、自考素質教育等內容。發文量排在第二名的分別是北京教育考試院的高洪軍、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試院的高川、河南大學遠程與繼續教育學院的李中亮,均發表6 篇文獻,對自考助學體系的理論與實踐工作分別從多角度進行研究探索。
同時,采用 g-index 算法、pathfinder 和 pruning sliced network 裁剪策略,利用CiteSpace 軟件繪制了自考助學領域作者的合作網絡圖譜,如圖2 所示。從圖2 可以看出,在作者合作網絡中主要存在兩個主要的作者群。第一個作者群是來自濰坊醫學院的盧官廬、郭繼志、李星明、莊立輝、王在翔、劉光秀、閻瑞雪,其研究主要涉及護理領域自考助學和網絡助學共3 篇文獻;第二個作者群是來自揚州大學機械工程學院的孫進、陳麗華、龔俊杰、宋愛平、周建華,其研究主要涉及機械專業自考助學共2 篇文獻。由此可見,存在合作關系的作者群都隸屬于同一個研究機構,并且發文量也很少,研究的內容也很微觀,不是自考助學領域的主流研究團隊。其他作者都是相對獨立或者少數人合作的關系。這說明,自考助學的研究者之間還沒有形成跨機構及多學科融合的研究合作態勢,這不利于自考助學工作進一步發展。

圖2 自考助學領域作者合作網絡圖譜
(四)發文機構分析
利用與圖2 相同的CiteSpace 軟件參數設定方案,進一步對發文機構進行可視化圖譜分析,如圖3所示。某一機構在特定研究領域的發文體量直接決定了其在該領域的學術地位與話語權。
目前,在自考助學研究領域發文量較多、影響力較大的機構分為四個梯隊,共涉及13 所研究機構(見圖3 插入表)。第一梯隊包括教育部考試中心、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試院,其發文量分別為8 篇和7篇;第二梯隊包括北京教育考試院、四川師范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其發文量均為5 篇;第三梯隊包括河南大學、秦皇島職業技術學院、山東省教育招生考試院、鹽城師范學院繼續教育學院,其發文量均為4篇;第四梯隊包括四川大學中美大學戰略規劃研究所、哈爾濱建筑大學成教院、江西科技學院、江蘇省教育考試院自學考試處、廈門大學,其發文量均為3篇。從數據可以看出,專業的招生考試管理機構是自考助學領域研究的核心力量,主考學校、助學機構對于本領域的關注度還不高。此外,圖3 中顯示研究機構合作網絡的密度為0,這說明本領域各研究機構的相關工作都是獨立進行的。

圖3 自考助學領域發文機構合作網絡圖譜(插入表為高產發文機構統計)
四、研究熱點分析
(一)高頻關鍵詞分析
文獻中的關鍵詞是作者對自己研究成果的高度精練性概括,是引導其他研究者快速了解文獻精髓要義的鑰匙。聚焦文獻關鍵詞進行系統分析,對于全面展示文獻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向具有重要意義,也是深入揭示研究重點的主要手段[6]。
通過CiteSpace 軟件對關鍵詞進行了統計分析,并經排除檢索詞后,獲得了自考助學領高頻詞的共現圖譜與相關數據統計表(見圖4)。如圖4 所示,“網絡助學”露出的頻次最高,達到37 次;“助學班”的頻次也達到35 次;“普通高校”“高等教育”“對策”這三個關鍵詞頻次也均超過20 次,故上述關鍵詞構成了關鍵詞知識結構圖譜中的關鍵節點。從圖4 插入表的關鍵詞中心性數據可以看出,“助學班”“普通高校”“網絡助學”的中心性排在第一梯隊,分別為0.17、0.16 和0.16,表明這三個關鍵詞在自考助學領域十分重要,是本領域研究歷程中的焦點。此外,“助學模式”“自考生”“高等教育”的中心性數值也都超過0.1,說明這些關鍵詞在本領域也受到相當多的關注。

圖4 自考助學域關鍵詞共現圖譜(插入表為高頻關鍵詞統計)
(二)關鍵詞聚類分析
將特定研究領域中相似程度較高的研究成果劃分為同一類型的研究策略被稱為“聚類分析”,以文獻關鍵詞為特征的聚類分析又被稱為“關鍵詞聚類分析”。關鍵詞聚類分析是CNKI期刊文獻計量的核心方法,可以為研究者迅速掌握本領域的研究動態提供智力支撐。在CiteSpace 軟件的“Node Type”中選擇“Keyword”選項作為節點,并對生成的關鍵詞共現網絡圖譜采用LLR 聚類算法,最終得到自考助學關鍵詞聚類圖譜,如圖5 所示。圖譜中模塊值Q=0.7972>0.3、平均輪廓值S=0.9283>0.5,均達到優質聚類指標要求,表明此聚類操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可以用于進一步分析[7]。
由圖5 中的聚類網絡可知,目前自考助學的研究主題主要分為15 個聚類,分別為#0 助學班、#1 網絡助學、#2 對策、#3 助學模式、#4 高等教育、#5 助學工作、#6 自考生、#7 普通高校、#8 人才培養、#9護理專業、#10 助學服務、#11 中職服務、#13 助學管理、#14 意義、#16 繼續教育。不同聚類間的聯系可知,除了#9 護理專業和#16 繼續教育這兩個聚類具有獨立性之外,其他聚類都處于高度關聯與交叉的狀態。

圖5 自考助學領域關鍵詞聚類圖譜
導出各聚類標簽下包含的標識詞和二次文獻閱讀梳理,得到自考助學聚類主題及標識詞,如表3 所示。從表3 可以看出,目前的聚類可以分為四大主題。其中,“助學基本理論”主題對應#4、#14、#16 三個聚類,反映了研究者對于自考助學基本理論及發展方向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質量監控、運作方略、推向農村、社會助學職業指導、變革與發展問題、拓展建議等;“助學班管理”主題對應#0、#5、#6、#13 四個聚類,反映了研究者對于自考生管理以及各類助學班教學組織的探討和實踐工作,主要包括學生管理、養成教育、定向培養、學籍管理、學習意志、畢業學員、助學管理體系、學習動機、分層教學、學法指導、安全管理、助學平臺、第三課堂、專業選擇、考試通過率等;“助學方式探討”主題對應#1、#2、#3、#10四個聚類,反映了研究者對自考助學模式及方案的研究探索,主要包括網絡助學、農民群體、面授輔導、助學資源、自主學習、現代信息技術、慕課、移動學習、小組模式、互聯網+、模式探析等;“自考與其他教育形式融合”主題對應#7、#8、#9、#11四個聚類,反映研究者構建自學考試與其他教育形式銜接溝通“立交橋”的研究與實踐工作,主要包括普通高校、專業技能、高職高專、人才培養、電力行業、醫療護理、第二學歷、多元合作、中職教育、現狀和發展趨勢等。

表3 關鍵詞聚類圖譜主題及信息詳情表
(三)熱點演進分析
關鍵詞時間線聚類分析是分析不同聚類在同一時間線上研究熱點分布和推進情況的主要手段。利用時間線聚類圖譜可以對同一聚類的成果隨時間演進情況進行分析,分析同一聚類中成果的走勢情況并根據不同聚類之間節點的相互關聯,可以全面系統掌握本領域研究工作的歷史進程和未來發展趨勢。以自考助學關鍵詞聚類圖譜(圖5)為數據基礎,通過選擇“Timeline View”選項生成時間線分布圖譜,如圖6所示。
由圖6 可見,在15 個聚類中,只有#10 助學服務聚類在早期形成(1991 年)并持續輸出至今,其他聚類的研究在2020 年或更早時間就出現停滯現象。雖然#10聚類的研究持續時間較長,但是其研究數量和熱度始終不高。#0 助學班聚類是形成最早的研究聚類,在1986 年就出現了并立即形成了研究熱點,但是在2017年出現研究停滯現象。#1 網絡助學聚類隨著家用電腦的普及而形成,并在2002 年形成自考助學領域最大的關注熱點,其研究持續高強度輸出至2017年。#2 對策聚類也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形成,并在21 世紀初連續形成熱點,并高強度輸出至2018 年。#3、#6、#7 三個聚類均是在形成之時就出現熱點,其余聚類在發展過程中均沒有出現被高度關注的研究熱點。圖6 信息顯示,除#9 護理專業和#16 繼續教育兩個聚類外,其他聚類之間存在著高度關聯關系,這與圖5分析結果一致。

圖6 自考助學領域關鍵詞時間線分布圖譜
五、研究前沿分析
通過對一段特點時間線內各類關鍵詞出現的頻次變化率進行精確計算,并將變化率強度高的對應關鍵詞明示出來,這就是CiteSpace 軟件中的突現詞探測功能。采用此功能可以揭示出特定領域突現詞的變化規律,研究者可以此為依據對該領域的研究前沿進行分析[8]。圖7 為通過CiteSpace 軟件獲得的自考助學關鍵詞突現詳情表。經過綜合分析,可以將自考助學的研究過程以年份為依據劃分為五個階段。

圖7 關鍵詞突現詳情表
第一階段(1990 年至1995 年),突現詞為“助學班”“委托開考”“助學工作”“及格率”,說明此時各種社會辦學力量對開辦集體助學班的工作十分關注,并且考試的及格率是核心,并沒有更深層次的考慮和追求。
第二階段(1997 年至2005 年),突現詞為“普通高校”“高教自考”“素質教育”“管理模式”,說明此階段普通高校對于自考助學的研究和實操等工作均有了強勢介入,其4.68的突現詞強度就是最好的證明。同時,對自考助學的管理模式和對自考生加強素質教育的研究探討工作也在高效推進。
第三階段(2009 年至2010 年),突現詞為“對策”“問題”“現狀”“全日制”“網絡助學”“管理”,說明經過前面很長時間的發展,研究者對自考助學進入了反思和總結的階段。此時,自考助學,尤其是全日制助學的現狀、問題、管理等都被大量的研究者列為關注焦點,并強化對策研究。在眾多的解決方案中,網絡助學作為現代信息技術的產物受到重點關注,其突現詞強度也達到5.02,是本階段最高值。
第四階段(2012 年至2014 年),突現詞為“人才培養”“護理”“專本銜接”“改革”,說明對自考人才培養的改革成了研究者在此階段的重點研究方向。在眾多人才培養策略中,專科生銜接自考本科的辦學方向成了工作重點,其研究熱度持續至今,同時護理專業專本銜接的關注度最為突出。
第五階段(2017年至2021年),突現詞為“移動學習”“終身教育”“助學模式”,說明在此階段對于助學模式的探討已經由原先單純從自考層面出發,向助力終身教育體系建設方向轉變,這與當前黨和國家對于自學考試的重新定位和戰略部署是一致的。在眾多助學模式中,基于云計算和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的移動學習技術也在自考助學領域逐步普及。
六、結論與展望
(一)研究結論
綜上所述,自1986 年以來,我國在自考助學領域的研究成功總體上看呈現增加態勢,并隨著形勢變化和政策演進而不斷波動。相關研究的質量和深度在自考各領域研究中處于領先地位,但依然沒有呈現出顯學趨勢。雖然自考助學的研究工作持續很長時間跨度,但自考助學領域研究者的發文量普遍較少,最高發文量作者也只發表了7 篇文獻,沒有形成核心作者群,并且研究群體和研究機構的交流合作十分匱乏。35 年來,自考助學領域的研究主要圍繞助學基本理論、助學班管理、助學方式探討、自考與其他教育形式融合四個維度進行。對獲得文獻進行二次查閱,發現相關研究除了在初期涉及一些助學發展理論研究以外,其他均聚焦在學生班級管理、助學具體手段、多種教育形式溝通銜接等微觀和中觀層面,缺乏進一步的理論研究與體系建設思考,這嚴重影響了自考助學研究水平和工作質量的提升。
(二)未來展望
經過對自考助學領域文獻的可視化圖譜分析,系統梳理了本領域的研究現狀、研究熱點和研究前沿,并發現了研究工作存在的問題與短板。為持續提升自考助學研究工作的水平,充分發揮自考助學在構建學習型社會中的關鍵作用,現對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議與展望。
1. 厘清各相關機構的職責功能
國務院于1988 年頒布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暫行條例》是目前為止我國在自考領域的唯一法律性文件,然后從此以后自考的法制化進程就進入了停擺狀態,更談不上專門為自考助學這個具體工作制定獨立的頂層法律法規。《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暫行條例》中對于自考助學的描述相對簡要,已經與當前助學工作的發展情況和現實需求不相適應。這導致各省行政審批部門、教育行政部門、省級自考委在對社會助學機構的管理指導和對助學工作的研判謀劃中定位不清、職責不明、溝通不暢,進而導致工作成效不佳。目前,教育部已經關注到了這個問題,并在即將出臺的國家繼續教育改革總體方案中明確提出要由教育部制定自考助學相關管理辦法。作為自考助學領域的研究者和工作者,必須緊緊抓住國家對自考助學進行頂層設計的歷史機遇期,深入探究自考助學領域的法制建設問題,為進一步理順自考助學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提供有力支撐。
2. 搭建智慧高效的自考助學平臺
當前,自考助學工作仍然主要依靠各類助學機構進行線下面授。雖然依托互聯網進行助學活動的理念已經被提及十余年,但是其服務只是流于發布一些教學視頻這種表面形式,沒有提供更優質的深層次服務,因此導致網絡助學依然沒有成為自考助學的主要形式。在當前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貫徹國家提出了“互聯網+”戰略,不斷提升并持續完善網絡助學服務,著力搭建現代化的智慧助學平臺將是“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自考助學研究者和工作亟須關注的熱點問題。建議從三個方面進行研究:一是由全國自考委牽頭、各省自考委參與,進行自考網絡學習平臺軟硬件技術標準、學習成果認證規范等,為自考智慧助學平臺建設提供制度支撐環境;二是充分認識教學資源建設的重要性,利用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虛擬現實等高新技術優化線上課件功能,提升線上課件適應性,解決當前存在的短板和問題;三是研究將學習成果分析、專業就業競爭分析等評價反饋機制引入自考網絡助學平臺的實施路徑,為考生提供更高質量的考后綜合服務,不斷提升考生的融入感與獲得感。
3. 構筑服務新時代職教改革的“立交橋”
職業教育是我國國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培養高素質、高水平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徑,承擔著傳承技術技能和助力就業創業的重要職能。近年來,黨和國家對職業教育領域體系建設和深化改革給予了空前的重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包括制定《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啟動省部共建職教發展高地試點、推進職教東西協作行動計劃、出臺《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深化職教高考改革、完善職教本科學士學位政策等。自考工作者很早就開始關注與職業教育的銜接溝通,例如天津在十余年以前就針對技校、中職、高職制定了有針對性的學習支持政策,并取得了良好效果[9]。然而,以往對于自考與職教的銜接策略都是以通過自考來彌補職教體系缺乏學歷上升通道為指導思想制定的,這與當前職教改革的大形勢已經不相適應。為此,廣大自考助學領域研究者和工作者必須對當前各級各類職業院校考生所面臨的新問題、新困惑、新隱憂進行重新、徹底、全面的再調研、再剖析、再探索,從而研究制定服務新時代職教改革的自考助學新方略、新政策、新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