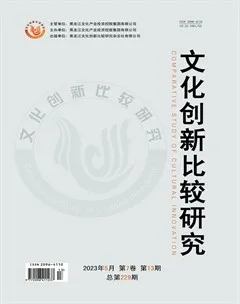云南大理喜洲白族家庭語言政策代際差異研究
孟雪凡
摘要:我國是多民族國家,擁有錯綜復雜的語言體系。如何科學協調處理多語(通用語、方言、民族語)之間的關系,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語言,使多語相互交融、相互促進,最終共同發展,是保護和維持我國多元文化資源的主要任務之一。該文以Spolsky語言政策理論為支撐,通過對世居在大理喜洲鎮的一個四代同堂的白族家庭進行研究,以期探究白族家庭語言政策特點和白族語言使用現狀及其影響白族語言活力的因素。結果表明,白族家庭成員之間存在代際差異,且其家庭語言政策不斷變化發展;白族語言流失現象顯現;宏觀和微觀因素共同作用導致白族家庭成員間語言政策的代際差異。
關鍵詞:家庭語言政策;少數民族語言;繼承與保護;家庭語言;民族語言保護;多語和諧共存
中圖分類號:H002?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文章編號:2096-4110(2023)05(a)-0029-06
A Study on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Language Education in Xizhou Bai Families in Dali, Yunnan Province
Abstract: As a multi-minorities nation, China contains a various and difficult language system.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ultiple languages, inherit and protect ethnic languages to reach the goal of co-development among multiple languages have been one of the main tasks of maintaining the multi-cultural resources in China. Supported by Spolsky's(2004) language policy theory, this paper studies a four-generation Bai family living in Xizhou Town, Dali,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i family language polic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Bai language use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vitality of the Bai langu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among Bai family members, and?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s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developing; the loss of Bai language appears; both macro and micro factors lead to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policies among Bai family members.
Key words: Family language policy; Minority languag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Family language; Ethnic language protection; Coexistence of multilanguage
早在20世紀50年代國外學者已開始對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進行“自上而下”的研究,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Cooper指出語言規劃不僅作用于宏觀層面,也作用于微觀層面。Spolsky也將家庭納入語言規劃的7個范圍內。此后語言政策規劃研究逐漸轉向家庭層面。保證母語使用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保證母語在家庭中的使用[1]。國外家庭語言政策研究以跨文化移民家庭為主要研究對象,包含家庭語言實踐、家庭語言信念及家庭語言管理3個要素[2]。
21世紀以來,我國少數民族語言學研究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亟待今后加強研究[3]。國內家庭語言政策研究起步較晚,據“中國知網”和“超星發現”兩個數字資源庫的信息顯示,國內家庭語言政策規劃相關文章僅十余篇。在理論研究方面,李麗芳提出家庭語言政策無顯性成文的管理和語言規章制度,只是基于語言實踐和語言信念的語言選擇問題[4]。許靜榮強調了家庭語言政策在兒童語言發展方面的系統規劃功能[5],劉群指出家庭語言關系的有效平衡需同時考慮家庭的內部因素(家庭成員)和外部因素(社會和政府)[6],李英姿概括了家庭語言政策的理論與方法,給予國內研究一定啟示[7]。在實證研究方面,李秀錦以兩例民族志個案試圖證明家庭語言政策對兒童文化認同產生直接作用[8]。
總之,在國內外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中,家庭語言政策研究都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而少數民族家庭語言政策研究更是稀缺,有待國內學者探索與研究。
1 家庭語言政策與少數民族語言保護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有許多少數民族。在多語言環境中,研究人員逐漸將研究視角轉向少數民族語言的保護和發展這一熱門話題,如民族語言的代際傳承、民族語言和國家通用語的協調發展,以及構建和諧的語言生態系統。顯然,家庭語言政策已成為當今語言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
研究人員普遍認為,家庭是獲取、使用和繼承民族語言的重要場所。大多數涉及民族家庭語言保護的研究都表明不同民族、不同層次的少數民族家庭有不同程度的代際語言差異。民族語言使用的平均年齡越來越大,使用民族語言的人數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急劇下降。此外,由于語言態度的影響,一些少數民族家庭出現了母語或民族語言流失的現象。 總之,民族語言的保護和繼承不容小覷,家庭作為民族語言習得和繼承的重要場所,對其進一步的研究應提上議事日程。
庫珀指出,語言規劃同時作用于宏觀和微觀層面,例如教會、學校和家庭等較小的社會群體。2004年,斯伯爾斯基提出語言政策和規劃是跨學科的研究,其組成系統應包含3部分:語言意識或者語言意識形態,指的是語言政策背后的語言和語言使用的信念和觀點;語言實踐,即在不同環境中為不同目的使用實際語言變體;語言管理,即通過語言干預、計劃或管理影響他人的語言實踐或語言意識形態的行為。相應地,家庭語言政策也由3部分組成:家庭語言意識形態,即家庭成員對所選語言的態度和意見;家庭語言實踐,即家庭成員習慣性選擇使用哪種語言;家庭語言管理,這是家庭成員干預、計劃或管理家庭語言意識形態和實踐以糾正、影響或改變家庭語言實踐的活動。此外,斯伯爾斯基還表示,這3種情況的發生將觸發家庭語言規劃:第一,當家庭中的權威角色改變其他家庭成員的語言實踐時;第二,當家庭成員逐漸開始使用不同語言時;第三,當家庭搬到另一個語言環境時。
2 研究方法
大理市,位于云南省,其語言包括地方方言和白族語言。喜洲鎮是大理的下轄鎮,位于大理市中心地段。然而,洱海、蒼山、蝴蝶泉、三塔等周邊的著名旅游景點的開發使得旅游業成為喜洲鎮的主要特色發展產業之一。旅游業的發展給其帶來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帶來了來自國內乃至世界各地的大量旅游者及他們的語言,這對當地語言造成了潛在的威脅。此外,由于普通話和國家義務教育的普及,青少年可以在學校系統地學習普通話,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另外,在外地工作的當地居民返回后帶回了一些其他語言到家庭中,導致了對當地語言,特別是白族語言的沖突和影響。因此,多語環境的喜洲鎮在語言研究中的無限價值使其成為一個極好的語言研究場所。
本研究為個案研究,從2016年到2019年,喜洲鎮的白族家庭已被觀察了3年。這項研究不同于“大數據”研究。在確定了研究的主題和地點后,為了更好地了解喜洲鎮的具體情況,筆者于2016年7月至2019年1月多次訪問該地,最終決定將最具象征意義的四代同堂白族家庭作為研究對象。這個家庭由四代人組成,家庭成員的職業范圍廣泛,覆蓋范圍廣,生活和工作條件多樣,因此對這個家庭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說服力。在這個典型的白族家庭中,四代家庭成員大多數時間生活在一起,包括第一代爺爺A;第二代父親B、母親C、阿姨D、叔叔K;第三代兩姐妹E和G,他們各自的丈夫F和H,以及堂兄M、N和O;第三代兩對夫婦各有一個女兒I和J作為第四代。
通過訪談,研究人員可以從參與者那里獲得一手數據,并了解把握他們生活的背景和內容。本研究與白族家庭的四代人共進行了6次訪談,包括與不同世代的家庭成員的訪談,并記錄整個過程(獲得研究對象的許可),以方便后期文本分析。 每次訪談持續6—8分鐘,并以受訪者想運用的語言在較為舒適和放松的環境中進行。
根據研究得知,該白族家庭的語言能力如下:第二代B、K,第三代E、F、M、N、O具有3種語言能力;第一代A和第二代D可以講白族語言和方言;第三代G可以講白族語言和普通話;第三代H可以講普通話和方言;第二代C只會講白族語言;而第四代I只學會了普通話。
3 白族家庭語言政策與代際差異
3.1 語言意識形態
因為B和D的工作性質,他們與來自不同的少數民族的人接觸,并且在這一代人看來,他們不熟悉普通話而且使用普通話與他人交流的機會較少,方言反而是最好的交流工具。在早年間,當N和O都是小孩子的時候,K帶著N和O搬遷到楚雄居住,遠離家鄉大理。K擔心N和O無法適應大理以外的生活環境,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并確保兒童能夠融入新城市的生活和交流,K決定讓他們學習當地方言以便幫助他們更好更快地融入楚雄的新生活。同時,他認為學習方言也有助于他的孩子們的課程學習及處理好在當地學校的人際交往關系,也就是說,方言可以有效地轉化為提高學習和生活能力的資源。因此,在楚雄K堅持在家中用方言與N和O溝通。
本科生M、O和H多年的大學學習經驗使他們意識到,作為現代社會交流的主要語言,普通話很重要。盡管E和F夫婦在語言學習方面沒有太多經驗,但是他們作為服裝店的銷售人員會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們認識到了普通話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地位。與此同時,學校規定學生必須與教師和同學講普通話。故此,E和F夫婦決定讓孩子們流利地使用普通話,以更好地適應大理這一旅游城市的生活,從而幫助她更快成才,更好地適應社會。另外,E說白族語言是白族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如果I不能說白族語言也沒關系,但至少當別人對她說白族語言時她必須能夠聽懂。
雖然G和H夫婦住在昆明,但他們的歸屬感并不強烈。這種移居者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對下一代語言教育的態度,特別是在語言學習方面。在他們看來,掌握普通話是他們的女兒在昆明取得學業成功的必要基礎;只有當他們的女兒成功接受教育,她才能擺脫附在她身上的移居者身份的標簽。根據他們自己習得普通話的經驗,這對夫婦認為,如果學習者有沉浸式的語言環境和語言學習動機,就可以自然而流利地學習語言。因此,基于這樣的語言意識形態或信念,為了讓女兒J習得標準普通話以便她能成為真正的昆明市民,G和H最終決定在家中主要用普通話與女兒溝通。此外,G擁有強烈的民族認同感,H也強調少數民族在學習和就業方面的優勢和地位。因此,他們都認為J學習白族語言是很有必要的。然而,他們并不擔心女兒普通話和白族語言的習得和發展。相反,他們對多語共存持積極態度。
3.2 語言管理與語言實踐
在采訪中,A說他非常喜歡白族語言,并且大多用白族語言與家人交流。只有接待外來游客時,他才會說方言。此外,由于第四代語言使用習慣,他學會了幾句普通話與I和J交流。
第二代通常使用白族語言和方言的混合語與第三代交流,同時使用方言與訪客和親屬進行交流。當M在學校時,他的老師和同學都說白族語言和方言,因為在學校里沒有說普通話的規定。中學畢業后,M參加工作,并在工作領域學習了普通話。
E、G與M有著相同的生活經歷。有趣的是,G在采訪中提到,方言中含有她不喜歡的口音和發音,她從頭到尾都沒有學習方言。雖然方言已被M和G掌握,但由于其在工作領域的使用頻率較低,因此逐漸被普通話取代。自從N和O上學以來,他們開始學習和說普通話。他們與老師、同學和朋友都說普通話。回到家后,即使K堅持和他們說白族語言和方言,他們也只使用白族語言回應他們的父親并拒絕使用方言。他們最終獲得了學士學位,在社會生活中主要使用普通話,而只與家人用白族語言交流。
第四代I幼兒時期,E和F夫婦每天晚上都會用普通話讀睡前故事給她聽,這使得I喜歡上閱讀。她臥室的書架上裝滿了中文的兒童閱讀材料和漢語拼音的書。雖然她才小學二年級,對漢字的了解也非常有限,但她已經掌握了基本的普通話拼音。在父母及閱讀書籍中普通話拼音的幫助下,她可以準確地閱讀大部分包含新詞的書籍。另外,E和F夫妻彼此用白族語言交流, I在的情況下,他們便使用普通話。有時候他們偶爾會跟I說幾句白族語言,I會用幾個簡單的白族語言回答。但是,當I進入小學時,情況發生了變化。在小學,因為老師和同學之間的溝通都使用普通話,現在即使她的父母E和F使用白族語言與I對話,她也只用普通話來回答。如果E和F明確要求I用白族語言回答,I便什么也不說自己跑開。從那時起,E和F就不再強迫她使用白族語言,而只是要求她能理解聽懂他們對她說的白族語言。
當筆者收集語料庫數據時,J只有兩個月大。 G和H夫婦優先使用普通話與她進行交流。 由于G的母親C用白族語言與J交談,所以他們并不擔心J白族語言的習得。 更重要的是,G和H說,等J一百天大時,她將被送回大理的家待上幾個月,讓她沉浸在白族語言環境中,接受白族語言的語言輸入。 這一決定進一步促使他們在昆明的家中更愿意使用普通話與J進行交流。 有趣的是,C雖然不具備說普通話的語言能力,但是在與昆明的G和F夫婦共同生活了半年之后,她學會了幾句普通話,并且在她照顧J時偶爾會說出幾句普通話。 同時,A在與I的交流中也有類似的負影響發生。
3.3 語言使用代際差異
四代白族家庭成員在日常交流中的語言選擇具有差異性特征,本研究分析了白族的語言使用和變化,結果表明:不同世代的家庭語言使用存在共性,也存在代際差異;白族語言使用者的平均年齡越來越大,使用白族語言的人數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急劇減少; 在第四代家庭成員的語言使用中出現了白族作為母語退出白族家庭的現象。
由于宏觀和微觀環境因素的變化,家庭語言政策也呈動態發展。家庭內外的環境變化可能導致家庭語言政策的動態變化。對白族家庭四代人的調查表明,家庭中的語言意識形態、語言管理和語言實踐表現出動態的代際差異,而這個家族所持有的家庭語言政策也呈一個漸進發展的過程。第一代家庭成員使用白族語言作為與下一代交流的主要語言。然而,隨著后代語言能力的發展,不同輩分的家庭成員表現出不同的家庭語言政策變化。B和C夫婦,以及D開始意識到方言的實用性,K想讓他的孩子們更好地融入新城市的生活,所以他們都在家庭領域中使用方言,他們的家庭語言政策已經從“白族語言作為主要交際語言”轉變為“白族語言和方言雙語”。第三代逐漸將其家庭語言政策發展為“白族語言和普通話雙語”。一方面,E和F夫婦及G和H夫婦都希望能讓他們的孩子習得流利的普通話;另一方面,包括M、N和O在內的第三代人過上更好的生活,結果導致普通話逐漸取代了家族中白族語言的核心地位。I在家庭中只使用普通話的情況致使她逐漸實施“普通話”的單語家庭語言政策。值得一提的是,J的父母G和H強烈希望J傳遞白族語言。一方面,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掌握普通話,以便迅速融入昆明的新環境;另一方面,他們始終牢記白族文化的重要性,并具有承擔保持白族語言的意識。因此,J有可能在未來發展為實施“白族語言和普通話雙語”的家庭語言政策。
3.4 家庭語言政策影響因素
導致白族語言政策的代際發展及白族語言流失的因素既有宏觀層面也有微觀層面。
3.4.1 微觀層面
白族家庭語言政策的微觀影響因素或內部因素主要包括父母因素和兒童主觀能動因素。一方面,父母作為家庭語言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實施者,更傾向于根據自己的語言學習經驗做出關于孩子教育的決定。J的父母G和H從他們學習普通話的經驗中得出結論,語言習得需要積極的學習動機和沉浸式語言學習的經驗。這種語言意識形態充分反映在他們的語言管理和語言實踐中,他們將普通話傳授給J,并將她送回大理一段時間學習白族語言。顯然,G和H的主觀語言學習經驗可以有效地指導家庭語言政策的制定和積極的家庭語言生態學的構建。同時,父母的語言能力和語言態度自始至終影響著家庭語言政策的形成和管理。具有雙語能力的父母可以利用更多的語言資源與孩子交流,他們可以直接向孩子提供有效的語言管理。另一方面,一般來說,兒童被認為是家庭語言政策的被動接受者,他們在家庭環境中的語言行為受父母語言意識形態的影響。然而,本研究發現,兒童作為家庭的核心成員,也參與家庭語言政策的形成和實施,因為他們的語言態度和做法也影響了父母家庭語言政策的實施。 E和F第三代夫婦試圖用白族語言與第四代I交流,并要求她用白族語言回答,但由于I的態度非常不合作,導致家庭語言政策無法按照父母意愿實施。女兒I對白族語言的消極態度最終間接地促使父母放棄了對白族語言的語言管理。第三代N和O對方言的消極態度也影響了他們父親K的家庭語言政策的實施。同時,在僅使用白族語言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家庭語言政策下,I沒有受到第一代和第二代家庭語言實踐的影響,反而逆影響導致第一代和第二代人在家庭中說普通話。
3.4.2 宏觀層面
白族家庭語言政策深受宏觀政治結構的影響,包括國家語言政策、語言教育政策,以及工作和學習場所、生活城市,同齡群體和教育機構等社會和社區等環境因素。研究中的四代人都承認普通話的重要性,源于他們認為普通話是社會經濟和社會政治的主要資源。首先,旨在促進使用普通話的宏觀國家語言政策,以及規定學校必須規范語言使用并將普通話作為禮貌象征的語言教育政策,導致白族語言逐漸失去其使用領域,被普通話取而代之。其次,同一年齡人群和社區內外教育機構對本族語言的態度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如果他們支持維護和發展少數民族語言,少數民族家庭的孩子將對自己的民族語言持積極態度;相反,則民族語言很可能逐漸退出少數民族家庭子女的語言習慣,最終導致他們對民族語言產生負面情緒和不合作態度。例如,白族中的第三代N和O,以及第四代I正是如此。
4 結語
本研究獲得了三項研究成果,具體如下。其一,由于宏觀和微觀環境的變化,家庭語言政策呈現出動態特征。家庭內外的環境變化將導致家庭語言政策發生動態變化。對四代白族成員的調查顯示,家庭中語言意識形態、語言管理和語言實踐存在動態的代際差異,白族家庭所持有的家庭語言政策呈現出一個逐漸發展的態勢。其二,在白族家庭成員中,第一代發生“自然代際傳承”的喪失; 第二代逐漸成為雙語人士;第三代通常會成為一個只會說當地主流語言的單語者。只能學習一點或完全失去母語是語言喪失的主要標志[9]。本研究涉及的白族家庭是喜洲鎮的典型研究對象,由四代人組成。通過對每一代人的采訪和觀察,結果表明: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可以流利地使用白族語言;第三代雖然也掌握了白族語言,但更傾向于使用普通話;而第四代則只講普通話,只習得了少數白族語言詞匯表達,基本上不會說白族語言[10]。顯然,白族語言在四代人的代際傳承中出現了語言流失現象。其三,導致白族語言政策的代際差異及白族語言流失現象的因素包含兩個層面,即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11]。微觀層面上是白族父母和子女的主觀能動因素;宏觀層面上是白族家庭成員受國家語言政策、語言教育政策和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包括工作和學習環境、生活城市、同齡群體和教育機構等[12]。
本研究旨在揭示白族家庭語言政策及影響其制定和實施的因素。當然,本研究不可避免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主要以喜洲鎮四代白族人為研究對象,雖對不同世代進行研究和分析,但其他白族人并未全部涉及。該白族家庭雖具有一定典型性,但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存在其個體差異和獨特性,它只能反映出包含相同研究對象情況的白族家庭語言政策。因此,需要更多的家庭案例來研究和探討所有白族家族的語言政策。其次,由于筆者不具備說白族語言的能力,故只能通過白族語言—普通話翻譯將一些白族語言語料集合翻譯成普通話。因為兩種語言之間的差異,普通話語料庫的翻譯結果與原始的白族語言語料可能存在一些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恰當性和準確性[13]。
基于上述局限性,對于未來研究的建議可歸納如下:一是應將更多的少數民族家庭納入研究對象進行分析和描述,以獲得更全面、更完善的研究成果;二是為了奠定更好的研究基礎,研究人員應該一定程度地了解和掌握研究對象使用的民族語言,以便更為準確地收集研究信息和語料。
參考文獻
[1] SPOLSKY B. Family language policy: The critical domain [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 opment, 2012(1):3-11.
[2] FISHMAN J A.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M].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1.
[3] 鄧文彬.21世紀以來少數民族語言學研究述略[J].民族學刊,2016(5):83-90.
[4] 李麗芳.國外家庭語言政策研究現狀分析[J].云南農業大學學報,2013,7(5):87-90.
[5] 許靜榮.家庭語言政策與兒童語言發展[J].語言戰略研究,2017(6):15-24.
[6] 劉群.家庭語言規劃和語言關系[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6):117-121.
[7] 李英姿. 家庭語言政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J].語言戰略研究,2018(1):58-64.
[8] 李秀錦,劉媛媛.家庭語言政策與兒童文化認同構建:兩例民族志研究個案報告[J].語言政策與語言教育,2017(2):13-22.
[9] FISHMAN J A. Sociolinguistics: A Brief Introduction [M]. Rowley: Newbury House,1970.
[10]巴戰龍.如何打造雙語家庭:裕固族語言文化遺產傳承問題研究[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5):58-63.
[11]戴慶廈.開展我國語言和諧研究的構想[J].黔南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13,33(3):1-5.
[12]戴慶廈,鄧佑玲.瀕危語言研究中定性定位問題的初步思考[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2):120-125.
[13]鄔美麗.內蒙古一牧區村蒙古族語言使用的代際差異[J].中國社會語言學,2014(2):7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