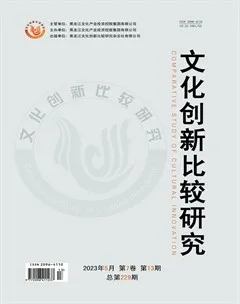芒市傣族祭寨神儀式呈現的歷史記憶
郭敏 李瑋琪
摘要:中國史學界用“歷史記憶”觀察族群認同、族群關系。芒市傣族地區寨神祭祀活動不僅是傣族宇宙觀載體,更是傣族人民祖先崇拜、靈魂信仰的具體體現,傣族后輩在祭祀儀式中接受長輩的社會教育,在祭祀寨神儀式中了解本寨歷史。該文通過對芒市軒崗鄉M寨祭祀寨神儀式的描述與分析,探討祭祀寨神儀式中蘊含的傣族村寨歷史記憶。該文認為:從寨神位置中可以探知村寨歷史;寨神崇拜是芒市傣族民間信仰的核心;雙重信仰融合形成當地傣族功德觀。該文從歷史記憶的角度研究某一族群,有利于探索歷史記憶在該族群繁衍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關鍵詞:芒市傣族;祖先崇拜;寨神;祭祀儀式;歷史記憶;功德觀
中圖分類號:B933?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文章編號:2096-4110(2023)05(a)-0093-05
Historical Memory in the Ceremony of Sacrificing Gods to the Village of Dai Nationality in Mangshi
—Investigation Based on M Village
Abstract: The Chinese historical community uses "historical memory" to observe ethnic identity and relationships. The worship activities of the village gods in the Dai area of Mangshi are not only a carrier of the Dai people's worldview, but also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ir ancestor worship and soul belief. Dai descendants receive social education from their elders during the worship ceremony, and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ir village through the worship ceremony of the village god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ritual of sacrificing village gods in M Village, Xuangang Township, Mangshi, and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Dai villages contained in the ritual of sacrificing village gods.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location of the village god can reveal the history of the village, the worship of village gods is the core of the folk beliefs of the Dai people in Mangshi, and the fusion of dual beliefs forms the local Dai people's view of merit and virtue. This article studies a certain ethnic gro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emory, which is conducive to exploring the role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the reproduction process of that ethnic group.
Key words: Dai nationality in Mangshi; Ancestor worship; Village God; Sacrifice ceremony; Historical memory; View of merit and virtue
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界興起了“新文化史”的史學研究思潮,在中國史學界更多地稱為“社會文化史”,隨著這股新史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和流行,一些史學者于20世紀末開始進行歷史記憶的研究。
1950 年,莫里斯·哈布瓦赫用法文出版了《集體記憶》一書,專門論述了“集體記憶”,美國道格拉斯于1980年將之翻譯成英文。20世紀70年代,皮埃爾·諾拉編寫的《記憶之場》是集體記憶史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推動了法國記憶研究史的全面發展。1992年,臺灣學者朱元鴻將“集體記憶”概念正式運用于史學研究。1993年,臺灣《當代》雜志刊載“集體記憶專輯”,其中邱澎生翻譯的美國社會學者科塞《阿伯瓦克與集體記憶》,掀起了中國關于歷史記憶的研究熱潮。大陸學者歷史記憶的研究受到中國臺灣學者的影響。1997年,楊念群在介紹景軍英文著作《神堂記憶》時闡述了“歷史記憶”的相關概念[1]。2000年,納日碧力戈翻譯的《社會如何記憶》豐富了國內史學界對國外社會記憶理論的認識。中國史學界用“歷史記憶”觀察族群認同、族群關系,王明珂應屬最早。他在《當代》雜志上發表的《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一文,強調集體歷史記憶在形成族群上具有凝聚、認同功能[2]。此外,他對社會記憶、集體記憶與歷史記憶3個概念做出了界定。他認為“社會記憶”是“所有在一個社會中籍各種媒介保存、流轉的‘記憶”;集體記憶是“前者中的一部分‘記憶,經常在社會中被集體回憶,而成為社會成員間或某次群體成員間分享之共同記憶”;歷史記憶是“在一社會的‘集體記憶中,有一部分以該社會所認定的‘歷史形態呈現與流轉”[3]。本文采用王明珂對歷史記憶的定義,論述皆在此限度內對歷史記憶進行討論。
傣族寨神的研究,朱德普從祭壇位置、貢品、祭祀人員、儀軌、祭文等方面對德宏各個不同地區歷史上的祭祀勐神儀式進行了詳細的考究[4];金少萍從性別視角探討了傣族原始宗教祭祀中對女性的禁忌及排斥現象[5];楊光遠指出祭祀寨神時,對牛、雞等貢品的顏色有一定要求[6];閻莉、莫國香探討了寨神、勐神祭祀活動的集體表象特征,認為這種具有嚴格排他性的集體祭祀活動是社會團結的根本性力量[7];何慶華對傣族祭寨神儀式空間的排他性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論述[8]。
綜上所述,傣族祭祀寨神研究多從祭祀儀式、祭祀禁忌,以及排他性等方面進行論述,較少從歷史記憶理論的角度對祭祀寨神中呈現的傣族族群認同進行研究,傣族祭祀寨神中呈現的歷史記憶研究略為薄弱。所以,有必要從歷史記憶的角度研究某一族群,甚至某個村寨的祭祀寨神所呈現的歷史記憶,探索歷史記憶在其族群繁衍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本文力求從兩方面做到創新:一是從歷史記憶本身擴大其研究范圍;二是擴大芒市傣族祭祀寨神的研究內容。
1 M寨的寨神
M寨位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芒市軒崗鄉M村委會,距離軒崗鄉政府所在地5 km,距州府芒市24 km。M寨整體位于二級坡地地帶,在傣語中,芒為“寨”,棒有“坡地”之意,意思是“建在坡地上的寨子”,當地村民認為其祖上從緬甸遷來過程中,因壩區平地早已被更早遷居至此的德昂族占盡,于是只能在壩區附近的山地落腳,逐漸發展形成村寨。
芒市每個傣族村寨都有寨神,各寨寨神互不相通,互不隸屬,他們有各自的傳說,這些傳說均與建寨歷史有關。傣族有句諺語:“召很歹兵弟娃拉很,召曼歹兵弟娃拉曼,召很歹兵弟娃拉勐”,其意為“家長死后當家神,寨子首領死后當寨神,召勐死后當勐神”。從這里可以看出寨神一般是去世的建寨首領,有的村寨指建寨后第一位去世的祖先。有的寨子寨神不止1位,M寨一共有3位寨神:主寨神叫做“混像拉勐”,當過元帥;第二位寨神叫“趙朗祥”,當地人說是一位公主,吃素;第三位叫“趙和紳”,是一位將軍。村民為寨神建立了神廟,寨神廟內沒有寨神塑像,僅放置了一些簡單家具用于擺放貢品和蠟條。M寨的3位寨神的坐騎不同,主寨神坐騎右邊是馬,左邊是大象,公主的坐騎是兩匹馬,將軍的坐騎也是兩匹馬。主寨神在寨子的中心位置,建在奘房不遠500 m處。公主“趙朗祥”在寨子頭附近,將軍“趙和紳”在寨尾附近,守候著寨子的墓地,三位寨神分別都在大青樹的保護之下。傣族地區有兩種神樹:一是榕樹(大青樹),一是菩提樹。正如姚荷生先生所說,“前者的下面埋著死者的尸體,平時沒有人敢走在它無數的氣根中間,每年都在這時舉行一次神秘的祭禮;后者矗立在村頭路邊,樹大葉密,蔭廣數畝,是行人憩涼好去處”[9]。
2 祭寨神儀式
2.1 祭寨神的時間
祭寨神傣語叫做“拜召”,“拜召”就是祭拜老大。由于歷史變遷的不同,影響傣族地區的歷史人物互不相同,被尊奉為寨神的對象也就互不相同,各村寨祭寨神以本寨為單位,互不干涉,祭寨神成為一種凝聚傣族民眾精神力量的社會活動。M寨每年會有3次集體祭寨神活動:第一次是傣歷十月份(即公歷八月份),收稻谷之后;第二次祭祀的時間是干朵節即出洼的時候;第三次是農歷春節。由村長負責組織,M寨有3個組,每組推選出祭寨神的人,最后推選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當主祭。祭拜日一般是收稻谷后屬馬日,祭品為黑豬,不選擇白豬或者花豬是因為白豬、花豬是新品種,以前只有黑豬,祖先只識得黑豬。收谷后祭寨神規格最大,寨子所有的村干部都要參加,由村長安排祭祀人員。祭祀時,分別準備3份祭品,分成3隊人馬,一隊去一個地方祭祀。其他的時間,如婚禮、上新房、買車等,只用去主寨神處,請3位寨神一同到主寨神處祭祀。
凡寨子舉行重大活動,進洼、出洼,紅白喜事,都要祭寨神,祈求平安順利。當地人認為重大活動不去祭寨神就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忽視寨神則可能招致不幸。村支部書記項大姐介紹說:“有一次我們寨子舉辦婦女活動,正在跳著舞,音響忽然就燒了,后來我仔細想了一下,可能是之前忘記去拜廟了。”凡寨子中出現不順利、不吉利、不潔凈之事,村民也往往認為是得罪了寨神而導致的,因而也要舉行祭寨神,甚至洗寨子。
2.2 祭祀寨神的禁忌
按照涂爾干的觀點,宗教信仰表達的是人們對神圣事物的認定及對神圣事物之間關系、神圣事物與凡俗事物之間關系的理解,宗教儀式有各種行為準則,它們規定了人們在神圣事物對象面前應該具有怎樣的行為舉止。寨神廟是寨子里婦女和兒童的禁忌之地,僅有男性能夠進入寨神廟并舉行相關儀式活動。祭寨神嚴格的禁忌表現為:第一,女人不能去祭寨神;第二,妻子懷有身孕(包括準備懷孩子的家庭),男人也不能去祭寨神;第三,做錯事,寨子里所有人都知道其行為的人(如有吸毒、通奸、偷盜行為的人)不能去祭寨神;第四,祭拜寨神的飯菜必須由男人做,而且在做飯菜的時候,不能嘗味道,因為給寨神吃的東西,寨神必須第一個吃。寨神沒有吃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吃。參加祭祀的人必須經過嚴格的挑選,是“好的”“干凈的”才能去。擔任祭祀寨神的主祭,必須是父母健在,有兒有女,家庭美滿的,“不干凈”的人,是不允許去的,年紀小的人也不能去。M寨三社的金某說,“因為我們這個廟太干凈了。以前條件不好,我們的寨神沒有蓋房子,去到大青樹下面。燒一下香蠟燭,擺一下東西就可以了,現在政策好了,我們給寨神蓋了房子,放有凳子,還有專門兒點香點蠟燭的地方。我們在祭的時候告訴他們,3個一起來保佑親戚的姑娘出嫁,順利出嫁,不有什么事,出門好好的出。”
2.3 祭寨神的過程
到M寨時,恰遇一戶人家嫁女,筆者有幸參觀了整個的祭祀活動。
祭祀寨神儀式在婚禮的前一天下午舉行。當天下午4點,主人家開始準備祭祀寨神的飯菜。祭品一共有三葷(剁生的肉、炸過的肉、煮的肉)、一素、酒、餅干、飲料、稻谷、香、蠟條等。祭寨神儀式在主寨神處舉行,同時邀請其他兩處寨神到主寨神處祭祀。在祭祀寨神之前,將寨神廟周圍打掃干凈,再為廟內的塑料花換水并清洗干凈,之后點一把香和三根蠟條,放在寨神屋內。然后將帶去的飯菜、糖果、飲料、酒等擺在桌上,擺好飯菜之后,倒上酒和飲料,將筷子插在飯碗里。當地人說,筷子插在飯上,表示祭鬼。要是筷子放在飯上,表示給活人吃。以上準備工作完成之后,所有人退到了屋外,跪下磕頭,主祭的人念著敬語(大概內容是:今天某某嫁女,我們請寨神吃飯,告知此事,請求保佑他們婚姻美滿,萬事如意)。念完之后回到寨神屋外的亭子里面休息幾分鐘,再去為寨神加菜、加酒等,這樣反復3次。最后把祭品搬到涼亭處,前去祭祀的人圍坐在亭子,與寨神共享祭品。為什么要與寨神共享祭品?涂爾干說,貢獻給神的東西是神圣的,只有吃掉貢品,才能與神建立聯系,與神溝通,才能達到祭祀的目的。因為飯菜已經供給寨神,寨神享用的飯菜,凡人也一起享用,便有了寨神的庇佑。奉獻犧牲的崇拜者與他們所尊奉的神共享犧牲。犧牲某些部分為神而保留,而其他部分則由奉獻犧牲的人來享用,在大多數社會里,據說共享進餐可以在出席者之間建立起人為的親屬紐帶[10]。
3 祭寨神儀式中呈現的歷史記憶
3.1 從三位寨神廟所處的位置,可以看出村寨的歷史
按照傣族的習俗,地位最高的神,所在位置應該是寨子的最高處,坐北朝南。經過調研發現,M寨的主寨神,建廟位置并不是最高的,而是在奘房附近。經過詢問寨長還有其他老人得知,寨子所在的區域早先是四個德昂族村寨所有,他們各信奉不同的寨神,后來傣族遷居此地,德昂族在爭搶地盤過程中失利,遷出此地,但寨神作為創寨之主卻保留下來。所以現在寨子里最大的寨神,其實是最早的創寨之主,是德昂族。傣族凡是婚姻嫁娶、喪葬禮儀,必祭寨神,嫁娶從寨子頭進,喪葬則從寨子尾出。“我們寨子是有寨門的。我們小時候,經常到寨子頭玩,寨門都是好好的,現在不有得了,都爛完了。但是在我們寨民的心中,寨門永遠都是存在的。”從這里可以看出,M寨同其他傣族村寨一樣,有著自己的寨門,將本寨與外寨明顯地區分開來,將本寨的人封閉在一個完整的空間,受寨神的庇佑,村寨的歷史,從寨神的位置當中得到了呈現。
3.2 寨神崇拜是傣族民間信仰的核心
傣族將寨神稱做“召曼”,“召曼”是寨子的保護神。寨子里的老人金某說:“很久以前,外寨的人想要來燒我們的寨子,召曼出現了,將我們的寨子隱身起來,外寨的人就看不見我們的寨子,我們寨子才保存了下來”。當問及寨神情況,金某的孫女回復道:“寨神都叫召曼,他們會保護村寨。”她講述了一件召曼顯靈的事:“今年二三月份的時候,全寨的人都在收砂糖橘,在洗橘子,非常忙。有的人家請了很多緬甸的人來幫忙。從白天洗到晚上,晚上洗到白天。凌晨四點鐘左右,有一些緬甸人在公主廟的旁邊丟東西,把這個地方弄得很臟很亂,垃圾到處都是。這個時候公主就出現了,站在一輛摩托車的旁邊,非常的美,亮晶晶的。只要寨子有事情發生,他們都會出來,寨子秩序亂的時候就會出來保護。”金某描述時一臉崇拜,并且說:“好可惜,我去看的時候,召曼已經不見了,真想看看她。壞人或有惡意的人出現在寨子,他們就會阻擋。如果牛走丟了,去祭拜召曼,牛就會自己回來。寨子里的人做什么召曼都知道。”從上文描述中看出,在寨民心中,召曼一直存在,負責保護寨子的平安。召曼是神圣的,是寨子里所有人崇拜的對象。因為有了召曼,寨子才能平安,才能正常運作,他們可以保護寨子不受侵犯,保護寨子的安寧。
在傣族的歷史記憶中,有兩個階段的代表人物影響傣族的發展,一個是氏族首領沙羅,一個是部落聯盟首領叭桑木底。按照《沙都加羅》記載,沙羅因把傣族群眾聚集起來,一同打獵,開啟了傣族的“盤巴時代”[11],他死后,人們為其建了“獵神廟”,稱他為“獵神王”。而叭桑木底,將傣族人民從游獵時代引向聚居時代,他將人民集聚在一起,一同砍樹,建新房,建寨子,在寨子的大樹下,供奉著寨神勐神。寨子建好后,他又用紅色石頭栽在寨子中央,立為寨心。選了一片樹林,作為神林,宣告了“寨神勐神”的誕生。傣族重視祭祀寨神勐神,他們認為,一切動植物都虔誠忠實于他們祖先的靈魂,人應當崇拜祖先,尊崇祖先的靈魂,傣族寨神的祭祀正是傣族人們崇拜和敬重祖先的方式。M三組金某說:“寨神是我們寨子建寨時候去世的第一位祖先,我們都很尊敬他,保佑寨子的平安。寨神最怕吵、最怕鬧、怕人多。祭寨神是因為來的人太多,怕嚇到他。所以做什么事之前,都要向寨神匯報,到奘房旁邊的這個寨神廟去祭,把其他兩位寨神一起召過來,一起祭。”
M寨之前的寨神是沒有任何庇護場所的,村寨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向前發展,但是人們不會因為社會進步,而遺忘寨神,他仍舊是全寨人的中心,全寨人的精神信仰。他們之所以要去祭拜寨神,是怕寨神受到驚擾。如果某家人有事,沒有去祭拜寨神,有可能招致不幸。寨神知道寨子里的一切人與事,任何事情都要告知寨神,如果沒有祭祀寨神,寨神有可能認為當地人忘記了祖先、不尊重祖先,就會施加“祖先陰影”[12],甚至作祟于后人,讓想要做的事情做不成,甚至是往壞的方向發展,這里體現出M寨靈魂空間與生命空間的互動。寨神是逝去的祖先,了解整個寨子所有的日常事、日常人。人們的一舉一動,都在寨神的掌控之下,寨神掌控的是現實生命空間中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人們通過祭祀寨神,祈求寨神的庇護,而寨神接受了寨民的供奉,保佑整個村寨的平安,兩者相互依存,成為當地傣族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精神氣質。
3.3 雙重信仰融合形成的芒市傣族功德觀
芒市傣族核心的價值觀念是舍功德。舍功德的實際表現就是做好事、做善事。舍了功德就會樣樣好,就會“汝你金玩”。功德觀貫穿芒市傣族群眾的一生,當地人認為,今生舍的功德越多,來世回到自己身上的就越多;今生功德積累得越多,來世升入天道的機會就會更大。舍功德的目的:一是為了今生圓滿,順利達到彼岸世界;二是為了來世的積累。當地人說“鹵么來,歪么臘”,譯成漢語是“今生鹵,來世得”,鹵是“供”,歪是“藏、留著”的意思。今生供,來世這些東西將全部回到個人的頭上,來世生活便有了保障。他們認為,人獲得的功德,不僅在來世可以兌現,在今生也可以看見。當地人舉例,如果一個人生病了,去醫院看不好,打針吃藥都不好,但是請摩達看“來西達”,舉行搭橋、供飯團等儀式,反而就好了,這就是今生積累的功德起了作用。褚建芳說,“在人生禮儀和時令節慶儀式中所祈求的福佑和庇護并不是要等到來世才兌現,而是要在今生今世,甚至是當下兌現”[13]。M寨的傣族也是如此,在生存問題上,他們更注重的是現世,而不是來世。
和少英、魏茜提出,如果說“大供”做“擺”是將大量的功德寄存于神、佛之處并于來世悉數取出,那么“小供”功德約定俗成的求取方式則是將零碎的功德一點一滴積累于經龕之中,并通過生肖和名字對某段時間的運勢施加影響[14],M寨傣族人的命也由一點一滴積累的功德所定。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M寨的寨民們每家只能養一只報曉的公雞,還有犁田用的水牛和黃牛,其他牲畜一律不養。當地人認為,不殺生、不偷盜、不奸淫、不說謊、不酗酒,便可以獲得功德。所以,在M寨,活的動物是賣不出去的,如街子天的魚,殺死之后,才有可能賣出去。去奘房鹵鮮花、供奉水果,獲得神的庇佑,屬于外部傳入信仰,搭橋、供飯團,屬于當地民間信仰,當地人將兩者融合起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形成當地人特有的功德觀。而這種功德觀,在寨神崇拜中也得到了體現。以前祭祀寨神,各家有事,才去祭拜,現在,關門節、開門節,村干部、寨子里老人頭會商議祭祀寨神的時間,代表全寨的人祭祀寨神,告知寨神,并邀請寨神同寨子里的人一起進洼。佛祖崇拜和寨神崇拜兩者相互依存,共同構成了當地傣族的精神世界,共同形成當地的功德觀。
4 結語
寨神祭祀活動不僅是傣族的宇宙觀體現的載體,還承擔著濡化后代的任務,年輕的傣族后輩在祭祀儀式中潛移默化地接受著來自長輩的社會教育。祭祀寨神是全寨人的大事,關乎全寨人的生存、生活,對待寨神的態度,感受到傣族人們對祖先的崇拜及對靈魂的信仰。從祭祀寨神當中,可以了解傣族村寨的歷史,還可以了解現代化進程當中,有著雙重信仰的傣族村寨,如何在兩者之間達到平衡。在當地,外部傳入信仰與民間信仰形成了兩個對立的統一體,這兩種力量看似對立,無法和解,但實際上兩者被當地民眾接受,相互認同,形成了強有力的格式塔,共同維系著傣族村寨的運行。本文描述的祭寨神儀式只是德宏芒市眾多村寨中的一個村寨情況,但是,也可以從一個地方的祭祀寨神禮儀中窺探傣族永恒不變的寨神崇拜。祭祀寨神在全寨的心中屬于何種大事?寨神在寨民心中占有何種地位?怎樣在祭祀寨神當中看出整個社會對寨神的態度,歷史記憶如何在祭寨神當中得到體現?芒市傣族地區祭祀寨神中呈現的歷史記憶,如何促進族群的認同還需要在更廣泛的基礎上進一步調研,在觀察祭寨神儀式當中得到答案。
參考文獻
[1] 楊念群.歷史記憶之鑒[J].讀書,1997年,第11期.
[2] 王明珂.過去、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臺灣的族群經驗[C]//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臺北: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1994.
[3]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J].歷史研究,2001(5):136-147,191.
[4] 朱德普.傣族神靈崇拜覓蹤[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
[5] 金少萍.傣族原始宗教研究的一個視點──傣族女性與原始宗教[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0(3):70-76.
[6] 楊光遠.德宏傣族的佛教和原始宗教[J].云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1):72-76.
[7] 閆莉,莫國香.傣族寨神勐神祭祀的集體表象[J].廣西民族研究,2010(1):51-56.
[8] 何慶華.傣族祭寨神儀式空間的排他性[J].思想戰線,2019,45(4):78-85.
[9] 姚荷生.水擺夷風土記[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
[10]愛彌爾·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東,汲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11]祜巴勐.論傣族詩歌[M].巖溫扁,譯.昆明:中國民間文學出版社,1981.
[12]特納.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M].黃劍波,柳博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13]褚建芳.人神之間——云南芒市一個傣族村寨的儀式生活、經濟倫理與等級秩序[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14]和少英,魏茜.傣卯人功德觀探析[J].民族研究,2022(1):93-109,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