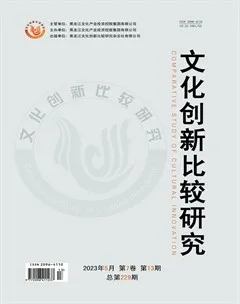文化記憶視角下拉祜族文化身份建構探析
馬行天 劉楚婷
摘要:拉祜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淀著拉祜族最久遠、最深層的精神追求。拉祜族文化記憶確立和鞏固了拉祜族的文化身份。著眼于云南在新時代下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的發展定位,拉祜族文化在建設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該研究運用文化記憶理論,以拉祜族的文化空間和記憶形象為切入口,對拉祜族代代相傳的集體知識進行分析,系統地解讀拉祜族文化身份內涵。在這一過程中,記憶形象成為拉祜族文化身份的建構基礎;通過活態傳承,拉祜族實現記憶重塑,結合時代條件對民族文化加以繼承與發揚,賦予其新的時代意義;作為文化記憶的首要組織形式,儀式存儲和激活民族記憶,增強主體性,促進民族文化的傳承和文化身份的建構。
關鍵詞:文化記憶;拉祜族;自我認同;主體性;歷史語境;民族認同
中圖分類號:C912.4?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文章編號:2096-4110(2023)05(a)-0098-05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Lahu Nati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ultural memory of Lahu nationality establishes and consolidates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Lahu nationality, accumulating the longest and deepest spiritual pursuit of Lahu people.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positioning of Yunnan's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Demonstration Zone in the new era, Lahu cultur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building a demonstration area of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This study elaborates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taking the cultural space and memory images of the Lahu nationality as the entry point, analyzes the collective knowledge of the Lahu nationality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s the connotation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In this process, the memory images become the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ahu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living inheritance, the Lahu people realize the memory remodeling,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ethnic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times, endowing it with new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As the primary organizational form of cultural memory, rituals store and activate ethnic memory, enhance subjectivity, and promot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ultural memory; Lahu nationality; Self-identification; Subjectivity; Historical context; National identity
文化記憶是一個民族的基因,其核心是記憶,它既可以被理解為一個過程,即記憶及記憶傳承、保存和延續的過程;又可以被理解為一個結果,即被篩選、被揭示、被重新發現和重新建構之后的結果。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延綿數千年的群體,在文化上呈現出多元性,各民族成員借助文化記憶,通過保存和傳遞集體知識,充分挖掘歷史傳統文化的精髓,確保相關群體的精神維系和文化認同,以建構他們的文化身份。
“文化記憶”是德國的揚·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婦在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體記憶”概念基礎上提出的。文化記憶包含了每個時代、每個社會反復出現的文本、圖像和儀式等內容,有助于相關人群確立和穩定自我形象。基于此,該集體的成員們意識到共性和與眾不同之處。“記憶形象”這一概念描述了文化記憶的過程[1]。阿斯曼夫婦認為,記憶形象在文化記憶中起媒介作用,人們通過回憶對“記憶形象”進行傳喚和激活。借助文化記憶,屬于同一個集體的成員確立和鞏固其集體身份,能夠在事關集體命運的大事上意見一致,并且能夠采取統一的行動[2]。近年來,文化記憶研究在后現代理論的語境中興起,拓展到文學、民族學、宗教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多個學科領域,逐漸呈現出跨學科和多元化發展的態勢。
主體性與身份認同的概念聯系緊密。人在生活中難免受制于其所置身的社會,從而界定群我關系,使自身有了主體性。在社會接觸過程中,自我對自己的認識形成自我認同,他人對自我的認識形成社會認同。文化身份與文化認同息息相關,因相同或相似文化而形成的群體,擁有著相同的群體身份,故群體中的人會對文化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并建構起屬于自己的文化身份。換言之,文化身份是人們在一個共同體中長期生活而形成的,對該群體文化精神的肯定性認識,它集中體現為對該群體核心價值的認同,是提升其凝聚力和創造力的精神力量。文化認同理論最初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由美國著名的精神分析家埃克里松(Erik H Erikson)提出,后被其他學者廣泛運用于社會、歷史、政治、文化等領域的研究。國內文化身份建構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主要涉及國際關系的文化認同研究、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或族群的身份認同研究、世界不同種族的文化認同研究等方面。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各民族之間通過交流不斷融合與發展,對少數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構問題的討論也逐漸增加。
拉祜族源于古代羌人族系,屬跨境民族,分布于中國的云南省和緬甸、老撾、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山區。拉祜族是沒有文字的民族,對其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是探究其文化身份建構的主要途徑。在文化探究方面,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赴云南拉祜族山寨進行田野考察,圍繞拉祜族的文學、歌舞、節日、儀式、隨身納物、圖騰藝術、社會機制等開展了多樣化的關于拉祜族社會文化的研究。在文化認同方面,學者們通過分析拉祜族有象征意義的符號和行為,探究民族文化對民族認同的作用及在文化傳承、功能教育等方面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各民族文化日趨頻繁的交流與融合,拉祜族文化正在不斷地進行記憶與重塑。在這一過程中,文化記憶將“已逝”的過去與“活著”的現在聯系起來,不僅起到保留信息的作用,更成為一種塑造文化身份的精神力量。
1 記憶形象:拉祜族文化身份的建構基礎
文化記憶理論為拉祜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提供了多元化的研究視角,較為清晰地展示了拉祜族如何通過記憶形象建構文化身份。在文化記憶理論視野下,集體記憶保存在由個體聚集而成的聚合體之中,同時,個體也從這個聚合體中汲取能量。個體只有將自己置于集體記憶的范疇之下才能進行記憶與身份認同。哈布瓦赫認為,集體記憶并不是個體記憶的機械相加,而是用一些工具重建關于群體過去的種種意象,而這些意象則是群體在每個時代的主要思想的折射與呈現。拉祜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其先民隨古代羌人族系遷徙,早期輾轉于中國西北地區的黃土高原、青海湖地帶,后沿橫斷山南下,分路跋涉于云南西北部,并逐漸生存在今天的瀾滄江、元江、紅河下游兩岸的山林地帶。走得最遠的拉祜族已跨越國界,遷移到中南半島諸國。在遷移過程中,拉祜人不斷回憶象征著本民族的種種意象,想方設法為本民族創造一個“記憶之所”。這一空間為本民族成員間的各種交流提供信息與線索,成為其身份認同的象征和身份構建的生成土壤。
回憶扎根于“被喚醒的空間”,存在于被經歷的時間,這些“記憶之所”,充當了回憶的時間或空間框架,即使它們不在場,也會被當成“記憶形象”,在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中存儲并重現。“記憶形象”不僅包括圖像性的文化符號,也包括敘事性的形式,比如神話、諺語、經文、繪畫,甚至一條街道、一座建筑等,都是“記憶形象”的載體[3]。拉祜族擁有諸多獨特的“記憶形象”,這些“記憶形象”并不是抽象的載體,而是一些文化符號,如葫蘆、狗牙、火塘、民族服飾等,在文化記憶中起媒介作用。通過回憶,拉祜人對“記憶形象”進行傳喚和激活。
1.1 葫蘆、狗牙
拉祜族自認為是吃著狗奶長大、從葫蘆里走出來的狩獵民族,葫蘆和狗牙也因此成為拉祜人最親密的伙伴和最久遠的文化記憶之一。拉祜人的日常生活離不開葫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生活所在區物資匱乏,拉祜族沒有原料和工藝制作金屬的鍋碗瓢盆,他們便把葫蘆做成各種形狀的廚具,滿足生活需求。千百年來,葫蘆不僅成為上好的食材和藥材,也被拉祜人制成各種實用的生活工具和美觀的工藝品。此外,拉祜人還用葫蘆做成樂器葫蘆笙,將其視作自己民族身份的象征。拉祜族的古歌《年歌》中唱道:“金竹葫蘆做蘆笙,吹出拉祜人的心聲。”拉祜人認為,不能吹蘆笙與唱歌,在社會上就孤寂寡歡,缺乏戀愛求偶的可能性[4]。因此,于拉祜族而言,葫蘆象征著吉祥及無限的可能性。現如今,拉祜族民居墻上各式各樣的葫蘆形狀的裝飾亦是拉祜族的記憶形象,它早已不僅是一種植物,而是一種拉祜族的民族圖騰和特有的文化符號。狗牙在拉祜族村落中也很常見,除了用于房屋裝飾,拉祜人還會將狗牙穿上紅線,佩戴在手上或者脖子上,有辟邪之意。
在回憶被喚醒的空間里,葫蘆和狗牙充當“記憶形象”,在村落中頻繁重現,是拉祜族生存繁衍的精神母體,代表拉祜族對遠古先民及其精神的念想,時刻提醒著拉祜人要懷揣向太陽奔去的精神和對幸福生活的無限希望。在拉祜族人眼中,只要彼此都信仰同一圖騰,那么他們就擁有集體記憶,就把彼此視為親屬。圖騰就像黏合劑,使更多的族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定的族群。因此,拉祜人對于圖騰的文化記憶強化了族群內部的緊密聯系,鞏固了氏族團體,構建起特有的身份認同,促進民族團結。
1.2 火塘、民族服飾
拉祜族家家都有一個火塘,是家居生活的中心,亦是族人文化認同的核心。火塘是拉祜族作為高寒山區甘青高原羌人后裔的一大文化昭示,一般設在前房中央,兩側放置床鋪供父母等長輩用。火塘正中架有鐵三腳架,用以煮飯。拉祜族火塘里的火是常年不熄的,象征著家族興旺昌盛,幸福永駐。即使晚上睡覺不用火時,也要將火炭聚攏,用火灰將其輕輕覆蓋,使之低氧慢燃。待到清晨起來時,慢慢扒出紅紅的火炭,用干草引燃加柴塊續火。在火花的爆裂聲中,拉祜人開始新一天忙碌的生活。傍晚歸來,一家人圍坐在火塘邊,邊感受火的暖意邊談論家族事宜。可以說,火塘見證了拉祜族人家的婚喪嫁娶、建房修屋、安排農作等家政大事,是族群勞作生活的“集散地”。此外,拉祜族服飾承載著拉祜民族祖先遷徙、生產、生活、節慶、審美觀、價值觀等歷史文化,也是拉祜族文化身份建構的基礎。拉祜人無論上山、下田做活、趕集,還是跳舞,都背著織有各種圖畫的彩色織錦挎包。挎包是拉祜族在遠古時期傳承下來的服飾。挎包上的白色象征狗牙齒和山峰、紅色象征太陽、藍色象征天空、綠色象征森林,線條象征河流,太陽花及各種花草符號象征人們對厄莎和自然的崇拜,戀愛花和兄妹花象征著民族生存繁衍和團結發展。拉祜人之所以會將這些“記憶形象”背在身上,是因為他們的先輩懷念以前生活的高山草原,便越過千山萬水將這份想念帶到現在居住的地方,也預示著將民族的精神和福氣背在身上,成為其文化身份的又一種體現。每個拉祜族婦女都會紡織手工包,紡織包上的圖騰及紡織技術即是拉祜族人連接過去與現在的紐帶,拉祜人在呼喚“過去”中尋找其現實社會意義。
記憶的核心問題是重現,是表征,是語言和實在之間的邏輯聯系和審美聯系。這些聯系只有通過符號才會發生[5]。“記憶形象”便是符號,拉祜人通過自覺再現“記憶形象”,實現民族文化在社會層面的“第二次誕生”,成為可供認知、交流和建構的文化現象。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增強主體性,凸顯群我關系,形成穩定而又持久的群體認同。
2 活態傳承對拉祜族文化展開記憶重塑
根據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在時間維度上,社會的自我形象與社會回憶之間的關系,即歷史意識問題,社會需要“過去”,是因為社會要借“過去”來進行自我定義。通過在當下的社會框架中建構過去,個體和集體完成記憶這一行為。記憶不僅可以借助“過去”喚起被遺忘的深層記憶、潛意識的知覺,同時還可以在不斷重現的歷史意識中重塑本民族的文化框架,以達到構建文化身份的目的。
2.1 《牡帕密帕》承載文化記憶
在拉祜族文化中,創世史詩《牡帕密帕》凝聚了拉祜族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豐富內涵,融合數代拉祜人的“記憶形象”,秉承拉祜族的生活經驗和精神文化,在拉祜人追求民族認同的道路上具有無可比擬的作用。《牡帕密帕》是拉祜族的創世神話史詩,其主要內容包括:天神厄莎創造天地萬物,引導拉祜族繁衍壯大,遷徙南下,尋找安居之地等。吟唱《牡帕密帕》是拉祜族村寨社區生活的重要內容,在春節、拉祜年“擴”和新米節及舉行婚禮時,拉祜人總要吟唱《牡帕密帕》,載歌載舞,以增加節日氣氛,感激創世之神厄莎的恩典。當代埃及作家穆罕穆德·侯賽因·海卡爾曾說過:“只有使過去復活,一個民族才能活。”[6]吟唱《牡帕密帕》的氛圍被建構成一個通過記憶來塑造并強調民族文化身份的特殊“記憶之所”,拉祜族的“過去”在吟唱中經過時間的篩選和考驗,最終重現為拉祜人的文化記憶,濃縮了拉祜人對宇宙萬物的原初解讀、拉祜先輩的生產生活經驗及民族的價值觀念,從而起到鞏固族群成員集體性身份的重要作用。
2.2 音樂和舞蹈重現文化記憶
文化記憶維系著集體的文化認同,現實的交往需要文化記憶保持鮮活狀態。為了保證民族文化的“延續性”和“真實性”,拉祜族運用活態傳承儲存并重現文化記憶。拉祜族的音樂和舞蹈便是其文化記憶重現的重要形式。拉祜人利用蘆笙相伴的歌聲和舞步創設群體成員間各種交流的線索,促使群體成員在特殊的記憶場中強化身份認同,反復確認自己即是集體中的一員,從而使文化身份得以建構并延續。拉祜民間舞蹈歷史悠久,具有濃郁的民族性和廣泛的群眾性。其中,流傳最廣的便是蘆笙舞。蘆笙舞以蘆笙為伴奏,集拉祜族宗教、禮儀、娛樂、藝術為一體,用腳部和腿部動作模仿人們日常勞作生活。過拉祜年時,各村寨舉行規模壯觀的蘆笙舞會,融傳統的拜祭厄莎、新年祈福和群眾性狂歡活動為一體,層層圍圈起舞,蘆笙吹響,歡樂聲不斷。拉祜人對蘆笙舞的重現不僅是對過去文化的簡單回憶和“復刻”,也是吸取當下的時代特色和外來音樂元素的一種文化重塑。在瀾滄縣酒井鄉老達保村,就出現了以西洋樂器為伴奏樂器的多聲部合唱。拉祜人借吉他及和聲演唱方式改編出許多歌曲,其中,《快樂拉祜》《狩獵歌》《實在舍不得》等廣為流傳。老達保村也成為吸引大批游客觀光的音樂小鎮。從這一角度看,文化記憶以洋為中用的方式實現了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也真正實現了拉祜文化記憶在“與時俱進”中的“活態傳承”。
在文化記憶的傳承中,新一代拉祜人通過活態傳承的媒介空間還原記憶場景,加入現代元素,透過自己的身體感知文化記憶,在無形中建構了民族身份,豐富了文化認同的內涵,進一步提升了民族自信心。
3 儀式動力推動拉祜文化的延續與重構
文化記憶借助受過專門訓練的人員,如祭司、吟游詩人來完成,通過固定和經常性的集體活動得以存在和延續,如儀式、紀念活動、節日慶典等[7]。儀式作為一種文化記憶術,在文化傳承中承擔著存儲、激活和傳達民族記憶的功能[8]。拉祜族的儀式重現于拉祜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民族重大節日的慶典儀式到祭告厄莎的祈福儀式,從全民娛神的祭祀儀式到尋常百姓家的歌舞儀式,無不體現拉祜族人借助儀式建造動態空間,傳遞民族記憶,促進文化傳承的延續與演變。
3.1 傳統歲時節日
拉祜族傳統歲時節日都與原始的宗教儀式有關,如“擴”、新米節、火把節等。以“擴”為例,由于拉祜族沒有文字,族群居住地較為分散,拉祜族過“擴”的時間在古時候無法統一在某一天,現在大多參照農歷的春節進行。“擴”的第一天(初一)清晨,拉祜男女青年點起火把,背起竹筒、葫蘆到水源地搶象征吉祥的新水,將新水送給村里最年長的老人,老人則給予舂好的粑粑,并為年輕人拴上福線,祝年輕人幸福吉祥。伴著晨光,男女老少在村寨頭人(拉祜村寨實行頭人制度,頭人主持紅白事等重大祭祀活動)的帶領下到“塔國”(每個村寨固定迎年神的地點)迎接年神,他們把糯米粑粑和象征吉祥的“朱結”放置于神樁之下,燃起香燭,圍著神樁跳蘆笙舞,進行莊重的祭祀儀式。每逢“擴”,拉祜族還會舉行陀螺比賽。陀螺象征著技藝與智慧,陀螺比賽的優勝者將得到全村人的贊賞。
3.2 祭祀活動
拉祜人通過親身參與直接的、現場的儀式,感受文化記憶的熏陶。節日演示了與祖先的關系及對死亡和重生的基本看法[9]。伴隨著節日進行的儀式不僅是一種活動,還是連接“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一種媒介,這一媒介發揮了繼承文化的巨大潛能。除了節日儀式,拉祜族的祭祀活動也在“重復”和“現實化”的過程中激活民族記憶。以辦白事為例,拉祜人有白事不殺生、不下地做農活的傳統。當村寨中有人去世,村民們便會停止做農活,到那家幫忙處理后事。拉祜族的喪葬是土葬,無需火化,逝者入木棺,眾人抬著棺材去選墓地。關于選墓地,拉祜族有自己獨特的方法,即抬棺人一路將土雞蛋扔在地上,雞蛋破碎在哪兒,就說明逝者想長眠于哪兒,若是雞蛋不碎,就說明逝者不愿葬在那里。拉祜族沒有穿孝服的習俗,喪葬的祭祀儀式圍繞著為后人祈福展開。儀式的真正價值在于其中隱含的象征意義和人們內心的狀態[10]。儀式中,拉祜人所使用的每一件物品、做出的每一個手勢、唱的每一首歌或存在的每一個空間單位,在文化記憶中都代表著除了本身之外的另一件事情,蘊含著比表層更深的含義,時刻強調以血緣關系締結的家庭觀念,建構血濃于水的族群關系網。
記憶通過重現的儀式解讀和重塑著過去,組織當下和未來的經驗。儀式是“文化記憶的首要組織形式”,儀式對于任何一種文化的意義,遠遠超出我們的認識。與文本相輔相成,儀式在很大程度上具備了超越文本的巨大潛能[11]。儀式存儲拉祜族的節日慶典文化、紀念活動文化、祭祀文化及歌舞文化,是對于拉祜族傳統精神和未來暢想相協調的文化進行選擇、強調或扶持的結果,目的是強化儀式參與者對本民族集體的認同。文化記憶具有很強的可塑性,它并非借助基因繼承,而是通過文化重現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在拉祜族的重大紀念活動及儀式中,新一代拉祜年輕人在老一代拉祜人的帶領下,通過親身參與的形式,感受傳統文化的熏陶,不斷強化“我們”這一民族與其他民族不同的意識,凸顯“我們”的共同屬性,確立拉祜族的主體性,構建身份認同。
4 結語
總之,文化記憶理論為探討拉祜族文化身份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撐和研究視角。拉祜族文化記憶呈現“群體關系”,其主要功能是為身份“定位”。通過保存代代相傳的集體知識,拉祜族確證民族文化的連續性,從而建構起文化身份。在這一過程中,記憶形象跨越代際的界限以文化符號和標志的形式穩定保存,使后代不需要借助個人經驗和個人記憶就可以進入共同的回憶,是拉祜族文化身份建構的基礎;通過活態傳承,拉祜族人實現記憶重塑,結合時代條件對民族文化繼承與發揚,賦予其新的時代意義;儀式存儲和激活民族記憶,在時間和空間方面為拉祜人提供一種整體意識和歷史意識,強化參與者對本民族集體的身份認同。在當今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形勢下,拉祜族文化記憶彰顯拉祜族獨特的文化身份,是推動民族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動力引擎。因此,在建設云南“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的過程中,重新審視拉祜族文化記憶的現實價值,探索拉祜族文化身份建構與延續的實踐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 金壽福.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J].外國語文,2017,33(2):36-40.
[2] ASSMANN J. Kollecktives Gedachtnis und kulturelle Identitat[G]//ASSMANN J,? HOLSCHERo T. Kultur und Gedachtni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8:30.
[3] 王蜜.文化記憶:興起邏輯、基本維度和媒介制約[J].國外理論動態,2016(6):12.
[4] 劉勁榮,張錦鵬. 瀾滄笙歌[M].上海: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 2017:94.
[5] 趙靜蓉.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M].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6] (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M]. 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7] ASSMANN A.Zwischen Geschichte und Gedachtnis[G].Stuttgart:Verlag,1999:22.
[8] 呂進,何佳佳.傳承與重塑:文化記憶視角下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探析[J/OL].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1[2023-05-05].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 1023.C.20210920.0906.002.html.
[9] 阿斯特莉特·埃爾,馮亞琳.文化記憶理論讀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38.
[10]邱莉芳,潘磊.民族認同在儀式中的凸顯與強化——以云南拉祜族“花節”儀式為例[J].云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5(4):20-24.
[11]王霄冰.文化記憶、傳統創新與節日遺產保護[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21(1): 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