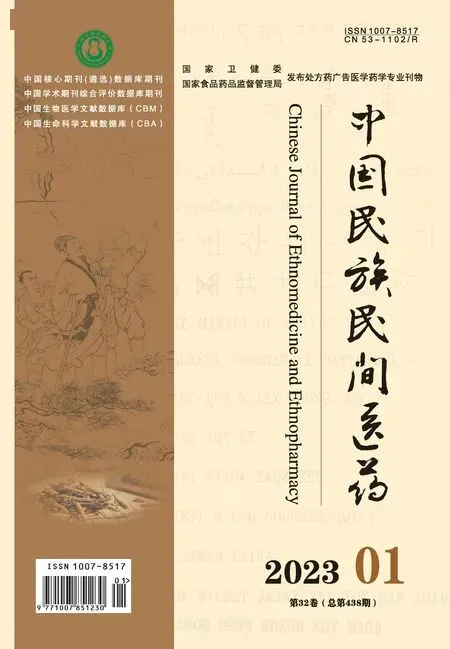中醫辨證論治緊張型頭痛研究進展
王子楊 徐舒暢
1.河北北方學院,河北 張家口 075000; 2.秦皇島市中醫醫院,河北 秦皇島 066000
緊張型頭痛(tension-type headache,TTH)亦稱作“肌收縮性頭痛”,是原發性頭痛中最常見的類型[1],典型臨床表現為額部、頂部、枕部、顳側中的單個或多個部位,甚至整個頭部的持續性輕、中度鈍痛,常伴有緊箍感、沉重感、壓迫感等異常感覺。一般認為,TTH的發生可能與肌筋膜結構改變、炎性因子釋放增多、神經遞質釋放異常、應激反應、抑郁情緒等因素有關[2-3]。目前,針對TTH的治療常選用非甾體抗炎藥、肌肉松弛劑、三環類抗抑郁藥等藥物,但存在頭痛容易反復、難以根治、藥物不良反應較大等問題。隨著社會壓力的普遍增大,TTH患者不斷增多,中醫藥療法和針灸、推拿療法安全可靠,在TTH的治療中發揮著越來越多的作用。
TTH屬中醫“頭痛”范疇,歷代醫家對此病均有獨到見解。本文以“緊張型頭痛”“中醫”“辨證”“論治”為檢索關鍵詞,檢索了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等數據庫中公開發表的文獻,排除重復文獻及數據真實性存疑的文獻,從而分析總結近5年來TTH的中醫辨證論治研究進展,現試述如下。
1 六經辨證
傷寒六經俱有頭痛[4],《傷寒論》中已有對太陽證、陽明證、少陽證及厥陰證相關頭痛的論述。李東垣在此基礎上補充了少陰頭痛與太陰頭痛,形成了較為完善的頭痛六經辨治體系。朱震亨進一步總結了六經頭痛的引經藥物,對后世醫家選方遣藥影響深遠,如“六經兼治”“三陽并治”之九味羌活湯,至今仍為治療各型頭痛的常用基礎方劑之一。
馬良等[5]通過對150例TTH病例的判定與分析,發現在150例患者中,按照發生頻率分別為少陽太陰合并證(30.0%)、少陽太陽合并證(21.3%)、少陽陽明合并證(20.7%)、少陽證(18%)、陽明太陰合并證(5.3%)、少陽少陰合并證(1.3%)、太陽證(1.3%)、陽明少陽太陰合并證(0.7%)、太陽少陽太陰合并證(0.7%)、太陰證(0.7%)。并進一步指出少陽證及其合并證是TTH最常見的六經證型,故臨證時,當重視和解少陽法的應用,同時兼顧其它證型,靈活選擇藥物。
2 臟腑辨證
2.1 從肝論治 賈孟輝等[6]認為,怒氣沖肝,肝氣郁滯是TTH發生的關鍵,郁久化火,肝火上擾輕竅,是實證TTH的核心病理環節,治療當在疏肝解郁基礎上辨證論治,輔以清火、熄風、活血、祛痰等法。雷玉嬌等[7]認為,肝臟為TTH中醫辨證分型的核心,臨證之時當以肝為著手點,首辨虛實,次辨表里寒熱。并提出綜合選擇開郁理氣法、清肝瀉火法、滋水涵木法、平肝息風法、疏肝健脾法、疏肝養血法、疏肝柔筋法等方法治療TTH。裘昌林[8]認為,TTH的發生責之于肝脾腎三臟,而病機之關鍵在肝。特別是肝陰肝血之不足、肝風肝陽之上亢、肝體之失柔、肝氣郁久而化火等肝系異常情況是TTH的重要發病因素,同時,裘昌林強調在TTH的中醫治療中,疏肝之時當結合柔肝,常用平和輕靈之梅花、玫瑰花、佛手等藥物,并配合歸、芍等滋陰養血之品,以防柴胡、香附等香燥藥物疏泄過度。此外,重視平肝、清肝法的應用,常將梔子、桑葉、菊花等清肝藥與元胡、石決明、牡蠣等平肝藥同用,并加入滋補腎水之品,以防擾動相火,往往可取得較好的遠期效果。
陳艷等[9]通過綜合分析1992年至2017年中醫藥治療TTH相關文獻中常用藥物的歸經情況,發現歸入肝經的藥物在所有藥物中出現頻次最高,約占24.36%,可見由肝論治為近年來中醫藥治療TTH的最常用思路之一。一項針對TTH常用中藥的Meta分析[10]指出,出現次數最多的10個藥物為白芍(7.1%)、川芎(6.5%)、當歸(5.8%)、柴胡(5.2%)、甘草(5.2%)、白芷(4.5%)、天麻(3.9%)、鉤藤(3.2%)、全蝎(3.2%)、細辛(3.2%),其中柴胡-白芍和白芷-川芎是出現頻次最高的2個藥對,并總結出平肝熄風法和火郁發之法是近年來治療TTH的常見治法。
2.2 從心論治 心為五臟六腑之大主而主神明,若心血不足,則無法上養清竅;心氣不足,可使血行推動無力,血瘀而痛,心陽不足,血液無以溫煦,以致頭面清陽不升;心陰不足,營血無以化生,陰血凝滯于脈內,故攣急疼痛。李曉剛等[11]以寧心安神養血為治法,應用歸脾湯加減治療TTH患者35例,總有效率為85.7%,有效改善了患者頭痛癥狀及睡眠質量。
2.3 從脾胃論治 脾胃為后本之本,五臟氣血生化源泉,且脾胃居于中焦而為氣機升降之樞紐。脾胃運化無力及升降之紊亂,可致清陽不升,氣機不暢,腦絡拙急。現代人思慮過多,嗜食肥甘的生活習慣進一步損傷脾胃,氣結于中焦,聚濕生痰,日久則擾于神明之府。姜振遠等[12]認為脾胃因素是TTH發生的根源,并分析臨床常用于治療TTH的桂枝湯、葛根黃芩黃連湯、半夏白術天麻湯、歸脾湯、補中益氣丸、升陽益胃湯等古方中,均寓有調和脾胃之意,可見從脾胃論治TTH的依據充分。宋琪等[13]以調理脾胃中焦氣機為治法,以清震湯為基礎方治療慢性TTH,獲得了良好的遠期療效。王懿娜等[14]以健脾和胃,降濁升清為著入點,運用“老十針”療法,以中脘、足三里為主穴,內關、上脘、下脘、天樞、氣海為配穴,治療慢性TTH患者29例,總有效率達93.1%,為TTH的針刺治療提供了新思路。
2.4 從腎論治 腎藏精主骨生髓,通于腦絡。先天不足,勞倦久立,脾腎不調,水火不交等因素均可導致腎精、腎氣的不足,久而致腦絡空虛,不榮則痛。黃巧藝等[15]認為補腎達肝法是TTH的重要治法,應用《輔行決臟腑用藥法要》中大補腎湯治療腎精虧虛型TTH患者34例,總有效率為94.12%,明顯改善了患者頭痛程度,減少了頭痛持續時間和發作次數。商燕等[16]依據“從腎治腦,腎腦同治”理論,應用自擬腎腦復元湯(熟地、黃芪、山藥、山萸肉、紅景天、丹皮、赤芍、當歸、地龍)治療老年TTH患者36例,總有效率為94.45%,高于常規治療組77.78%,且此法可改善后循環血流。
3 六淫辨證
3.1 風邪 風邪為百病之長,善行數變,易襲于頭面清竅,同時,風邪常挾雜他邪共同致病,是TTH發生的重要因素,風去則其它諸邪無所依附,浦家祚多用羌活、荊芥、防風、葛根、白芷等祛風藥治療,并根據所挾之邪種類,配伍散寒、潤燥、除濕藥物,清散風邪及其后所挾之邪,以頭目清利為期[17]。
3.2 寒邪 寒性收引,TTH患者多有頭部分緊箍感、壓迫感,與寒邪關系密切。舒慧敏[18]通過一項對344例TTH患者的橫斷面調查研究發現,天氣變化是TTH的重要觸發因素之一,在344例患者中,有116例因天氣變化而誘發,其中50例因“吹風”而誘發,39例因“遇冷”而誘發,證明風寒之邪侵犯頭面是誘使TTH發作的重要病機。張立平等[19]以發散風寒為治法,應用葛根湯治療頻發型TTH患者40例,發現該方案可有效改善患者頭痛癥狀,并在不同程度上減輕了患者失眠、頭暈、心悸、出汗、焦慮等伴隨癥狀。
此外,暑熱之邪、濕邪等外感邪氣亦為TTH的致病因素。患者體質不同導致機體對自然界六淫邪氣耐受程度不同,若衛氣虛弱,腠理不固,則稍有風雨寒暑之變則致外邪乘虛而入,誘使THH發生。過偉峰[20]治療實證TTH時,除應用祛風、散寒、解表類藥物外,常加入黃芪、白術等扶正固表之品以扶助正氣,增強機體對天氣變化和異常氣候的耐受程度。
4 七情辨證
TTH的發生,與社會心理因素關系密切,中醫辨治TTH強調身心同治,重視對患者不良情緒的干預。
4.1 思 思則氣結,日久則易于化火化熱,思慮過度損傷脾胃,影響清陽之上升,則發頭痛。王婉喻等[21]通過系統脈學分析,指出存在“思慮過度狀態”的TTH患者寸口脈多表現為“思”動,來緩而去疾,脈內曲、細、斂、直,并認為治療當用半夏厚樸湯加減以理氣散結,解思除慮。
4.2 驚 突如其來的驚嚇、緊張等應激反應是TTH的觸發因素之一,驚恐型患者多有心悸、膽怯、易驚、不寐等臨床表現。脈象多表現為來疾而去疾,兼有動、數、駛、剛、斂、細之形[19],治療可用朱砂安神丸加龍骨、牡蠣等藥物以定驚安神。
4.3 怒 怒與肝臟風木之氣相應,為較劇烈的情緒反應,與THH關系密切。《證治準繩》言:“怒氣傷肝及肝氣不順,上沖于腦,令人頭痛。”指出“怒”在頭痛發病過程中的作用。因發怒而引發的TTH常表現為陣發性兩側頭痛。或伴有頭暈、頭部沉重、壓迫感等[6],治療當以平肝清火為法,同時注重對患者負面情緒的疏導。
5 氣血津液辨證
氣血津液同為機體內維持生理機能的基礎物質,氣、血、津液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一方面,氣血津液的虧虛可致腦絡失養,不容則痛;另一方面,氣血津液代謝的紊亂和關系的失調,特別是瘀血、痰濁等病理產物的產生可致腦絡受損,不通則痛。
5.1 不榮則痛 《濟生方》指出:“凡頭痛者,血氣俱虛。”頭面部五官清竅皆依賴于氣血津液等精微物質的濡養,氣虛則無力推動血行,血虛則不能榮養頭面,津液不足則難以濡潤周身百骸。特別是脾胃運化無力,氣血生化不足;或情志郁結日久化瘀,耗傷陰液,水不涵木,虛陽上擾,均可致TTH的發生。養血清腦,補中調氣[22]是TTH治療的重要步驟,應衛真等[23]運用中成藥養血清腦丸聯合西藥氟桂利嗪治療63例TTH患者,在提高總有效率、緩解頭痛癥狀、減少不良反應等方面發揮了較好效果。李曉剛等[11]應用氣血同治之歸脾湯治療合并有睡眠障礙的TTH,在緩解疼痛、提高睡眠質量、改善不良情緒等方面取得了較好效果。
5.2 不通則痛 氣血津液代謝的失常及各自間關系的失調,常可導致氣機郁滯,血行不暢,津液結聚,甚至產生瘀血、痰濁、水飲等病理產物,從而進一步阻礙氣機,影響血行津布,蒙蔽清竅,導致頭痛屢屢復發,纏綿難愈。其治療當以理氣活血,化痰通絡為關鍵[22]。王辛坤等[24]以痰濁論治TTH,選用半夏白術天麻湯配合艾灸治療TTH患者38例,總有效率為92.1%,優于氟桂利嗪對照組73.7%(P<0.05)。段金蓮等[25]應用柴芩溫膽湯治療頻發性TTH痰氣郁結患者31例,總有效率為96.3%,明顯高于阿米替林組71.0%(P<0.01)。劉雪亮等[26]應用自擬化瘀通絡湯(赤芍、黃芪、丹參、葛根、桃仁、當歸、羌活、白芷、乳香、沒藥、甘草)治療TTH患者30例,總有效率為100%。張智勇[27]以平肝活血通絡為治法,應用自制川芎舒竅顆粒(川芎、柴胡、元胡、葛根、白芷、天麻、鉤藤、蒿本、牛膝、白芍、丹參、龍膽、菊花)治療TTH,在減輕疼痛等方面取得了與尼莫地平相當的效果,且該方案可有效改善THH患者顱內動脈的平均血流速度。
6 經筋辨證
十二經筋是經絡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連接四肢骨骼肌筋,維持關節屈伸運動,保證機體運動功能的作用。六淫七情,瘀血、痰阻等因素均可使經筋肌肉拘攣、結聚,以致頭痛的發生。邵冰[28]認為,TTH以頭痛、顱周壓痛、結節、肌肉緊張、痙攣等為主要表現,屬中醫“經筋病”范疇,通過手法觸診顱周壓痛點可明確發現顱周肌筋膜中的疼痛觸發點。聶文斌等[29]通過對TTH患者進行顱周壓痛點觸診,發現觸痛結節主要分布在足太陽經經筋、手少陽經經筋及足少陽經經筋。于川[30]進一步根據主要疼痛部位分為前額、兩側、巔頂、后枕四個區域,并由此探討頭痛觸發點與經筋循行的關系,指出前額部TTH主要與足陽明、足太陽經筋相關,觸發點位于胸鎖乳突肌和枕額肌;兩側部TTH主要與足少陽、手少陽、手太陽經筋相關,觸發點位于頭半棘肌、枕下肌群、上斜方肌、胸鎖乳突肌和顳肌;巔頂部TTH主要與足太陽、足少陽經筋相關,觸發點位于胸鎖乳突肌胸骨部和頭夾肌;后枕部TTH主要與足太陽經筋相關,觸發點位于頭半棘肌、斜方肌及枕下肌群等肌束。
經筋病的針灸治療多采用“以痛為腧”的局部取穴及“經脈所過,主治所及”的遠端取穴相結合的方式,重視調節局部攣急之經筋及機體整體氣血運行狀態。聶文斌等[29]根據《靈樞·經筋》中“治在燔針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腧”的原則,提出用火針速刺速出法針刺患者的疼痛觸發點和筋結點,以取得散寒止痛,助氣行血之效。一項針對TTH火針治療的臨床研究[31]表明,相比于常規針刺治療,火針治療可取得更好的療效,特別是在治療早期,火針治療體現充分優勢,在減輕頭痛程度,提高患者生活質量等方面優于常規針刺組,可更快緩解頭痛癥狀。張琳等[32]應用毫刃針焠刺法治療TTH患者40例,通過毫刃針焠,依據筋膜走向行針刺、溫通、松解、復位等手法,總有效率為97.5%,可有效解除筋膜粘連,減輕疼痛,縮短疼痛持續時間。熊志堅等[33]結合經筋理論與現代筋膜相關理論應用骨膜壓揉術,選用頭頸部經筋及壓痛點進行揉壓、調整、松解等,同時配合針刀治療,起到改善血運,緩解痙攣,解除卡壓等作用,可緩解疼痛,縮短療程。
7 其它辨證方法
7.1 從督脈論治 督脈為陽脈之海,奇經八脈之一,既絡于腎臟,又絡于腦絡,可調節諸經之陽氣。孫辰等[34]認為,督脈與脊髓、腦髓均有密切聯系,故選用“通督調神法”針刺百會、神庭、啞門、風府、頸部夾脊穴、大椎等穴,有效改善了TTH患者等頭痛評分、頭痛指數、頭痛發作次數等指標。
7.2 從毒邪論治 “毒損腦絡”理論最早由王永炎院士于1997年提出,近年來不斷發展完善。一般認為“毒邪”與“六淫”同屬“邪氣”范疇,但與六淫有著明顯的不同,是一種相對獨立的特殊邪氣。凃晉文認為,慢性TTH的根本病因在于腦絡受損后絡脈阻澀不通而有邪毒內聚,其治療當重視解毒通竅,應用自擬清腦通絡湯(當歸、牛膝、川芎、細辛、白芷、全蝎)治療23例TTH,總有效率為95.65%,顯著高于阿米替林對照組82.61%(P<0.01),且遠期效果良好,可有效降低復發率[35]。
8 總結與展望
綜上,中醫藥辨證論治TTH理論基礎豐富,百家爭鳴,各有千秋。近年來,醫家多從太陽證、肝風、氣郁、風寒、怒、思、痰、瘀、虛及手足太陽經筋證等角度論治TTH,治療方案包括藥物治療、毫針治療、火針治療、推拿治療等,通常可取得解除筋膜粘連、較快緩解頭痛、延長疼痛間歇期,改善生活質量、減少不良反應等作用,療效確切,副作用少[14,17,29,34]。但筆者亦發現,目前公開發表的研究中,尚存在一些不足:①近年來研究多以經驗總結和臨床療效觀察為主,尚缺乏對中醫治療TTH相關機理的高質量研究;②對遠期療效及頭痛復發情況的關注不足;③多以患者癥狀改善程度為療效判定標準,缺乏統一的客觀標準;④多選用單一治療方法,對綜合治療方案(如中藥聯合針刺)療效的相關研究較少。
同時,筆者在臨床中發現TTH患者常伴有焦慮、抑郁等情緒,但近年來針對中醫療法改善TTH患者負面情緒的研究較少,提示在臨床施治和確立研究方案時,應當將“以疾病為中心”的治療思路轉換為“為病人為中心”,注意患者心理狀況的變化。目前,TTH的發病率仍處于上升趨勢,未來應開展更高水平的臨床研究,以期建立統一的辨證論治方案和公認的療效評定標準,在臨床實踐中更充分的發揮中醫綜合療法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