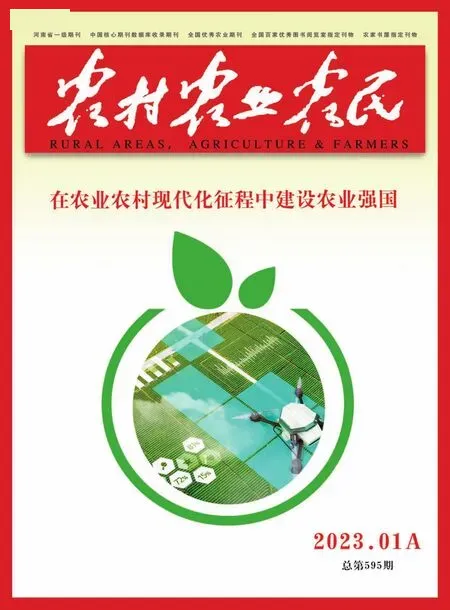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質量調查研究
——以河南省為例
劉 婭
(鄭州電力高等專科學校經濟管理學院)
一、文獻回顧
就業質量的內涵闡述。目前學者們主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對就業質量的概念進行界定。從宏觀角度看,就業質量是從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整體衡量勞動者就業情況包括生產率水平、就業與生產資料的關系等。從微觀角度看,就業質量更多的是指個體勞動者之間在就業收入、就業環境、就業權益等方面存在的差異。李軍峰(2003)認為,就業質量高低是就業者的就業穩定性、工作機會的獲取、職業安全、職業發展和職業聲望等多種因素的綜合考量。
就業質量的測量指標。收入水平是學者們早期使用頻率最多的指標(彭國勝,2008;謝勇,2009)。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何亦名等(2012)將測量指標細化為主觀和客觀兩個層次。錢芳等(2013)通過與就業相關的一級指標和二級指標經德爾菲法賦值后構建了就業質量指標體系。盡管學者們運用了不同指標體系和構建方法,但收入水平、工作時長、就業保障、合同簽訂以及就業滿意度等是他們都認同的就業質量測量指標。
農民工就業質量現狀。學者們對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農民工就業質量進行了研究。從歷史變遷來看,農民工整體就業質量不斷提高,國家對農民工就業幫扶政策起到了推動作用。從不同地區來看,東部地區農民工就業質量高于中西部地區農民工就業質量。韓東(2019)通過農民工與城鎮工的就業質量比較研究發現,農民工無論是收入、勞動保障還是職業發展水平都低于城鎮工。
以往研究界定了就業質量的概念,構建了就業質量測量指標體系,通過不同數據來源對農民工就業現狀進行了分析。然而,現有研究對中部地區農民工就業情況研究不足,缺乏對新生代農民工高質量就業困境的系統分析,特別是農民工數量龐大的河南省的區域性研究更顯匱乏。
二、調查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自“河南省農民工高質量就業困境分析與對策研究”項目發放的網絡問卷,通過“問卷星”進行在線調查,調查對象為目前為外出務工狀態的河南籍農民工,問卷內容主要圍繞農民工就業過程中的相關問題,包括個人基本情況、目前工作基本情況和以往就業經歷等。本研究抽取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作為研究樣本,共得到樣本312份,其中有效樣本296份。
(一)新生代農民工個體特征
性別。被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中,男性占比為60.87%,女性占比為39.13%。研究樣本男女比例與國家統計局2021年調查數據基本一致,說明了樣本采集的可靠性。同時,男女比例的變化說明了更多的女性參與到城市就業當中,這可能與當下農民工城市就業模式的改變有關,以往農民工多為男性,女性一般在家照顧家人,而如今多為舉家遷移。
年齡結構。被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中,“80后”農民工占比為43.3%,“90后”農民工占比為30.07%,“00后”農民工占比為26.73%。從年齡結構來看,“80后”農民工為主要勞動力來源。
教育水平。新生代農民工中高中(中專)學歷居多,占比為65.22%,大專學歷占比為13.04%,初中學歷占比為17.39%,小學學歷占比為4.35%。從以上數據可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普遍文化水平為高中(中專)水平,約5%的新生代農民工未完成義務教育。進一步查看學歷水平較低的新生代農民工出生日期后發現,學歷水平在初中以下的主要是“80后”和“90后”農民工。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水平隨著時代變遷而不斷提高。
婚姻狀況。被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中,未婚農民工占比為34.78%,已婚農民工占比為65.22%。從結果來看,外出農民工中多數為已婚狀態,這與農村人口結婚較早的風俗習慣有關,也說明了婚姻狀態對農民工外出決定的影響日益下降。
職業資格證書持有數量。被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中,持有1個及以上職業資格證書的農民工占比為43.48%,沒有任何職業資格證書的農民工占比為56.52%。雖然新生代農民工學歷水平不斷提升,但技能水平不足,缺乏專業能力培訓的意識和行動。
(二)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特征
合同簽訂。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占比為38.67%。簽訂合同的農民工就業持續時間長,勞動合同能夠保障農民工的收入權利、安全權利、健康權利,是對農民工就業最有利的保障,能夠提高農民工就業滿意度。被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中,只有1/3的農民工簽訂了勞動合同,這主要是由于許多農民工就職于私營企業,企業規模小、市場風險大、管理不健全,但工資較高。因此,農民工自愿放棄合同簽訂帶來的利益而主動選擇承擔風險。
收入水平。就業收入代表了是否獲得公平的報酬,是勞動者的價值體現。被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中,平均工資在3500~4500元的占比最高,為67.19%,農民工收入水平穩步提高能夠增強農民工群體城市就業的信心,有利于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但是,農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較高,還要贍養老人、撫養孩子。因此,其收入水平還不足以滿足家庭支出。
就業保障。就業保險是就業者的權益,包括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內容。被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中,表示企業為其購買工傷保險的占比為33.43%,表示不清楚企業是否為其購買工傷保險的占比為30.56%。根據以上數據可以發現,一方面,企業主動為員工購買非強制性保險意愿不夠強烈;另一方面,農民工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對自我享有的就業權利不清楚。
就業穩定性。根據以往研究,換工次數被用來衡量農民工就業穩定性程度。被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中,75.45%的農民工有過換工行為。其中,45.34%的農民工有過兩次以上的換工經歷。進一步分析發現,換工原因中,企業原因諸如企業倒閉、企業辭退等占比較小,而自身原因如自己不想干、工資太低、工作太累、干著沒意思等占比較大。
三、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困境分析
(一)就業能力不足,難以滿足產業發展需要
新生代農民工被定義為新型產業工人,是未來推動產業發展的主要參與人群。目前,我國產業發展呈現規模化、標準化、智能化特征,低端技術崗位將被取代,更多的是需要同時具備計算機能力和管理能力的產業工人。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雖具備基本的教育水平,但前沿能力欠缺,崗位中信息化能力應用不足。雖然產業發展已經進入新的階段,但是工人上崗能力和素質欠缺、止步不前。調查顯示,有一半以上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相應的職業資格證書,進而詢問持證農民工目前工作是否與職業資格證書相匹配時,60%以上的農民工表示不相關。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持證比例較低的同時“崗證不一致”進一步削弱了農民工取得職業資格證書的積極性。
(二)就業質量較低,穩定性不足
從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區間來看,基本與中部地區平均收入水平一致。進一步分析發現,新生代農民工超時工作占60%,也就是說,如果將月收入轉換成正常小時工資后再進行比較,新生代農民工月收入仍然低于城鎮人口。同時,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合同簽訂率不高,主要原因是部分農民工自身法律意識不夠強,“嫌麻煩”思想嚴重,甚至擔心簽合同可能會影響“跳槽”,也說明了企業對新生代農民工勞動保護不足,就業保障不夠完善。超60%的新生代農民工有過換工行為,約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有過兩次以上的就業經歷,說明了就業不穩定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典型特征。
(三)參與教育培訓的意愿不夠強烈
提高農民工人力資本的主要途徑包括培訓和教育。培訓的主體是企業,但從企業方來看,一方面,由于農民工的高流動性,使得企業不愿意承擔培訓費用,培訓動力不足,“脫嵌式雇傭關系”是大多數企業的主動選擇;另一方面,農民工一般從事的崗位技能水平較低,專用人力資本需求不足,更多需要的是通用人力資本,因此,企業不必要提供技能培訓。從農民工自身來說,培訓參與度不足的同時接受繼續教育的意愿也不夠強烈。根據調查,高學歷農民工接受繼續教育的意愿強烈,低學歷農民工則不強烈,但低學歷農民工才是繼續教育的重點人群。
四、解決思路
(一)進一步完善監督機制,加強法律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民工數量的不斷增加,我國制定了一系列關于農民工就業的政策,特別是針對農民工“討薪難”,國家還專門設立了農民工工資保障機構,為農民工開設工資發放專用賬戶。因此,近年來農民工工資發放已取得重大成效,農民工基本不再為拿不到工錢而發愁。但是,農民工就業過程中仍然存在監督不到位的問題。一些企業存在僥幸心理,利用法律法規中的空白和不清晰的區域,對農民工心理和身體造成了傷害。因此,需要根據農民工流動性強、收入水平低的情況,按照區域特點分類制定不同的管理辦法,加大對農民工保障的覆蓋力度,加強農民工在戶籍地和就業地保險關系的互通互用。要建立適合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目前已有關于農民工的保障包括基本醫療和養老,但城鎮人口所享有的生育、工傷、大病等保險還有所欠缺。同時,需要提高農民工參保率,增強農民工參保意識。
(二)多種形式開展農民工就業培訓,提升農民工就業能力
人力資本提升是解決農民工就業能力不足的有效方式。在過去10年間,我國開展了一系列農民工相關培訓項目,包括以扶持貧困戶為主的“雨露計劃”和以技能扶貧為主的“陽光工程”,這些培訓項目對我國農村地區貧困問題的解決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是我國取得脫貧攻堅勝利的重要支撐。然而,此類培訓項目覆蓋面有限,主要針對的是農村地區,不包括已經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因此,國家需要加強對已經在城市中就業的農民工的技能培訓,特別是不同區域應根據地方產業的不同,區別化開展就業技能培訓,強化培訓的針對性和專業性。此外,新生代農民工信息化能力較強,就業形式多樣,應根據其群體特點,充分利用新生代農民工傾向網絡學習方式的特點,發揮職業教育作用,利用網絡課程資源給新生代農民工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為滿足農民工創業需求,還應為其提供創業相關的培訓和學習內容。
(三)加快建立統一規范的就業市場,為農民工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由于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農民工長期處于次級勞動力市場,工資低、就業環境差,影響農民工就業滿意度。應盡快建立“同工同酬”勞動制度,避免由于戶籍制度帶來的就業歧視,從而促進農民工職業化發展。同時,農民工為城市中的外來人員,信息獲取渠道有限,應充分發揮勞務公司的作用,改變以往第一代農民工就業以親友介紹為主的方式,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更豐富的就業機會;發揮社區就業幫扶作用,加強農民工工作機會供給,強化社區就業幫扶功能,建立農民工個人信息檔案,發揮社區網格化管理優勢,及時收集企業用工需求,做好用工需求和供給的匹配。